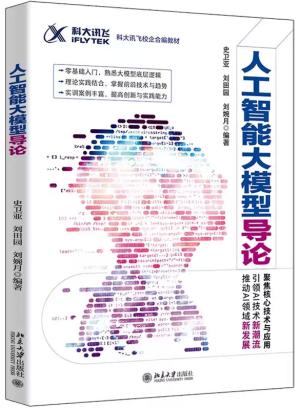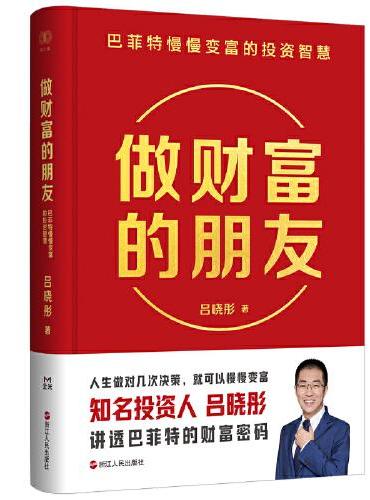新書推薦:

《
软体机器人技术
》
售價:NT$
454.0

《
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
》
售價:NT$
347.0

《
奴隶船:海上奴隶贸易400年
》
售價:NT$
352.0

《
纸上博物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诞生(破译古老文明的密码,法国伽利玛原版引进,150+资料图片)
》
售價:NT$
398.0

《
米塞斯的经济学课:讲座与演讲精选集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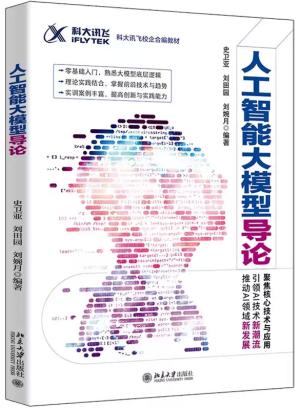
《
人工智能大模型导论 科大讯飞校企合编教材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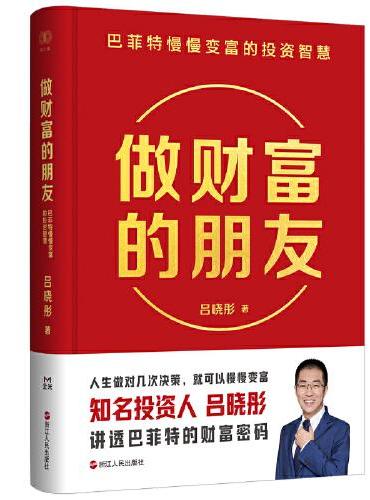
《
做财富的朋友:巴菲特慢慢变富的投资智慧
》
售價:NT$
383.0

《
一群数学家分蛋糕:提升逻辑力的100道谜题
》
售價:NT$
281.0
|
| 編輯推薦: |
简媜写作三十余年,珍藏版短篇小说集大陆首度面世(未删减)
在不惑之年,简媜决定出版一部短篇小说集,这也是她创作30余年来首部短篇小说集。在《十种寂寞》里珍藏着她漫漫人生路上瑰丽的碎片,是经过岁月淘洗的文字。
在被问道,为什么要出版一部短篇小说集,她打趣道:
小说家出散文集,而且(大)畅销,这、这、这不就是“侵门踏户”吗?我这个写散文的岂能坐视不管,好,揭竿起义,换我出小说去偷袭一下小说国!
对了,写作上,我的字典里确实有“安分”这个词,只不过前面插了一根晃来晃去的羽毛,叫“不”。
多说一句,活到看倦了人生的年纪,就像田里收成太盛,有时需要大篓子才装得下那些恩怨情仇。
在这本书里,她用深具体感温度的笔触,勾勒出了平凡人生中的寂寞浮世绘。
于她而言,寂寞不是一个可以被观看的姿态,也不是一个清晰的人物或是标准的场景,寂寞是在一个不相关的生活瞬间突然出现的裂缝,里面不断释放着一丝丝的凉意。
但峰回路转之间,这些看似寂寞的人,都在不经意的时刻,陪伴彼此走过了不平整的人生。
当时发生的事,需要很多年后才能得知全部的情节。悲伤、痛苦时
|
| 內容簡介: |
华语文坛大家简媜的全新短篇小说集,讲述十个关于寂寞的故事,每个故事彼此独立,但又互有关联。她用深具体感温度的寂寞书写,刨开掺甜放盐的人生;掘出男女老幼体内的那一枚寂寞种子。
细腻深刻的笔触,诚挚通透的情感,呈现出简媜对生命的思考、对人生的感悟、对理想与现实的审视、对故乡与亲情的眷恋与珍重。简媜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写尽平凡人生命中的喜怒哀乐。
——————
“周围的蓊郁人生太猖狂,收割了几个小人物故事,他们在各自的寂寞里载沉载浮,看似彼此不相涉,但终究在同一块风吹雨打的田地里。”
寂寞是被误解:一只猫头鹰不知何时飞来,十岁的阿金觉得只有这只猫头鹰知道他的委屈,特地飞来陪他。他对着猫头鹰哭,好像它是他的朋友。
寂寞是被遗弃:他忽然一惊:“天生傻也是父母给的啊,老爸老母给的要接受,那生下我们这样的小孩,老爸老母也接受吗?”
寂寞是被欺凌:她发誓:“明天,太阳下山的时候,我也要翻过这一页。”
寂寞是失败时:“待续”两个字带着强烈的暗示,留在世上的要替离去的人活下去,活得惊天动地,活到爱尽恨消。
寂寞是落空时:他看开也原谅,恶作剧的岁月曾经像一只野猫扑向他,留下花一般的泥巴印。
寂寞是抉择时:不满的是不够自由还是太自由?潘多拉的盒子打开,蹦出来的件东西叫作分享,而她不能忍受跟别人分享情爱。
……
我的主角们都有困境,但也都勇敢地奋战着,不逃避,而且具有本能式的自信,相信自己会是打胜仗的人。 ——简媜
|
| 關於作者: |
“身为作家只能葬在白纸黑字里,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江湖”
简媜,台湾大学中文系毕业,华语文坛无可争议的实力派女作家。著有《胭脂盆地》《旧情复燃》《梦游书》《天涯海角》《红婴仔》等。
下笔一贯摇曳恣纵,自成风格。其血色旺盛过人,却始终维持着一种从容的学院气息。
自悟:身为作家只能葬在白纸黑字里,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江湖。
齐邦媛称赞她才思丰沛、情韵优美,她的文字影响了一代人的表达,曾以高票被授予“青年爱作家”。
简媜是台湾中生代优异的散文作家之一,她才思丰沛,观察敏锐,在她笔下的台湾本土文化,缤纷多彩,自成一个情韵优美、人情馨暖的社会。
——齐邦媛
少年时代起就热爱她的作品,简媜老师给我的印象,可以用马一浮先生的那句话来描述: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 ——七堇年
文字医心。 ——朱丹
|
| 目錄:
|
001 猫头鹰出来的晚上
019 黑夜
047 一天一夜和第二天早晨
067 待续
107 弱水三千
147 花
175 回
219 老姐妹
243 三温暖
267 寂寞公寓的幸福纪事
315 后记
|
| 內容試閱:
|
猫头鹰出来的晚上
小灯泡不够亮,
仿佛一句听不清楚的梦话。
晚秋的夜已经深了,
露珠一颗颗凝结。
阿金满十岁一个月那晚,躲在一棵桑树上,一只猫头鹰陪他。
月亮出来了,从树叶间望去,像在哭。他咽了口水,猜想现在所有人应该都吃饱了,连猪也吃饱了,鸡鸭更不用讲——每天晚饭前,阿嬷一定叫他“去把鸡鸭饲一饲”,所以他家吃饭的顺序是:鸡鸭、小孩、猪、阿嬷阿母(这也不用讲)。
他不喜欢喂鸡鸭,尤其对那群四处闲逛的小鸭仔很生气,他得持竹竿口念:“鹅爸爸爸爸,鹅爸爸爸爸……”赶它们回后院才能喂。
有次,一只小鸭仔不听话,呱呱叫往别处跑,好像要找它老母。他发火,高举竹竿像武侠片那样挥下去,哪知就这么把它打昏了。阿嬷远远瞧见,小跑步抄田埂赶来急救那只鸭仔,无效,一把抢过竹竿替那只鸭仔报仇,一竿直接落在他肩头,好像那只死鸭才是她的长孙。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叫你饲鸡鸭这么不甘愿!”
他两手护着头、蹦蹦跳跳一溜烟逃了,好在只沾到一棍而已。他跑,阿嬷在后面追,校庆两百米赛跑的奖状就是靠平日祖孙长跑练出来的。阿嬷战败,一肚子气没出完,指天恨地骂他:“夭寿死囡仔,好胆不要给我回来,我没把你剥皮装粗糠,我就输你!”
这还用讲吗?不回去睡哪里?当然要回去啊。小时候闯祸听到阿嬷的狠话吓到哭,经验老到之后,他把这种状况当作“巡田水时间”,既然暂时不能回家,那就到处巡巡,反正外面天大地大没有栏杆。
他常巡的地方是几畦田之外的阿郎哥家,茂密的竹围里,跟他家一样是单户。阿郎哥到处当小工,他老爸早死了,与一弟一妹过活,很少见到他们的老母。阿郎哥的弟弟有点不灵光,讲话不清不楚,年纪虽然比阿金大,但傻傻的很好欺负。阿金不会主动欺负他,但也不敢讲有时候嫌他勾勾缠可能赏给他一个小拳头,说不定两个也是有可能的。
阿金喜欢在阿郎哥家晃,没有大人啰里啰唆赶他回家,晃来晃去就变成自己家。他勤快地帮忙挑水、顾灶火,帮阿郎哥管一管那个憨弟,好像他才是他的亲弟弟。这时候的阿金应该是天底下乖的小孩,他忍不住幻想:消息被晚风吹到校长耳中,不对不对,是校长正好骑车经过这里,看到瘦瘦小小的人影挑着两只水桶,从背影一眼看出是自己学校的学生,心中很不舍,停车一问,居然是帮没父没母的邻居挑水,当场拍拍他的头流下眼泪。第二天朝会唱完歌、升好旗,校长喊他上台,含着眼泪当着所有老师、学生的面,把他的善行讲一遍,表扬他好善乐施,是全校模范生,要大家向他学习,“啪啪啪”鼓掌声响起……不对不对,校长没有那么爱哭,不过,掌声“啪啪啪”应该是有的,而且停不下来。灶火也烧得“啪啪啪”,火光照着他的脸又热又红,露出一朵自我陶醉的微笑。负责炒菜的阿郎哥的妹妹骂他:“阿金仔,莫再添柴啦,你眼睛糊到蚬肉喔,没看见鼎内是空的吗?”
虽然阿郎哥邀他一起吃饭,但他从不在他家吃。一来,没时没准去别人家吃饭很失礼;二是豆腐乳、萝卜干、地瓜叶跟自家差不多,没什么好吃的,不如回家去吃,赶快把这些东西吃完——应该没那么容易,墙角整坛整瓮都是腌渍的酱瓜、豆腐乳——重要的是,估计阿嬷肚内那粒气球消了,天暗,鸟都知道归巢何况是聪明的小孩。他跑回后院,先在井边洗净手脸,鬼鬼祟祟地从后门进屋,直奔厨房饱餐一顿。一日恩仇到这时刻算是一笔勾销了。
第二天上学,无须大人交代,他拎着那只小鸭尸弯到大河边竹林浓密处放水流。“下辈子,做人莫做鸭!”他学大人念咒相送,看着小鸭尸随河水往下流,仿佛开开心心地要去投胎,经过一个漩涡转两圈沉下去了,像进去有神明居住的地方。既然来到河边,当然要放下书包玩一会儿:摘一两枝野姜花插在田埂上好像它们跑出去兜风,勘察树上有没有超级大只的天牛、金龟子可捉来跟同学炫耀或干脆脱掉制服下去摸几颗蚬仔。此时当然不能把蚬仔带去学校,离水会死,他把摸到的一把蚬仔埋在一处,再折树枝插在岸边做记号。布置好这个只有他与河知晓的秘密基地让他很得意,好像埋入的是载满稀世宝藏的沉船一般,他是大家都没想到的那个真正拥有权力与财富的人,为此,他当然必须更慎重地搬几块石头围住蚬仔,免得它们被水流冲散。这件小工程耗去不少时间,他感到太阳变热了,如梦初醒,匆匆整装跑去学校。真糟糕,正在唱歌,听到歌要立正不能动,可是不动的话怎么跑?他不管了,反正动也是打、不动也是打,早点到校早点打。老师的脸色不好看,表情像吃太多番石榴籽有点便秘,接着请出棍子叫他站好不要动。他很听话,主要是经验告诉他,此时不要动就是打三下结案,要是又动又躲,刺激老师的欲望——他发觉每个大人一大早都有打小孩的欲望——至少五六下才收棍,更重要的是,千万不可用手去护屁股,不然棍子打在手背上更痛。屁股肉多本来就是用来被打的,这种人体设计他从小就发现,而且知道当棍子快要落下时,快速把屁股肉绷紧再往前微缩一下下,好像跳土风舞要跟舞伴配合,那就根本不会痛,不过时间要抓得刚刚好,他靠多次练习已经很熟练,心里很得意。三下打完,他向老师一鞠躬说:“谢谢老师。”笑嘻嘻地回座位,他一向很有礼貌。
他很习惯这种三餐饭前饭后加上睡前都可能看到棍子倩影的生活,这是小男生的童年标准配备,大家都这样,无须抱怨。他跟厝边隔壁一起长大的男孩们有个默契,到校不提在家被打,回家也不提在校被揍,谁敢违反江湖规矩(例如有一次,有人说溜嘴:“阿婶,你家阿金今天被两个老师打。”),寻得适当时机,苦主是可以把“抓耙仔”(间谍)打一顿的。这,也算是小男孩世界里微薄的福利吧。
他又咽口口水,肚子叫得咕噜咕噜的。这棵桑树长在离他家后院十步远的地方,靠近草垛,也靠近隔壁阿婆家的鸡寮,再过去是她家厕所,这几个地方都跟食物无关。数代之龄的老桑树长得高大,枝叶茂密,当然,高树永远张开手臂欢迎“猴死囡仔”来爬。尤其是桑葚成熟之时,他与弟弟、妹妹争相爬树采食,常吃得浑身红紫。他的爬树技术好,总能吃到高枝上一颗颗黑晶油亮的桑葚,甜死人的美滋味。这么一想,嘴内注满口水,只好又咽下。不过,这时节桑树上只有叶子,还有一群比他还饿的蚊子。
其实,他根本没想要躲这里。
刚刚,阿嬷发狂般从竹帚抽出一枝细枝,每个小孩都知,这是狠毒的武器。他一见,立即变成一头小牛犊往后门逃窜,经过草垛、菜园、稻田,上了小路,继续依本能往学校方向快跑,速度比上次运动会夺得两百米冠军还快,而且这次没穿鞋——不,本来穿拖鞋,一跑,鞋子不知丢哪里去——他真的跑到学校门口
才停下,迎面碰到校长牵出摩托车,把公文包绑在后座要下班。
“校长好。”他说。
“放学了,怎么还没回家?”校长的话藏在噗噗噗的机车发动声中。
“我去阿姑家拿东西。”他撒谎。
“好,快回去听到没?功课要写,听到没?”校长说。
“好。”他说。没撒谎,他也想快点回家,天在黑了。
阿金只好往回家的路走。经过阿姑家,姑丈看到他,问:
“放学了,你怎么在这里?”
他只好再撒谎:“我去学校一下。”
“快回去,天黑喽。”
“好。”没撒谎,他真的想快快回家。国文、数学功课还没写,明天免不了又要挨两个老师的两种粗细不同的棍子打。打就打没什么,偏偏他们三餐吃饱饱的力气都蛮大的。但眼前他没空想那么多,今晚阿嬷的棍子先挨了再说。
他觉得做小孩好烦,到处都有要打他的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