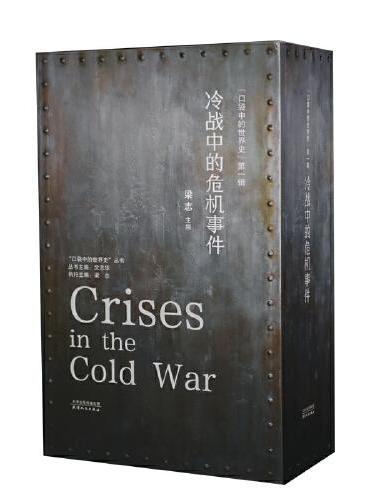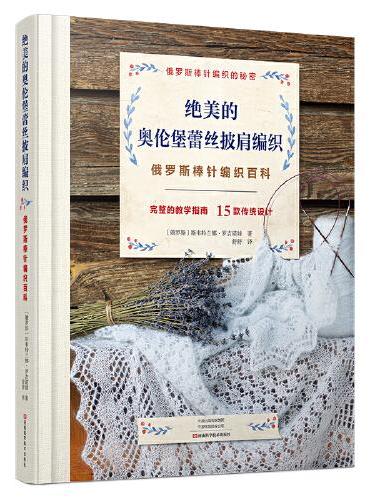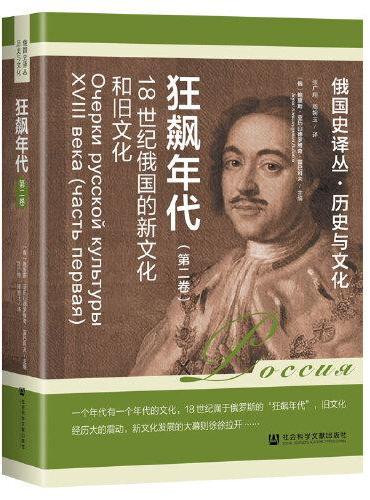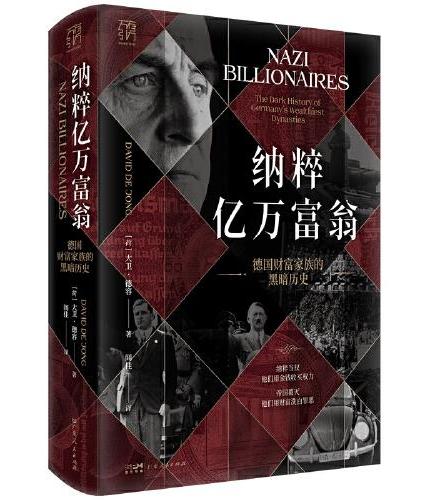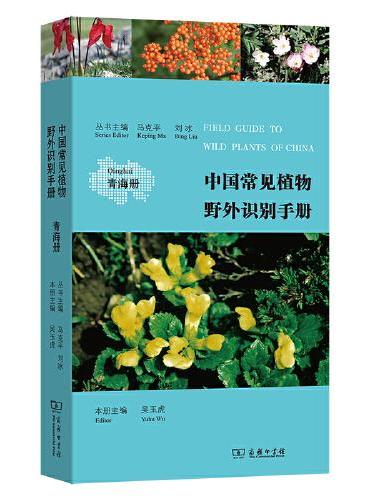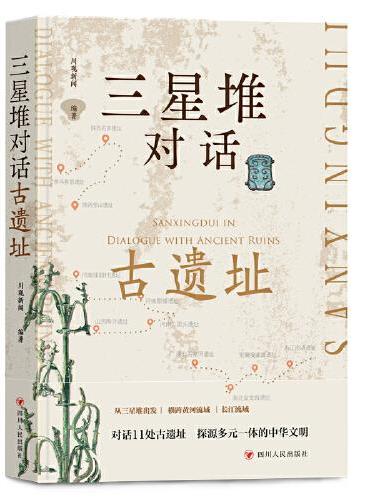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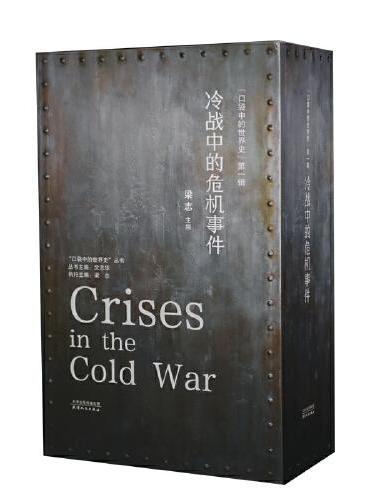
《
“口袋中的世界史”第一辑·冷战中的危机事件
》
售價:NT$
132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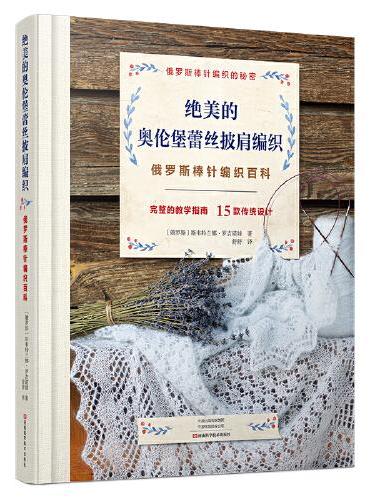
《
绝美的奥伦堡蕾丝披肩编织
》
售價:NT$
8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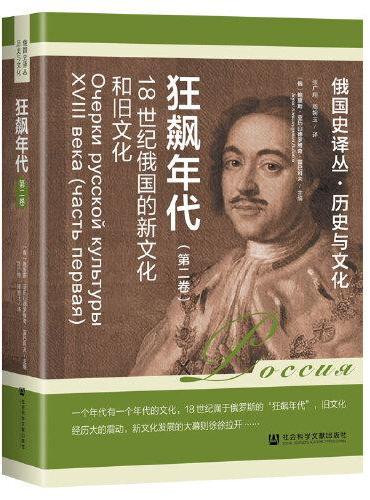
《
狂飙年代:18世纪俄国的新文化和旧文化(第二卷)
》
售價:NT$
8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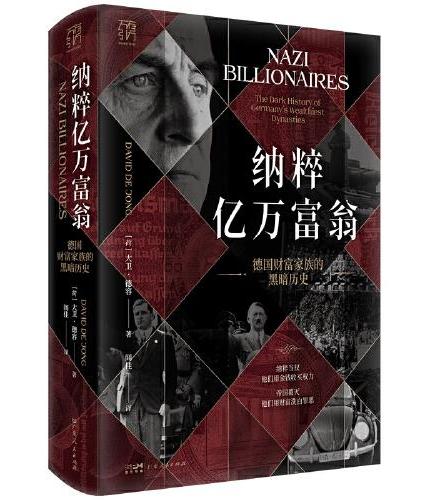
《
万有引力书系 纳粹亿万富翁 德国财富家族的黑暗历史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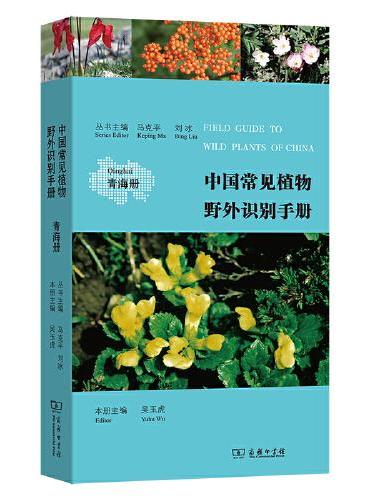
《
中国常见植物野外识别手册:青海册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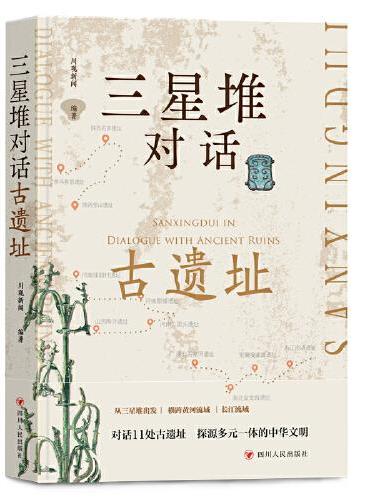
《
三星堆对话古遗址(从三星堆出发,横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对话11处古遗址,探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
售價:NT$
398.0

《
迷人的化学(迷人的科学丛书)
》
售價:NT$
653.0

《
宋代冠服图志(详尽展示宋代各类冠服 精美插图 考据严谨 细节丰富)
》
售價:NT$
398.0
|
| 編輯推薦: |
农民对这个世界的耐心和忍耐,胜过所有的花开花落,胜过一切植物的生长与衰败。
1、朝九晚五的人都在疲于奔命,与土为伴的人都在自由生长。
2、被称为“下一个李娟”的文坛新星吴莹的村庄笔记,媲美《阿勒泰的角落》,被誉为中国乡村真实的文字纪录片。
3、全文搭配摄影照片,全面展现中国乡村的质朴民风。
4、随书特别赠送“村庄烟火图”巨幅海报,还原在村庄的悠闲与自在。
5、封面采用双面印刷设计,一面封面,一面海报,一面是向往的村庄,一面是真实的村庄。关于美好,大概只有这两种。
他们多好,可以在一个地方生老病死。
|
| 內容簡介: |
夏舍是苏北平原上一个非常偏僻的小村庄,在夏舍,人们总是不停地忙忙碌碌,种下收割,再种下再收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辈子都是这样。他们关心庄稼的收成,关心田里的麦子、地里的菜秧,他们没有时间再去关心这世界的巨浪什么时候会涌到自己的面前。
追鸡赶鸭的小耳朵,从不知停歇的姚大妈,喝酒打牌又好脾气的姚仁义,到处串门的孤独老太,见谁都叫“宝宝”的邻里乡亲……这些个性鲜明的人都是夏舍流动的文化,演绎着一个充满烟火气和人情味的新世界。
|
| 關於作者: |
吴莹
青年作家、戏剧课老师,擅长非虚构写作。儿时长于鄱阳湖畔,现定居于成都。常年运营公众号“塘镇故事集”,被读者称为“温暖的记录者”。
吴莹的文风细腻、平实,不追求华丽,喜欢从平淡的叙述中表达真情实感。她常常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散文,无论是刻画人物性格还是描写社会环境,都非常善于从人的内心出发,挖掘人性中隐藏的部分,让人感到温暖。
|
| 目錄:
|
01 养鸡场场主小耳朵 / 002
02 婆媳关系 / 007
03 夏舍的冬天 / 012
04 一场乡村漫游 / 019
05 夏舍解谜专员 / 025
06 乡村运动会 / 030
07 夏舍大嫂子 / 035
08 城里的房子 / 040
09 风雨七十年 / 045
10 姚家继承人 / 052
11 春天潮水般来 / 056
12 春天的养鸡场 / 061
13 春天的集市 / 065
14 呦喳喳喳 / 069
15 孤独终老的自然学家 / 072
16 夏舍姚大哥 / 076
17 舅爹爹 / 081
18 娘喊千里 / 086
19 田边菜场 / 090
20 美梦一场 / 095
21 我们家的姚仁义 / 101
22 村里的休闲娱乐 / 107
23 欠了一屁股鸡蛋 / 111
24 夏舍养鸡大业 / 115
25 东边的老太和西边的老太 / 120
26 鱼精 / 126
27 总是遭骗的老人们 / 130
28 奶奶的韭菜墩子 / 136
29 等一场春雷 / 141
30 这些奇奇怪怪的风俗 / 144
31 南大围和北大围 / 149
32 窑厂 / 156
33 沿河的打鱼翁 / 160
34 夏舍的女人们 / 164
35 姑奶奶姚玉花 / 170
36 船上的家 / 177
37 寻路黄芦沟 / 181
38 立夏 / 186
39 蚕豆熟了 / 189
40 立夏后的一场暴雨 / 193
41 栽山芋秧子 / 196
42 打粽剌 / 199
43 夏天的一场雪 / 203
44 晒稻 / 206
45 庄稼熟了 / 210
46 暂别夏舍 / 216
47 重返夏舍 / 220
48 外出苦钱的姚大妈 / 226
49 清晨去做一桩大买卖 / 230
50 黄豆地里拔草 / 234
51 伯华二爷 / 237
52 桥头乘凉 / 241
53 一个人住的苏老太爷 / 245
54 村里的小贩子 / 249
55 南边的苏老太爷 / 253
56 守望相助 / 257
57 乡村凶猛 / 261
58 家是百宝箱 / 267
59 平原上的游荡 / 271
60 续命的脑白金 / 275
61 人生果实 / 279
62 寂静的村庄 / 283
后记 这些平凡又普通的故事 / 290
|
| 內容試閱:
|
这些平凡又普通的故事
一
伯华二爷家的老太太死了。
就在我们离开夏舍的第二天晚上,沤死在了河槽里。
一整个晚上她就那么孤零零地漂在河槽上。第二天早上伯华二爷左等右等,始终没等来他那个痴子妈从铺上起来吃早饭,进房里一喊铺上连个人影都没有。肯定是又犯痴了,早饭都不吃就外出乱逛,他决心出去把他那个痴子妈找回来。伯华二爷穿过院子,走过华山大爷的黑麦地,走过平时夏舍人围在一起乘凉的小桥,北边水田里的稻子长得好着呢,他左边看看右边望望,想看看稻田里的水够不够,想着等会儿是不是要出来打缺子。
他探着身子伸长了脖子,忽然就望见了漂浮在水田旁河槽里的那个人。
这个人不是旁人,就是他那个92岁,老得都痴了的妈。
知道这个消息时,我站在原地反复回想,我们离开夏舍时到底有没有和老太太说再见。
没有,真的没有。
晚上我给小耳朵奶奶打电话问她具体怎么回事。
“她太老了,死了就死了吧。”
乡下人对死亡有着近乎冷酷的淡漠,他们似乎不愿意在死上面多费半点感情。
老太太前阵子死活不肯剪头发,闹着要上街去剪。好容易女儿从城里回来,左劝右哄的才肯让女儿洗个头剪个头发。隔天她就顶着头整整齐齐稀稀疏疏的头发在巷子里走来走去。
她走到了小娟家屋后,那下院子里头坐着好几个村子里的女人,也不晓得是谁聊起了村子里那些早逝的人,老太太一出现,大家似乎有一肚子惆怅,指着远处的老太:“让妈妈的,你看看这些不该死的都死了,这些老不死的一直在眼前。”
现在老不死的终于孤零零地躺在河槽里,她“终于”死了。
二
很多人问我,夏舍这个名字是你取的吧?这么好听。
不是的,那个静静矗立在苏北平原上的小庄子,它叫夏舍已经很多年了。
有时候夏舍的人坐到一块,听说外头的人说“夏舍”这个名字好听时,都笑得拍腿:“夏舍还好听,城里人都在想个甚哩哟。”
你问我觉不觉得这个名字好听?
我这个外地媳妇儿和你们一样觉得真好听,就像霍比特人的夏尔,这个名字自带魔法。
不仅仅是这个名字,我笔下那些夏舍的人夏舍的事,在当地人看来都是“这有多大个交易”。可是我在夏舍的日子,每天都兴致勃勃地看着这些没甚哩交易的人和事。
年初我刚去夏舍时,那个时候我状态并不好,工作的繁忙、带孩子的疲惫、城市生活的各种压力和焦虑统统裹挟着我。我的心是干巴巴的,脑子里净是一个又一个处理不完的待办事项,我坐在电脑前什么都写不出来,就像一盏洋油灯,灯芯烧到了尾巴,油也快耗干了。
我就是带着这样的状态走进了夏舍。
起初我对这个苏北平原上的村子谈不上一星半点的感情,那些动不动就把脑袋探进房间张望的乡里乡亲一度令我非常头疼。加之年初疫情的发生,点开朋友圈和微博,似乎全世界没一个人有好心情。我也坐立难安,整宿整宿地睡不着,就像创伤后应激障碍一样,伤心恐慌愤怒无缘无故地哭起来。
可是我的婆婆、屋前的小娟、东边西边的老太、独居的太爷,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日三餐餐餐不落下,他们一辈子都是这样,这个冬天仍旧是这样。当我关上手机走出房门,那些站在屋外院子里抱着手拉呱闲谈的乡亲们,始终兴高采烈。
我为此还生过气,认定自己是到了另外一个鲁镇。
我就这么糟糕地在夏舍过了一天两天三天四天……直到大雪落了下来。我没见过平原上的大雪,雪停后的清晨,平原上一片寂静,朝阳从树杈和屋檐之间一点点升起来,成群的鸟从雪地滑翔冲向云霄,又从云端像羽毛一样飘落下来,雪地和天际相交的地方,这些鸟不断地交织往来,叫声清脆。
我牵着小耳朵的手站在雪里,似乎有那么一刻好像听到了一种声音,我仔细辨认四下张望,才发现原来是我和小耳朵的呼吸声。
村子里的红灯笼终于让我有了过年的喜悦,村里的农妇们裹着鲜红翠绿的头巾,站在自家门前铲雪,男人们戴着顶大帽子拢着手互相打招呼。
“有什么比眼下我正在过的日子更真实呢?”
自那场雪后,我好似忽然心里有了一汪水。又有一天下午冬日暖阳照在身上,我们种下去的桃树居然开了一朵小小的花。当时有种很强烈的渴望,驱使我跑进房里端出电脑,写起了夏舍的故事。
我当然没想到会写这么多,原本只是心血来潮随手记一两篇,后来写着写着,发现因为写作,我和夏舍竟然拥有了一种非常奇妙的关系,我的眼睛、鼻子、耳朵以及身上的每一个毛细孔都在夏舍努力张开。
那些之前让我头疼的乡亲、不适应的生活环境、疫情带来的恐慌,统统因着我对夏舍兴致勃勃的观察,慢慢烟消云散,我心里的那汪春水越来越温润。
三
很多时间里我都怀疑自己的写作能力。我发现点开任何一个公众号,看到的文章都是观点都是评论都是辩论,里面有大量的信息,看完总让人觉得自己似乎又学到了点什么,比看之前又多了一些长进。
可我的文章,来来回回读一百遍也没有这些,那种有气魄、雄辩、华丽的评论性文章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心里来来去去挂念的始终都是很小的事。
今天在公园看见了两个老太爷,一个人坐在轮椅上,一个坐在长椅上,抱着头大声唱歌真有意思。昨天戏剧课上,学生表演的老太太抢公交车座位太逗了。
就是这些琐琐碎碎的小事,这些普普通通的人,总是让我充满了记录的热情。
就像我热情洋溢地带着学生排桑顿·怀尔德的《我们的小镇》一样,一个普普通通的镇子,里面的人物全部都是平凡人,可我就是爱极了里面那些每天做一日三餐,做了几十年却从未精神崩溃过的家庭主妇,她们坐在一起谈的那些日常琐碎,怎么就那么吸引我呢。
在夏舍,我就好像进入了桑顿·怀尔德笔下的格洛弗角镇。这里的每件事每个人都让我着迷,我像一台摄影机似的穿梭在村子里,对准每个人每件事,力图原原本本把这些全部录下来。
这几个月在夏舍,我们的计时方式变成了二十四节气,从立冬到春分、惊蛰、谷雨、清明、立夏……每一个节气都对应着夏舍的生活安排,在恰当的时候做该做的事,就是乡下生活的本质。这几个月我写了很多夏舍普通人很细小的事,好似在用文字拍一部纪录片,顺着这些时节,每发生点什么让我兴致盎然的事,我便提笔记下来。
现在回过头来再读这些文字,发现我也像个农民一样,随着二十四节气记录,春种秋收,耕耘播种,这些文字它们自己就形成了一卷时间之书。这些文字里有事也有人,和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一样,夏舍的每个人和每个家庭都有他的欢喜和忧愁,地上年月短暂,他们步履不停勤勤恳恳地活着,我尽量忠诚地记录我所见的一切。在这场刻骨铭心的疫情之下,有许多优秀的写作者记录着这个时代这个时期的宏大横截面,而我只是写了一个很小的地方,一些很普通的人。这似乎并不是我主动的选择,而是命运把我推到了这里:“喏,这有个小村庄,你去吧,你写吧。”
我很喜欢读史书,但是当我在读史书时,我总是更着迷于书中作者无意间提到的那些普通人,总想沿着他们的步履去看看那个时代的图景。
我总是幻想也许等小耳朵长大后,他忽然对这场疫情有了兴趣,于是他找来很多资料书籍开始阅读,读着读着不停地扼腕叹息。然后某个时刻,他无意间翻开了妈妈记录的这些故事,发现疫情之下竟然还有这样的小村庄,村庄里的人还在每分每秒地生活。他沿着这些普通人的步履,又看到了这个时代的一点点因为日常因为平凡而莫名生出的生机,因此他长舒了一口气。
在写这些时,我始终提醒自己要保持克制,只用故事说话,因为我相信故事自有力量,尤其是真诚的故事。
多余的抒情和评价只会让这些故事变得让人难为情。
当然,即便如此,这些故事有时候仍旧让我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它们太真实,一点遮掩都没有。好多人写文章可以藏在本章背后,可是我却始终只能站在文字中间,我把自己的感情、经历、身边的人和事和盘托出,用一种近乎笨拙的真诚,这真诚有时候让我感觉自己比任何人都脆弱。
写这些故事时,我也无数次问自己这其中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从实用功利的角度而言,这些故事没什么阅读量,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公众号粉丝,更勿谈收益。从文学性而言,这些故事是如此的小,也许并不具备什么社会性价值,更何况我写得并不高明。
直到老太太的死凭空而至,我对意义的追问也随之烟消云散。
这个世界上还有谁会写一写这个90多岁的老太太呢?她如此平凡和普通,她一生去过的远的地方可能就是镇上、县里,了不起也就是市里。她一辈子待在夏舍,种田种地生儿育女,没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就是一个苏北平原上的农妇。
丈夫死了、大儿子也死了,但她活着。一直活到整个人变成了痴子,一脚踏下河槽才算终于了结了这一生。
夏舍的每个老人基本都度过了这样的一生,他们一天比一天老,这个庄子一天比一天衰败,没有年轻人会回来。夏舍正在和这些老人一起,一天比一天更接近死亡。
我唯有老老实实将这些记录下来,才能安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