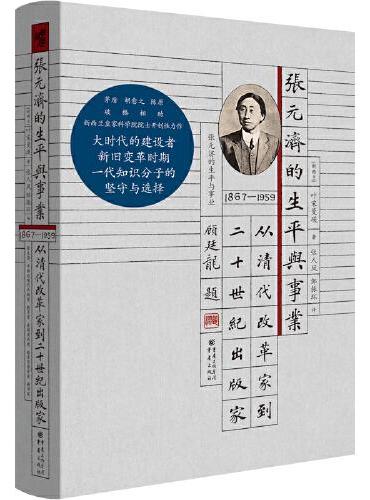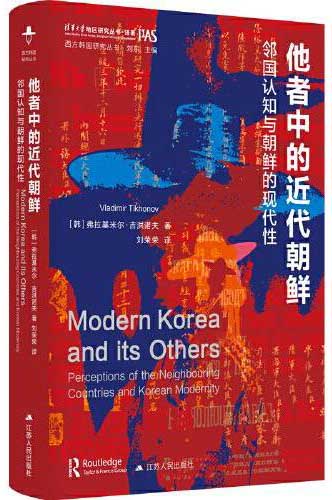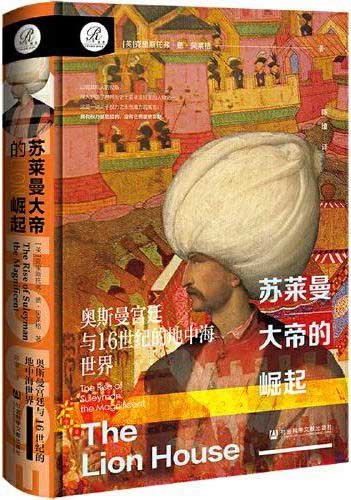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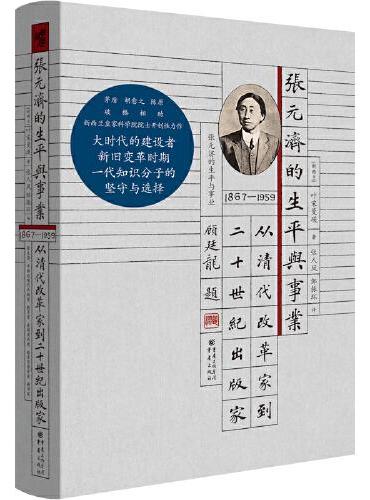
《
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从清代改革家到二十世纪出版家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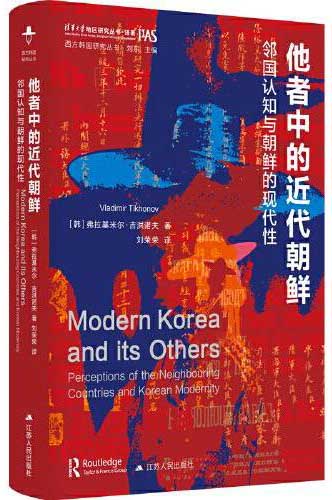
《
他者中的近代朝鲜(西方韩国研究丛书)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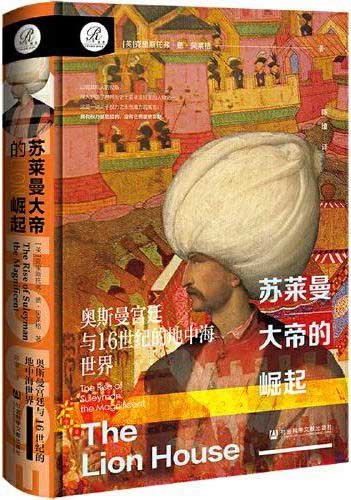
《
索恩丛书·苏莱曼大帝的崛起:奥斯曼宫廷与16世纪的地中海世界
》
售價:NT$
403.0

《
攀龙附凤:北宋潞州上党李氏外戚将门研究(增订本)宋代将门百年兴衰史
》
售價:NT$
454.0

《
金钱的力量:财富流动、债务、与经济繁荣
》
售價:NT$
454.0

《
超越想象的ChatGPT教育:人工智能将如何彻底改变教育 (土耳其)卡罗琳·费尔·库班 穆罕默德·萨欣
》
售價:NT$
352.0

《
应对百年变局Ⅲ:全球治理视野下的新发展格局
》
售價:NT$
398.0

《
前端工程化——体系架构与基础建设(微课视频版)
》
售價:NT$
454.0
|
| 編輯推薦: |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M. 库切成名作
改编电影由约翰尼·德普、罗伯特·帕丁森主演
库切目光与笔触为尖锐的作品,
当野蛮人终真的被塑造为野蛮人。
没有人能在即将来临的战争中全身而退。
|
| 內容簡介: |
“除了街上歇斯底里的疯子,没人相信我们这个平静稳固的世界将要完结;没人想得通帝国的军队居然会被长矛大刀加上几支破枪的野蛮人击溃(那些住在帐篷里从来不洗澡不洗衣服,完全没有文化的野蛮人)。我是什么人,可以嘲笑给人以希冀的幻想?”
几十年来,治安官一直是帝国的忠实仆人,管理着一个小小的边境要塞的事务,对即将到来的与野蛮人的战争视而不见,只一心研究边境埋藏的古代文字碎片。然而,当帝国的审讯专家到来时,他目睹了对战俘的残酷和不公正待遇,并与一个野蛮人女孩产生了情愫。对受害者的同情,使他做出了一种古怪的反叛行为:在审讯专家离开时将女孩送回了部落,而这使他成为国家的敌人……
|
| 關於作者: |
J.M.库切:
南非当代著名小说家,被评论界认为是当代南非重要的作家之一。曾两度获得布克奖,并于20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940年出生于南非开普敦,现居澳大利亚。
文敏:
译者,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专职记者工作之余翻译有J.M. 库切的小说《等待野蛮人》《内陆深处》《耶稣的童年》等;保罗·奥斯特小说《纽约三部曲》等;唐·德里罗小说《人体艺术家》等。共译有四百余万字四十种书。
|
| 內容試閱:
|
译后记(节选)
我们对南非那个国家非常陌生,不知道那儿是干旱还是多雨,是丘陵山岳还是一马平川,在翻译库切的小说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那儿是否也有飘雪的冬天。可是我们知道它曾有过非常严酷的种族隔离制度,南非前总统曼德拉为了反抗那种非人道的制度曾被监禁二十七年之久。库切在描写那个崇仰和平、相信人人生而平等的老行政治安官时,是不是也想到了关在牢中的曼德拉?当然,库切的主人公并非曼德拉那样刚毅果敢的民权斗士,就身份而言也根本不是殖民主义者眼里的“野蛮人”,倒是属于“文明世界”,应该说小说借此表述的是“文明人”的自省。一个平庸而善良、高雅却未必称高尚的老人,在帝国讨伐“野蛮人”的战争中重新审视人类文明的价值理念,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不由自主地跨入了灾难之门……
《等待野蛮人》的写作手法相当另类,可以说是一个寓言,一个虚拟的帝国,一段虚构的历史。人物大多是虚写,出现和消失都带有某种随意性,在某个段落中会突然冒出一个前面不曾提起的人物,而后这些人物往往又不知所终。人物和情节的虚化,时空界限的模糊,无疑给作品带来了指涉更为广泛复杂的意象性。显然,库切不想把自己的主题限定在南非种族主义那段历史上,他要说的是人类的一段痛史,从“文明人”眼里检讨“文明”如何戕害文明。那个作为帝国官员的主人公是整部小说几乎有性格塑造的人物,此人政绩平平,没有什么与时俱进的念头,却喜欢考古、爱好打猎,闲暇时则有文学、音乐相伴,既然镇上三六九等的女人都乐于讨好他,自也不乏寻花问柳之举。这算是一个有修养的人,但不是善于自我拷问的思想家,库切让这样一个优游自适的太平官走向高尚的殉道之路,终完成灵魂救赎的主题,整个叙述过程居然如此丝丝入扣,好像过去的小说家未见有这等本事。
作者将帝国与“野蛮人”的战争作为故事背景,一开始就引入一种严峻气氛,随着战事一步步拉开,人性终于被置于非常岁月的炼狱之中。乔尔上校的到来打破了边境地区的平静生活,从这一刻起老行政治安官就感受到内心被蹂躏的痛楚,然而正是这位代表帝国意志的国防部第三局要员唤醒了他的救赎之念。当那个流落街头的野蛮人女孩出现在自己眼前时,老行政治安官内心的宁静被打破了(而且是永久性地打破了)。由同情变成爱,自然不是一蹴而就,小说层层推进的描述委婉有致,人物心理过程的反反复复也写得非常精彩。就说这两个人的反差也真够大的——老/少、富/穷、官员/乞丐、文明人/野蛮人、言述者/沉默者……小说的戏剧因素不谓不丰富,但库切不是那种卖弄噱头的戏剧化写手,他的兴趣不会停留在这个反差强烈的男女故事上面。正如他的主人公惦念着绿色沼泽地里新生的芦苇,留恋那喧嚣过后洒满月光的湖面,库切的文字很自然地赋予对象一种超越之势,因为人的精神归宿才是他关注的重点。于是有了老行政治安官历经千辛万苦把那女孩送回野蛮人部落去的一章。照《纽约时报》一篇书评文章的说法,这是全书漂亮的一章,许多段落充满诗一般的语句。小说家在这里显示了罕见的描述技巧,当我翻译到这一章时,一边尽情欣赏那极富美感的原文,一边又深觉译笔支绌之窘。这个华彩章节几乎给人一种结束感,末了是那女孩随野蛮人的队伍离去,你怎么也不会想到她和老行政长官就这么分别了,互道“再见”之后,那女孩再也没有回到故事中来。天哪,故事到这儿才写了一半,接下去的文章怎么做?但是随着老行政治安官的厄运降临,读者自然有了新的企盼,心灵的旅途尚迢遥无期。库切这部小说有许多不按常理出牌的地方,那些收放自如的笔墨不但让人感到惊讶,也伴随着沉思的韵律。
一个孩子眼中的阴霾在雪后的泪水中融化了,他复明了,这是上帝的奇迹。一个孩子在空无一人的广场上搭建雪城堡的梦,这是库切内心深怀恐惧的镜像。为什么雪城堡里没有人,为什么那蛮族女孩总是无动于衷,为什么帝国的臣民要把野蛮人视为异类,为什么……读着老行政治安官被殴打被监禁遭受种种折磨的痛苦经历,你不得不怀疑人类正义的思维在这混乱的世间是否还能给灵魂以关照。信仰在现实面前低下了头颅,道德良知陷入思想和主义的围剿。流言和恐惧,新思维和集体意识,所有这一切使得人们在失衡中的挣扎变得愈加无力。正如老行政治安官所说:“行刑者对疼痛的程度并不在意,他们要向我证明的是活着的身体意味着什么,一个活着的身体,只有当它完好无损时才有可能产生正义的思维,当这身体的脑袋被掐住,喉咙里被插进管子灌进一品脱盐水,弄得咳嗽不止,呕不出东西又连遭鞭笞时,它很快就会忘记一切思维而变得一片空白。”这番内心独白可谓字字带血,让我们知道乔尔上校那类人物用什么方法使得正义的诉求变成了对它的阉割。
帝国跟野蛮人的战争没有胜者,人们输掉的是人性和有关“文明”的信念。这本书要读到后才能明白书名的含义,“等待野蛮人”跟“等待戈多”不同,这种“等待”不仅是一种精神折磨,而且带有灵魂追问的深意。在老行政治安官心目中,这是一个混合着恐惧和快意的字眼,还带着无尽的慨叹。故事结尾的地方倒不大像结尾,后只写到边境小镇孤立无援的“等待”,若是野蛮人打进来那几乎等于引颈受戮,可是没有下文。野蛮人会来吗,兵燹之后又将是什么局面?后面的事情库切就不管了,大概在他看来,检讨“文明”是每一个文明人应有的功课。
文敏
今天,离开上校的涉险之旅才四天,他的批俘虏已经送来了。我从窗子里看到他们被骑马的卫兵夹在中间经过广场,满面尘土、疲惫不堪,缩着身子从一大堆围着看他们的人群、跳上跳下的孩子们、汪汪嚎叫的狗中间穿过去,在军营围墙的阴影里,卫兵下了马;囚犯们也马上蹲下休息,只有一个孩子,单腿站着,一只手搭在他母亲的肩上,好奇地回望着那些围观者。有人送来一桶水和长柄勺。他们急不可耐地喝了起来,他们四周的围观者越来越多,慢慢地向中间挤进去,弄得我什么也看不到了。我不耐烦地等着卫兵推开人群,穿过军营大院到我这里来。
“你怎么向我解释这件事?”我对他叫喊着。他鞠了一躬,往口袋里摸索着什么。“他们都是捕鱼的!你怎么能把他们带到这儿来?”
他掏出了一封信。我开启封印抽出信看,那信上写的是:“请将这些人和将陆续到达的犯人单独关押起来,一直到我返回。”在他的签名下面又是那个封印,那个第三局的封印给他带到荒漠里去了。如果他不测的话,毫无疑问我还得再派一队人马去把那封印找回来。
“这个人真是太荒唐了!”我叫喊起来。我在房间里大发雷霆。人不应在他人面前贬低上级,正如不应在孩子面前贬低父亲,但对这个人,我的心里毫无忠诚。“没人告诉他这是些捕鱼的人吗?把他们带到这儿来是浪费时间!你们应该是帮他缉拿窃犯、土匪、帝国的侵略者的,可是他们像是那种危害帝国的人吗?”我把信扔向了窗子。
我出现时,人群在我面前分开了,我走到中间,站在那十来个可怜兮兮的囚犯面前。在我的盛怒之下他们朝后退缩着,那个小男孩滑进了母亲的手臂中。我对那些卫兵做了个手势:“叫人群散开,把这些人带进军营院子里去!”他们驱赶着俘虏聚在一起向前走,军营的大门在我们后面关上了。“现在,解释一下你们自己的行为吧,”我说,“没有人告诉他这些囚犯对他来说一点用都没有?没有人告诉他用渔网捕鱼的人和野外带弓骑马的游牧部落之间的区别吗?没有人告诉他这些人甚至讲的是另一种语言吗?”
一个士兵解释说:“当他们看到我们走近时,他们试图躲藏到芦苇丛里去。他们看见骑马的人来了,所以他们躲起来了。所以那位长官,那位大人,命令我们逮捕他们。因为他们当时躲了起来。”
我恼怒得几乎咒骂起来。好一个警察!好一个警察抓人的理由!“那么大人有没有说过为什么要把他们带到这儿来?他有没有说为什么他不能在那儿就地审讯他们?”
“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说他们的语言,长官。”
当然没人会!这些人是河边的土著,他们的历史甚至比游牧部落还悠久。他们的家庭三三两两地分布在河边的定居点,一年里大部分时间打鱼或是设陷阱捕猎,秋天则划船到南边遥远的湖畔,去捕捉赤虫,把它们晾干。他们用芦苇建造窳陋的栖身处,寒流袭来时冻得直叫唤,他们穿的是兽皮做的衣服。对任何人都害怕,总是躲藏在芦苇丛里,他们怎会了解什么大群野蛮人反对帝国的计划?
我派了一个士兵去厨房弄点食物。他带来昨晚剩余的一块面包,他把这面包交给了囚犯中年长的一个。这个老人虔敬地用两只手接过面包,先用鼻子嗅了嗅,然后掰开来。把面包块分给周围的人。他们都狼吞虎咽地大口吃起这“吗哪”来,快速地咀嚼着,他们都没有抬起眼睛。一个女人把嚼过的面包吐进手掌里喂她的孩子。我示意再拿些面包来。我们就站在那里看他们吃,好像是看一群奇怪的动物。
“让他们待在院子里,”我告诉他们的守卫们,“当然这会给我们造成不便,但也没其他地方可去。如果今晚天气转冷,我会另外安排地方。留心他们有没有吃饱。给他们派些事情做做免得他们闲着。把门关好。他们不会跑掉的,我只是不想闲人进来瞪着他们看。”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