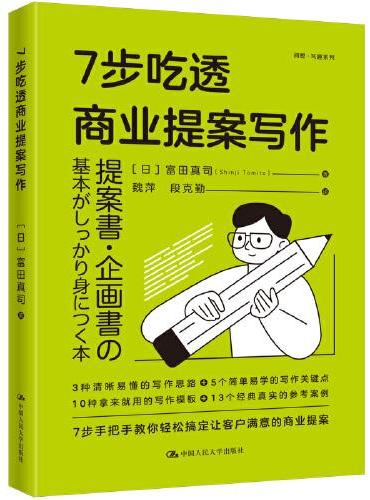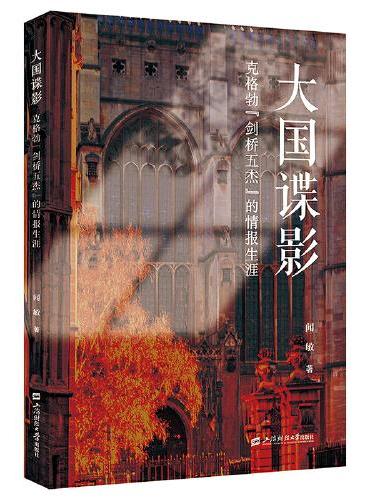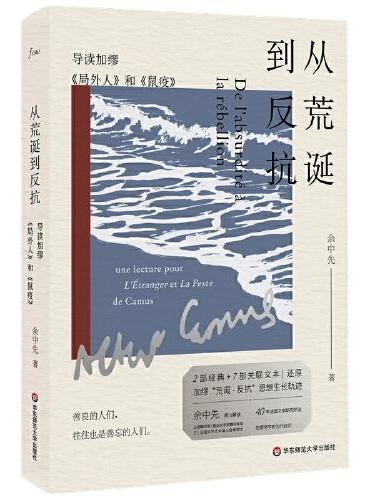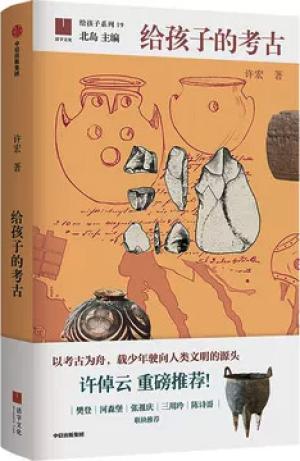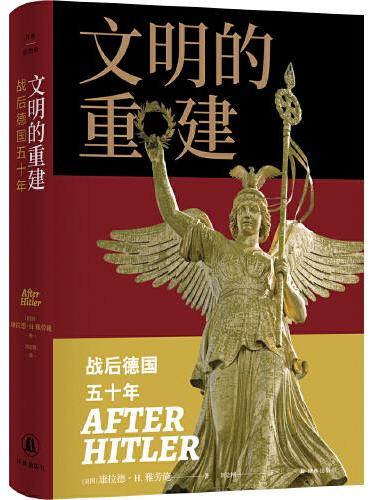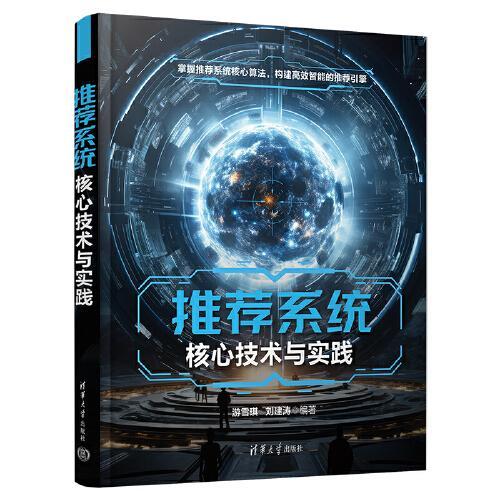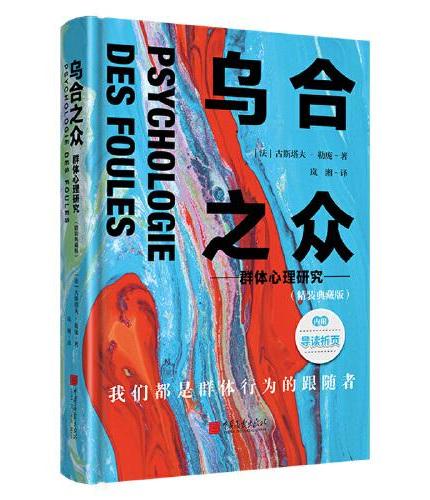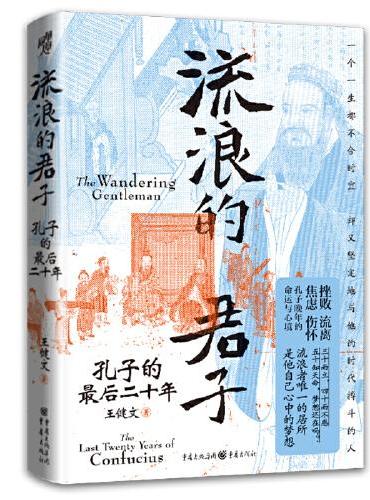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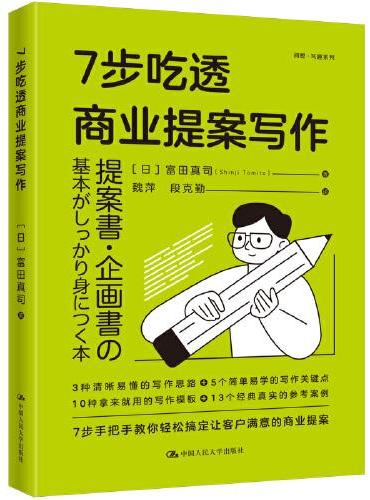
《
7步吃透商业提案写作
》
售價:NT$
3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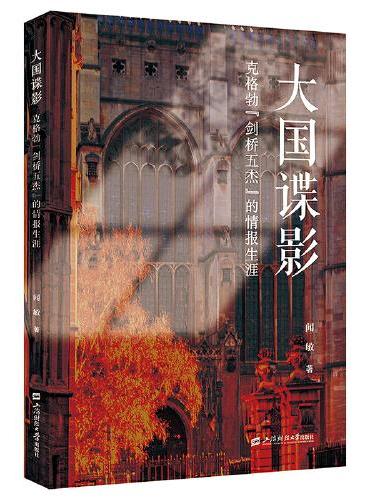
《
大国谍影
》
售價:NT$
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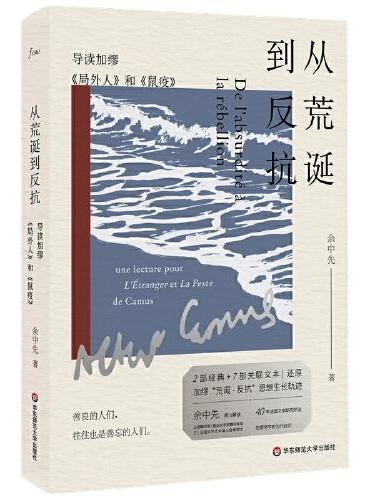
《
从荒诞到反抗:导读加缪《局外人》和《鼠疫》(谜文库)
》
售價:NT$
3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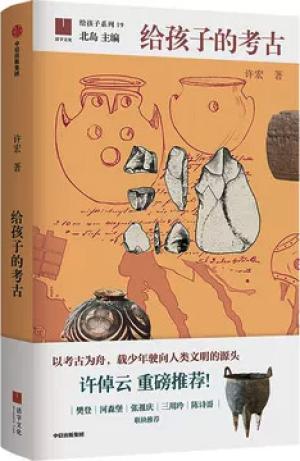
《
给孩子的考古
》
售價:NT$
2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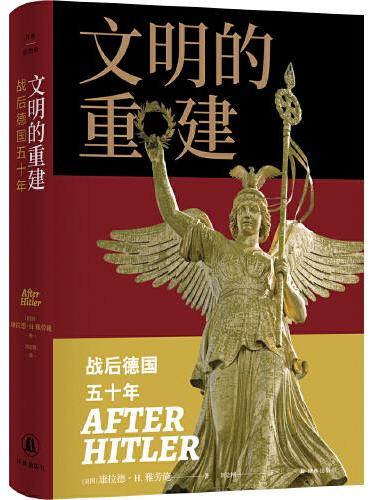
《
文明的重建:战后德国五十年(译林思想史)从大屠杀刽子手到爱好和平的民主主义者,揭秘战后德国五十年奇迹般的复兴之路!
》
售價:NT$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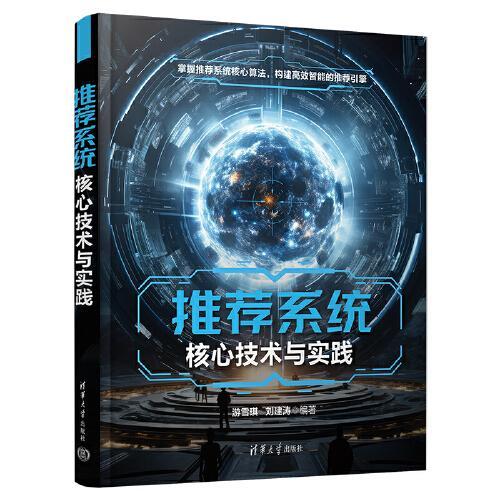
《
推荐系统核心技术与实践
》
售價:NT$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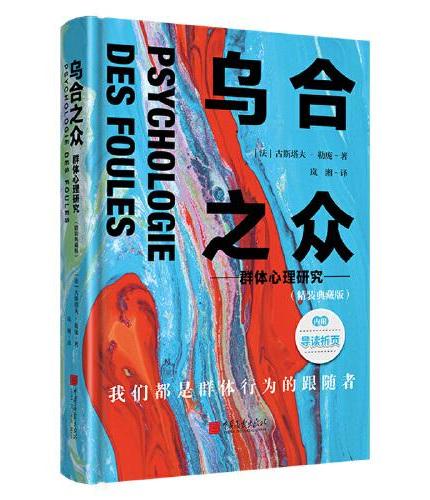
《
乌合之众:群体心理研究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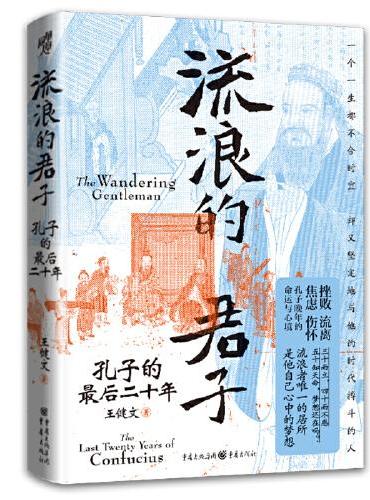
《
流浪的君子:孔子的最后二十年 王健文
》
售價:NT$
254.0
|
| 編輯推薦: |
★炽烈的爱情和绝望的现实,无论何时阅读《茶花女》,现实与虚幻的悲剧都令人泪流满面!
★法国文豪小仲马的成名作!法国殿堂级的爱情!多次改编成电影、戏剧、歌剧!该由著名歌剧作曲家威尔第改编的歌剧!
★著名翻译家李玉民译作,依据法国出版界传奇“伽利玛出版社”底本译出,诠释令人唏嘘悲叹的爱情故事!
★引入中国的西方文学名著,影响无数中国作家的爱情故事!鲁迅、严复、周作人、钱钟书等名家一致推荐的传世佳作!深深感动列夫·托尔斯泰、亨利·詹姆斯的爱情!
★新增超1000字生平传记及9幅珍贵照片,全面了解小仲马和玛丽·杜普莱西的爱情故事,进而感受玛格丽特和阿尔芒的凄美爱情,了解为何《茶花女》被认为是小仲马的半自传作品。
★内外双封,渐变加专金烫印,封面是红艳的炽烈的茶花和白色的微微侧身的女性,内封茶花逐渐变淡,女性逐渐变浓,直至封底纯白点金色毫不沾染尘世的白色茶花。
★附赠封面同款书签,炽烈的茶花和侧身的女人。
★内文胶版纸,极致翻阅手感。
|
| 內容簡介: |
|
《茶花女》是小仲马的成名作。像茶花一样美丽的农村姑娘玛格丽特来到巴黎谋生,不幸做了妓女。税务官之子阿尔芒真诚地爱她,使一向被人玩弄的玛格丽特深受感动,渴望通过纯真的爱情开始新的生活。但阿尔芒的父亲反对他们的爱情,迫使玛格丽特离开阿尔芒。阿尔芒不明真相,愤然折磨羞辱她,玛格丽特终于在冤屈和疾病中含恨死去。
|
| 關於作者: |
亚历山大·仲马(Alexandre Dumas fils,1824—1895),法国著名小说家、戏剧家,19世纪末法国戏剧三大领军人物之一,入选法兰西学士院。其父大仲马也是法国著名的文学家,《基督山伯爵》的作者。
1824年7月27日,出生于法国巴黎,是大仲马与女裁缝玛丽-凯瑟琳·拉贝的私生子,直到7岁时才被父亲承认。在大仲马奢华又飘浮不定的生活影响下,小仲马起初“觉得用功和游戏都索然寡味”,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同时又热切期望自己能像父亲一样名扬文坛。于是,他开始从现实中取材,从妇女、婚姻等问题中寻找创作灵感。
1844年9月,小仲马结识了当时的名妓玛丽·杜普莱西,虽然和玛丽的关系只维持了不到一年,但1847年玛丽的去世仍震动了小仲马。根据这段经历小仲马创作完成了一生中重要的、影响深远的作品《茶花女》,后被搬上剧院舞台,轰动了整个巴黎。
自此小仲马开始了专门的戏剧创作,共完成二十多个剧本,包括《半上流社会》《金钱问题》《私生子》《放荡的父亲》《克洛德的妻子》《福朗西雍》等。在作品中,小仲马力图尽显社会生活情状,以真切自然的情理感人。
1895年11月27日逝世,享年71岁,安葬在巴黎蒙马特公墓,距离玛丽的墓地仅百米。
|
| 內容試閱:
|
第十四章
我回到家里,就像小孩子一样哭起来。凡是男人,哪怕受过一次骗,也无不深知这种痛苦的滋味。
人总是自以为有勇气坚持在冲动时所做出的决定,我就是在这种决定的压力下,想到必须立即斩断这一情缘,还焦急地等待天明,好去预订驿车的座位,回到我父亲和妹妹身边,他们二人的爱我有把握,绝不会欺骗我。
然而,我不愿意这样一走了之,而不让玛格丽特明白我为什么离去。一个男人,只有根本不再爱他的情妇,才会不辞而别,连封信也不写。
我反反复复,不知打了多少封信的腹稿。
我面对的一个姑娘,同所有青楼女子一模一样,被我过分美化了,她把我当作学童那样对待。为了欺骗我,竟然耍了这样一个简单的花招,欺人太甚,这是明摆着的事。于是,我的自尊心占了上风。必须离开这个女人,又不让她得意地了解,这次断绝关系给我造成多大痛苦。我眼含悲愤的泪水,以美的笔体,给她写了如下一封信:
我亲爱的玛格丽特:
但愿您昨日身体不适无关大碍。昨天夜晚11点钟,我前去探问,得到回答说您还没有回去。德·G先生比我运气好些,他随后不久去拜访,直到凌晨4点钟还待在您家里。
请原谅我让您度过的那些烦闷的时刻,还请相信,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您给我的幸福时光。
今天我本想去探望您,但是我打算回到我父亲身边了。
别了,我亲爱的玛格丽特。我还不够富有,能按照我自己的意愿去爱您;我也不那么穷困,能按照您的意愿去爱您。让我们都忘却吧,您呢,忘掉一个您不大在乎的名字,我呢,忘掉一种我不可能实现的幸福。
您这把钥匙现在奉还,我始终没有用过,而您可能用得着,假如您像昨日那样时常生病的话。
您看到了,我若不是用一句放肆的挖苦话,就没有勇气结束这封信,这表明我还多么爱她。
这封信我反复读了十来遍,想到它会让玛格丽特不舒服,我的心情才平静了一点儿。我尽量利用信中佯装的情绪来壮胆,等我的仆人走进我房间,我便把信交给他,要他立刻送去。
“要等回信吗?”约瑟夫问我(我的仆人叫约瑟夫,同所有的仆人一样)。
“如果问您要不要回复,您就说不知道,在那儿等着就是了。”
我还抱着这种希望不放:但愿她给我回信。
我们这些人啊,真是又可怜又软弱!
我的仆人出门这段时间,我六神无主,坐立不安,时而回想起玛格丽特如何以身相许,我扪心自问有什么权利,给她写一封放肆无礼的信。按说她完全可以回答我,并不是德·G先生欺骗我,而是我欺骗了德·G先生,这种辩解之词,能允许不少女人有好几个情夫。时而又回想起这个姑娘的誓言,我就要说服自己相信,我这封信写得还是太温和了,用什么严厉的措辞,也不足以痛斥一个嘲弄我这样真挚爱情的人。继而我想到,也许我好不给她写信,白天照样去她家中,这样一来,我就会让她流泪,当面出口气。
后,我还想她会怎么回答,我在思想上已经准备相信她要做出的解释了。
约瑟夫回来了。
“怎么样?”我问他。
“先生,”他回答道,“夫人还在睡觉,没有起床呢。不过,等她一摇铃,就会把信交给她,如果回信,也会有人给送来。”
她还在睡觉!
不知有多少次,我就要派人去取回那封信,然而我心里总是这么想:
“信也许已经交到她手里了,要取回来,我反倒显得悔不该写信了。”
越接近她可能给我回信的时刻,我越是后悔写了信。
10点钟、11点钟、12点钟,相继敲响了。
中午时分,我要去赴约,就当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终我也没有想出什么法子,挣脱箍住我的铁圈。
这时,我怀着等待的人所容易产生的迷信心理,认为我稍微出去一会儿,回来就能收到回信了。焦急等待的答复,总是当人不在家的时候才送到。
我借口吃午饭,便出了门。
这次没有照往常的习惯,去这条大街的街角富瓦咖啡馆吃午饭,却穿过昂坦街,跑到王宫一带去吃饭。每次我远远望见一个女人,就以为是纳妮娜给我送回信去。我穿过昂坦街,连一个跑腿的伙计也没有碰见。到了王宫街区,我走进维里餐馆。伙计侍候我用餐,更确切地说,我不吃他也随意给我上菜。
我不由自主,眼睛总是盯着一座挂钟。
我往回走的路上,确信一定能收到玛格丽特的回信。
门房什么信件也没有收到。我还寄希望于我的仆人,可是我出去之后,他就没见有谁来过。如果玛格丽特要给我回信的话,信也早该收到了。
于是,我又开始后悔信上写了那种话。我本该完全保持沉默,这样一来,她见我昨天未赴约,就会感到不安,必然有所行动,问我没有赴约的原因,到了那时,我就可以讲给她听了。接下来,她就只能为自己辩白了,而我所希望的,也正是要她为自己辩白。我已经感到,无论她向我提出什么理由,我都肯定相信,只要能见到她,让我做什么都好。
我甚至还认为,她会亲自来我这里,然而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她并没有来。
显而易见,玛格丽特与众不同,因为在收到我那样一封信之后,很少女人不回敬几句的。
到了傍晚5点钟,我跑到香榭丽舍大街。
“假如遇见她,”我心中暗道,“我就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让她确信我已经不再想她了。”
在王宫街拐角,我看见她的马车驶过。这次相遇突如其来,我的脸唰地白了,不知道她是否瞧见我激动的样子,而我一时又特别慌乱,只看见她的马车了。
我就不再沿香榭丽舍大街散步了。我看了看各家剧院的海报,觉得还有机会见到她。王宫剧院有一出戏首场演出。玛格丽特肯定会去观看。
7点钟我到了剧院。
所有包厢都坐满了人,但是玛格丽特没有露面。
于是,我离开王宫剧院,又挨家进了她常去的剧院,诸如沃德维尔剧院、杂耍剧院、喜歌剧院等。
哪里也不见她的踪影。
或许我的信过分刺痛了她,令她无心看戏了,或许她怕撞见我,就干脆躲避一场解释。
我在大马路上,正沿着虚荣心的思路想去,无意碰见加斯东,他问我这是从哪儿来。
“从王宫剧院来呀。”
“我刚离开歌剧院,”他对我说道,“我本以为能在那儿见到您呢。”
“为什么?”
“因为玛格丽特在那儿呀。”
“哦!她在那儿呢?”
“对呀。”
“独自一个人?”
“不是,由她的一个女友陪同。”
“再没有别人?”
“德·G伯爵到她的包厢待了一会儿,但是她是同公爵一道离开的。我无时无刻不以为您会露面。我旁边的一个座儿一直空着,我想肯定是您定的座儿。”
“玛格丽特去的地方,为什么我就得去呢?”
“这还用说,就因为您是她的情人啊!”
“是谁告诉您的?”
“普吕当丝,昨天我遇见她了。我祝贺您啊,亲爱的,那可是个漂亮的情妇,不是想要就能弄到手的。把她守住了,她会给您增光。”
加斯东这一简单的想法向我表明,我这样赌气恼火有多么可笑。
假如昨天遇见他,听他这样讲,那么今天上午,我肯定不会写那封愚蠢的信了。
我真想去普吕当丝家,求她去对玛格丽特讲,我要跟玛格丽特谈谈,但是又担心人家报复,给一句恕不接待,于是我走过昂坦街,回到我的住所。
我再次问门房,是否有我一封信。
根本没有。
“也许她就是要等着瞧瞧,我是否有什么新的举动,会不会今天收回我的信,”我躺到床上这样想道,“后她看到我没有再写信反悔,明天就会给我写信了。”
那个夜晚,我特别追悔自己的所作所为。我在家孤寂一人,睡又睡不着,心被不安和嫉妒所啮噬,假如当初什么事我都顺其自然,那么此刻我就会在玛格丽特的身边,听她讲迷人的情话,而那种情话我仅仅听过两回,在这孤寂中还使我脸烧耳热。
我处于这种境况:糟糕的是从情理上讲是我错了。按说,一切都向我表明,玛格丽特爱我。首先,她就计划和我单独去乡间,度过整个夏天;其次,可以肯定,没有什么迫使她非做我的情妇不可,因为我并不富有,满足不了她的生活需要,甚至不够她随意的花费。因此,她只心存一种希望,在我身上找到一种真挚的感情,一种使她在卖身的生涯中得以休息的真情,可是第二天,我就摧毁了她这种希望,用放肆的嘲讽回报她给我的两夜恩爱。我这种行为何止可笑,简直是粗野可鄙。第二天就不辞而别,难道我不像个情场中的食客,晚宴之后害怕人家让我买单吗?难道我付给这个女人多少钱,自认为有权谴责她的生活吗?怎么!我结识玛格丽特才三十六小时,当她的情人才二十四小时,我就这样使性子。她让我分享爱,我非但不感到万幸,反而想独占一切,逼使她断绝过去的关系,而那些关系正是她未来的生计。我有什么可指责她的呢?什么也没有。本来她可以赤裸裸地告诉我,她要接待一个情人,就像某些直白得令人难堪的女人那样,然而,她却给我写信说她身体不舒服。我非但不相信她信中所言,到昂坦街之外的巴黎所有街道去散步,非但没有约朋友一起度过那个夜晚,第二天再按她指定的时间赴约,反而扮演起奥赛罗的角色,侦察她的活动,还以为再也不见她就是对她的惩罚。其实恰恰相反,她一定巴不得这样分手,也一定认为我是个天大的傻瓜,而她保持沉默,连怨恨都谈不上,那只是鄙夷。
看来,我本该送给玛格丽特一件礼物,不让她对我的慷慨心存一点儿怀疑,从而把她当作青楼女子对待,也就算同她结了账。然而我早就认为,哪怕有一丁点儿交易的迹象,也会伤害我们的爱,即使伤不着她对我的爱,至少也伤了我对她的爱。而且,这种爱极为纯洁,容不得他人染指,对方给予的幸福无论多么短暂,用多贵重的礼物也偿付不了。
这就是在不眠之夜,我一再重复的想法,也是我时刻准备要对玛格丽特讲的话。
天亮我还没有睡着,浑身发烧,一心放在玛格丽特身上,不可能想别的什么事情。
您也理解,必须当机立断,或者同这个女人了断,或者同我的顾忌了断,当然这还得她同意接待我才行。
然而您也知道,人总是当断不断。这样,我在家待不住,又不敢贸然去见玛格丽特,就不妨试试接近她的一种办法,如果成功了,我的自尊心也可以推脱,就说事出偶然。
已是9点钟了,我跑到普吕当丝家中。她问我这么早登门,有什么事情。
我不敢对她直说我的来意,只是回答说,我早早出门,是为了定去C城的驿车的座位,家父就住在C城。
“您的运气真好,”普吕当丝对我说,“赶在这样的晴天离开巴黎。”
我注视着普吕当丝,心想她是不是在嘲笑我。
她倒是一脸正经的神情。
“您去向玛格丽特道别吗?”她又问道,始终是一本正经的神态。
“不去道别。”
“您做得对。”
“您这样认为?”
“当然了。您既然同她断绝了关系,何必还去见她呢?”
“怎么,您知道我们的关系断了?”
“她把您的信给我看了。”
“她是怎么对您说的?”
“她对我说:‘我亲爱的普吕当丝,您引见的这个人真没礼貌,这种信,只能心里想想,谁也不会写出来。’”
“她讲这话是一种什么口气?”
“笑着说的,她还补充一句:‘他在我这里吃了两顿夜宵,都不说来看看我道声谢。’”
这就是我那封信和我的嫉妒所产生的效果。我这爱情的虚荣心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昨天晚上她干什么啦?”
“去了歌剧院。”
“这我知道。后来呢?”
“她回家吃夜宵。”
“独自一个人?”
“我想,有德·G伯爵陪伴吧。”
这样看来,我同玛格丽特决裂,丝毫也没有改变她的习惯。
碰到这种情况,有些人就会对您说:
“不要再想这个女人了,反正她也不爱您了。”
“好哇,我很高兴地看到,玛格丽特没有为我伤心。”我勉颜一笑,又说道。
“她做得太对了。您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表现得比她要理智,因为,这个姑娘爱您,总把您挂在嘴边上,真能干出荒唐事儿来。”
“她既然爱我,为什么没有给我回信呢?”
“就因为她明白了,她不该爱您。再说了,女人有时允许别人欺骗了她们的爱情,但是绝不允许别人伤害她们的自尊心,而无论谁,同一个女人相好了两天就离开她,不管给这种关系的决裂找出什么理由,总要伤害那个女人的自尊心。玛格丽特我可了解,她宁死也不会给您回信。”
“那我该怎么办呀?”
“怎么也不怎么办。她会忘记您,您也要忘记她,你们彼此都没有什么可指责对方的。”
“假如我给她写信,请求她原谅我呢?”
“您可千万别写,她会原谅您的。”
我真想扑上去,搂住普吕当丝的脖子。
一刻钟之后,我回到家中,给玛格丽特写了这样一封信:
有个人昨天写了一封信,追悔莫及,如果得不到您的宽恕,明天他就动身了。他渴望知道什么时候能匍匐在您脚下,向您表达悔意。
他什么时候能单独见您呢?因为您知道,做忏悔,就不应该有旁人在场。
这是散文诗式的一封书信,我折好派约瑟夫送去。他亲手把信交给玛格丽特本人,对方说晚些时候再回复。
我只出去一会儿用晚餐,等到晚上11点钟,还没有收到回信。
于是我决定不再苦熬下去,次日就动身。
既然做出这种决定,就开始收拾行装,反正我上床也肯定睡不着觉。
第十五章
约瑟夫和我忙了个把小时,为我出行做好了准备,忽听有人猛力地拉门铃。
“要不要开门?”约瑟夫问我。
“去开门吧。”我对他说道,心里纳罕这么晚了有谁会来我家,实在不敢猜想是玛格丽特。
“先生,”约瑟夫回来对我说道,“来了两位女士。”
“是我们,阿尔芒。”一个声音冲我喊道,我听出是普吕当丝。
我走出卧室。
普吕当丝站在那儿,正欣赏客厅里摆的几件古玩,而玛格丽特则坐在长沙发上,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我一走进客厅,便直趋到她面前,双膝跪下,抓住她的手,激动万分地对她说道:“请原谅。”
她吻了一下我的额头,对我说道:
“我这已经是第三次原谅您了。”
“本来我明天要走了。”
“那么我来拜访,怎么能改变您的决定呢?我前来不是要阻止您离开巴黎,我来这儿,是因为白天没有时间给您写回信,又不愿意让您以为我对您恼火了。普吕当丝还不愿意让我来呢,她说我还可能打扰您呢。”
“您,打扰我,您,玛格丽特!怎么会呢?”
“怎么不会!说不定您这儿有个女人呢,”普吕当丝答道,“她看见又来了两个女的,可不会觉得好玩。”
在普吕当丝表示这种看法时,玛格丽特则注意看着我。
“亲爱的普吕当丝,”我回答道,“您在这儿胡说什么呀?”
“您这套房子,倒还挺雅致的,”普吕当丝接口道,“那间卧室,能进去瞧瞧吗?”
“可以呀。”
普吕当丝走进我的卧室,她并不是真要参观,主要是弥补一下刚才讲的蠢话,知趣地避开,让玛格丽特和我单独谈谈。
“您为什么把普吕当丝带来呢?”于是我问玛格丽特。
“因为她陪我看戏了,再说,从这儿走的时候,我也希望有个人陪伴我。”
“不是有我陪伴吗?”
“不错。但是,我不想打扰您,此外,我又确信到了我家门口,您准要向我提出上楼进家门,由于我不能同意,我就不想让您离开时有权指责我把您拒之门外。”
“为什么您不能接待我呢?”
“只因我受到严密监视,稍微引起怀疑,就会给我带来极大的损害。”
“真的只有这一条理由吗?”
“如果还有别的理由,我就会告诉您了。我们两个人之间,彼此不应该再有秘密。”
“喏,玛格丽特,我不愿意兜许多圈子,才说出我要对您说的话。坦率地讲吧,您有一点点爱我吧?”
“很爱您。”
“那么,您为什么欺骗我?”
“我的朋友,假如我是某某公爵夫人,有二十万利弗尔年金,做了您的情妇,又另外找了一个情人,那么您就有权问我为什么欺骗您。然而,我是玛格丽特·戈蒂埃小姐,有四万法郎的债务,没有一文钱的财产,每年我还得花费十万法郎,因此,您提的问题毫无意义,用不着回答。”
“是这个理儿,”我说着,就把头偏在玛格丽特的膝盖上,“可是我呢,却像一个疯子似的爱您。”
“那好,我的朋友,您就少爱我一点儿,多理解我一点儿。您那封信让我十分难过。假如我是自由的,那么前天我就不会接待伯爵,或者接待了他,我也要来这儿请求您原谅,就像刚才您请求我原谅似的,而且今后,除了您,我也不会有别的情人。有一阵我倒以为,这种幸福我可以享受半年。然而您不愿意,一定要了解通过什么办法,哼!我的上帝,办法很容易就能猜出来。我采用这种办法,做出的极大牺牲,远远超出您的想象。本来我可以对您讲:‘我需要两万法郎。’您既然爱我,就会筹到这笔钱,但是将来您就有可能因此怪我。我宁愿什么也不欠您的,而这番苦心,您却没有理解,要知道,这可是用心良苦。我们这种女人,还有一点良心的时候,说话行事都有引申和发挥的含义,是一般女人所办不到的。我再向您重复一遍,玛格丽特·戈蒂埃本人找到付债的办法,又不向您要必需的钱款,这就是一番苦心,您应当利用而一声不吭。假如您今天才认识我,那么您听了我的许诺就会高兴万分,绝不会问我从前干了什么。有时候,我们不得不牺牲点儿肉体,来换取心灵上的一点满足。不过,等这种满足离我们而去之后,我们就会感到更加痛苦。”
我怀着钦佩的心情,倾听并注视着玛格丽特讲话。这位出色的女性,我从前渴望吻她脚的女性,肯让我进入她的头脑了解情况,还让我在她的生活中扮演个角色,她给了我这些我还不满足,想想人的欲望还有没有止境,就连我这么快就如愿的欲望,又垂涎别的东西了。
“的确,”她又说道,“我们这些有命无运的女人,我们产生的欲望很怪异,产生的爱情也不可思议。我们以身相许,时而为了这样东西,时而为了另一样东西。有的人为我们倾家荡产,却什么也没有捞到;还有的人只送了一束鲜花,就得到了我们。我们的心往往任性,这也是它仅有的消遣、的挡箭牌。我对你一见倾心,我向你发誓,比跟任何男人都要快。为什么呢?就因为你见我咯血,马上抓住我的手,因为你流了泪,因为你是世上从心里怜悯我的人。我来告诉你一件荒唐事:从前我养了一条小狗,在我咳嗽的时候,它就一副忧伤的样子看着我,它是我爱过的生灵。
“小狗死的时候,我比死了母亲流的眼泪还多。倒也是,母亲生我之后十二年间,动不动就打我。就是这样,就像对我的狗,我立刻就爱上了你。假如男人知道能用一滴眼泪换取什么,那么他们就会多得几分爱,我们也将少毁几分人家的财产。
“你的信表明了你的不同面目,向我揭示了你不能完全做到心灵沟通,而且,它给予我对你的爱情的伤害,超过了你可能对我做的任何事情。固然还是出于嫉妒,但这种嫉妒是嘲讽式的,放肆无礼。看了你那封信,我已经够伤心的了,本来指望中午见面,同你一起吃饭,总之,面谈能消除一直纠缠我的念头,而在认识你之前,有这种念头我也无所谓。
“况且,”玛格丽特接着说道,“只有在你面前,我才能自由地思考和讲话。围着我这样姑娘打转的那些人,都喜欢揣测我们的一言一语,从我们微不足道的行为中得出结论。我们自然没有朋友,只有一些自私的情人,他们挥霍家产,正如他们所表明的那样,并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而是为了满足他们的虚荣心。
“对于那些人,他们快乐的时候,我们也必须高兴;他们要吃夜宵,我们必须显得胃口好;他们怀疑什么,我们也必须跟着怀疑什么。总之,不准我们有自己的心情,否则就要遭人笑骂,毁掉自己的声誉。
“我们不再属于我们自己了。我们也不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成了物品。我们在他们的自尊心上排在前列,在他们的尊重里排在末尾。我们有一些女友,像普吕当丝这样的女友,往日的青楼女子,她们仍然喜欢挥霍,可是年龄不饶人。于是,她们成为我们的朋友,确切点儿说,成为我们的食客。她们的友谊能一直到低三下四的地步,但是永远达不到无私的程度。她们只会给你出有利可图的主意。我们的情人就是再多出十个,她们也觉得无所谓,只要能捞几件衣裙,或者一副手镯就行,只要能不时乘坐我们的马车出游,到我们的包厢看戏就行。她们拿走我们隔夜的鲜花,借走我们用过的开司米披肩。她们从来不白帮忙,哪怕做一点点小事儿,也要收双倍的报酬。你也亲眼看到了那天晚上的情景,普吕当丝应我的请求,去向公爵替我要来六千法郎,当时就向我借了五百法郎,而这笔钱她永远也不会还给我,再不就拿不是从包装盒取出来的帽子顶账。
“因此,我们只能有,确切点儿说,我只能有一种幸福,就是我这样一个时常忧伤,又总病歪歪的人,能找一个比较超脱的男子,他不盘问我的生活,只做重我的感觉而轻我的肉体的情人。这种人,我在公爵身上找到了,然而,公爵毕竟年迈,而年迈之人既不能保护人,也不能安慰人。我原本以为能接受他为我安排的生活,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烦闷得要命,反正也得把人消磨死,那么被炭火的煤气熏死,还不跟跳进大火里烧死一样。
“正是这种时候,我遇见了你,一个热情而幸福的青年,我就试图把你变成我在喧闹的孤独中呼唤的那个男人。我在你身上所喜爱的,不是你现在的这个人,而是你应当成为的那个人。你不接受这一角色,认为它配不上你而丢弃它,你也是个平庸的情人,那你也照别人那样做,付给我钱,这事儿再也不要提了。”
玛格丽特这样长篇大论,表白之后就疲惫不堪,仰身倒在长沙发上,她用手帕捂住嘴,乃至蒙上眼睛,以便憋住一阵轻微的咳嗽。
“对不起,对不起,”我讷讷说道,“这一切我早就明白了,不过还是想听您亲口讲出来,我亲爱的玛格丽特。让我们只记住一件事,其余的全忘掉。记住我们相互拥有,我们年轻,我们也相爱。
“玛格丽特,你就随意支配我吧,我就是你的奴隶,你的狗,但是,看在上天的分儿上,还是把我给你写的信撕掉吧,不要让我明天启程,那样我会伤心死的。”
玛格丽特从衣裙的领口里掏出我那封信,交还给我,还微微一笑,以难以描摹的温和语气对我说道:
“拿着,我给你带回来了。”
我撕掉信,眼含热泪吻了伸给我的那只手。
这时,普吕当丝从里间出来。
“说说看,普吕当丝,您知道他向我请求什么吗?”
“他请求您原谅。”
“正是如此。”
“您原谅吗?”
“怎么也得原谅,不过,他还有别的要求。”
“还要求什么?”
“他要去同我们一起吃夜宵。”
“您同意吗?”
“您看怎么样?”
“我看你们是两个孩子,哪个也没有头脑。不过我也考虑到我很饿,您越是早点儿同意,我们就越能早点儿吃上夜宵。”
“好吧,”玛格丽特说道,“我们就三个人挤在我的马车里吧。对了,”她朝我转过身来,又补充一句,“纳妮娜一定睡下了,您开房门吧,拿好我的钥匙,千万别再丢了。”
我搂住玛格丽特,几乎使她喘不上气来。
这时候,约瑟夫走进来。
“先生,”他一副自鸣得意的样子,对我说道,“行李打好了。”
“完全打好了?”
“对,先生。”
“那好,都解开吧,我不走了。”
译后记
小仲马式的忏悔
书应需而至,是我的一大快事。这次应约翻译《茶花女》,法国友人斯坦麦茨教授得知,就赠给我一种好版本。所谓好版本,就是由名家安德烈·莫洛亚作序,正文后又有注释,还附录了有关作者和人物原型的资料。无独有偶,译完小说要写“译后记”时,我又在书橱里发现一本应需之书,波罗·德尔贝什著的《茶花女与小仲马之谜》(沈大力与董纯合译)。这一发现改变了我写后记的方向。
初想写的后记题为《多余的茶花女》,是因为看了一篇批评外国文学名著的重译现象的文章。不料文章刚看过,就有出版社约译《茶花女》,全然不顾已有多种译本的存在。
对我而言,约稿却之不当,受之又有“多余”之嫌,因此就要趁写后记之机,找几条辩白的理由。现在想来未免多余了,还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让市场去淘汰多余的吧。多种译本并存不算坏的状况,可以比较优劣,不断提高译文质量,至少还可以满足读者的不同口味。假使某家出版社买了一部外国名著的版权,推出的却是一种拙劣的译本,那情况就更尴尬了,谁想重译都不成,终倒霉的是读者和作者。
小仲马就不会碰到这种尴尬事了,他的作品已列入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谁翻译都不受限制。如果小仲马在天或地下之灵有知,他看到自己的作品在中国争相被翻译,一定会窃笑和得意非凡:广泛流传是一些作家成功的不可替代的标志。我说小仲马窃笑和得意,因为他在本国还从未受此礼遇,赢得一致的赞赏。
说来也怪,在世界上,《茶花女》是流传广的名著之一,而在法国还称不上经典杰作,也就是说进不了学校的课堂。在课堂之外,《茶花女》在舞台上成为久演不衰的保留剧目,还由威尔第作曲改编成歌剧,可以入选世界歌剧十佳;至于搬上银幕的版本就更多了,世界著名影星嘉宝等都演绎过茶花女。可见,从名气上讲,《茶花女》不亚于任何经典名著。
就是在法国文学界,也无人不承认《茶花女》是一举成功的幸运之作。1848年,小说《茶花女》一发表,就成为热卖的畅销书。改编成戏剧四年后得以公演,又一炮打响。小仲马春风得意,成为文坛的宠儿。此后小仲马又创作并发表了许多小说和戏剧,有些还轰动一时,总之,到了1870年大仲马去世的时候,小仲马的荣耀已经完全遮蔽了父亲的声名。他拥有广大的读者和观众,在许多人眼里他是那个时代伟大的作家。1875年,小仲马进入法兰西学士院,可谓功德圆满,成为四十位“不朽者”之一。
对于这样一位成功的作家,称颂者自然大有人在,其中不乏乔治·桑、托尔斯泰、莫泊桑等名家,但时至今日,批评之声仍不绝于耳。的批评之作,就是摆在我面前的这本《茶花女与小仲马之谜》,写于1981年,作者以尊重史实的态度,披露《茶花女》神话的底细。书中第5页这样一段话特别引起我的注意:
“她将在祭坛上为资产者的体面而献身。”小仲马为自己虚构的“纯真爱情”辩白,对父亲说:“我希望一举两得,即同时拯救爱情与伦理。既然也赎了罪,洗涤自身的污秽,任何权威都不可能指责我选择了一个婊子当小说的女主人公。有朝一日,倘若我申请进法兰西文学院,他们也无法说我颂扬过淫荡。”
这段话又让我想起我本不愿理睬的、一种对《茶花女》的轻蔑的评价,即说这是一部“玫瑰露”小说。写一个名妓的故事则是不争的事实,而这名妓又确有其人,名叫玛丽·杜普莱西,一个沦落风尘的绝色女子。且不说纨绔子弟、风流雅士趋之若鹜,大仲马也与之有染;单讲小仲马,1844年二十岁上,就得到比他大半岁的玛丽的青睐,很快成为她的“心上情人”。可是一年之后,两个人就因争吵而分手,小仲马给玛丽写了《绝交书》。
小仲马想跻身文坛,试笔不成,早就打名妓玛丽的主意,开始搜集写作的素材。就在玛丽去世不久,他就把她献上祭坛,写成了小说《茶花女》,又改编成剧本,成功首演,被称为19世纪法国重大的戏剧盛事。然而,小仲马的创作命运已定,此后不管他又写出多少作品,也只是绿叶,陪衬他桂冠上的那朵大茶花。《茶花女》始终是他的成功的基点和顶点,也一直是对他评价或毁或誉的起点和终点。此后小仲马的全部文学创作活动,都旨在逃出《茶花女》这个魔圈,逃出这块骷髅地,另建他的文学王国;他要走下原罪的十字架,坐上真正的文学宝座。
于是,他开创了“命题戏剧”,主张“戏剧必须服务于社会的重大改革,服务于心灵的巨大希望”。他按照这种主张创作的一些剧本,连题目都已命定:《半上流社会》(1855)、《金钱问题》(1857)、《私生子》(1858)、《放荡的父亲》(1859)、《妇女之友》(1864)……
于是,无论法国进入第二帝国时期,还是变成资产者显贵们的共和国,小仲马始终以伦理的权威自居,高举社会道德这杆大旗。
于是,他不失时机地忏悔青春时期的“原罪”:“读者朋友,我怀着对艺术的热爱和尊重,写了所有这些剧本,唯独种例外,那是我花一周时间炮制出来的,单凭着青年的胆大妄为和运气,主要是图钱,而不是有了神圣的灵感。”
他所说的“例外”,当然是指《茶花女》,令人深思的是,围绕着给他带来名利的这部作品,他总是否定别人肯定的东西。
想当初,小仲马写《茶花女》时,抛却功利的动机不说,他毕竟是写自身的一段感情经历,尤其这是同一个红极一时的名妓不可能长久的恋情,极具新闻看点,即使原本原样写出来,就可以成为畅销读物了,更何况是美化(艺术加工)了呢?
小仲马自然不会简单地叙述同妓女的爱情故事,否则他就真的创作出一部“玫瑰露”小说了。他深感“同时拯救爱情和伦理”的必要,以免落个颂扬淫荡的恶名。因此,他一方面把这段放荡行为美化成“纯真爱情”,另一方面又准备为了伦理而牺牲掉爱情。
应当指出,小仲马的高明之处,就是通过忏悔的口吻来完成这种美化的。他采用忏悔的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固然是模仿普莱伏神甫的《玛侬·列斯戈》,也是受缪塞的《世纪儿的忏悔》的启发。但是,一般意义的忏悔,总是痛悔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小仲马痛悔的却是他在现实中莫须有的、仅仅在作品中才有的思想和行为,这是的区别,也是他成功的创新。
在小仲马的笔下,一次放荡行为转化为“纯真爱情”,阿尔芒一片真心追求茶花女,却总误解玛格丽特的真情。故事自始至终,二人都在表述这种心迹。更令人叫绝的是,阿尔芒和茶花女要争取社会和家庭的认同,把他们不为伦理所容的关系纳入伦理的规范,获得合法的名分,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只可惜碰到不可逾越的障碍,从而酿成悲剧。
F.萨尔塞1884年谈到《茶花女》时,有这样一段话:“这个年轻人根本不在乎规则,也不理睬他所不了解的传统习惯。他将这个热辣辣、活生生的故事搬上舞台,再现日常生活的各种细节……他却没有意识到引入生活细节的同时,就更新了戏剧的力量,进行了一场变革……这是舞台上所见到的真实、感人的作品之一。”
正是这种“热辣辣、活生生的故事”,给了作品以感人的力量和长久的生命力。但小仲马却认为这是要赎的“罪”,要洗涤的“污秽”。他认定《茶花女》的成功是他忏悔的成功。的确,伪装成纯真爱情的放荡,再加上忏悔的调解,就既能满足那些有产者的欲望,又符合当时社会的道德观念了。
然而,小仲马混淆了,或者根本没有分辨清艺术的成功和社会的成功。他错误地以为社会的成功就是艺术的成功。《茶花女》之后四十年的文学创作,小仲马在社会成功的路上步步攀登,不断地忏悔他的原罪《茶花女》。四十年社会成功的掌声和喝彩一旦安静下来,他的众多作品摆到《茶花女》旁边,就显得那么苍白。
白白忏悔了四十年。
小仲马仿佛要夺回那四十年,就在1895年亡妻之后,他又娶了比他年少四十岁的亨利埃特·雷尼埃。
新婚半年之后,他便去世了。应小仲马临终的要求,家人没有把他葬到他家庭在故乡维莱科特雷的墓地,而是葬在巴黎蒙马特乐公墓,离茶花女玛丽·杜普莱西的香冢仅有百米。
这也是小仲马的后忏悔。
李玉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