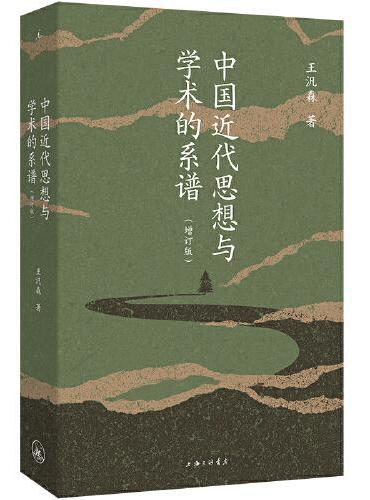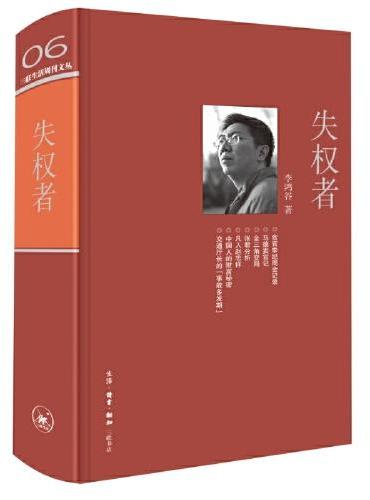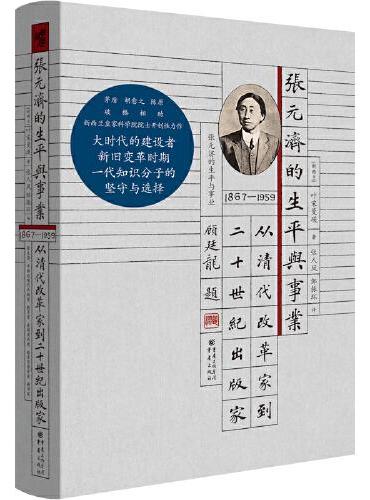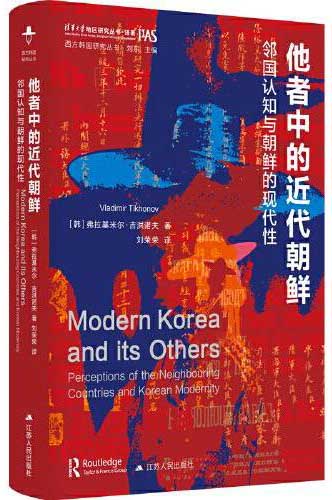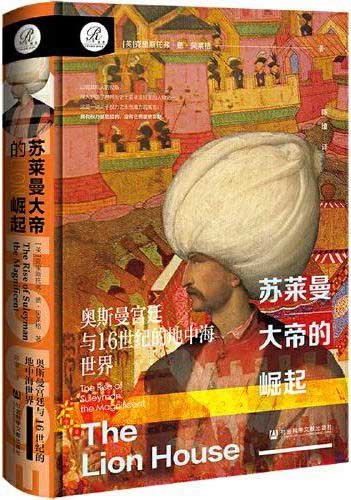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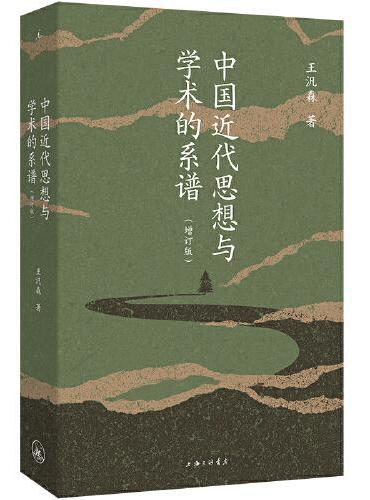
《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增订版)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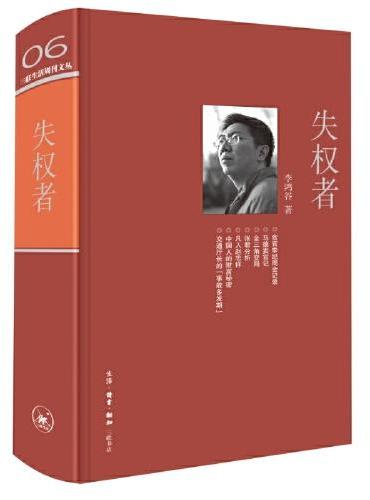
《
失权者(三联生活周刊文丛)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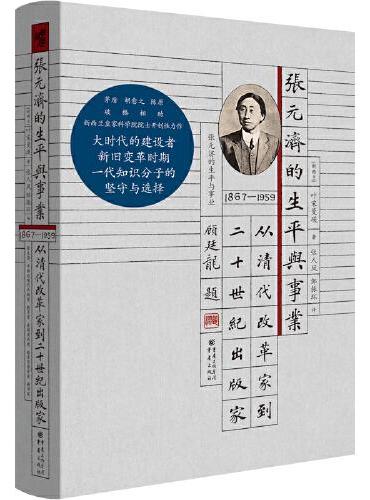
《
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从清代改革家到二十世纪出版家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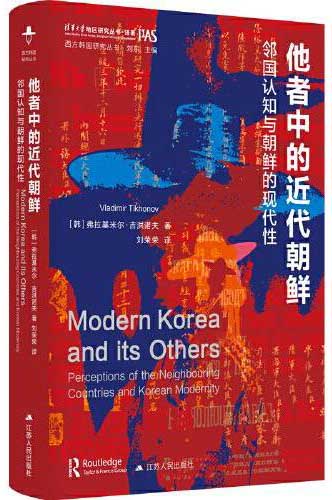
《
他者中的近代朝鲜(西方韩国研究丛书)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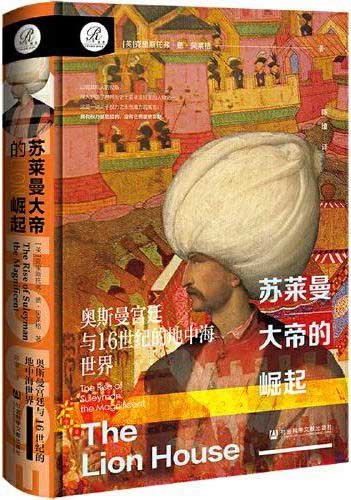
《
索恩丛书·苏莱曼大帝的崛起:奥斯曼宫廷与16世纪的地中海世界
》
售價:NT$
403.0

《
攀龙附凤:北宋潞州上党李氏外戚将门研究(增订本)宋代将门百年兴衰史
》
售價:NT$
454.0

《
金钱的力量:财富流动、债务、与经济繁荣
》
售價:NT$
454.0

《
超越想象的ChatGPT教育:人工智能将如何彻底改变教育 (土耳其)卡罗琳·费尔·库班 穆罕默德·萨欣
》
售價:NT$
352.0
|
| 編輯推薦: |
|
一夫多妻制下的尼日利亚,一对中产夫妻正在经历婚恋与生育之痛。获得多项欧美文学大奖,现代文明下的女性“黑镜”。
|
| 內容簡介: |
在尼日利亚,一对年轻的夫妇正经历生育问题。
埃金和叶吉德在大学相识相爱后结婚,尽管许多人希望埃金再多娶几个妻子,但他和叶吉德一致认为——一夫多妻制不适合他们,因为他们深爱彼此。但结婚四年后,在接受了各种治疗之后叶吉德仍然没有怀孕。她以为她还有时间,直到她的家人带着一个年轻女孩按响门铃,他们说年轻女孩是为埃金准备的第二个妻子。叶吉德愤怒、震惊、嫉妒至极……
拥挤的婚姻里,多少挣扎才可以平息她心底的嘶吼?
|
| 關於作者: |
|
阿约巴米·阿德巴约,尼日利亚人,曾在英联邦短篇小说比赛中获奖,奥巴菲米奥洛沃大学英语文学学士和硕士学位、东安格利亚大学的创作文学硕士学位,并在那里获得了国际创作奖学金。《听见她的声音》是她的处女作,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媒体巨大的反响和社会讨论。
|
| 內容試閱:
|
1985年起 伊莱沙市
即使那个时候,我都能感觉到他们是有备而来干架的。我能透过门上的玻璃板看到他们的身影。我能听到他们的说话声。将近一分钟的时间里,他们似乎没注意到我一直站在房门的另一侧。我想将他们拒之门外,上楼睡觉。如果他们在太阳底下站的时间足够久,也许会融化成一摊摊褐色的泥巴。玛莎妈的屁股那么大,若是融掉的话,会把我家门前的水泥台阶全占满。
玛莎妈是我的四位母亲之一;是父亲的大老婆。与她一同前来的是劳拉爸,埃金的叔叔。他们俩都弓着背,背对太阳,紧锁的眉头让他们的脸看起来令人厌恶。可我一开门,他们立马停止交谈,绽露笑容。我能猜到首先开口的会是那个女人。我知道,这是为了夸张地展现我们的亲密关系,可实际上,我们之间从未存在什么亲密关系。
玛莎妈用两只潮乎乎的胖手捧起我的脸庞,咧嘴笑着喊道:“叶吉德,宝贝女儿!”
我也对她咧嘴一笑,屈膝问候:“欢迎,欢迎。今天啊,定是老天爷开眼了。所以你们会一同前来。”他们进屋到客厅坐下后,我又行了个屈膝礼。
他们笑起来。
“你丈夫呢?在家吗?”劳拉爸一边说着,一边环顾屋子,就好像我把埃金藏在椅子底下似的。
“在的,先生,他在楼上。我给你们上茶后,就上去喊他。我该备些什么食物呢?山药泥?”
男人在暗自排演接下来将要展开的剧情的同时,瞥了一眼我的继母,仿佛他不知该如何回答我的话。
玛莎妈摆摆头。“我们不吃东西,去叫你丈夫。我们有要事跟你们俩商量。”
我微笑着离开客厅区,奔向楼梯。我想我知道他们来商量的“要事”是什么。在此之前,埃金家的多位亲戚已来过我们家,商量过同样的事。此类谈话就是他们说,我跪着听。彼时,埃金假装边听边记,但却在罗列第二天的待办清单。这些亲戚团里没人识字,他们对识字的人充满敬畏。埃金记下他们的话,让他们很感动。有时,如果埃金停下笔,正在发言的人就会埋怨没有得到埃金的尊重,因为埃金没把他或她的话悉数记录下来。在此类来访的过程中,丈夫常常会把整个星期的待办清单都列好,而我的双腿则会跪得抽筋。
这些访问把埃金惹恼了,他想要告诉亲戚们管好自己的事,可我不许他这么做。长时间的讨论的确让我小腿抽筋,可至少让我觉得我还是他家的一分子。在那天下午之前,自我婚后,还没有一位娘家的亲戚曾来做过此类访问。
上楼时,我心里就明白,玛莎妈的出现意味着他们会提出某种新对策。我不需要他们的建议。哪怕没有他们口中必提的“重要东西”,我的家也很好。我不想听到劳拉爸在咳嗽间歇费力挤出的嘶哑声音,不想看到玛莎妈再次闪露的牙齿。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对此,我跟埃金一直深有同感,我们想法一致。
但今天,我意外地发现埃金醒着。他每周工作六天,星期天基本都在睡觉。可当我进入房间的时候,他正在踱步。
“你知道他们今天要来?”我仔细察看他的神色,寻找那种熟悉的又惧又恼的表情。每次特别亲戚团来访时,他脸上都会带着这种表情。
“他们到了?”他站定,双手在脑后交叉。没有恐惧,没有恼怒。房间里开始有种窒息感。
“你早知道他们要来?但没告诉我?”
“那就下楼吧。”他走出房间。
“埃金,怎么了?怎么回事?”我在他身后叫道。
我坐在床上,双手抱头,努力呼吸。我就这么待着,直到听到埃金喊我的声音。我下了楼,走进客厅。我面带微笑,并非那种露齿的笑容,只是嘴角微微扬起。这种笑容仿佛在说:即使你们这些老东西对我的婚姻一无所知,我也很高兴,不,狂喜,听到你们必提的那些重要事情。但依旧,我是个好妻子。
一开始,我没注意到她,虽然她就坐在玛莎妈的椅子边上。她长得挺漂亮,肤色浅黄,仿若未成熟的杧果肉。薄薄的嘴唇上抹着猩红色的唇膏。
我靠向丈夫。他浑身僵硬,并没有伸出双臂抱住我,将我拉过去。我想搞明白这个黄皮肤的女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有那么一会儿,我有种疯狂的念头:玛莎妈进来时,是不是把她裹着藏了起来。
“叶吉德啊,我们说当男人拥有的一样东西变成俩的时候,他不会生气,对吧?”劳拉爸说。
我点点头,微微笑着。
“好,叶吉德啊,这是你丈夫的新妻子。一个孩子会将另一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谁知道呢,天帝可能会因这个妻子而回应你的祈祷。一旦她怀孕得子,我们确定你也会得到一个孩子的。”劳拉爸说。
玛莎妈认同地点头说道:“叶吉德,我的女儿,对于这件事,你丈夫的家人,还有你其他的母亲们,我们反复思量,寝食难安,”
我闭上眼睛。当我再次睁开眼,从恍惚的状态中醒来,那个肤色犹如杧果的黄皮肤女人还在那里,虽然变得有点模糊,可还在那里。我茫然不知所措。
我早料到他们会谈论我没孩子,我有千千万万种微笑来武装自己。歉意的微笑,“可怜我”的微笑,“我仰望上帝”的微笑——各式各样的假笑,只要能让我熬过这个午后,与这群口口声声说全为我好,却同时拿棍子直戳我伤口痛处的人在一起——我已做好准备。
我准备听他们告诉我:你必须采取行动,改变自己的处境。我料想会听到:你要去拜访新牧师;爬上另一座高山祈祷;向遥远村庄或小镇里的老医师请教。
我已武装好自己:双唇含笑,眼中恰如其分地噙着闪光的泪水,鼻子不断抽泣。我准备好在接下来的一周里紧锁美发沙龙的大门,与婆婆一道去寻找奇迹。
但我没料到的是房间里另一个面带微笑的女人,一个红唇烈焰的黄皮肤女人,如新娘般笑意盈盈。
我希望婆婆能在场。她是我喊过“妈咪”的女人。我去看她的频率比她儿子还勤。当我新烫的卷发被牧师摁到奔流的河水里洗掉的时候,妈咪就在场看着。母亲生下我没过几分钟就离开了人世,那牧师的理论是:在离世前,母亲给我下了诅咒。当我三天三夜坐在祈祷毯上,一遍遍吟诵那些我无法理解的祈词时,妈咪就在场。直到第三天我晕倒,提前结束了本该七天七夜的禁食守夜。
当我在卫斯理公会医院病房养病的时候,妈咪握着我的手,让我祈求上帝赐予力量。她说:好母亲的生活是艰苦的,一个女人可以做个坏妻子,可绝不能做个坏母亲。妈咪告诉我:在求上帝赐予我孩子之前,我必须恳求上帝开恩,让我拥有为这个孩子受苦的能力。她说:如果我在三天禁食之后就晕倒,那么我还没做好当母亲的准备。
这时,我意识到妈咪在第三天没有晕倒,是因为她可能已经历过几次诸如此类的禁食,代表她的孩子去安抚上帝。那一刻,妈咪眼睛与嘴巴周围刻着的皱纹变得邪恶起来,对于我来说,它们开始不仅只是年老的象征。我进退维谷。我想要成为那个我从未当过的人。我想要成为一个母亲,像妈咪那样,眼中闪烁着神秘的欢愉与智慧的光芒。然而,所有那些她谈到的苦难太吓人了。
“她的年纪比你小很多,”玛莎妈在椅子上向前探身,“他们赞赏你,叶吉德,你夫家认可你的价值。他们告诉我,在你丈夫的家族里,他们认为你是个好妻子。”
劳拉爸清了清喉咙:“叶吉德,作为个人,我要赞美你。我要感激你为保埃金死后能留下子女而做的努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你不会把新妻子当作竞争对手。她名叫芬米拉尤,我们相信,你会把她当作妹妹。”
“朋友。”玛莎妈说。
“女儿。”劳拉爸说。
玛莎妈拍了一下芬米的后背,说道:“来吧,去跟你大姐打声招呼。”
当玛莎妈让芬米唤我作大姐时,我打了个冷战。这词在我耳朵里炸开了,大姐——大老婆。这是一个判决,标志着我不是一个能满足自己丈夫的女人。
芬米走过来,挨着我在沙发上坐下。
劳拉爸摇摇头:“芬米,跪下。火车开得再远,前头总归是土地。这所房子里,叶吉德事事都在你前面。”
芬米跪下,双手放在我的膝盖上,面带笑容。我真想扇她一个耳光,把这笑容打掉。
我转身,看着埃金的眼睛,心中万分期盼他没参与这场伏击。他凝视着我的眼睛,眼中流露出默默的恳求。我脸上本已僵硬的笑容隐去了。怒气在心中汹涌,仿佛被人击中头部,正中眉心。
“埃金,你知道这事?”我用英语说,不让两位只会讲约鲁巴语的长辈听懂。
埃金一言不发,只用食指擦着鼻梁。
我环顾房间,想找到某件物品可以让我集中精神。滚着蓝边的白蕾丝窗帘,灰色的沙发,配套的地毯,地毯上有块一年多以来我一直想清除掉的咖啡污渍。那块污渍离地毯中心太远,桌子盖不住;离地毯边缘也很远,扶手椅也挡不住。芬米身穿米色的裙子,与咖啡污渍色调相同,与我穿的短上衣色调相同。她的双手就放在我膝盖下方,抱着我裸露的双腿。我的视线无法越过她的双手,无法越过卷起的长裙袖。我无法看到她的脸。
“叶吉德,把她拉近点。”
我不确定刚才谁说了这话。我的脑子热乎乎的,越来越热,近乎沸腾。任何人都有可能说了那句话:玛莎妈、劳拉爸、上帝。我不在乎。
我再次转向丈夫:“埃金,这事你知道?你知道,也不告诉我。你知道?你这可恶的杂种。在我们经历一切之后!你这可恨的杂种!”
在我的手掌落到他的脸上前,埃金抓住我的手。
令我住嘴的并非玛莎妈狂怒的尖叫,而是埃金拇指在我手心轻柔的触摸。我的目光从他的眼睛上挪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