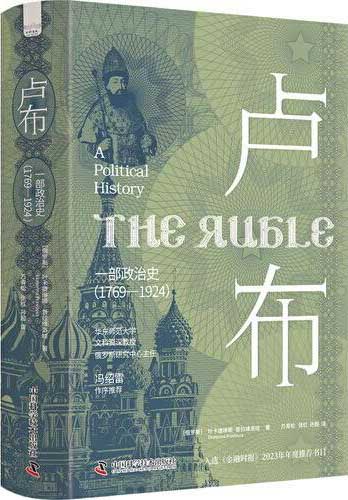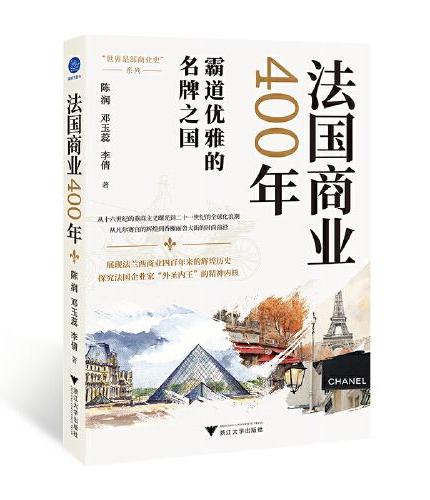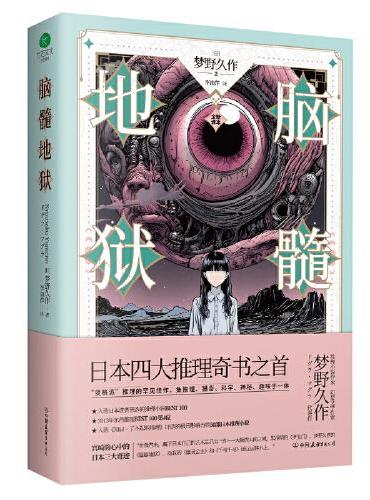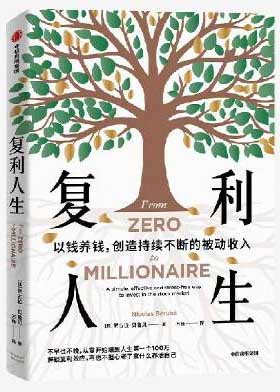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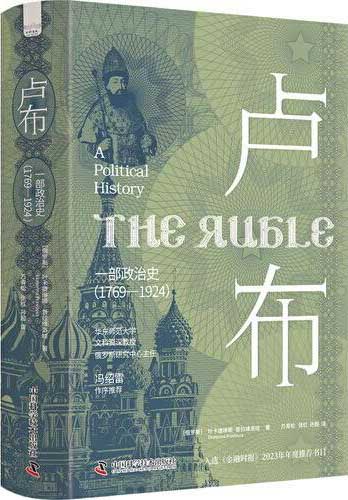
《
卢布:一部政治史 (1769—1924)(透过货币视角重新解读俄罗斯兴衰二百年!俄罗斯历史研究参考读物!)
》
售價:NT$
55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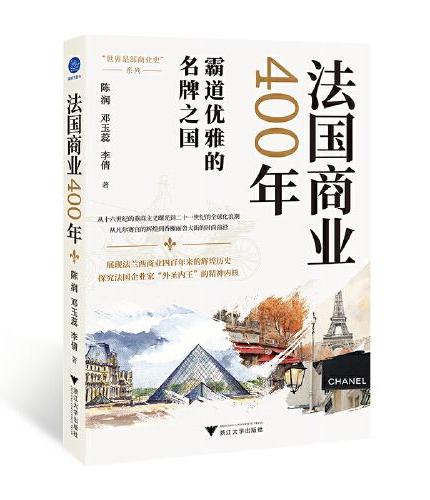
《
法国商业400年(展现法兰西商业四百年来的辉煌变迁,探究法国企业家“外圣内王”的精神内核)
》
售價:NT$
347.0

《
机器人之梦:智能机器时代的人类未来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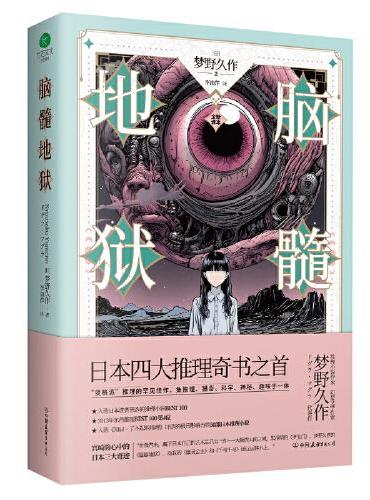
《
脑髓地狱(裸脊锁线版,全新译本)日本推理小说四大奇书之首
》
售價:NT$
28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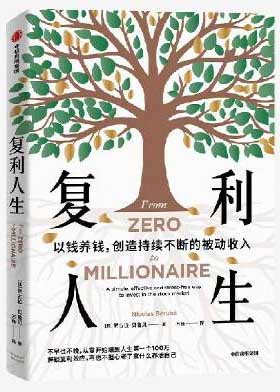
《
复利人生
》
售價:NT$
352.0

《
中国绘画:元至清(巫鸿“中国绘画”系列收官之作,重新理解中国绘画史)
》
售價:NT$
857.0

《
这里,群星闪耀:乒坛典藏·绽放巴黎(全套7册)
》
售價:NT$
1204.0

《
想通了:清醒的人先享受自由
》
售價:NT$
281.0
|
| 內容簡介: |
《群山之巅》是著名作家迟子建暌违五年之后,长篇小说。写作历时两年,是呕心沥血之作。
这部小说比《额尔古纳河右岸》更苍茫雄浑,比《白雪乌鸦》更跌宕精彩。
小说分“斩马刀”、“制碑人”、“龙山之翼”、“两双手”、“白马月光”、“生长的声音”、“追捕”、“格罗江英雄曲”、“从黑夜到白天”、“旧货节”、“肾源”、“暴风雪”、“毛边纸船坞”、“花老爷洞”、“黑珍珠”、“土地祠”等十七章,笔触如史诗般波澜壮阔,却又诗意而抒情。
中国北方苍茫的龙山之翼,一个叫龙盏的小镇,屠夫辛七杂、能算生死的精灵“小仙”安雪儿、击毙犯人的法警安平、殡仪馆理容师李素贞、绣娘、金素袖等,一个个身世性情迥异的小人物,在群山之巅各自的滚滚红尘中浮沉,爱与被爱,逃亡与复仇,他们在诡异与未知的命运中努力寻找出路;怀揣着各自不同的伤残的心,努力活出人的尊严……
“写完《群山之巅》,我没有如释重负之感,而是愁肠百结,仍想倾诉。这种倾诉似乎不是针对作品中的某个人物,而是因着某种风景,比如滔天的大雪,不离不弃的日月,亘古的河流和山峦。但或许也不是因着风景,而是因着一种莫名的虚空和彻骨的悲凉!所以写到结尾那句:‘一世界的鹅毛大雪,谁又能听见谁的呼唤’,我的心是颤抖的。”
——迟子建
|
| 關於作者: |
|
迟子建,女,1964年元宵节出生于漠河。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1987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1990年毕业后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至今。1983年开始写作,已发表以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六百余万字,出版有八十余部单行本。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逝川》《清水洗尘》《雾月牛栏》《踏着月光的行板》《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我的世界下雪了》等。出版有《迟子建长篇小说系列》六卷、《迟子建文集》四卷、《迟子建中篇小说集》五卷、《迟子建短篇小说集》四卷以及三卷本的《迟子建作品精华》。曾获得、第二、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文学奖。作品有英、法、日、意、韩等海外译本。
|
| 內容試閱:
|
一:斩马刀
龙盏镇的牲畜见着屠夫辛七杂,知道那是它们的末日太阳,都怕,虽说他腰上别着的不是屠刀,而是心爱的烟斗。
只要太阳好,无论冬夏,辛七杂抽烟斗是不用火柴的。他的两个裤兜,分别装着一面拳头般大的凹凸镜,和一沓桦树皮。抽烟斗时他先摸出凹凸镜,照向太阳,让阳光赶集似的簌簌聚拢过来,形成燃点,之后摸出一条薄如纸片的桦树皮,伸向凹凸镜,引燃它,再点燃烟斗。当然,取天火不那么容易,阳光灿烂的夏日,凹凸镜瞬间就把火给他盗来了,而隆冬时节,北风呼啸,太阳精气不足,火来得就慢。不过辛七杂也不怕慢,他说用太阳火烧的烟斗,有股子不寻常的芳香,值得等待。那面凹凸镜在他身上,像他雇来的长工,被吆来喝去,尽兴使唤着。
除了烟斗和凹凸镜,辛七杂的宝贝还有形形色色的屠刀——那是他赖以为生的家把什,他也不能不爱吧。但他的这种爱,却是牲畜们的恨!他在龙盏镇做了几十年屠夫,身上那股挥之不去的血腥气,对有着灵敏嗅觉的牲畜来讲,就是一条隐秘流淌的死亡之河,再熟悉不过了。所以他去江边,在岸边吃草的牛马羊见了他,不管身处的草地多么肥美,也要扬蹄奔向别处;他走在街巷中,晒太阳的猪见了他,趴着都哆嗦,有的甚至遗下尿来;而邻家的狗逢了他,不是缩头缩脑地溜回主人身边寻求庇护,就是讨好地凑向他,用舌头舔他的鞋子,好像在为自己争取永久的死亡豁免权。辛七杂不穿皮鞋,不然,他都不用擦皮鞋了。
辛七杂不宰也不吃家禽,说它们弱小无力,对它们下手下嘴太残忍,所以龙盏镇的鸡鸭鹅是不在乎他的。鸡看见他,照旧溜达它的;鸭子也敢晃着膀子与他并行;而那公主似的大白鹅觅食时,发现他的裤脚沾着牲畜的碎肉,会毫不客气地探出长脖子,取而食之。
辛七杂的屠宰用具齐全,杀猪刀,杀牛刀,宰羊刀,剔骨刀,刮毛刀,解牛刀等,大大小小,形制不同,但无一不是锋利的。他爱惜屠刀,从来都是自己磨刀。青灰的长方形磨刀石,摆在屠宰棚西北角,像块巨砚。他磨刀时,将方脚矮板凳放在磨刀石上,横跨着它,像在驯马。
这些手工打制的屠刀,都出自王铁匠之手。如今王铁匠还活着,可他的铁匠铺早就黄摊儿了。跟铁匠铺一样消失了的,还有供给制时期的供销社,粮店,以及弹棉花和踞锯缸锯碗的铺子。而这些店铺,在三十年前的龙盏镇,还是名角。
屠刀也得吃喝,也要睡觉,这是辛七杂一贯的说法。屠刀吃什么呢?在辛七杂眼里,它们爱牲畜的油脂,所以屠刀越使越锋利,而放置久了,就会饿出锈来。屠刀睡觉时呢,跟人一样得盖被子,被子要轻便、隔潮、透气,不然它们会喘不过气来。辛七杂用过屠刀,擦拭干净后,会将它们依次摆放在屠宰棚南窗的松木条桌上,蒙上一块油渍渍的白麻布。南窗照见月亮,屠刀上的白麻布便透进月光了,辛七杂说月光是好的擦刀布。
有两把刀,辛七杂近年是不碰的,一把是七寸长的杀猪刀,还有一把是斩马刀。辛七杂初宰猪,都是百八十斤的,七寸的屠刀游刃有余。后来的猪呢,即便属于绿色养殖,买来的饲料中,也难免有各类添加剂,一头当年的猪,少说也能长到二百斤,用七寸刀结果它们,明显局促了。为了打制九寸杀猪刀,辛七杂还破费不少,给王铁匠买了一箱高粱烧酒,让他回到废弃的铁匠铺,重启烘炉。王铁匠的力气江河日下,拉风箱时气喘如牛,在铁砧上锻打烧得红彤彤的屠刀时,抡铁锤的胳膊像遭遇了狂风的树,颤抖不已。所幸他技艺未失,淬火回火恰到好处,那把九寸杀猪刀,形态大方,刀身厚薄适中,亮白如雪,刀尖弧度优美,锋利无比,为他续写着一个铁匠的传奇。九寸杀猪刀在握,辛七杂为它镶嵌上柞木刀柄后,又求绣娘镌刻花纹。
辛七杂使用的屠刀的木柄,为防滑而镌刻的花纹,均出自绣娘之手,这把九寸杀猪刀当然不能例外。为此,他给绣娘送去了两斤自制的牛肉干,一包花茶。辛七杂晒的牛肉干味道好,但是出名的难嚼。别看绣娘上年纪了,牙齿仍是冲锋陷阵的勇士,消受得起。绣娘也没白吃肉干和茶,她给这把杀猪刀,雕刻了两只展翅的鹰!鹰那刚健的羽翼,在刀柄留下细密幽深的纹理,华美,耐用。九寸杀猪刀出世后,七寸杀猪刀虽说还和其他屠刀一起摆在桌上,但已派不上用场了。
另一把闲置起来的屠刀是斩马刀,不过它不在屠宰棚,而是挂在辛七杂家厅堂的墙上。王铁匠说斩马刀是旧时步骑两用的战刀,杀人的兵器,杀马并不适用,所以当年辛七杂让他打制斩马刀时,他抵制过,说这样的刀命相不好。但终他拗不过辛七杂,或者说抵御不了他接二连三奉上的酒肴,打制了这把刀。它形制如剑,一搾来宽,长约一米,水曲柳的刀柄上,镌刻的尽是天上奇迹:闪电纹和彩虹纹。为了试锋刃,辛七杂曾和王铁匠携其入林,砍向一片春天的红柳。刀起刀落之际,一片红柳倏然折腰,倒伏在林地上,宛如落霞。辛七杂将斩马刀磨得雪亮,挂在厅堂的墙上。那面墙从此就拥有了一道永恒的月光,从未黯淡过。辛七杂说,他手中的屠刀,没有不沾血迹的,他要拥有一把干干净净的屠刀,不然睡不踏实。
这把没沾过一滴血的斩马刀,那些年杀倒的,不是红柳,就是碧草,锋刃横溢着植物的清香气,好像他家吊着一只香水瓶。不过自从辛七杂的父亲辛开溜,说他在山中发现了一条白蛇后,辛七杂的老婆就不让他拿斩马刀出去了,说白蛇都是得道成仙的,万一伤及它,神灵降罪,家里就会遭殃。
辛七杂不待见父亲,在龙盏镇人心目中,他是个贪生怕死、假话连篇的人,不足尊重。可辛七杂心疼老婆,这个比自己大六岁的女人命苦,为她娘家和辛七杂父子操碎了心,没多少欢乐,所以他凡事都依她,不给她添堵,斩马刀便束之高阁了。月亮好的夜晚,辛七杂起夜路过厅堂,总要多看它几眼。月光在刀上行走,似在燃烧。他曾将烟斗凑向它,企图点燃,可斩马刀上的月光,一副舞娘的姿态,无意做播火者,根本不理会他。
雪藏在岁月之河的斩马刀,并没有伤到辛开溜说的白蛇,可还是在冰消雪融时节,闯下大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