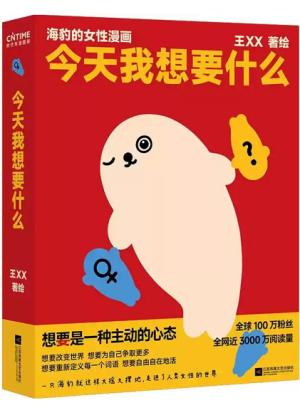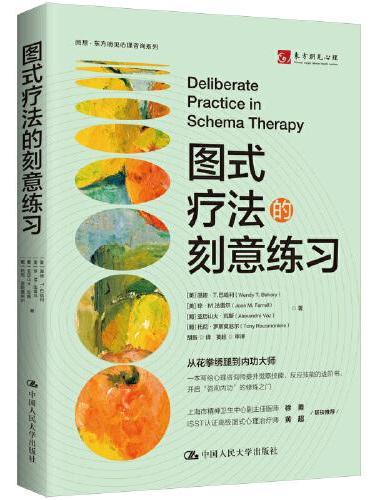新書推薦: 《
诡舍(夜来风雨声悬疑幻想震撼之作)
》 售價:NT$
254.0
《
讲给青少年的人工智能
》 售價:NT$
245.0
《
海外中国研究·宋代文人的精神生活(经典收藏版)--重构宋代文人的精神内核
》 售價:NT$
500.0
《
埃勒里·奎因悲剧四部曲
》 售價:NT$
1426.0
《
今天我想要什么:海豹的女性漫画
》 售價:NT$
347.0
《
日常的金字塔:写诗入门十一阶
》 售價:NT$
347.0
《
税的荒唐与智慧:历史上的税收故事
》 售價:NT$
500.0
《
图式疗法的刻意练习
》 售價:NT$
408.0
內容簡介:
《白痴 21世纪年度外国小说》叙述“我”十八至二十二岁之间即1958年至1962年间向成年迈进的阶段。我对女性身体的探求,我与所谓“现实”的冲突性关系,走向艺术、走向更广大的人性的各个瞬间里我的紧张,我持续的反叛冲动:反抗我深爱的父亲;我应征入伍继而成为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的一兵,反抗军事权威,被逮捕、被控告、被拷问、被监禁,然后被遣送到惩戒处。
關於作者:
皮埃尔·居约塔(1940—2020),生于法国中部卢瓦尔省,是法国当代重要的作家之一。少年时代醉心文学,早早确立写作的志向,1961年出版处女作小说《在马上》。1967年出版的以殖民战争为背景的小说《五十万士兵的坟墓》,被福柯誉为“我们这个时代核心的作品之一”。1970年出版《伊甸,伊甸,伊甸》,米歇尔·莱尔斯、罗兰·巴特、菲利普·索莱尔斯为其作序,但成为禁书,直到11年后才解除。2014年和2016年分别出版《苦难的快乐动物》第1卷和第2卷,其语言之有力,虚构之大胆令人着迷,在法国和其他国家影响广泛。他的画作在巴黎、柏林、伦敦和洛杉矶均有展出。因其毕生创作,获2010年法国国家图书馆奖和2018年费米娜奖特别奖。
內容試閱
译者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