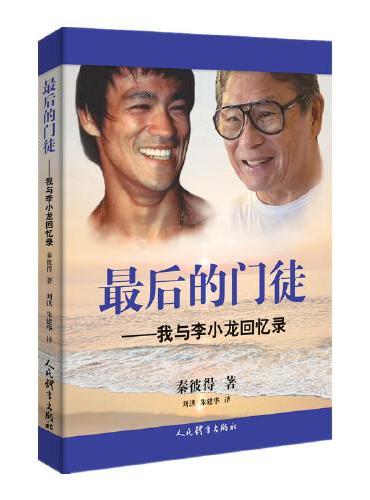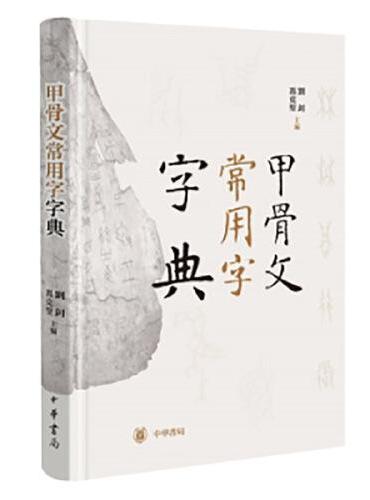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害马之群:失控的群体如何助长个体的不当行为
》
售價:NT$
449.0

《
性别:女(随机图书馆01)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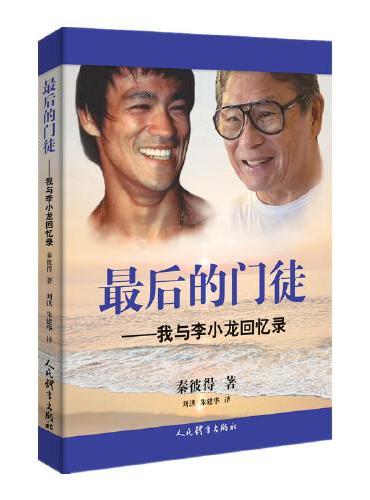
《
最后的门徒——我与李小龙回忆录
》
售價:NT$
347.0

《
没有明天的我们,在昨天相恋
》
售價:NT$
218.0

《
流动的白银(一部由白银打开的人类文明发展史)
》
售價:NT$
296.0

《
饮食的谬误:别让那些流行饮食法害了你
》
售價:NT$
296.0

《
三千年系列:文治三千年+武治三千年+兵器三千年
》
售價:NT$
9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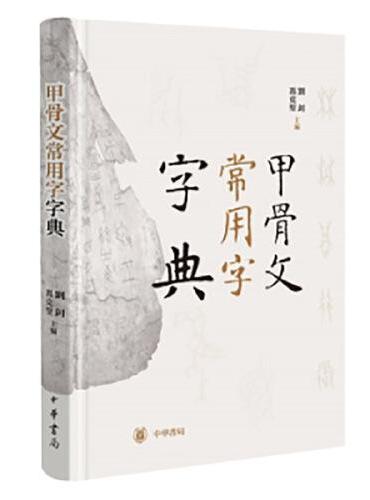
《
甲骨文常用字字典(精) 新版
》
售價:NT$
347.0
|
| 內容簡介: |
|
这是一部传记小说。讲述了冀东抗日民族英雄节振国的故事。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由节振国带领的工人游击队在唐山及冀东地区打鬼子、除汉奸、平土匪及在日本鬼子血腥的“扫荡”中打击侵略者英雄事迹,体现了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是一部史诗性的文学作品。时至今日,节振国极富传奇色彩的故事仍被人们广为传颂,其事迹永远激励着后人。本书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书后,曾引起广泛反向,被誉为“影响过整整一代人的优秀作品”。
|
| 關於作者: |
|
王火,本名王洪溥,1924年生于上海,194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44年开始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及论文。茅盾文学奖得主,四川文艺出版社原书记、总编辑,四川人民出版社原副总编、编审,四川省第五、六届政协委员,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1987年春离休。1995年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
| 目錄:
|
目录
章前夜(001)
第二章惊雷怒涛(013)
第三章宝剑篇(025)
第四章北风中的笑声(037)
第五章里应外合(050)
第六章义无反顾(065)
第七章煤场喋血(077)
第八章软硬不吃(087)
第九章叛卖(098)
第十章刀光闪闪(107)
第十一章失群飞散(117)
第十二章慈母心(128)
第十三章破釜沉舟(139)
第十四章关家梢聚义(148)
第十五章明争暗斗(166)
第十六章寻找引路的镀灯(178)
第十七章喜相逢(189)
第十八章兵权转手(202)
第十九章卷地洪波滚滚来(214)
第二十章赵各庄狂飙(226)
第二十一章风雨良(239)
第二十二章桃林口(251)
第二十三章寒霜红叶(261)
第二十四章人头(270)
第二十五章温泉会(280)
第二十六章流水疾风(289)
第二十七章“燕春楼”传奇(302)
第二十八章血淋淋的冬天(317)
第二十九章鱼游大海(335)
第三十章青集的怀念(347)
第三十一章“办年货”(360)
第三十二章冰雪肝胆(372)
第三十三章金针峪(381)
第三十四章汉奸末路(391)
第三十五章“铁石犹存死后心”(400)
第三十六章威震冀东(413)
第三十七章不寻常的清明节(432)
第三十八章敲虎舌,拔虎牙(447)
第三十九章陈仓行(457)
第四十章水酒送别(467)
尾声(476)
|
| 內容試閱:
|
章前夜
初春的时候,在河北唐山开滦赵各庄矿一带,很少能看到令人悦目的绿色。除了零零落落的常青树外,别的树木都光秃着枝干在冷风中颤动。苍黄的田野、丘陵间,常有成群的老鸹“呀呀”叫着在觅食。天,铁青着脸压在头顶上,使人心情沉重。矿区的道路、房屋、空场,到处被煤炭染成了黑色。面带饥寒之色的矿工,穿的是又脏又破的窑衣,戴的是积聚着黑垢的柳条帽,有的下井去干活,有的踯躅在街头……
这是一九三八年三月中旬的一天清晨。赵各庄矿上的气氛显得非常紧张。保安第三署那些穿着黑制服、戴着大盖帽的保安队和穿黑制服腰系皮带的矿警列队在街上巡逻,工人们东一伙西一伙地聚在一起谈话议论……矿工正在酝酿罢工,原因是要求增加工资;加上这一向矿方设立了井下牌子房,防止工人在井上拿了牌子不下井或提前上井。实行这种“井下记工制”的办法后,工人领牌、交牌要排好几个钟点的队,而且不能打连班——一班接着一班地干。工人收入少,不打连班家里老幼多的就无法糊口。赵各庄矿的工人对这种无理的制度感到十分愤怒。昨天夜里,有一伙工人自发地将井下牌子房砸了。今天一早,矿司陈祥善就派了矿警去抓昨夜带头砸牌子房的工人。风声传到工人耳里,工人情绪当然更加激荡。
这时,在东大街上,有一个方圆脸盘、长得十分英俊壮实的矿工经过。他个儿不高,只不过五尺刚出头,两条浓眉下有一双机智深邃的大眼。他的名字叫节振国,是个运木工,今年三十岁。他正要下井去干活,没想到斜刺里跑来了一个长腿的年轻矿工,喘着粗气大声叫道:“老节!矿警抓了小佟!快去救他!”
这长腿的矿工是节振国的结拜二弟,名叫纪振生。节振国历来是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一听矿警抓了小佟,说:“走!”马上跟着纪振生向前奔跑。
四个如狼似虎的矿警正押着年轻瘦弱的矿工佟树安迎面走来,后边跟着许多愤愤不平的工人。小佟已被矿警打得满脸是血。
节振国和纪振生大步上前。节振国伸出两臂横着一拦,说:“停下!”
那几个矿警认识节振国,知道这是个武艺高强、在工人中有威信的矿工,不好惹,都停下了脚步,后边跟着的矿工们马上围成了一个圈子。带头的一个矿警吆喝地说:“节振国,你想干什么?”
节振国两眼盯着问话的矿警,字字沉着地说:“把小佟放了!”
纪振生和一伙矿工也高嚷:“把小佟放了!”
那矿警说:“我们是奉命捉拿砸牌子房的凶犯!”
节振国怒气腾腾,指着满面是血的小佟说:“你们将他打成这样!你们才是凶犯!要是不放他,小心我们不客气!”
另一个矿警说:“不放你敢怎样?……”
节振国看见路边有根住户拴绳晒衣用的木柱,有碗口粗,指着那结实的木柱对围着的众人说:“闪开!”
大家刚一闪开,节振国走上前去,推出一掌,只听“咔嚓”一声,木柱折断,被打得远远飞到一边去了!矿警瞠目结舌,围成一圈的矿工欢呼喝彩。
节振国对矿警怒目而视,指着断了的木柱说:“是它硬还是你们的脑袋硬?!”
四个矿警面面相觑。节振国用命令的语气高吼:“放了小佟!”
矿警们正难以下台,忽然人丛里急急忙忙钻出一个长头发、黑脸的高个儿,肩上背着些布匹,一看是个布贩子。他像个半路里杀出来的程咬金似的冲着矿警说:“长官和弟兄们!有两个人拿着钢斧抢走了我几匹布和钱钞,劳驾快帮着去追一追!追到了我重重酬谢!”
这里节振国和纪振生已经将小佟被反绑着的双手解开,四个矿警顺坡下驴,匆匆跟着布贩子跑了。一场看来难以解决的纠纷顺利解决了。围着的矿工们又是一阵欢呼。
节振国指指小佟嘱咐纪振生:“老二,快带小佟去歇歇。等会儿再找根木柱给埋上!”见纪振生扶小佟走了,他紧一紧系在窑衣外的腰带,打算去上班。一转身刚迈步,发现黑瘦瘦的胡志发已在他身边跟他并肩而行,不禁“咦”了一声,说:“老胡,你也在这儿?”
胡志发是井下的挖煤工,比节振国大五六岁年纪,看上去老成持重,其实聪明干练,有人叫他“智多星”。节振国一直将他当大哥对待。这时他笑笑点头说:“老节,下了班到我住处来一下!”
节振国刚想问“什么事?”老胡没停留,已经转身走了。节振国心里纳闷,不禁转起磨来。
老胡同节振国交情深厚,他虽没在节振国面前承认过自己是共产党员,可是从接触中节振国断定他一定是共产党。从酝酿罢工以来,老胡经常同工人们一块儿商量问题,矿工们都要求节振国带头罢工。节振国从小当矿工,知道矿工的痛苦,恨英国毛子对工人的剥削压迫。冀东成立了“防共自治政府”一九三五年十一月, 日寇唆使汉奸殷汝耕在冀东二十二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从此,冀东实际上沦入日寇之手,冀东人民在日寇铁蹄下饱受痛苦。后,工人头上又踩着日本鬼子的铁蹄,生活当然更痛苦了!对于工人的罢工要求,节振国是从心眼儿里拥护的。老胡约他晚上去,节振国推测一定同罢工的事儿有关。
傍晚从井下上来,因为活儿很重,节振国累得脊背酸痛。春寒料峭,小北风轻轻刮来,冷得透骨,他脸上和手上都沾满黑色的煤粉,也没吃饭,就急急向胡志发的住处跑去。
天空里的灰云混浊郁积,路边杆子上的电线在冷风中“嗡嗡”怪叫。天,快暗将下来了。街上卖炒饼的小饭馆里散发出葱油香味和锅勺响声来,测字摊前围着人,赌场里响着吆五喝六声和“哗哗”的骨牌声,到处有衣衫褴褛的矿工此来彼往……墙上刷着醒目的白底蓝字标语:“冀东是防共的前卫!”“铲共和平一致奋起!”“日华实现真正亲善!”……路边墙上有新刷的“仁丹”“中将汤”的日本广告。那“仁丹”广告上的一个翘胡子、穿日本海军大将服的半身头像示威似地看着节振国,脸上的表情仿佛是说:“支那人!亡国奴的滋味儿怎么样?”两个醉酒的日本浪人,一个穿和服一个穿西装,从街边一家小酒店里出来,歪歪斜斜地走着,嘻嘻哈哈地笑着,咿咿呀呀地唱着,钻进对面一家窑子里去了。节振国“呸”地对着日本浪人的背影仇恨地吐了口唾沫,脚下的步子噔噔地迈得更快了。
胡志发是河北曲阳人,光杆一条,在靠近天主教堂的地方租了一间简陋的小屋居住。通向胡志发住处的那个小胡同口外,有一块三尺来高的青石碑。老工人都知道,胡志发住的那地方原先是个煤矿工人夜校,碑是早年一个到夜校上课的年轻教书先生请人刻了竖在那儿做指路标的。后来工人夜校的屋子倾塌了,石碑仍旧竖立着。石碑上刻的是一首《咏煤炭》的诗:
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深。
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
鼎彝元赖生成力,铁石犹存死后心。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那位不到三十岁的教书先生,被英国毛子和国民党指控为“乱党”,八年前被抓走了。正因为对这位留长发穿长衫的教书先生有感情,矿工们经过这儿常好看一看石碑,用手摸一摸。天长日久,石碑已经被摸得光溜溜的了,字迹却仍清楚。节振国从小跟着哥哥在矿上识字上学,对这首诗虽不全懂,经人一讲也能领会大意了。他老觉得胡志发在这工人夜校旧址上新盖起的小屋里住,是有深意的。每当他到老胡这儿来时,看到石碑,也总要有些感触地看看碑上的诗句。这会儿,也是这样。他停步又看一看碑上的诗句,才继续迈步又走。
一会儿,他到了胡志发的住处,这是一间石基土坯垒成的小屋。节振国推门掀开脏黑的旧棉帘走了进去。
屋里黄烟味浓重,点着一盏棉籽油的小油灯,一颗豆大的灯火放出昏黄的光亮。老胡盘腿坐在炕上;炕上还有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正同老胡在细声低语。节振国一看,就怔住了:这不是早上那个节外生枝拽矿警去帮他抓人的布贩子吗?!他怎么也在这儿呢?
布贩子两眼看起人来尖刀似的锐利。他穿一套半旧的黑平纹布中式棉衣,吧嗒吧嗒地抽一个小烟袋。胡志发见节振国来了,沉着而高兴地点点头,说:“老节,你来了,上炕坐。”说着,他用烟袋杆指着介绍说:“老周,这就是节振国。”
老周挺深沉,一举一动不慌不忙,态度虽有些严肃,却平易近人。他微笑着,跟节振国打招呼,亲切地在热炕上让出地方给节振国坐,说:“哈哈,早上见过面了!我的布并没被人抢走。我那么一来,就把矿警带走了!”
胡志发和节振国也不禁哈哈笑了起来。
谈话中,节振国了解到老周名叫周文彬,是从唐山来的。周文彬和节振国一见如故,他们很快就热烈地谈起了当前的形势。
老周大口大口抽着烟。云雾似的浓烟,袅袅地从他那沉思的目光中飘过。他说:“抗日战争进行已经八个月了。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进入主要地位。共产党和八路军决心坚持华北的游击战争,来捍卫全国,钳制日寇的进攻。八个月来,国民党丢失大片国土,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无法动员全国人民来抗战。我们在鬼子铁蹄下生活,当然痛苦,但共产党是民族的救星。我们跟着共产党干,一定能为国雪耻!”
节振国想:老周一定也是共产党!他听着老周的话,眼睛发亮,心里十分带劲儿。这些年,在他心目中国民政府像一座破庙,蒋介石像是这座破庙里供的凶神恶煞。说他不存在,他过去总是青面獠牙站在那儿震慑老百姓;说他存在,他今儿把东三省拱手给了日本鬼子,明天又让冀东像一张荷叶饼似的囫囵吞进了日本刽子手的嘴里,后天又断送了平津、华北。听了老周的话,节振国浑身热血都沸腾了。天很冷,他敞开了怀,脸上发烧,只觉得自己的心同老周、老胡的心贴得那么紧,那么紧……
胡志发就着烧炕的火熬了一盆玉米粥。他放下烟袋杆,下炕拿了三只粗碗盛满了粥,又拿出放在炕口烤热的几个红高粱饼子,递给周文彬和节振国。他们边吃边谈,听着老周从冀东六百万同胞在膏药旗下受煎熬谈到矿工的痛苦,又从矿工的痛苦谈到当前的斗争任务。老周说:“根据我的观察,这次你们如果挂队罢工,目的很明确:一是工人实在生活不下去了,需要通过罢工增加工资、废除井下记工制等不合理制度;二是现在鬼子侵华要把开滦的煤拿来军用,罢工可以打击日本鬼子,罢工也可以提高工人反对帝国主义的觉悟。你们看我说的符合实际吗?”
节振国点头说:“你说得很对!工人太苦了!这儿流传着这样的话——‘井下阎王殿,出煤拿命换。’‘丈夫下窑,妻儿抱瓢,衣不蔽体,沿街乞讨!’‘十年一件破窑衣,井上井下身不离。’‘男的死在矿井底,寡妻卖到火坑里!’……英国毛子、包工大柜、查头子像大山压在工人头上,现在还要受鬼子和汉奸的欺侮,矿工怎么能忍受下去!?”
老周点头继续说:“正因为工人已经动起来了,所以说现在赵各庄矿罢工的时机很好,条件已经成熟。”他扳着指头分析道,“现在有很多矛盾可以利用。鬼子跟英国毛子有矛盾,因为鬼子想夺取英国在开滦的矿权。包工大柜同开滦资方也有矛盾,因为开滦资方打算取消包工大柜,好直接向工人进行剥削和奴役;矿方增设了井下牌子房,包工大柜就不能吃黑工。连商人也跟矿局有矛盾,矿局要办消费合作社,会夺去了商人的生意。当然,日、英之间有矛盾,镇压工人还是一致的。不过我们可以很好地利用各种矛盾,使鬼子不会一下子就来镇压,使包工大柜和商人多少也能支持一下工人,使罢工能够胜利……”
周文彬的话打动了节振国。节振国觉得周文彬像《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打仗前会神机妙算,能有条有理地分析敌情,忍不住说:“老周,你怎么对赵各庄的事儿知道得这么清楚?”
周文彬笑了,说:“我来赵各庄已经好多天了!我来,一是为了摸清这儿的情况;二是想同老胡和你见面商量商量,听听你们的意见。你苦大仇深,在工人中有威信,现在矿上有些坏人也想出来领导工人罢工,罢工的领导权太重要了!你们一定要掌握!”
节振国忍不住问:“老周!你是干什么的?”
老周笑笑,说:“以后告诉你,行吗?”
节振国心里更明白老周一定是共产党了!他知道,这种事不该问,问了老周也不会说,就不再问,只是更加详细地把矿上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讲给老周听。
外边天色墨黑,屋内灯光昏黄。一个罢工的计划逐渐酝酿、形成着 ……
约莫九点多钟的时候,周文彬站起来,说:“该谈的我们都谈了,我该走了!”
虽然相识不久,他和节振国彼此已经十分信任。节振国对于他信任的人总是表现得特别热情,他说:“这几天外边风声挺紧,常有保安第三署的人巡逻。我来送你绕小道出庄口!”
周文彬点头同意。胡志发没有送,只轻轻叮嘱节振国出去时小心。
天上挂着一弯冷月。外边静静的无人。到了胡同口,在竖着石碑的地方,周文彬忽然停住了脚步,手抚石碑,说:“老节,这块碑上的诗你读过吗?”
节振国在月下看着老周锐利的双目,点头说:“读过!”
周文彬若有所思地说:“诗是古人写的,但写得很好。‘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现在我们不正是在寒冬黑夜里吗?要让春天来到,要让火光照红照亮夜空,意境多好啊!为了我们中华民族不再受帝国主义蹂躏,为了使咱们的穷兄弟都饱暖,我们就该当像煤炭一样,‘不辞辛苦出山林’,燃烧自己,放射出光和热,使人们得到温暖、光明!你说是不是啊?”
老周的话像磁石似的吸引住了节振国。节振国听了,心里像有热腾腾的火焰燃烧,不禁想——老周讲得多好,多有意思哪!坦率地点头说:“对!”
周文彬怕人注意,故意绕进僻静的小道,低头匆匆走着,老是跟节振国离开几步,保持一定的距离,直到走出了庄口。分手时,他紧紧握住节振国的手,恳切有力地说:“老节,听说共产党八路军的部队快挺进到冀东来抗日了!敌后的游击战一开展,武装斗争火一样燃烧起来,咱们冀东的局面会不同的!这次酝酿的罢工,实质上是一次反日罢工!我们这些有血性的人得团结起来,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好好干!你侠义心肠,勇敢热情,在工人里有威信,要好好利用这条件!”老周的话使节振国开了心窍,使他感到有了斗争的方向。他浑身热血沸腾,特别是听到八路军要来到的消息,更加心潮澎湃。他用两只机智深邃的大眼看着周文彬,用两只手紧握住周文彬的手使劲摇了几下,向周文彬表达了他的决心与勇气,脸上带着尊敬的表情斩钉截铁地说:“老周,我一定好好干!你放心吧!”
他看着周文彬转向东南朝林西矿走去,高大的身影逐渐隐没在夜色中,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既惜别,又激动。他微喟了一声,转身正要回去,感到有一只手“啪”的搭在他的右肩上,他心里一惊,回头一看,出乎意外地看到身后站着的是一个中等个儿的年轻人,他“啊”了一声:“是你?夏连凤!”
“是我,大哥!”夏连凤含着烟卷儿回答。
夏连凤精巴干瘦,白净脸,稀淡眉,两只一眨一眨的眼睛里闪着机灵的光芒。他披一件旧棉袍,用手拂了拂额上的头发,带笑走上来说:“嗐!我在那儿打少林拳,看见你跟那个大个儿走来,我就跟上你了。你不练练武吗?大个儿是谁啊?怎么过去没见到过他?”
赵各庄的矿工,练武的很多。打拳、摔跤、举仙人担、玩石锁、耍弄十八般武器的都有。在练武的人里,节振国闪侧腾挪武功出色。他徒手同人打架,七八上十个人近不了他的身;纵身跳起来,丈把高的墙一攀就上。舞起刀剑来,白光护身,水泼不进;拉弓射箭,虽不说百步穿杨,总能靶中红心。练武的人,没有谁不把节振国当作英雄好汉的。夏连凤也在井下干活,跟节振国是拜把子兄弟。节振国老大,纪振生老二,夏连凤老三。节振国这时看到他,心里挺高兴,简单地答了一句:“一个新认识的朋友。”接着,招呼夏连凤,“老三,咱们坐下谈谈。”
夜空的月色冰凉,薄雾轻纱似的笼罩在庄外,树影稀疏地映盖在地上。远处赵各庄大街上,“燕春楼”戏园里有胡琴锣鼓声隐约传来。庄外,零零落落从西边轻轻飘来狗吠的声音。在一棵枝条粗壮还未发芽的大槐树下,他们找了两块大石头坐下。夏连凤抽着烟卷,灰色的烟从他嘴里一股一股地吐出来,散开去。
节振国忽然鼻子里深沉地哼了一声,好像要把胸膛里无穷的闷气压出去一样,对着夏连凤说:“老三,咱们非挂队罢工不可了!你们道巷里今天的情况怎么样?你听到些什么消息没有?”
夏连凤往节振国跟前凑了凑,心里有数地说:“咱们那儿的井下牌子房昨天也砸了,今天矿司又派人修了起来,大伙儿可气愤着呢!”他讲了些工人们气愤的情况,接着挤挤眼睛,扯长了声音说:“老节,快领着大伙儿挂队吧!这么窝着脖子受洋罪,可不行!要是挂队,这次是炮药房放火,一点就着!”
节振国皱着眉,思忖着朝他望望,又问:“包工大柜的情况怎么样?”
夏连凤甩手做着姿势说:“为了牌子房的事,包工大柜们也怒气冲天。杨增他们那几个大包工向工人拍胸脯,说要是为这罢工,在罢工期间,‘锅伙’锅伙:是包工大柜为了盘剥工人开的窑户铺,一般是盖的一溜溜简易的阴暗、破烂的平房。工人无处吃住的,可以在包工大柜苛刻的条件下缴款在此吃住。新招来的工人非住锅伙不可。一般先扣三个月工钱,吃住在锅伙里记账,等干够四个月才发给工钱,但仍押一个月的工钱垫底。里照旧让工人住,让工人吃。”夏连凤得意地舐着嘴唇继续讲,“听说,驻在古冶的日本宪兵队里的便衣跟咱们矿上运煤去的工人说,要是咱们罢工对付英国毛子,日本人不想干涉,说不定还能支持咱们。”
节振国听夏连凤的话越说越离了板儿,耳朵里像给什么东西蜇了似的,眉头儿圪揪着,睁大了眼朝夏连凤看了一看,挥着大巴掌斩钉截铁地说:“日本鬼子是咱们的仇人;包工大柜一向把工人当作牛马,打骂压迫,剥削欺侮,他们都不会安着好心,咱们要利用他们,可不能指望他们!”
“那当然!”夏连凤抛掉了烟头,眨了眨眼睛看看节振国的脸色,像蛐蛐瞪眼子溜须看阵势,又重新点上一支烟,突然把话岔了开去,“劳资接洽处的刘青山,这两天满嘴狼烟大话。他在工人俱乐部里对大伙说,‘我跟大伙始终一条心。无论起早贪黑,风里雪里,只要对咱们兄弟哥儿们有好处,要我去干,不说二话!’有些人已经要选他做罢工代表了!”
刘青山本是黄色工会的头子,过去在工人中尽干些吃里爬外的勾当,一方面蒙骗一部分工人,一方面讨好英国资本家和赵各庄矿的矿司陈祥善。听到这儿,节振国气愤地说:“刘青山那葫芦里卖的没有好药!”他知道夏连凤消息灵通,就又问:“还听到些什么?”
夏连凤低着头想了想,说:“今儿下午,我在小酒店里听一个喝酒的人说,如今河北、山西,共产党的游击队到处都起来了!别看日本鬼子神气活现,它是旱地里的蛤蟆——干鼓肚,没有办法;也是瘦驴拉硬屎,硬撑架子!”
节振国听见这话,突然又想起周文彬刚才说的事儿,忍不住攥着拳高挑着眉毛说:“要是咱这儿也有游击队,我一定干!出出这心头的闷气!”
夏连凤听了懒洋洋地说:“去年底,有个叫王平路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中国共产党发出“关于开展游击战争是华北全党中心工作的指示”。冀东党在九月就建立了统一战线组织——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冀东分会,会员发展很快遍及冀东各县,十二月,党在滦县多鱼屯村秘密召开会议后,王平路同志等组织了游击队,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攻打青龙县青河沿敌据点,但由于缺乏战斗经验,王平路同志牺牲。的铁路工人,听说是共产党,组织游击队,带着人在热河青龙县打鬼子,牺牲了。这种事儿我看不那么好干,还是先顾着咱眼面前矿上的事儿,给穷哥儿们挣点好处,先不去想那远的!”
节振国皱着眉像个大哥开导兄弟似的说:“三弟,不那么好干的事,该干也得干啊!”节振国的话太锋利了,两个结拜兄弟脸对着脸,一时无言。接着,夏连凤笑笑,打岔说:“就怕大嫂她不让你冒险啊……”说到这里,他忍不住又觑着眼悄声问,“大哥,刚才你送走的那个高个儿是谁呀?”
节振国同纪振生、夏连凤拜把子时,三人都盟誓同生共死。往日,节振国有事常同两个把兄弟商量,今晚也没有例外。自从跟周文彬谈过话以后,他觉得心里更亮堂了。他决定参加筹组罢工委员会,要夏连凤也帮着发动各道巷里的工人罢工。夏连凤一再问他,他觉得藏着掖着的就不义气了。他四下望望,便翻盆倒罐地把周文彬讲的话简单扼要地告诉了夏连凤,勉励夏连凤好好干。不过,他平日虽然喜欢夏连凤聪明伶俐,也喜欢夏连凤对他唯命是从,却也知道夏连凤那张嘴是个漏水的槽,不牢靠。他怕暴露胡志发,所以他把周文彬说成是自己新结交的朋友,没有提起胡志发。
听了节振国的话,起初,夏连凤脸露惊讶,眨眨两只机灵的眼睛,没有作声,后却一拍巴掌,激昂地说:“大哥,干吧!大雁要飞得有个领头的!只要你领头,我三弟跟着你飞到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