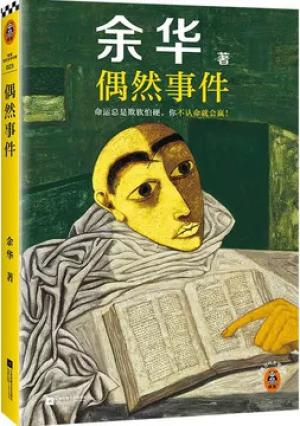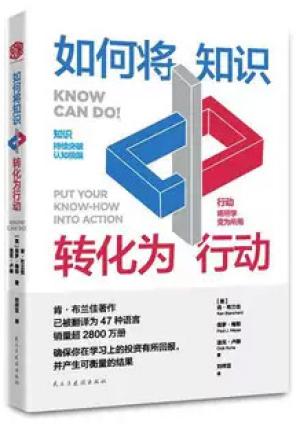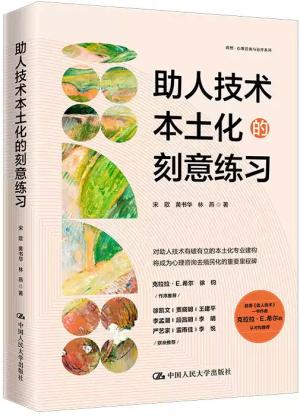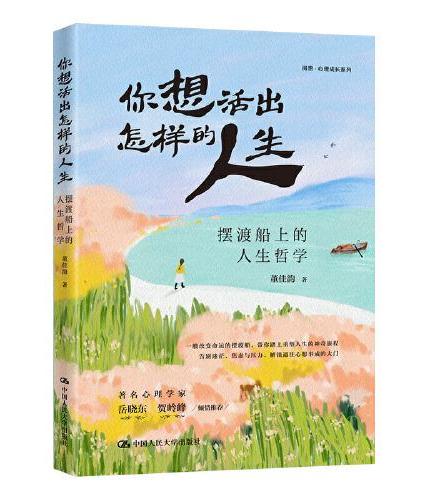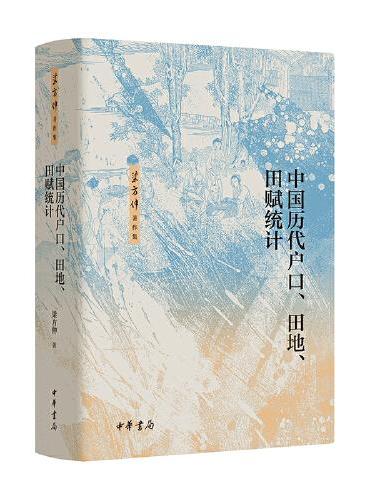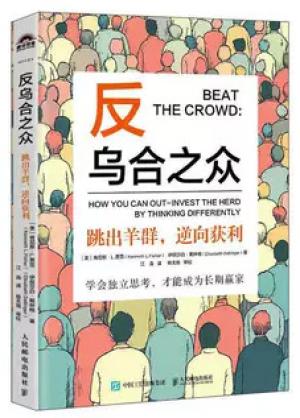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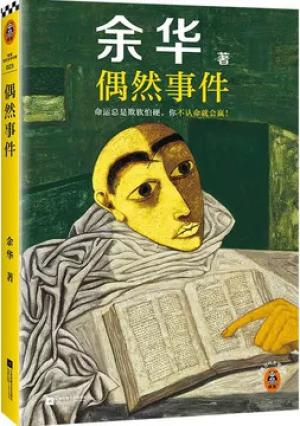
《
偶然事件(命运总是欺软怕硬,你不认命就会赢!)
》
售價:NT$
255.0

《
余下只有噪音:聆听20世纪(2025)
》
售價:NT$
95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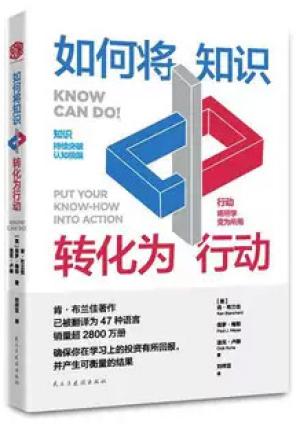
《
如何将知识转化为行动
》
售價:NT$
35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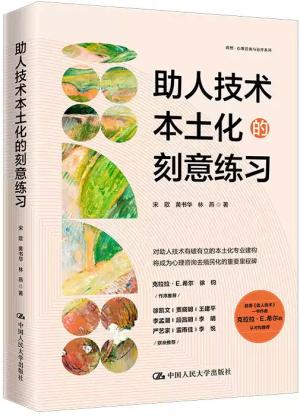
《
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
》
售價:NT$
408.0

《
中国城市科创金融指数·2024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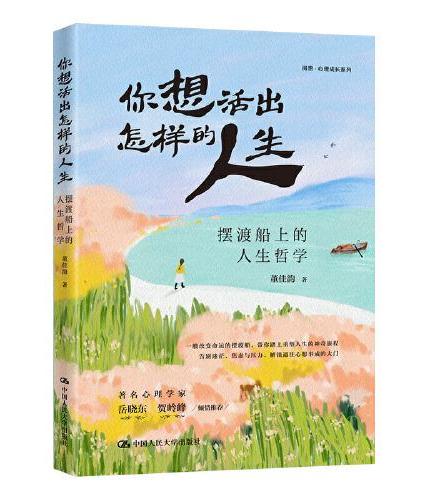
《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摆渡船上的人生哲学
》
售價:NT$
3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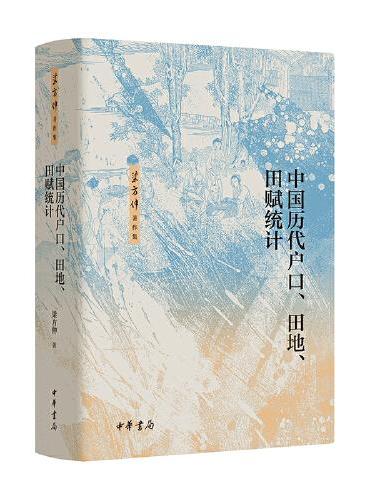
《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梁方仲著作集
》
售價:NT$
68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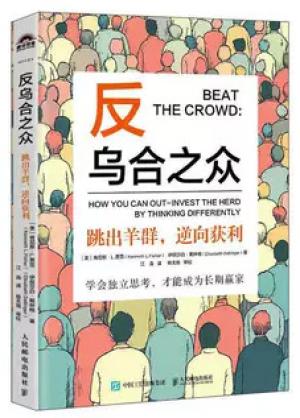
《
反乌合之众——跳出羊群,逆向获利
》
售價:NT$
356.0
|
| 編輯推薦: |
推荐语1
《岁华晴影》一书虽是散文集,却无处不体现出周汝昌先生治学注重“活”“悟性”、“文、史、哲会通”的一贯宗旨。欣赏文章篇幅短而内涵深远的概括力,“活而不板,能放能收”的灵活性,能三言五语说到“点子上”的“片言居要”之功夫。
推荐语2
从这本散文集中,可看出周汝昌强调更重要的还是“好头脑好心灵”的悟性;既对读书“浮光掠影”“深悔自愧”,又警惕“书厨”式的死记硬背。应该说,这是贯穿周先生一生的治学之心得和经验,“绣取鸳鸯从君看”并不想密藏啬敛而切望“度与人”的“金针”宝典。
推荐语3
中华文化的“慧命”,就是通过红学家周汝昌先生身上“学术成就”与“文采风流”的辩证统一,而得到体现,这就是周汝昌作为一个中国文化人的文化意义。
推荐语4
《红楼梦》书迷之书。自乾隆至今,《红》迷数不胜数,《红楼梦》到底养活了多少人难以估计,《红楼梦》之所以受追捧,是因为写尽了人学,一个把《红楼梦》研究到骨子里的红学家,在耄耋之年写出了这部平淡之中见深长的“满汉全席”式的散文集,文化大家的灵心神笔、喜怒哀乐、海纳百川尽显其中。
|
| 內容簡介: |
|
《岁华晴影》是著名红学家周汝昌的随笔集,全书辑选了作者随笔精品88篇,大致有读书治学、自我观照、讲“红”说“梦”、追忆故交、前尘往事、文化反思几方面的内容。《红楼梦》书迷之书,一本“满汉全席”式的散文集,满足你对古代传统节日吃喝玩乐的好奇。
|
| 關於作者: |
|
周汝昌,天津人,中国红学家、诗人、书法家,是继胡适等诸先生之后新中国红学研究人,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被誉为当代“红学泰斗”。
|
| 目錄:
|
随笔与掉书袋_ 001
读书似水能寻脉_ 006
文采风流_ 009
对待书的方法和态度_ 013
读书与治学_ 017
艺术古今杂话_ 022
八旗文赞_ 028
漫话“工具书”_ 031
诗文化_ 033
文之思_ 037
诗人什么样子_ 041
悲剧性人物——漫画家_ 044
潇洒意如何_ 047
羡鱼_ 051
谈笑_ 055
谈哭_ 058
挤和捧_ 062
虚字和实_ 066
念半边字及其他_ 070
京剧之思_ 073
缘话_ 079
多少楼台烟雨中_ 083
逢年到节系人思_ 087
太原随笔_ 090
女士颂_ 094
四通八达百和祥_ 099
新秋漫笔_ 101
妙语与妙人_ 105
毫厘之差_ 109
不悔——知愧_ 113
少年书剑在津门_ 120
何限深情_ 124
我和胡适之_ 131
自家的癖性_ 137
我与“红楼”有夙缘_ 141
我的笔_ 145
看画与观化_ 149
《三国》补诗与《西游》骈语_ 154
岂敢岂敢_ 158
“恨水两埋肩”_ 161
青石板的奥秘_ 164
雪芹曾客“富儿”家_ 169
长安·种玉及其他_ 172
普度寺·福佑寺·克勤郡王府_ 176
龙年与曹雪芹_ 178
雪芹遗物_ 183
红楼竟亲历_ 187
上元佳节访芹居_ 191
“红楼”本是燕京典_ 193
从红楼到康熙_ 196
绛珠草·文化教养_ 199
不敢提芹字字清_ 202
世事无如纠谬难_ 204
“六朝人物”说红楼_ 207
潘霍芬与太虚幻境_ 210
雪芹·水星·红祠_ 213
芹庙·芹像·红楼升官图_ 216
藕香名榭在津门_ 220
万安山访古刹_ 223
太平湖梦华录_ 227
字比巴斗大_ 233
金陵红楼女_ 242
翰墨缘_ 245
什刹海边忆故交
——记张伯驹先生轶事_ 248
黄裳·我·红楼梦·水西庄_ 251
“真”亦可“畏”
——吴宓先生史片_ 255
中华文化八千年_ 260
世间曾有这么一个人
——悼亡兄祜昌_ 264
黄氏三姊妹_ 269
海外红友小记_ 273
渊渊鼓音_ 280
海大道·柳劫·皇会_ 286
曹寅题画与天津鉴藏家_ 291
王维·年画·美容院_ 294
《岁华纪丽》与“热爱生活”_ 298
图书馆·齐如山·《红楼》秘本_ 303
哈门鸦儿的_ 307
老掌柜的_ 311
黄叶村·小蒸食·蒲包_ 315
腊鼓催年 人天同庆_ 319
因粽叶想到“人大”提案_ 324
“对对子”的感触_ 328
教学是一门艺术_ 331
岂止“胜读十年书”
——读唐君毅先生论中西文艺精神之不同而有感_ 337
翻译的慷慨和“乱来”_ 342
深刻的不幸_ 345
读“史”有感_ 349
城·红楼茶社·三毛_ 352
佳节话清明_ 358
校后记_ 360
编后缀语_ 363
|
| 內容試閱:
|
序
我们中华文献自古分四大类,名为“四部”“四库”,即经、史、子、集是也。经史不消多说自明,倒是子与集如何区别,值得弄个清楚。我引光绪二十三年(1897)严复与夏曾佑二先生合撰的《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中的几句话:“书之实欲创教而其教不行者,谓之子。书之出于后人一偏一由,偶有所托,不必当于道,过而存之,谓之集。”可见集是够不上哲士贤人之言、没有足以创教济世的大道、而只记下些零星的一偏一隅之见的东西,——扔进字纸篓又觉心疼,于是“过而存之”罢了。
过而存之呀,怎不先就让人脸红。
我从初中时代十四五岁时喜弄笔墨,积习甚深。在报纸上发表小文,为时也是很早的,今皆难寻。以后作了“考证派”,写些“论文”,而诗词随笔等“非论文”实亦未曾停笔,所积数量实在不小,但大抵随缘信笔,寄兴抒怀,根本无意为文——也够不上“文”的真规格。信笔漫谈的“信漫性”太强了,就不免落于草率粗疏,很少是精心措意、经营缔造的用功之作。
但近年忽蒙《光明日报》的韩小蕙女士——散文创作、编集、评论专家——在报上发文,把拙文列入“高境界”等级内,与季羡林先生诸前辈“平坐抗礼”,可真使我汗颜而内愧!这实在是她的偏爱与谬许。我很感谢她,人都会因有赏音而欣幸喜慰,文人尤甚——于是我也因此进入了“文”坛。幸甚至哉,愧甚至哉!
这本集子收录的,有一部分是我早年写就的。因年深日久,自己赋性散漫,没有一点儿条理性,破书残稿乱极了,有些旧文是连记都不记得了,记得的也无法找全了。这就定会“遗珠”,而编收在此的更难免“滥竽”之叹。明眼高人自能鉴之。
此外,有一部分是在编辑时新写的,未曾发表过。
编时原则有二:一是不修饰“加工”,一一存其历史本真。例如《黄氏三姊妹》,把二姐与三妹两个人的芳名都弄颠倒了,以致有“饥凤”先生在成都报上为之补纠,我对此另加注,文中则不做改正——因为一改就失了真,而人家的纠补也落空了,那是不对的。
第二是“尽力”校正原刊时的错字、漏字与被人改坏了的字法句法、文理与音律节奏——汉字文章是要讲这些的。我平生所发文字,刊出时几乎百分之九十九是带错刊误植的,有的令人啼笑皆非,行家也会哂我“不通”。但“命”中注定,办法不多,常以为“恨事”。今次乘此机会,应该消灭补正那些了吧?
书名取《岁华晴影》,因为我很喜欢“岁华”二字,它就是人生的佳境。至于“晴”,我从幼年就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开始自学作七绝诗就有一句“檐牙小雀噪晨晴”之句;后来把“词集”题名曰“晴窗语业”。近年给报纸写专栏随笔又叫作“响晴轩砚渍”。这番晴意,大约与生长在北国的晴空高爽的气候里大有关联。
岁华是流转不居的,秦郎少游的佳句“东风暗换年华”就写得特好。既然它是流转的“逝水年华”,所以只能用笔来叙写一些偶然可以捕捉的影子。既是影子,于是它总在清晰与模糊之间,似有如无之际。何况“文不逮意”,古人早有此叹了。就连曹雪芹也自称“未学无文”,则可见要想为岁华留影,谈何容易——须学,第二须文,而我之“学与文”,比之前代文星,那又该用何言何语来“自云”呢?
再有一点,不怕您见怪:我根本不喜欢胡适之先生平生至极得意的“白话文”,因为“白话”实不成“文”;而强名为“文”,尽失中华汉字文章之大美至味了,这种想法大约很“荒谬”吧?而自己也只好写些“白话文”,真是自相矛盾,“违心之文”,既可笑,又可叹。
这样写“文”,它能好得了吗?
但世上万事有缘,我这种无学不术的“文”,居然也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春瑜先生的谬识,他定要我选编一本“文”集。这真让我惭感交加,非常感谢他的至意高情,也益发“自惭‘文’秽”。
因双目俱损,工作艰甚,此一小册之编整缮录,亦须女儿助手伦玲出力,出版社责编以及校对、美工等位贡劳者,在此谨表谢忱。
校后记
病目校书,十分吃力,女儿又助校一遍,希望“基本上”消除了作稿、缮录、排字……等工序中出现的误字误句。“校书如扫落叶”,古语不虚,难保已无“漏网”的残“鱼”,深盼读者发现时赐示,以便改正。
在此附带解说几处并非误排的——或者说是“文义”上的事:
“掉书袭”,掉的本义是摇晃、摆动,引申为显示、卖弄一类意思。书袋,古时书是卷轴,分用袋装,叫作“帙”,俗呼书囊。掉书袋是显弄书多,与“掉进袋里”无关。拙文中有一处故意借用现今“掉”的另一俗义,不过是一种趣语,请勿误会。
“巴斗”,似多写作“笆斗”,我引用的是复印本原字。笆斗,柳条编的农具,个头儿很大,容粮米甚多,故以“大”显名。
“够呛”,北方俗语,呛是“吃”的打趣语,够呛犹言“够受的!”,即“难以消受”“苦于承当”之意,“汉文章”,语称“西汉文章两司马”,谓太史公与司马相如,皆前汉人也。若“汉文章”,应包两汉而言,故拙文举司马迁、班固为例,不必拘看。
《谈笑》篇写时本意在于借此小例以展示我们汉文的语汇之丰富而愿今之为文者能够多读些书而不致文词十分单薄贫瘠;但文体是半庄半谐的。未料后来选入中学教材书中。近一位教师惠函指教,指出此文的许多“文病”,如“证明了”须改“表明了”,“吧”后要用“?”,等等。他是善意的,但经他一“改卷”,文趣全失,话也死板了——这是不明“文各有体”之故,而要“规范化”。文字的风格与风趣,只在分寸之间,把它消灭了就不再可读了。
万安山访古刹,据同游的刘女士(现在日本教学)说,我把时日记得不尽准确。但已无法追查改正。
“红楼升官图”,近北京竟发现了宫内所传彩绘本,是一位满族老人之家藏。报纸上称之为“红楼梦棋”。附记于此,读者或感兴趣。
《太平湖梦华录》中提到一个石羊卧于古城墙与护城河之间的茂草之中。后来方知,西便门外的石羊,乃是北京九门古文物的一项名品,我们所见的,即此无疑了。
《雪芹遗物》中所叙旧砚,镌有“千山老芹”之疑识。假若此疑不是伪造,则必又有人据此“考证”曹雪芹祖籍了。按曹寅诗集曾署“千山”,实为当时汉人身隶满洲包衣旗籍(旗奴)的避讳含糊之设词隐语,并非实指某一地点,正如也署“长白”“满洲”,其义无异。已有学者指出,从古之辽阳籍人氏,绝无自称本贯为“千山”之例,岂可以此二字为实际地名?其说是。拙文是随笔,原不涉“论文”之事,但恐因此又生是非纠缠,故略为解说于此。
周汝昌
丙子重阳佳节前
编后缀语
这本书,初版于1997年初,至今已经过去了25个年头。如今蒙作家出版社厚意再次印制精美图书,不胜感慨系之。
那是1996年,父亲收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春瑜先生的来函,告知东方出版中心拟推出一套《当代中国学者随笔丛书》,因常读父亲文章,以为年高事繁,却能写出大量随笔,表示赞叹;还说父亲的随笔,深受读者的喜爱,因此希望能将文章选编,收入这套丛书中。父亲十分感谢王先生的这一番厚爱至意,就答应了下来。而这一任务,他的目力已难做到,就落在了我的肩上——当然这是责无旁贷的乐为之事。
父亲的“美名”是“红学家”,罩在他这“红学家”头上的,是一顶“考证派”的帽子。父亲为此遍尝了嘲骂与讥讽。他对红学的贡献,自有公论,不是二三人所能左右的。父亲的诗学、红学,在十几岁时就埋下了深深的种子,待根深叶茂,挺拔高大,直插云霄时,什么“桂冠”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然而不为人知的是,他在研红之外,还写了大量的信笔漫谈,寄兴抒怀的文章。五十年代,他就为《人民日报》《文汇报》写过一些这类文章,还写了一些例如《学书杂语》《退谷》《板桥逸文》等短篇文章,后刊载于《春游琐谈》一书中。六十年代,他又为《光明日报》《大公报》《中国妇女》等撰过文章。1962年陆续发表在《天津晚报》上的一组《沽湾琐话》,可以说是他在这方面的一个“多产”时期。“文化大革命”初期批判“三家村”时,吓得他把“琐话”交出来接受“审查”,万幸没有当成“黑话”。
进入八十年代,父亲的创作状态可谓“如日中天”,他不仅出版了几部专著,在极为艰难的目力下及繁冗杂事之中,写了几百万字的学术论文,还为几家报纸、杂志分别开辟了《响晴轩砚渍》和《七十二沽人语》等专栏。九十年代,又写出了一批很受读者注目的随笔文章。
父亲的这类文章数量很大,每一篇都是对中华文化的阐释、热爱,更离不开对“红学”的执著。 我从一个“先睹为快”的“读者”来看父亲的这些杂文,有一特点,即真正是名副其实的“信笔”,文章是从他笔下“流出”的,写得很快,很自如,不苦思冥索,更不打磨造作,如行云流水,而无“八股”气。这样行文,是他的主客观条件造成的习惯,也许不免一个“率”字:不精不细,但好处就在一个“真”字上。有一位朋友曾特言:过去之文是功力,近来之文是升华,父亲则说:岂敢当此!
我还清楚地记得1996年年末,父亲突然得了一场大病,来势凶猛而重,高烧不退。1997年1月28日,我们取到《岁华晴影》,送到父亲手边时,他很高兴,还写下一首诗:
丙子腊二十为五九第三日病始愈值沪寄《岁华晴影》文集亦到因赋诗纪之
五九六九河边柳,大化生机浩荡春。
我独病中吟好句,谁能枕上作闲人。
民间药物皆神圣,故里年光想焕新。
欣喜岁华晴影丽,刊成吉日贺良辰。
初版书原是作为父亲八十寿辰的庆典礼品。如今手捧这本精美图书,父亲的灵心神笔,他的喜乐哀怒,他的海纳百川……流连回转,难以逝去。
父亲逝世十周年,我把《岁华晴影》放在墓前,作为好的纪念。
感谢作家出版社,感谢责编刘潇潇、单文怡两位女士,感谢为本书贡力之全体同仁。
周伦玲
壬寅二月十二花朝日
岁华晴影
随笔与掉书袋
随笔与掉书袋,好像天生不相合套,有点儿“矛盾”——在“子平学”中就是“犯六冲”的关系。既曰随笔,那何必诗云子曰,引经据典?若一繁征博引,那“随笔味儿”即使不变,也要大减了。它们两“家”难以并存是真的,虽然说不上“势不两立”。
有些人一听掉书袋就摇头——也许摇头是头疼的一种“表现”?所以愿意听“随笔”二字。更多的人是嘲笑掉书袋,连大词人辛稼轩都因此而“虚心接受”了岳倦翁的“批评”,真是其来尚矣!
那么,掉书袋这“东西”就注定是坏的了?
我看也不一定。谁叫咱们中华的文化如此悠久而丰富得惊人呢?从秦火焚烧,以后的无数的浩劫,到今日的书还装满了亿兆的“袋”,则又何怪乎一不小心就“掉”进去了?
只要不是为了卖弄炫耀,在需要的时候掉它一掉,应该是“无可厚非”,未必那么可笑甚至可怕,避之如洪水猛兽。
掉书袋,也不一定非具“形式”“体例”不可,比如列出某书、某题、某册、某卷、某页……一大串,清楚明确(也用以表示“目验”而非“转贩”,其实,标明出处的转贩更多);不具“形式”“体例”的掉法儿也不胜枚举。胡适先生反对“用典”,就是反对掉书袋。但是当他自己说他当年的文学革命是“逼上梁山”,这又算不算掉书袋与用典?且不必说“梁山”一典,就说“革命”吧,如果不是汤周武很早“革”过桀纣的“命”,那胡先生自己用的“革命”一词,又从何来?难道可以说是他自创的“革新”的“白话”?
说到这个词,我想起被关在“牛棚”时,因晚上要吃药,向那位看守的“革命派”姜公申请拿药瓶儿(那是必须放在外屋,现吃现要,我屋里是任何“身外之物”不许有的)。他恶狠狠地吼道:“这不是疗养所,我们是革你的命!”我听了心下暗想,原来我也与纣王有同等的身份资格,岂不大哉。
说到随笔,其实不管你如何地“随”——随时、随地、随事、随境、随想、随感……也还是不知不觉地要掉几回书袋的。小例不用多举了,我只说一句总话吧:我们中华的汉字,即大家写“随笔”用的文字,它本身就是一个特号的大书袋。你不掉进它去,那你文章怎么写成的呢?
随笔的“随”,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对不起,我这就先得一掉。
书袋是汉代大师许慎在《说文》里说了的:“随,从也。”
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跟着走”。好比排着队次第行进,你不能掉队,也不能挡碍后边的人走,更不能“走自己的路”——所谓“另辟蹊径”,那就不是随了。
因此,随也就有了随顺、随和的含义。
这不有点儿太“被动”了吗?不然的。据《易经》上讲,“随”乃第十七卦的卦名,震下兑上,是个吉卦。儒师的解释说,随有两重意蕴:一是让自己随从众人,二是让众人随从自己,谐和团结,都为大家的公益,而不为个人的私利。这种精神可太好了!一点儿也不是个“被动”的问题。
那么,无怪乎《易经》说是“随之时义大矣哉”了。
既然如此,则敢来写随笔的,可不是“闹着玩的”,其意义价值就值得重新估量,刮目相视了。
自己跟着人走,而又不等于“被动”,那必然就是心里明白所跟的前行者是个正确的真理正道者。这就不是甘做糊里糊涂的盲从奴役。而能使众人愿随自己而行,又必然须是你自己也是个讲真理正道的人,因为众人也不低智,即不会盲从你。
如此看来,我们的这“随”,确非“随随便便”或者“随心所欲”的小事一段,实乃“人际关系”的事,群众之间的事,亦即社会生活的一桩大事。把“随”看小了,“随笔”的市场价格也就不值大钱了。
我说这话,千万别误会,以为我是对随笔的“稿酬标准”有所不足而借题发挥,小题大做。
旧时在戏台上拉胡琴的,鼓书园子里弹弦子的,都没有福分享到今日的美称,叫作“伴奏艺术家”,只叫“随手”——梅兰芳先生的文章里就还这么用。虽说是“随”,可要紧极了,比如梅先生他若没有徐兰沅、王少卿,简直唱不了戏,更成不了名,他没有笛师马宝明,他怎么唱得出那么优美动人的《奇双会》?有一年,尚和玉这位长靠武生大师到天津的天华景戏园去演出,一出拿手的绝活《挑滑车》,那靠把武功架势气魄就不用多说,单说那唱,是昆曲牌子,随手是唢呐小海笛,一曲《上小楼》,“遥望那杀气天高……”真是揭响入云,令人意气昂扬激越,慨慷击节而唤“奈何”!然而你别忘了那位吹唢呐的。他平时只拉胡琴,坐台的开场戏,都是他的活,那胡琴真叫无精打采,听了让人昏昏欲睡——谁知他一给尚老吹唢呐,那全副的精气神,都透出来了!那份儿精彩,使得尚老的技艺更显神威十倍。由此例(还有很多可举)可见,这“随”可不只是个简单的可有可无的“附加物”,它是一种骨肉、鱼水的关系。也由此我才懂得,中华古语“夫唱妇随”,绝不意味着妇只是个“百依百顺”的应声虫,那“随”乃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道理。而人们往往误解了真义。
人们说“随分守常”。鲁智深唱《寄生草》说“芒鞋破钵随缘化”。佛门还有一句话叫作“随喜”,也很有滋味可寻。
这实在够不上“书袋”的规格,可我已经掉了一番。虽不免为大雅方家所哂,毕竟给“随”添了点儿颜色。随笔之身价,是否能因之稍加尊崇?实在难保;但在我自己来说,则书袋虽不广不深,倒是掉过之后比原先的“水平”提高了一些:原先只以为随笔者,和“闲聊”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间耳,如今却觉得“随笔”的“随”非常重大起来了。书袋给随笔撑了腰,谁曰不然。
“笔”呢?又怎么掉法?这也大有来历,孔圣曾云:“笔则笔,削则削。”也翻今日之言:该写的写;不该写的,写了也得删去。
这多么好!“随”了之后,再来“笔”之于纸,才可称为文章,而这里面也包含了削的工序,外行人,哪得知哉。
书袋本身,其实并不总是可怕可厌,可怕可厌的只是那“掉”者若是个冬烘腐儒,本来好好的书袋也被他掉得一派酸气、腐气和架子气。
若是真有能掉得风流潇洒的能手才人,那就不但不嫌他掉,还巴不得他多掉一番,也是一种“美学享受”,开心益智——我的话题范围当然还是“掉书袋的随笔”,不涉其他文体。
——可是,到哪儿去寻这种风流潇洒的“书袋随笔家”呢?我满怀虔敬,盼望能多遇到一些,盼望这些也能被认可算为一个新的“随笔流派”。
读书似水能寻脉
1954年之春末,我奉特调由成都四川大学回到北京。川大历史系老教授、诗词名家缪钺先生深怀惜别之真情,作有七律一章见赠,其中一联写道是:“读书似水能寻脉,谈艺从今恐鲜(xiǎn)欢。”
他赞称我的话,实在愧难克当;但读书要能“寻脉”,却是我们两人(忘年之深契)治学上彼此的交流体会,不同于泛泛之词,俗常的套语。
读书要能寻脉,至少有两层意义:一是从一部书来看时,要理会其间的首尾章法,起伏呼应,萦回曲折,放收擒纵,开合跌宕……此为行文赏笔,明义识旨的必由之路,书中有脉,隐显无常,含露不定——是以贵在能寻,方不迷惘。
二是从多部书之间的承传演化关系而寻其脉络,识其意旨。比如说,以《红楼梦》这一部书来说,那要寻起来,其来龙去脉就太丰富了!
先说“去脉”。雪芹之书一经问世,仿、续、补、翻……之作纷纷出现,至于不可胜数(至少可列七八十种之多)!那从嘉庆初年开始,络绎不绝。迨到《镜花缘》《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海上花列传》这几部出名的书,没有一部不在“脉”中——李汝珍写一百名才女,是正面效颦;文康是反面“对台唱戏”大翻案;刘铁云金针暗度,遗貌取神;“海上花”揭题“列传”实实得雪芹本怀——因为《金陵十二钗》这个题名之后面原是省去了“列传”二字的(雪芹原书写百零八位不幸女子的“列传”,十二钗仅仅是以“正钗”为代表之义)。这都分明清楚的。
但若回过头来再寻“来龙”,便更有意趣了。早有汉代刘向,创了一部《列女传》;到晋代皇甫谧,他又撰出一部新的《列女传》。这就都是雪芹要写他自己赞美、悯惜、悼念、愤慨、悲痛的一大群“列女”的真正源头启示。
如若不信,那么请君一读清代记载戏剧演员的《燕兰小谱》吧,著者还要正式说明,其选列的人数为何是“七十二”?那是从《列女传》而来的。
中华的“七十二”,是个文化象征数字,意思是“很多很多”,不要拘认是个实数。七十二是“九”的八倍。“九”已代表多了,故“四九”三十六与“八九”七十二都运用到《水浒》里去了。四九加八九,正得百零八位——《水浒》《红楼》,皆取此义(四九、八九,共十二个九。九为阳数,十二为阴数)。
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妙谛,如今能理会古代作家的文心匠意的读者也渐渐少起来了,所以对“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十二正钗”“九十六副钗”的涵义也就莫名其妙,囫囵吞下一个个的大枣罢了。
本文以“数”讲“脉”,其他可悟,所谓“隅反”之理,自不须絮繁琐琐逐一详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