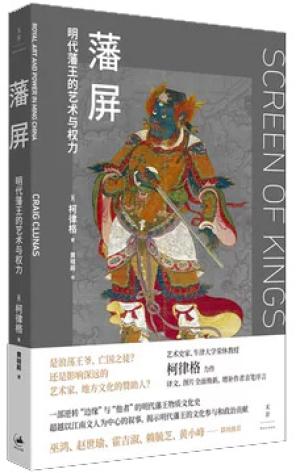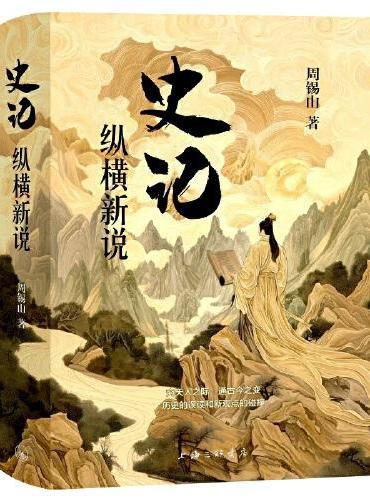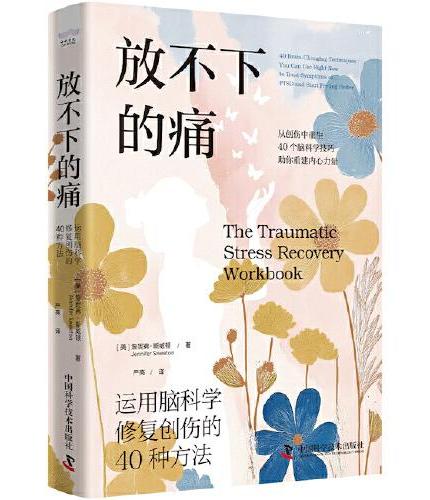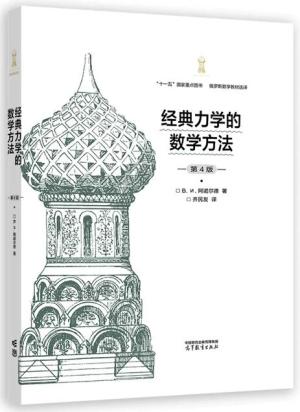新書推薦: 《
藩屏:明代藩王的艺术与权力(柯律格代表作,一部逆转“边缘”与“他者”的明代藩王物质文化史,填补研究空白)
》 售價:NT$
551.0
《
《史记》纵横新说
》 售價:NT$
305.0
《
放不下的痛:运用脑科学修复创伤的40种方法(神经科学专家带你深入了解创伤背后的脑机制,开启全面康复之旅!)
》 售價:NT$
305.0
《
经典力学的数学方法(第4版)
》 售價:NT$
403.0
《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跟随历史的足迹 见证一个民族的觉醒与抗争
》 售價:NT$
305.0
《
功名诀:左宗棠镜像
》 售價:NT$
908.0
《
布克哈特书信选
》 售價:NT$
439.0
《
DK园艺的科学(100+个与园艺有关的真相,让你读懂你的植物,打造理想花园。)
》 售價:NT$
500.0
編輯推薦:
本书部分内容已于2021年改编成热门纪录片《消失的达·芬奇》(The Lost Leonardo)在国外上映。本书细致研究了达芬奇的艺术创作、个人生平及其油画《救世主》的神秘起源与真实性;从英王查理一世的艺术收藏宝库开始,生动描绘了艺术品收藏与交易如何发展至今,以及与艺术始终相伴的金钱游戏、权力斗争,背后更牵扯出站在艺术界、收藏界、政治界金字塔顶层的人物。书中深度访谈的对象包括:油画《救世主》的发现者、修复者、持有者,包括马丁坎普在内的众多达·芬奇专家和艺术史学者,英国国家美术馆、法国卢浮宫、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等艺术品收藏殿堂的负责人,以及佳士得拍卖行、苏富比拍卖行、俄罗斯寡头、中东皇室等艺术品交易圈中的大腕。作者通过调查取证,获得了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构建起油画《救世主》完整的藏家史。39幅彩插,全面展示达·芬奇油画《救世主》在发现、修复、拍卖等不同时期的状态;另有文艺复兴时期《救世主》的各种仿画、《救世主》不同时期的持有者照片、画作拍卖现场等精彩图片。超大尺寸封面折叠设计,展开即为达芬奇4.5亿美元油画《救世主》的同尺寸海报。200多年来,艺术史学家和收藏家一直在徒劳地寻找艺术史上的
內容簡介:
2005年,达·芬奇的油画《救世主》重现于世,在美国的一家二流拍卖行被人以1175美元购得。辗转于画廊、修复室、博物馆、自由港、拍卖行之后,2017年,《救世主》以4.5亿美元的创纪录价格成交,顶着“男版蒙娜丽莎”“世界最昂贵画作”“最后的达·芬奇”等头衔,再次隐匿。
關於作者:
本·刘易斯,英国艺术评论家、作家、纪录片制作人,伦敦沃伯格研究所访问学者。刘易斯拥有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历史和艺术史硕士学位,曾在柏林弗雷大学学习。他为包括《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在内的众多国际媒体撰写了大量艺术、文化评论文章,摄制的多部纪录片获奖。
目錄
序 言 达·芬奇传奇
內容試閱
序 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