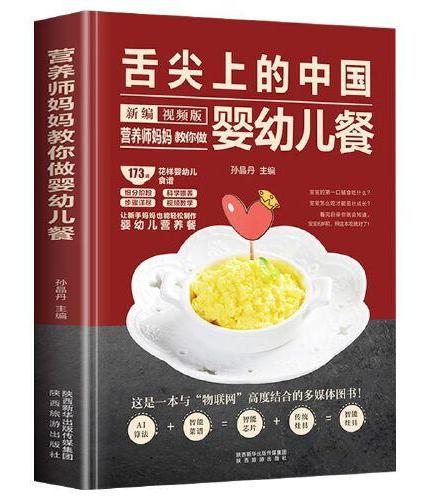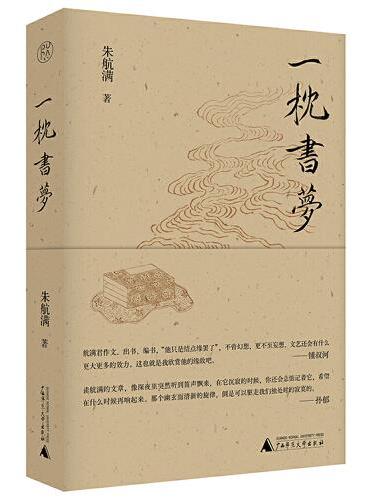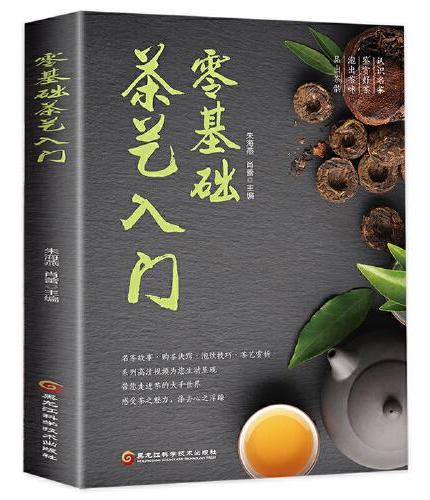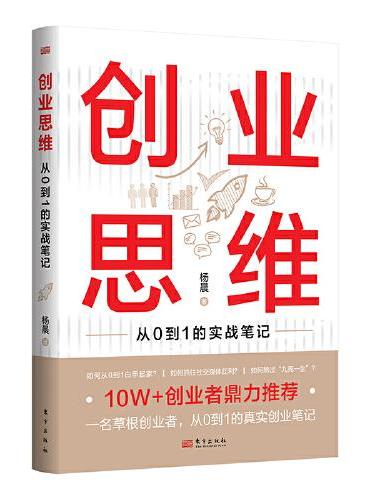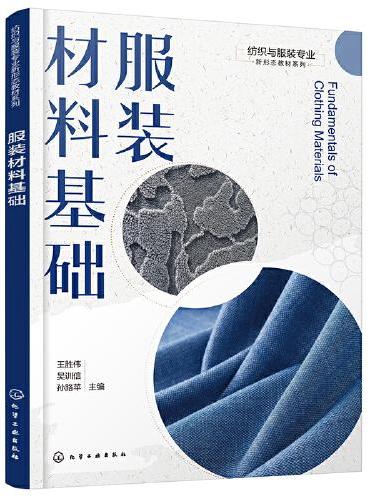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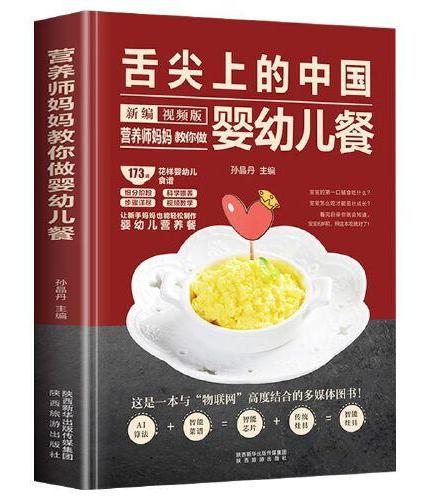
《
舌尖上的中国新编视频版营养师妈妈教你做婴幼儿餐
》
售價:NT$
296.0

《
Scratch创意编程进阶:多学科融合编程100例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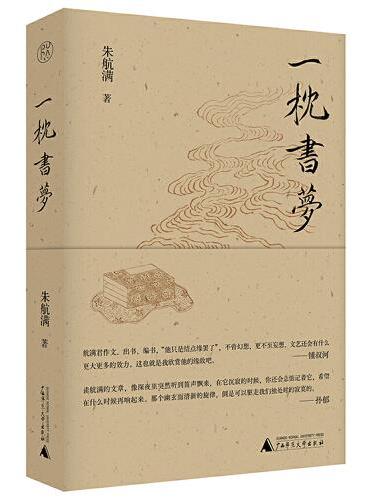
《
纯粹·一枕书梦
》
售價:NT$
36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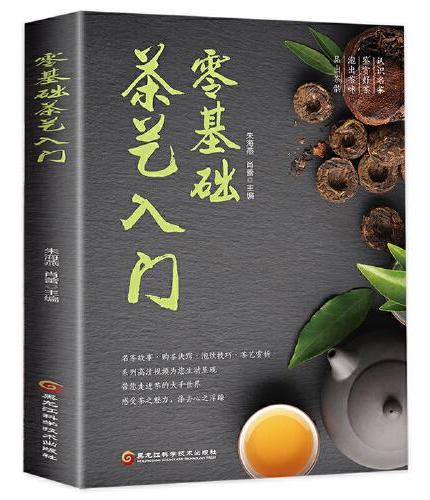
《
新版-零基础茶艺入门
》
售價:NT$
17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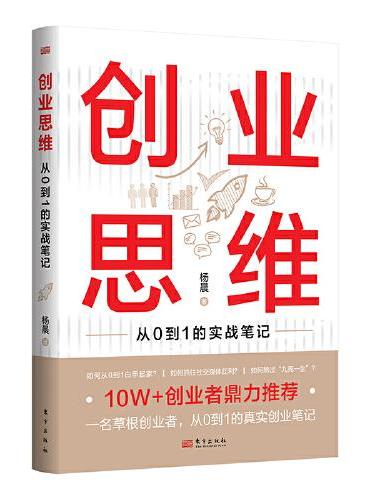
《
创业思维:从0到1的实战笔记
》
售價:NT$
356.0

《
家庭财富管理指南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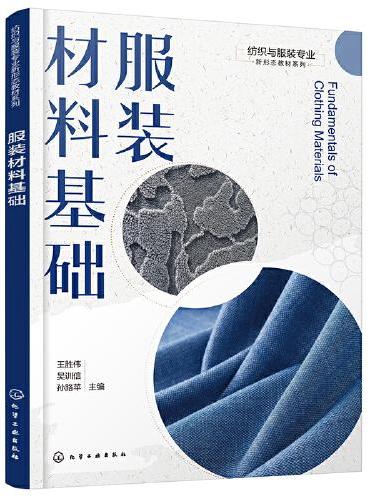
《
服装材料基础
》
售價:NT$
296.0

《
国家名片C919(跟踪十余年,采访百余人,全景式呈现中国大飞机C919,让读者领略到中国航空科技的最新成就)
》
售價:NT$
653.0
|
| 編輯推薦: |
1.《好笑的爱》是米兰?昆德拉整个小说创作的出发点,预示了昆德拉所有重要的复现主题:自我哄骗和幻象,性欲和爱的滑稽,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辩证关系,历史、青春和抒情诗,记忆和遗忘,笑(包括“玩笑”的概念),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悖论……
2.《好笑的爱》是博尔赫斯唯一一部短篇小说集。短篇小说是一种“小的形式”,却属于“大作”范畴。就像博尔赫斯、契诃夫和卡夫卡的短篇集不能随意打乱重排一样,昆德拉的短篇小说集也经过精心构思和巧妙的编织。
3.在文学中,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话语、我们的行动中,我们会提高或贬低爱的实践,恰恰使得爱成为极其严肃、或许是现代主题里最严肃的一件事。
如果我们把爱从笼罩它的诗意和神圣中分出来的话,它还剩下什么?
如果我们从小说的角度去注视它,它还剩下什么?
在现代社会的陷阱中,爱的情感变成了什么?
如果爱不再严肃,意义消失了,变成一种游戏,它会不会变成恶魔的笑声?
|
| 內容簡介: |
|
《好笑的爱》是米兰?昆德拉的短篇小说集,被誉为“昆德拉的整个小说创作的出发点”。该书以冒渎不恭的轻佻手法,提出对生命本质最沉痛的质疑。在《搭车游戏》《谁都笑不出来》《爱德华与上帝》等篇章中,将那些他乐于认真思索的玩笑,以奇思异想为始,以灾难告终,而游戏和权力常是最关键的中心主题。
|
| 關於作者: |
Milan Kundera
米兰?昆德拉(1929- )
小说家,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自一九七五年起,在法国定居。
长篇小说《玩笑》《生活在别处》《告别圆舞曲》《笑忘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和《不朽》,以及短篇小说集《好笑的爱》,原作以捷克文写成。
小说《慢》《身份》和《无知》,随笔集《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帷幕》和《相遇》,以及z新小说《庆祝无意义》,原作以法文写成。
《雅克和他的主人》,系作者戏剧代表作。
|
| 目錄:
|
Ⅰ 谁都笑不出来
Ⅱ 永恒欲望的金苹果
Ⅲ 搭车游戏
Ⅳ 座谈会
Ⅴ 让先死者让位于后死者
Ⅵ 哈威尔大夫二十年后
Ⅶ 爱德华与上帝
收集者的小说集
弗朗索瓦·里卡尔
|
| 內容試閱:
|
我们被蒙住眼睛穿越现在。至多,我们只能预感和猜测我们实际上正经历着的一切。只是在事后,当蒙眼的布条解开后,当我们审视过去时,我们才会明白,我们曾经经历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才能明白它们的意义。
那天晚上,我为我的成功而畅饮,我根本没有想到,这竟是我末日的序幕。
由于我什么都没有预料到,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心情舒畅。
克拉拉还在幸福的熟睡之中,我就拿起扎图莱茨基先生随信附来的文章,带着一种好玩的漠不关心的心境,坐在床上,读了起来。
这篇题为《米科拉什?阿莱什,捷克绘画的一位大师》的文章,根本不值得一读,我为它花费半个小时都是冤枉了。通篇堆积了陈词滥调,没有一丝儿合逻辑的展开,没有一丝儿独特的思想。
毋庸置疑,这是一大堆蠢话。确实,就在当天,《造型艺术思维》杂志的主编卡劳塞克博士(不过,他是最让人讨厌的人物之一)在给我的电话里,就这样给它定了性。他把电话打到我的学校,对我说:“你收到了扎图莱茨基先生的论文没有?这样,请你帮我一个忙,给我写一篇阅读报告吧,五位专家已经否定了他的文章,但他还是一味固执,他以为,你是独一无二的权威。请写上几行字吧,就说它怎么怎么站不住脚,你有资格说这话,你知道该怎么把话说得尖酸一点,这样,他就会让我们清静了。”
但是,我心中有什么东西在反对:为什么偏偏是我,恰恰是我,要成为扎图莱茨基先生的刽子手?再说,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造型艺术思维》曾自认为很有道理地拒绝过我的文章呢;此外,对我来说,扎图莱茨基先生的这个姓,还跟克拉拉,跟那瓶斯利沃维什酒,跟一个美妙的夜晚密切相连呢。无论如何,我不会否定它,那样做不人道,我只需伸出一只手,掰着手指头数,就能数出有谁把我当作“独一无二的权威”,甚至只要伸出一根手指头就够了。为什么要把这个惟一的崇拜者变成我的敌人呢?
电话说到最后,我使用了一些巧妙而又含糊的措辞,让我们两人谁都以为其中的意思很明白,卡劳塞克认为是一种承诺,而我认为是一种脱身之计。我挂了电话,拿定主意,坚决不写那篇关于扎图莱茨基先生论文的阅读报告。
于是,我从抽屉中拿出信纸,给扎图莱茨基先生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小心地避免对他的研究作出任何形式的评判,我对他解释说,我关于十九世纪绘画的想法,通常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尤其是在《造型艺术思维》的编辑眼中,因此,我的介入不仅不会有用,反而可能坏事;同时,我回敬了扎图莱茨基先生一大堆友好的客套话,我相信他不会看不出字里行间对他的一种感激之情。
信投进邮筒之后,我就立即忘记了扎图莱茨基先生。但是,扎图莱茨基先生并没有忘记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