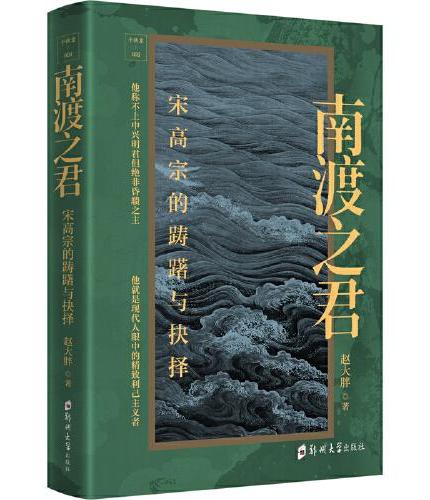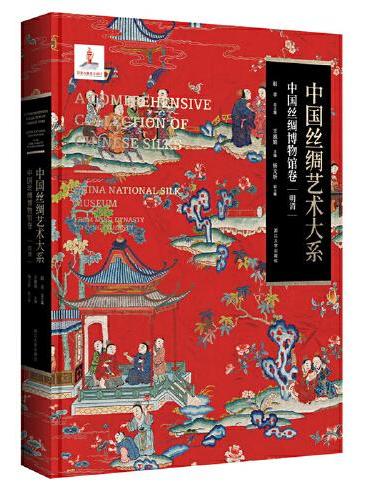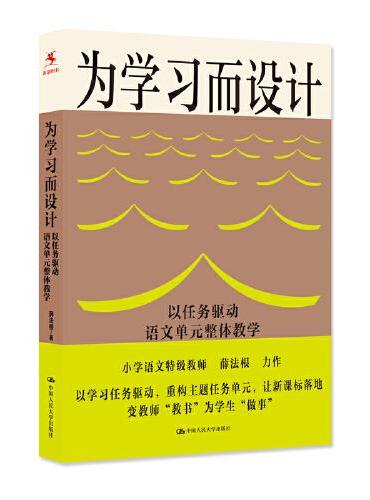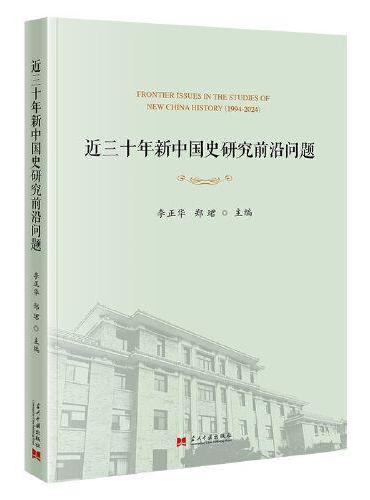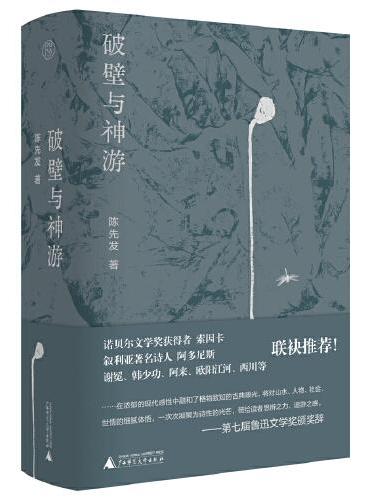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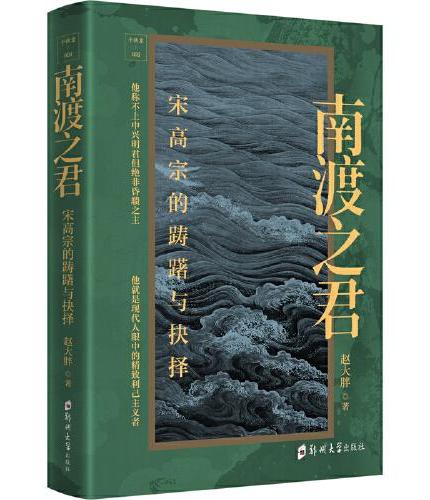
《
千秋堂丛书003:南渡之君——宋高宗的踌躇与抉择
》
售價:NT$
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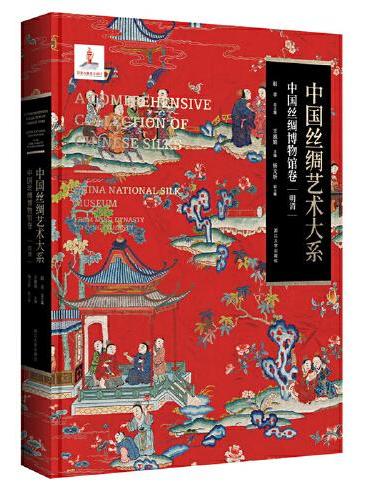
《
中国丝绸艺术大系·中国丝绸博物馆卷(明清)
》
售價:NT$
49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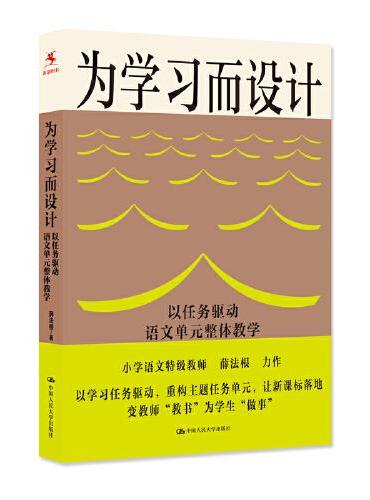
《
为学习而设计:以任务驱动语文单元整体教学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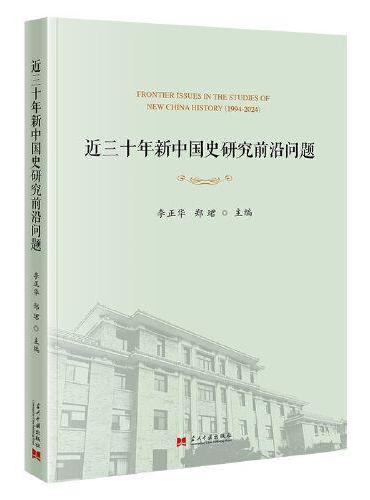
《
近三十年新中国史研究前沿问题
》
售價:NT$
500.0

《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
售價:NT$
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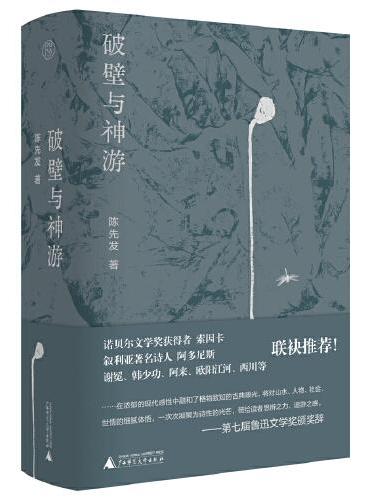
《
纯粹·破壁与神游
》
售價:NT$
418.0

《
春秋大义:中国传统语境下的皇权与学术新版(小学《论语》,大学《春秋》代表中国精神的政治哲学至高圣典。得到近80万总订阅主理人熊逸代表作)
》
售價:NT$
449.0

《
女人们的谈话(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提名、最佳改编剧本奖 原著!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简直是《使女的故事》现实版!”)
》
售價:NT$
286.0
|
| 編輯推薦: |
法兰西经典,当今西方古典学研究者必读的经典之作
《古希腊神话与悲剧》一书对古希腊悲剧产生的条件、特点等进行了论述,通过对悲剧作品《俄瑞斯忒亚》《俄狄浦斯王》《菲罗克忒忒斯》等的具体分析,展现了悲剧作家作品的内部结构与外部的政治、社会制度之间的关联,并在不同程度上质疑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和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对古希腊悲剧的阐释。此外,本书在研究埃斯库罗斯的《七雄攻忒拜》、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和欧里庇得斯的《酒神的伴侣》时,在方法上除了采用最传统的语文学手法,还借用了结构分析的方法。由于在观点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性,本书已成为当今学者研究古希腊悲剧必读的经典之作。
|
| 內容簡介: |
《古希腊神话与悲剧》是法国著名古希腊研究专家让-皮埃尔·韦尔南和皮埃尔·维达尔-纳凯的研究论文合集,分为两卷。卷一出版于1972年,收录了七篇古希腊研究论文,这些论文主要是将古代文本置于结构性分析、文学性研究和社会学剖析的视角之下。然而,在这三重视角之下,其研究重点却并非神话本身,而是更加注重对悲剧和各具特色的悲剧作品的研究。卷二出版于1986年,该卷拓展了研究视角,重点分析研究公元前5世纪悲剧作品中的神灵,尤其是戏剧中戴面具的神:狄俄尼索斯。除了古代戏剧之外,作者也在思考为什么这种古希腊戏剧的古典性会演变成法国后来的古典主义。
本书已成为当今西方古代历史和古典学研究者们必读的经典之作。
|
| 關於作者: |
让-皮埃尔·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1914—2007),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古希腊研究专家,法兰西公学院荣誉教授。主要著作有《希腊思想的起源》《古希腊神话与社会》《古希腊神话与思想》《希腊宗教与古代宗教》《宗教、历史、理性》《古希腊神话与宗教》《神话与政治之间》等。
皮埃尔·维达尔-纳凯(Pierre Vidal-Naquet,1930—2006),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古希腊研究专家,研究领域涉及古希腊、犹太历史和现代历史。主要著作有《古希腊经济与社会》《多重视角下的希腊民主》《希腊人、历史学家与民主》《破碎之镜:雅典悲剧与政治》《荷马的世界》等。
译者简介:
张苗,2006年获得中国海洋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和金融专业毕业证书,2008年获得法国西布列塔尼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谢阁兰文学院欧洲国家语言、文学和文化专业),2009年获得中国海洋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法语语言文学)。现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与巴黎三大(新索邦大学)联合培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法比较文学。
杨淑岚,1985年生,上海外国语大学法语系博士在读,曾在里昂政治学院研习阿拉伯世界课程一年,目前在波尔多政治学院学习非洲研究课程,主修政治学。在政治学理论和地域历史文化研究以外,探索用哲学思维研究人文学科。
|
| 目錄:
|
卷一
序言 / 3
一、悲剧在古希腊历史背景下的社会条件和思想条件 / 8
二、希腊悲剧的张力与模糊性 / 14
三、在希腊神话中,“意志”开始显露 / 36
四、无恋母情结的“俄狄浦斯” / 71
五、模糊性与逆转:论《俄狄浦斯王》的结构之谜 / 95
六、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俄瑞斯忒亚》中的狩猎与献祭 / 131
七、索福克勒斯作品中的“菲罗克忒忒斯”和预备公民培训制 / 157
附录关于叙拉古博物馆的一个陶瓶 / 179
卷二
序言 / 189
一、悲剧传奇之神/ 198
二、古希腊面具的形象/ 204
三、跛脚僭主:从俄狄浦斯到佩里安德/ 221
附录 / 244
四、悲剧的主题:历史性和跨历史性/ 254
五、埃斯库罗斯,过去和现在/ 264
六、英雄们的盾牌:论《七雄攻忒拜》的核心一幕/ 288
七、俄狄浦斯在雅典/ 321
八、俄狄浦斯在两城之间:论《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 344
九、俄狄浦斯在维琴察和巴黎:两个历史时刻/ 382
十、欧里庇得斯《酒神的伴侣》中戴面具的狄俄尼索斯/ 405
|
| 內容試閱:
|
一、悲剧在古希腊历史背景下的社会条件和思想条件
在20世纪的下半叶,研究古希腊的学者尤其注重研究悲剧的起源问题。即使他们能给予起源问题一个总结性的回答,但悲剧问题也还是没有最终得到解决。需要明白问题的实质是在于:从艺术、社会制度和人类思想角度来说,雅典悲剧(或称阿提卡悲剧)所带来的革新,使悲剧成为一种创新形式。悲剧是具有自身规则和特色的新颖的文学样式,它在城邦的公共节日体系中建立了一种新型表演。此外,作为特殊的表达形式,它还揭示出当时一直未被认识到的人类经验的各个方面,它标志着人类的内在塑造和责任观树立进入一个新阶段。悲剧的形式、悲剧的表征和悲剧人物这三个方面标志着悲剧现象的产生,并具有强大而鲜明的特性。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起源问题其实是一个假象问题,我们更应称之为:在某一现象出现之前必然会存在的先例。也应该注意到的是,我们并不需要为这些先例寻求解释,而是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它们,而且因为它们已经超越了自身范围,所以也并不能用于解释悲剧本身。举例来看,“面具”强调的是悲剧与宗教仪式中的假面队伍的同源关系。但是,从本质和功能方面来讲,悲剧中的“面具”却是另外一回事,它并不是宗教性的乔装改扮,也不是动物化的装扮,而是一个人类的面具。它的作用是审美意义上的,而不是宗教仪式角度的。另外,“面具”能够强调悲剧舞台上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两种元素的距离和区别。一方面,起初没有戴面具而只是乔装打扮了的合唱歌队,似乎是象征着一个集合人物,由一群公民组成的团体所代表。另一方面,如果是由专业演员去扮演悲剧人物,那他的面具与匿名合唱队相比就更加个体化了。这种个体化并不是将佩戴面具者变成一个思想主体、一个个体化的“人”,相反地,面具将这一悲剧人物融入一个很具体的宗教和社会阶层:英雄的阶层。面具象征着英雄人物,而英雄的传说,体现了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在那段历史的一个层面。这些传说着重体现了诗人们所歌颂的英雄主义传统。那段遥远而动荡的历史与城邦秩序形成对比,但它却始终活跃在公民的信仰中,英雄崇拜在这种公民信仰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暂不涉及荷马和赫西俄德)。因此,在悲剧技巧中,存在以下两个极端代表:一个部分是匿名的群体合唱队,它的作用是在合唱队的恐惧、希望和评判中表达出观众的感情,而观众就是公民团体的组成者;另一部分是个体化的人物,他的言行是悲剧的重点,他代表着另一个时代的英雄的形象,而且其存在环境也总是异于普通的公民生活环境。
合唱队和悲剧人物的这种双重性与悲剧语言的双重性相呼应:一方面是合唱队的抒情性的表达方式;另一方面则是悲剧主角们的对话式的表现形式,其格律与散文更为接近。英雄人物说着跟常人一样的语言,这使得他们的距离感被弱化,但他们不仅将自己呈现在舞台上和观众的眼前,还与合唱队或其他对立人物之间进行争辩,最终他们就变成了辩论的目标。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在公众面前自我质询。另外,合唱队在演唱部分较少展示英雄的光辉品格,正如在西莫尼德斯(Simonide)和品达(Pindare)的抒情传统中,合唱队不关注也不质疑主体。在新的悲剧模式中,英雄不再是一个典范,而是成了一个问题聚集点——无论是对于他自身而言,还是对于其他人而言。
这些初步的基本观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限定与悲剧相关的研究主题。古希腊悲剧被看作一个明确限定了范围和年代的历史时期。我们看到它在雅典产生,随之在一个世纪的时空范围中繁荣,继而衰退。为什么呢?我们首先注意到,悲剧传达的是一种悲痛的意识,一种将人分裂为自我对立状态的极度矛盾感;此外,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在古希腊时期,悲剧的各种矛盾冲突所处的层面、所涉及的内容及其产生的原因。
这就是路易·热尔内通过对每部悲剧作品的词汇和结构分析所试图要解决的问题。他曾成功阐释了悲剧的真正素材就是城邦的社会观念,尤其是正在广泛兴起的法律观念。在悲剧诗人笔下出现的法律专用名词,突出体现了悲剧的偏好主题与某些法院权能范围的案件有很大的相似性。那些较新设立的法院,能让人充分感受到价值的更新,而且正是新的价值观的出现才要求创立法院,并规定了法院的功能。悲剧诗人在运用法律词汇的同时,也故意利用这种词汇的不确定性、飘忽不定性和未完成性:专用词汇的模糊性、含义的变化性、不连贯性和对立性,这些都会导致法律观念内部的不协调,体现出法律观念与宗教传统的冲突,也体现了还未明确限定范围(与法律相比较而言)的道德思考。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法律已经与道德思考区分开了。
这是因为,法律不是一个逻辑性的构建,而是由起初的习惯性程序随着历史的推进而逐步形成的。它与起初的习惯性程序的关系是:前者源于后者,既相互对立又部分相关。希腊人没有一个“绝对法律”——即建立在规则基础之上、拥有连贯统一的系统——的观念,对于他们而言,有的只是法律的不同层次:一方面,法律依靠的是事件的权威性和约束性;另一方面,将神权也纳入法律体系,包括世界的秩序、宙斯的公正。同时,法律也涉及与人的责任相关的种种道德问题。从这方面来看,神圣的“正义”(Dikē)本身也很模糊,晦涩难懂:对于人来说,它包含了原始冲动力量的不理智因素。比如在《乞援人》(Les Suppliantes)中,“力量”(kratos)的概念,就一直在两种相反的意义中摇摆不定:时而,它指的是合法的权威,合法设立的控制权;时而,它又指暴力方面的野蛮力量,与法律和公正完全对立。同样地,在《安提戈涅》(Antigone)中,“法规”(nmos)一词会因戏剧角色的不同而具有完全相反的含义。悲剧所体现的是:一种“正义”与另一种“正义”之间的斗争,一种始终向其对立面转化的、未被确定的法规。当然,悲剧并不是一场法规间的斗争,而是将活着的人本身作为这一斗争的对象,人被迫做出一个决定性的选择,并将自己的言行引向一个标准模糊的价值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任何事物在任何时候都是不稳定的、非单义的。
这就是在悲剧素材中的第一个冲突面。此外,还有第二个冲突面,与前者也有密切的联系。显然,当悲剧依然活跃的时候,它会从英雄的传奇故事中汲取素材。这种扎根于传统神话传说的特点,也解释了为什么从诸多方面来看,一些著名的悲剧作家体现出了比荷马更明显的宗教方面的仿古性。悲剧从某些英雄的传说中受到启发,自由地将其改造成悲剧故事,然而,悲剧本身也与这些英雄传说保持一定的距离,并提出质疑。悲剧将英雄主义的价值观和古代宗教的表征与新的思维方式进行对比,这种新的思维方式标志着在城邦范围内出现了法律。事实上,英雄的传说与王室后裔和贵族谱系密切相关,尽管从价值范畴、社会实践、宗教形式和人类行为的角度来看,城邦本应斥责和反抗这些王室贵族谱系,并应与之不断斗争以建立城邦,但这些王室贵族谱系在英雄传说中都是以支持城邦的姿态出现的,也正是基于此,城邦才得以构建。因此,城邦与王室贵族谱系始终具有深层的关联。
所谓的悲剧时刻,即在社会经验的中心成功开凿出一段距离的那一时刻。这段距离足够远,使以下的两组对立面都得以明确地呈现:一组是法律思想与政治思想,另一组是神话传统与英雄传统;而这段距离也足够近,因此能痛彻心扉地体会到价值的冲突,也足以使冲突能持续不断地产生。关于人的责任问题,大概情况也是这样的,在法律摸索前进的过程中,人的责任问题开始不断显露出来。当人界与神界区分较为明显的时候,他们既相互对立又不可分割,此时,就有一种责任的悲剧意识。当人的言行成为思考和内心冲突的主题时,责任的悲剧意义就产生了,然而,人的言行本身还并未取得足够自主的地位来充分实现自我掌控。悲剧的范畴就确立在这个边缘区,在这一区域内,人的行为与神的力量相伴而行,并揭示出被忽略的人的行为的真正意义,人主动发起了行为,并为其负责,又将其置于超越自身、无法掌控的秩序中。
现在,我们更加明白,悲剧其实就是一个“时期”,可以用两个时点来限定它的兴盛期,这两个时点也定义了对于悲剧表演的两种态度。起初,第一个时点是梭伦(Solon)的愤怒,他极为气愤地离开一场戏剧表演——那是在悲剧竞赛设立之前,最早出现的悲剧表演;轮到泰斯庇斯(Thespis),他为自己的表演辩护说:无论如何那只是一种游戏,而梭伦这位老立法者为庇西特拉图日渐增长的野心而感到担忧,他反驳道(源自普鲁塔克[Plutarque]的观点):不久大家就会看到此类的虚构表演对公民间的关系会产生重大影响。对于智者、道德家和政治家而言,因为他们致力于建立节制和契约为基础的城邦秩序,所以,他们必须要破除贵族的优越感,努力避免这个阶层的僭主变得更加狂妄自傲(húbris),而英雄的过去与现实离得太近,无法以戏剧的方式搬上舞台。谈到后来的发展,我们就看一下亚里士多德(Aristote)关于阿伽颂(Agathon,与欧里庇得斯同期的悲剧诗人,他自己虚构创造出新情节,著有多部情节新颖的悲剧作品)的评论。自阿伽颂以后,悲剧与英雄传说之间的关系变得很松散了,已经不再需要讨论英雄的过去。剧作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写作方式——只要不触犯之前伟大的剧作家们的作品——继续创作戏剧作品,也可以自己虚构创造故事结构和情节。在阿伽颂的作品中,在他那个时代的观众中,乃至在整个希腊文化中,悲剧的原推动力就此被打断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