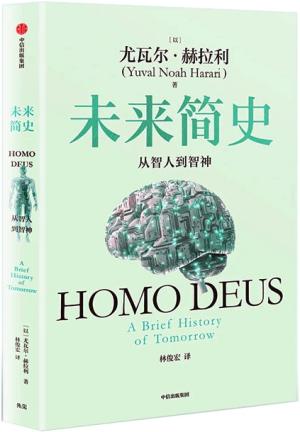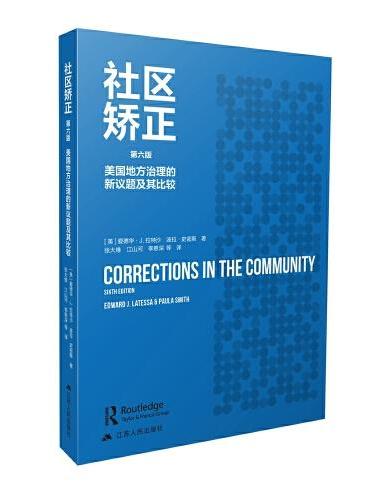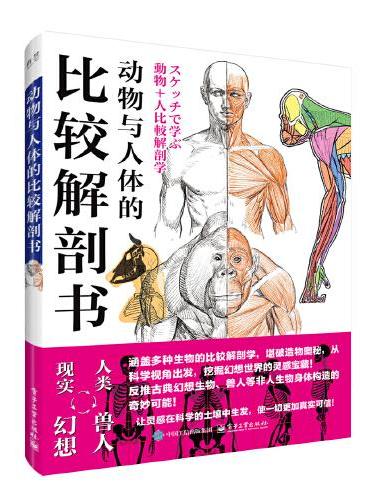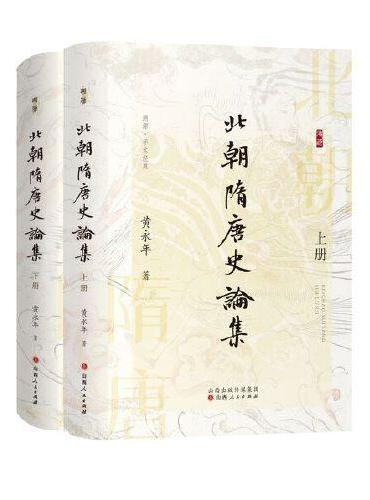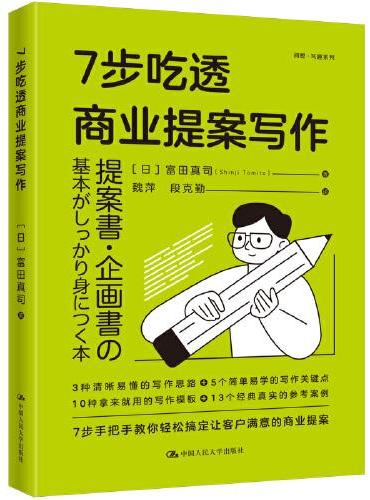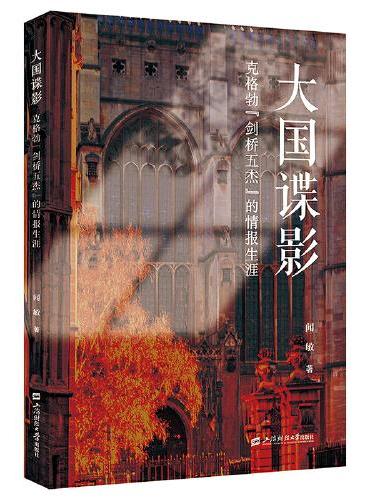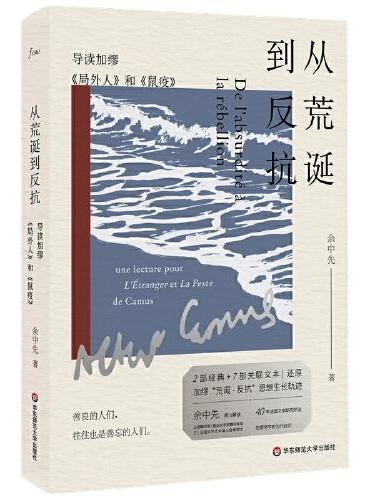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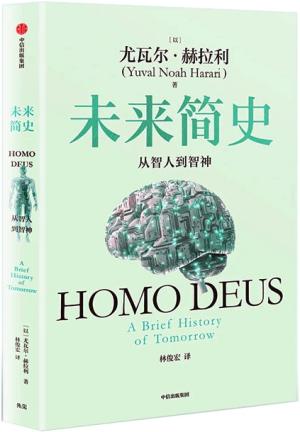
《
未来简史 从智人到智神(2025白金纪念版)
》
售價:NT$
4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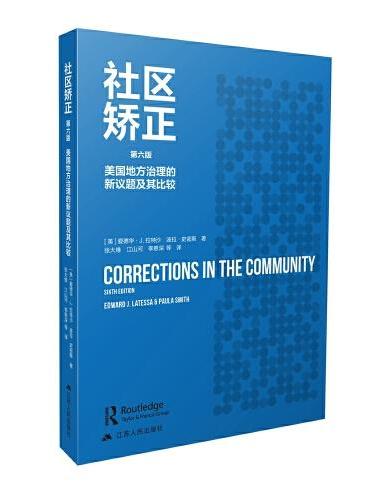
《
社区矫正(第六版):美国地方治理的新议题及其比较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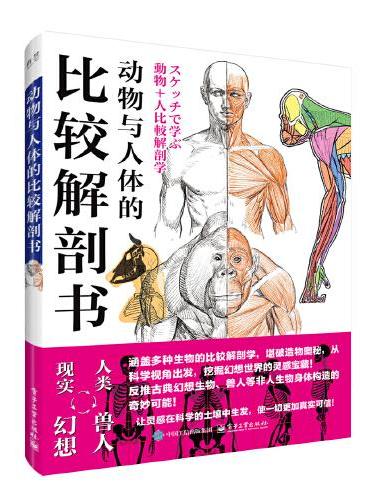
《
动物与人体的比较解剖书
》
售價:NT$
45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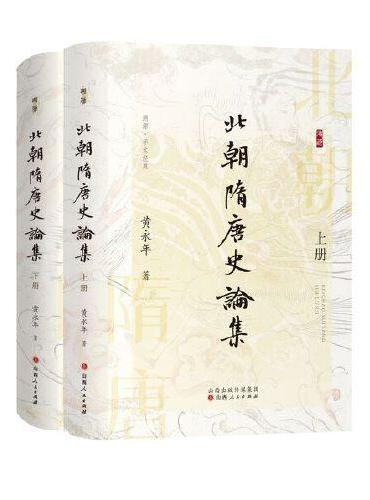
《
北朝隋唐史论集
》
售價:NT$
1270.0

《
半小时漫画中国史(全5册)
》
售價:NT$
127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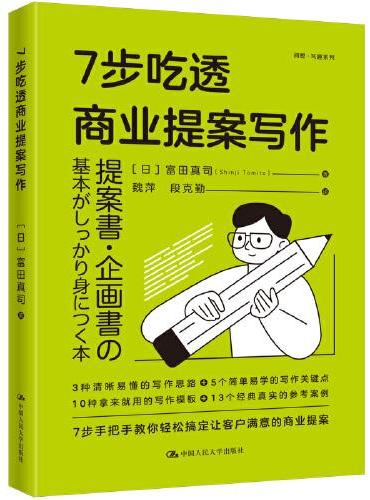
《
7步吃透商业提案写作
》
售價:NT$
3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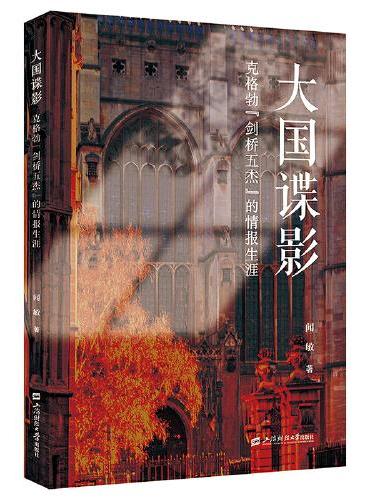
《
大国谍影
》
售價:NT$
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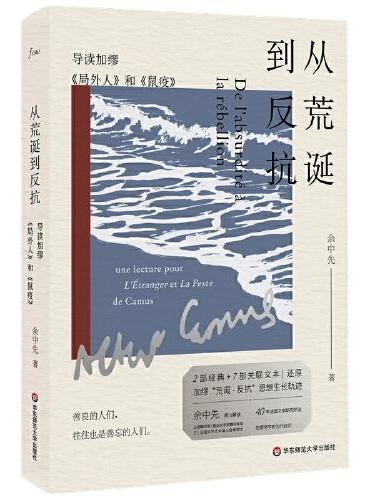
《
从荒诞到反抗:导读加缪《局外人》和《鼠疫》(谜文库)
》
售價:NT$
305.0
|
| 編輯推薦: |
|
内含现代与正义,连接传统与世俗的晚清民国侦探小说,对其研究和解构,揭示了小说研究中的理性与想象的关系。本书从不同侧面关注晚清民国侦探小说中的正义想象、都市书写、理性迷思与类型演变等问题。
|
| 內容簡介: |
|
本书以晚清民国时期的侦探小说为研究对象,借助类型文学研究、翻译研究、文化研究等多种思路与方法,重点关注晚清民国侦探小说中的正义想象、都市书写、理性迷思与类型演变等问题,并进一步述及传统与现代、翻译与创作、文学与文化等多方面内容的辩证思考。
|
| 關於作者: |
战玉冰,文学博士、博士后,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类型文学与电影、数字人文等。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及博士后项目3项。入选上海市“超级博士后”、复旦大学“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在《学术月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比较文学》等CSSCI来源期刊及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部分文章被《新华文摘》等转载。在《南方周末》开设《百年中国侦探小说》专栏。专著有《现代与正义:晚清民国侦探小说研究》和《民国侦探小说史论(1912—1949)》(即出)。
|
| 目錄:
|
第一辑侠义与正义
003清末民初中国侦探小说中的传统性因素
023正义,侠义,民族大义?——以亚森·罗苹系列小说的翻译、模仿与本土化创作为中心
044亭子间、咯血症与“侠盗”想象——以20世纪40年代孙了红的居室及“侠盗鲁平奇案”系列小说为中心
第二辑侦探与都市
081从匿名性到“易容术”——现代都市与侦探小说起源关系初探
102晚清民国侦探小说中的“苏州书写”
116罪案与舞厅——民国侦探小说中的“舞女”书写
139民国时期电影与侦探小说的交互影响——以陆澹盦的观影活动、影戏小说与侦探小说创作为中心
第三辑百年类型史
157“侦探小说女王”的两次“来华”——以20世纪40年代和80年代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小说汉译为例
179知识癖、叙事迷宫与摄影术——小白的谍战小说及其类型突破
第四辑科技与传奇
205早期侦探小说中的理性精神
219侦探小说里的“动物杀人”
227火车、时刻表与陌生人——晚清民国侦探小说中的现代性想象
238民国侦探小说中的摄影术
248侦探小说研究中的类型理论与“远读”方法随想
255后记: 做学术,像侦探一样
|
| 內容試閱:
|
本书中所收录的文章主要是围绕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侦探小说而展开,大概可以视为我近几年对于相关问题的思考成果集结和部分内容呈现。其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面向:
首先,侦探小说作为诞生于现代法制社会之中,以罪案和破案为主要情节内容的小说类型,先天便内含了对于“正义”问题的考量。这既包括小说中作为主角的“私家侦探”和国家司法体系之间的复杂关系(法律之外的正义与法律之内的正义),也涉及侦探小说作为“小说”本身的“诗学正义”想象与“法律正义”之间所存在的一致性及裂隙。而聚焦到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侦探小说,则又多了一个“传统侠义”如何转化为“现代正义”的思考向度,以及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民族大义”中的“正义性”在具体伸张过程中,又和“传统侠义”“法律正义”“诗学正义”等在精神内核与实践形式层面怎样相互融合或彼此抵牾等。本书“侠义与正义”一辑中的相关内容,即对上述问题所作出的尝试性回答。而当我们看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侦探小说作家孙了红笔下的“侠盗”鲁平形象兼具古代侠客之风采、现代侦探之才干与民族气节之担当,作者孙了红本人却贫病潦倒、一无所为时,就完全可以知道侦探小说中的这种“正义想象”,其实不过是一种“正义的虚张”。
其次,诚如本雅明所言,世界早期侦探小说同时又是现代都市的产物: 从爱伦·坡笔下侦探杜宾昼伏夜出的巴黎,到柯南·道尔所塑造的福尔摩斯对伦敦街巷的了若指掌、堪称“城市活地图”,再到民国时期霍桑、李飞、鲁平等侦探或“侠盗”大显身手的上海……小说中适合侦探们施展才华的舞台无一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为充分和成熟的现代化大都市。甚至于我们可以说,现代都市不仅是早期侦探小说的故事发生空间,更是深刻参与构成了侦探小说自身的类型气质与形式特征。本书“侦探与都市”一辑中所分别讨论的,则包括充满了“惊惧体验”的都市街头,作为金钱与欲望交换场所的舞厅,以及提供另一种侦探叙事传播媒介的电影院等现代都市场所。此外,中国传统文化场域对于西方都市现代性的接受与抵抗,则被形式化为“苏州案件与上海侦探之关系”这个有趣的侦探小说情节想象而得到讨论和处理。
再次,侦探小说作为一种类型小说,其类型自身的传承演变也是相关研究所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本书“百年类型史”一辑中,主要以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小说的百年汉译历程和作为侦探小说“亚类型”的中国间谍小说百年发展史作为研究案例,从类型小说、文学翻译、文学史、时代思潮等方面初步探讨中国侦探小说的类型承续与断裂,其涉及历史范围其实已经不止于晚清民国时期,而是会一直延续到当下。但晚清民国侦探小说既是中国百年侦探小说的时间与逻辑起点,又是与后来者可资比较的参照对象,在百年中国侦探小说史乃至百年中国类型小说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而这两篇文章中具体时间范围上的“超出”,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要反过来凸显晚清民国作为中国侦探小说史发展起点对于后来者的重要意义。
最后,侦探小说中一方面充满了关于现代科技的想象,而这些“科技想象”在晚清民国时期则常被视为“夷之长技”“奇技淫巧”“西方巨兽”,并相应伴生了崇拜、不屑或恐惧的不同心理反应;另一方面,西方侦探小说不容忽视的来源之一却又是哥特小说与都市怪谈,其传奇性、幻想性的情节成分也是普遍存在(虽然这些内容在侦探小说里最终往往要寻找到一个符合逻辑的解释)。本书最后一辑“科技与传奇”中的几篇文章,先借助克拉考尔《侦探小说: 哲学论文》一书中精辟论述的启发,着力探讨世界早期侦探小说中的理性精神;之后分别以“动物杀人”“铁路巨兽”“摄影术”为例,对相关议题进行案例式分析。而《侦探小说研究中的类型理论与“远读”方法随想》一篇小文,则既可以视为对相关类型研究方法的总结与反思,也是对当下或未来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展开侦探小说研究的一点遐想。
总的来看,一方面诞生于现代都市之中的侦探小说成功捕捉到了现代都市人群的某种“惊颤体验”或“感觉结构”,并承载了他们关于理性的信仰、秩序的想象和自我主体性的乐观;另一方面,正义又是侦探小说中重要的价值范畴,这既包括福柯所说的侦探小说产生于国家权力展现方式转型的这一历史过程之中, 即从视觉暴力的展演转变为专业知识的档案,又进一步涉及司法正义、法外正义、诗学正义、传统侠义和民族大义的相互辩证。因此,本书取名为“现代与正义”,正是试图揭示晚清民国侦探小说中这两个方面的内涵与意义。
早期侦探小说中的理性精神
从世界范围来看,侦探小说诞生并发展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从爱伦·坡到柯南·道尔的系列侦探小说创作构成了世界侦探小说发展的第一轮高峰。其时,在物质经济上,第一次工业革命在欧美发达国家业已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各种新能源、新技术、新发明不断产生,人们研究自然、对抗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日益加强。在思想文化上,这一时期正逢欧洲启蒙运动的发展进行到后半程,人们普遍表现出对启蒙的乐观与对理性的自信。人类认知世界的愿望空前高涨,通过科学技术手段与理性逻辑思维就可以掌握一切复杂事物并能够穿透认知其本质的想法已经渐渐深入人心。侦探小说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应运而生,或者我们也可以说,侦探小说是理性时代的文学产物。
侦探小说与西方理性精神传统
西方世界对于“理性”概念的探讨早已有之且传统悠久: 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关于作为第一性的、永恒普遍的“理式”世界的构想,到笛卡尔《方法谈》与《沉思录》里对理性确定性的追求;从斯宾诺莎通过《伦理学》对于理性和理性知识的宣扬和实践,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对理性自身能力的批判性考察……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一条西方思想家与哲学家们对于“理性”问题思考和探讨的粗疏脉络。而明确将“理性”这一哲学概念与侦探小说这一文学类型进行相互关联思考的学者当首推德国思想家、电影理论家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1889—1966)。在《侦探小说: 哲学论文》一书中,克拉考尔提出,在现代社会中宗教逐渐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中隐退,理性取而代之成为新的宗教与上帝。而在侦探小说中,面对理性这个现代社会的“上帝”,“侦探也被借予修道士的品质”,他是理性在小说中的代言人,甚至可以“作为理性的人格化,侦探既不是在追踪罪犯,因为后者已经犯法,也没有自我认同为合法性原则的承担者,可以说,他解谜只为猜谜的过程”。
与之相应地,克拉考尔认为,侦探小说以其较为纯粹的、单向度的文本形式而承载并贯穿了理性的意义:“尽管并非艺术品,然而,一个去现实社会的侦探小说对这个社会本来面目的展现比这个社会通常能够发现的更加纯粹。社会的载体及其功能: 在侦探小说里,它们自行辩护,也交代了隐藏的含义。可是,小说只能强迫自我遮蔽的世界进行如此一番自我暴露,因为,孕育出小说的是一种不受这个世界限定的意识。担负着这一意识,侦探小说的确首先对由自治理性统治的,仅存于理念中的社会进行了通盘思考,然后合乎逻辑地推进这一社会给出的开端,理念借此在情节和人物中得到完全的充实。如果单向度之非现实的风格化得到了贯彻,侦探小说就根据它的实存性将刚好满足构造性前提的单一内容并入一个封闭的意义关联(Sinnzusammenhang),此实存性不会被置换为批评和要求,而是转化为审美的编排原则。”在克拉考尔的这段论述中,侦探小说因为其特殊的、纯粹的“审美编排原则”构造出了“一个封闭的意义关联”,使得“单向度之非现实的风格化得到了贯彻”,并因此被视为呈现理性观念的完美的文学体裁。
可以说,克拉考尔成功地挖掘出了作为通俗小说类型之一的侦探小说本身所蕴藏的理性精神和现代性因素。但也正如后来学者所评价的那样,克拉考尔“他的兴趣在于对一种审美形式进行历史哲学的和形而上学的阐释”。即他更多的是从抽象的意义层面来考察作为对象的侦探小说,并探究其理性特质。而在这里,我们或许还可以借助齐美尔的论述来更为具体地理解理性与侦探小说所产生的现代都市背景之间的内在关联:“在我们看来,大城市理性观念的加强也是由心理刺激引起的。” “这里,首先要理解大城市精神生活的理性主义特点。大城市的精神生活跟小城市的不一样,确切地说,后者的精神生活是建立在情感和直觉的关系之上的。直觉的关系扎根于无意识的情感土壤之中,所以很容易在一贯习惯的稳定均衡中生长。相反,理智之所在却是我们的显而易见的有意识的心灵表层,这里是我们的内心力量最有调节适应能力的层次,用不着摇震和翻松就可以勉强接受现象的变化和对立,只有保守的情感才可能会通过摇震和翻松来使自己与现象相协调。当外界环境的潮流和矛盾使大城市人感到有失去依靠的威胁时,他们——当然是许许多多个性不同的人——就会建立防卫机构来对付这种威胁。他们不是用情感来对这些外界环境的潮流和矛盾做出反应,主要的是理智,意识的加强使其获得精神特权的理智。因此,对那些现象的反应都被隐藏到最不敏感的、与人的心灵深处距离最远的心理组织中去了。”在齐美尔看来,理性的产生与现代大都市的生活方式与背景密不可分,甚至于“这种理性可以被认为是主观生活对付大城市压力的防卫工具”
客观世界的“可知”与“可控”
具体谈到侦探小说中的理性精神,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次来进行理解:
一方面,侦探小说中的理性首先体现为一种认知世界的方式,即小说中的侦探们往往被设定为理性的拥笃者和忠实信徒。他们天然地相信世界是可以被认知的,相信借助理性主义的认知,生活中的一切奥秘都可以找到合乎理性的解释。侦探往往对于通过观察与思考来洞穿事物背后本质的可行性与有效性保持着一种乐观和自信,自信可以将看似无从索解的神秘案件还原成理性可以把握的因果链条。甚至于我们可以说,这一信念本身就是对理性主义的最大彰显。再次借助克拉考尔的精彩表述,即“侦探并不指向理性,他就是理性的化身,他不是作为理性的造物去履行理性发出的指令,准确地说,是理性自身不带人格地执行着它的任务——因为,要以审美的方式表明世界与其条件之间的张力收缩,最有力的办法莫过于令人物对自设为绝对的原则完成认同”。而这种对于世界本质“可知”的自信,恰好又非常形象地体现在世界第一篇侦探小说,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的《莫格路凶杀案》开篇所引用的诗句之中:“塞壬唱的是什么歌?躲在妇女群里的阿喀琉斯用的是什么名字?问题虽不容易回答,却并非没有答案。”想要回答都市中的种种问题,寻找到隐藏于“人群中的人”是需要侦探具备一种观察与思维方面的穿透力。在这个意义上,侦探的工作即努力阅读城市表象之下的秘密,即对于现象背后因果关系的“看穿”与深层把握。而这种“看穿”与“把握”是需要以理性为依归的,并且侦探通过理性思考来“看穿”秘密本身,在侦探小说中,就具有一种力量。
另一方面,对世界“可知”的承认同时意味着将世界本身视为一种有秩序的对象,而侦探小说里侦探破案的过程本质上正是从混乱、纷繁、令人迷惑的案件背后发现潜在的条理和确定的关系,进而恢复这个世界的固有常态秩序。如克拉考尔所说:“侦探小说的特点是,理性发现了一份材料,材料的不充分看起来几乎无法为理性贯穿始终的过程提供攻击点。在被摆在理性面前的少量事实的周围,一开始就弥漫着一片无法穿透的黑暗,或者,一派诱人的前景展开了,这景象一定会把人送上歧途,而且表示骗得刑警的盲信。” “在侦探小说里,一个神秘事件就可以将人们投入恐慌,让人透不过气的不是事件的威力,而是决定事实的因果链条未被识破。” “直至最末,一连串事实才给出那个符合理智的解释,唯有这解释才可能制止笼罩着被卷入者的灾难。”
克拉考尔所说的这一点在爱伦·坡的侦探小说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前文所述,爱伦·坡的侦探小说创作一方面明显受到了他早期哥特小说创作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对其有所突破。这种突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爱伦·坡的侦探小说在如同其哥特小说一样渲染过悬疑、恐怖的气氛之后,最终必须让侦探杜邦依靠理性分析推理出事实真相,即在认识论意义上完成了理性主义对神秘主义的破除。在侦探杜邦具体分析与推理的过程中,也一般遵循着从包含有多种可能性的开放模式抵达唯一真相的水落石出的过程。而在侦探通过理性思考,找出克拉考尔所说的“因果链条”上的缺失的环节,最终推导出事实真相的同时,也意味着整个“秩序”从混乱恢复到有序。爱伦·坡所开创的这一侦探小说结构模式,基本上奠定了后来侦探小说这一小说类型的写作规范和基本叙事成规。而在民国时期中国侦探小说作家长川创作的“叶黄夫妇探案”系列中的《红皮鞋》一篇中,也有一个与此相关且颇耐人寻味的细节。小说里警官叶志雄“转过身来,向全房间瞥了一眼,觉得整个房子的布置非常得宜,各样用具也安置得和谐,运用方便。突然看见床边一只樟木箱的地位实在放得不妥切,志雄想宋嘉春的太太一定是个聪明贤惠的妇女,样样东西都安排得妥妥帖帖,惟有这只樟木箱子不大合适,也许其中有什么道理在”。这样一个警察在失踪者(后来证明是死者)房间内发现箱子“放得不妥切”,并以此为切入点展开案件调查的细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对侦探小说中理性“秩序”的绝妙隐喻。在侦探小说所构建的“理性”“有序”的世界中,侦探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使“失序”的社会恢复曾经的秩序,因而他们会格外注意处于秩序之外的“不和谐”与“不妥切”的事物,并把这些秩序的“裂缝”作为他们恢复秩序工作的入手点和出发点。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民国作家徐卓呆的小说《犯罪本能》,在这个故事里男主人公韦心泉因为车祸而产生了精神错乱与犯罪妄想,认为自己打劫运钞车、开枪杀人,最后还夺飞机逃走——用小说中的说法就是“刺激了犯罪本能”,出现了“用夸张的形式浮到意识中来的事”。而精神科医学博士在小说里就起到了类似于“侦探”的功能,他“不独事实,连心中想的念头都调查着”,并“最终得到了解决之钥”,不仅破解了一切真相,还成功治愈了韦心泉,恢复了世界的秩序——这里不仅指客观世界的秩序,更指男主角主观世界的秩序。
当然,这种关于“秩序”的想象在相当程度上不过是现代人的一种精神幻象,正是现代人的不安全感使他们尽力让一切看上去都是秩序井然且逻辑清晰的,似乎所有事物都是精确且可预测的,从而让人们形成一种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假象和错觉。但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侦探小说中尚未出现关于这一问题的有效反思,而西方侦探小说对此形成比较深入的思考,也要等到后来被称为“玄学侦探小说”的出现,或者是侦探小说与严肃文学更深层次的结合(如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意大利作家翁贝托·埃科、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和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部分作品)之后,才得以成为可能。
知识的占有与逻辑运思方式的使用
必须进一步指出的是,无论是世界的“可知”与“可改”,还是秩序的“先在”与“恢复”,其投射到侦探的主观世界都体现为其对于理性运思方式的使用与信赖,以及对于知识与知识之间逻辑关系的严格依照。这方面代表性的例子当首推福尔摩斯的“演绎法”,即如福尔摩斯自己所说:“逻辑学家从一滴水就能推测出它是来自大西洋还是尼亚加拉瀑布的,而无需亲眼见到或听说过大西洋或尼亚加拉瀑布。生命就是一条巨大的链条,只要见到其中的一环,我们就可以推想出整个链条的特性。”中国侦探小说作家程小青也曾对此提出过类似的反问:“故事结束了,一切疑窦都已给确凿的事实说明了,便觉得这把戏也平淡无奇。但在未明之前,它的迷离扑朔,仿佛给一层厚幕掩盖着,谁又看得透它的幕后?”在程小青的侦探小说中,能“看透幕后”之人当然只有侦探霍桑,而霍桑看透一切的方法相当程度上也要归功于其对于理性运思方式的使用。换个角度来说,在这一切情节的背后其实是作者程小青在创作侦探小说时对于理性运思方式的使用。比如郑逸梅就曾形容程小青创作侦探小说时的状态和匠心:“小青思想致密,胜于常人,当他编撰探案,例必先构一情节图。情节由甲而乙,由乙而丙丁,草图既成,进一步更求曲折变幻,在甲与乙之间,乙与丙丁之间的大曲折中再增些小曲折,极剥茧抽丝的能事,使人猜摸不出,及案破,才恍然大悟。”其中“思想致密”“构情节图”“曲折变幻”等都是理性运思方式在程小青侦探小说创作过程中的具体体现。
而在承认世界“可知”、秩序与逻辑的前提下,侦探小说中的理性又表现为一种认知的欲望,即侦探小说中的侦探通过对知识的占有来完成对客观世界的把握以及一种秩序感、可控感的获得。比如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通过对伦敦街道地名的熟稔来达到他对这座城市进行认知占有和精神把控的效果,并由此在读者心中将福尔摩斯与伦敦这座城市紧密捆绑在一起,甚至于后来的很多影视改编作品都将福尔摩斯视为伦敦治安的捍卫者与守护神。又比如由英国侦探小说家巴拉涅斯·奥克兹的《角落里的老人》所开创的“安乐椅侦探”传统中的侦探主人公们,他们足不出户,只是通过对信息和知识的掌握、分析与推理就完成了对案情真相的破解,同时也完成了对世界的“认知掌控”和想象性把握。
当然,侦探们并不是渴望占有一切知识,事实上他们也无法占有一切知识,即使是被称作“他是一架世界上最完美的用于推理和观察的机器”的福尔摩斯也要对自己所需要掌握的知识进行一番遵循实用主义原则的严格筛选:“我认为人的脑子是一个有限的空间,你必须有选择地吸收知识。你不能把什么东西都放进去,那样做是愚蠢的。如果那样做,就会丢掉有用的东西,至多是和许多其他东西混杂起来,到时候也难以应用。因此,会工作的人一定要进行非常仔细的选择,记住对他有用的东西,抛开无用的一切,并把有用的东西条理化。如果认为大脑的空间具有弹性,可以任意扩展,那就错了。请你相信,总有一天,随着你的新知识的增加,你会忘记以前熟悉的东西。因此最重要的是,不能让无用的东西排斥有用的东西。”福尔摩斯对于自己掌握知识的选择性和倾向性有时候甚至到了令人惊叹的偏激地步,比如,华生就曾对福尔摩斯在某些方面的“无知”表示感叹:“在19世纪,一个有知识的人不知道地球绕太阳运转的道理,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怪事。”
由此,华生还曾为福尔摩斯相当惊人却又十分偏颇的知识范围列出了一份“知识清单”:
文学知识——无。哲学知识——无。天文学知识——无。政治学知识——浅薄。植物学知识——片面,但对莨蓿制剂和鸦片非常了解;对毒剂具有一般知识,但对实用园艺学一无所知。地理学知识——限于实用。他一眼就能分辨出不同的土质。他散步时曾把泥点儿溅在了裤子上,根据泥点儿的颜色和硬度他能告诉我是在伦敦还是在别的地方溅上的。化学知识——精深。解剖学知识——准确,但不系统。惊险文学——十分广博,他熟悉近一个世纪发生的几乎所有恐怖事件。提琴拉得很好。善用棍棒,精于刀剑拳术。具有丰富实用的英国法律知识。
福尔摩斯通过这份他所掌握的“知识清单”完成了他对世界的认知和把握,而小说也通过这份“知识清单”完成了对福尔摩斯这个人物形象的功能性塑造。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略的是,负责列出这份“知识清单”的人是华生,而他在判断福尔摩斯具备哪些知识、又不具备哪些知识、对哪些知识有着异于常人的了解、又对哪些原本应该知道的东西一无所知的时候,其潜在的话语前提是对于一个在当时具有一般认知能力和知识储备的英国人应该掌握的知识范围的理解和预设。即我们通过华生所列出并表述的福尔摩斯的“知识清单”可以逆向推出一份华生的“知识清单”,这里面或许会有一定的文学知识、哲学知识和天文学知识等内容。小说在借助华生之手列出福尔摩斯的“知识清单”的同时,也是在间接通过华生所拥有的知识来完成对华生这个人物的塑造与想象,而这种塑造与想象同时又构成了作者对于当时英国社会中产阶级白种男性人群描摹与重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认知的欲望以及对知识的占有,落实到具体破案过程中,即表现为侦探们对具体科学技术手段的使用和信赖。众所周知,福尔摩斯经常做化学实验,比如在整个小说系列中,福尔摩斯第一次见到华生时就正在欢欣于自己“发现了一种试剂,只能用血红蛋白沉淀”,又如他非常擅于观察犯罪现场的指纹、足印、毛发、血迹等痕迹,并且能够据此作出重要的分析和判断。他甚至将这种破案技术手段从具体的探案实践层面上升到一种科学研究层面,同时还可以用来指导其他人进行类似的探案实践(即符合科学理论的可检验性与科学实验的可重复性原则)。按照福尔摩斯自己的说法:“我写过几篇技术方面问题的专论,比如有一篇叫《论各种烟灰的区别》。在里面,我列举了一百四十种不同形状的雪茄、纸烟、烟斗丝,还配有彩色的插图来说明各种烟灰的不同。”“还有一篇关于脚印跟踪的专论,里面有对于使用熟石膏保存脚印的一些介绍。这里还有一篇奇特的小文章,是关于一个人的职业怎样影响他的手形状的,配有石匠、水手、木刻工人、排字工人、织布工人和磨钻石工人的手形版画,这些对于科学的侦查是有很大的实际作用的——特别是在碰上无名尸体的案件或是发现罪犯身份等时都会有帮助。”这里的福尔摩斯俨然从侦探“摇身一变”成为“科学家”和“实验者”,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现代实验室中理性/科学/知识的神秘性也反过来为福尔摩斯这个人物的塑造增添了新的光环。
综上所述,侦探小说中的探案故事往往建立在对一个“可知”的世界想象的基础之上,将客观世界(包括他者的主观世界)理解为一种有着某种既定秩序与规律的所在。当侦探面对这种既定秩序与规律时,需要使用理性的运思方式,即通过对因果链条的遵循和严格的逻辑推理来完成对案件前因后果的整体性把握。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是侦探的认知欲望及其对于丰富且有效的知识的占有,而这种知识占有落实到具体的探案过程中,就表现为对一系列科学技术手段的借助和使用。以上这些环节共同构成了侦探小说中的理性因素。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这些意义上,侦探小说并非反映“社会现实”(social reality)的文学,而是反映“理性现实”(rational reality)的文学,因而也有学者就此提出侦探小说应该属于“浪漫主义文学”或“幻想小说”。或者用克拉考尔的话来说,“细究之,他们的作品属于一个含义层面并且听从相似的形式法则。将他们全体捆扎又铸上印记的是它们所证明的以及它们由之产生的理念: 全盘理性化的文明社会的理念,对这个社会,它们进行极端片面的把握,风格化地将之体现在审美折射当中。它们感兴趣的不是逼真地再现那些被称为文明的实在(Realitt),而是一开始就翻出这实在的智性特征。”在充盈着理性精神的侦探小说中,“作为理性轻松的扮演者,侦探漫游在人物之间的空间里”且“从一个任务赶赴又一个任务,他独自展示着理性向着无限的前进(Progressus ad indefinitu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