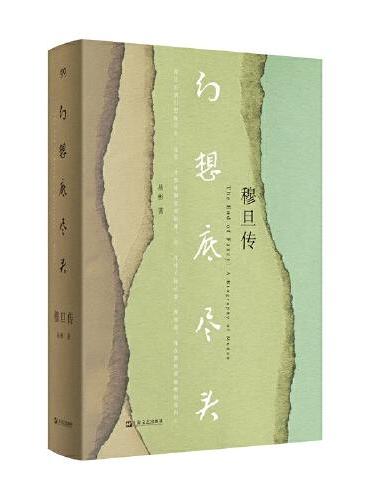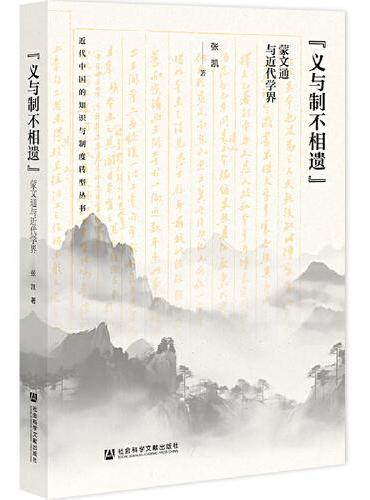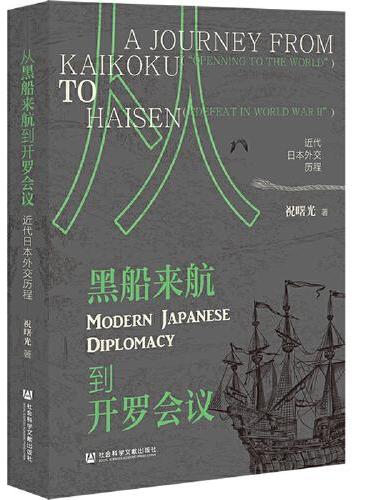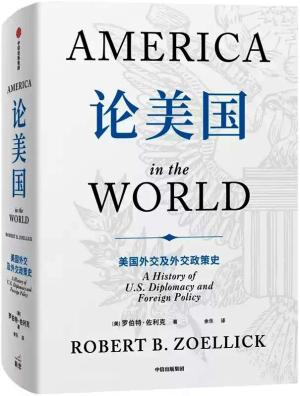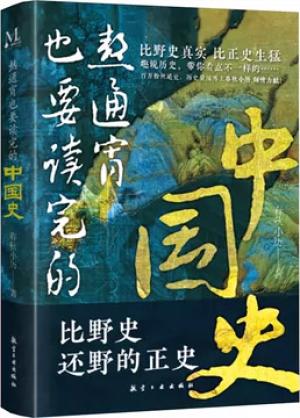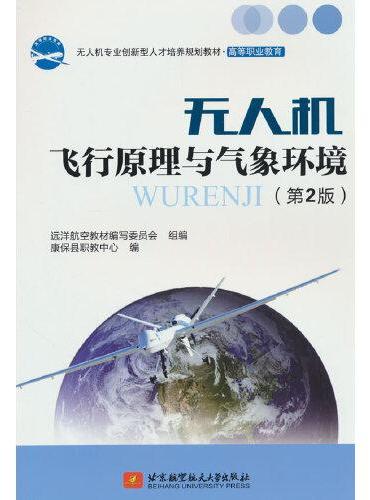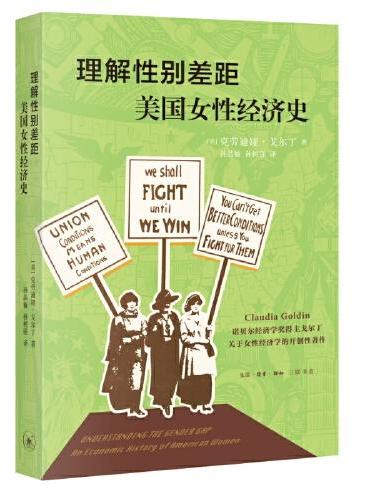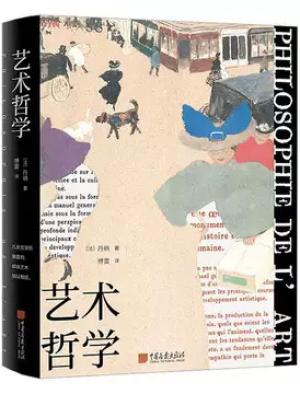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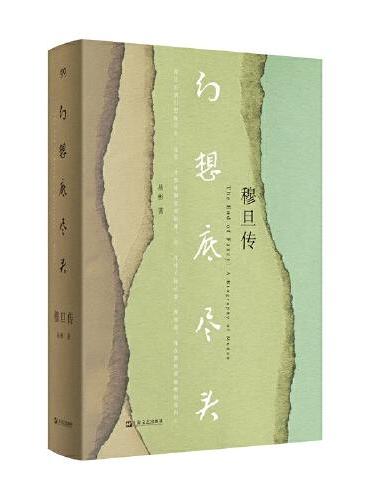
《
幻想底尽头:穆旦传(《穆旦年谱》编撰者历时二十余年心血之作,基于《穆旦评传》精心修订,文献翔实可靠,完整讲述了一位中国诗人与翻译家并不平顺的一生。)
》
售價:NT$
6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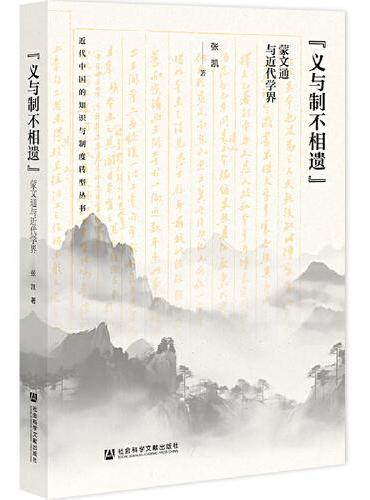
《
“义与制不相遗”:蒙文通与近代学界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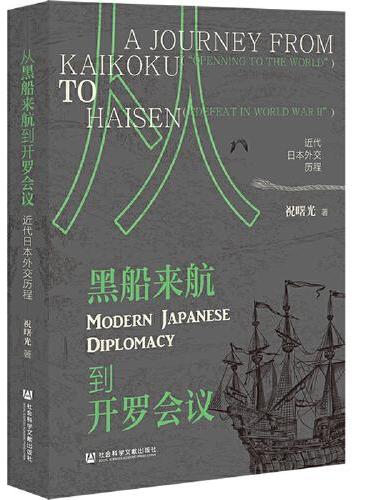
《
从黑船来航到开罗会议:近代日本外交历程
》
售價:NT$
6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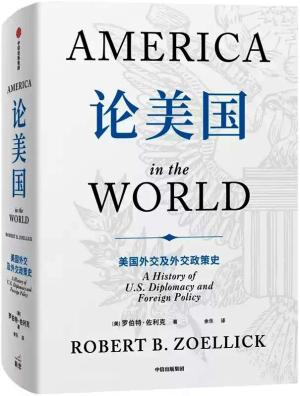
《
论美国(附赠解读手册)
》
售價:NT$
6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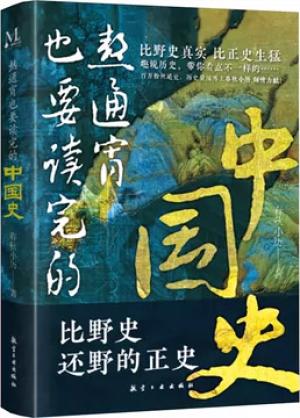
《
熬通宵也要读完的中国史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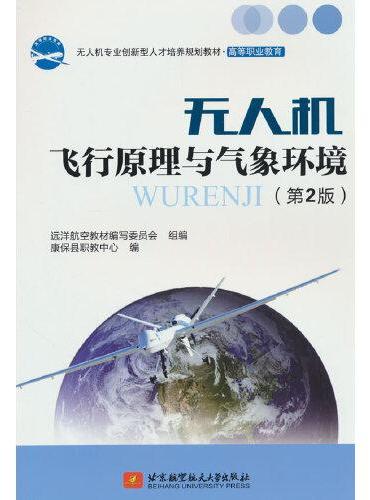
《
无人机飞行原理与气象环境(第2版)
》
售價:NT$
14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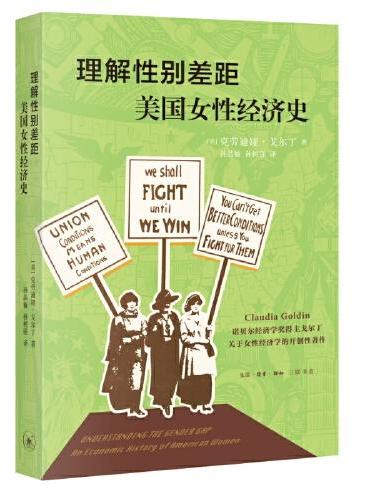
《
理解性别差距:美国女性经济史
》
售價:NT$
41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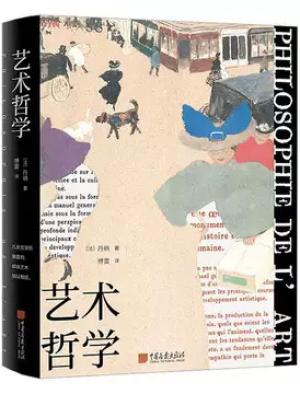
《
艺术哲学
》
售價:NT$
449.0
|
| 編輯推薦: |
站在生与死的边界,你才能看透人生参透人性,才知道什么不可缺什么不必要,勇敢地走向属于你自己的丰饶花园。书里全是香水、花卉以及不死的浪漫,正在感动全世界……
连续两年超过“那不勒斯四部曲”成为意大利热销书,30000条读者好评,看完不禁感叹:“这就是法国人!”
|
| 內容簡介: |
假如我再也听不到你的脚步声,我该如何是好?
离去的是你的生命还是我的生命?我不知道。
紫堇·万圣是勃艮第一座小镇的墓园守护人,路过的人和熟人都会来她的住处,在她为他们准备的咖啡里,混合着笑声和泪水。她的日常生活总是伴随着他们的知心话语。有一天,一个从马赛来的男人敲开了她的房门,提出将他母亲的骨灰埋葬在一个男人的墓里……从此一切都变了,记忆和现实交织在一起,生者与死者的纽带被挖掘和联接起来,一些幽暗的人生故事开始闪闪发光。瓦莱莉·佩兰与我们分享了一个女人惊心动魄的经历,她尽管经受了生活的悲辛与考验,仍执着地相信幸福终会到来。
|
| 關於作者: |
瓦莱莉·佩兰(Valérie Perrin),法国女作家,也是摄影师和电影编剧。1967年出生于孚日山区的勒米尔蒙,成长于勃艮第,1986年居巴黎,1995年移居诺曼底。
2009年,出版电影《这样的爱》(由其伴侣克洛德·勒卢什执导)图文并茂的拍摄手记。
2015年,出版长篇小说《星期天被遗忘的人》,荣获包括“书店最爱”在内的13项文学奖,被翻译成外文在十多个国家出版。
2018年,出版《墓园的花要常换水》,取得非同凡响的成功,荣获法国“新闻之家”奖和口袋书读者奖。2019年,被《费加罗报》列入“法国10位最畅销作家”,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在32个国家出版。2020年,成为意大利最畅销作家。罗马的帕洛玛(Palomar)影视公司买下改编权,她着手将这部小说改编成电视连续剧。
2021年,出版《三个人可以走多远》,再度被《费加罗报》列入“法国10位最畅销作家”。
【译者简介】
周小珊,青年翻译家,南京大学法语文学博士,巴黎第八大学文学博士,现为法国阿尔多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译著有小说《爱情没那么美好》《6点27分的朗读者》《白日美人》、亨利·米肖诗集《夜动》、让·科克托专著《关于电影》、尚塔尔·托马文论《被遮蔽的痛苦》等。
|
| 內容試閱:
|
1
只少了一个人,到处已是荒芜。
与我同住一个楼层的邻居浑身是胆。他们没有烦恼,不会恋爱,不咬指甲,不相信巧合,不做承诺,不发出声音,没有社会保险,不哭,不找他们的钥匙、眼镜、遥控器和孩子,真幸福。
他们不看书,不纳税,不减肥,没有偏好,不改变主意,不整理他们的床铺,不抽烟,不写清单,说话前不左思右想。也没有人来替换他们。
他们不拍马屁,不野心勃勃,不记仇,不爱俏,不小气,不大方,不妒忌,不邋遢,不干净,不俊美,不风趣,不上瘾,不吝啬,不爱笑,不狡猾,不粗暴,不多情,不抱怨,不虚伪,不温柔,不冷酷,不懦弱,不恶毒,不撒谎,不偷窃,不好赌,不勇敢,不懒惰,不虔诚,不奸诈,不乐观。
他们死了。
他们之间唯一的差别,是棺材的木头:橡木、松木或桃花心木。
2
假如我再也听不到你的脚步声,我该如何是好?
离去的是你的生命还是我的生命?我不知道。
我叫紫菫·万圣。我以前是看守铁路道口的,现在看守墓园。
我品味着生活,把它当作加了蜂蜜的茉莉花茶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当夜幕降临,墓园的铁栏门关上,钥匙挂在我浴室的门上时,我便置身天堂。
不是我同一楼层的邻居们的那个天堂。不是。
是活人的天堂:来一口——1983年酿制的——波特酒,约瑟-路易·费尔南德兹每年9月1日给我送过来。剩余的假日被倒进一只小小的水晶杯里,犹如秋天里的暑热,无论下雨、下雪还是刮风,我晚上七点左右都要把它打开。
两小杯红色的液体。波特葡萄的血液。我闭上眼睛。我品味着。一口就足以让我的夜晚变得愉悦。两小杯是因为我喜欢醉意,但不喜欢酒精。
约瑟-路易·费尔南德兹每周一次来给妻子玛利亚·平托的坟墓送花,除了七月份,是我代替他。所以送波特酒感谢我。
我的礼物是上天的礼物。我每天早上睁开眼睛的时候都这样想。
我曾经很不幸,甚至陷入绝望。丧失存在,被掏空。我就像我同一层楼的邻居,不过更糟糕。我的生命机能还在,但是内部已经没有了我。没有了我灵魂的重量,好像不论胖瘦、高矮,年轻或年迈,灵魂的重量都是二十一克。
而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不幸,我决定这种情况不能延续下去。不幸,总有一天必须终结。
我开始人生的方式极为糟糕。我是母亲匿名生下来的孩子,在阿登省北部,这个与比利时勾勾搭搭的角落里,那里的气候被看作“恶劣的大陆性气候”(秋季多雨,冬季常常结冰),我想雅克·布雷尔[1]的运河就是在那里上吊的。
我出生那天,没有哭。于是先申报我死亡再申报我出生的那段时间里,我被放到一边,如同一个2.67千克的包裹,没有贴邮票,没有收信人的名字。
死婴。没有生命、没有姓名的孩子。
助产士必须草草给我起一个名字,好去填写空格,她选择了紫菫。
我猜想我当时从头到脚都是紫色的。
等我变了颜色,等我的皮肤变成粉红色,她不得不填写出生证的时候,没有改掉我的名字。
我被放在暖气片上。我的皮肤热了起来。一定是不想要我的母亲的肚子让我变得冰冷。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我那么喜爱夏天,像向日葵花一样,从来不错过任何舒适地沐浴在第一缕阳光下的机会。
我没结婚前姓特雷内,跟夏尔[2]同姓。肯定是同一个助产士在紫菫之后,给我取了一个姓。她应该很喜欢夏尔。就像我后来也喜欢他那样。我很长时间都把他当作远房亲戚,好似某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美国叔叔。因为总唱一个歌手的歌而喜欢上他的时候,就会有类似亲戚的关系。
万圣后来才出现,我跟菲利普·万圣结婚之后。这样一个名字,我不得不保持戒心。但是有些男人姓春天,照样打他们的女人。一个漂亮的姓,不能阻挡任何人变得卑鄙。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母亲。除了我发烧的时候。我身体健康的时候就长个子。我长得笔直,仿佛父母的缺失为我的脊椎骨搭了一个支柱。我站得笔挺。这是我的一个特点。我从来没有弯过腰。甚至伤心的日子里也没有。常常有人问我是不是跳芭蕾舞的。我回答说不是。是日常生活训练了我,让我每天都把杆、踮脚尖。
3
让他们带我走吧或者带我亲人走吧,
因为所有的墓园总有一天都有花园。
1997年,我们的道口栏杆自动化之后,我和丈夫就失去了工作。我们上了报纸。我们代表了进步导致的最后的间接受害者,法国操作手动栏杆的工人。记者为了给文章配图,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菲利普·万圣摆造型的时候甚至用一条胳膊揽着我的腰。虽然我面带微笑,天知道这张照片里我的眼睛看上去多么忧伤。
文章发表那天,菲利普·万圣从如今已经不存在的国家职业介绍所回来,心灰意冷:他刚刚意识到他必须要工作了。他已经习惯了我替他承担一切。跟他在一起,从懒惰程度上来说,我真是撞大运了。抽到幸运数字,大奖随着而来。
为了让他振作起来,我递了一张纸给他:“墓园看守人,有前景的职业。”他看我的方式,好像我失去了理智。1997年,他每天看我的方式,就好像我失去了理智。一个不再爱他妻子的男人,看他曾经爱过的妻子的方式,是不是就好像看着失去了理智的女人?
我向他解释,我恰巧看到这则启事。沙隆河畔布朗西雍镇政府在找一对夫妻照看墓园。死人的时间是固定的,他们也没有火车那么嘈杂。我已经跟镇长谈过了,他可以马上录用我们。
我丈夫不相信我。他告诉我,巧合,他是不相信的。他宁可死,也不愿意去“那里”,去吃死人的饭。
他打开电视,玩“马里奥64”。游戏的目的,是抓住每个世界里所有的星星。我呢,我只想抓住一颗星星:幸运星。我看到马里奥四处奔跑去拯救被酷霸王掳走的碧奇公主时,就是这样想的。
我不肯放弃。我告诉他,成为墓园看守人,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份工资,比抬栏杆的工资要高很多,死人比火车赚钱。会给我们配一间非常漂亮的住房,没有任何费用。跟我们住了多年、冬天像漏水的破船夏天像炎热的北极一样的陋室大不一样。这将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很是需要,我们可以给窗户挂上漂亮的窗帘,就看不到邻居、十字架、寡妇等等。这窗帘,就是我们的生活与别人的悲伤之间的界线。我本来可以告诉他真相,告诉他这窗帘,是我的悲伤与别人的悲伤之间的界线。但千万别告诉他。什么也别说。让他信以为真。假模假样。让他屈从。
为了最终说服他,我向他承诺,他什么也不需要干。已经有三个掘墓人负责墓园的日常维护、挖掘和规划。这份工作,只不过是开开关关铁栏门而已。人要在场。工作时间不是很讨厌。假期和周末像瓦尔瑟里恩河上的高架桥[3]一样长。我呢,剩下的都由我去做。剩下的一切。
超级马里奥不再奔跑。公主滚了下去。
睡觉之前,菲利普·万圣又读了一遍启事:“墓园看守人,有前景的职业”。
我们的道口栏杆位于南锡地区马尔格朗日。我生命中的那段日子里,不能说我还活着。“我死去的那段日子里”也许更合适。我起床、穿衣、工作、买菜、睡觉。吃一颗安眠药才能睡。甚至两颗。甚至更多。我看着丈夫将我视为失去理智的人。
我的工作时间无聊透顶。我一周当中每天大约放下、抬起十五次栏杆。第一辆列车4:50通过,最后一辆列车是23:04。我脑子里自动设置了栏杆的铃声。铃声没响我就听到了。这个高强度的节奏,我们本来是应该分工的,滚动轮班。但是菲利普·万圣只会滚动两样东西,他的摩托车和他的情妇们的肉体。
从我面前经过的乘客多么令我神往。其实,那不过是从南锡到埃皮纳勒的地区小火车,每一趟停留十来座偏僻的小镇,方便当地人。但是,我羡慕这些男男女女。我想象着他们去赴约,我多么希望像这些从我眼前飞奔而去的旅客一样,能拥有这样的约会。
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三个星期之后,我们向勃艮第进发。我们从灰色过渡到绿色。从柏油路过渡到牧场,从铁路的沥青味道过渡到乡村的味道。
我们1997年8月15日来到沙隆河畔布朗西雍的墓园。法国正在放假。所有的居民都走了。在坟墓间飞来飞去的鸟儿也不飞了。在花盆之间伸懒腰的猫消失了。天气对蚂蚁和蜥蜴来说都太热了,大理石滚烫滚烫的。我一个人在小径中间闲逛,读着那些我永远都不会认识的人的名字。但是我立即就觉得很舒畅。这里才是我待的地方。
[1] 雅克·布雷尔(Jacques Brel,1929-1978),比利时歌手、作曲人。在他的歌曲《平原》里,有一句歌词是“天空如此之灰,运河也上吊”。
[2] 夏尔·特雷内(Charles Trenet,1913-2001),法国歌手。
[3] 法国里昂到瑞士日内瓦的火车铁路线上的专用桥,长158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