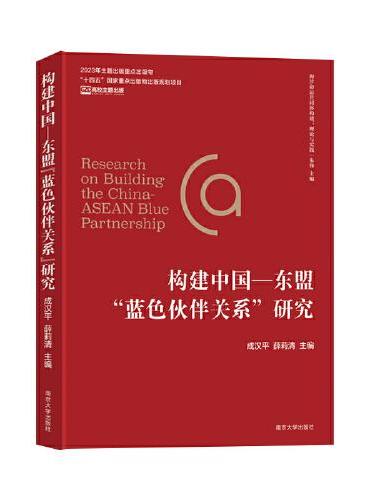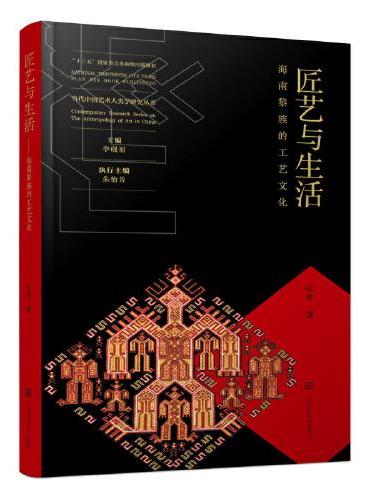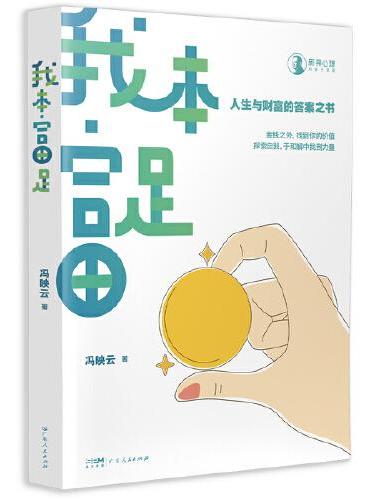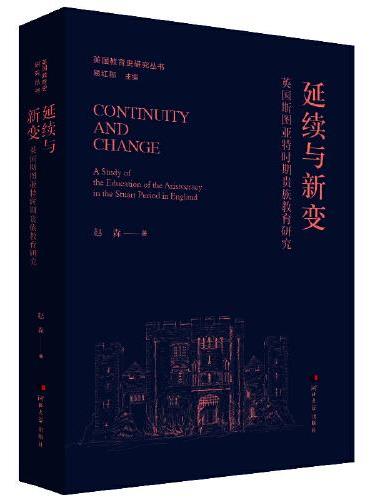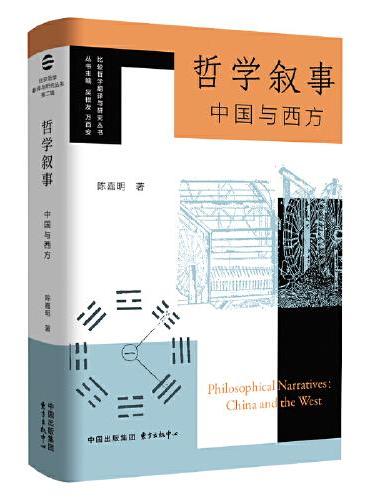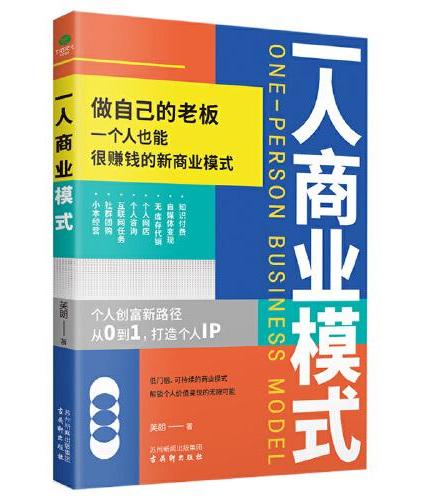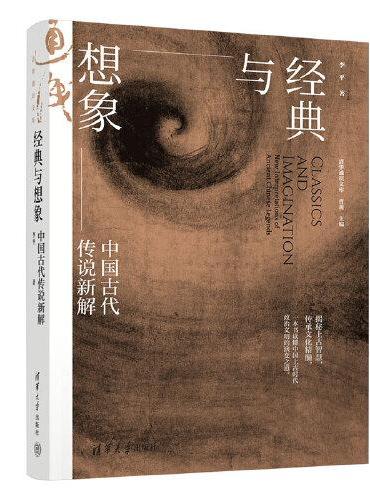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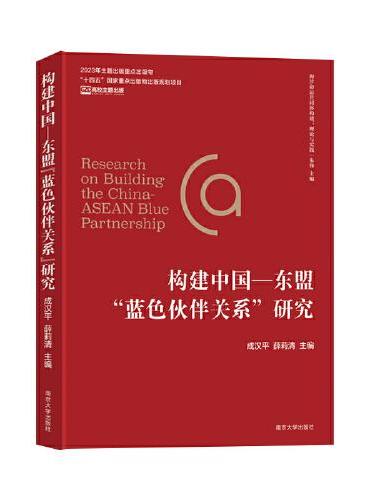
《
(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 理论与实践)构建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研究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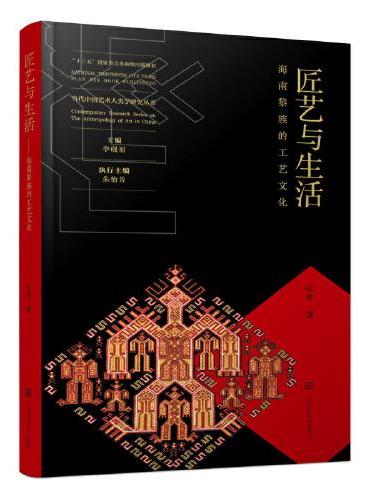
《
匠艺与生活:海南黎族的工艺文化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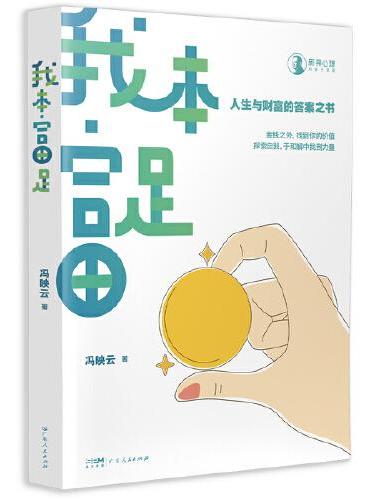
《
我本富足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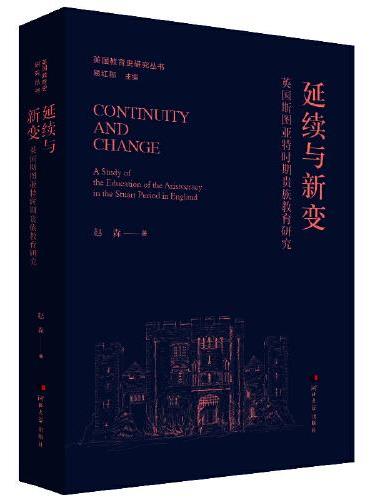
《
英国教育史研究丛书——延续与新变:英国斯图亚特时期贵族教育研究
》
售價:NT$
505.0

《
更易上手!钢琴弹唱经典老歌(五线谱版)
》
售價:NT$
2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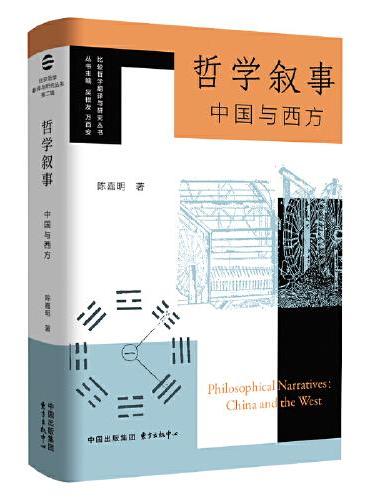
《
哲学叙事:中国与西方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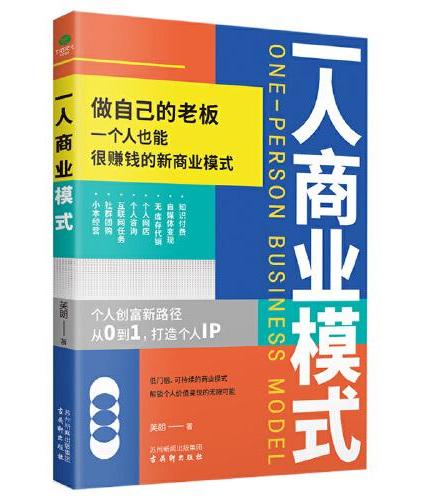
《
一人商业模式 创富新路径个人经济自由创业变现方法书
》
售價:NT$
2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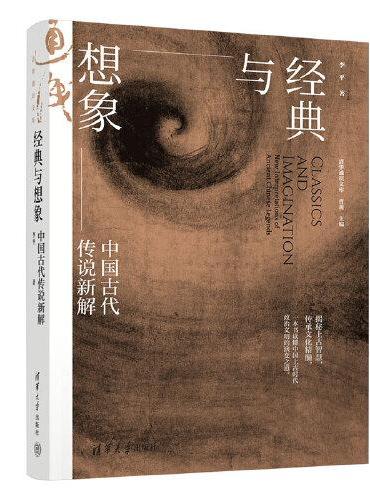
《
经典与想象:中国古代传说新解
》
售價:NT$
398.0
|
| 編輯推薦: |
1、何塞·埃米利奥·帕切科被公认为是20世纪西语文学大师之一,与定居墨西哥的阿根廷大诗人胡安·赫尔曼以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克塔维奥·帕斯并称为当代墨西哥诗坛三巨头,生前几乎拿遍西语文学界所有重要文学奖项,更于2009年荣膺有“西语诺贝尔文学奖”之称的“塞万提斯奖”。
2、《沙漠中的战斗》帕切科的短篇小说精选集,其中同名短篇是墨西哥的国民级小说,在墨西哥几乎无人不晓,被誉为“墨西哥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小说以儿童的视角出发,讲述20世纪50年代墨西哥的社会生活与权力变革,将个人经历与社会变迁相结合,感人至深,是20世纪西语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
3、本书是帕切科的小说的中文译本,由知名西语文学译者侯健编选、翻译,译文准确流畅。
|
| 內容簡介: |
|
《沙漠中的战斗》是墨西哥著名作家何塞·埃米利奥·帕切科的短篇小说精选集。同名短篇是墨西哥的国民级小说,讲述了在20世纪50年代的墨西哥——一个挣扎于贫穷、疾病和自然灾害的国家,少年卡洛斯爱上了自己最好朋友的母亲玛莉亚娜,后者是唯一真正理解并关心他成长的人,却最终被世俗社会“杀死”,消失在墨西哥的土地上。小说不仅入木三分地刻画了懵懂少年情窦初开,却最终被世俗拖垮的过程,也深刻反映出了那个年代墨西哥社会的权力构成及其经历的种种变革。而除了《沙漠中的战斗》之外,本书也同时选入了《快乐法则》《远风》等帕切科的其他短篇小说代表作,为读者全面呈现这位伟大作家的创作面貌。
|
| 關於作者: |
|
何塞·埃米利奥·帕切科(José Emilio Pacheco,1939—2014)墨西哥诗人、散文家、小说家,被公认为20世纪墨西哥的文学大师之一。其诗歌以简单直率的语言和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著称,备受卡洛斯·富恩特斯、奥克塔维奥·帕斯等大师推崇。2009年,因其崇高的文学成就而荣膺西语文学的崇高奖项——“塞万提斯奖”。侯健1987年生,文学博士,西安外国语大学欧洲学院西班牙语系副教授,拉丁美洲研究中心负责人,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文学翻译者。译有《从马尔克斯到略萨:回溯“文学爆炸”》《普林斯顿文学课》《五个街角》《科幻精神》《萨拉米斯的士兵》《33场革命》,合译有《饥饿》《书店漫游》《最后假期》。
|
| 目錄:
|
|
暗中之物 1八月的那个下午 21低洼的公园 29快乐法则 43冥河 107你是不会明白的 113女囚 123沙漠中的战斗 133耶利哥城 199远风 203译后记 209
|
| 內容試閱:
|
耶利哥城
H沿着秋意盎然的小径前进。正值正午,烈日灼人,云层时而聚拢,时而又飘散开去。他在森林里找到了一处阳光照射不到的空地,他抬头望了望天,然后在那块清凉的地面上躺了下来,他点了根烟,听着风在枝叶间穿行的呼啸声。
没有什么东西来打破这种宁静,天地万物井然有序。H目光下移,发现一队蚂蚁正在落叶之间游走,它们在搬运一只蜘蛛的尸体。还有一些在搬运食物残渣、叶片碎屑或细小的种子,它们靠近另一波蚂蚁,互相触碰触须,就像是在传递命令或交换情报。在那座地下城市的入口处,大部分蚂蚁在推动细小的沙粒,想要建造起一座壁垒来。
蚂蚁的这种努力、团结、精力和纪律性让H钦佩不已。也许这些奴隶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它们的旅程,又也许那段旅程才刚刚开始,可无论怎样,这些蚂蚁都不会想要对他造成哪怕一丁点伤害。不过H抵挡不住那种诱惑,他捏起一只蚂蚁,用指头碾碎了它。然后,他又用烟头烧得其他蚂蚁四散溃逃。
蚂蚁们扔下了它们的囚徒,队形也乱了。H烤炙那些想要藏起来的蚂蚁。消灭毫无抵抗之力的对手是一种隐秘的快乐。H变得无所不能了起来。一整个村庄就在这种破坏欲的驱动下被摧毁了。
等到地面上已经不再有活着的蚂蚁时,H便开始挖掘那些隐藏在地下的房间、客厅、讲堂、酒窖和囚室。可是翻动已经松弛的土地只是在做无用功:那座地下城市的大街小巷早就不复存在了,H永远也无法亵渎蚂蚁们最神圣的领地。在站起身子前,他把周围的干草堆了起来,在废墟之上又点了把火。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奇怪的味道。
半小时后H爬上了可以俯瞰首都的大山。他走到陡峭的悬崖边,立刻就看到了恐惧、混乱、吞噬整座城市的火焰和被遗弃的房屋,致命的气体弥漫在所有角落,与此同时,蘑菇状的烟雾和瓦砾碎片随风盘旋而上,朝着高悬在空中的正午烈日袭去。
远风
骚动的夜晚,只有流动游乐场还保持着宁静。茅屋的一端,一个大汗淋漓的男人抽着烟,盯着镜子,看着镜中烟雾弥漫。灯灭了。空气仿佛凝滞了。男人走到水族箱前,划亮火柴,借着火光望向卧在水中的乌龟。他想到了把他和它分隔开的光阴,也想到了那些被远风卷走的日子。
阿德里亚娜和我在村中闲逛。我们在广场上遇见了那个流动游乐场。我们坐了摩天轮、碰碰车和旋转飞椅。我射中了小铅人,做了泥塑手工,忍受了电击游戏,还从一只训练有素的金丝雀那里拿到了预言我未来命运的红纸。
我们在那个周日的夜晚遇见了这片让我们体验到幸福的地方;换句话说,这里让我们暂时将过去和将来抛在了脑后。我拒绝进入一个摆满镜子的房屋,这时阿德里亚娜看到游乐场的边缘有间透着悲伤气息的荒凉茅屋。我们走到它跟前时,站在门前的那个男人说道:
“请进,贵客们。来听听‘丛林之母’的故事吧,她是个不幸的小姑娘,由于不听长辈的话,也不在周末去望弥撒,被上帝降罪变成了乌龟。来看看‘丛林之母’吧。诸位可以听她亲口讲述自己的悲惨故事。”
我们走进茅屋。“丛林之母”就在一个被灯光照亮的水族箱里,她长着小女孩的脸,却有具乌龟的身躯。阿德里亚娜和我感到羞愧,因为我们置身于她的面前,以羞辱这个男人以及极有可能是他女儿的这个小姑娘为乐。讲完故事,“丛林之母”透过水族箱望向我们,她的表情像极了倒在猎人脚下鲜血淋漓的动物。
“太可怕了,太糟糕了。”我们走出茅屋时阿德里亚娜这样说道。
“每个人都要尽己所能去谋生。还有很多比这更糟糕的事呢。你听我说,那个男人会模仿其他人说话,而那个小姑娘其实是跪在水族箱后面的。
他们借助光影效果让你相信她长了具乌龟的身子。这就跟变魔术一样好理解。你要是不信的话,我可以带你去搞清楚他们耍的是什么把戏。”
我们返回茅屋,我在隔板中间寻觅着凹槽。过了一分钟,阿德里亚娜乞求我带她离开那里。不久之后我俩就分手了。后来我们还见过几次,但从来没谈起过在游乐场中度过的那个周日。
乌龟的眼中噙着泪水。那个男人把它从水族箱里抱了出来,放在地上。乌龟脱掉了小女孩头套。它真正的嘴巴说着些无法在水外听到的深沉话语。男人跪了下来,把它搂入怀中,抱到胸口,他亲吻它,在它那潮湿的硬壳上哭泣。没人会理解他对它的爱,也没人会理解把他和它分隔开来的那种无尽的孤独。他们就那样静静地相拥了几分钟。后来,他又给它戴上了那个塑料头套,再次把它放到水中淤泥之上,他控制住抽泣的冲动,又走到门外,再次售卖起了门票。水族箱被照亮了。泡沫升起,乌龟的故事在继续。
女囚
早晨六点时,剧烈的震动似乎要将整个村子连根拔起。我们跑到街上,十分害怕房子会塌。后来我们又担心大地会裂开一道缝隙,把我们都吞进去。震动平息后,我们的妈妈们依旧在祈祷。有人说地震会卷土重来,而且威力还会更大。我们以为既然大家如此焦虑,那么我们肯定不必去上学了。我们还是上学去了,比平时到校的时间晚了两小时,可其实我们压根儿就没有上课:我们只是交流着彼此的经历。
“1934年的时候,”老师说道,“流传着许多迷信的说法,你们肯定想象不到那些说法让你们家里的大人们感到多么害怕。今早发生的事情并不是神的惩罚。只不过是个自然现象罢了,是地壳运动的结果。通过地震的事我们就能看清楚新
东西远比旧东西要好得多。你们都能看到,在地震里面受损严重的基本都是殖民时期的建筑。那些现代建筑则经受住了考验。”
我们在各自的父母面前复述了老师的观点。他们认为这证明公立学校是在通过这些说法来使我们背弃信仰。下午,一切恢复正常之后,我和好朋友吉列莫、塞尔希奥见了面。吉列莫提议我们到修道院废墟去探险。我们早就想去那里玩了,尤其想藏到里面的单人牢房中去。修道院是1580年时在山顶建成的,人们想从那里掌控生产谷物的谷地。十九世纪时胡亚雷斯政府把它征用了,法国人入侵期间那里又变成了军营。由于战略位置过于重要,革命战争时期那里遭受到了轰炸,1929年反取缔教会战争时期被彻底废弃。没人敢靠近那里,“那儿太吓人了”,大家都这么说。
尽管如此,我们却总是把深入探索那里当成冒险游戏,可是在那之前我们一直不敢在晚上到那里去玩。正常情况下,在那个时间跑到那所修道院里去肯定会让我们吓破胆。不过那天下午发生的一切都难以解释,我们只是觉得好玩。
我们穿过河流和墓地之间的草地。垂到西边的太阳照着墓碑。我们没有走那片被汽车和骡车摧残得不成样子的斜坡,而是走了条我们惯抄的近道。我们爬上另一个陡坡,后来由于坡度过大,我们几乎是紧贴着坡面前进的。没人敢扭头看,因为高度会让我们感到头晕目眩。可是我们每个人都在默默地坚持着,我们想证明其他两个人才是懦夫。
到达山顶后,我们没时间欣赏修道院外墙上新添的裂纹。这片废墟又一次战胜了彻底摧毁它的企图。唯一一件奇怪的事情是地上有大量蜜蜂的尸体。吉列莫用手指夹起一只,然后又走到我们身边。中央庭院不断被杂草和荆棘丛侵蚀。朽掉的房梁从墙壁裂缝中伸了出来。
我们沿着盖满苔藓的走廊向里走去。潮湿气息和硝石抹掉了这个古老的回廊给人带来的一切清凉感,它还曾被用作矿工们吃饭的地方。我们每向前走一步,心中的恐惧就更盛一分,可是我们都不敢承认这一点。
我们觉得回廊比修道院中的其他地方受损更
严重。我们沿着破损的台阶上了楼。天已经黑了。外面开始下雨了。雨水敲击着多孔的石块,不断发出回响。夜的声音慢慢在周边响了起来。光线在黑暗中扩散,风在低吟。我们只带了一个手电筒,那是吉列莫从他爸爸那里借来的。
塞尔希奥从窗户探出头去,他说墓地那边有很多火球。我们都发起抖来。远处传来阵阵雷声。几只蝙蝠飞离房顶,它们扇动翅膀的声音在穹顶回荡。我们撒腿就跑。我们下到一半楼梯时又被塞尔希奥的喊叫声吓了一跳。吉列莫和我返回去找他。我们看到他缩在阴影中发抖,还指着一间单人牢房。我们搀扶着他的胳膊把他架了起来,我们不再掩饰自己的恐惧了,不过我们还是往他一边从嗓子里发出咕噜的声音一边用手指着的那个地方走去。
走进那个房间后,塞尔希奥挣脱了我们。他拔腿就跑,逃走了,把我们两人留了下来。吉列莫打开了手电筒。我们发现地震震倒了一面墙,一片埋骨地暴露了出来。借助手电筒的光线,我们能在头骨和骨骼之间辨识出一个被捆绑在金属
椅子上、穿着黄色大褂的女人:那是一具被风干的尸体,她的躯体流露出无尽的平静和永恒的静止。
我感到恐惧游走于全身。我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不过我在一瞬间战胜了恐惧,朝着死者走了过去。吉列莫嘟囔了句什么,想要阻止我。我走到埋骨地里,一直走到死者身前,她的面孔已经模糊不清了,我伸出几根手指,用指尖触碰了一下她的额头。我用的力量极小,可哪怕如此,她的整个身体也立刻垮了下去,变成了覆盖在金属椅子上的一摊灰尘。
仿佛整个世界都随着那个女囚化为了灰尘一般。我好像听到了一声压抑了几个世纪的巨响。天地在我眼前旋转了起来。我以为秘密被揭穿后,修道院就要在我们面前垮塌了。我被吓得呆立在原地。吉列莫反应了过来,把我从那里拉了出来,我们冒着坠亡的危险飞速奔下山去。
我们在山坡上遇到了我们的父母和其他一些出来找我们的人。他们已经听依旧在发抖的塞尔希奥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有几个人还想过爬到废墟上去。桑蒂延神父把我们带去了他的教堂,用
圣水给我们划十字。吉列莫的妈妈则给我们灌草药水和玉米茶。
一个半小时后,那些爬上山到修道院里查证我们讲述之事的人们回来了,大家在圣器室碰了头。老师试图找到某种合理的假设来说服全镇的人并羞辱神父。地震,他坚持说道,暴露出了一个古老的地下墓穴,里面的人骨早就差不多腐朽殆尽了。根本没有什么风干的尸体。当然了,墓穴里出现一把金属椅子的事确实有点奇怪,但很可能是负责管理墓穴的神职人员留下的。没有什么被我一碰就散的尸体,都是我们的想象罢了,因为我们当时太害怕了,毕竟那个地方很黑,而且还流传着许多没有历史依据的传说。我们的幻觉,他总结道,是合情合理的,每个人在由地震造成破坏的房间里都会感到极度不安。
解释是无用的,人们只是开着玩笑,安慰我们。我一整晚都没合眼。那具被我轻轻一碰就化为尘埃的尸体的样子不断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在所有那些问询者中只有桑蒂延神父没有威吓我们,而是接受了我们的说法。他说我们为镇子里的一桩传奇罪行画上了句号,人们认为那样对待她只是为了复仇,尽管没人能搞清楚那件事的真相是什么。
那具在我的触碰下瓦解掉的尸体属于一个在十八世纪被灌下麻醉药的女人。当她再次睁开眼睛时,她发现自己被关到了一个地下墓穴之中。她是在焦虑、饥渴、无法从那把我们在一百五十年后找到的椅子上离开的状态下死去的。她是镇上一个官员的妻子。她被控犯下了两种重罪:和修道院里的一个修士通奸,还把他们生下的男孩扔进了井里。
吉列莫问当时的人是如何惩罚那个修士的。
“他被发配到菲律宾去了。”桑蒂延答道。
“神父,您不觉得这很不公平吗?”我大胆地问道。
“也许也应该严惩那个修士。尽管我不赞同把她关到那里去的做法,可是你们也不要忘记德尔图良*说过的话:‘女人是魔鬼的大门。她把邪恶放入天堂,把天堂变成满是泪水的谷地。’”
时光飞逝。1934年的那些男孩子如今已经长成了大人,我们也分散了。我在镇子上的生活永远结束了。我再也没回去过,也没再见过塞尔希奥或吉列莫。但是每次地震都会让我感到无比恐惧。我总感觉大地会把藏在它体内的尸体送到我的眼前,借我之手给他们带去宁静的结局和又一次死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