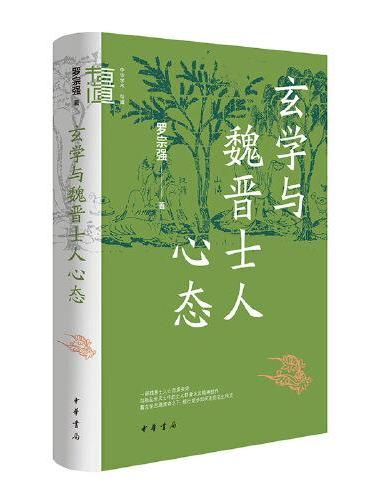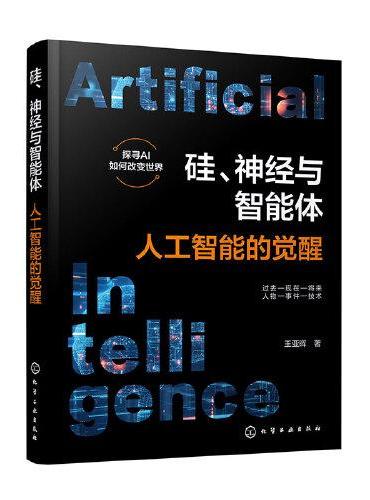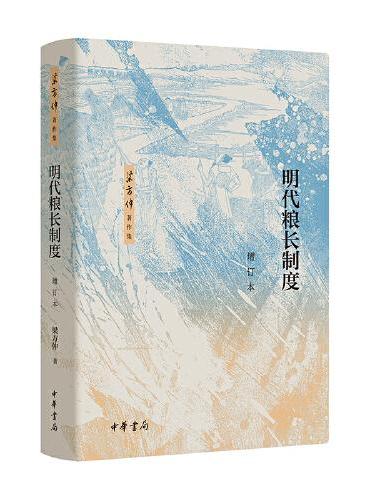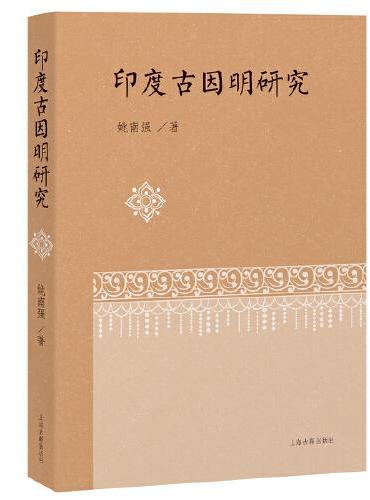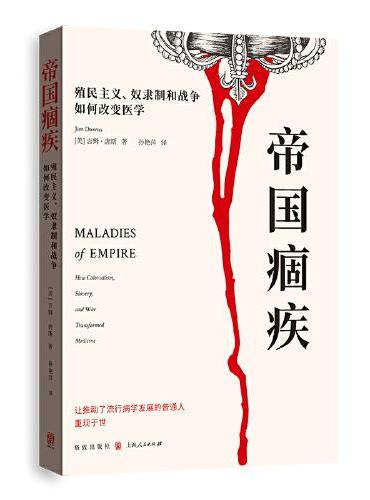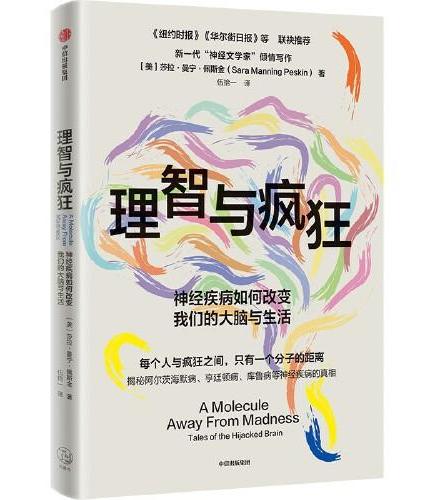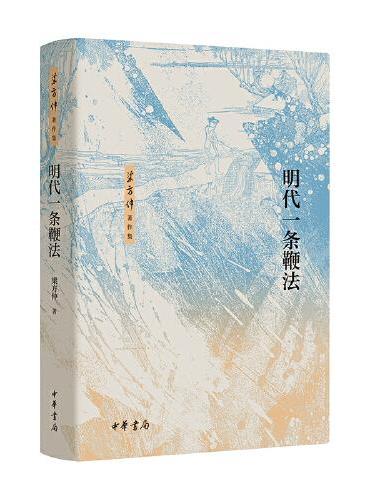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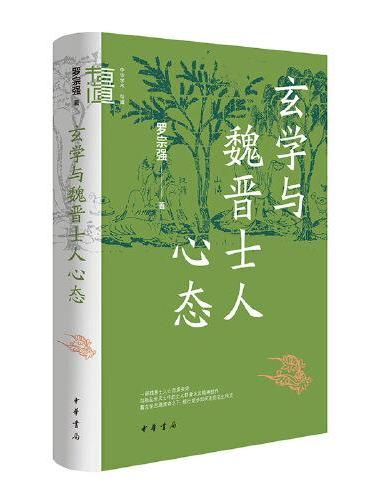
《
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精)--中华学术·有道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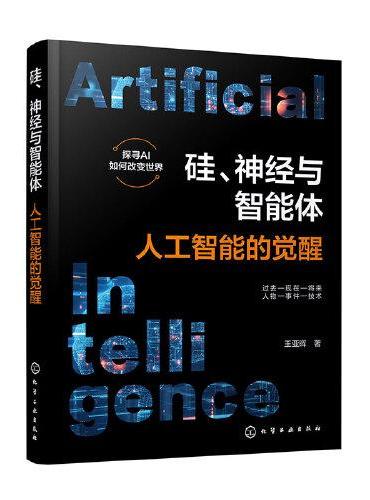
《
硅、神经与智能体:人工智能的觉醒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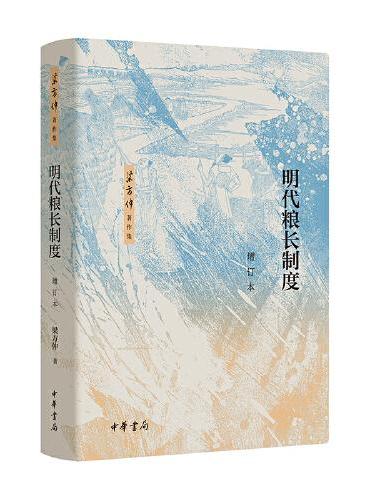
《
明代粮长制度(增订本)精--梁方仲著作集
》
售價:NT$
316.0

《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本雅明精选集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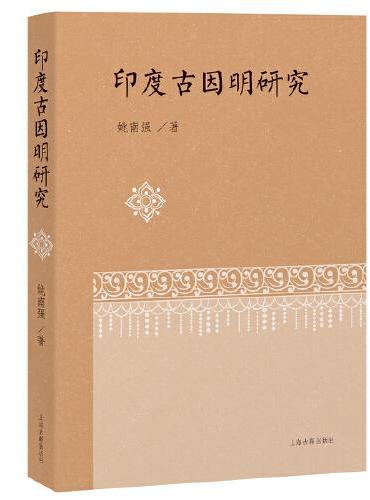
《
印度古因明研究
》
售價:NT$
6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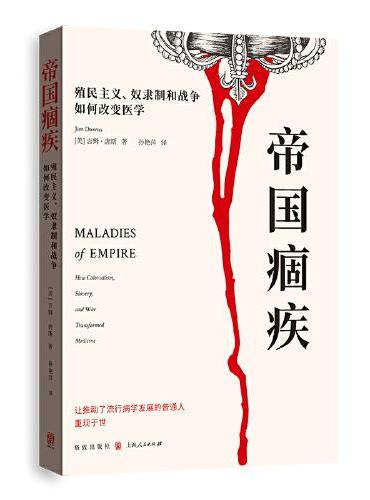
《
帝国痼疾:殖民主义、奴隶制和战争如何改变医学
》
售價:NT$
36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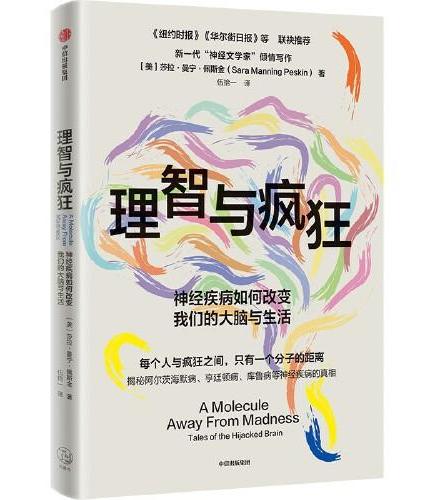
《
理智与疯狂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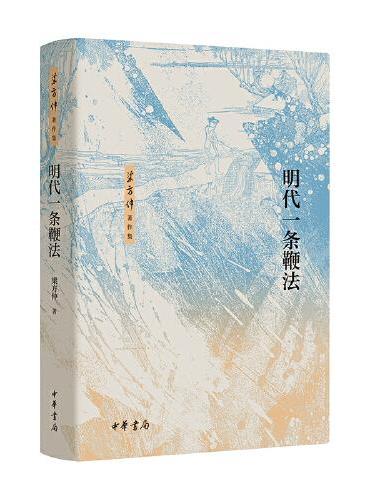
《
明代一条鞭法(精)--梁方仲著作集
》
售價:NT$
398.0
|
| 編輯推薦: |
▲ 阿乙蕞具风格的作品之一,冷峻写实 冷酷想象,写作内容极大丰富
《情史失踪者》是阿乙蕞具风格的作品之一,既有冷峻的写实,也有冷酷的想象:小城里互相敌视的祖母和孙女,目睹儿子重病眼睁睁看他离去的母亲;村民活捉死神,残忍折磨后却又被他逃脱,王国太子在神秘的舞蹈仪式之后,等来了自己最终的命运……
相比于以往的小镇青年题材,《情史失踪者》写作内容极大丰富,正如题献页写下的那句:“尽量多地表现。”
▲ 写给每一个在故事里失踪的人,八篇故事,总会使你想起自己故事里的“失踪者”
每一个人都是自己或他人故事里的失踪者:在爱情,在事业,在故乡,在梦境……《情史失踪者》写给每一个在故事里失踪的人。八篇故事,总会使你想起自己故事里的“失踪者”——你被寻找,或者,你被遗忘。
▲ 精准而老辣的笔法,令人印象深刻的金句
阿乙以精准而老辣的笔法著称,在《情史失踪者》中留下了众多令人印象深刻的金句:
“她就像一头看似庞大的抹香鲸,孤独地死在我记忆的脑海里,被腐食者及多毛类和甲壳类小型生物食用四到二十四个月,悄然分解。我一生中要忘记很多这样的人,经过我的,我经过的。几百个,成千个,上万个。”
“我们多
|
| 內容簡介: |
《情史失踪者》是阿乙的短篇小说集,写给每一个在故事里失踪的人:
身患绝症的丁洁妮如愿见到失踪已久的爱人,然而一切不过是一场梦境;
失去公职的李伟成为生活里的失踪者,等待着他的,是一次阴差阳错的抓捕;
作家陈白驹在读到年轻人神灵附体般写就的文字时心下恍然:从前的自己早已失踪;
离家已久的艾国柱回到老家,自以为是失踪之人,却被盲眼的算命先生直接道出身份;
天真的太子春卿对周围众人的舞蹈苦思无解,在王国的记忆里失踪是他逃脱不了的命运……
|
| 關於作者: |
|
阿乙,江西瑞昌人,生于1976年。出版有小说集《灰故事》《鸟,看见我了》《春天在哪里》《情史失踪者》《骗子来到南方》,中长篇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模范青年》,随笔集《寡人》《阳光猛烈,万物显形》。作品被翻译成十三种语言在海外出版。
|
| 目錄:
|
对人世的怀念
虫蛀的外乡人
作家的敌人
肥鸭
情史失踪者
虎狼
永生之城
忘川
|
| 內容試閱:
|
情史失踪者
———来自朋友的一个浅薄的梦
我从梦中完全醒了过来。一位陌生人站在黑暗中。因为穿着深颜色的皮鞋、长裤及高领毛线衣,他的身躯融化进黑暗中(此时,光明就像大军从紧闭的绛紫色窗帘外浩浩荡荡地经过)。而那张梨色的形同老尸的脸犹如一盏点亮的光线暗淡的许愿灯,悬浮在我眼前。挺吓人的。他向后退却,就好像不是他不事声张地站在这里吓坏了我,而是我的苏醒吓坏了他。他试图掩盖什么,却什么也掩盖不了,或者说,也没什么具体的东西需要去掩盖。后来我从他那总是盯着一个人看形若痴呆的眼神觉察到,他要掩饰的正是对我的长久注视。他是在我睡觉时潜进来的,一直看着我睡(在睡眠中我咂嘴,像一条毛毛虫那样蠕动与翻转身体,有时还拿爪子在胯裆?痒)。他一边看着我一边比较他自己,然后不服气地想:这个人何德何能啊,他也不瞧瞧他自己。
醒来时,房间里多出一人,而且还是名男性,我却不害怕,或者说害怕也只是程序性地害怕,这让我对自己感到不可思议。我们僵持的时间越长(他将右手半举在左胸前,呈半握拳状;左手抚摸着腹部;他的八字胡与络腮胡连接在一起;头发拳曲,然而拳曲得不太自然,就像是被他姨公硬生生扯成这样的;毛线衣显得松垮肥大,肩膀又过于瘦削,因此整个人看起来像是一株被遗弃的黑色圣诞树;他的脸显得小,额头小,眼睛小,鼻子小,嘴唇小,下巴颏儿小,眉骨倒是挺高,就像是立着的一处高墈,从陡峭的眉骨下到深陷的眼窝那儿可能还需要纵身一跃呢;在他身上散发着一股自以为是的悲伤感、正义感,一举一动都有很强的仪式性;他这会儿正半歪着头,眼带一丝哀求,一动不动地看着我),我心里就越出现一个念头。这个念头要我——一名被害人——去同情已来到面前的擅闯民宅的强盗。我估摸着他年龄比我还要大。应有四十岁。这是个来自时间深处、像是重复过多次甚至有点喋喋不休的念头:对他好点。我越是这么强调,越是控制不住自己。在他从背后抽出那把刃长十九厘米、柄长十二厘米、宽度最宽只有三厘米的妄称是不锈钢刀的裁纸刀后,我粗鲁地夺过它。这真是一把滑稽的刀啊,将将能切动西瓜,铅笔都削不了。正因为它丝毫起不了恐吓的作用,我只用单手去夺它。不过当它在纠缠中割坏他长着不少毛细血管的透明耳朵并使耳廓那里冒出一滴饱满的血时,我还是为它所拥有的破坏力感到吃惊。他摸摸,搓捻搓捻,懊恼地看着指尖黏糊糊的血迹,说:“有纸吗?”于是我扯出一张又一张一共四张抽纸给他。
他叫马丁。跟着他来的那伙人就没那么好说话了。在听见楼上的动静后,他们冲上来,以饱满的激情—我们常在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那里见到这股激情—踹开我所侨寓的这间屋子的房门。插销给踹脱了。你妈×给脸不要脸是吧,他们连出数掌,将我推向墙边。马丁厌烦地走到他们和我之间,埋怨他们。可以想见,起初他们是想一起上来的,被阻止了。马丁说:“让我一个人先上去试试。”而这可能还是她的意思。不要得罪他,她凄凄切切、病病殃殃地躺着,声音微弱地向她的表哥马丁交代。
他们不是出于恶意,而仅仅只是认为这样做效率更高,才将我架起来。我感觉自己就像是在云端飞翔了一会儿,然后被塞进一辆黑色的没洗过的奇瑞轿车里。车内满是烟蒂被残茶浸泡过的气息。他们烦躁地放了一会儿Lady Gaga、刀郎与庞龙的歌,尽显京郊农民本色。途中,我突然抓了一下马丁的上臂,说:“你还是单身吧?”
“你怎么知道的?”他显得诧异。
“你脸上有一股像秋霜一样严峻的东西。”我说。
我就没说我注意到他总是拿鼻子去嗅自己惯用的那根食指。在侦察学里,犯罪的人总是控制不住想回到作案现场,以排查是否仍留有证据。
他的母亲叫丁弟英,舅舅叫丁本领,表妹叫丁洁妮。若不是他这次前来绑架,我可能要永远忘记丁洁妮这个名字了。
我是在当时还健在的钱柜KTV套间认识她的,或者说是她在那里认识我的。当时我与身边一位丰腴的女孩相谈甚欢(不知为什么,一想到白嫩丰腴的女人我就心头发紧,喘不上气来),直到我违背祖训(“紧闭嘴,慢发言。”我的父亲屡次这样交代),轻易置评当时流行的某位明星(我认为双栖是一个人在躲避自己两方面的无能),挨到对方的一顿狠戗。我望着茶几上像塔楼一样林立的喜力酒瓶,懊恼极了。这次打击给我留下严重的心理阴影,以至于有三周时间我都不怎么敢议论别人。我哪知道到处都是这歌星的粉丝呢。我以如厕为名义,离开了钱柜。有人为这次周末常有的聚会留下一帧照片。当时我处在右二,右三是胖姑,而丁洁妮处在右六,也可以说是左一。那是个沙发转角的地方。她双手抱头,仰着脸,静听在房间内冲来撞去的歌声,以及梳着大奔头的我对邻座的恭维。那时我表现得像一名雄辩家,像一头狮子。几十天后,我对胖姑娘没演说完的东西,滔滔不绝地对丁洁妮说完了。我说得是那么痛快和意犹未尽。我想起一位卖力的球员,在得到教练的明确指示后,上场将几乎能碰见的对手都铲翻了,铲完大嘴一咧,齿上还滴着痰。当时我和丁洁妮坐在一把海蓝色遮阳伞下,她南我北,雨急切地来了一阵,打落在伞布上的铮铮淙淙的声响让人想起歌剧院经久不歇的掌声。《新京报》最后一版预测这是场“廿年不遇的大雨”。然而一会儿它就变小了,毛毛细雨在意外出现的日照里斜飘着。其间,一架飞机从平地起飞,在上升的过程中,都能看见它收起机轮,就像鹞鹰缩回双爪并将之贴紧于腹部。我静静地看了一会儿森白的机腹,接着讲了下去:不敢相信这样的事实就在眼前发生,哇哦。她一直饶有兴致地听着,简直入了迷,尽管我看出这其中还是掺入了一些礼节性的坚持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