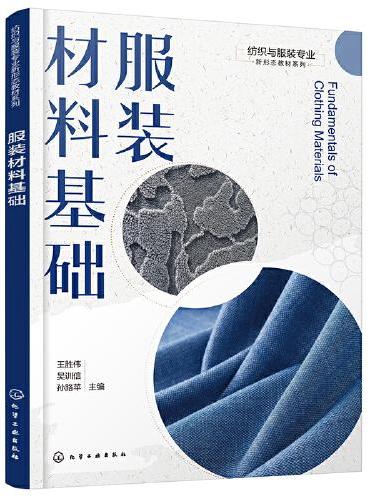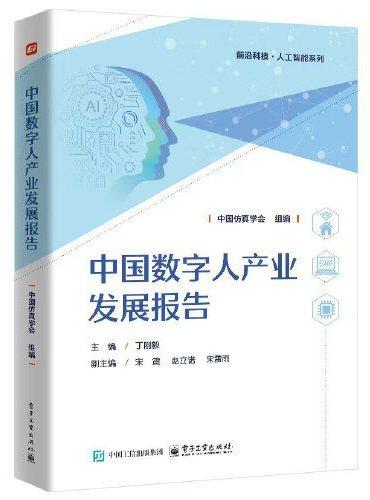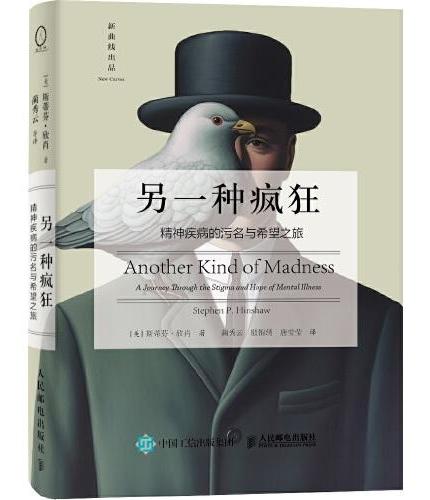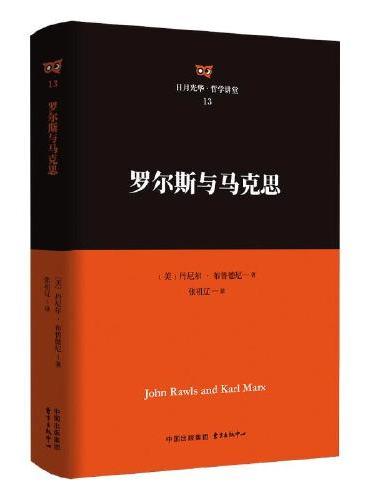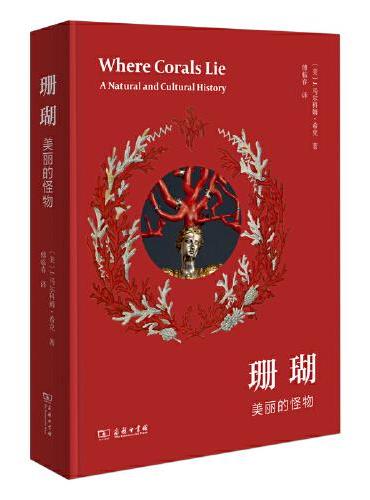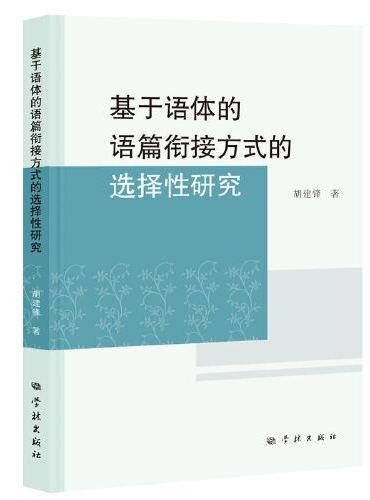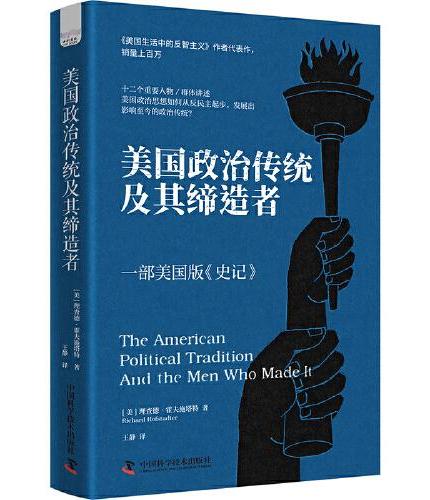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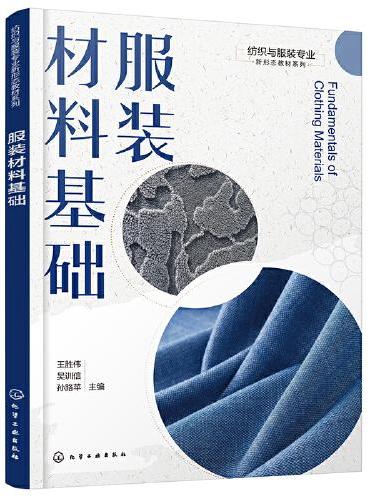
《
服装材料基础
》
售價:NT$
296.0

《
国家名片C919(跟踪十余年,采访百余人,全景式呈现中国大飞机C919,让读者领略到中国航空科技的最新成就)
》
售價:NT$
6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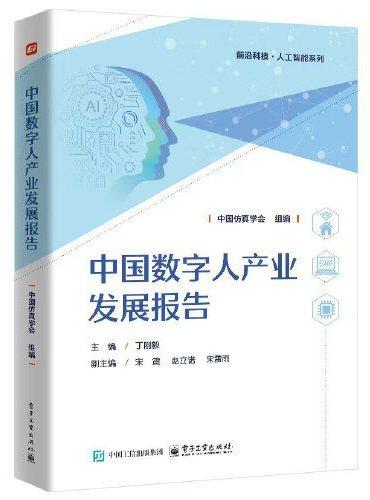
《
中国数字人产业发展报告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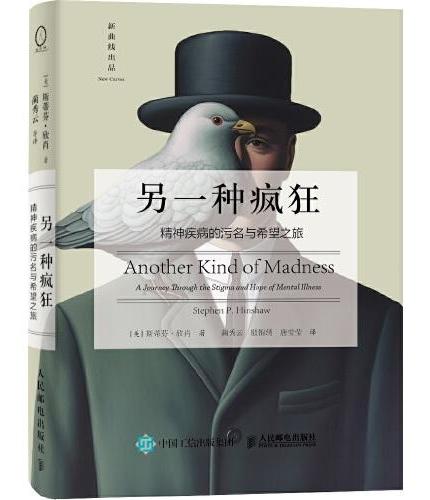
《
另一种疯狂:精神疾病的污名与希望之旅(APS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斯蒂芬·欣肖教授倾其一生撰写;2018年美国图书节最佳图书奖)
》
售價:NT$
2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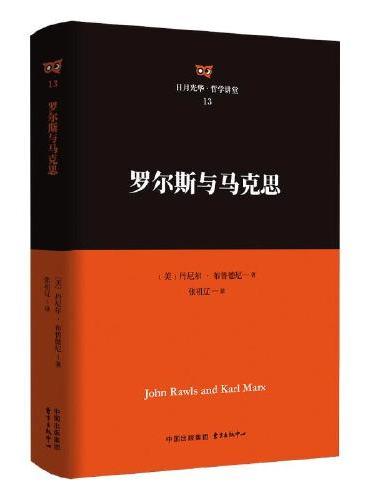
《
罗尔斯与马克思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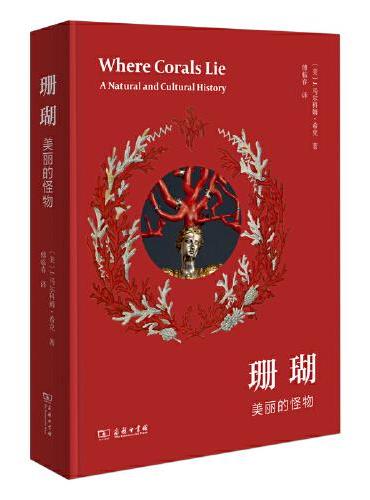
《
珊瑚:美丽的怪物
》
售價:NT$
58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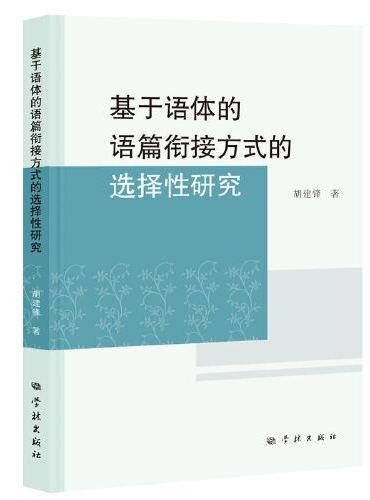
《
基于语体的语篇衔接方式的选择性研究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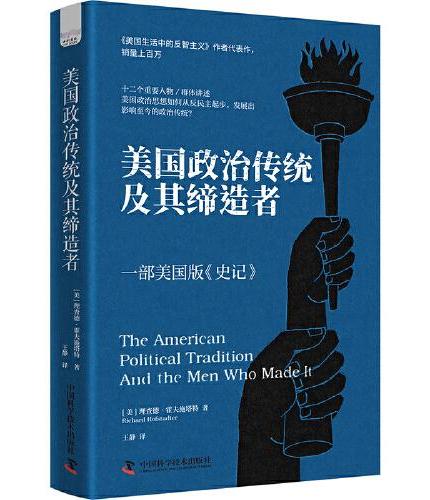
《
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一部美国版《史记》
》
售價:NT$
449.0
|
| 編輯推薦: |
李零的杂文作品,因其敢于说真话、笔下有真情而备受关注,拥有大批读者。本书是继《放虎归山》《花间一壶酒》《何枝可依》《鸟儿歌唱》后,李零的又一部重磅新作,汇集了作者近三十年写作的怀念亲友、师长,以及记述自己人生经历的文章,是李零杂文作品中别具特色的一部。
在众人眼中,李零是一位成就斐然的学者、追捧的对象;在这本书中,李零却用极为平实的语言讲述着自己“出乎意料”的人生经历:没上过大学,也没读过博士,现在走到这一步,自己也没想到;小学和中学时代,是个“坏学生”,却发誓将来要当个好老师;插队期间真的当了老师,又自我感觉很失败……“工农兵上大学”没上成,遂埋头研究银雀山汉简,结婚生子了,却还没有工作,面对两份“铁饭碗”,终究没能下决心……没想到后来当上了大学老师,更没想到会拜在名师门下,做自己一生最想做的事……
在这本书中,李零自始至终“用自己的生命体验来讲话”。对故人、故事的记述,也蕴含了有价值的学术史料;对亲人、师友的追忆,也让自己的人生经历跃然纸上。一篇篇文章也是一帧帧老照片,它们铸成的记忆大厦,是对李零其人的最好注脚。
|
| 內容簡介: |
|
这是一部怀人忆旧集,汇集了李零近三十年所写的怀念亲友、师长,以及记述自己人生经历的文章。父亲、母亲、岳父,张政烺、俞伟超、高明、张光直……书中所记述的亲友、师长,对李零影响深远。本书带有显著的自传色彩,是一部散点透视般的回忆随笔集。
|
| 關於作者: |
李零,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研究、著述范围涉及诸多领域,如考古、古文字、古文献,以及方术史、思想史、军事史、艺术史和历史地理。
李零已在三联书店出版了《我们的经典》《我们的中国》《波斯笔记》《铄古铸今》《万变》《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兰台万卷》《小字白劳》《十二生肖中国年》等书。他说,他的书都是读书笔记。
|
| 目錄:
|
写在前面
自 序
第一辑
读《少年先锋》
大山中的妇女解放
母也天只(短札三则)
黄泉路上蝶纷飞
——怀念我敬爱的傅懋先生
天地悠悠(上)
天地悠悠(下)
第二辑
三位贵人
——程德清、侯大谦、常任侠
我的老师梦
赶紧读书
——读《张政烺文史论集》
成人一愿,胜造七级浮屠
——我的老师和我的老师梦
第三辑
写在前面的话(《四海为家》)
我心中的张光直先生
第四辑
最后的电话
第一推动力
——怀念俞伟超老师(摘录)
持诚以恒,终无愧悔
——从高明老师的书读到和想到的
《高明先生九秩华诞庆寿论文集》献辞
我认识的李学勤先生
第五辑
维铮先生二三事
纪念齐思和先生
——写给齐思和先生诞辰一百一十一周年纪念会暨欧洲史博士生论坛
上海有个陈建敏
留住时光,与你同在
给食指
——PPT :为郭路生七十周岁生日
纪念吉德炜教授
悼念魏立德
附 篇
何以解忧,唯有读书
——李零先生谈求学之路与为学之道
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
|
| 內容試閱:
|
写在前面
杂文的特点是“杂”,不用板着面孔用学术讲话,我喜欢。
古之所谓“杂”有双重含义:一是兼收并蓄,什么都包括,如《吕览》之“杂”;二是无法归类,内篇不收,外篇不入,最后剩下的话,如《庄子》分内、外、杂篇之“杂”。前者不以学科、门派、家法划界,后者是“多余的话”。
我的杂文写于不同时期,随作随辍,难免杂乱无章,但编成集子,还是要分分类。
我写杂文,大约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最初用笔名(吴欣)。我写过一篇小文,《服丧未尽的余哀》,刊于《东方纪事》1989年1期。谁来约稿,我已记不清。当时,没人知道我是谁,使用笔名,就更没法知道。杂志介绍作者,说我是“理论家”,真逗——“理论家”就是无法归类的家!
从那个时代起,我拉拉杂杂写过不少文章,前后编过四个集子:
1.《放虎归山》,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6年8月。2008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过此书的增订本,所谓“增订”,主要是加了“近作十篇”。
2.《花间一壶酒》,同心出版社,2005年。2010年和2013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再版,先出平装本,后出精装本。
3.《何枝可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4.《鸟儿歌唱——二十世纪猛回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201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过此书的繁体版。
上述四集多讲“当下感受”,等于个人眼中的“现代史”,即古之所谓“私史”。读者不难看出,前两个集子,喜怒笑骂,语多嘲讽,后两个集子,越写越严肃。风格不同,时代使然。我的每个集子各有主题,为了突出主题,后出的集子有时会酌收早先收过的文章,现在搁一块儿出,当然不合适。
这次汇集旧作,除上述四集,又加了两个集子,《我的天地国亲师》和《蟋蟀在堂》。责编李方晴跟我反复商讨,对所有文章做重新调整。旧集,凡重出之作,尽量删除,只保留最初出现的文章,唯一例外,我把怀念父母老师亲友的文章从各集中抽出,编入《我的天地国亲师》。这活儿挺烦人,我很感谢她的耐心和细心。
另外,与杂文创作有关,我还有两个集子,顺便提一下。
2013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过我的自序集《小字白劳》(孟繁之编)。这些自序是我的另一类杂文,特点也是讲“当下感受”,搁笔之际的“当下感受”。
2014年,我还出过一个杂文选,题目作《大刀阔斧绣花针》,强调文体改造。此书是应北岛、李陀之邀,先刊于《今天》2014年秋季号《视野:李零特别专辑》,后作为“视野丛书”之一,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2015年,“活字文化”在中信出版社出过大陆简体版。此书所收几乎全是旧集中的旧作,没什么新鲜玩意儿。同年三晋出版社出版的《回家》也是。
上述六个集子,不包括《大刀》《小字》中的文字。
上面说了,我的杂文多是记录眼前发生的“一刹那”,包括自序。多少年过去,回头一看,这不就是“今天”刚变“昨天”、学者叫作“历史”的东西吗,一幕一幕,历历在目。
考古学家讲“历史”,喜欢用“过去”一词,如“阅读过去”。
“历史”就是“过去”,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逝者如斯,不可能推倒重来。我的文章肯定有不少错,一下笔,白纸黑字,追悔莫及。我爱截句,截句也有截过头、标点太碎的毛病。错字病句应该改,可以改,但历史不能改,不可能改,想改也改不了。
这次重出的旧作,凡旧作按出版社要求“自我纠正”因而以省略号隐去的地方,请参看旧作。旧作还保留着历史原貌,包括我的各种错误。新作,有些不便讲的,咱们也撤掉。
文天祥《正气歌》有这样两句,“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董狐是山西人,我敬佩的山西人。我想尊重历史,尽量保存历史原貌。
2022 年8 月14 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自 序(注释从略)
利玛窦初入中国,最想弄清一件事,中国人最看重什么。这事,扎根中国多少年,他总算看清楚想明白了,中国人最重礼。但礼是什么?它是宗教吗?这个问题,他最关心,也最困惑。为了吸引中国精英入教,跟罗马教廷有个交代,他宁愿相信,中国的礼并非宗教,但罗马教廷内部,反对者大有人在。
中国的礼与“三才”有关。《荀子?礼论》有言:“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三才”天地人,天、地合在一起,算一类;人三分,先祖是死人,算一类;君、师是活人,合在一起,算一类。学者多认为,这是“天地君亲师”的源头。
鲁迅《我的第一个师父》:“我家的正屋的中央,供着一块牌位,用金字写着必须绝对尊敬和服从的五位:‘天地君亲师’。”“天地君亲师”是把“三本”拆开,解构为“五位”。这种牌位打什么时候才有?据考,是明以来。
出土发现,还有一种牌位,上面有八个字,“天地日月国王父母”,含义与上相近。这种牌位,例作龟趺驮碑式,类似制的出土物有海云禅师墓志和昭惠灵显真君(二郎神)牌位。上述牌位主要流行于元代。“天地日月”相当“天地”,“国王”相当“君”,“父母”相当“亲”,唯独没有“师”。为什么没有“师”?蒙元的帝师是道士或和尚(如丘处机、海云法师、八思巴)。
“天地君亲师”最能代表中国的“礼”。
“天地”是个虚拟领导,在“君”之上,或许有宗教意味,但更主要是政治符号,代表政权合法性,未必等于日月山川大自然,也未必相当西方的上帝。古人云,“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历代统治者拿这玩意儿吓唬老百姓,也吓唬自己,有非常现实的考虑。老百姓造反,他们也会说,“老天爷你塌了吧”,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叫“替天行道”,同样有非常现实的考虑。
“君亲师”,这三个字都是人,不是神。君是国君,亲是父母,师是老师。君是代表国家,父母的父母是祖先,老师的老师是孔子。中国,只有国家大一统,没有宗教大一统,与西方相反。这条很重要。不懂这条,读不懂中国。
民国,帝制被推翻,中国南方多把“天地君亲师”换成“天地国亲师”,印在纸上,贴在墙上。一字之易,改天换地,只有亲、师换不了。天还是中国的天,地还是中国的地,人还是中国的人。没有“君”,还有“国”。
我们的“国”是中华民族“五族共和”的国。
我们的“国”是靠人民的力量,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再造统一,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
敬畏天地、忠诚国家、孝养父母、尊重老师仍是中国人强调的美德。这五个字,普普通通,实实在在。
我这一辈子,当然离不开这五个字。
我有我的“天地国亲师”。
2021 年3 月19 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选摘一
母也天只(短札三则)
最早的记忆
2001年5月2日,早晨5点30分,单单打电话,他说,请你千万别难过,奶奶走了。
想不到已经出院的她,还是无法抗拒衰老。单单说,奶奶睡着了,九十四岁的她,安静地停止了呼吸。
我躺在床上,泪流满面,想,拼命想,追寻记忆中的母亲。
现在算起来,妈妈整整大我四十岁,她是1908年生,我是1948年生。妈妈说她有过七个孩子,和爸爸的兄弟姐妹一样多,可惜前面的四个男孩都夭折了。第一个孩子死,她很伤心。她说,现在回想,恐怕是得了大脑炎。第二个孩子,是受飞机轰炸惊吓,也死得可怜。后来,她从沁源领养了大姐,视同己出。大姐长我五岁。妈妈特别疼大姐。后来,解放军进京途中,有了二姐,有了我。
我今生最早的记忆,有个坐标,是妹妹的出生。那是我对妈妈最早的记忆。爸爸带我到医院看妈妈,买了苹果。她躺在床上,我说,妈妈吃苹果,妈妈说,俺孩吃。这种声音对我有强烈刺激。小时候,她给我念小人儿书,也是这种声音。在武乡,我也听到过这种声音,带着乡土气息的爱,动物式的爱。她用一把水果刀,慢慢地削苹果。因为妹妹比我小两岁,那肯定是1950年9月15日后的几天,我两岁零三个月。
后来,我们不断搬家。妈妈说,最初我们住先农坛,那时,我还不记事。有点记忆的家在拈花寺。
小时候,妈妈总是叮嘱我,不许说假话,不许拿别人的东西,出门一定告她我到哪儿去了。我很害怕,因我不在,让她担心。现在,我不在她身边,她走了。她已痴呆多年,她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
2001 年5 月2 日写于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
一把银勺
一把银勺,陪我七十多年,普普通通,平平常常,每天吃饭,从筷笼中掏出,吃完,洗净,再插回去,不知多少回。
这把勺子并不起眼儿,一点儿都不起眼儿,因为从一侧入嘴,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年头久了,勺口左侧被磨损,变薄,缩进去一块儿,好像不太圆满的月亮,细长的勺柄,后端有只线刻的蝴蝶,因为过于简化,好像一只小蛾子。银器,长期不用,早晚会氧化变黑,我这件不同,每天用,颜色虽不够鲜亮,有点灰不溜秋,称为银灰色,总还说得过去。
妈妈说,小时候,我脖子上挂副银锁。她把银锁拿去化了,打了些小玩意儿,手镯和勺子。小时候,我不爱穿带扣子的衣裳,上衣拉锁的拉头挂个兽头状的小铃铛,就是那副银锁剩下的玩意儿。最后,什么都没了,只有勺子留下来。妈妈就是拿这把勺子喂我,看我一天天长大。
我们都是吃“妈妈饭”长大,擦圪蚪、抿圪蚪、和子饭(一种小米、杂面、红薯、山药蛋混合的食物)、苦累(也叫傀儡、不烂子、蒸菜)、黄煎(一种用鏊子烙的玉米饼)、砍三刀(一种黄米面油炸的东西)……那种味道,你一辈子忘不了。
枕边,妈妈给我念书,印象最深是《西游记》,柔声细气,抑扬顿挫,好像山西版的孙敬修〔“那个孙(乡音sōng)悟空呀”〕。苏联动画片,变成小人儿书,有《一朵小红花》《金羚羊》……那种声音,你一辈子忘不了。
有时,妈妈会哭,有时为我,有时为她自己,更多不知为什么。她走的时候,我心中蹦出一句诗,“梦里依稀慈母泪”,那是鲁迅的句子。
妈妈不在了,只有这把勺子还在。
有一天,我突然感到这把勺子的珍贵——对我珍贵,只对我珍贵。我请朋友给它做个囊匣,准备把它供起来,不再用它吃饭。她把勺子用纸包了包,揣进兜里。
这一去,等呀等,好久没消息。
有一天,朋友来了,拿出个漂亮的盒子,里面放着一套银餐具,雪白锃亮,她说,憋了很久,真不好意思跟你说,那把勺子找不到了,我买了这个……
我一时无语。
郁闷归郁闷,没辙还是没辙。我跟她说,算了,那是件无法替代的东西,无法赔偿也无需赔偿,你还是把它拿回去吧。启功临走时还惦着他的画。他说,“物能留下,人留不下呀”(允丽《外家纪闻——启功先生外祖家的事》,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2年, 6—13页)。
其实,物也会消失,经常是莫名其妙地消失,掉进记忆的黑洞,永远回不来。
2021 年3 月13 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母也天只
《诗?鄘风?柏舟》有此语,毛传:“母也天也,天谓父也”。汉儒旧说,以父为天,听上去,很男权,然而先母后父者何,马瑞辰说,那是为了押韵。朱熹的解释不同,他说:“母之于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极……不及父者,疑时独母在。”(《诗集传》)说母恩大如天,与父无关,喊妈的时候,他可能早不在了。
呼母吁天,咏叹之辞。西人惊呼,恒曰“My God”,那意思有点像我们的“天呀”或“我的老天爷呀”。东北人不同,直接喊的是“哎哟我的妈”。喊妈比喊天嘴顺。
很多人临死,想到的是妈,口中念念有词,念的是妈。
2021 年3 月16 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选摘二
我的老师梦(节选)
我想当个好老师,因为我是坏孩子。
假如时光倒转,我又回到人大附中(以下简称“人大附”),老师命题作文,要我写“我的理想”,我敢说,我的想法他猜不着。因为那时的我总是一肚子怨愤,就像出身卑贱的于连跟贵族呕气、一心想当拿破仑。我想当的什么都不是,只是我最痛恨的老师。我真想像有个苏联电影里演的那个和蔼可亲、催人泪下的女老师,把爱的阳光洒满世界,特别是坏孩子待着的角落,让他们知道只有我还疼着惦着他们……
我是坏孩子,父母疼爱娇惯坏了的那种,脆弱敏感,受不了一点儿委屈。是个朋友就想肝胆相照,话不投机又拳脚相加,老师越说我是耗子屎,我越要坏他一锅汤。为什么我想当老师呢?说实话,我是想向别人证明,我根本就不是坏孩子,就像三岛由纪夫笔下的那只老鼠,为了证明自己是猫,不惜以死明志,一头扎进大水缸。
现在回想起来,我上学那阵儿,人大附还算不上什么好学校。因为海淀一带,凡是有点出息的孩子,全让清华附中、一○一他们给搂走了。你千万别把现在的人大附当成了我们那阵儿的人大附。
人大附,前身是作为人大预科的工农速成中学。这所中学本来是培养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像高玉宝、郝建秀他们的地方。人大附办普通高中是在1956年,最初跟工农速成中学混在一起办。我大姐比我大五岁,就在人大附上的高中。初中办得晚,1960年才有,我二姐是初中第一届,叫六三级;我比她晚一年,叫六四级。
这个学校,论师资,论设备,都是一流,不行是不行在生源。我们那两届的初中生,大多来自干部子弟学校,如五一、六一、七一、八一、十一、育才、育英。他们是冲着“人大附伙食好”而来。人大附确实吃得好,每月伙食费才十块钱,什么都有。六三一班和六三二班的孩子,尽是些自行车后面夹个篮球的主儿。打架一块儿上,一块儿受处分。难怪“文革”期间,我们这儿成了打手云集的地方。破“四旧”、打“流氓”、斗老师、斗“反动学生”、欺负所谓“出身不好”的同学,血战三司、冲公安部、反中央“文革”,特别能折腾。
说实话,在这样的学校里,我真算不上“坏”,可谁让我摊上六四四班呢。我们班是优秀班集体,在全年级甚至全校都相当优秀。它让我像毛遂自荐,脱颖而出。别的不说,光我在教室中的位置就很说明问题。老师安排,眼神差的坐前边,好的坐后边,左右隔一阵儿一换,这不挺好。但为了班集体的荣誉,他们非让视力绝佳的我到前排就座,前边老师,后边好孩子,左边、右边也是好孩子,无论怎么换行倒排,总有三个小美人包围我,监视我,数落我。还有,班上有个记事本,老师说了,请大家一人一天,把每天的好人好事、坏人坏事全都记下来。他们真行,不管轮到谁,每天的坏人坏事,全归我一人,很有“春秋笔法”。我想证明我能力有限,但什么也证明不了。好一点的孩子疾我如仇,差一点的也佯装不识。最可气的是,即使臭味相投、近我者黑的落后分子,见了面也嬉皮笑脸一收,居然板起面孔教训我。老师领着大家集体给我造越位,天罗地网撒到一切角落,我就跟印度的首陀罗一样,属于种姓低下的“不可接触者”。我连同学家都去不了。他们说,老师早跟家长打过招呼,不让他们跟我玩。当今世界的军事围堵、经济制裁,联手打造“共同价值观”,我早就深有体会。
初中,我学习还不错,比拔尖的女孩不足,比一般的男孩有余,但品行不成,是个人都起码得良,我却年年是中,甚至受了处分。
这是一场噩梦。有一天,教室里阳光灿烂(或者灯光灿烂),我在写作业,有个女孩飘然而至,好像是个组长,她的嘴一张一翕,两只手不停比画,正在历数我的罪状。我的头像破鼓乱人捶,嗡嗡作响,挥手她不走,臭骂也不去,竟然把我的墨水瓶打翻,洒满我的课本和作业。我勃然大怒,抄起墨水瓶就砸过去。血从她的额头流下来……我闯了大祸。按罪量刑,教导处向全体同学宣布,为了严肃校纪,他们要处分我,但不是马上。他们说,他们有足够的耐心“以观后效”,全看我的下一步表现。他们宁肯把刀悬我头上。
我想,我得忍。可结果没忍住。我终于因再次打架受了处分。
初三,我忍了一年,多读书,少说话,少跟人来往,终于把帽子摘掉。帽子摘了,人也变了,蔫蔫的,好像换了一个人。
我可以保证,十五岁以后我没打过架,这得感谢书。读书好。读书不仅可以帮我消愁解闷,治病疗伤,还可以遏制暴力倾向。我说,我是这样走上学术之路。
(后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