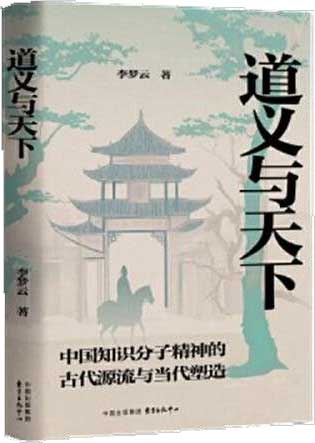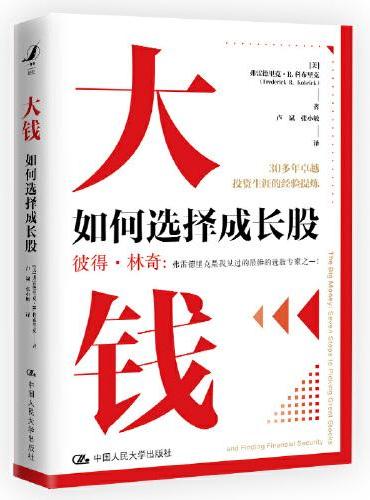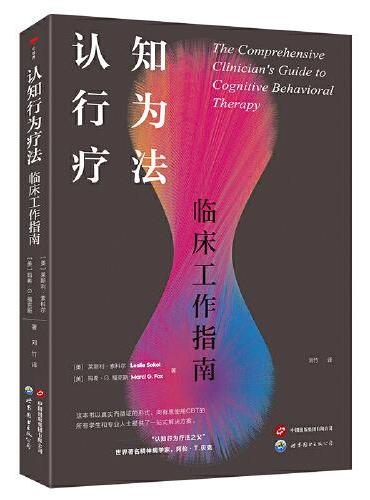新書推薦:

《
金钱的力量:财富流动、债务、与经济繁荣
》
售價:NT$
454.0

《
超越想象的ChatGPT教育:人工智能将如何彻底改变教育 (土耳其)卡罗琳·费尔·库班 穆罕默德·萨欣
》
售價:NT$
352.0

《
应对百年变局Ⅲ:全球治理视野下的新发展格局
》
售價:NT$
398.0

《
前端工程化——体系架构与基础建设(微课视频版)
》
售價:NT$
454.0

《
《诗经》全注全译全本彩图 全书系列50万册焕新升级典藏纪念版
》
售價:NT$
25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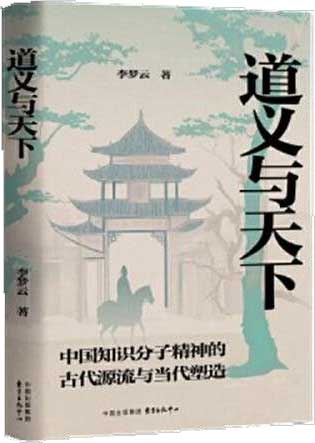
《
道义与天下: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古代源流与当代塑造
》
售價:NT$
40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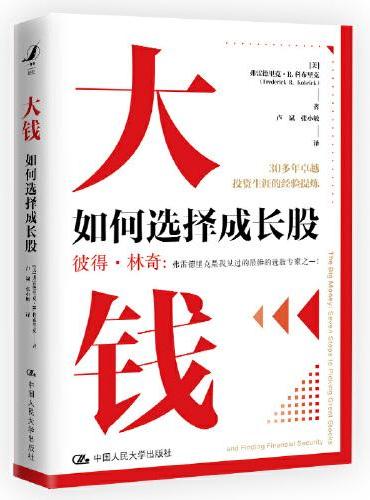
《
大钱:如何选择成长股
》
售價:NT$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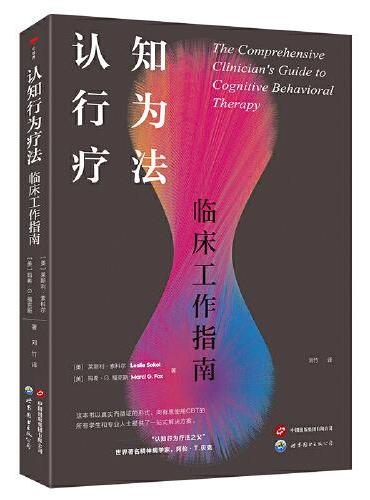
《
认知行为疗法:临床工作指南
》
售價:NT$
398.0
|
| 編輯推薦: |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不朽经典,全球媒体盛赞的唯美主义必读之作。
入选哈佛、东京大学、清北等世界名校书单,照亮莫言文学道路的灯塔。
乘坐列车驶往《雪国》,欣赏川端康成笔下唯美细腻的爱与徒劳。
特别收录“初恋小说”题材珠玉短篇,品味影响一代文豪的初次爱恋。
无论《雪国》还是《伊豆的舞女》,我都是怀着对爱情的感谢之情来写的。
——川端康成
|
| 內容簡介: |
本书收录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小说《雪国》,及初恋题材短篇合集《初恋小说集》中的《油》《五月之幻》《篝火》《她的盛装》《千代》《孤儿的感情》《人心》7篇经典之作。
《雪国》是川端康成的唯美主义代表作,作者用婉约哀伤的笔调,为读者描绘了一个虚无之美、洁净之美与悲哀之美交织的雪世界。故事主要讲述一位名叫岛村的东京舞蹈艺术研究家,三次前往雪国的温泉旅馆,与当地的艺伎驹子以及萍水相逢的少女叶子之间发生的爱情纠葛,文中充满了爱与徒劳的细腻情感。
|
|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日]川端康成(1899―1972)
著名小说家,日本当代文学的杰出代表,在1968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1972年却以自杀谢世。他是日本传统美的继承和发扬者,字里行间充满了优雅、感伤、克制与和谐;同时他也是日本现代文艺的开拓者,印象主义特有的新鲜与律动之美流溢在他的作品之中。
译者简介
陈江
自由翻译,福建师范大学日本语学士,日语专业八级,CATTI日语笔译三级。已出版译作:《拒绝谬论》《本格推理》《飞鸟高作品集》《高木彬光短篇集-假象/最后的自白》等。
|
| 目錄:
|
雪国
初恋小说集
《油》
《五月之幻》
《篝火》
《她的盛装》
《千代》
《孤儿的感情》
《人心》
|
| 內容試閱:
|
穿过长长的县界隧道,便是雪国。黑夜的深处透出一片雪白。火车在线路所停下来。
对面的姑娘站起身,过来把岛村前面的玻璃车窗打开,冰雪的寒气一拥而入。姑娘从逼仄的车窗探出身,向远处喊:
“站长先生,站长先生!”
一个男人提着灯,踏着雪徐徐而来,围巾直盖到鼻子,帽子的皮毛护耳垂在耳边。
已经这么冷了吗?岛村心想。他向远方眺望,只见零星几间木板房,疏疏落落地瑟缩在山脚,似是铁路职工的宿舍,雪色未及近前,便被黑暗吞没了。
“站长先生,是我,您好。”
“哟,这不是叶子姑娘吗,这是要回家?天又冷啦。”
“听说我弟弟这次派到这里工作,承您多照顾了。”
“在这种地方,他早晚会闷得发慌,年纪这么小,怪可怜的。”
“他还不懂事,有劳您多多指点他,拜托您了。”
“没问题,他正干得起劲儿呢。往后还会更忙,去年这时候可是碰上了大雪呢,老是闹雪崩,火车进也进不去,出也出不来,村里人都忙着给旅客烧水送饭,忙得很。”
“您穿得真厚实呀,我弟弟信上说,他背心都还没穿上呢。”
“我里里外外套了四层衣服呢!天一冷,小伙子们就一个劲儿喝酒,结果都伤了风,一个个横七竖八躺着动不了啦。”
站长把手上的灯往宿舍方向扬了一扬。
“我弟弟也喝酒吗?”
“没。”
“您要回去了吗?”
“我受了伤,要去看医生。”
“哎呀,您可真得小心。”
站长和服上罩着外套,大冷的天,他似乎不耐烦继续站着闲聊,转过身说:
“那你也多保重。”
“站长先生,我弟弟现在没出来吗?”叶子的目光在雪地里搜寻着,“站长先生,我弟弟就拜托您了,谢谢您!”
她的声音美得近乎悲凉,清亮的余音久久地回荡着。
火车开动了,她没缩回身子,等火车追上走在轨道旁的站长,她又喊:
“站长先生,请您转告我弟弟,叫他下次休假的时候回趟家!”
“好的——”站长大声回答。
叶子关上窗,双手捂住冻得通红的脸颊。
这些县境的山里通常配备三辆除雪车,静候着大雪降临。隧道的南北两端已架好雪崩警报电线,还安排了五千名扫雪工和两千名青年消防员,都已整装待发。
铁路线路所即将被大雪掩埋,而这位叶子姑娘的弟弟今冬起就在那里工作了。岛村知道这个情况后,对她越发感兴趣了。
但是,称她“姑娘”,只是岛村的直观印象。与她同行的男子是她什么人,岛村自然无从知晓。两人举止形同夫妻,但那男子分明生着病。与病人相处,男女之间的界限难免比较模糊,越是悉心照料,看起来越像夫妻。那男子其实较她年长,可她操心病人那副稍显稚嫩的慈母模样,乍一看,难免把他们当成夫妻。
岛村把她单独抽离,观察她的举止,推断她是个姑娘。但是,也或许是因为他凝视她的眼光太过异样,掺杂了太多他自己的感伤。
三小时前,岛村百无聊赖地胡乱摆动左手食指,反复端详着它。关于那个即将相会的女人,能唤起他鲜活记忆的,终究只有这根手指。越急着想回忆得清楚些,记忆越是无从捉摸,模糊不清。只有这根手指还残留着女人的些许触感,似乎要将他牵引到远方,牵引到她身边。他觉得不可思议,不时将手指凑近鼻子闻闻,蓦地在玻璃窗划出一条线,不料上面清晰地映出一只女人的眼睛,他几欲失声惊呼。不过,大概是因为他一时心神飘向了远方。回过神来,才发现不是别的,而是对面女人的身影映在了玻璃窗上。窗外天色垂暮,车内灯火通明,玻璃窗成了镜子,可温热的暖气让玻璃蒙上厚厚的水汽,手指擦拭之后才显出映像。
星眸虽只一点,更显美丽动人。岛村忙将脸挨近窗户,摆出一副欲观赏暮色的旅人愁容,手掌揩了揩玻璃。
姑娘上身微微前倾,全神贯注地守着躺在面前的男人。她耸肩弓背,聚精会神,那双略带寒意的眸子眨也不眨。男人倚窗而卧,双脚蜷缩在姑娘身旁。这是三等车厢。他们的座位不在岛村正对面,而是斜对面,那男子侧身躺着,窗镜只照到他耳朵。
姑娘正好坐在岛村的斜对面,他原本能直接看到。但是,他们刚上车时,这姑娘冷艳的美使岛村感到心惊,他不由垂下目光,却瞧见姑娘的手被那男人蜡黄的手紧紧攥着,便觉得不好再往那边望了。
窗镜中的男人神色平静,似乎只要瞧得见姑娘上身及胸脯,他便心中安宁,虚弱中飘溢出怡然自得。他把围巾枕在头下,绕过鼻子,遮住嘴巴,往上包住脸颊,套头包脸一番。围巾时不时掉落下来,或是盖住鼻子。不等男子眼神示意,姑娘便温存地给他掖好。他们二人心无旁骛地数度反复,看得岛村心下焦灼。男人双脚裹在外套里,外套下摆不时松开掉落,姑娘随即发觉,为他裹好。这一切显得十分自然,仿佛他们会永远这般亲密无间地随列车去到远方。因此,岛村觉得眼前的景象并不惹人哀伤,仿若遥望着一场梦境。或许也因为这一切只是镜中影像吧。
暮色在镜后流转,镜面映像与镜后实景如同电影的叠影一般,变幻不停。人物与背景毫无关联,透明虚幻的人物与苍茫暮色中流转的风景交融相衬,映照出一个不似人间的意象世界。尤其寒山灯火叠现姑娘面容间,那难以言喻的美,更令岛村心神激荡。
远山上空的晚霞余烬未消,透窗望去,远处的风景仍依稀可见,但霞色已褪,本就平平无奇的原野显得更加寡淡,惹不起半点注意,也因此反而有某种澎湃的情感奔流其间。这自然是因为上面浮现着那姑娘的面容。她的身影遮住了一部分窗外的风景,可轮廓周边,黄昏景象波动不断,姑娘的脸也给衬得仿佛透明,但是,面容背后,黄昏景象流淌不休,仿佛要自表面穿过,使人分辨不出是否真的透明。
火车内光亮不强,窗玻璃也不比真镜子,反射不出光,岛村看得入神,渐渐忘了窗镜的存在,只觉得姑娘宛如飘浮在变幻不停的黄昏景象中。
她的脸上闪着灯火。镜中映像虚浮,抹不去窗外的灯火,灯火也掩不住映像。灯火闪过她的脸庞,却没使她的面容熠熠生辉。那是清冷遥远的一星光亮。小小的眸子周边泛出微光,姑娘的眼睛与灯火交叠的一瞬,她的眼眸化为妖冶的夜光虫,在暮色流波中漂浮。
叶子没有发觉有人正这样凝视着自己。她一心只扑在病人身上,就算扭脸往岛村的方向看,大概也看不到自己在窗镜中映出的身影,一个眺望着窗外的男人她更不会留意。
岛村窥看叶子良久,却不曾自察失礼,也许是给暮景之镜虚幻的魔力擭住了吧。所以,见她招呼站长时显出的过分认真劲儿,岛村恍惚间感到一种看戏的兴味。
经过线路所时,窗玻璃只剩一片漆黑,外面流动的风景不见了,镜子的魅力也消失得无影无踪。窗玻璃仍旧映着叶子美丽的脸,岛村却有了新发现,她虽举止温婉,可莫名透着一股澄澈清冷。窗镜越发朦胧了,他没有再去揩拭。
然而,约莫半小时后,叶子他们竟也和岛村在同一站下了车。他急切地掉过头去看,想知道又发生了什么,可是给站台上的寒意一激,他突然就对火车上的失礼行径感到羞愧,便头也不回地从火车头前面走过去了。
男人搭着叶子的肩膀正要下铁轨,站务员招了招手,拦住了他们。
不一会儿,黑暗中驶来一辆长长的货运火车,淹没了两人的身影。
旅店揽客的掌柜一身夸张的雪天装束,穿得像火灾现场的消防员,耳朵包着,脚上是长胶鞋。一个女人站在候车室窗边,遥望着铁轨,身上也披了斗篷,裹着头巾。
岛村还没从火车里的暖和劲儿中缓过来,外面实际的温度还感受不到,可毕竟是头一回冬天来雪国,先给本地人的装束震惊到了。
“那么冷吗?要穿成这样。”
“是呀,都穿上过冬的衣服了。雪后放晴的头一晚格外冷,今晚看样子已经到零下了。”
“这就零下了吗?”岛村望着檐头玲珑的冰柱,同旅店的茶房坐上了汽车。家家户户低矮的屋檐给雪色压得更低了,村子像是整个儿寂寂沉入了地底。
“还真是摸哪儿都冷冰冰的。”
“去年的最低温度是零下二十几度。”
“雪呢?”
“记不清了,通常有七八尺厚,多的时候有一丈多两三尺厚吧。”
“那还有得下了。”
“还有得下呢,这雪最近下了一尺多,现在都快化完了。”
“还有化的时候啊。”
“大雪可是说来就来的。”
正是十二月初。
岛村的伤风久久不愈,鼻子原本堵得慌,倏地一股气从鼻腔直冲脑门,似秽物被涤荡过一般,鼻涕直往下流。
“师傅家的姑娘还在吗?”
“嗯,在的在的。您下车时没见着她吗?披着深蓝色斗篷。”
“那是她吗?……等会儿能见到她吧?”
“今晚吗?”
“今晚。”
“说是师傅的儿子会搭刚刚那趟末班火车回来,她跑去迎接的。”
暮景之镜中,受叶子悉心照料的病人,原来是岛村来相会的女人家的儿子。
岛村心中似乎有什么东西一掠而过,他对这场邂逅倒不觉得太奇怪,甚至觉得对此不以为意的自己有些奇怪。
不知为何,岛村心中某处隐隐觉得,指尖留忆的女人和眸中灯火闪烁的女人之间,像是有什么因缘,会发生些什么。是因为自己还没从那暮景之镜中缓过劲儿来吗?他喃喃道:“那流淌的暮色,竟象征着时间的流逝吗?”
滑雪季到来前的这段时间,是温泉旅店一年中客人最少的时候。岛村从室内温泉上来时,已是夜深人静。他在古旧的走廊上每踏一步,玻璃窗都轻轻发颤。走廊尽头账房转弯处,亭亭玉立地站着一个女子,裙摆泼洒在地,漆黑的地板泛出清冷的光。
终于还是当了艺伎吗,岛村望着那裙摆,心中一震。她没有走过来,也不施礼迎接,只寂寂地,一动不动地立着。远远地,他领会到她无言中的真切情意,连忙上前,站在女人身旁,却只是沉默着。女人抹了浓浓白粉的脸上想要堆出笑容,反倒事与愿违,变成个哭脸,二人也就默不作声朝房间走去。
曾经那样深切地交往过,却连一封信都没寄回,也没有来看她,说好送她的舞蹈书也不见影子,女人准以为自己早就忘了她。岛村原想理应自己先开口道歉,或扯些借口,可并肩走的这一路,他察觉到,她不仅没有责备他,反而全身心地翻涌着思念之情,他更觉得自己无论说什么,都只会显得自己虚情假意。他被她震惊到了,心里荡漾起一种甜蜜的喜悦。走到楼梯口,他突然把左手伸到女人眼前,伸出食指道:“它最记得你了。”
“是吗?”她握住他的手指不松开,牵着他拾级而上。
手在被炉前松开了,她脸倏地红到了脖颈。她不愿被发觉,慌忙又拾起他的手,说道:
“它记得我?”
“不是右边,是这边。”岛村从女人掌心抽出右手抄入被炉,又把左手伸了出去。
“我知道的。”她板脸道,又格格含笑着,摊开岛村的手掌,把脸在上面熨帖着,“是它记得我吗?”
“哟,好冰,头一回摸到这么冰凉的头发。”
“东京还没下雪吗?”
“你当时虽那么说,到底还是骗人的。不然,谁会年末了还到这么冷的地方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