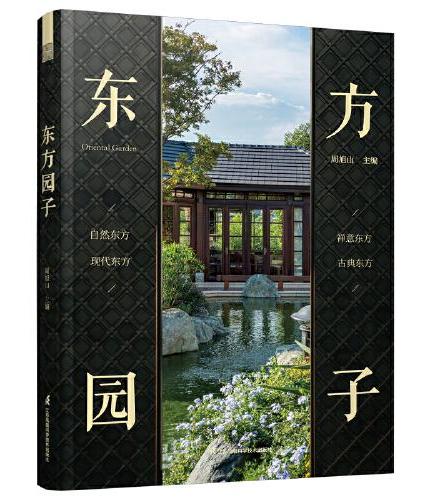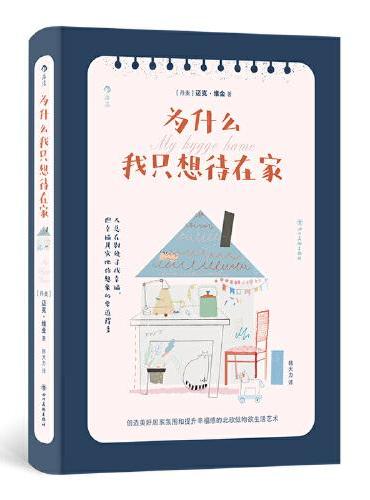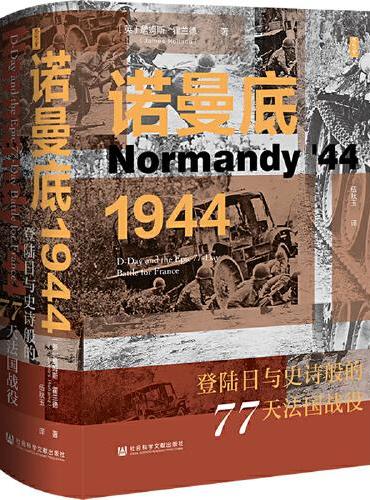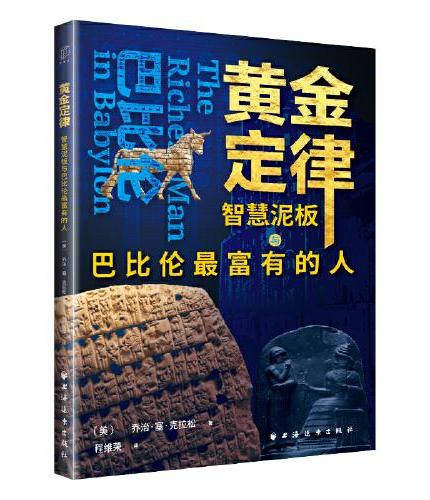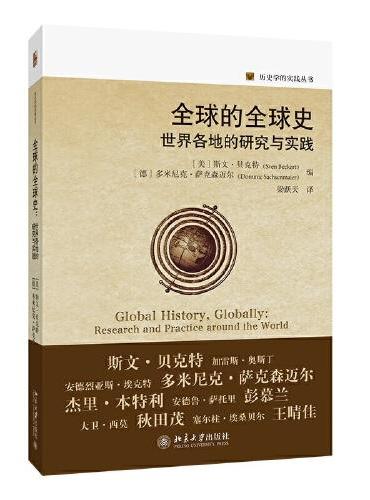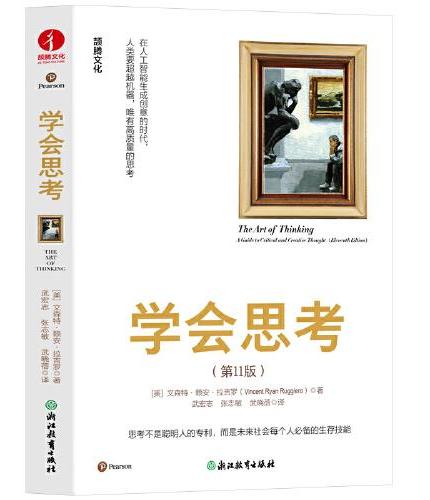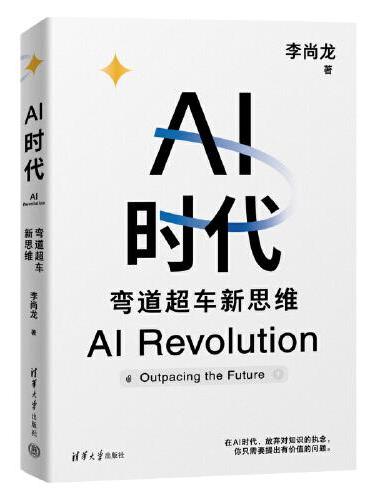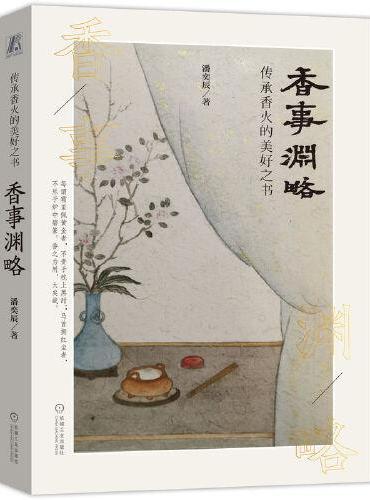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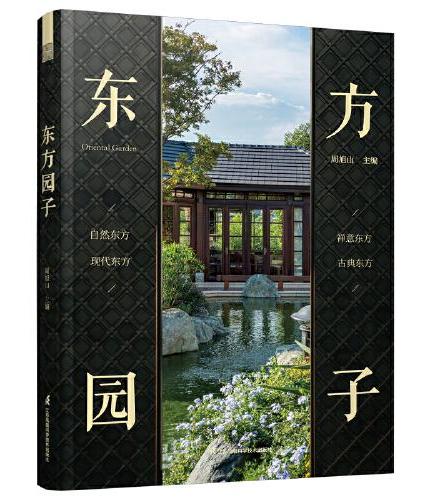
《
东方园子:中国古典园林现代应用 园冶 禅庭 东方美学 造园 庭院造景施工 国风 作庭记 景观设计
》
售價:NT$
146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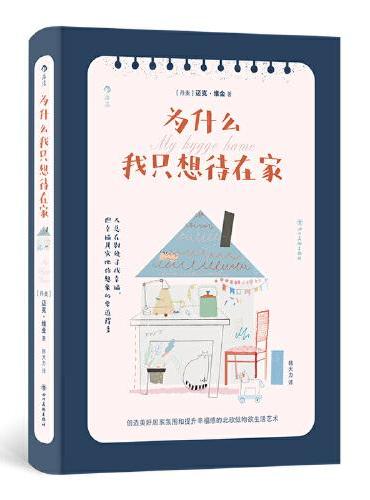
《
Hygge Home(为什么我只想待在家)
》
售價:NT$
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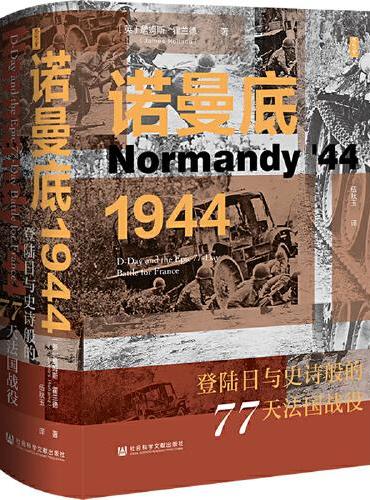
《
思想会·诺曼底1944:登陆日与史诗般的77天法国战役
》
售價:NT$
91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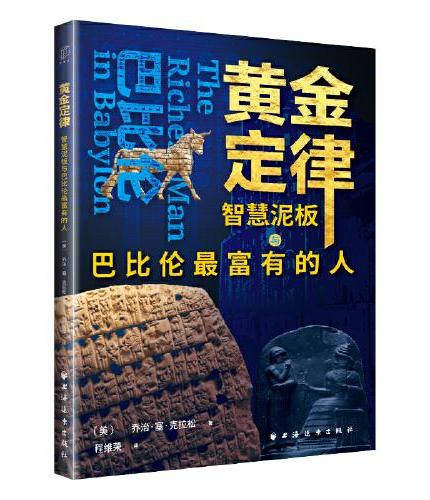
《
黄金定律:智慧泥板与巴比伦最富有的人(全球畅销书!来自古巴比伦的财富课,教你摆脱贫困,智慧管理财富,实现财富持续增长!)
》
售價:NT$
2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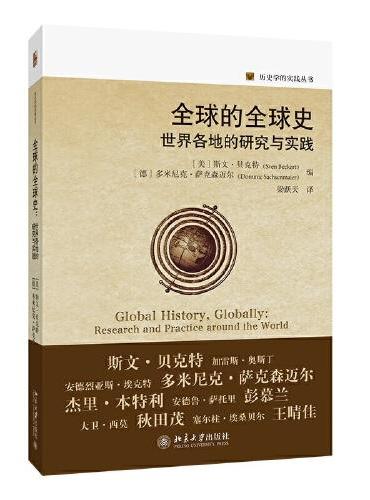
《
全球的全球史:世界各地的研究与实践 历史学的实践丛书
》
售價:NT$
40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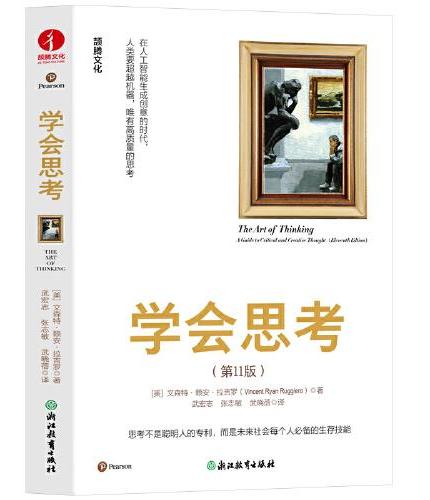
《
学会思考 批判性思维 思辨与立场 学会提问
》
售價:NT$
4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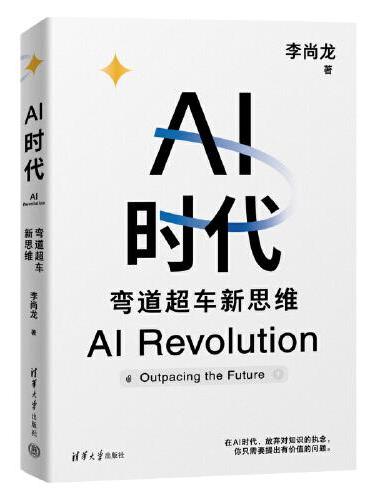
《
AI时代:弯道超车新思维
》
售價:NT$
35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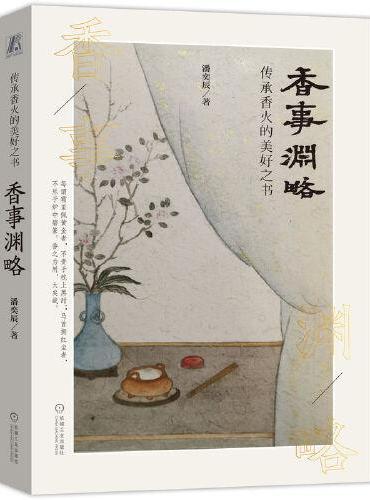
《
香事渊略
》
售價:NT$
505.0
|
| 編輯推薦: |
本书卖点
本书对“时间修辞与当代文学的美学演变”“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及评价纷争问题”“世纪之交以来诗歌流向的几个问题” “当代诗歌中的地方美学与地域意识形态”“从文化地理观察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个视角”等问题的探讨深入而精当,反映了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的实绩,客观呈现了现当代文学写作领域的诸多理论问题,是一部值得细读的文学评论精品集。
编辑推荐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大家之作,这部文集体现出作者一贯的深邃、独到、与时俱进的风格,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向及评价纷争、现当代诗歌中的地方美学与地域意识形、先锋的终结与幻化等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诸多现象,做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只眼别具,洞幽烛微。对莫言、余华、苏童、食指、海子等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诗人,结合其作品做了全面、精当的评价,言他人所未言,是一部值得细读的文学评论精品集。
|
| 內容簡介: |
|
文学评论家张清华从“时间修辞与当代文学的美学演变”“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及评价纷争问题”“世纪之交以来诗歌流向的几个问题”“当代诗歌中的地方美学与地域意识形态” “从文化地理观察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个视角”等议题展开叙述,对莫言、余华、苏童、食指、海子等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精当、恰如其分的评价,言他人所未言,角度独到,内容深刻,是一部值得细读的文学评论精品集。
|
| 關於作者: |
|
张清华,1963年生,山东博兴人。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副主任。出版《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等学术著作15部。学术编著有《百年中国新诗编年》等10 余种;曾获省部级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北师大教学名师奖等;曾讲学德国海德堡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另外涉猎诗歌散文写作,出版诗集《形式主义的花园》、散文集《海德堡笔记》《春梦六解》等7 部,获多种创作奖。
|
| 目錄:
|
辑一
I
时间的美学
——论时间修辞与当代文学的美学演变
003
在世界性与本土经验之间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及评价纷争问题
042
辑二
II
叙述的极限
——论莫言
071
文学的减法
——论余华
112
春梦,革命,永恒的失败与虚无
——从精神分析的方向论格非
135
天堂的哀歌
——论苏童
186
在命运的万壑千沟之间
——论东西,以《篡改的命》为切入点
209
辑三
III
价值分裂与美学对峙
——世纪之交以来诗歌流向的几个问题
247
个体的命运与时代的眼泪
——由“底层生存写作”谈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
269
当代诗歌中的地方美学与地域意识形态
——从文化地理观察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个视角
284
从精神分裂的方向看
——论食指
313
“在幻象和流放中创造了伟大的诗歌”
——论海子
342
辑四
IV
民间理念的流变与当代文学中的三种民间美学形态
369
先锋的终结与幻化
——关于近三十年文学演变的一个视角
404
论《蝴蝶》的思想超越与语言内省
——一个历史的和解构主义的细读
433
|
| 內容試閱:
|
代序
狂人的谱系学
——从解读鲁迅开始
我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
……我独自远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
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
——鲁迅《野草·影的告别》
一曲狂想,一幕悲歌,一切都从这里开始,也必将在这里结束。
20世纪中国文学中有一个不幸的狂人家族,一个知识者的谱系,从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开始,它就开始了它的繁衍。这个谱系在过去似乎已经被梳理过,但还很不够。没有人将它们联系起来看,更没有人将现实中的和文学中的知识分子看成同一个群体。因为如果不能获得一个整体性眼光的话,将无法得出有启示意义的结论。钱理群有个很著名的说法,叫作“堂吉诃德与哈姆莱特的东移”,这是西方文学史上两个最著名的疯子,他们后来拥有了众多的追随者和影子,依次传染给了东方民族的文学。而且这个传染的过程是一个在时间中渐变、空间上慢慢“东移”的过程。以至于一位当代的作家格非干脆就认定,“精神病是可以传染的”——他在自己的小说《傻瓜的诗篇》中,令人震惊地、诗意而形象地诠释了这一点。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研究文学或者研究思想史者就应该这样。没有精神发现的文学研究算什么研究呢?因此这是令人鼓舞的发现。我这里要借用这样一个发现,来谈谈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这个现象是如何“变迁”和“移动”的。
一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
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鲁迅的《狂人日记》,首先就是书写了一个中国式的“多余人”形象,一个有着久远血缘的疯子。这不是偶然的,历来文学只要写到知识分子,写到有点思想和独立意志的人物,都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异类”或间离的倾向。“狂人”之所以被视为狂人,既是误读,也是实情。为什么这样说?狂人是被庸众恶意地“矮化”和放逐的,有独立思想的人通常会共有这样的一个境遇。因为他不能苟同于这社会,因而在这社会上便成了一个无用之人,一个多余的闲人,只有被嗤笑、放逐甚至管制的份儿。狂人的表征是“妄想症”和“谵妄症”,是说诳语和危言,内里则是对规训和规则的抗拒。他在外观上的确很容易就会被视为精神异常者、偏执狂和病人,但鲁迅却告诉我们,这是世俗给他打上的恶毒标记,是“人群的专制”对异类的划分和定性,并且具有在人格意义上的贬抑与侮辱意味。然而如果仅仅是这样的一个深度,那也还不是鲁迅,鲁迅之不同寻常的深度在于,他同时也告诉我们:狂人自己也会真的变疯——被社会命定的处境,会转化为主体自我的暗示性心理与错乱式行为逻辑,以至于成为其性格和命运。哈姆莱特就是由佯疯到真疯的,开始他是佯疯,但当他选择了混乱的逻辑和倒错的语言之后,他就一步步走上了深渊之路,错上加错,起先是对自己所爱的人恶语相加,随后又错杀了自己未来的岳丈,最后又和自己所爱的人的哥哥决斗……他的每一步都是由于自己的疯狂和混乱的暗示所驱动的,这一切反过来铸就了他的深渊性格和命运。自从奥菲莉亚死后他就真的疯了,因为他作为一个与命运赌博的赌徒,已经输光了。对狂人来讲,他的病状的自我体验是源于他深刻和无助的孤独感,孤独转化为了恐惧,并表现为真形一样的病状。当所有的人都声称他是一个病人的时候,当他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他的时候,他也无法不自我怀疑自己是一个病人。
一个走错了房间的人,一个生错了时代的人,一个先知式的遭到了庸众嘲笑和捉弄的人,一个惊慌失措的人,一个精神病人……就是这样诞生的。他慢慢地接纳和适应了这样一个角色,无法拒绝。他不能不感到惧怕。一个人对他的歧视只是一种伤害,一群人对他的歧视就是一种扭曲,而一切人对他的歧视则无疑就是毁灭,他怎么能不疯呢?
鲁迅自己就是一个狂人:他就是一个对着羊群和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鲁迅《题〈彷徨〉》
“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太平……但他举起了投枪!”
——鲁迅《野草·这样的战士》
多像一个堂吉诃德!他的后半生一直在拿风车和羊群练习,最重要的已不是和什么人作战,而是作战本身,至于对象则可以借代和假想。他又是一个哈姆莱特——他的《野草》的语式多像是哈姆莱特的朗诵:“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我姑且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我将在不知道的时候独自远行……”(《影的告别》)只有在“思”的状态并且以思的话语方式出现的时候,他才能对自己的人格予以肯定,才会有稍许的自信。所以他不得不沉湎于这种话语游戏之中。伴随着这华美而苍白的修辞,他挥舞着自己的思想之剑,环顾四周,找不到对决的人,悲壮中显得多么滑稽。的确,没有人比鲁迅更接近一个西方意义上的人文知识分子,更接近于尼采、叔本华,更接近于俄罗斯和欧洲文学的精神原型,更接近于一个现实中的哈姆莱特。这在他最早期的著作《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中,可以说就已经跃然纸上了。
但不同寻常之处在于,鲁迅总是因为其可以上升到哲学的境地而产生多解,《狂人日记》也一样。这其实也可以理解为鲁迅对“青年”——他原来所深信的“必胜于老年”的一代“新人”——的失望与怀疑。他要确认原来这样一个想法的荒唐:青年一定是纯洁的。现在他明白他们的勇敢是短暂的,他们很快就会屈服于规训,并变得“成熟”起来,与成年人和老年人一样世俗化,变得狡黠和市侩。实际上也只有未曾世俗化的青年敢于讲出“吃人”这样的话,那是他因为自己的纯洁而说出了惊世骇俗的真理,并且敢于声称自己将要与旧世界的法则决裂,但这样的豪情壮志能持续多久?很快他就将溃败下来,在被视为“异类”和“狂人”之后收敛自己,最后变成常人,并且“赴某地候补”。这即是意味着他与现实已达成了完全的妥协,他完成了自己的“成人仪式”,经过了一番挣扎和挫折,终于“回归”了社会——与之同流合污了。
历史还是没有什么进步,就像人性从来没有什么进步一样。鲁迅自己终其一生是在反抗这个“规律”,他拒绝让自己世俗化,到死还“一个都不原谅”——即便不能完全达到这样的境地。为了暗示自己这样一种“悲剧处境”,他坚持了自己的“病症”,一方面是与忧郁和愤怒共生的“肺病”;另一方面就是与风车和羊群作战的“佯狂”。他不是完美的,甚至也不是最纯洁和真诚的,但他是一个“任性”的勇敢者,一个富有牺牲精神的人,一个流着接舆和屈原的血脉的真正的狂人。
一个诗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