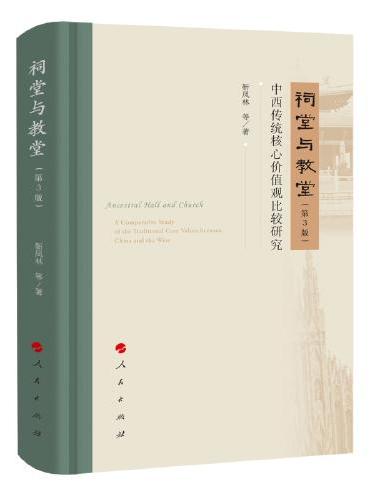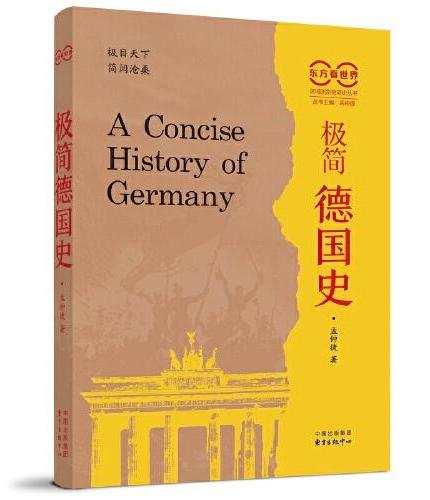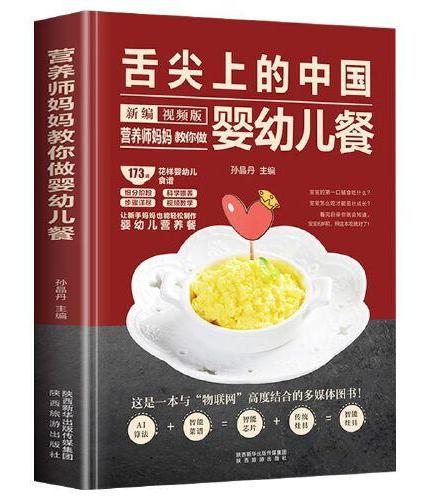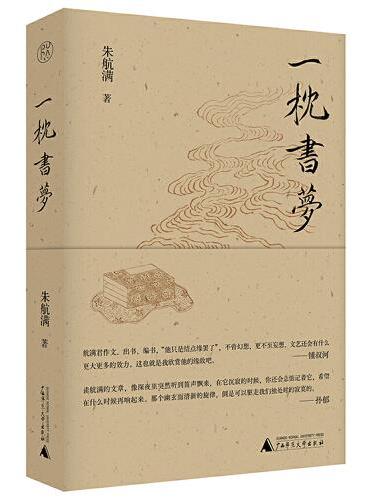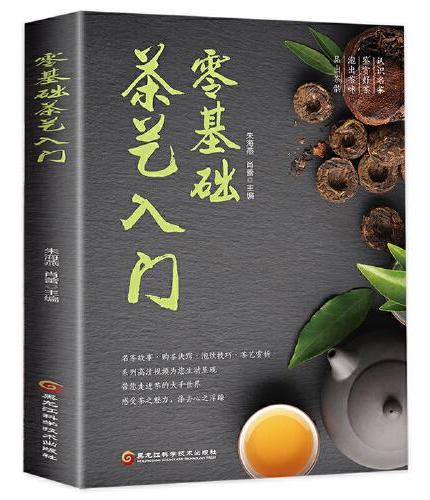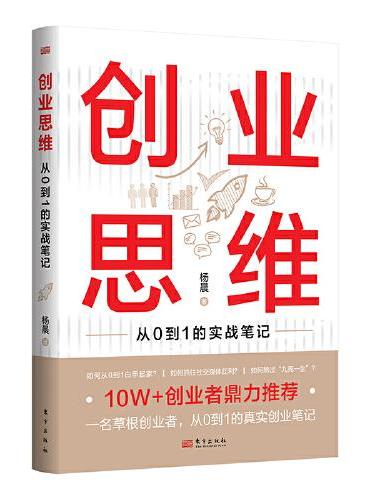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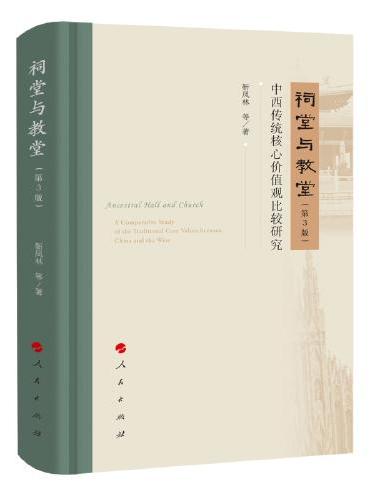
《
祠堂与教堂:中西传统核心价值观比较研究(第3版)
》
售價:NT$
55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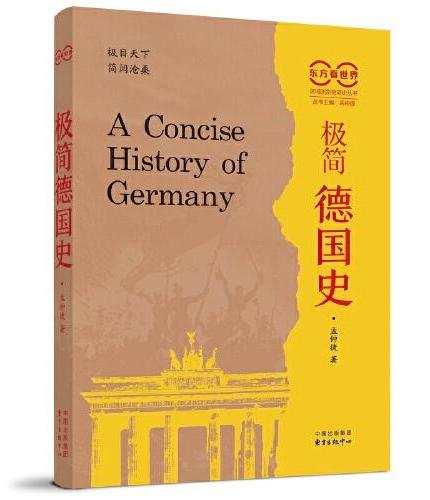
《
极简德国东方看世界·极简德国史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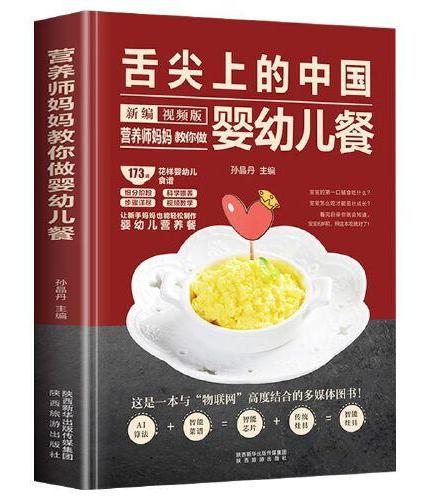
《
舌尖上的中国新编视频版营养师妈妈教你做婴幼儿餐
》
售價:NT$
296.0

《
Scratch创意编程进阶:多学科融合编程100例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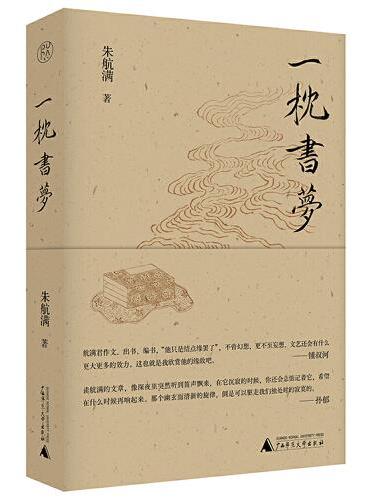
《
纯粹·一枕书梦
》
售價:NT$
36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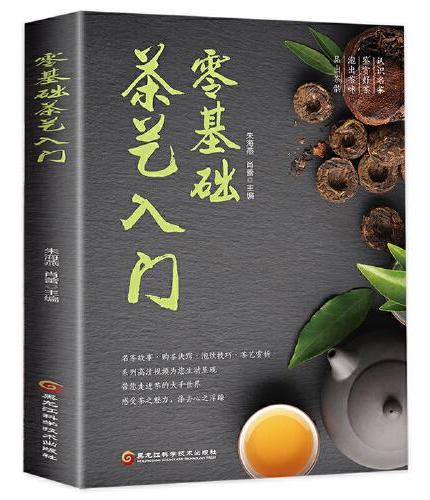
《
新版-零基础茶艺入门
》
售價:NT$
17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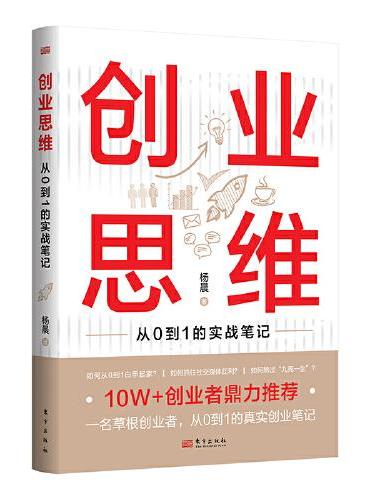
《
创业思维:从0到1的实战笔记
》
售價:NT$
356.0

《
家庭财富管理指南
》
售價:NT$
398.0
|
| 編輯推薦: |
一颗樱桃,窥见人到中年的柔肠百结,绝处逢生
“无赖派旗手”生命绝境前的后书写
重新审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难解关系
全新译本,描摹赤裸众生,全面呈现太宰治半生的总决算
|
| 內容簡介: |
作为父亲?丈夫的“我”以及作为母亲?妻子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我”深信妻子欲摧毁“我”对生活的希望和信念,妻子对这样软弱的“我”却全盘接受……短小章节、绵密文笔,自我与理智相互拉扯,穿透生命绝境前的死亡阴影。
本书共收录太宰治晚期共十三篇异色之作,涵盖短篇、女性独白体以及思想类随笔,展现作者晚年独特的思想风貌。
|
|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太宰治(1909—1948)
小说家,日本“无赖派”代表作家。本名津岛修治,出身地方名门望族,曾就读于东京大学法文系,后被除籍。著书四十余部,或颓废阴郁或轻快风趣;作品被后世誉为“昭和文学的金字塔”,逝世逾半世纪仍拥有大批年轻读者。
太宰自20岁起先后四次自杀未遂,他借笔下人物之口说出“搞笑,是我对人类后的求爱……”;同年留下未完成的幽默小说《Goodbye》,遗言“我已无心再写,故决意赴死”,与情人投水而亡。终年39岁。
【译者简介】
王述坤
日本近现代文学领域资深学者,在国内外媒体发表中日文专栏文章数百万字,出版有日本文史领域著作多部。译有川端康成《岁岁年年》、芥川龙之介《罗生门》等。
竺祖慈
资深日本文学编辑、译者。鲁迅文学翻译奖获得者。译有藤泽周平《小说周边》、三岛由纪夫《假面自白》等。
赵仲明
日本学研究者,译者。译有小谷野敦《双面之人:川端康成传》、是枝裕和《比海更深》等。
|
| 目錄:
|
卷一? 久经人世
亲友交欢
叮咚、叮咚
美男子与香烟
候鸟
樱桃
Goodbye
家庭的幸福
卷二? 幽微时刻
维荣之妻
阿桑
好客的夫人
卷三? 思想芦苇
苦恼的年鉴
Chance
聊聊我的前半生
|
| 內容試閱:
|
昭和二十一年九月初,有位男子来找我。
这一事件几乎毫不浪漫,也完全不具备话题性,可是,它令我难以释怀,我想它可能会在我心里留下至死都无法擦除的痕迹。
事件——
当然,称之为事件或许言过其实。我和这位男子一起喝酒,并没有发生口角等诸如此类的情况,至少表面上,我们在和睦的氛围中道别,仅此而已。然而,我还是觉得发生了让自己耿耿于怀的重大事件。
总而言之,这位男子十分厉害,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我对他没有一丝好感。
去年,因为战火,我不得不投奔位于津轻的父母家避难,几乎每天都老老实实地把自己关在里屋,偶尔有当地某某文化协会或某某同人会邀请我去举办演讲或出席座谈会,我一概拒绝:“讲得比我好的人多得是。”我独自闷头喝酒,酒后倒头就睡,每天过着近似隐士的生活。过去生活在东京的十五年时间,我出没于下等的居酒屋,喝劣等的酒,与所谓底层的人交流,对各种泼皮无赖早已司空见惯。可是,我对这位男子却束手无策。总之,他身手不凡。
九月初的某天,吃了午饭后,我在主屋的起居室里百无聊赖地独自抽烟,有位身着宽大田间工作服的男子有气无力地站在玄关换鞋子的地方。
他“哎呀”了一声。
他就是我故事中的“亲友”。
(虽然下面这些话略显迂腐,但是为了防止误解,我想言明在先。我在这篇手记中描绘了一位农夫形象,向世人揭示他令人厌恶的个性,但是,完全不存在借此声援阶级斗争中的所谓“反动势力”的意图。对于这一点,大部分读者在读完本手记后自然心知肚明。虽然这种声明无疑大煞风景,但是,近来那些智力极度堪忧,不可理喻之人,动辄利用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小题大做,下不负责任的结论,因此,请允许我对这些因循守旧、愚昧无知—不,或许他们反倒聪明伶俐—的人用片言只语追加几句本不值一提的解释。出现在这篇手记中的男子,虽然长着一张庄稼人的脸,但他绝非“意识形态专家”们热爱的农夫。他是一位十分复杂的男子。反正我是次遇见这种人,可以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我甚至预感到一种新型人类的诞生。我无意从善与恶的角度对他进行道德审判,倘若能为读者提供诞生这种新型人类的预感,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他声称是我小学时代的同学,名叫平田。
“你忘了吗?”他说着,露出一口白牙笑了起来。我隐隐觉得他的脸有些熟悉。
“记得,进来吧。”那天,我在他面前的确变成了阿谀逢迎的社交家。
他脱下草鞋,走进起居室。
“好久不见啊,”他大声说道,“几年没见了?不,是几十年?啊,二十多年没见啦。早听说你来了,田里的农活太忙,没时间来找你呀。听说你也变成酒鬼啦。啊哈哈哈。”
我苦笑着,沏了茶端到他跟前。“你忘了和我打架的事?我们经常打架。”
“有这回事吗?”
“什么有这回事吗。你看,这手背上还留着伤疤,被你抓伤的。”
我仔细看了一下他伸到我眼前的手背,没有任何抓伤的疤痕。
“你的左腿迎面骨应该也有伤疤,有吧?肯定有啊。那是我用石头扔你时留下的伤。哎呀,我和你干过不少次架呢。”
无论我的左腿迎面骨还是右腿迎面骨,没有一处受过那样的伤。我只是不置可否地微笑着听他说话。
“言归正传,我想和你商量件事。召集个同学会,怎么样?不想?大家一起开怀痛饮。找十个人参加,两斗酒,我来搞定。”
“主意不错,两斗酒会不会有些多?”
“不,不多。一人不喝两升多没劲。”
“能搞到两斗酒吗?”
“没准搞不定。我不确定,试试看。别担心。不过,就算是在乡下,近酒也不便宜,这件事得拜托你。”
我心照不宣,起身走进里屋取来五张大纸币。
“这些钱你先收着,不够的话之后再补。”
“等等,”他把纸币推回给我,“我不是这意思,我今天不是来向你要钱的,只是来找你商量,想听听你的意见。反正后你免不了要出千八百的。今天我是来找你商量,也是想见见你这个老同学。就这么定了,事情交给我办,这些钱,你先收起来。”
“这样啊。”我将纸币收进上衣口袋。
“没酒吗?”他突然问。
我不禁重新看了看他的脸。一瞬,他也表情尴尬地眯了一下眼睛,不过,他固执地追问:
“听说你家里老备着两三升酒,让我喝点儿。你老婆呢,不在家吗?让你老婆出来给我斟杯酒。”
我站起来。
“好吧。你跟我来。”
我深感无趣。带他走进里面的书房。
“房间很乱。”
“不,我不介意。作家的房间都差不多。在东京的时候,我也和很多作家打过交道。”
可是我压根无法相信他说的话。
“果然很乱,不过,房间不错。到底是大户人家。院子的视野很开阔。还有柊树啊。你听说过柊树的传说吗?”
“没有。”
“没听说过?”他一下子得意起来,“这个传说,往大里说是世界的,往小里说是家庭的,还能用作你的写作素材。”
他的话完全不知所云,我甚至觉得他脑子有问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很快,他向我展示了诡计多端、工于心计的另一面。
“是什么呢?那个传说。”
我不禁笑道。
“以后告诉你吧,柊树的传说。”他煞有介事地说。
我从壁橱里取出还剩一半酒的长方形威士忌酒瓶。
“威士忌,你介意吗?”
“行啊。你老婆不在家?快让她出来斟酒啊。”
我在东京生活了很久,招待过众多客人,从没有人对我说过这种话。
“内子不在家。”我撒了个谎。
“别这么说。”他根本不理会我的话。“快把她叫出来,给我斟酒呀。我特意跑来,想喝一杯你老婆斟的酒。”
大城市里的女人,优雅、妩媚的女人,如果这是他的期待,那么不仅对他十分抱歉,而且对内子也很残忍。内子虽然是城里人,但是气质粗鄙,长相丑陋,待人冷淡。要把内子叫出来,我颇觉得为难。
“算了吧。让内子斟酒,这威士忌反而不香了。”我说着把威士忌倒进写字台上的茶杯里。“这酒在过去的话是三流酒,不过,倒不是用甲醇勾兑的。”
他咕嘟咕嘟一口气喝完,又啧了几下嘴。
“像蝮蛇烧酒。”他说。
我再次为他斟酒。
“喝太猛的话一会儿上头,会不舒服。”
“什么?你太小看人了吧,我可是在东京一次喝过两瓶三得利的人。这威士忌,我想想,大概六十度吧?一般,劲不大。”他说着再度一饮而尽。此人毫无酒品可言。
这次他给我斟酒,又把自己的茶杯斟满。
“已经完了。”他说。
“哦,是吗。”我像个一流的社交家,心领神会地爽快起身,从壁橱里重新取出一瓶威士忌,打开瓶盖。
他若无其事地点点头,又喝了起来。
我未免有些不爽。我从小养成了浪费的恶习,爱惜东西的意识(虽然这绝不值得自满)和常人相比略为淡薄。然而,这些威士忌算是我的珍藏品。虽然过去是三等酒,但现在无疑成了天下一等的佳酿。这些酒固然价格不菲,然而更重要的是,为了搞到这些酒我费尽了心机,不是有钱就能入手的。很久以前,我好不容易从别人手里匀了一打,并因此倾家荡产。但是,我并不后悔。我非常珍惜这些酒,一小口一小口地慢慢品尝,嗜酒的作家井伏等人来我家时,请他们喝上一杯。不过,这些酒逐渐喝完了,当时,壁橱里只剩下两瓶半。
他提出喝酒时,清酒等酒恰好全都喝完了,所以我取出所剩无几的珍藏的威士忌,没想到被他鲸吸牛饮。虽然这话听上去像个十足的吝啬鬼在发牢骚(不,恕我直言,对这些威士忌,我就是吝啬鬼,心有不舍),可他竟喝得如此理直气壮,天经地义,我情不自禁地感到厌恶。
而且,他嘴上说的话丝毫无法引起我的共鸣。这并非因为我是有文化、趣味高雅的人,而对方是不学无术的乡巴佬。我没有这种意思。我甚至和没有半点学识的娼妇认真交谈过“人生的真谛”这种话题,也有过被目不识丁的老工匠教训而流泪的事情。我甚至怀疑社会上所谓的“学问”。他说的话之所以没让我产生任何愉悦,理由的确在于其他方面。理由是什么呢?我与其在此三言两语地妄下定论,不如如实记录下那天他在我家的言行举止,任由读者进行判断,这看上去更像是符合作家身份的所谓健康手段。
他起初喋喋不休地絮叨“我的东京时代”,乘着酒兴发作,他愈发滔滔不绝起来。
“可你在东京也栽在女人手里了呀。”他大声嚷着,笑了起来。“实际上,我在东京的时候也差点栽了。差一点就和你一样栽个大跟斗。真的呀。实际上就差那么一点儿,可我跑了呀。嗯,我跑了。女人一旦爱上男人就忘不了。啊哈哈哈。她现在还给我写信呢。嘻嘻。前一阵还寄来了年糕。女人真是痴情啊,真的。要想让女人爱上你,不靠颜值,不靠钱,就靠你的心情,靠心啊。其实我在东京那会儿也过得放荡不羁。仔细想想,那个时候你在东京,不用说也在和艺妓厮混,惹得她们为你寻死觅活,可是你一次都没有遇到我,这太不可思议了。你那时候究竟在什么地方浪?”
我不明白他说的那个时候是哪个时候。而且,我在东京从来没有像他推测的那样玩过艺妓,也没人为我寻死觅活。我大多在露天烤鸡肉串的小摊位上喝冲绳的泡盛酒或者烧酒,醉后说着车轱辘话。他说我在东京“栽在女人手里”的事情,岂止一两回,我屡次三番栽大跟头,害得父母和兄弟姐妹脸上无光。不过,我至少可以这么说,“我绝不是倾尽所有,把自己打扮成美男子,玩弄艺妓,并且为此沾沾自喜!”这虽说是可怜的申辩,可是就连这样的申辩,至今也无人相信,从他说的话中我明白了这一点,觉得厌烦。
但是,这种不愉快,也不是这个男人让我首次体验到的,例如东京文坛上的评论家,还有其他各色人等,甚至有的是我称之为朋友的人,他们也让我饱尝了痛苦。虽然,现在这一切都已经成了听后一笑了之的事情,可是面对眼前这位农夫模样的男子,我感觉他似乎把这些当成了我的巨大软肋,企图乘虚而入,他的用心何等险恶,无聊至极。
可是,那天的我是一个极度卑微的社交家,拿不出任何勇气。说到底,我是一个一文不名的战争受害者,拖家带口挤进这个并不富裕的城镇,好不容易勉强糊口,这无疑就是我与生俱来的命运,所以我不得不对过去就居住在这个城镇里的居民投其所好,成了阿谀逢迎的社交家。
我去主屋拿来了水果请他吃。
“你不吃吗?吃水果能醒酒,接下去又能一醉方休了。”
我想,他以这种势头咕嘟咕嘟喝威士忌,早晚会喝得酩酊大醉,即便不发酒疯,也会不省人事,到时便很难收场了。为了让他平静下来,我削了一个梨递给他。
他看上去并不想醒酒,看都不看水果一眼,手一直放在盛有威士忌的茶杯上。
“我讨厌政治家,”他突然将话题转到了政治上,“我们农民不用懂什么政治。谁让我们的实际生活哪怕有一丁点所得,我们就支持谁。这就够啦。谁把看得见的利益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抓住,我们就支持谁。这就够了,不是吗?我们农民没有野心,懂得知恩图报,这就是我们农民实诚的地方。管他是什么进步党还是社会党。我们农民只要能种田、耕地就够了。”
我一开始并不理解他为什么突然说出这么奇怪的话,等到他说了下面这番话之后,我才终于理解了他的真实意图,并不由得苦笑。
“上次选举,你也为你哥大肆活动过吧?”
“没有,我没为他干过任何事。我每天都在这个房间里忙自己的工作。”
“撒谎。就算你是文学家,不是政治家,这也都是人情世故。你一定为你哥鞍前马后出过力。我虽然是个不学无术的农民,可我也懂人情世故。我讨厌政治家,也没有野心。我不怕什么社会党、进步党,可我是讲交情的。我和你哥谈不上很熟,但至少你和我是老同学,是好朋友,不是吗?这就是交情。尽管没人求我,可我还是投了你哥一票。我们农民根本不管什么政治,只要不忘记一样东西,交情,这就够了,你说呢?”
这一票难不成就是你来我家畅饮威士忌的权利吗?他的花招显而易见,我愈发觉得索然无味。然而,他也不是头脑简单的人,忽然,他似乎敏感地察觉到了什么。
“我也不是想变成你哥的家臣啊。不用那么看不起我。就说你家,查查你家的祖上,也就是个卖油出身。你知道吗?我是听我家老婆子说的,给买一合1油的人奖励一颗糖,靠这种生意发了财。再说河对岸的斋藤家,现在是大地主,神气活现的,往上数三代,他家就是在河里捡柴的。把柴禾削成竹子,再把河里抓到的小杂鱼串起来烤熟,一文两文卖出去,靠这种生意赚了钱。还有大池先生家,在路边放一排木桶,让过路的行人往里面撒尿,木桶里的尿装满后卖给农民,这就是他家掘到的桶金。有钱人家,查一下他们的老底,都是这么过来的。我家,你给我听好了,在这一带可是古老的家族。据说我家祖先是京都人,”他话说到一半,似乎也有些不好意思地“嘿嘿”笑了起来,“虽然老婆子的话不可靠,完整的家谱倒是有的。”
“可能真的出自公卿名门。”为了满足他的虚荣心,我一本正经说道。
“嗯。当然,我不是很确定,差不多这种程度。只有我每天弄得浑身脏兮兮地在田里干农活。我哥,你也认识吧,他可是大学毕业生。他是大学棒球队的队员,不还经常上报纸吗?我弟弟现在也在上大学。我因为有自己的想法当了农民,可我哥和我弟现在照样不敢在我面前抬头。不管怎么说,东京又不产粮食,我哥虽然大学毕业后当上了科长,却老来信要我给他寄大米。寄大米可麻烦了。我哥自己来取大米的时候,他要多少我都让他扛走。不过,毕竟是东京衙门里的科长,他也不能老来扛大米吧。还有你,缺什么,随时来我家。我可不想白喝你的酒呀。农民都是老实人,受过别人的恩惠一定会如数奉还。哎呀,我不喝你斟的酒了!把你老婆叫出来。你老婆不给我斟酒,我不喝了!”我觉得不可思议,我又没让你没完没了地喝我的酒。“我不想喝了。快把你老婆带来!你不把她带来,我就去把她拽出来。你老婆在哪儿?在卧室吗?睡觉的房间?我是天下无敌的农民。平田家族你不知道吗?”他醉得越来越厉害,开始胡闹,摇摇晃晃站起来。
我笑着安抚他坐下。
“好吧,我把她带来。她是个无趣的女人,行吗?”
我说着去了内子和孩子待着的房间。
“我说,过去上小学时的同学来家里玩了,过来打个招呼。”
我煞有介事地说。
我不愿意让内子看不起自己的客人。家里的来客,不管什么类型,只要我家人对他们稍有轻贱,我就会十分痛苦。
内子抱着小儿子走进书房。
“这位先生是我小学时代的亲友,名字叫平田。我们上小学时经常打架,他右手还是左手手背上还有被我抓破后留下的疤痕,所以今天来找我算账了。”
“是吗,好可怕。”内子笑道。随后,她又恭恭敬敬鞠了一躬,“请您多多关照。”
他似乎很满意我们夫妇极其谦卑的社交礼节,喜形于色。
“哎呀,那些见外的客套话就免了。夫人,你来我这边,给我斟酒。”他也是个精明过人的社交家。背后称呼内子“你老婆”,当面改口称作“夫人”。
内子为他斟酒,他一饮而尽。
“夫人,我刚才还和修治(我的小名)说,家里缺什么东西,尽管来我家取。我家什么都有,番薯、蔬菜、大米、鸡蛋、鸡肉。马肉怎么样?你们吃吗?我是剥马皮的名人。想吃的话,来我家取。我让你们扛一条马腿回去。爱吃野鸡吗?山鸡比较好吃吧?我可是猎手啊。只要提起猎手平田,这一带无人不晓。你们喜欢吃什么,我都能为你们打。鸭子怎么样?鸭子的话,明天一早我就去田里打十只送给你们。我曾经在吃早饭前打落过五十八只鸭子呢。如果觉得我骗人,你去找桥边的铁匠笠井三郎问问。我的事,那男人一清二楚。提起猎手平田,这一带的年轻人服气。对了,明天晚上,喂,文学家,和我一起去八幡神社逛庙会吧。我来找你。可能会有年轻人打群架,局势不稳啊,我会冲进人堆里让他们住手!就像幡随院的长兵卫1。我已经不在意死活了。就算死了,我还有财产,老婆和孩子都不会活不下去。喂,文学家,明天晚上,一定要陪我一起去啊。我要让你见识一下我的本事。每天待在这里屋无精打采地过日子,写不出好作品。你究竟在写什么作品?呵呵,艺妓小说吗?你没吃过苦头不行。我已经换过三个老婆了,越到后面的越可爱。你呢,你也有两个吗?三个吗?夫人,怎么样?修治疼你吗?别看我这样子,我也是在东京生活过的男人呀。”
情况变得非常不妙,于是我吩咐内子去主屋取些下酒菜,把她支开了。
他不慌不忙地从腰间取出装烟的荷包,又从荷包附带的布袋里取出装有火绒的小盒子和打火石。他“咔嚓咔嚓”地在烟管上点火,可是总点不着。
“我这儿有很多香烟,你抽这个吧,抽烟管很麻烦吧?”
我这么一说,他注视着我,抿嘴一笑。他收起装烟的荷包,十分自豪地说:
“我们农民用的都是这玩意儿呀。你们可能瞧不上,可是很方便。哪怕下雨天,只要‘咔嚓咔嚓’打几下火石就能点着。下次去东京,我就想拿着这玩意儿去银座热闹的地方,‘咔嚓咔嚓’来那么几下。你很快就要回东京了是不?我一定会去找你玩。你家在东京什么地方?”
“我家遭轰炸了,还没决定去哪儿呢。”
“这样啊,遭轰炸啦。我次听说。那你领了不少救济物资吧。前不久好像为遭到轰炸的人发了毛毯,送给我吧。”
我茫然不知所措,难以理解他说此话的真意。可是,他似乎并不是开玩笑,且反复唠叨着。
昭和二十一年九月初,有位男子来找我。
这一事件几乎毫不浪漫,也完全不具备话题性,可是,它令我难以释怀,我想它可能会在我心里留下至死都无法擦除的痕迹。
事件——
当然,称之为事件或许言过其实。我和这位男子一起喝酒,并没有发生口角等诸如此类的情况,至少表面上,我们在和睦的氛围中道别,仅此而已。然而,我还是觉得发生了让自己耿耿于怀的重大事件。
总而言之,这位男子十分厉害,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我对他没有一丝好感。
去年,因为战火,我不得不投奔位于津轻的父母家避难,几乎每天都老老实实地把自己关在里屋,偶尔有当地某某文化协会或某某同人会邀请我去举办演讲或出席座谈会,我一概拒绝:“讲得比我好的人多得是。”我独自闷头喝酒,酒后倒头就睡,每天过着近似隐士的生活。过去生活在东京的十五年时间,我出没于下等的居酒屋,喝劣等的酒,与所谓底层的人交流,对各种泼皮无赖早已司空见惯。可是,我对这位男子却束手无策。总之,他身手不凡。
九月初的某天,吃了午饭后,我在主屋的起居室里百无聊赖地独自抽烟,有位身着宽大田间工作服的男子有气无力地站在玄关换鞋子的地方。
他“哎呀”了一声。
他就是我故事中的“亲友”。
(虽然下面这些话略显迂腐,但是为了防止误解,我想言明在先。我在这篇手记中描绘了一位农夫形象,向世人揭示他令人厌恶的个性,但是,完全不存在借此声援阶级斗争中的所谓“反动势力”的意图。对于这一点,大部分读者在读完本手记后自然心知肚明。虽然这种声明无疑大煞风景,但是,近来那些智力极度堪忧,不可理喻之人,动辄利用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小题大做,下不负责任的结论,因此,请允许我对这些因循守旧、愚昧无知—不,或许他们反倒聪明伶俐—的人用片言只语追加几句本不值一提的解释。出现在这篇手记中的男子,虽然长着一张庄稼人的脸,但他绝非“意识形态专家”们热爱的农夫。他是一位十分复杂的男子。反正我是次遇见这种人,可以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我甚至预感到一种新型人类的诞生。我无意从善与恶的角度对他进行道德审判,倘若能为读者提供诞生这种新型人类的预感,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他声称是我小学时代的同学,名叫平田。
“你忘了吗?”他说着,露出一口白牙笑了起来。我隐隐觉得他的脸有些熟悉。
“记得,进来吧。”那天,我在他面前的确变成了阿谀逢迎的社交家。
他脱下草鞋,走进起居室。
“好久不见啊,”他大声说道,“几年没见了?不,是几十年?啊,二十多年没见啦。早听说你来了,田里的农活太忙,没时间来找你呀。听说你也变成酒鬼啦。啊哈哈哈。”
我苦笑着,沏了茶端到他跟前。“你忘了和我打架的事?我们经常打架。”
“有这回事吗?”
“什么有这回事吗。你看,这手背上还留着伤疤,被你抓伤的。”
我仔细看了一下他伸到我眼前的手背,没有任何抓伤的疤痕。
“你的左腿迎面骨应该也有伤疤,有吧?肯定有啊。那是我用石头扔你时留下的伤。哎呀,我和你干过不少次架呢。”
无论我的左腿迎面骨还是右腿迎面骨,没有一处受过那样的伤。我只是不置可否地微笑着听他说话。
“言归正传,我想和你商量件事。召集个同学会,怎么样?不想?大家一起开怀痛饮。找十个人参加,两斗酒,我来搞定。”
“主意不错,两斗酒会不会有些多?”
“不,不多。一人不喝两升多没劲。”
“能搞到两斗酒吗?”
“没准搞不定。我不确定,试试看。别担心。不过,就算是在乡下,近酒也不便宜,这件事得拜托你。”
我心照不宣,起身走进里屋取来五张大纸币。
“这些钱你先收着,不够的话之后再补。”
“等等,”他把纸币推回给我,“我不是这意思,我今天不是来向你要钱的,只是来找你商量,想听听你的意见。反正后你免不了要出千八百的。今天我是来找你商量,也是想见见你这个老同学。就这么定了,事情交给我办,这些钱,你先收起来。”
“这样啊。”我将纸币收进上衣口袋。
“没酒吗?”他突然问。
我不禁重新看了看他的脸。一瞬,他也表情尴尬地眯了一下眼睛,不过,他固执地追问:
“听说你家里老备着两三升酒,让我喝点儿。你老婆呢,不在家吗?让你老婆出来给我斟杯酒。”
我站起来。
“好吧。你跟我来。”
我深感无趣。带他走进里面的书房。
“房间很乱。”
“不,我不介意。作家的房间都差不多。在东京的时候,我也和很多作家打过交道。”
可是我压根无法相信他说的话。
“果然很乱,不过,房间不错。到底是大户人家。院子的视野很开阔。还有柊树啊。你听说过柊树的传说吗?”
“没有。”
“没听说过?”他一下子得意起来,“这个传说,往大里说是世界的,往小里说是家庭的,还能用作你的写作素材。”
他的话完全不知所云,我甚至觉得他脑子有问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很快,他向我展示了诡计多端、工于心计的另一面。
“是什么呢?那个传说。”
我不禁笑道。
“以后告诉你吧,柊树的传说。”他煞有介事地说。
我从壁橱里取出还剩一半酒的长方形威士忌酒瓶。
“威士忌,你介意吗?”
“行啊。你老婆不在家?快让她出来斟酒啊。”
我在东京生活了很久,招待过众多客人,从没有人对我说过这种话。
“内子不在家。”我撒了个谎。
“别这么说。”他根本不理会我的话。“快把她叫出来,给我斟酒呀。我特意跑来,想喝一杯你老婆斟的酒。”
大城市里的女人,优雅、妩媚的女人,如果这是他的期待,那么不仅对他十分抱歉,而且对内子也很残忍。内子虽然是城里人,但是气质粗鄙,长相丑陋,待人冷淡。要把内子叫出来,我颇觉得为难。
“算了吧。让内子斟酒,这威士忌反而不香了。”我说着把威士忌倒进写字台上的茶杯里。“这酒在过去的话是三流酒,不过,倒不是用甲醇勾兑的。”
他咕嘟咕嘟一口气喝完,又啧了几下嘴。
“像蝮蛇烧酒。”他说。
我再次为他斟酒。
“喝太猛的话一会儿上头,会不舒服。”
“什么?你太小看人了吧,我可是在东京一次喝过两瓶三得利的人。这威士忌,我想想,大概六十度吧?一般,劲不大。”他说着再度一饮而尽。此人毫无酒品可言。
这次他给我斟酒,又把自己的茶杯斟满。
“已经完了。”他说。
“哦,是吗。”我像个一流的社交家,心领神会地爽快起身,从壁橱里重新取出一瓶威士忌,打开瓶盖。
他若无其事地点点头,又喝了起来。
我未免有些不爽。我从小养成了浪费的恶习,爱惜东西的意识(虽然这绝不值得自满)和常人相比略为淡薄。然而,这些威士忌算是我的珍藏品。虽然过去是三等酒,但现在无疑成了天下一等的佳酿。这些酒固然价格不菲,然而更重要的是,为了搞到这些酒我费尽了心机,不是有钱就能入手的。很久以前,我好不容易从别人手里匀了一打,并因此倾家荡产。但是,我并不后悔。我非常珍惜这些酒,一小口一小口地慢慢品尝,嗜酒的作家井伏等人来我家时,请他们喝上一杯。不过,这些酒逐渐喝完了,当时,壁橱里只剩下两瓶半。
他提出喝酒时,清酒等酒恰好全都喝完了,所以我取出所剩无几的珍藏的威士忌,没想到被他鲸吸牛饮。虽然这话听上去像个十足的吝啬鬼在发牢骚(不,恕我直言,对这些威士忌,我就是吝啬鬼,心有不舍),可他竟喝得如此理直气壮,天经地义,我情不自禁地感到厌恶。
而且,他嘴上说的话丝毫无法引起我的共鸣。这并非因为我是有文化、趣味高雅的人,而对方是不学无术的乡巴佬。我没有这种意思。我甚至和没有半点学识的娼妇认真交谈过“人生的真谛”这种话题,也有过被目不识丁的老工匠教训而流泪的事情。我甚至怀疑社会上所谓的“学问”。他说的话之所以没让我产生任何愉悦,理由的确在于其他方面。理由是什么呢?我与其在此三言两语地妄下定论,不如如实记录下那天他在我家的言行举止,任由读者进行判断,这看上去更像是符合作家身份的所谓健康手段。
他起初喋喋不休地絮叨“我的东京时代”,乘着酒兴发作,他愈发滔滔不绝起来。
“可你在东京也栽在女人手里了呀。”他大声嚷着,笑了起来。“实际上,我在东京的时候也差点栽了。差一点就和你一样栽个大跟斗。真的呀。实际上就差那么一点儿,可我跑了呀。嗯,我跑了。女人一旦爱上男人就忘不了。啊哈哈哈。她现在还给我写信呢。嘻嘻。前一阵还寄来了年糕。女人真是痴情啊,真的。要想让女人爱上你,不靠颜值,不靠钱,就靠你的心情,靠心啊。其实我在东京那会儿也过得放荡不羁。仔细想想,那个时候你在东京,不用说也在和艺妓厮混,惹得她们为你寻死觅活,可是你一次都没有遇到我,这太不可思议了。你那时候究竟在什么地方浪?”
我不明白他说的那个时候是哪个时候。而且,我在东京从来没有像他推测的那样玩过艺妓,也没人为我寻死觅活。我大多在露天烤鸡肉串的小摊位上喝冲绳的泡盛酒或者烧酒,醉后说着车轱辘话。他说我在东京“栽在女人手里”的事情,岂止一两回,我屡次三番栽大跟头,害得父母和兄弟姐妹脸上无光。不过,我至少可以这么说,“我绝不是倾尽所有,把自己打扮成美男子,玩弄艺妓,并且为此沾沾自喜!”这虽说是可怜的申辩,可是就连这样的申辩,至今也无人相信,从他说的话中我明白了这一点,觉得厌烦。
但是,这种不愉快,也不是这个男人让我首次体验到的,例如东京文坛上的评论家,还有其他各色人等,甚至有的是我称之为朋友的人,他们也让我饱尝了痛苦。虽然,现在这一切都已经成了听后一笑了之的事情,可是面对眼前这位农夫模样的男子,我感觉他似乎把这些当成了我的巨大软肋,企图乘虚而入,他的用心何等险恶,无聊至极。
可是,那天的我是一个极度卑微的社交家,拿不出任何勇气。说到底,我是一个一文不名的战争受害者,拖家带口挤进这个并不富裕的城镇,好不容易勉强糊口,这无疑就是我与生俱来的命运,所以我不得不对过去就居住在这个城镇里的居民投其所好,成了阿谀逢迎的社交家。
我去主屋拿来了水果请他吃。
“你不吃吗?吃水果能醒酒,接下去又能一醉方休了。”
我想,他以这种势头咕嘟咕嘟喝威士忌,早晚会喝得酩酊大醉,即便不发酒疯,也会不省人事,到时便很难收场了。为了让他平静下来,我削了一个梨递给他。
他看上去并不想醒酒,看都不看水果一眼,手一直放在盛有威士忌的茶杯上。
“我讨厌政治家,”他突然将话题转到了政治上,“我们农民不用懂什么政治。谁让我们的实际生活哪怕有一丁点所得,我们就支持谁。这就够啦。谁把看得见的利益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抓住,我们就支持谁。这就够了,不是吗?我们农民没有野心,懂得知恩图报,这就是我们农民实诚的地方。管他是什么进步党还是社会党。我们农民只要能种田、耕地就够了。”
我一开始并不理解他为什么突然说出这么奇怪的话,等到他说了下面这番话之后,我才终于理解了他的真实意图,并不由得苦笑。
“上次选举,你也为你哥大肆活动过吧?”
“没有,我没为他干过任何事。我每天都在这个房间里忙自己的工作。”
“撒谎。就算你是文学家,不是政治家,这也都是人情世故。你一定为你哥鞍前马后出过力。我虽然是个不学无术的农民,可我也懂人情世故。我讨厌政治家,也没有野心。我不怕什么社会党、进步党,可我是讲交情的。我和你哥谈不上很熟,但至少你和我是老同学,是好朋友,不是吗?这就是交情。尽管没人求我,可我还是投了你哥一票。我们农民根本不管什么政治,只要不忘记一样东西,交情,这就够了,你说呢?”
这一票难不成就是你来我家畅饮威士忌的权利吗?他的花招显而易见,我愈发觉得索然无味。然而,他也不是头脑简单的人,忽然,他似乎敏感地察觉到了什么。
“我也不是想变成你哥的家臣啊。不用那么看不起我。就说你家,查查你家的祖上,也就是个卖油出身。你知道吗?我是听我家老婆子说的,给买一合1油的人奖励一颗糖,靠这种生意发了财。再说河对岸的斋藤家,现在是大地主,神气活现的,往上数三代,他家就是在河里捡柴的。把柴禾削成竹子,再把河里抓到的小杂鱼串起来烤熟,一文两文卖出去,靠这种生意赚了钱。还有大池先生家,在路边放一排木桶,让过路的行人往里面撒尿,木桶里的尿装满后卖给农民,这就是他家掘到的桶金。有钱人家,查一下他们的老底,都是这么过来的。我家,你给我听好了,在这一带可是古老的家族。据说我家祖先是京都人,”他话说到一半,似乎也有些不好意思地“嘿嘿”笑了起来,“虽然老婆子的话不可靠,完整的家谱倒是有的。”
“可能真的出自公卿名门。”为了满足他的虚荣心,我一本正经说道。
“嗯。当然,我不是很确定,差不多这种程度。只有我每天弄得浑身脏兮兮地在田里干农活。我哥,你也认识吧,他可是大学毕业生。他是大学棒球队的队员,不还经常上报纸吗?我弟弟现在也在上大学。我因为有自己的想法当了农民,可我哥和我弟现在照样不敢在我面前抬头。不管怎么说,东京又不产粮食,我哥虽然大学毕业后当上了科长,却老来信要我给他寄大米。寄大米可麻烦了。我哥自己来取大米的时候,他要多少我都让他扛走。不过,毕竟是东京衙门里的科长,他也不能老来扛大米吧。还有你,缺什么,随时来我家。我可不想白喝你的酒呀。农民都是老实人,受过别人的恩惠一定会如数奉还。哎呀,我不喝你斟的酒了!把你老婆叫出来。你老婆不给我斟酒,我不喝了!”我觉得不可思议,我又没让你没完没了地喝我的酒。“我不想喝了。快把你老婆带来!你不把她带来,我就去把她拽出来。你老婆在哪儿?在卧室吗?睡觉的房间?我是天下无敌的农民。平田家族你不知道吗?”他醉得越来越厉害,开始胡闹,摇摇晃晃站起来。
我笑着安抚他坐下。
“好吧,我把她带来。她是个无趣的女人,行吗?”
我说着去了内子和孩子待着的房间。
“我说,过去上小学时的同学来家里玩了,过来打个招呼。”
我煞有介事地说。
我不愿意让内子看不起自己的客人。家里的来客,不管什么类型,只要我家人对他们稍有轻贱,我就会十分痛苦。
内子抱着小儿子走进书房。
“这位先生是我小学时代的亲友,名字叫平田。我们上小学时经常打架,他右手还是左手手背上还有被我抓破后留下的疤痕,所以今天来找我算账了。”
“是吗,好可怕。”内子笑道。随后,她又恭恭敬敬鞠了一躬,“请您多多关照。”
他似乎很满意我们夫妇极其谦卑的社交礼节,喜形于色。
“哎呀,那些见外的客套话就免了。夫人,你来我这边,给我斟酒。”他也是个精明过人的社交家。背后称呼内子“你老婆”,当面改口称作“夫人”。
内子为他斟酒,他一饮而尽。
“夫人,我刚才还和修治(我的小名)说,家里缺什么东西,尽管来我家取。我家什么都有,番薯、蔬菜、大米、鸡蛋、鸡肉。马肉怎么样?你们吃吗?我是剥马皮的名人。想吃的话,来我家取。我让你们扛一条马腿回去。爱吃野鸡吗?山鸡比较好吃吧?我可是猎手啊。只要提起猎手平田,这一带无人不晓。你们喜欢吃什么,我都能为你们打。鸭子怎么样?鸭子的话,明天一早我就去田里打十只送给你们。我曾经在吃早饭前打落过五十八只鸭子呢。如果觉得我骗人,你去找桥边的铁匠笠井三郎问问。我的事,那男人一清二楚。提起猎手平田,这一带的年轻人服气。对了,明天晚上,喂,文学家,和我一起去八幡神社逛庙会吧。我来找你。可能会有年轻人打群架,局势不稳啊,我会冲进人堆里让他们住手!就像幡随院的长兵卫1。我已经不在意死活了。就算死了,我还有财产,老婆和孩子都不会活不下去。喂,文学家,明天晚上,一定要陪我一起去啊。我要让你见识一下我的本事。每天待在这里屋无精打采地过日子,写不出好作品。你究竟在写什么作品?呵呵,艺妓小说吗?你没吃过苦头不行。我已经换过三个老婆了,越到后面的越可爱。你呢,你也有两个吗?三个吗?夫人,怎么样?修治疼你吗?别看我这样子,我也是在东京生活过的男人呀。”
情况变得非常不妙,于是我吩咐内子去主屋取些下酒菜,把她支开了。
他不慌不忙地从腰间取出装烟的荷包,又从荷包附带的布袋里取出装有火绒的小盒子和打火石。他“咔嚓咔嚓”地在烟管上点火,可是总点不着。
“我这儿有很多香烟,你抽这个吧,抽烟管很麻烦吧?”
我这么一说,他注视着我,抿嘴一笑。他收起装烟的荷包,十分自豪地说:
“我们农民用的都是这玩意儿呀。你们可能瞧不上,可是很方便。哪怕下雨天,只要‘咔嚓咔嚓’打几下火石就能点着。下次去东京,我就想拿着这玩意儿去银座热闹的地方,‘咔嚓咔嚓’来那么几下。你很快就要回东京了是不?我一定会去找你玩。你家在东京什么地方?”
“我家遭轰炸了,还没决定去哪儿呢。”
“这样啊,遭轰炸啦。我次听说。那你领了不少救济物资吧。前不久好像为遭到轰炸的人发了毛毯,送给我吧。”
我茫然不知所措,难以理解他说此话的真意。可是,他似乎并不是开玩笑,且反复唠叨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