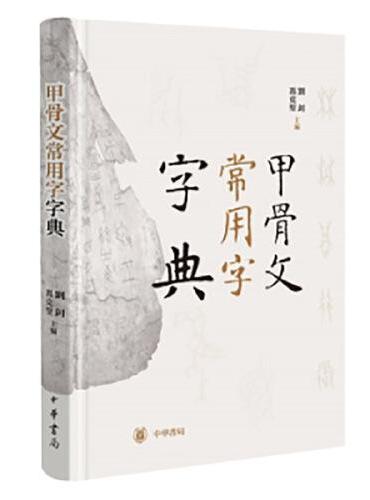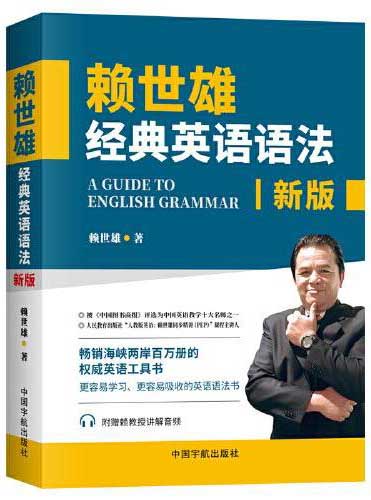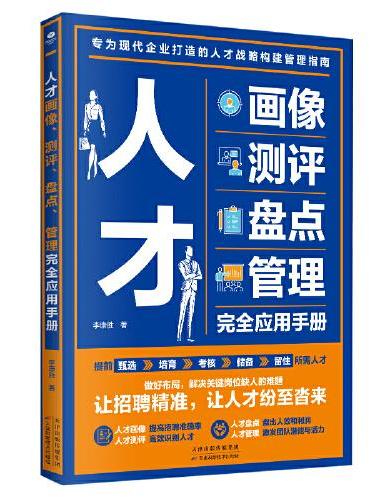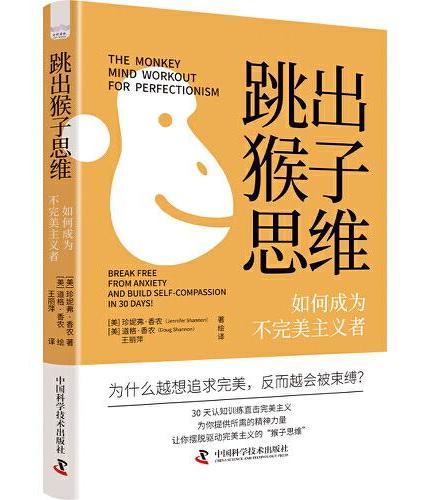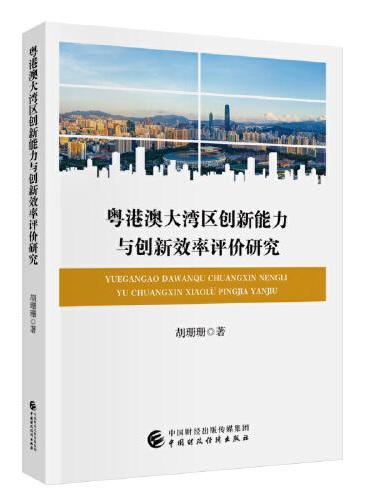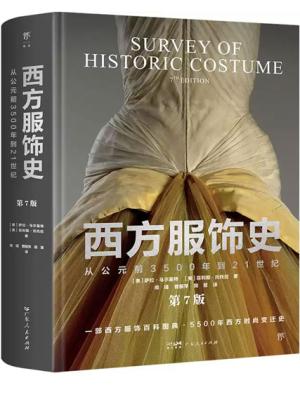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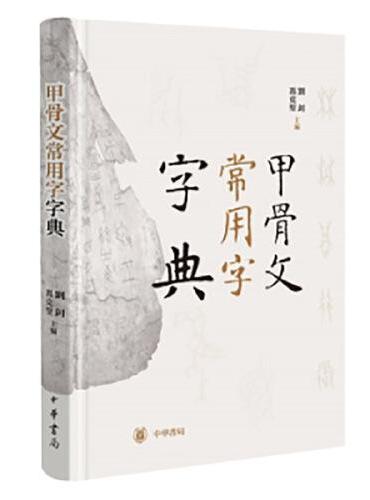
《
甲骨文常用字字典(精) 新版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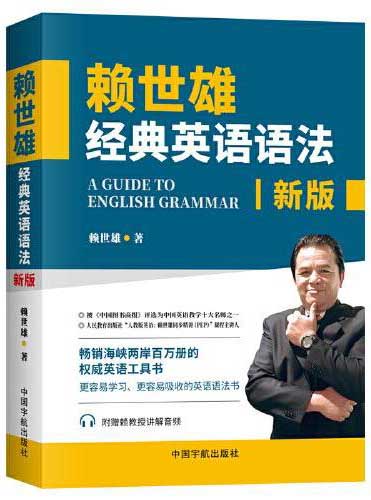
《
赖世雄经典英语语法:2025全新修订版(赖老师经典外语教材,老版《赖氏经典英语语法》超32000条读者好评!)
》
售價:NT$
305.0

《
影神图 精装版
》
售價:NT$
653.0

《
不止于判断:判断与决策学的发展史、方法学及判断理论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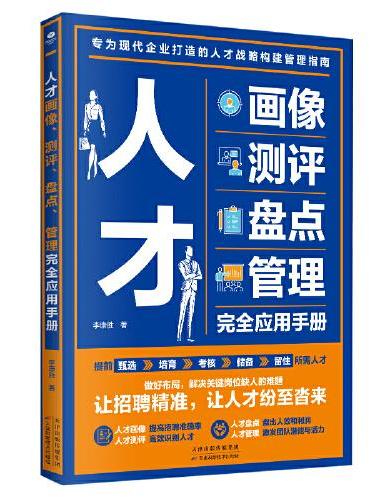
《
人才画像、测评、盘点、管理完全应用手册
》
售價:NT$
2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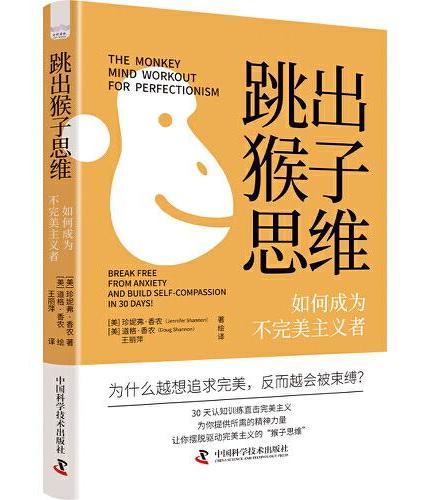
《
跳出猴子思维:如何成为不完美主义者(30天认知训练打破完美主义的困扰!实现从思维到行为的全面改变!)
》
售價:NT$
3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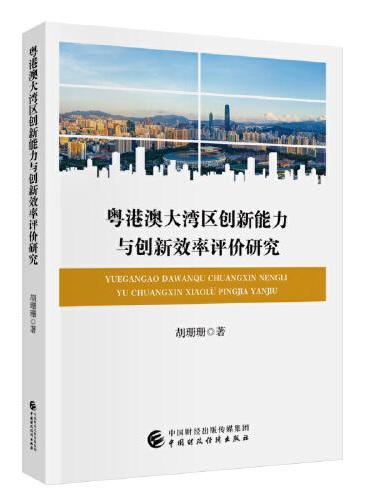
《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能力与创新效率评价研究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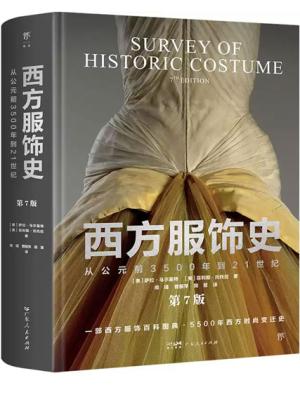
《
西方服饰史:从公元前3500年到21世纪(第7版,一部西方服饰百科图典。5500年时尚变迁史,装帧典雅,收藏珍品)
》
售價:NT$
2030.0
|
| 編輯推薦: |
1930年代,黄文弼两次进入罗布泊调查发掘,是位深入罗布荒漠的中国考古学者,他的《罗布淖尔考古记》是关于罗布泊的shou个有国际影响力的考古报告。
《罗布淖尔考古记》
☆ 本书是黄文弼考古“三记”之一,初版于1948年,由胡适等向教育bu申请经费出版。此后中国没有再版过本书。1968年日本出版本书的ying印版。目前,本书在市面上基本出于空缺状态。
☆ 罗布淖尔,即罗布泊,著名的楼兰古国所在地。本书重点记述了楼兰古国重要遗址的发掘,结合遗址出土物和历史文献,揭开楼兰古国的神秘面纱。
☆ 书中展示了丰富多彩的考古资料,包括文书写本、钱币、碑刻拓片、壁画等各类文物图片,其中很多实物今天已经不存,特别是黄文弼所获文书,如汉语、梵语、龟兹语、粟特语、婆罗谜字母、中古伊朗语等各个语种,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
☆ 中国学者的写作方式,语言凝练优美,可读性强。
《阿里木盆地考古记》
☆ 本书是黄文弼对塔里木盆地周边绿洲古国遗址的深入调查和研究成果,涉及众多经典遗址:焉耆、库尔勒、轮台、库车、沙雅、拜城、和阗、于阗、皮山、叶城等,内容丰富,精彩纷呈。
☆ 考察、考古经过的纪实性叙述
|
| 內容簡介: |
“考古三记”是被称为“中国新疆考古di一人”的黄文弼的新疆考古报告,是他一生重要的成就和贡献的集成,在学术界久负盛名。《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三部作品是黄文弼竭尽毕生精力整理编撰刊布的考古报告:《罗布淖尔考古记》是黄文弼两次赴新疆罗布淖尔(即罗布泊)考察所著;《吐鲁番考古记》是吐鲁番考古研究的奠基之作;《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继续发扬了前两部实地考察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特点与优势。“考古三记”是黄文弼考古研究取得极大成功,为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考古学赢得世界性声誉的证明。
《罗布淖尔考古记》是1930年和1934年,黄文弼两次赴新疆罗布淖尔(即罗布泊)考察,根据实地调查资料,对罗布泊及其附近水道变迁问题、河源问题、罗布沙漠迁移问题、楼兰国史及其国都方位问题、楼兰在中西交通上的地位及其与东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等都进行了详细地考察,并且黄文弼在书中对这些问题都做出了许多独到的论述。
《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以黄文弼两次在塔里木盆地的考古记录与采集文物为基础著成,体现出他对塔里木盆地深入调查与研究的成果,与其他两部考古记一样,发挥了实地考察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特点与优势。本书主要考察的范围包括:焉耆、库尔勒、轮台、库车、沙雅、和阗、于阗、皮山、叶城、巴楚、喀什、阿克苏等古代遗迹。
《吐鲁番考古记》内容分为文字版“吐鲁番考察经过”“遗物说明”和文物图版两部分,刊布了黄文弼两次在吐鲁番考察所获重要古籍和文书写本、钱币、拓片、壁画等珍贵资料。本书与《高昌陶集》《高昌砖集》合称“吐鲁番三部曲”,是吐鲁番研究的奠基之作。
|
| 關於作者: |
|
黄文弼(1893—196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学家、西北历史地理学家。先后四次到新疆进行科研考察。著有《高昌陶集》《高昌砖集》《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新疆考古发掘报告》《西北史地论丛》等。
|
| 目錄:
|
《罗布淖尔考古记》
篇 绪论
章 罗布淖尔水道之变迁与沙漠之移徙 2
一、罗布淖尔名称及位置 2
二、水道变迁探查之经过 4
三、水道变迁时代之推拟 6
四、罗布沙漠之移徙 15
五、附论:河源问题 19
第二章 楼兰国历史略述 30
一、鄯善国之初起及盛时期 31
二、楼兰故地之复活与后之放弃 34
三、鄯善与中原王朝之交涉及其衰亡 37
附论:鄯善与楼兰国都问题 39
四、吐谷浑之侵入与隋唐之经营 43
五、康艳典东来与吐蕃之侵入 45
六、罗布区域之荒废及罗布驿站 48
七、清之改县 51
第三章 楼兰及鄯善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 52
一、两汉至魏晋之南北道及新道 52
二、北魏至隋唐之吐谷浑道 59
三、宋高昌道及元之大北道与南道 62
四、明清时之嘉峪关道 68
第四章 楼兰文化与汉代之经营 72
一、楼兰土著民族之推测及其文化 72
二、汉代对于西域之经营 77
三、汉文明之输入 88
第五章 佛教之传入与其文明 95
一、佛教之传入 95
二、西方文化之输入 105
第二篇 工作概况
章 石器遗址 119
一、英都尔库什 119
二、罗布淖尔北岸 120
第二章 湖畔古冢 128
第三章 古代遗址 141
一、汉烽燧亭遗址 141
二、汉代古道及住宅 147
第三篇 器物图说
章 石器类 158
…………
第四篇 木简考释
…………
《塔里木盆地考古记》
考察经过
章 焉耆
―、焉耆山中及东部之探查4
二、焉耆南部及西部古址之发掘与探查6
(一)锡科沁之明屋6
(二)霍拉山废寺9
(三)阿拉尔旧城10
(四)四十里城市旧城11
(五)哈拉木登旧城13
第二章 库尔勒、轮台
一、库尔勒至轮台途中遗址之探查14
(一)库尔楚15
(二)野云沟16
(三)卡尔雅河畔古址及石刻16
二、轮台草湖中之古城17
(一)克子尔河畔之古城17
(二)第纳尔河畔之古城19
第三章 库车、沙雅
―、库车西部佛教遗址之工作23
(一)库木土拉千佛洞23
(二)铁吉克遗址30
二、沙雅西北部之古址31
(一)大望库木旧城及周围之古址31
(二)通古斯巴什旧城及周围之古址34
(三)羊达克沁大城及周围之古址37
三、库车、沙雅东部之古址39
(一)沙雅东部之古址39
(二)库车东部之古址44
(三)库车城附近之古址49
第四章 拜城
一、库车、拜城山中之古迹52
(一)可可沙之古迹区域52
(二)博者克拉格沟口刻石55
二、克子尔明屋之工作58
三、往返拜城、阿克苏途中之古址61
第五章 和阗及于阗
―、横渡大沙漠与和阗河67
二、和阗、于阗沙漠中之古址73
(一)和阗北沙碛中之遗迹73
(二)达摩戈一带古址75
(三)克里雅河及喀拉墩78
三、古和阗河畔之古址81
(一)阿克斯比尔83
(二)什斯比尔85
第六章 皮山、叶城及巴楚等地
―、皮山及叶城山中之古址87
(一)皮山山中之古址 87
(二)叶城山中之古址88
二、喀什噶尔河畔之古址92
(一)伽师之古址93
(二)托和沙赖古址94
三、阿克苏河畔之古址98
…………
《吐鲁番考古记》
一、吐鲁番考察经过
次工作经过 2
(一)高昌城之沿革 4
(二)高昌古城之现状 5
(三)高昌古城附近之情形 6
第二次工作经过
二、遗物说明一:古籍写本及题记
(一)《毛诗·简兮》校记 24
(二)《尚书·大禹谟》校记 27
(三)《孝经·三才章》校记 27
(四)《孝经·□宗明义章》 校记 29
(五)佛书《善见律》音义校记 30
(六)佛书音义校记 30
(七)《文选序》校记 32
(八)阴阳杂书校记 32
(九)《佛说首楞严三昧经》及题记 34
(一〇)《维摩诘所说经注·方便品第二》 35
(一一)比丘尼僧写《涅槃经》题记 36
(一二)为开元皇帝祈福文残片 37
(一三)观音奴别译文题识 37
(一四)汉文佛经印本 38
(一五)《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拓本 39
三、遗物说明二:古文书写本(附钱币及碑志拓本)
(一)白雀元年物品清单 40
(二)□露二年残牒 41
(三)安末奴等纳驼状 43
(四)西州征物残牒 44
(五)开元十三年征物残牒 44
(六)张元璋残牒 45
(七)府司阿梁状词并批 45
(八)高昌县征夫残状 46
(九)虞候司及法曹司请料纸牒 47
…………
|
| 內容試閱:
|
再版前言
一
《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西北历史地理学家黄文弼先生的新疆考古报告,与他所著的《高昌砖集》《高昌陶集》合称“三记两集”,在学术界久负盛名。
“三记”的写作缘起,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成立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有着直接关系。1927年春,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征得北洋政府同意,准备单方面开展他的第四次中国西北考察。中国知识界对这种有损国家主权的行为极力抵制,并组成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斯文·赫定反复谈判,终成立了由中外学者共同主持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自1927 年至1935年,在中国西北地区开展了长达8年的科学考察活动,成就了人类科学探查史上的一个壮举。
时任北京大学国学门助教的黄文弼,出于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和对考古学的浓厚兴趣,主动请缨加入考查团,成为团中一名中方考古学者。1927年5月9日,他暂别“在故纸堆中讨生活”,随队踏上西北科考的征程,在内蒙古,特别是在新疆地区进行了历时三年多艰苦卓绝的野外探查。擅长文物搜集、整理的他,在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这所“流动的大学” 中,获得了难得的田野考察与发掘实践经验,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鼓舞了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考古学,历来被当做中国学术界在新疆地区进行科学考古的起点。他此后的三次新疆之行,都可以视为本次考察的延续。就黄文弼个人而言,这次西北科考经历也成为其学术道路的重要转折点,以此为契机,他将一生精力都聚焦于新疆考古和西北史地研究,并完成了“三记两集”的名山事业,以及后来的《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等论著。
《罗布淖尔考古记》于1948年作为“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丛刊” 之一,由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印行,是“三记”中早问世的一部。罗布淖尔古称盐泽、蒲昌海,今作罗布泊,汉代楼兰国就位于此地。19世纪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到来,打开了罗布泊闻名世界的大门,此后斯文·赫定、斯坦因接踵而至。1930 年4月8日,黄文弼从吐鲁番出发,翻过库鲁克山,于1930年4月13日抵达罗布泊北岸,目睹罗布泊水向北回流的情况,验证了斯文·赫定称罗布泊是“游移湖”的假设。
黄文弼这次在罗布泊地区考察了20多天,但由于时间紧迫,很多调查未能充分展开,回来后一直对罗布泊念念不忘。1933年10月,为巩固边陲,开发西北,国民政府铁道部决定出资组建“绥新公路查勘队”,黄文弼在教育bu资助下,以考察新疆教育文化专员的身份参加查勘队,二入新疆。1934年5月9 日,黄文弼再次踏上闻名世界的“土垠”——在这个四年前由他发现的汉代驿站遗址,找到了军营、古道、屯垦区遗迹,并采集到西汉《论语》残简及记“居卢訾仓”事简。《罗布淖尔考古记》就是黄文弼这两次罗布泊考察成果的汇集。
《吐鲁番考古记》1954年在科学出版社初版,1957年修订重印,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丁种第五号”。该书与《塔里木盆地考古记》都是黄文弼首次新疆考察成果的结晶。
吐鲁番地区是黄文弼正式开启新疆考察的站,也是他日后转向新疆考古与西北史地研究的学术起点。在参加西北科学考查团期间,黄文弼曾三至吐鲁番:1928年2月,他由哈密赴乌鲁木齐时路过吐鲁番,仅在此稍作停留,访查了吐峪沟千佛洞; 1928年4 月19日,他对交河故城、高昌故城、柏孜克里克千佛洞进行了初步踏查;1930 年2月19 日,他带队对交河故城北部寺庙遗址、沟西墓地、南部古坟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全面发掘,成为个在吐鲁番地区进行考古工作的中国学者。
从今天保留下来的黄文弼《吐鲁番研究手稿》来看,他在考察途中就已经开始对吐鲁番地区古代文化进行研究。1931 年和1933 年,黄文弼根据考察所得,分别出版《高昌砖集》与《高昌陶集》。而出土墓砖与陶器以外的文物、文书以及相关研究,都收录在《吐鲁番考古记》中,这三部著作又构成黄文弼的“吐鲁番三种”,内容各有侧重,相互补充。
1957年,黄文弼发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序言摘要》一文,次年《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即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考古学专刊丁种第三号”。
塔里木盆地周缘的大小绿洲,自古就是东西方文化传播与交汇的核心地带,特别是随着佛教东渐,更在古代塔里木盆地形成举世闻名的佛教文化。黄文弼于1928年5月19 日自吐鲁番出发,穿越阿拉癸沟直奔焉耆,在七个星佛窟遗址、四十里城等地考察了40 余天,采集到大量的泥塑佛像、石刻模型、木器、铜器。1928年9月中旬到11月中旬,他无论“沙漠湖滩,有古必访”,将古代龟兹国所在的库车地区全部走遍,新发现古城遗址10多处。1929年4月5日,黄文弼沿和阗河一路南行,为了寻找“死亡之海”汉唐时期曾经存在过的繁华历史,完成了横渡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举。1929年11月8日,黄文弼结束对塔里木盆地周缘的全部考察,这段考古资料的精华均刊布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
二
1929年冬季和1930年春末,考查团收获的考古文物由袁复礼两次组织东运,其中包括黄文弼的80余箱采集品。1930年秋季回到北平后,黄文弼立刻投入到新的研究工作中,他很早就明确了自己“首高昌,次蒲昌,次焉耆,次库车,次和阗,次佉沙”的工作目标和规划。按照计划,在完成《高昌砖集》《高昌陶集》后,黄文弼即将开展对罗布淖尔考察的系统研究,并先期完成《楼兰之位置及其与汉代之关系》《释居卢訾仓》《罗布淖尔水道之变迁》系列论文。然而,接下来的研究工作却阻力重重: 工作频繁调整,抗战爆发,经费紧缺,使得考古报告迟迟不得与世人见面。
1934年12月5日,黄文弼受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派遣,在安阳、洛阳、西安、南京等地进行考古工作,随后又担任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西安办事处主任。他将一部分考察采集品带在身边,白天全力进行西安碑林的修复工作,夜晚则继续投入采集品的整理与研究。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撤销,西安办事处同时停止工作。当时,国立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机构迁往西安,成立了西安临时大学,随即又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校址迁到陕西城固。黄文弼也辗转离开西安,赴城固任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一年后,西北联合大学分立为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师范学校五所院校,黄文弼又转任西北大学,同时受聘兼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
1939年至1942年间,黄文弼基本都奔波在川陕两地,一边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一边利用中英庚款董事会资助,从事考察报告的撰写和西北史地研究。在城固无数个一灯如豆的夜晚,他抱定随身携带的少量采集品进行撰述; 在四川峨眉,他一度“静居山中,重理旧稿”,笔耕不辍。据《罗布淖尔考古记·自叙》所说,该书正 文部分实际在1939 年底就已经完稿,黄文弼曾通过蔡元培联系商务印书馆出版,但由于大量文物实物照片要印制为彩色画及珂罗版,成本过高而没了下文。1944年初,顾颉刚帮助他向中华书局推荐此书,黄文弼也亲自与编辑金兆梓、姚绍华接洽出版事宜,但又因经费问题未能如愿。在1947年写给徐旭生先生的系列信件中,他也曾提及此书出版经费问题。一直到1948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以 “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理事长名义,领衔给国民教育bu递交呈文,向部长朱家骅申请经费,并多方努力周旋,寻求中美基金会的资助,才使《罗布淖尔考古记》历经波折,得以出版。
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黄文弼曾利用参加第二届全国美展之机,将部分西北科学考察的采集品带到南京,后来为躲避日军对西安的空袭,又在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协助下,把存放在陕西的文物转运到汉口。寄居川陕期间,黄文弼一直牵挂着这些文物的安危。抗战胜利后,他曾亲自去汉口英国洋行堆栈查访寄存文物,得到的却是大部分物品毁于战火的不幸消息,这些都对黄文弼的后续研究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新中国成立后,黄文弼由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转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沐浴在科学事业蒸蒸日上的氛围下,他再次全身心地投入到科学研究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术著作出版困难的境遇一去不返,黄文弼对考古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也终于厚积薄发,《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相隔不到四年先后面世。自1928年首次踏上新疆的热土,到1958年完成《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的出版,“三记”的写作整整经历了三十个寒暑。从烽火连天的旧社会,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从年富力强的中国西部考古拓荒人,到白发苍颜的老年学者; 从踌躇满志的学术规划,到皇皇巨著的终杀青:无论对于黄文弼本人,还是整个学术界来说,“三记”的写作和出版都可谓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长达三十年的学术跋涉,以及迟到的“三记”,也都成为黄文弼波澜壮阔的一生的缩影,成为中国早年新疆考察与研究史的见证,成为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乃至国家命运的回顾。其中饱含着以黄文弼为代表的一代学人的坚韧毅力,以及他们为追逐理想而终生奋斗的执着与热情。
三
早在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出发伊始,黄文弼就曾说过自己此行的目的:“一者为监督外人,一者为考察科学。”监督外人、维护国家主权的使命与责任,让他从初与外方团长斯文·赫定互相“心存芥蒂”的私人关系,终于在两人第二次新疆考察期间爆发。由于斯文·赫定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致使黄文弼的个人声誉及成果在国外学界一度受到抵制。不过,随着“三记两集”的渐次问世,黄文弼的新疆考古成就终究难掩其光芒,逐渐成为国际学界有目共睹的焦点。
《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出版后不久,就受到日本学界的关注,藤枝晃、石田幹之助分别发表评介文章。此后,日本京都大安书店于1968年影印出版《罗布淖尔考古记》。1984年,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宫川寅雄倡议组织翻译《黄文弼著作集》,经过四年的努力,由田川纯三翻译的《黄文弼著作集》册《罗布淖尔考古记》日译本在东京恒文社出版。1990年,土居淑子的日译本《黄文弼著作集》第二册《吐鲁番考古记》(包括《高昌砖集》《高昌陶集》《吐鲁番考古记》)继由恒文社出版。
《黄文弼著作集》的日译工作,因主持者宫川寅雄及诸位翻译家的离世而搁浅,但是其影响力已然形成。日人井上靖即认为:“无论从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的业绩中正确汲取经验,对不明之处进行确定、补足,或加以修订,黄文弼的调查报告都是不可或缺的。……我认为这为我国的西域研究打开了一扇清新明快的大窗。”同一时间的欧洲也开始出现对黄文弼及其著作的评述,有代表性的当属德国汉学家瓦尔德施密特1959年发表《中国考古学家在新疆的调查》一文,对《吐鲁番考古记》,特别是《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相关内容进行了介绍。
在中国,“三记”更是新疆考古与西北史地研究不可或缺的案头书,滋养了无数后辈学人。甚至有许多专家学者直言他们在新疆从事考古工作时,都是背着黄文弼先生的著作在全疆各地跑,这些著作为他们提供了引路人的作用。
黄文弼哲嗣黄烈先生曾说:“黄先生经过大范围的考察,写出了系列的考古报告。由于他具有深厚的中国学问基础,结合实地考察所写出的几部巨著,其学术价值为其他单纯考察家所写报告难以企及。当然,当时的考察手段与技术远非今日所能比,其论断也受历史的局限,不一定尽皆妥当,但大部分内容至今仍不失其光辉。他的考察距今已有三分之二世纪,当时的遗址、遗物历经沧桑之变,有的已不复存在,有的已大为改观,他的记录作为手资料就显得分外珍贵。”这实际上已经道出了“三记”的学术里程碑价值:
首先,“三记”代表了中国学者在新疆自主的科学化考古之后,对该地区进行的全面系统的研究,不仅在学术价值上具有领先意义,更打破了长久以来中国学者在新疆考古与研究领域追随国际学界惯例的落后状态。例如黄文弼在土垠遗址采集到70余枚木简,是新疆所获汉通西域后早一批文字记录。从这些木简的内容,能够看出汉代在西域的职官设置、驿传制度、屯戍仓储、往来交通等情况,打开了人们了解汉代西域经营的新窗口。
其次,“三记”中所刊布的丰富多彩的考古资料,包括文书写本、钱币、碑刻拓片、壁画和各类文物,其中很多实物今天已经不存,赖有“三记”才得以保存。这些一手资料的公布,改变了以往中国学者研究资料靠国外“恩赐”的局面,也给国际学界注入了新鲜血液。特别是黄文弼所获文书,包括汉语、梵语、龟兹语、粟特语、婆罗谜字母、中古伊朗语等各个语种,许多都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时至今日,依然是世界各国研究者们的关注点与学术增长点。
后,“三记”熔铸了黄文弼的考古经验,发挥了实地考察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特点与优势,充分展示出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等多学科融汇的特点,是黄文弼学术研究“三重证据法”的直接体现,为今天的新疆考古事业及西北史地研究树立了方法论的标杆。
囿于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三记”中难免存在一些错误。例如日译本《黄文弼文集》出版时,榎一雄就针对《罗布淖尔考古记》指出,其中对楼兰人与印度拜火教徒的关系的推测有所不确。今人庆昭蓉也考证出《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四件龟兹语文书出土地的记载系黄文弼先生误记。今天,罗布淖尔、吐鲁番、塔里木盆地的考古与研究工作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三记”的筚路蓝缕之功,永远不会磨灭,其价值也必将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在新疆考古、丝路研究的殿堂中发挥出永恒的光热。
四
如前所述,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三部著作相继问世,一时洛阳纸贵,很快就供不应求。1984年宫川寅雄发愿翻译《黄文弼著作集》而驰书夏鼐先生索要“三记”时,作为黄文弼同事的夏鼐也无法购得此书,只好将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中的藏书寄赠。除了1968年日本早期的影印版,日人榎一雄提及1988年香港无名书店也曾出版《罗布淖尔考古记》影印版,但纸张、质量均欠佳,如今早已绝版。2009 年,线装书局将“三记两集”策划为《中国早期考古调查报告》第二辑,按照初版原书影印出版,但是影印本数量偏少,市面仍寻觅不易。为了满足国内外读者的需求,也为了弘扬、传承优秀历史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整理出版了《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
此次“三记”的整理再版工作,分别以《罗布淖尔考古记》(1948年版)、《吐鲁番考古记》(1957年版)、《塔里木盆地考古记》(1958年版)为底本,用规范简体字进行录排,并对图片进行现代技术处理,进一步提高了图片的精美度。为保证著作原貌,除就现行出版规范做出个别校订外,其余均一仍其旧。
“三记”的整理再版工作,得到了黄文弼先生后人黄纪苏先生等的大力支持。北京大学朱玉麒教授对整理再版工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后,受出版社委托,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朱玉麒教授领衔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9ZDA215)课题组团队与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对再版工作给予了学术指导和支持。具体参加人员为: 北京大学朱玉麒教授与博士生徐维焱、陈耕、袁勇; 新疆师范大学教师吴华峰、刘长星、潘丽、徐玉娟。朱玉麒、吴华峰共同制定校勘原则,此后两校同时展开校勘工作,其中,徐维焱、刘长星负责校勘《罗布淖尔考古记》,陈耕、潘丽负责校勘《吐鲁番考古记》,袁勇、徐玉娟负责校勘《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吴华峰负责统稿和审订,并编制《地名索引》。
谨以“三记”的重版,纪念黄文弼先生诞辰130周年。
吴华峰
2023 年1 月
第二章湖畔古冢
一、Lㄋ古冢
当余之赴罗布考察也,意在南行访楼兰故墟,阻于水,不得达。而余之助手早舍弃其渡河计划,转从事于探古之工作矣。在四月十五日之暮,小侯拾一美丽之蓝黄色残衿归。称距此西北约六七里土阜上有一古冢。试掘之,出女人头骨,髻发尚存,额前乱纸覆之,旁陈残绢帛及毛绳麻布之类,似为死者头部之饰物也。余于十七日复偕小侯往视其遗址,抵土阜旁,阜高百余英尺,宽约相当,长三百余英尺。阜中倾陷若沟渠,宽十英尺许,深亦十英尺许,长百余英尺。死者即藏于此倾陷处,覆以芦苇,以未经修凿之木料支持之。土阜上层为黄土,厚六七英尺,或十余英尺,下为干沙,凝结坚固死者即埋藏于沙土层内,衣衿骨络,几与干沙胶结为一。掘现木把杯二,在头部旁(图版一七,图8、9)。又有羊骨二枚,以木板承之,木板形如芭蕉叶,说者谓蒙古风俗如此,然不必仅蒙古人始然也。死者衣服,均为丝织,约有五袭,衫、襌、纱、纩均备。袖口宽尺许,指骨外露。其颜色有谷黄及紫绛等色,惜迎风而碎,未能取出以飨读者为憾耳。又死者右手第四指,戴有戒指一,以薄铅为质,上刻环圈五,状类梅花(图版一〇,图56)。衣衿中,藏铁刀一,柄已碎断。综合观察,极类似一贵妇人之墓,惜无文字以为佐证耳。又左侧亦有古冢一,掘现木把杯及几各一件,形式略同于前。在此阜南半里许戈壁上,有木橛一行,环栽土中,复露出地面尺许,说者亦指此为古时冢墓之故居也。在其西南约七八里许。枯胡桐林中,时露古时陶片,则为当时居民居住之所,而埋其死者于山边耳。(参考《次考察路线图Lㄋ》)
二、L匚古冢
在余等方工作Lㄋ古坟时,余之毛拉等则四出探寻古迹。据称:在东约十余里许,有古房及古冢遗址,乃决计东征。当日晚大风,次日仍未息,尘沙弥漫,白昼昏黑,石子飞扬如雨,不能张目。故决定休息一日。据余之猎户云,此地多大风,风多作西南向,每五日或十日必有一次。据此,是沙磧之迁移与海水之变迁,与风沙不无因果关系也。四月二十日,虽风力稍杀,而酷冷如严冬。吾人均衣老羊皮袍,犹不足以保温暖,沙漠天气转换之剧烈如此。余等于上午七时出发,向东北行,遵来时旧道。九点转东行,时有溢水。十一点东行微偏南,抵河岸。河宽约百余步,两岸枯胡桐横陈。沿河而进,溢水载道,时阻予之行程。十二点转东偏北行,抵古房遗址。在一大土阜上,顶颇平整,长约五六十步,宽约二三十步不等,遗址即在土阜之洼陷处。叠咸块为墙,芦苇覆之,方径丈许,有房十余间,羊粪骨角,散布地表。检亦无他物。余等即驻于其南傍水之平滩上,并在其附近作古物之探寻也。(附图一一)
在余住处西北有一土阜,前后宽广,中腰颇狭,形间葫芦。阜上坦平,面覆枯胡桐树六株,即为古坟井口所在。循迹发掘,深四尺许,发现尸骨四具,重叠而葬,衣服已腐朽矣。头部有漆木桶状杯,及木把杯(图版一三,图3;图版一七,图10),圆底木俎(图版一六,图1、2)之类。又有残块铜镜(图版八,图7)及耳饰等,由铜镜之边缘,可决定其为汉物无疑也。是此冢亦为两千年前后之遗址矣。又在土阜附近,拾铜三棱镞,及石矢镞之类,及土阜上红陶片内含灰陶,想与此墓中人之时代相距或不甚远。但四尸骨重叠于一穴为可异耳。(参考《次考察路线图L匚》)
三、L万古冢
在余住处之南约里许,四周积水,有风化层之土阜一座,屹立中洲,上栽立木杆为标帜(附图一二)。发掘其下,有石柱作长方形,长约三尺许,直立穴中,或用以支持土块为墓室之架梁者。尸骨均已搅乱。同时墓中发现草篓一具(图版二六,图L),以藤为经,再以劲草编织之。两旁有耳,系绳之痕犹存。圆底豁口,形状椭圆。疑为死者生时盛食物之具,死后即以此殉葬焉。又有漆木桶状把杯一件(图版三,图2),外涂朱漆,但彩色已毁,形式与L匚冢中把杯相同。又有骨器六件(图版二八,图1—6),均作锥形。图1—4各器,一端尖锐,疑为古人搔发之簪。图6一端作柄状,用意不明,然以3、4两图言之,疑为女人头上饰物。疑冢中死者,或为一女人也。又有玉、石、骨等件(图版三〇)与之同时出土。其中有玉耳饰二枚(同版,图1、2),作椭圆形,中空。又有方形者,有圆粒形者,有薄叶状者,无疑的皆为耳上之饰物。又骨粒一串,形同冠缨(同版,图20)。又一长方石块(同版,图27),三面磨制甚光,一面为天然石状,底凿一横槽,用意不明。但亦疑为本地人装饰之具也。(参考《图说》第十章《杂类》)
四、Lㄇ古冢
当余之工作Lㄋ古冢也。余之助手毛拉告余云:在此地之西土阜上有一古冢,尸骨尚未腐化,采归草篓二枚为证,余甚异之。及余移驻于L万也,急使导余往观。累越高仰层之土阜,至一三面有水之三角洲。其高阜,四周风化,显露其泥层绉折之迹。在沙土岩处,有木桩一(附图一三),犹以为偶置之也。审视其沙土倾陷处,露毛织品之一角。余乃大异,去其沙土,即露以木钉锋合之木板,形如扁叶,以黑牛皮覆之。木板刨制甚光,显为长久工作水中者。长五尺,宽三尺许,缺处另以木片补之,疑为死者之舟。旁树立之木杆,盖为拨船之具也;一端颇尖,形类今之撑篙,死后其亲族即以其具殉焉。次揭去木板,即显露以毛织物包裹之腊尸。头戴毡帽,高十英寸,上形尖锐,帽系骨粒帽缨六七股,垂络唇颚。毡帽内,尚有红毛索编成之里帽,冠戴不正。头发截断,下披两肩。额部及两眉间,有红绿色所绘之横纹三道,极类本地女人之画眉。两耳穿孔,尚有毛索遗痕,以备系耳珠之用。两眼微陷,两颧耸起,鼻陷而唇斜,似负痛苦以死,而表现忧戚之容者。在其头部,有草篓二个,一外涂朱漆,死时即以此殉葬焉(图版二六、图2、3)。次除去其包裹之毛织品,即呈露其身体,经盐硝之浸炙,皮肉坚结,尚保存其原形,毫未腐化。两手下垂,下围以棕黑色毛线织成之长带,带绥下垂至足,足履皮靴,毛里而皮外。身作绛色,骨骼坚结为僵质,击之作木声,直立转侧皆可如意。头长二五厘米,额宽一〇厘米,面宽一一厘米,下腮突出,显现尖削之状,通高一六。厘米(附图一四)。据医学家言,凡腊尸皆由盐水之浸炙,积久遂成腊形,永久不坏。然非有两千年之浸炙,不能成功也。据其所述,参合此处有水之时代,及同时发现之遗物,当亦在两千年前后。盖以后海水南徙,当无此腊尸之造成。头部之草篓与L万冢中之草篓形式质料相同,当为同一时代之产物。而L万同时发现之骨器、漆、木器,余已订为两千年前后之故物,彼此互证,则此腊尸有两千年历史之说益可信也。
其次言及死者种型问题。余对于人种学,毫无研究。且亦未加科学测量。但以由死者埋葬之方式及其殉葬物品,推测死者确为本地人,与汉通西域时之楼兰国人,或为一致。盖其所表现,完全为游牧人及渔猎人之生活,与中原人久孕育于东方文明者,决然不同。故吾人在编第四章中,已略有论述。但为引起读者兴趣起见,再补述末意,以备参考。斯坦因氏在L.F.4古冢中,发现死者头畔衣襟中,系二小口袋,中盛小麦粒,及其他细枝。纳恩德博士(Dr.A.B.Rendle)认此细枝为在西藏至波斯一带繁殖的胡麻,据伯格曼君称印度跋希人(Parsees)现仍用麻黄细枝代替能产生浩玛或所玛(Haomaorsoma)之某种植物。(所谓浩玛或所玛,在古印度、伊兰人祭祀中,曾占重要地位。)余在L匚古冢中,发现纻麻质口袋一,亦有同样盛物,但当时不注意,遂致遗失。在此地僵尸中则未之见也。但以麻黄细枝为殉葬品,确可代表此一带一部分墓葬之习俗。换言之,即为本地人墓葬之习俗。若然,则楼兰人,或即与印度跋希人,有密切之关系也。至此,余当另引中国记载所述一事,以助研究之兴趣。按斯坦因氏所述之跋希,与中国记载所述之白题西音相近似。杜氏《通典?西戎传》云:“且末国,汉时通焉。北接尉犁丁零。东与白题西接波斯精绝,南至小宛可三日行。地有葡萄诸果。人皆剪发。着毡帽。小袖衣。为衫,则开颈而缝前。”按《通典》所述与《梁书?末国传》字句微异。如云:“末国北与丁零,东与白题,西与波斯接。……”按此处均有脱误。其云“东与白题,西接波斯、精绝”义意不可通。波斯在葱岭西,如何可接。故此处当云:“东与白题西接,西接精绝。”波斯疑为白题西之小注,表明其为波斯人。后人遂将小注录为正文,而又删去“西接”二字,义意遂不明了。《太平寰宇记》,引作“东接白题,西接波斯精绝”,错落同上。盖波斯仍当为白题西下之小注也。使余之解释不误,则且末东为白题西人,即波斯种人所占据也。又据中国史书所记,且末在三国时,已为都善所并。故《通典》所云且末人,亦当即汉时之都善人。所述之且末人之习俗,亦当即都善国人之习俗。剪发着毡帽,小袖衣,开颈而缝前,且末人既如此,则汉时都善国人亦当如此。由余等所发现僵尸之形态,即其剪发戴毡帽事,更可证明其然也。彼此互证,则汉时楼兰人种型不难推知,或即属于印度伊兰人种型也。现昆仑山中,有操伊兰语之噶尔喀族人(Galca),或为其遗种欤。
以上皆为余次所考察湖畔古冢之经过也。第二次之赴罗布淖尔考察也,适值战乱,且准备未充实,不能尽量考察。但亦略有所见,兹略述如次。
当余等于五月初间,由鲁戈斯特南抵孔雀河畔也,由余一驼病足,放置于此。即率其余驼东行,沿一干河岔,枯桐红柳,迤逦如带,时有土阜间之,阻余行程。傍晚驻一咸滩中,一面派毛拉赴辛吉尔购办米面,余等则作古坟之探查。在余等驻地旁有一风蚀土阜,上竖枯胡桐三株,作交叉状。以余等次探查之经验,凡类此者上必有古人墓室,即攀登察看:上颇平坦,作椭圆形,有井穴二,南北对峙,穴口有枯胡桐六株,长丈许,骈比横陈,二穴相同。余等掘其南穴,深至三尺许,发现见棺一,作长方形,四围板壁已遗失,仅存底部。冢中土层搅乱殊甚,出木几二,已腐朽倒置其中,又几足四,作屈腿状,显系早为他人盗掘,而留其遗弃物于冢中。故余亦不欲尽取之。八日转东行,在戈壁上见一地室,屋架犹存,以枯胡桐作檩条,覆以芦苇,涂以泥浆。据本地人称述,在室中曾发现古棺木数具,现已无存。复东行戈壁上,时见以木桩栽立之椭圆形建筑,数冢相连,组合为群,据猎户云,此亦为死者之居室。其栽立之木桩,长二尺许,一端尖锐,入土不深。因余忙于行路,未加工作,殊可惜耳。
五、Lㄖ古冢
当余等于古烽燧亭工作完后,五月十四日复返西行,路遇毛拉于途,并携米面而归。庆幸之余,复谈及往西约十余里土阜上,有一古冢,衣巾外露,乃使导之前往。试作发掘,出小头骨一,黄发尚存,作黄金色,审视为七八岁之姣童,所谓黄发小儿是也。冢中绸绢衣巾,尚未腐朽,有枕头一,四方形,头枕之迹犹存。手帕一,亦为长方块,一端具带,疑为缀系于衣巾之用。袖口缥骧,均崭然如新。一袖口黄绢为底,绿绸为边缘。图版(二一、二二)虽属小儿,亦副戴满身文明,供吾人之鉴赏,与裸体葬者,有文野之别矣。(参考《第二次考查路线图Lㄖ》)
综上一二两次所获,由其埋葬方武,及装殓物,显有两种不同之现象:前者为赤身葬,后者为衣冠葬。在汉通西域以前,楼兰人民之生活如何,吾人在《汉书?西域传》中不难窥其一二。《西域传》云:“都善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民随畜牧遂水草,有驴马,多橐驼,能作兵,与婼羌同俗。”又云:“自且末以西,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能作兵,略与汉同。”是楼兰本为行国,不事耕作,至为显然。及楼兰迁都伊循,改国号为都善,汉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屯田伊循以镇抚之,楼兰至是始有田作。然皆在汉通西域以后,田作者亦多为汉人,非本地人也。据此,楼兰文化,可分两阶段,即汉末通西域,在纪元前一世纪以前,为前期,完全为本地土著文化;自一世纪以后为后期,盖受东方文化之影响,渐变其习俗也。前在《石器遗址》章中,已由石器部分略有阐述。今据湖滨古冢,其情形亦大抵相同。由余之Lㄇ冢言之,露体埋葬,断发文面,革履、裹毡,皆非东方之习俗。而东方文明,以丝绸为大宗。凡在西域之被汉化者,莫不锦绣珠玉。而此冢除毛革二种外,不着衣裳,十足表现为畜牧,或渔猎生活状况。其殉葬物品,除草篓外,再无他物。而此物质料,又大概为本地所出,亦显未受东方文明之影响也。惜余所工作只此一冢,而斯坦因在楼兰附近,柏格孟在阿德克一带,所工作之古冢,其情形与此近似者甚多。阿德克之D1冢,与余Lㄇ尤为接近。然其殉葬之物品,不出毛织、皮革、树枝、木条之类,与余所拾大致相同。而余Lㄇ冢中不见树枝,毡帽上不盘红索,及饰鼬鼠皮,较为稍异耳。但此为繁简之别,而于人民生活状况初无有异也。又其埋葬仪式,露体裹毡,凿木为棺,覆以牛皮,冢后树一木杆,则所有古冢皆同。此与较进化之埋葬法,已大异矣,此可注意者也。其次说到后者,柏格孟在阿德克另一区域,发现三座小坟地,在EI冢中发现之僵尸,为一年高有德之绅士,白须面窄,确为典型长头种人。衣黄绢外衣,边缘镶以红绸。CI冢中为一妇女骨骸,衣绸外衣,镶棕、红、绿三色边缘,袖长过手,袖绣各色条纹。并副带铁镜一,覆以红绸。又有皮质及丝织小口袋。又铁剪一把,挂在腰际。颈上再挂有白色骨质佩饰一串。复次,再北行,将近库鲁克河南岸又发现A冢,内尚保存颇完整的黄绢外衣,缘领露胸,系结于内,袖长而小,还有毡袜、高靴、皮裤之类。凡此诸冢,虽各个微有差异,但有一共相,即均用丝织物装殓,全幅带着东方文明,则此类古冢,必在汉通西域以后,无可疑也。至是否为汉人,则有待于人种学之研究矣。又此项小坟群,均在库鲁克河以南,及渐近于库鲁克河一带,与余发现之文明冢,相距虽有数十里之遥,但均在库鲁克河流域也。例如余之Lㄋ、L匚、L万,其埋葬方式,与柏格孟E、C等冢大致相同,即同具衣冠葬者。不过余冢中所发现之殉葬物品,较为丰富,而表现文明,更为明确耳。尤其L万、L匚之铜镜碎片,及漆木把杯与簪栉之类,与Lㄇ之殉葬物品,确为两个不同的来源。无疑的,一为土著,一已接受外来文明,生活遂有优劣之别耳。但余所发现之冢,均在库鲁克河北岸,正当汉通西域路线孔道。援鱼豢《魏略》所述,西汉通西域路线中道经居卢仓,西北行,过龙堆,到故楼兰,即余所发现之古烽燧亭遗址地。再西行,沿库鲁克河,直诣龟兹,此为径道。而余所检查之文明冢,完全在大道两旁,其受汉文明影响,毫无可疑。虽Lㄇ亦在大道附近,犹留着本地土著之风尚,然余所发现仅此一冢,且亦不如阿德克古坟中之纯土著化。由此吾人所述汉通西域后,本地人已远徙,或渐被同化。因此一带已被汉人视为军事政治之重要区域,其柔土处或为屯田之地带,本地游牧生活已无可用其力也。反之阿德克在库鲁克河南约七十余里,不当西行孔道。故本地土著人民,尚仍然保存其旧生活,游牧渔猎。如现今之罗布里克人,在生活上甚少改变,可为证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