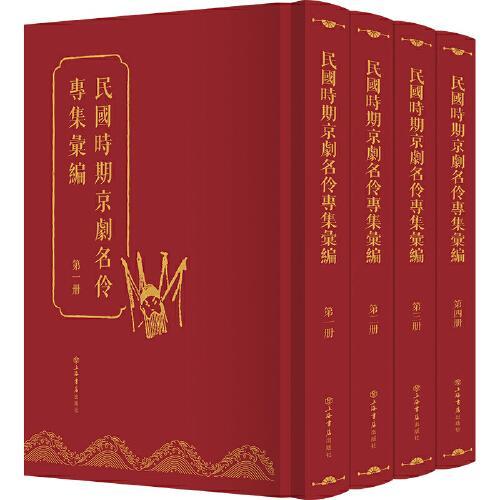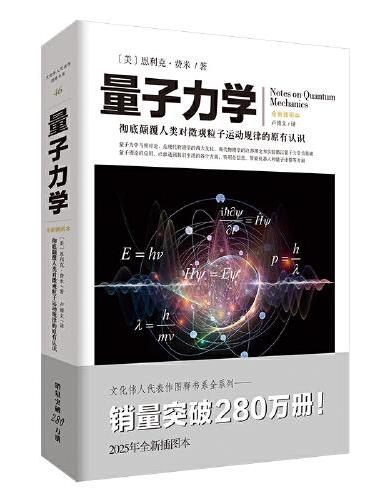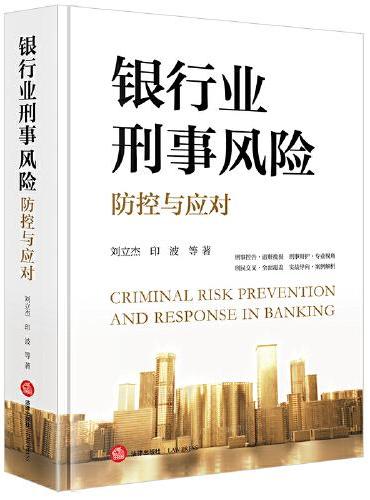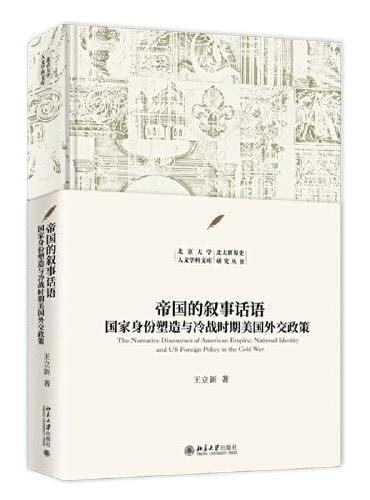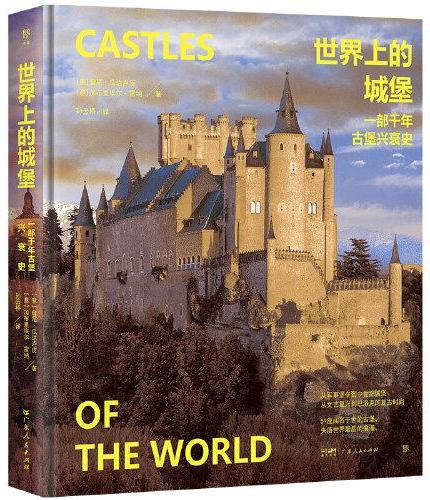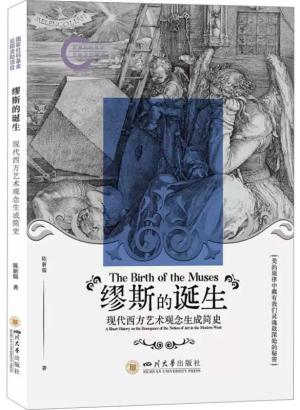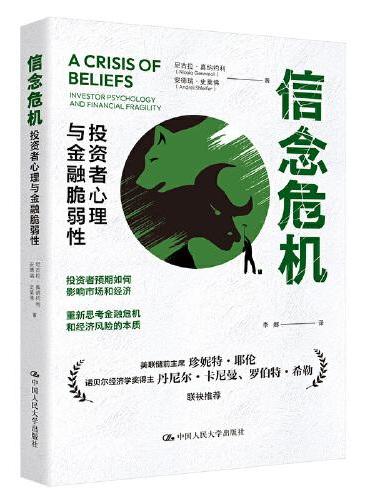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民国时期京剧名伶专集汇编(全4册)
》 售價:NT$
20298.0
《
量子力学 恩利克·费米
》 售價:NT$
245.0
《
银行业刑事风险防控与应对
》 售價:NT$
449.0
《
语言、使用与认知
》 售價:NT$
321.0
《
帝国的叙事话语:国家身份塑造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 北京大学人文学科文库
》 售價:NT$
704.0
《
世界上的城堡:一部千年古堡兴衰史(从军事建筑到中世纪城堡,59座经典古堡,高清全彩图文,精装收藏品质)
》 售價:NT$
1214.0
《
缪斯的诞生 现代西方艺术观念生成简史
》 售價:NT$
398.0
《
信念危机:投资者心理与金融脆弱性
》 售價:NT$
347.0
編輯推薦:
《四万万顾客》作者卡尔·克劳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 “爱伦·坡”奖得主、《午夜北平》作者保罗·法兰奇追溯前辈生平、还原老上海风貌。 这是卡尔·克劳的人生故事,是上海城市兴衰与个体生命的交织过往,也是关于上海乃至整个中国在动荡年代的历史书写。 人生起落与上海城市兴衰,时代洪流滚滚而过,从一无所有到扬名立万,从踌躇满志到仓皇逃离……“老中国通”如何应对? 跨越世纪的时间之旅,从个人记忆中打捞生动细节,生动还原真实的“老上海”生活。 本书基于丰富的史料,生动再现了卡尔·克劳动荡起伏的一生,以及他与上海城市命运的紧密联系,透过一个西方人的视角,反映了上海近现代史的一个侧面。
內容簡介:
卡尔·克劳于1911年来到上海,在上海居住生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在上海,他当过记者、开过报社,并创立了自己的广告公司。此外,他还担任过人质谈判员、临时警官、乡绅农民、美国政府中介和宣传员。他在上海发展自己的事业,也见证了上海命运的变化。克劳初到时,上海还只是一座沉闷的殖民城市,而到1930年代,这里已经是一派繁荣、充满商业气息的大都市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克劳写下了自己的开创性著作《四万万顾客》,介绍充满活力的中国市场,鼓励国外企业进入中国。
關於作者:
保罗·法兰奇(Paul French)
目錄
货币说明/ 1
內容試閱
中文版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