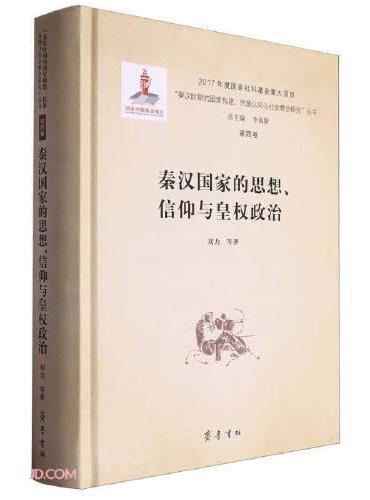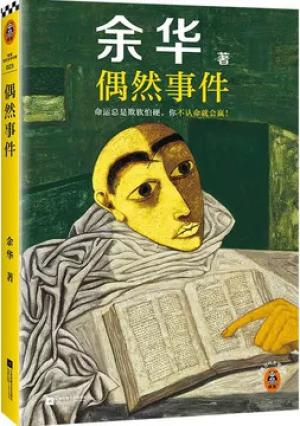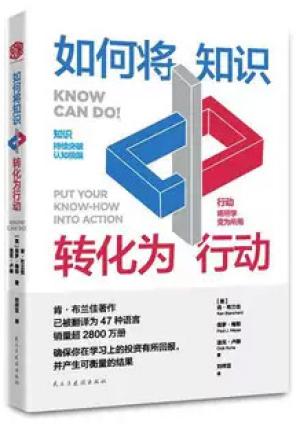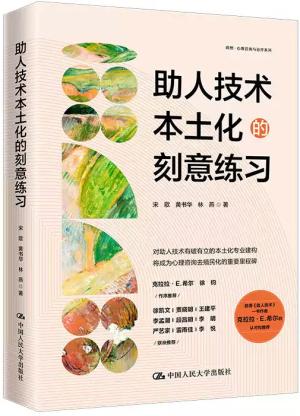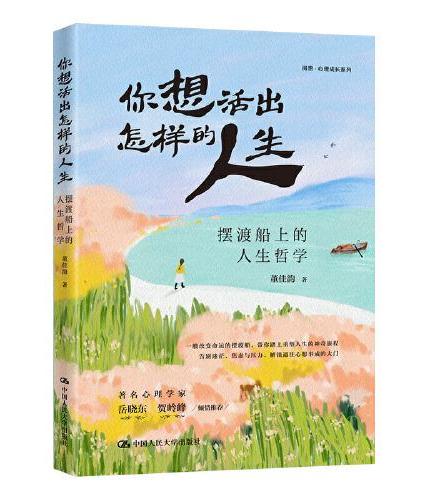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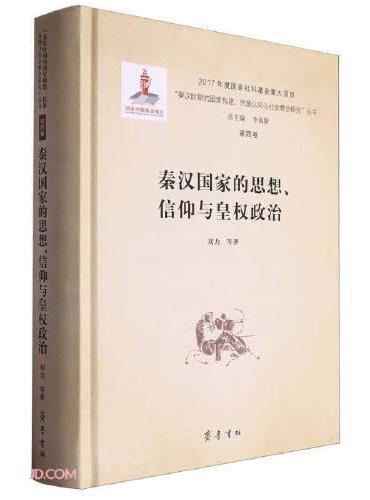
《
秦汉国家的思想、信仰与皇权政治
》
售價:NT$
1000.0

《
反卷社会:打破优绩主义神话(一本直面焦虑与困境的生活哲学书!)
》
售價:NT$
38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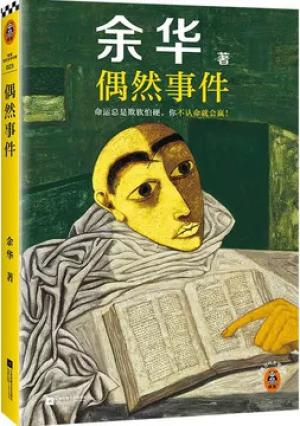
《
偶然事件(命运总是欺软怕硬,你不认命就会赢!)
》
售價:NT$
255.0

《
余下只有噪音:聆听20世纪(2025)
》
售價:NT$
95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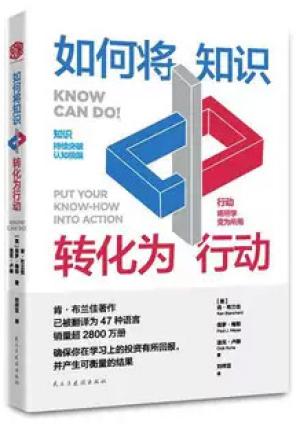
《
如何将知识转化为行动
》
售價:NT$
35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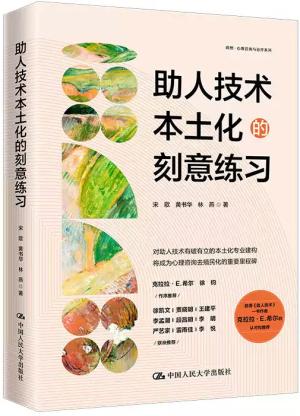
《
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
》
售價:NT$
408.0

《
中国城市科创金融指数·2024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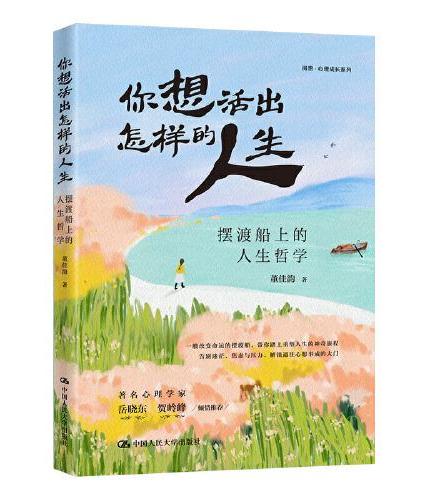
《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摆渡船上的人生哲学
》
售價:NT$
306.0
|
| 內容簡介: |
“我们必须改头换面,发展新的思想,尝试着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人。”
《大地上受苦的人》出版于1961年11月,是反殖民斗士弗朗兹·法农病榻上的绝唱。这本书的出版,与他的本书《黑皮肤,白面具》相隔了九年,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民族解放事业如火如荼,从殖民地独立的国家越来越多。法农个人的变化也很大,他直接参加了民族解放事业,因此本书也可以看作一部政论类的著作,主要讨论在民族独立后的“去殖民”问题,为全方位的独立指明未来努力的方向。
本书论及五个方面:殖民地的暴力问题、民族解放的自发性问题、民族意识、民族文化以及殖民战争中的心理失调问题。通过一个个实例和层层论证,作者作出结论,前殖民地人民应该重塑新的人格和文化,通过创新和发现,寻求人类的进步,回应自己人民的期待。法农在本书中展现了一位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才能和远见,半个多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人在去殖民化的进程中从这本书获得启发,引为参照,直至今天,书中讨论的主题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
| 關於作者: |
|
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1925-1961),精神病理学家、政治思想家和哲学家,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先驱,也是第三世界论述的缔造者之一。1925年出生于法属殖民地马提尼克岛法兰西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自愿入伍参战,战争结束后,他进入里昂大学攻读精神医学。1952年,他出版了震惊世界的《黑皮肤,白面具》。1953年,他到阿尔及利亚行医,广泛接触当地底层民众,次年参加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事业,1959年出版《阿尔及利亚革命第五年》。1961年,他饱受病魔的折磨,仍在病榻上奋力写出了至今仍极具影响力的《大地上受苦的人》。法农去世后,按他生前的遗愿,安葬于阿尔及利亚。
|
| 目錄:
|
永远追问的人(艾莉丝· 谢尔基)
灼热之声(让-保尔· 萨特)
章 论暴力
第二章 自发性的伟大和弱点
第三章 民族意识之厄运
第四章 论民族文化
第五章 殖民战争和心理失调
结 论
|
| 內容試閱:
|
永远追问的人
(二〇〇二年)
精神科医师、《黑色呐喊:法农肖像》作者
艾莉丝·谢尔基(Alice Cherki)
《大地上受苦的人》一书于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月底,由法国马斯佩罗出版社出版,当时作者弗朗兹·法农罹患白血病,正在美国华盛顿附近的贝塞斯达医院与死神奋战。为了避免一出版便被查封,这本书是在半隐秘的状态下很艰辛印刷出来的,但还是一发行便以“有害国家内部安全”的主要罪状遭到查禁。
这种情形早已发生在法农的上一本书《阿尔及利亚革命第五年》(一九五九年同样由马斯佩罗出版),其他一些有关阿尔及利亚战争的书籍亦同(比如:莫里斯·马辛诺的《拒绝》、亨利·阿莱格的《问题》)。这种查禁在当时是屡见不鲜的。
然而,这本书仍开始流通,并且在媒体上引起极大的反响。经过一番非常繁琐的运送过程(甚至绕道土耳其),法农终于在十二月三日收到一本样书,另有一些剪报,其中包括一篇让·达尼埃尔(Jean Daniel)写的长篇论述,发表于十一月三十日的《快报》,可以算是一篇褒扬的评论。法农让人把这篇文章念出来给他听之后,说道:“没错,但这也不能唤回我的骨髓。”几天后法农便与世长辞,日期是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八日。当时他三十六岁。
精神医学与政治之路
法农于一九二五年出生于马提尼克岛的法兰西堡,来自一个富裕的小资产阶级家庭,手足众多,成长在一个老殖民世界里,还没开始对奴役的现象提出质疑。不过,法农倒是在十分年轻的时候,便参加了“第五部队”——由戴高乐主义力量整编的加勒比籍自愿军。参与这个活动的过程,培育了他的反抗意识,但也让他体验到层出不穷、无所不在的种族歧视。复员之后,他于一九四五年戴着十字勋章返回马提尼克(颁给他勋章的人就是后来的萨朗将军,他后来常说这是他和对方有过交集的东西),通过高中会考并经常与埃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往来(他十分欣赏塞泽尔,不过当时已经很不认同对方的政治观点)。彼时,塞泽尔选择把马提尼克视为属于法国的一个省份。
很快,法农来到法国,于里昂攻读医学。除了这门科目之外,他也非常热爱哲学、人类学与戏剧,并且很早就投入精神医学专业。与此同时,他虽没加入任何党派,却参与了所有反
殖民主义的运动,还编辑了《达姆达姆报》——一份属于殖民地留学生的小期刊。特别是,一九五二年他在《精神》杂志发表了篇文章《北非症候群》,探讨的是来自北非的劳工:这些人离乡背井,承受着“每天每日都死去活来”的痛苦,和自己的家乡切断了联系,与他们的终极目标相距甚远,成了一件给乒乒乓乓扔掉的东西。
他在圣亚尔邦精神病院待了十五个月,并认识一个很重要的人:托斯克尔(Fran?ois Tosquelle),原籍西班牙的精神科医师,也是一位反佛朗哥派的斗士。这对法农之所以走上精神医学这条路,以及他后来对于政治的投入,都是个关键性的过程。他在这里得以从各个层面研究精神疾病,这里是精神与肉体、历史与社会结构的交会之所。一九五三年,他通过精神科医师资格考,接着被派往阿尔及利亚的卜利达精神病院。不过早在一九五二年,在弗朗西斯·让松(Francis Jeanson)的奔走下,法农的本著作《黑皮肤,白面具》已由法国门槛出版社
出版。
在阿尔及利亚,他不仅发现自己与院方的传统精神医学格格不入,同时也不太认同阿尔及尔学派那些精神医师对于“土著的原始状态”的理论。他逐渐洞悉当时阿尔及利亚作为一个殖民地的现状,随即全力改造院里的精神科,并负责引进他与托斯克尔共同实行的“社会治疗法”。他因而不停修正医护人员与精神病患之间的关系,他不仅和欧洲人,同时也和信奉伊斯兰教的那些“土著”一同试图恢复他们的本土文化、他们的语言、他们的社会生活组织,亦即所有能够形成意识的东西。这一场小型的精神医学革命,获得了医护人员的赞同(他们绝大部分都很关心政治),同时也得到当地政治活动分子的认可。法农的名声从此远播。当时是一九五五年,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已然开打。
面对阿尔及利亚人追求独立的希求,法国社会党政府竟视若无睹,让法农感到相当不解;此后他的反殖民立场愈来愈闻名。后来“阿尔及利亚之友”的运动找上了法农:这是一个对
政治犯家属提供物质协助的人道主义协会,领导者是主张国家主义的政治活动分子,与占领卜利达附近那些基地的游击分子有所联系。他们对法农的个请求,是要他负责医疗那些饱受精神错乱之苦的游击队员。
就这样,在精神医学及政治活动的交替作用之下,法农投身于阿尔及利亚追求独立的奋战之中。一九五六年年底,在一封写给总督罗贝尔·拉科斯特(Robert Lacoste)的公开信里,他辞掉了精神科医师的职务;他在信中写道,他已经无法解救某些人,“使他们等到应有的待遇,这是一个把剥夺人权及不平等和谋杀当成合法原则的国家,当地人在自己的国家里永远都是疯子,生活在一种完全没有人格的状态下。”于是法农被赶出了阿尔及利亚。
接着,一九五七年的季,他在法国度过三个月的时光;虽然他坚信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已然势不可挡,然而旅居法国这段期间,这样的立场却没获得任何回响。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FLN)法国总会的帮助下,法农得以前往突尼斯——那里是民族解放运动境外组织设置的地点。与法国正式决裂。
法农在突尼斯同时从事精神医学及政治这两种活动。后来他成为民族解放阵线的刊物《斗士报》工作团队的一员。他从内部亲眼目睹民族解放阵线的所有矛盾之处,其中包括了政治代表和军队之间愈来愈严重的争执。尽管经常大失所望,他仍旧继续支持阿尔及利亚的解放运动,同时也是一位不断创新的精神科医师。他对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愈来愈感兴趣,并于一九五九年年底由阿尔及利亚共和国的临时政府任命为黑色非洲的巡回大使。那是非洲各国争取独立的年头。法农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巡回大使,尽心尽力从加纳赶至喀麦隆,从安哥拉赶至马里,为真正的独立而鼓吹战斗。他甚至还想出一条可行的路线,由马里出发,穿越撒哈拉沙漠去和阿尔及利亚的反抗分子会合。
然而一九六〇年十二月,法农于旅居突尼斯期间,发现自己罹患骨髓性白血病。他仅存一年的生命,并于这段时间写了《大地上受苦的人》这本书。
为受苦者所发的呐喊
这是一本由他自己选择书名的著作(而非由出版社决定)——身为医师,他很清楚自己的病,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法农与时间及死神展开一段真正的竞赛,一边还期望着要向外传递一个后的讯息。传递给谁呢?给那些不幸的人。然而这里指的,绝大部分已经不再是十九世纪末工业国家里的那些无产阶级,那些高唱着“起来,大地上受苦的人;起来,饥寒交迫的人”的无产阶级。法农想要与之对话的,那些在大地上受苦的人,是指贫穷国家里那些不幸的人,那些真正想要土地和面包的人;彼时,西方世界的劳工阶级大多有种族歧视,而且显然对海外的人民一无所知,再加上殖民地能间接带来一些利益,因此他们对这些殖民地的命运,都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冷漠。
这本书并非经济论述,亦非社会学或政治性的评论,而是就殖民地国家的现状与变化所发出的呼吁,甚至可说是呐喊。
在整本书中,法农着力研究政治、文化与个人的关系,而且很强调经济、政治及文化等层面的控制对被殖民者产生的效应。他的分析,注重的是奴役制度的后果,对象不仅包括各种民族也包括个人,同时他也强调这些人要获得解放的条件,首先在于个人的解放,亦即“人的去殖民化”。
《大地上受苦的人》是弗朗兹·法农的后一本著作。他在一九五二年,年仅二十七岁时,便写了《黑皮肤,白面具》;一九五九年写的《阿尔及利亚革命第五年》,则是马斯佩罗早期出版的书籍之一。此外他还发表了为数众多的文章:包括先前已提过的《北非症候群》,以及一些精神医学的相关文章,特别是一九五六年在次黑人作家与艺术家研讨大会发表的《种族歧视与文化》;接着是《文化与民族》,于一九五九年在罗马召开的第二次黑人作家大会上发表。在所有这些文章当中,论据的推展并非建立于理论之上,而是以实务经验作为基础;这些经验同时也是他思想发展的起始点。早在《黑皮肤,白面具》一书,关于种族主义的反思,便聚焦于某些文化片面宣告的文化统治:种族主义并非偶发事件,亦非恣意妄为,而是一种宰制的文化体系,这种体系也在殖民地运作。若是不看清统治文化所带来的压迫效应,那么对于种族主义的抗争便是徒然,因为这种压迫的触角广及社团、政治与文化,甚至也会影响个体的精神状态。
《大地上受苦的人》一书,持续对统治阶层所造成的奴役现象提出上述质疑;这个统治阶层,能同时使团体与个人在各自的变化中遭受破坏、有所转变。本书提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的现况,也提出解放的条件,除了政治文化的解放,还要加上个人的解放,政治斗争更为激进。此外,后两个章节当中,一章是探讨文化及建构国家的关系,另一章则是阐述阿尔及利亚战争所造成的心理创伤。
法农由自己的特殊经历出发,从贴身的故事写到他投身其中的过程,而这样的经验也是他不得不书写出来并传达给旁人知晓的。他的书写依循着以下的脉络:组成本书的五个章节各有不同主题,一段一段,有如诗歌里的段落,穿插严谨的分析,书写的语言,总是企图在意义之外,能促进了解,而非只是玩弄抽象观念,正如同年轻的法农提到自己的本书《黑
皮肤,白面具》时讲的那样。
有人曾经责备,也有权责备法农将不同文类及不同层次的论述混为一谈(政治、文化及心理分析),责备他援用了自己作为精神科医师的经验,将这些关于精神错乱的素材引入政治领域。有人曾经责备过他的风格,认定他的文字很激情,而且极富预言色彩。然而,矛盾的是,这正是法农的现代性所在。作为一个精神科医师,他苦难的主观性经验,使他与苦难的人直
接接触。
也有人责备他过于强调暴力。然而法农是由实地经验得知对一个个体行使暴力所造成的后果:这个个体没有出路,只会渐失人性,变成铁石心肠,或充满可怕的暴力冲动,终而付诸错误的行为。这种暴力,不应加以否定,而应该加以组织,进行解放斗争,从而超越暴力。在《种族主义与文化》一文,法农对自己的医疗行为作出如下结论:“占领者那种既扭曲又僵硬的文化,在解放之后,终于对另一个民族的文化开放(这个民族已经成为他们真正的兄弟)。这两种文化能互相对立,也能彼此相长。(……)一旦将殖民统治永远排除,决定包容不同文化的相对差异,就能找到普世共存的价值。”另外在《黑皮肤,白面具》一书,他也同样提出这种存在于黑人世界与白人世界的超越:“这两者必须脱离他们各自的祖先曾经有过的非人声音,让真正的沟通诞生。”这种超越的观点,彼时,已存在于《大地上受苦的人》一书当中。虽然后来在政治斗争中变得更为激进。
法农当时很希望萨特能为这本书写序,岂料过去这些年来,这篇精彩的序言竟比本书内文还拥有更多读者。然而,这篇序文多少扭曲了法农的关怀和语调。这篇序言主要是写给欧洲人看的,因而与书中内容并不是很协调。至于法农,他发表言论的对象,其实是除了欧洲人以外的所有人,他是在跟他们谈论未来,而在那个未来,他们终将超越“对他者的恐惧”。萨特的那篇序言尤其还夸大了法农对于暴力的分析。事实上,法农对暴力进行分析,萨特却是在为暴力辩解,法农并未将暴力当作目的,而是视它为一种无可避免的过程。萨特的文字有时充满鼓吹犯罪的口气。比方如下的句子:“读一读法农的书吧!你们就会知道,被殖民者在无能为力的时候,杀人的疯狂念头,就是他们的集体无意识。”或者还有这一句:“杀死一个欧洲人,这是一举两得的——同时清除一个压迫者与受压迫者,一个人死了,一个自由人活下来。”这其实都削减了法农那些主张的真义,因为看起来这些句子要辩解的已经不再是暴力,而是个人的谋杀行为。它所辩解的已经是那种犯罪的行为,而不再是人人天生都有的暴力——这种暴力唤起了人类自身内在可能存有的个性。法农当初阅读萨特这篇序文时,并未做出任何评论,甚至还一反常态,保持极度的沉默。不过,他倒是给出版社写了封信,希望将来时机成熟,能有机会说明自己的看法。
为受压迫的人而战
《大地上受苦的人》被视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指标性书籍,内容主要在探讨第三世界主义,然而政治议题掩盖了他对受压迫者之所以精神错乱所提出的强烈质疑,这本书随即遭人遗忘,法农的全部作品也都被视为不合时宜。他的政治胆识关注的是一个已过去的去殖民化时代,因此也被视为陈腐过时,而他本身的期待也迫于现实而无法实现。那么对于争取解放的那一大群农民,法农是否高估了他们的力量?我们可以发现,在当时阿尔及利亚争取独立的政治现状中,大部分参与奋战的斗士皆为农民。别忘了法农所写的是一个特定的历史经验。况且,在他看来,农民的活动力也能与革命的作用互相辉映,正如同他在本书第二章《自发性的伟大与弱点》解释的那样。
那么他是否低估了宗教的力量?事实上,他所参与的阿尔及利亚解放运动,呈现出来的并不是一种穆斯林的革命,反倒结合了各种不同潮流——一九五六年的苏马姆河(Soummam)大会纲领,虽然发起人立场不同,但没有特别强调宗教定于一尊,反而主张应该尊重多样化的意见。法农曾呼吁那些正在进行去殖民化的国家革新,并要他们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人,然而非洲国家后来的演变,不正否决了这样的呼吁?此后在地缘政治上的发展,不正好与他的期待背道而驰?事实上,这样的发展,倒是证明了他所提出的那些警告并非凭空无据(请见第三章《民族意识之厄运》)。
法农分析的是一件偶发的事实,因此我们若是只把他的作品局限在当时的时代背景,没有将之视为对于一切可能变革的呼吁,那么他的著作就很容易被评为与时代脱节。难道由于他的期待并未实现,我们便认定他针对现实所提出的那些论点谬误百出?我们都很明白,这个现实(其中也包括暴力)在今日,已经不再是“殖民压迫”或“第三世界的未来”,而是“愈来愈严重的不平等”“南北之间愈来愈大的差异”“被边缘化”“把人类物化”。
去殖民化运动及阿尔及利亚战争经过四十年后,在一个朝着全球化经济的“强权”迈进的世界里,这个事实不断出现在南/北的关系之中:浮上台面的那种有计划的腐败,乃由非洲国家的政府一手安排,并由发达世界的那些大型石油企业、医药企业及其他大公司一手促成。与此同时,对一切有害于民主解放运动、有害于人民主动参与政事的行为,这个已开发世界却以不主动干涉作为借口(尤其是以维持经济帝国主义作为借口),表现出无动于衷的态度,而那些民主解放运动及人民主动参与政事的行为,正是法农所鼓吹的,并使他从一个关心时事的精神科医师,变身为政治活动分子,为那些受压迫的人民而战。
然而这件事实并不仅仅与那些所谓的“发展中国家”有所关联。它同时也攸关所谓“发达世界”里愈来愈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在这个发达世界,不幸的人必然生活不稳定或失业,他们的位置没有任何前景——被排斥、被边缘化。法农严词批判这种现象,因为他不希望对每个人而言,生活都像“死到临头”一样,每天每日苟延残喘,使得生命看起来“并非朝气蓬勃或方兴未艾,而是不断和无所不在的死神奋战”。法农希望每一个人在他的历史中都是主角,在政治上都是主动的参与者。
跨时代的思想论述
从卢旺达到波斯尼亚,从阿富汗到中东,连美洲与欧洲也不例外,处处都是分裂的世界,战火绵延,血流成河,暴力事件层出不穷,那些国家对于它们所挑起的一切感到既震惊又愤懑,而那些人民的暴力也导致一种没有人性的恶性循环,使二十一世纪那些时代的思想、生活与未来都为之崩解,无论就个人或集体的层面来看都一样。
现在还是有人在讨论阿尔及利亚战争;曾经有三十五年的时间大家都把它称为“事件”,如今终于为它正名了。大家又重新描述了那件事实,揭发那场酷刑。然而许多时事评论,对于当时敌对的那两个阵营的暴行,各打五十板,却忌谈两方的“不对称武力”。对于当时那两个彼此隔绝、拒绝沟通的世界,法农曾经针对它们的武力关系作出分析,而那种武力关系,在当今世上的许多地区,不是也依然存在?当那些发达的社会与国家,发现自己的领土竟惨遭暴力威胁而感到震惊之际,他们心中的愤懑难道不会取代原有的理性?试想:当两个世界之间无法缔结任何条约,当通过对话而进行调停的空间关上大门,当实力较强的那个世界自诩为另一个世界的主人时,会有什么结果?这可预见的前景,使法农忧心,并促使他撰写《大地上受苦的人》,正是对于这个世界的先见之明。
法农也见到战争(其中也包括民族解放)所带来的创伤性后果,造成无止境的后遗症,招来不断重演的暴力及种族和身份认同的倒退。而这些倒退,贯穿二十世纪的历史,并以一个既新颖又十分老旧的想法作为基础,进入新世纪:将他人视为邪恶的化身,并自诩为善良的体现。这些景象,法农在《大地上受苦的人》一书分析殖民地的形势时,便早已描述过:对殖民者而言,被殖民者就是邪恶的化身。除此之外,他还指出这种形势在主观层面所造成的毁灭性效应:被指为邪恶的那一方,由于在他人的眼光下动弹不得,首先会感到极度羞愧,接着就会变成仇恨。这个过程与今日情况,出奇地相似。
因此,阅读《大地上受苦的人》时,要先超越作者撰写这本书时在历史背景所受的限制,而且要根据我们的时代特性来解读。这本书究竟为我们带来什么启示?我们看到无论在南半球或北半球,因时代发展而受到遗弃的人愈来愈多,而且面对全球化的趋势,被这个时代特性认定为“一无所有”的人,所受的屈辱及自卑也屡见不鲜:他们没有祖国,没有国土,而且也没有家,没有工作,没有身份,更没有表达意见的权利。
所以阅读或重读《大地上受苦的人》一书,有助于了解这种对人的剥削会有什么后果:暴力、种族与身份认同的倒退。
然而除了书中强调的这些主题之外,法农的思想还有以下的时代性:当大家一方面否定对精神疾病与权力关系做唯物论式分析,另一方面,也否定存在主义或文化主义观点(或从心理分析角度,将之视为一种与周遭环境完全隔离的主观探险),法农却很有远见地试图建立起一个新的知识体系,将身体、语言及“他人”经验,视为建构未来政治所不可或缺的主观经验。这种方式,其实与马尔库塞学派的方法相去不远,或者更深入来说,与维也纳那些政治精神分析学家的研究课题也所差不远——后者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被迫逃亡至美国,饱受排挤与压迫。
因此,法农之所以能表现出一种伟大的时代性,并非偶然。借由自己的出身及经历,他见证发生于上个世纪的那些事件(他本身就是那些事件的主角之一),对抗那个时代不断出现的创痛。
若从法农的生活及思想活动来看,他也是极具时代性的:
在这个经济全球化、排斥个体的时代里,青年法农所写的那句话,那句代表他所有思想活动的话:“啊!我的身体!让我永远做一个追问的人吧!”超越了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垮台的那些东西,并在这个时代许多年轻人的心里引起共鸣——无论他们讲的是哪种语言,出生于何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