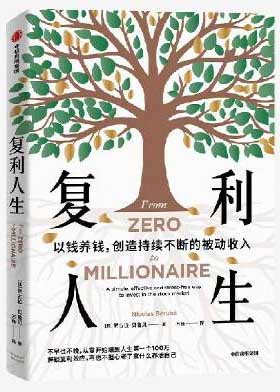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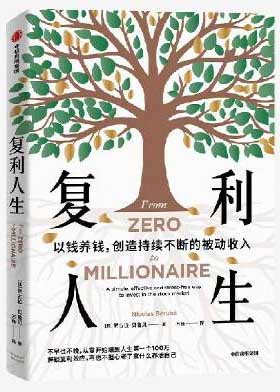
《
复利人生
》
售價:NT$
352.0

《
中国绘画:元至清(巫鸿“中国绘画”系列收官之作,重新理解中国绘画史)
》
售價:NT$
857.0

《
这里,群星闪耀:乒坛典藏·绽放巴黎(全套7册)
》
售價:NT$
1204.0

《
想通了:清醒的人先享受自由
》
售價:NT$
281.0

《
功能训练处方:肌骨损伤与疼痛的全周期管理
》
售價:NT$
653.0

《
软体机器人技术
》
售價:NT$
454.0

《
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
》
售價:NT$
347.0

《
奴隶船:海上奴隶贸易400年
》
售價:NT$
352.0
|
| 編輯推薦: |
1. 美国著名作家,国际笔会美国分会主席,美国“全国文学艺术院”院士,“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院士。
2. 两获普利策文学奖的文坛鬼才和数届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人。
3. 上过前线,当过导演,参加过纽约市长竞选,还结过六次婚,育有九个孩子,同时也是 “硬汉文学”、非虚构写作的践行者与新新闻主义写作的创始人之一。
4. 作为一个集小说家、政客、文化名人、随笔作家、记者、文学批评家、诗人、导演、编剧、演员、社会活动家、运动迷于一身的时代偶像,梅勒毕生将写作当成一项英雄般的事业。
5. 他不仅苛求自己与同时代的同行竞争,更把自己视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物,因此被称作“美国伟大的当代作家”。一位与海明威并驾齐驱的重量级作家。1923年生于美国新泽西州;194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44年至1946年在太平洋地区服役;1948年写出了成名作《裸者与死者》;1968年,《夜幕下的军队》获普利策奖;1980年,《刽子手之歌》)再获普利策奖;2005年获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的美国文学杰出贡献奖。
?
|
| 內容簡介: |
|
创作灵感日益枯竭的作家马登陷入了苦闷,终日饮酒寻欢。一日他邂逅一位美艳动人的金发女郎,与她一夜狂欢后却陷入了离奇凶杀案。他种植的大麻地莫名出现一颗金发女郎人头,同时,他胳膊上的纹身、家中和车内的血迹、通灵朋友的证词都表明凶手非他莫属。诸多巧合令马登毛骨悚然,而破碎混乱的记忆又让他茫然无措。为揭开凶手之谜,马登卷进了爱欲、血腥、谋杀的漩涡。然而,每一条蛛丝马迹都显示,身边每个人都与凶杀有难以分割的关系,每个人都不排除凶手的可能……包括他自己。死者是谁?凶手是谁?蒂姆陷入了理智与疯狂的双重煎熬。?
|
| 關於作者: |
|
美国著名作家、两届普利策文学奖得主。在美国文坛,梅勒被人们视为一个怪才,如果不是“全才”的话。他上过前线,打过仗;当过导演,拍过电影;参加过纽约市市长的竞选。他的作品之多创作期之长,让其他作家惊叹;他参政的热情之大,也许会让真正的政治家咋舌。几乎每一场政治运动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身上贴满了各种标签:运动迷、随笔作家、记者、文学批评家。
|
| 內容試閱:
|
译后记
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是美国当代杰出的也是有争议性的小说家之一。自1948年出版的部小说《裸者与死者》到这里译出的《硬汉不跳舞》,他已出版有二十余部小说作品。新作每出,即在美国文坛引起非凡的轰动。
《硬汉不跳舞》的出版昭示了梅勒创作思想的更为精深与艺术的更为纯熟。通过主人公—作家马登对自己的一段痛苦经历的诉说,小说成功地表现了当代美国知识分子与一般大众的具有零余者色彩的苦恼与绝望。小说以作者惯用的疑案小说的叙述套式展开了对于当代美国人的深层心理的细致入微的开掘与描画,情节曲折、悬念迭生。
小说结构密致而又无一丝雕琢的痕迹,语言通俗,简洁而又蕴藉深远,如此等等,都显示了一个卓越的小说大师的魅力与风采。
在我们着手翻译这部小说的时候,国内还没有一本梅勒小说的译本出版。我们觉得,对这样一位在当代美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小说家,我们没有较为系统而全面的介绍是令人遗憾的。鉴于此,我们动手翻译了这部小说。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各方面朋友的大力支持与勉励,在这里,我们向他们表示衷心的谢忱。
两位译者都还年轻,学识有限,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译界前辈与同龄的朋友们批评指正。
我笑了起来。我实在忍不住了。但这可能是我的反应。雷杰西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一口干了。这时我才意识到,从我提到大砍刀到现在,这是他的杯酒。
“好了,”他说,“我把我知道的告诉你。是条好消息。”他看了看我父亲。“道奇,”他说,“没多少人让我尊敬。可我尊敬你。我从刚进屋时,就敬佩起你来,能和你相媲美的是我在特种部队当兵时的上校。”
“提升他当上将。”道奇说。
“我们会这样做的。”雷杰西说,“但我想先说明白。我要讲的可不太中听。”
“我想会是这样。”道奇说。
“那你就不会同情我了。”
“因为你过去恨我儿子吗?”
“过去。那是过去时态。”
我父亲耸了耸肩。“看上去你现在也很尊敬他。”
“不是这样。我只尊敬他一年。以前我认为他很下贱、卑鄙。可现在,我对他态度有所改变。”
“这是为什么?”我问。
“你听着好了。”他说。
“可以。”
“直说了吧。我干了不少事儿。蒂姆,我一直想方设法要把你逼疯。”
“你差点儿大功告成。”
“我有权这样做。”
“为什么?”道奇问。
“我妻子,玛蒂琳。在我次见到她时,她都快完蛋了。是你儿子使她堕落的。她吸毒。我都应该把她抓起来。你儿子叫她无节制地放荡,然后跟别人撞车,把她子宫弄坏了。一年以后,他把她甩了。我得到的就是这么个女人,为填饱自己的鼻子,不得不用身子来换毒品。我和一个不能给你生儿子的女人在一起生活。所以,直说了吧,马登,我恨透你了。”
“而你呢,反过来又把我老婆拐跑了。”我心平气和地说。
“我是想这么干的。可能是你老婆把我拐跑了。我给夹在两个女人中间,你老婆和我老婆。”
“也有杰西卡。”我说。
“我不会向你表示歉意。你妻子跑了,她不单是离开了你,也离开了我,老兄。我有个习惯。爱情跟它没关系。我每晚要干两个女人。想知道本能的力量有多大吗?我甚至和斯都迪的几个窑娘们儿混过。”他有些自豪地说,“杰西卡只是帕蒂的代用品罢了。”
“那么,你跟玛蒂琳……每天晚上你都回家?”
“当然。”他又喝了几口酒,“这很简单。咱们别跑题。我想说的是,我恨你。我思想比较简单。所以,我把杰西卡脑袋砍了下来,放在了你的大麻地边上,然后告诉你去看看。”
“你不认为我会联想到你吗?”
“我想,这会让你惊慌失措得拉裤子的。我想,你会躺在你自己的屎尿里上西天。我希望的就这些。”
“是你把血洒在我车的前排座位上的吗?”
“是我干的。”
“那是谁的血?”
他没回答。
“杰西卡的?”
“是的。”
我刚想问:“你是怎么干的?”这时,我看见他眼神时隐时现,好像那个场面想从他的思维中挣脱出来,而他呢,拼命把它推了回去。我琢磨他是不是用她脑袋干同样的事,但我还没来得及细想,就赶快把它放到了一边。
“为什么,”我父亲问,“第二天你没化验车座上的血?”
雷杰西像猫一样地笑了笑。“要是我麻木不仁,没化验车座上的血,然后又让你用水把它冲掉,”他说,“没人会相信是我干的。他们怎么能指控我有罪呢?”他点了点头。“那天早晨,我一睁开眼,就担心有人会指控我陷害你。现在听上去有些发傻,可当时我就这么想的。”
“你想指控蒂姆的大部分证据就没了。”
“我并不想把他抓起来。我当时只想把他逼疯。”
“是你杀的杰西卡?”我问,“还是帕蒂杀的?”
“待会儿我会告诉你。这并不是眼下我想说的。我想说的是,我给帕蒂迷住了。可她说的都是关于你的事,说她都恨透你了,你怎么样耗费了她的生活。我能看出来,你点子没她多,所以她还发什么牢骚。后来我才明白。她他娘的必须得毁了个爷们儿,因此我要不整你一下,她几乎会把我给毁掉。她跑了。所以,我才明白。我应该把你干掉。把警察的誓言都丢了吧,干件事。”
“这可不是件小事。”道奇说。
“他娘的,妙极了。”他摇了摇头。“那细节才叫绝呢。我告诉帕蒂,要她把杀死杰西卡的那把枪不擦就放到枪盒里。捂的那股味可能就会让你心脏病发作。等你躺在那儿昏过去时,她来到床前,把枪拿走。”
“那天晚上,你是怎么找到我那些相片的?帕蒂不知道我把它们藏在哪儿了。”
他看上去茫茫然。
“什么样的相片?”他问。
我相信这回他没装模作样。我的心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里。“我找到了一些相片,相片上人的脑袋都给剪掉了—”我告诉他,“帕蒂说,你喝醉酒时,会做出些稀奇古怪的事儿来的。可能是你自己把那些相片的人脑袋给剪掉了。”
我并不想与那种想法生活一辈子,但我怎么能驳倒他呢?
“假设你剪断了一张相片,”我问,“那你干吗要这么做呢?”
“我不会这么做的。只有疯子才干那种事。”
“可是,你确实干了。你把杰西卡的相片给剪了。”
他呷了一小口波旁酒,突然感到嗓子难受,把酒又吐了出来。
“不假,”他说,“我是把杰西卡的相片给剪了。”
“什么时候?”我问。
“昨天。”
“为什么?”
我想,他可能要发病。“这样我就不会再看到后一个表情了,”他挣扎着说,“我想永远忘掉她。”
他的下巴来回抽动,眼睛往外鼓,脖子上的肌肉都抽在了一起。但他用力挤出个问题:“帕蒂是怎么死的?”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叫了一声,很吓人。他站了起来,朝门口走去,用脑袋往门的侧壁上狠狠地撞。
我父亲从他身后走过去,抱住他的胸部,试图把他拖过来。他把我父亲甩到了一边。我父亲都七十岁啦。但我不能相信。
但是,这倒让雷杰西镇静下来。“真对不起。”他说。
“它也是。”我父亲说,和他后一个幻觉彻底告别了。他以前总以为自己还有把子劲儿。
我又害怕起雷杰西来,好像我是被告,他是受害者的伤心丈夫一样。我轻声说:“我和帕蒂的死没关系。”
“你要是说一句谎话,”他说,“我就用手把你撕成两半。”
“我在地洞里看见她的脑袋时,才知道她死了。”
“我也是。”他说,然后哭了起来。
他可能从十岁起就再没掉过眼泪。他的哭声就像一台零件松了的机器发出来的声音。要是把我的伤心程度拿来和他比,我感到我就像妓院里打杂的小童。他真爱我妻子!
我知道,我现在可以问他所有问题。他哭得无依无靠的,他已经从领导席上下来了。他可以在由问题汇成的泥潭里打滚。
“是你把杰西卡的脑袋从地洞里挪走的吗?”
他翻了翻眼。“不是。”
我灵机一动。“是帕蒂?”
他点了点头。
我想问他为什么,可他说不出话来。我不知道再怎样问下去。
我父亲插了一句。“是不是帕蒂认为,”他问,“不管我儿子该得到什么样的报应,你也不该用那个人脑袋去陷害他?”
雷杰西犹豫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我怎么知道这是真的呢,还是她有意这样做,好使我更糊涂呢。但不管怎么说,他点头了。我也考虑到,帕蒂是不是想用这个人脑袋来敲诈沃德利,但我找不出答案来。
“帕蒂要你保管那个人脑袋吗?”我父亲继续问。
他点了点头。
“你把它藏起来了。”
他点了点头。
“然后帕蒂离开你跑了?”
他点了点头。“跑了,”他吃力地说,“她把人脑袋留给了我。”
“所以,你决定把人脑袋送回到原来的地方?”
雷杰西点了点头。
“在那儿,你也看到了,”我父亲用轻柔的语调说,“帕蒂的脑袋。它也藏在那个洞里。”
雷杰西把手放在脑袋后,然后压了一下脖子。他点了点头。
“那是你看到的可怕的情景?”
“是的。”
“你是怎么挺下来的?”
“我一直挺得住,”雷杰西说,“可现在坚持不住了。”他又开始哭起来。他的哭声就像马叫。
我想起了我们在他办公室里一起抽大麻那个时刻。他可能在我走进他办公室几个小时前就发现了帕蒂的脑袋,可他把焦虑藏在心底,从外表上根本看不出来。看到意志异常坚定的人在精神上垮下来,心情是不太好受的。这是否就是人在中风前的模样呢?
我父亲说:“你知道谁把帕蒂的脑袋和杰西卡的脑袋放在一起的吗?”他点了点头。
“尼森干的?”
他点了点头,然后又耸了耸肩。可能他不知道。
“是的,就是他。”我父亲说。
我同意父亲的看法,肯定是蜘蛛干的。我考虑,蜘蛛当时可能会感到自己要被牵连进去。当然,他也想把我拐带进去。是的,他跟斯都迪想在我拎那两个人脑袋时把我抓住。要是我真的被他们抓住了,谁还会相信我是清白的?
“你杀的杰西卡?”我问雷杰西。他耸了耸肩。
“帕蒂干的?”
他先是摇摇头,随后又点了点头。
“帕蒂干的?”他点了点头。我想,要是我不知道这一切该有多好。但我可以肯定:是帕蒂跟雷杰西,而不是沃德利,在维斯角见到了杰西卡,可能是帕蒂把装有朗尼尸体的那辆车开回了望夫台酒家。然后,他们三个人坐进同一辆警车里。在一片林子里,他们停了下来。在那儿,帕蒂开枪打死了杰西卡。
我说不好帕蒂干吗要那么做。在她有足够理由开枪打死杰西卡时,谁会知道她气成了什么样?杰西卡挖空心思要为自己买下帕拉米塞兹房地产。杰西卡又和阿尔文.·.路德有私情。在关键时刻,只要有一条理由就可以叫帕蒂火冒三丈。是的,现在我可以看见她把枪筒塞进杰西卡那张爱撒谎的嘴里时的情景。当时,要是庞德乞求雷杰西救她,要是雷杰西想把枪抢走,那她扣动扳机也是有道理的。帕蒂就跟我似的,多年来一直生活在扳机边缘。所以,像我俩这种情况,杀人是一剂包治百病的良药。我这么说可能太吓人了。
雷杰西坐在椅子上,就像个在后一轮比赛中让对手狠狠揍了一顿的拳击手。
“你干吗要把杰西卡的脑袋砍下来?”我问。刚才我已经问过一遍了,可我不得不再问一遍:在我脑海里,我看见了大砍刀从上面砍下来。
他的喉咙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脸向一边歪去。我想他确确实实是中风了。一个沙哑、充满了敬意的声音从他牙缝中挤出来,“我想,”他说,“把她的命运跟我的命运终结合在一块儿。”
他从椅子上滚到地上,四肢开始来回抽搐着。
玛蒂琳走了进来。她手里端着那支大口径短筒手枪,但我想她并没意识到她的这个姿势。也许她在楼上书房里一直端着来的。她看上去老了许多,更像个意大利人了。她面部表情麻木,可能就像一堵石头墙快要扒倒时所感觉到的那样。她一颗眼泪儿也没有,比我们更坚强。“我不能离开他,”她对我说,“他病了。我想他可能会死的。”
雷杰西除右脚外,一切都恢复了平静。他右脚还在地上来回抽搐,这是他所没有的那条尾巴在抽打。
我和我父亲用尽全身力气把他架到楼上,差点没把我俩累死。我把他放在我跟帕蒂曾经躺过的那张大床上。真奇怪,是他愿意为她而死,而不是我。
尾 声
雷杰西整天躺在床上,玛蒂琳无微不至地照料他,好像他是个奄奄一息的神仙。在普罗文斯敦,避开惩罚的方法,真是叫人难以置信。第二天早晨,玛蒂琳给警察局挂了个电话,说他身体不佳,她准备带他出去旅游,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他们能否帮助写个报告,替他请个长假?我灵机一动,在天亮前把那台警车的行李厢冲洗干净,然后又把它停在市政办公大楼旁,把车钥匙放在座位下面,这样他不上班就与我的房子没有任何关系了。玛蒂琳有意地每天都给他的办公室挂电话,和警察谈谈雷杰西的病情,巴恩斯特布尔的恶劣气候和她为了他的身体健康如何不让他接电话。她一连打了四天。她确实把电话撤了。第五天,雷杰西的病见好,这可是他的一个大错误。我们这些人可遭罪了。
他躺在床上,把我们骂了个狗血喷头。他说,他要把我们都抓起来。他要把我关进监狱,因为我有一块大麻地。他准备指控我杀死了杰西卡。他声明,我父亲是不公开的鸡奸犯。他,雷杰西,要到非洲去。他要当个职业士兵。他也准备在萨尔瓦多待几天。他要给我邮张明信片。那可能是他手拿大砍刀的照片。哈,哈。他坐在床上,身上的肌肉从丁字领衫里鼓了出来,嘴因为中风歪向了一边。他由于大脑发生了变化,声音也变得不一样了。他抓起电话,发现电线被切断时,狠狠地把它摔了(我反应很快,早就把电话线切断了)。我们给他吃了几片镇静药,可他就像一头撞坏篱笆墙的公牛一样挣破了药剂的束缚。
只有玛蒂琳能管住他。我看到了她的另一面,这是我在以前从没见到过的。她安慰他,把手放在他的前额上,让他镇静。如果这些都不成功的话,她就会责备他,把他说得不吭声。“安静点,”她常常这样对他说,“你这是罪有应得。”
“你打算还跟我在一起吗?”他问。
“我跟你一辈子。”
“我恨你。”他告诉她。
“这我知道。”
“你是一个肮脏的浅黑型女人。你知道浅黑型女人该有多脏吗?”
“你自己倒该洗个澡了。”
“你叫我恶心。”
“把药吃了,把嘴闭上。”
“这药会损伤我睾丸的。”
“对你有好处。”
“我都三天没硬起来了。我可能再也硬不起来了。”
“别害怕。”
“马登在哪儿?”
“我在这儿。”我说。我一直在那儿。她晚间独自一人照料他,可我和父亲总是轮班在门厅里守着,手持马格南左轮手枪。
楼下的电话响的次数很少。失踪的人与我的关系都不大。大家都知道,雷杰西现在正在旅途当中。贝思走了,蜘蛛也走了,所以每当人们想起他们时,会认为他们两口子出去旅游了。这是因为,他们那辆面包车也不见了。斯都迪的家人害怕他,所以不见他露面实在让他们感到高兴。我知道,没人会想念“博洛”。人们会认为帕蒂可能在大世界某处玩乐呢。沃德利也是这样。几个月后,沃德利的亲属可能会认为他走的时间太长了,上警察局去报案。七年之后,与他血缘近的亲属会把他的房地产归为己有。几个月后,我也会到警察局报案,说帕蒂失踪了。或者不吱声,把这件事瞒下来。我想,我听天由命,看看事态的发展再说。
杰西卡.·.庞德的儿子,朗尼.·.奥克伍德可能会把事弄糟。但,他怎么会把她跟我联系起来呢?但我担心的是我胳膊上那个刺花纹和哈坡,可并不十分担心。哈坡已经把我告了一次,他不会再干第二次了,至于那个刺花纹,我要想改,马上可以把它改了。
真正的麻烦是雷杰西。如果我们的安全都寄托在阿尔文.·.路德身上的话,那我们随时都会处在危险之中。他到处给你找麻烦。我也不喜欢他躺在床上的方式。从他那个样子来看,他是在等待时机,准备反扑。但不管怎样他没离开床一步。
但是,在这期间,他那张嘴可够吓人的。我们听到他对玛蒂琳说:“我让你一宿起来十六次。”
“这不假,”她说,“哪一次都不怀好意。”
“那是,”他满怀希望地说,“因为你没有子宫。”
她那天下午开枪把他打死了。我们谁都会开枪打死他,可这碰巧是玛蒂琳。我和父亲已经在门厅里谈过这种事情了。“没别的办法,”道奇说,“一定得把他杀了。”
“他现在有病。”我说。
“他可能有病,但并不是受害者。”道奇看了看我。
“我来干这件事。我了解他。他是我这号人。”
“如果你变了主意的话,”我说,“我也能干掉他。”我能。我能看到我将要干的事的那种该死能力变得越来越清晰了。在我的脑海中,我把雷杰西的马格南左轮顶在他胸上。枪把儿的剧烈振动把我的胳膊抛到空中。他的脸歪到了一边。我撂倒了这个疯子。雷杰西看上去就像头野熊。然后,他咽气了。他死后,脸上浮现出一种严肃的神色,他的下巴僵硬得就像乔治.·.华盛顿的下腭。
你知道吗?这就是雷杰西在死时贡献出来的后一个表情。玛蒂琳那支大口径短筒手枪响了两次后,我走进屋。他躺在我的婚床上,正在咽气呢。看上去在她扣动扳机之前,他说的后一句话是:“我喜欢帕蒂.·.拉伦。她叫我高兴。我是属于她的。”
“祝你走运。”玛蒂琳说。
“我见到你时,我认为你是会叫我高兴的,”他说,“但你是个小土豆。”
“这我信。”玛蒂琳说,然后扣动了扳机。
杀死个人是很平常的,但她是自己决定一定要干掉他的。在危险的地方的疯子一定得除掉。你在喝黑手党的奶时,学的就是这些。
一年以后,她在谈起这件事时,对我说:“我只等着他说那句呢。我一听那句话,肺都气炸了。”别管意大利女人叫小土豆。
那天晚上,我父亲把他的尸体扔到海里。和雷杰西一起下葬的是一块钢筋水泥板,我父亲用铁丝,分三道,在腋窝、腰和膝盖等处把尸体绑在水泥板上。当然了,我父亲已经进行过这方面的练习,在阿尔文.·.路德中了风,躺在地上失去知觉那天早晨,道奇坚持要我用船带他到鬼城,到沃德利的墓地那儿。他硬要我去找到那些坟。我找到了。那天晚上,当我守着我们那位倒下了的捉毒品犯的警察时,父亲卖了六个小时肮脏的苦力。天刚亮时,他迎着潮水,把五具尸体运到深水处,然后平平安安地把它们沉到海底。毫无疑问,我现在处于撰写一部爱尔兰喜剧的危险之中,所以我不想描述道奇为了把阿尔文.·.路德送到尸体安息地而做准备工作时的那股子热情。但我要提一下他干完活时说的那句话:“可能,我一直在干我不应该干的事儿。”可能是这样。
我和玛蒂琳到科罗拉多州待了一阵子。现在我们住在基韦斯特。我试图写点东西。我们是靠着她在本地一家饭店里当女招待挣的钱以及我在她饭店对面的酒吧当“业余”侍者挣的钱过活。偶尔,我们等待着有人敲门,但我不能肯定一定会有人找上门来。劳雷尔.·.奥克伍德的失踪引起了很大的骚动,许多家报纸上都有她儿子的照片。他说,要是找不到他的母亲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但我认为,从他的照片上看,他缺少做这种事儿的气质。报上的特写暗示说,圣巴巴拉的人认为劳雷尔和潘伯恩.·.朗尼曾在经济上犯了一两个小错误,现在可能找到了一个富有的新加坡商人或者是哪个有钱的人。尽管车后行李厢底部那摊血上有褶纹,警方照旧认为他是自杀。
《迈阿密先驱报》登出一篇文章,报道了米克斯.·.沃德利.·.希尔拜三世失踪的事儿。有位记者真的顺藤摸瓜,到基韦斯特来找我了。他问我,我是不是认为帕蒂和沃德利会再度结合。我告诉他,他俩已经和我没有任何来往了,现在他们可能是住在欧洲,可能是在塔希提岛,或是在两个地方之间的什么地方。我认为,那种事总是会再次出现的。
看起来似乎谁也不想知道雷杰西现在怎么样了。几乎没有什么人以官方的身份向玛蒂琳打听雷杰西的情况,这真叫人难以置信。华盛顿毒品管理局的一个人曾经给玛蒂琳打过电话。玛蒂琳告诉他,雷杰西和她开车准备到墨西哥去,但阿尔文在拉雷多就把她给甩了,所以她再也没有越过国境(早些时候,在我们去科罗拉多时,我们俩就绕道去了拉雷多,目的是弄到一张汽车旅馆的收据。这样,如果警方查问时,就有话说了)。但是,我认为,与毒品打交道的那些警官们对雷杰西失踪一事都会感到高兴的。现在,那件事就算了结了。有一次,我向玛蒂琳问起阿尔文的弟弟。可他那几个侄子照那张相时正是她的一次见到他的家人—他的一个弟弟。
我们由于手头的钱不充裕,所以想把我们各自的房子卖掉。但那两幢房子的房主名儿并不是马登和玛蒂琳。我猜,这两幢房子迟早会因交不上税金而被没收。
我父亲还活着。那天,我收到他的一封信,信上说:“祝我走运吧,但那些二百五大夫说,我的病好了许多。这叫他们大吃一惊。我病情的好转解除了他们的责任。”
可是,道格拉斯.·.马登的儿子,蒂姆.·.马登对此有自己的看法。我怀疑父亲近的心理状态这么好是与他沉到海底的那些人头和尸体有关。
怪不得治疗癌症得花那么多钱。
我自己呢?有许多事情把我牵连了进去,所以我必须用笔来把我从由忧郁、内疚和根深蒂固的精神罪孽组成的牢笼中解救出来。是的,我要利用这次机会。实际上,一切并不那么糟。我和玛蒂琳互相搂在一起睡觉。我生活在她的功绩的怀抱里,既舒服又安全,我同她结下了生死之交。同时,我也意识到,现在我头脑的清晰、平静是建立在杀人罪—这坚实的基础之上的。
但我不能说,我们彻底地、一点也没受伤害地摆脱了鬼城。我们住在基韦斯特时,有一个夏日的黄昏,赤道的热风越过加勒比海,朝我们这边刮来,室内空调机也不太管用,我想起了玛蒂琳和帕蒂的那些照片(我是用把剪子把她们的脑袋剪下来的)。睡不着,因为这迷人的黄昏使我想起我拿剪子剪照片那个时刻正是现在这时候。(当时我试着按伏都教a的说法从头部把照片剪开,我想这样就会阻止帕蒂离开我了。我剪完之后就和帕蒂去参加由哈坡主持的降神会。你可记得,在会上,尼森大声尖叫起来,因为他看到了帕蒂命运的结局。)
我能告诉你什么呢?我所听到的,来自普罗文斯敦的消息是,哈坡疯了。这我是从一位路过基韦斯特,心肠很好的流动工人那
a 西印度群岛和美国南部等地某些黑人中流行的巫术信仰。
儿听到的。他似乎是在前一段时间里又主持了一次降神会,并声称看见了海底的六具尸体。在海底,两具无头女尸跟他说过话。可怜的哈坡被关进了监狱。我听说,今年晚些时候才被放了出来。
喜剧:
坏人和坏事、婚姻、酒宴、赌博、诓骗、淘气的用人、好吹牛的老爷、阴谋、年轻人的轻率、吝啬的老年人、拉皮条和诸如此类的事,每天都会在普通人中间发生。
悲剧:
死亡、绝望、杀婴和弑父母、大火、乱伦、战争、叛乱、恸哭、嚎叫、叹气。
—马丁 · 奧皮茨 · 范 · 博勃费尔德(1597—163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