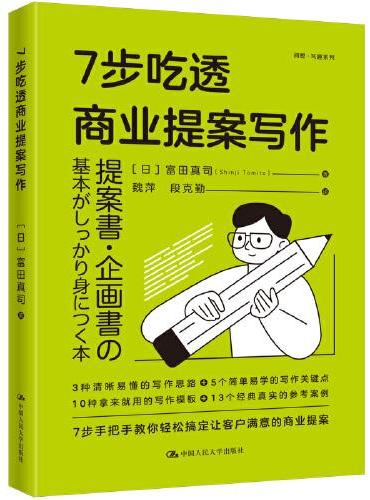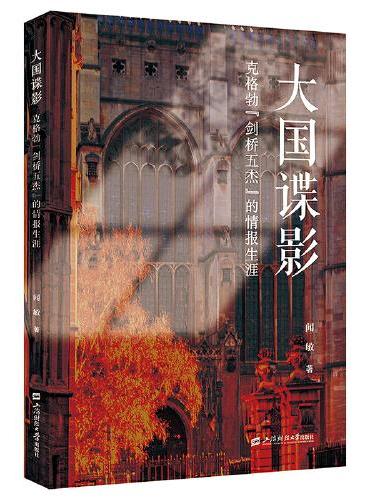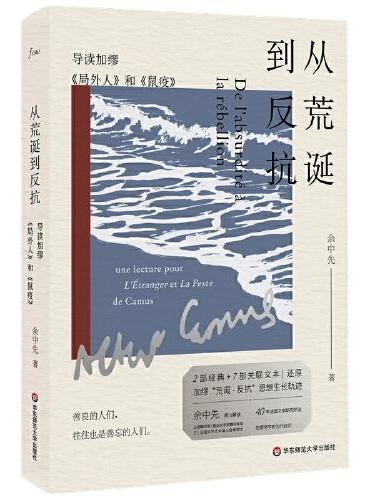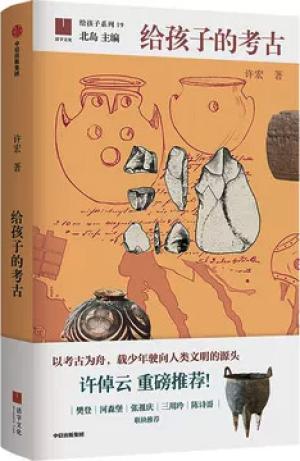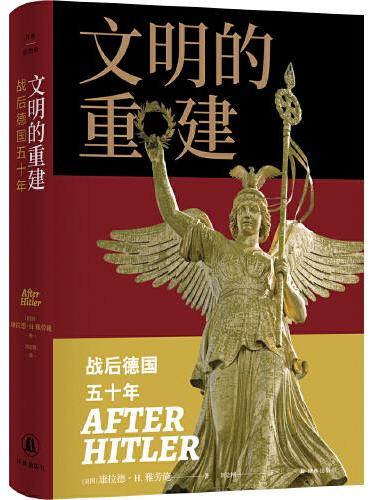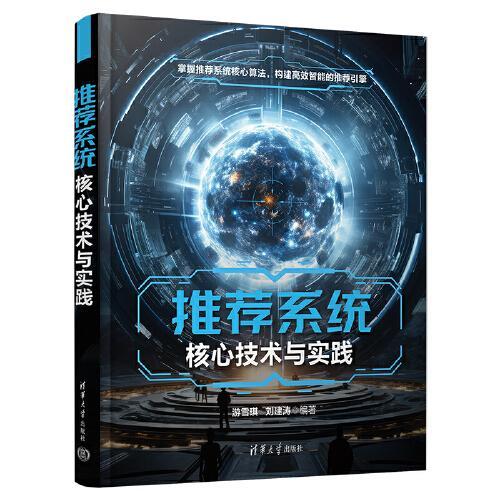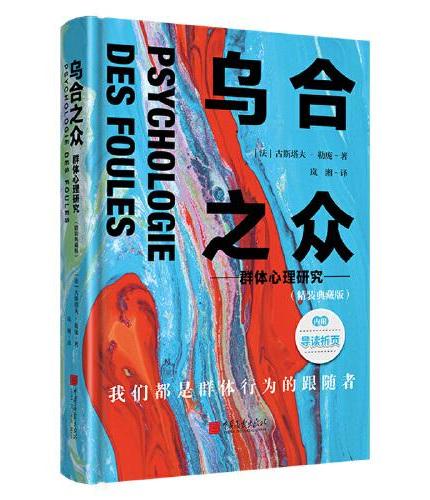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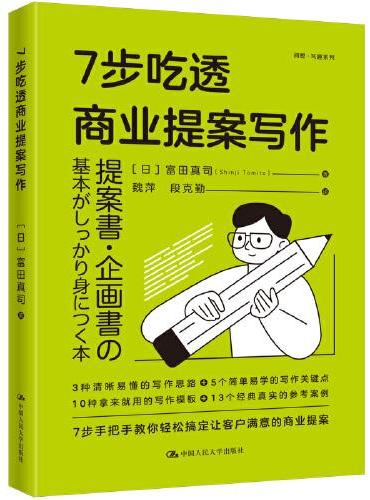
《
7步吃透商业提案写作
》
售價:NT$
3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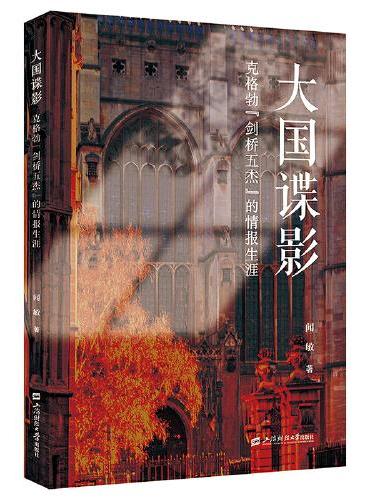
《
大国谍影
》
售價:NT$
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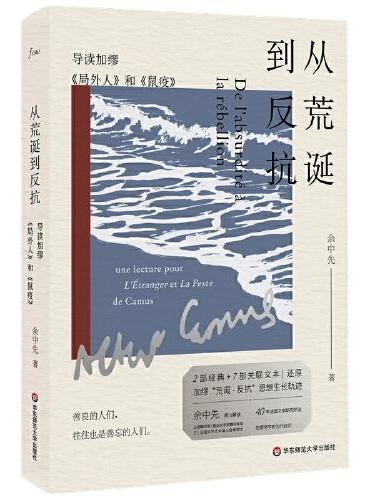
《
从荒诞到反抗:导读加缪《局外人》和《鼠疫》(谜文库)
》
售價:NT$
3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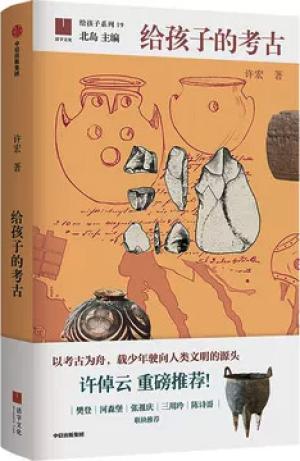
《
给孩子的考古
》
售價:NT$
2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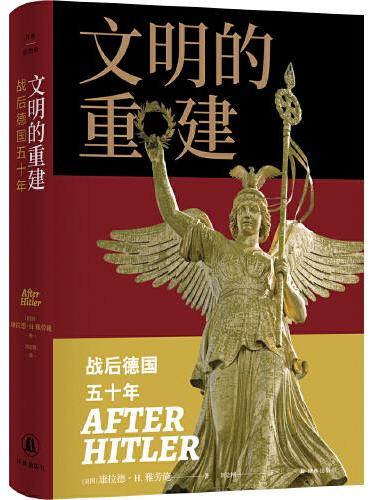
《
文明的重建:战后德国五十年(译林思想史)从大屠杀刽子手到爱好和平的民主主义者,揭秘战后德国五十年奇迹般的复兴之路!
》
售價:NT$
505.0

《
社会情绪的传递与互动研究:以情感符号为视角 (光明社科文库·法律与社会)
》
售價:NT$
43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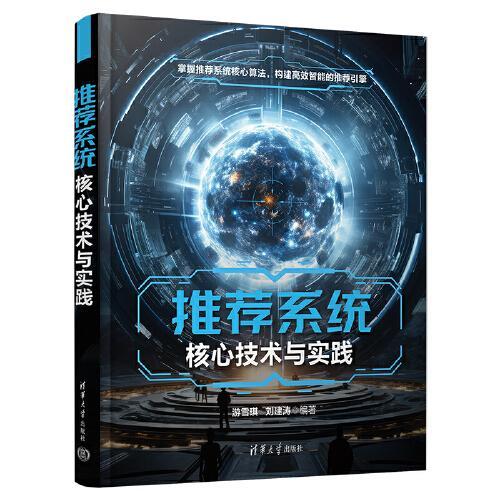
《
推荐系统核心技术与实践
》
售價:NT$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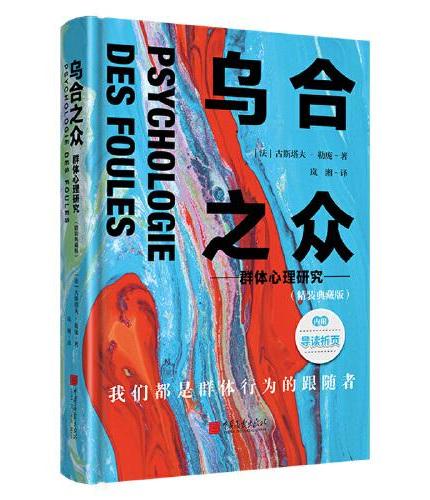
《
乌合之众:群体心理研究
》
售價:NT$
347.0
|
| 編輯推薦: |
★英国国家图书奖获奖作品、英国水石奖年度图书、国际都柏林文学奖提名作品;并入围科斯塔图书奖、英国女性小说奖、狄兰·托马斯奖;《纽约时报》《卫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科克斯书评》等众多媒体推荐;
★由艾美奖、金球奖得主克莱尔·丹妮丝?金球奖得主抖森出演同名英剧《埃塞克斯之蛇》;
★一部关于生命、爱与信仰交织碰撞的小说
探讨了爱情和友谊的界限,以及我们对彼此的忠诚,同时展现出人心的复杂和我们内心深的愿望以及恐惧;
★面对不确定的世界,我们必须找到自己的光源,才能充满力量地生活下去
女主角科拉走出不幸的婚姻,重获自由后,热爱博物学的她,以贝壳和骨头重建了自己的生活;
★小说既有神秘故事,又有自然历史课,既有浪漫爱情,又有女性主义寓言。
|
| 內容簡介: |
专横的丈夫去世后,科拉开始了寡居的新生活。过去的婚姻并不幸福,此时她感到解脱,尽管看起来不够体面。为了寻求新鲜空气,科拉决定离开伦敦,前往埃塞克斯海岸,不料被沼泽中游荡的可怕生物迷住。
威尔是埃塞克斯当地的牧师,他才智过人,聪明幽默。科拉的到来让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产生交集。他们相互较量,绝不轻易向对方的思想让步,又感觉到灵魂上的彼此吸引。此时,小镇上关于埃塞克斯之蛇的传闻正在蔓延,两人对于传闻各执一词,更有村民认为是科拉引来了巨蛇。危机与恐惧不断席卷着镇上的每个人,而科拉和威尔的生活也正在一场新的暴风雨中重建。
|
| 關於作者: |
莎拉·佩里,英国作家,1979年出生于埃塞克斯。她拥有英国皇家霍洛威学院创意写作博士学位,除了小说写作,也为《卫报》和《金融时报》撰写评论。2016年,莎拉在布拉格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文学之都驻地作家”称号。
《埃塞克斯之蛇》是她的第二部作品,书写了关于生命、爱情和信仰之间的隐秘碰撞,是一部充满智慧与波动的小说。这本书获得了多个文学奖项,包括2016年水石年度图书、2017年英国国家图书奖,并入围2017年科斯塔小说奖、2017年英国女性小说奖和2018年都柏林文学奖长名单。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已经上映。
|
| 目錄:
|
跨年夜
部分
埃塞克斯奇闻
第二部分
全力以赴
第三部分
看好,别眨眼
第四部分
后的叛逆时光
后记
|
| 內容試閱:
|
跨年夜
清冷的满月下,一个年轻人走在黑水河岸边。他一直在觥筹交错中辞旧迎新,直到眼睛酸了、胃痛了、厌倦了那明亮的灯光和喧闹。“我要下水去了。”他吻了一下离自己近的一张脸说,“钟声敲响之前我会回来的。”此刻,他翘首东望,回转的潮汐在黑暗中慢慢地流出河口,白色的海鸥在波浪上闪闪发光。
天很冷,他本来应该能感觉到的,但肚子里全是啤酒,身上还裹着厚厚的高档外套,让他产生了错觉。外套领子刮着他的后脖颈:他觉得自己晕乎乎的,肌肉发紧,舌头也干得厉害。我得下去游个泳,他想着,那样能让我放松放松;他沿着小路往下走,独自站在岸边,在那黑泥巴深处,所有的小溪流都在等待潮汐。
“友谊地久天长。”他用甜美的教堂男高音唱着,然后大笑起来,有人用笑声回应了他。他解开外套,拉向两边,但觉得还不够:他想体会寒风像刀一样在身上拉扯的感觉。他走到离水更近的地方,伸出舌头舔了舔咸咸的空气——是的,我要去游个泳,他想着,便把外套丢在了岸边的湿地里。以前他也曾这样做过,只不过那时他还只是个小男孩,而且有玩伴。午夜小游的无脑冲动随着过去的一年一起没入新年的怀抱里。潮汐退了下去,风小了,此刻的黑水河一点也不让人害怕。给他一杯,他就敢一饮而尽,管它是不是咸的,管它是不是有海贝、牡蛎还是什么其他东西。
但是,随着潮汐的回旋或空气的变化,有些东西发生了改变:河口水面不一样了,似乎(他往前走了几步)在有规律地脉动和抽搐,随即又变得光滑而平静;但很快又开始抽搐,仿佛是因为被触摸而退缩。他走得更近了些,仍然没有感觉到害怕;海鸥一只接一只地腾空,后一只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
冬日的寒冷仿佛给了后脖颈一记重击,他感觉到那种冷穿透了衬衫,深入骨髓。喝酒壮起来的胆子慢慢没了,站在黑暗中,他突然有些不安,转身去找外套,但云遮住了月亮,他什么也看不见。他的呼吸非常缓慢,空气像针扎一样,脚下的湿地突然浸满了水,仿若远处有什么东西迫着河水一下子涌了上来。没事,什么也没有。他一边想,一边给自己打气,但奇怪的事情再次发生,有一刻寂静得有些诡异,仿佛他眼前看到的是一张照片,然后是一阵疯狂的涌动,那不只是因为月亮对潮汐的吸引。他觉得自己看到了——不,他确定自己看到了——某种巨大的可怕生物,身上满是粗糙的鳞片,正缩成一团缓缓移动,然后便消失了。
他站在黑暗中,瑟瑟发抖。他感觉到了,那边有什么东西正伺机而动,它残忍、可怕,出生在水中,一只眼睛一直紧紧地瞄准他所在的方向。它一直沉睡在水底,现在终于出来了。他想象着它拥抱海浪,贪婪地嗅着空气。一阵恐惧袭来,他的心脏漏跳了一拍,就在那一瞬间,他受到了指控、谴责和审判:哦,他真是个罪人——他的心多么黑啊!他感觉自己一下子被掏空了,一无是处,他没有任何理由为自己辩驳。他望着远处黑黑的黑水河,它又来了,有什么东西劈开了水面,然后潜入水里—是的,它一直都在,一直在等待,终于把他给找出来了。他感到一种奇怪的平静,正义终会到来,他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孽——只有懊悔,没有救赎,他罪有应得。
但是随后又起风了,风把云彩拖走,露出了月亮那张害羞的脸。月亮自然不是很亮,但足以令人心安,他终于找回了外套,就在离他不到一码的地方,衣服边缘沾满了泥;海鸥回到了水面上,他觉得刚才的一切荒谬至极。上面的小路上传来笑声,一个女孩和男朋友一起穿着节日的盛装。他挥挥手,朝他们喊道:“我在这里!这儿!”是的,我在这里,他想,在这里,在湿地上,他对这里比对自己家还熟悉,潮汐慢慢转向,没有什么好害怕的。真是荒诞!他一边想,一边自嘲地笑了笑,突然的放松让他有些眼花,那边好像什么也没有,只有鲱鱼和鲭鱼!
黑水河里没有什么好怕的,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后悔的,就是在黑暗中有那么一瞬间的恍惚,还有就是喝得太多了。水流到了他脚下,老朋友又回来了;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又走近了些,湿了靴子,展开双臂。“我在这里!”他喊道。所有的海鸥都以叫声回应。就下去游个泳,很快的,他想着,友谊地久天长,然后大笑着脱掉了衬衫。
时钟的钟摆从旧年摆到了新年,黑暗遮住了水底的那张脸。
六天前,迈克尔 · 西伯恩死于咽喉癌,在此之前,他都对不断折磨他的疾病和医生的关心冷漠以待。不过,此刻加勒特关心的并非死者,而是他的遗孀,她(他笑着想)可能正在整理自己脏乱的头发,或是寻找漂亮黑裙子上遗失的一枚纽扣。
科拉 · 西伯恩对于丈夫去世的反应,是卢克所见过的奇怪的事。不过,当他次踏入他们位于福里斯街的家中时,就已经意识到有些不对劲。那些高顶房间里的氛围证实了一种与疾病无关的不安感。虽然当时病人脖子上缠着将领巾对折后做成的绷带,但情况相对来说还不错。领巾全是纯白色的丝绸,而且经常有些许污渍——对于那个总是吹毛求疵的男人,很难想象这不是故意的,卢克怀疑他试图让自己的访客感到不安。西伯恩瘦得出奇,让人觉得他特别高,而且他说话很轻,必须凑近才能听清楚他在说什么。他的声音中总伴着嘶嘶声。他很有礼貌,指甲床是蓝色的。西伯恩平静地听完自己的次会诊,然后拒绝做手术。
“我希望当我离开这个世界时,如当初来到这个世界时一样。”他拍拍喉咙上的丝绸说,“没有伤疤。”
“没必要这样受苦。”卢克主动上门劝说。
“受苦!”这个想法显然令他很开心,“那将是非常有益的经历,这一点我很确定。”随后,他似乎很自然地想到了下一个问题,问道:“告诉我,您见过我妻子了吗?”
加勒特常常想起他与科拉 · 西伯恩初次见面的情景,虽然实际上他的记忆并不可信,因为那都是根据后来的事情创造出来的影像。那一刻,科拉仿佛受到召唤一般翩然而来,站在门口打量着眼前的来访者。随后,她穿过地毯,弯腰亲吻丈夫的额头,站在他的轮椅后面伸出一只手。“查尔斯 · 安布罗斯跟我说,其他医生都做不了。他给我看了您那篇关于伊格纳兹 · 塞麦尔维斯的人生的文章,如果您的技术像文笔那样好,我们就都能长命百岁了。”这样舒适的恭维令人无法抗拒,加勒特只能笑笑,牵住她伸出的那只手弯腰鞠躬。她声音低沉,但并不微弱。起初他以为她是那种永远不会在一个国家逗留太久的流浪者的口音,她有一点语言障碍,会把一些辅音发得很长。她一身简单的灰色,但裙子上的织物却闪闪发光,仿佛是鸽子的脖子。她很高,不算单薄,眼睛也是灰色的。
接下来几个月,加勒特开始对福里斯街,以及檀香和碘那令人不安的气味有了些许了解。迈克尔 · 西伯恩虽然四肢疼痛,但仍然表现出与病人身份严重不符的恶劣影响。妻子总会为他准备好凉爽的衣服和好酒,并且十分积极地学习如何将针头插入静脉,让人觉得她可能已经把一本关于女人职责的指导手册一字不落地背了下来。但是,加勒特发现科拉与其丈夫之间从未表现出任何深情。他甚至怀疑她其实很希望这生命之火快些熄灭——有时候,加勒特很怕她会把自己拉到一边,在他准备注射时悄悄对他说:“给他多打点,稍微多打点。”她俯身亲吻枕头上那饥饿的圣徒的脸时,会十分小心,似乎觉得他肯定会暴跳如雷,不顾一切地扭断她的鼻子。他们曾经雇了护工来负责给他换衣服、排尿、保持床单整洁,但几乎都没有人能坚持超过一个星期。后一个护工(一个比利时女孩,非常虔诚)在走廊上遇到卢克,小声用法语对他说“他是个魔鬼”,然后给他看自己的手腕,但手腕上什么也没有。只有那只不知名的狗——忠诚、长满疥疮,却一直守在床前——毫不惧怕,或者说至少已经习惯了它的主人。
没过多久,卢克 · 加勒特便与西伯恩家的儿子——一头黑发、沉默寡言的弗朗西斯——混熟了,他跟保姆玛莎待在一起,玛莎总是喜欢站在那里,摆出卢克很不喜欢的一种占有的姿势——一只胳膊搂着科拉 · 西伯恩的腰。对病人的粗略评估很快出来(毕竟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呢?),卢克马上就会被拉去研究科拉在邮箱里收到的化石牙齿,或者被详细地询问他在推进心脏手术方面的野心。他曾对她进行催眠,并解释了催眠曾在战时用于缓解士兵截肢的痛苦;他们一起下棋,只是科拉后委屈地发现,对手排兵布阵,把她打得落花流水。卢克对自己的诊断是陷入了爱情,并且无药可救。
他总能感觉到她的体内有一股能量蓄势待发;他觉得等迈克尔 · 西伯恩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她的脚能在地上拍出蓝色的火花。这一刻终于还是来了,卢克见证了西伯恩的后一次呼吸,那呼吸声很大,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似乎在后一刻,病人早已放弃“死亡艺术”,只想再多活一会儿。但不管怎样,科拉还是老样子,既没有悲痛欲绝,也没有如释重负。只是听到有人发现那条狗也死了时,她的声音变了,但谁也不知道她是想笑还是想哭。签完死亡证明,把迈克尔 · 西伯恩的所有遗物都安放在别处后,加勒特便再也没有充足的理由去福里斯街了;但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他的脑子里都有一个目标,而且走到铁门前,会发现自己充满期待。
地铁驶入堤岸地铁站,他被人群裹挟着走到站台上。一阵悲伤在此刻袭来,既不是因为迈克尔·西伯恩,也不是因为他的遗孀。令他困扰的是,这可能是他与科拉的后一次见面——她在他眼中后的形象将是丧钟敲响时回头看的那一眼。“可是,”他说,“我必须去,哪怕只是看着棺材盖扣紧。”检票口外,人行道上的冰雪已经融化,苍白的太阳正在下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