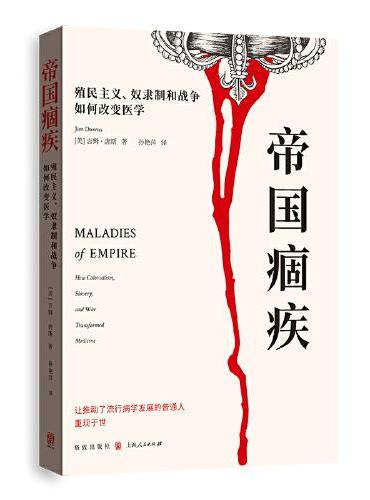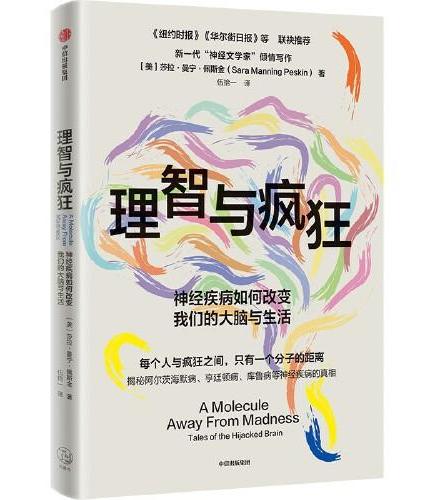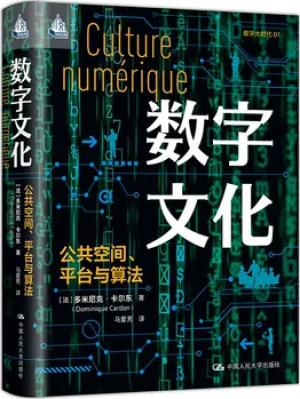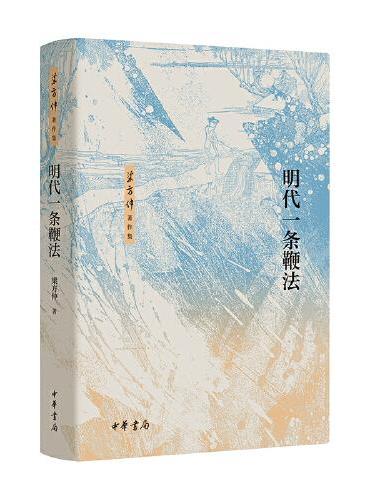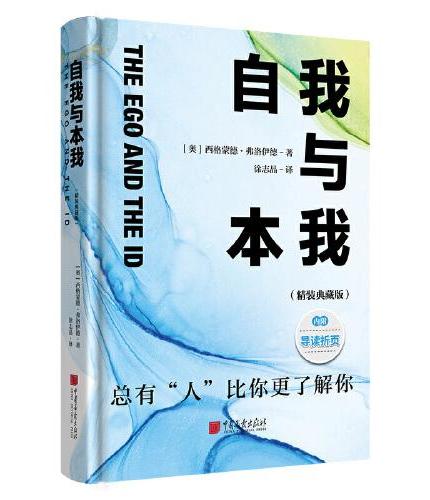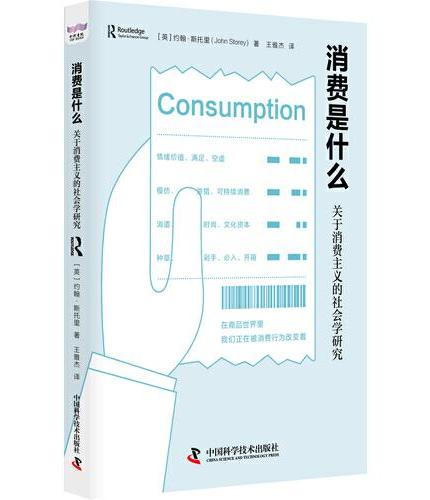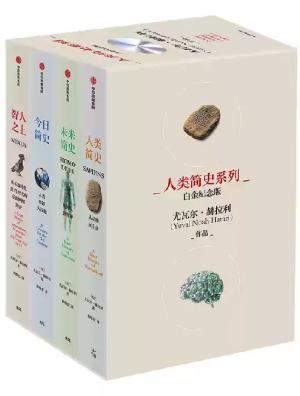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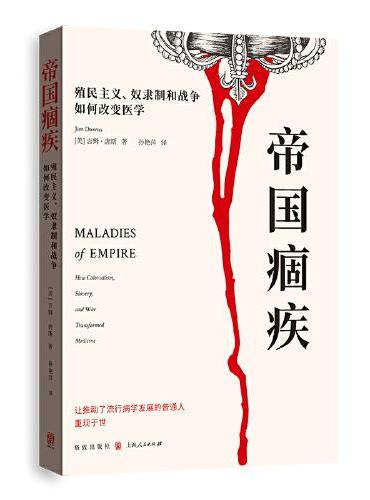
《
帝国痼疾:殖民主义、奴隶制和战争如何改变医学
》
售價:NT$
36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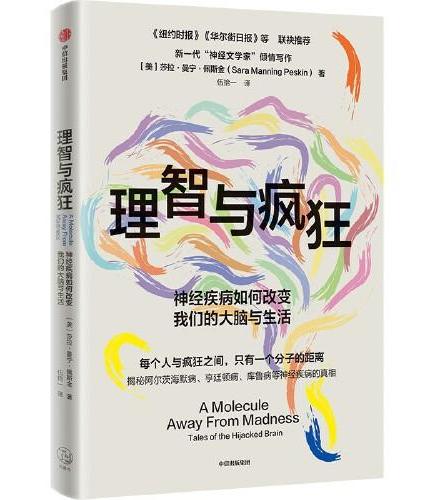
《
理智与疯狂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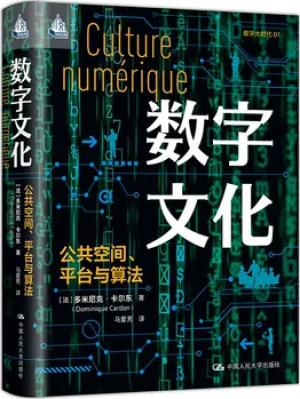
《
数字文化:公共空间、平台与算法
》
售價:NT$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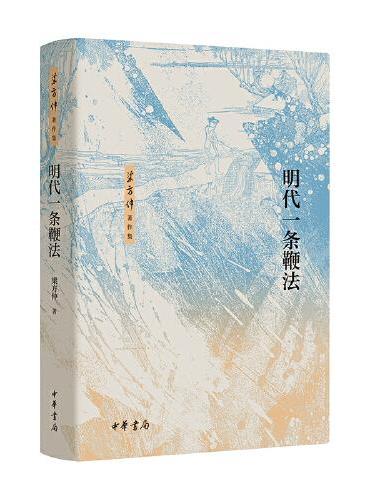
《
明代一条鞭法(精)--梁方仲著作集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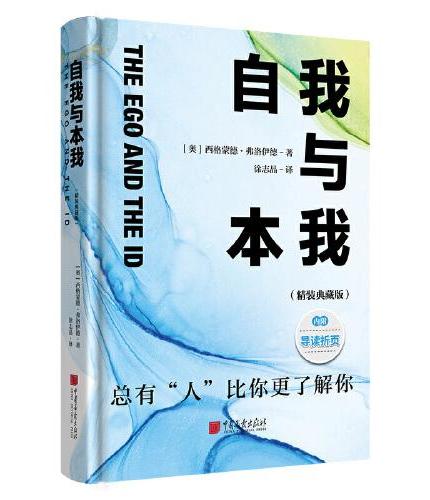
《
自我与本我:弗洛伊德经典心理学著作(精装典藏版)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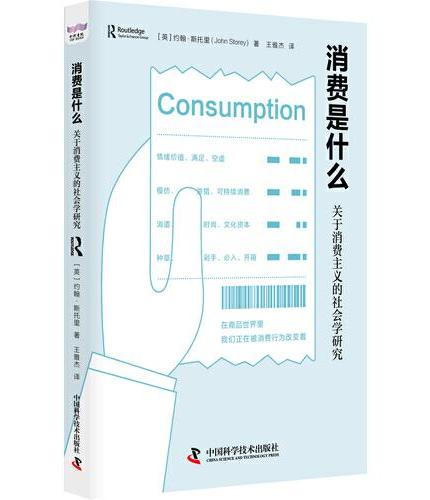
《
消费是什么 : 关于消费主义的社会学研究(一本书告诉你为什么买买买之后也有巨大空虚感)
》
售價:NT$
3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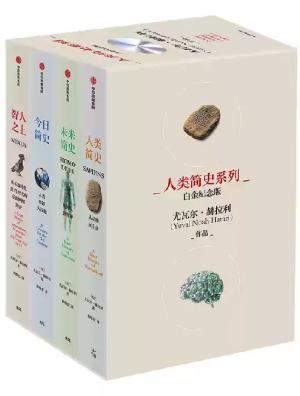
《
人类简史系列(白金纪念版)(套装共4册)
》
售價:NT$
1612.0

《
深度学习推荐系统2.0
》
售價:NT$
653.0
|
| 編輯推薦: |
★具有多年公安工作经验的作家潜心创作的社会派悬疑小说
★既深谙社会派推理之道,又突破了类型文学的传统范式,寻回文学的本源,指向宇宙神秘而深不可测的人心。——文学评论家、《科幻世界》副总编 姚海军
★作品可读性与现实关怀兼备,是继谍战小说大师麦家之后,又一位把类型文学和严肃文学完美结合的新锐小说家。——一位读者
★真相存于人心,不会随风而逝。炽烈而冷峻的西塘埂连环疑案。
★拍案叫绝的案情推理,惊悚屏息的追凶现场。抽丝剥茧,面具背后仍有面具,案件惊天逆转。
★层层伏笔,惊天逆转;人性对决,世相人心;善恶抉择,生死较量。
|
| 內容簡介: |
这是一个关于金钱与尊严、欲望与仇恨、道德与法制的故事,是一部具有多年公安工作经验的作家潜心创作的社会派悬疑小说。
河边发生命案。是意外,还是谋杀?作案动机何在?八年后,刑警俞东杰在调查走访中,发现这桩命案与另一起故意伤害致死案有着微妙的关联。经过缜密侦查和审问,与命案有关的四个年轻人渐渐浮出水面。与此同时,诡异命案再次发生,案情愈发扑朔迷离……
人性诡谲,在阴暗的心理动机支配下,每个人都在说谎。抽丝剥茧,面具背后仍有面具,案件环环相扣,惊天逆转。是命运裹挟还是脱逃诡计?这一切是否就是最终的真相?
|
| 關於作者: |
|
梁雨山 八〇后青年作家,河南驻马店人。曾在《北京文学》《莽原》等文学期刊发表作品,已出版长篇小说《黑名单》。从事多年警务工作,近年致力于刑侦小说创作。
|
| 目錄:
|
目录
001 一 告别
029 二 命案
041 三 追凶
119 四 审讯
152 五 鬼节
208 六 罪与罚
260 七 雨雪霏霏
|
| 內容試閱:
|
一
告
别
1
河水噙住河床,吞咽着泥沙,向东流去。
有的河段,水面宽阔,草木茂盛,弥漫着轻纱样的薄雾;有的河段,水流会形成大漏斗状的漩涡,路过的漂浮物统统被它囫囵
吞掉。
这条河在不同河段,当地居民对它的称谓不尽相同,老河、后河、南河都是它。地图上叫洪河,与淮河相汇。
带着潮湿的风,带着腥鲜的水土,带着未知的希望,大河心无旁骛,穿越森林,绕过伏牛山的余脉,继续向前。
流经蚌城那块广袤的平原时,它的脚步放缓。
堤岸两边人们忙着冬播,这一年的麦子比往年种得早,他们急等青苗出土,好多得些补偿。这是他们当前的头等大事,而那些少不更事的年轻人才不关心这个。
此刻,最后一拨迁徙的白鹭在天空盘旋,英子、邓光和晶晶说笑着在那座挂有“危桥”警示牌的桥上等人,没有谁意识到这将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下午。
他们不知道危桥很快会被炸掉,新的大桥将建起来。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村庄很快将在地图上消失,大湾新区将成为蚌城耀眼的
新城。
报纸和电视台鼓捣得有一阵子了,据说这是蚌城最大的地产开发项目。
大湾新区拆迁办已经成立,他们的担子很重,既要满足群众利益诉求,又要摆平违法违章建筑。他们拍着胸脯向上头保证,决不给市里添麻烦。
决不。
大湾新区被大河湾包围,是块风水宝地,许多人满怀憧憬。
大河湾处,河道变窄,水流湍急,白浪激溅,拍出哗哗的水声。
水流带动气流,形成呼呼的河风。河风裹挟着水烟翻过大堤,舔舐着阴郁天空下那行将逝去的村庄。
洪河从此由蚌城的“护城河”变成“内河”,两条河(另一条是清河)自西向东穿城而过,两条主干大道贯通南北,蚌城由此形成大“井”字形的城市格局。过不了几年,人们将忘记这些村庄,忘记这块古老的庄稼地,还有那座骨头皴裂的危桥。
桥墩霉黑,布满虫洞的危桥。
废弃的危桥。
他们仨就在那座危桥上等另一个年轻人。
离河湾不远,有片沼泽地,是旧河道形成的,它将被改造成风景优美的湿地公园,从丑小鸭变成金凤凰;湾区内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拆迁的村庄已经敲定。
这些事儿的风声天生是给人走漏的。
早在他们敲定之前,村子里便竞相扩建房舍,家家户户做起“拆迁拆迁,一步登天”的梦。
早在他们敲定之前,地产商便着手抢地了。五行上说“火生土,土生金”,火怎么生土他们不知道,但土生金他们知道那一点不假。等着瞧吧,他们有能耐把房价炒到天上;银行要分一杯羹,非法集资团伙不会缺席,主管事的家伙会插上一杠子,街头的打手混混们也将在关键的时候派上用场。
大河在拐弯之后,慢慢调回方向,划出一个不对称的大S形再次向东流去。而这片土地像日出日落一样平凡的命运永远结
束了。
2
英子是第一个来到危桥的。
通常在星期天下午,英子会先到父亲的修理铺,戴上那种加密的棉纱线手套,帮一会儿忙。都是些琐碎的事,给父亲找一把八英寸的活口扳手、及时拿着一颗螺丝钉而不必让父亲用牙叼着、打开电源给轮胎充气、把未用完的焊条放到盒子里,或者往父亲那个被茶碱蚀成褐色的七百五十毫升的塑料太空杯里倒满开水,诸如此类。母亲忙于家务,还要管理田间的庄稼。哥哥好吃懒做又爱面子,他不止一次对她说,父亲灰头土脸的修理铺常常让他在朋友面前难堪。英子喜欢各种形状的金属配件以及混合着机械润滑油的那种味道。她曾经考虑过她将来也许会成为一名机修专家。帮一阵儿忙,英子再赶去几里外的公交站台,坐上公交车进城上学。
但是近来不一样了,修理铺的生意越来越冷清。人们不再关心他们的农用机车有没有毛病、要不要修一修,至少眼下它们已无用武之地。父亲也开始不待见他的老本行,五金工具胡乱丢放一地,补胎胶片用完了也不进货,有时候干脆关门睡大觉。
修理铺就在胡同口对面的大路边上,英子出来的时候看见父亲正修理一辆自行车,头发蓬松着,额角上有一道墨色的机油灰。
父亲脸上总有一道机油灰,不在额角,便在下巴,或者在脸颊上。那样子很像刚刚被洗劫过。
“今天需要帮忙吗,爸?”英子问道。
“没什么活儿,去上学吧。”父亲抬头看看女儿,又说,“今天去恁早。”
“我和晶晶约好了的。”英子说。
“路上小心点。”父亲又埋头工作了。
英子只说了一半,因为约好了的还有邓光和程凯。她走出村子没有发现他们俩的踪影。她和程凯家一条胡同,前后隔一户,在西塘埂东头;邓光家在西塘埂西头。她不知道他们俩是不是出发了,她更不知道西塘埂村将要发生的事。
在英子的一生中,她常常回忆起拆迁之前的西塘,童年的西塘,初恋中的西塘。在回忆中她也会看看这天下午的天空——初冬阴冷的暮云笼罩着村庄,她背上书包去上学,父亲告诉她路上小心点。她也终将看透西塘的那些人和事。
第二个到达危桥的是邓光。
他一手拎着书包,一手抿着头发。他刚刚十五岁,刚刚成为坏小子,欢得像一只周岁狗,无须为食物操心,还没有体会过一毛钱的人间疾苦,狂妄到以为只要自己龇龇牙就能搞定全世界。
“你一个人,程凯呢?”英子问。
“不知道,可能跟晶晶在一起吧。”邓光把书包放在桥墩上。
“你没有去找他?”英子嘴角露出一朵微笑。
“没有。”邓光有点垂头丧气。
自从上次约会被发现之后,英子的父亲严禁英子跟邓光来往,他警告邓光要是再接近他女儿就打断他的腿。
“你连那条胡同也不敢去啦?”英子笑道。
“我不是不敢去那条胡同,我是怕变成一级残废。”邓光愤愤不平地说。
“你还斤斤计较了。”英子说。
“我来时看见王老六在你爸的修理铺里。”邓光说。
“怎么了?”英子的声音像花瓣一样温柔。
“你老爸居然在鼓捣摩托车,就是王老六那辆‘本田125’,排气筒至少烂了十八个窟窿。”
“他最近生意不大好。”
“我以为他除了修农用车别的什么也不会呢,其实我很怀疑他到底能不能修那些洋玩意儿。”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爸呀?”
“我是说你爸不喜欢洋玩意儿,他不是经常骂那些染黄头发、穿超短裤的年轻人狂浪得像外国人嘛。”
“所以你应该把头发染回来。”
“我凭什么染回来——那边,”邓光指着不远处,“林晶晶来了,凯哥呢?”
这时候林晶晶也看见他们俩,远远地朝他们挥了挥手。晶晶走到桥头,邓光问:“他呢?”
“我正想问你呢。”晶晶说。
“老七今天怎么啦?”邓光说着捡起一颗蟹壳色的鹅卵石。
“这是他的老毛病了。”晶晶说。
“毛病不少呢。”邓光拿鹅卵石嗒嗒嗒地磕着桥栏杆。
邓光小程凯两岁,邓光读小学五年级时程凯已经上初中了,因为程凯七年级、八年级连续留级,他们才成为同班同学。邓光曾经鼓励程凯九年级继续留级,这样就能拿双份毕业证了。程凯不爱说话,也不爱写字,考试常常交白卷。他出生时体重七斤,诨名便叫作“七斤”,邓光有时叫他“老七”,人称“七少”那是后来的事了。
三个人在桥上等了个把小时,程凯依旧不见人影。
“什么事都得慢半拍。”邓光开始埋怨。
“还不到四点,你急什么呢?”英子背靠桥栏,手里捻着一朵黄花地丁。
“当然,凯哥打架决不含糊,我对凯哥的身手佩服得五体投地。”邓光说,“他只用了一拳,就把‘龅奎’放倒了。”
龅奎本名叫朱一奎,是兴业路菜市场一位卖了二十年干货的老板的儿子,长了两颗龅牙,人称“龅奎”。邓光认为这个绰号完全对得起他。邓光刚到十一中那会儿,龅奎已经是一名八年级的大个子男生,除了打架斗殴,无所事事。他那帮学渣的带头大哥叫彭乐乐,江湖人称“乐乐哥”,因为加入他们要喝鸡血酒,大家便叫他们“鸡血党”。他们自己叫“兄弟会”。一名上了年纪的历史老师经常把他们误称为“同盟会”。那个时期蚌城十一中的恶名声多半是“鸡血党”这帮家伙打出来的。
“听说龅奎喝鸡血酒时吐了?”晶晶问。
“酒里鸡血加太多了,一碗血酒下去,鸡血犯了胃气,龅奎的咽喉瞬间变成了喷头。”邓光说。
“听起来好恶心。”英子说。
“你喝起来会更恶心。”邓光说。
龅奎是他们在十一中的死对头,邓光曾经被他揍成“熊猫眼”,是程凯为他报了一箭之仇。那天下午大扫除,他们把龅奎堵在厕所里,厕所里被偷偷抽烟的烟民弄得乌烟瘴气。程凯拨开云雾,一拳打在龅奎软肋上,龅奎捂着肚子、背靠廊柱、瘫坐在污迹斑斑的水泥地坪上,额头上直冒冷汗。邓光狠狠踹了他几脚。那是他第一次打架,荷尔蒙像公牛一样在他血液里鼓荡。他还记得龅奎的头枕在便池沿上,头发沾染了尿液。
“我可不想让这场电影泡汤。”邓光说。
他们准备去看五点那场电影。邓光看过盗版VCD,繁体字幕,粤语配音,看不懂,也听不清,人脸像打了“马赛克”一样。
晶晶用大拇指拨拉了一下自己的三星手机滑盖,再次给程凯打手机,依然无人接听。
“不会是怕买单,躲了吧?”晶晶说。
“他兜里从来不缺那点零花钱。”邓光说,“继续给他打电话。”
“算了,爱来不来。”晶晶趴在桥栏上,望着桥下的流水。
“凯哥不会放鸽子的。”英子安慰道。
晶晶掏出一包绿箭薄荷糖,给英子和邓光分发。
“拖拖拉拉,时间到他那儿至少打五折。”邓光叹了口气,一松手,那颗蟹壳色的石头掉进河里,发出咕咚的声响。
荒芜的桥面上长满车前子和蓬草,只有一条光秃秃的小道,桥身遍布青苔。湿凉的河风带着沼泽地淤泥的气味吹过危桥,吹起他们乌黑发亮的头发。他们等着程凯,等着看五点那场电影,而那场电影却不会在那天下午等他们。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终其一生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再去看那部影史上里程碑式的经典电影。
这时候,一位六十多岁的老男人骑着一辆老式自行车来到桥上,自行车后座两边挂着带格的铁皮箱,锈迹斑斑,不时颠簸出稀里哗啦的声音。
这声音为方圆几十里的人们所熟悉。
这声音不止一次提醒他们,家里有没有锅碗瓢盆需要锔补、有没有铁器需要打磨、要不要买一把剪子或者一把菜刀什么的。
这锔匠的手艺不错,人品也不赖,你买他的东西,他免费给你磨刀磨剪子。
这活儿他干了一辈子,没有半点干一行烦一行的意思。年轻人无论如何不理解,老郭这个营生到现在还能赚几个钱。
老郭把自行车扎在桥上,脱去浸满油污的深蓝色罩衣,叠好,放进车前篓里。然后一提屁股,坐在桥栏上。
“郭老板,生意怎么样?”邓光问道。
“到处是拆房子搬家的,西塘还有人打架,实在办不成业务。”郭老板说。
“该退休啦,现在谁还锔锅。”邓光道。
“不干这行,还能干啥呢。”郭老板挠了挠头顶的白发。
“其实,你可以转型升级开个杂货店嘛,比锔锅赚钱多了。”邓光掏出芒果牌香烟,给郭老板发了一支。
“唉,我这辈子没当大老板的命。”郭老板苦楚着脸说。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邓光点上一支烟,嘴一嘬吐了个烟圈。
英子发现,“光棍”近来爱装出一副老江湖的样子。晶晶笑着拍拍英子的肩膀,悄悄说了句什么。
老郭抽完烟,在水泥栏杆上蹭灭烟头,然后轻轻跳下来,骑上自行车稀里哗啦地走了,出了桥头,便习惯性地吆喝起来——“锔锅锔盆磨刀磨剪子嘞”。他行至公路上,那铿锵悠扬的吆喝声依然在大河两岸回荡,像一句古戏词的唱腔似的。
“刚才老郭好像说西塘有人打架,办不成业务。”邓光说。
“他那也叫业务啊。”晶晶鄙夷道。
“是谁打架,你们看见了吗?”邓光怀疑是不是凯哥又跟人打架了。
“你刚才怎么不问问郭师傅呢?”英子说。
“刚才没想起来。”邓光说,“你出来时,看没看见凯哥?”
英子摇摇头,“我没看见他,我出来的时候他家大门关着。”
“我来时路过荒坡陆村,看见十几辆大车,运了很多砖渣,他们正在把那片荷塘填起来,他们到底要干什么?”邓光说。
第一章
1
5 月 15 日。长假过后的第一个周六。上海市区气温陡高,阳光饱满。
徐家汇的汇洋商厦里人流如梭。下午 3 点 10 分左右,张约和徐鸣之已经出现在中央大厅,向咖啡吧走来。(据 6 号服务生回忆,应该是这个 时间。)尽管约定的时间是 3 点 30 分,还有足足 20 分钟。 两人的手里都没有购物袋。他们也许是约了提前在商厦的东门或南门见面,本来想顺便先逛逛楼上的商铺,结果大家都没什么兴致, 就直接来了约定地点。也许,他们本来就是从同一个住处而来,张约 或徐鸣之的公寓,起床之后,吃了早午餐,看了一会儿电视,心神不宁, 彼此谁也没办法安抚谁,于是干脆决定早些出门赴约。张约 35 岁,大江集成电路株式会社的高级工程师。如果不是今天 的表情,他应该是看上去比较开朗的类型,长方脸,眉毛架眼镜,头 发剪得很短。穿着不规则条纹的灰色 T 恤衫,一双运动鞋。175 厘米的中等身材,还没有发胖。他一边向咖啡座走近,一边不停地环视四周, 以致错过了咖啡吧的入口,又不得不折回来。
徐鸣之 30 岁,《新申晚报》的副刊编辑。身材修长挺拔,忽略鞋跟应该也有 168 厘米以上,五官虽算不上漂亮,但借着出奇白皙的皮肤, 显出一种特别的清秀。苹果绿的大领针织衫,很衬她的肤色,扎着马尾, 修身长裤,高跟鞋。与张约相比,她似乎是细致打扮过,脸上有得体 的淡妆。她挽着灰色的手袋,走在张约旁边,几次抬起右手,似乎是 想挽住他的胳膊,又被他手肘僵硬的姿态提醒,再次放下。
这家商厦的大厅特别宽阔,像是一整个街区似的。我也在里面逛 过几次,如果绕一圈,走得不快的话,足足需要一刻钟,而且高度直 达 9 层楼的穹顶。在最热闹的地段有这么大的空间,着实让人感觉气 派和心情开朗。
坐在大厅中央咖啡吧软绵绵的座位上,抬起头,可以望见自动扶 梯在 9 个楼层中穿行,还没摘尽的彩色纸带和亮闪闪的纸花从天穹中 垂下来。这时候,最好是微微眯上眼睛,因为商厦的穹顶是全透明的。 水流般的阳光正充盈着大厅的每一寸空间,尤其是正对天顶的这片咖 啡吧。好不容易熬过了上海阴雨绵绵的季节,谁不愿意在休息日的下午, 坐在这里尽情地沐浴太阳、发呆、做梦呢。
如果不是正好睡了个午觉,这个时候,也许我也乘着地铁来到徐 家汇,带上一本推理小说,在几乎满座的咖啡吧里占一个座位,晒着 太阳,翻着书,啜着卡布奇诺的奶泡。也许,一抬眼间,我就亲眼看 到张约和徐鸣之向我走过来。也许我刚好占了唯一剩下的位置,他们 只能怏怏地站在一边,等待约见他们的人。也许这样的话,后面的事情就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或者任何一位在座的年轻女士身上。 可是我不在那里。所以,当他们向咖啡座走过来的时候,发现在最靠近外围的地方,还剩下最后一个空着的座位。一个小方桌,两个 面对面的沙发座。
他们先是各自坐了一个沙发座,因为沙发座有点窄,坐一个人略 嫌宽敞,坐两个人又嫌拥挤。他们当时都心不在焉,张约在看周围, 而徐鸣之在留意着张约的表情。虽然座位窄,两个人下意识地就这么 坐下了。坐了两三分钟,据说是服务生们已经看见他们,还没来得及 把冰水和饮料单送过来之前,也许是徐鸣之发觉不对劲,提醒张约说 : “可是,这样的话……她来了坐在哪里呢?”
张约于是站起身。徐鸣之往沙发里面让了让,张约挤着她坐下来。 这沙发座确实太窄了,也许根本就是为一个人设计的。第二个人要是 想让整个臀部坐进座位里,两个人就不仅是手肘挨着手肘,简直是两 个身体都紧紧贴在一起,分外亲热的样子。
这时候,6 号服务生正好把饮料单递到张约手上,这是一个足足 八开大的褐色皮面本子。张约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这么挤,翻也不好 翻。”又重新站起来,坐回徐鸣之对面去。
徐鸣之说 :“这样她来了怎么坐?跟你挤在一起,还是跟我挤在一 起?”恼怒的片刻,她白皙的脸上升起一片红晕。6 号服务生正在欣 赏着这么细白的好皮肤,而这文静又纤弱的女人,忽然地这一下发作, 让他也有些尴尬了。好在张约似乎料到她今天会有这么一下子,说“:别 紧张,至于这样吗?”他站起来,又挤坐到她的身边,还故意往里再 挤紧一点,一只手放在她的手背上,用力握了握,对她露出了一个足以让她安心的微笑。 徐鸣之点了一杯热的低因蓝山。张约要了杯冰摩卡。 之后,因为阳光过于丰盛,连这位最勤勉的服务生都昏昏欲睡了一段时间。他只记得服务台接到过一个电话,说是找“张约先生”。他 在各个座位间依次询问了好一阵,最后在徐鸣之诧异仰视的目光中, 这个戴眉毛架眼镜的摩登男人起身走到吧台接了电话,但是电话已经 挂断了。
已经是3点40分。张约拿了几本咖啡吧的免费杂志在翻阅,只坐 了大半个臀部,斜着身体,半个背对着徐鸣之。在约定时间快要到达 和已经到达的那一阵,他曾经表现得有些坐立不安,左顾右盼,现在 他似乎已经拿定主意要让自己休息一下,整个人都钻进了杂志里,该 来的、迟来的或不来的人,爱来不来吧。
徐鸣之坐在张约的内侧,虽然被他半个背对着,她却并不觉得生气, 因为这是一个保护她的姿态。如果约他们的人走进咖啡吧,肯定是从 张约的那一侧朝他们走过来。张约会第一个看见,并起身跟来人打招呼。 那时候徐鸣之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所以她的状态也很放松。
她先是靠在沙发里,懒洋洋地眯着眼睛,望着周围发了一会儿呆。 有人坐在远处的大理石台阶上读书。有人在后方立柱边上的投币电话 亭打电话。更多的人匆匆埋头走过,即使休闲,也保持着他们平时工 作的一贯焦虑。有的人还冒失地踢倒了她左侧的花架。花架是当作咖 啡吧围栏用的,其实就是一条松木制作的狭长花槽,才 15 厘米宽,紧 贴着她这一侧的咖啡座,杂色石竹种得还不及她的肩膀。所以,那些 路人踢倒花架,其实就跟直接踢到她的座位差不多。
她发呆得无趣了,就掏出手机开始发短信。 “今天是你打电话到咖啡吧找张约吗?”她发送给她的闺蜜任锦然。
因为今天的约见她只告诉过任锦然,也许是她故意跟他们开玩笑也说 不定。
很快,短信回来 :“没有呀。你们见着了吗?谈得怎么样?” 她按着键盘打字道 :“别提了,人都还没来呢,我们很早就来了,一直等到现在……” 忽然间,屏幕上的光线被挡住了一瞬,她感觉到左边脸颊一阵冰凉,从耳根一直到嘴角,随即是横亘了半张脸的痛楚。她细细地叫了一声, 扔下手机,摸自己的脸颊,摸到了满手火热的液体,还有更多的正蜿 蜒流淌下来,沿着她的脖颈,浸入她的前胸、她的针织衫,有些就直 接滴到她的修身长裤上。
前几秒钟,极大的疑惑让她处于一种惊人的平静。她呆呆看着自 己满是鲜血的手掌、米色长裤上殷红的点点滴滴。直到张约惊慌失措 地推开小方桌,转到她正面,用恐慌的眼神直愣愣地看着她的脸颊时, 她猛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尖声地大叫起来,一声连着一声,攥着一 手浓稠的血,瞪大着眼睛,连哭都忘记了。
从沾满血点的手机屏幕的倒影中,她看见自己左边的脸颊上多了 一道骇人的口子,从耳根一直延伸到嘴角,现在它正像一片嘴唇那样 一点点翻张开来,血还在往下流。
据 6 号服务生说,当时的一幕,恐怕任何见过一眼的人都难以忘记。
前 1 分钟,还是姣好白净的美人,而且她似乎也知道自己的出色之处,即使只是随随便便靠坐着发一条短信,也显出几分骄矜。可是后 1 分钟呢,她方才所有的长处,都成了这个伤口最恐怖的衬托。请你想象 一下,小半身殷红的血,在特别白皙的肌肤和苹果绿针织衫的映衬下, 是怎样地鲜艳,乃至妖冶,而那个足足占了半张脸的残暴作品,在她 漂亮的修长身段上,又是怎样地让人震惊。张约的两只手一高一低举在半空,也许是想要用一些温柔的动作 抚慰她,或是想做什么救护的措施,比如拿起桌上纸巾替她按住伤口 止血。可是举高的右手只是绕了一个弧线,绕开徐鸣之鲜血淋漓的左 边身体,飞快地在她右肩上拍了拍,就收了回来。这个时候,人们才想到,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回想起来,就是眨 眼的瞬间,她的脸就忽然涌出鲜血,咖啡吧里没人走动,周围大厅里 的行人步伐如常。在这么多双眼睛面前,阳光是如此充沛而安宁,就 连一只苍蝇飞过时翅膀的振动都躲闪不过,可是,包括张约在内,谁 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瓦西里的口头禅,每当女儿哭鼻子时就会哄她—— “不要难过,不要哭。会有的,都会有的,面包会有的。”
2
无涯网是一个很小的网站。但是,编辑们的勤奋程度绝对值得支持, 特别制作了一个“‘5·15’汇洋商厦毁容案”的专题。这样一起人身 伤害事件,没有大规模的恶性效应,不涉及名人要员,转帖社会新闻, 短短百字不足。结果编辑们居然找到了 6 号服务生的博客链接,还加 了一个网络聊天采访。由此引来了一批自称当时在场的“目击者”,继续丰富内容。更有好事者搜罗信息,把受害者和男伴的私人资讯都查 得一清二楚。短短 10 天,细节已经展示得如此详尽,而且图文并茂。如果福尔 摩斯在这个世纪推理破案,简直都不需要去现场,光坐在液晶屏幕前, 每天等着看网络新闻就足够了。
我不是福尔摩斯,我只是一个患有轻微网络依赖症的女性网民。 或者正式一点地介绍,我叫周游,29 岁,标准的“剩女”一枚,还有 1 年就将正式晋升“败犬女”的行列。可是说实话,目前我还完 全没有想好,自己究竟想要过怎样的人生。是在职场上掘金扬名,过着一种让众人羡慕的生活,还是让自己好好爱上一个人。
所以,我这个华东政法法律系毕业的硕士生,无心去争当律师事 务所的合伙人,宁愿窝在法务部,做一个小小的法务。而且我懒得相 亲已经很多年。不但懒得相亲,我还懒得饭局聚会、卡拉 OK、BBQ 和 新年派对,以及一切与人交际的活动。
平时上班的时候,穿得领子笔挺、皮鞋死硬,跟人谈这个合同、 那个谈判的,已经快要了我的命。所以不用上班的时候,我最愿意穿 着粉红色的全棉运动服,把长发随便夹在头顶,披着毯子,窝在沙发 里看卫星电视,叫一个比萨外卖过一整天。高兴的时候,我也会一个 人出去逛逛,当然依然是恬不知耻地穿着运动服和球鞋,没准头发也 没想到放下来梳一梳。就这样邋遢地踱到门口的电影院,买票看一场 电影,或者大摇大摆走进饭店,旁若无人地叫一桌菜一个人吃。如果 没有意外的话,我打算这样过到老死。
因为我这个状态,何樱姐不知道跟我唠叨了多少回。“败犬女”这个词语,就是她从杂志封面的大标题上指给我看的,旨在引起我对这 一悲惨前景的重视。
当时我对着这三个大字直愣愣看了 5 秒钟,然后告诉自己,既然 出现了这个新造词,就证明了这已经是一种公众现象,我不算变态。 既然它还是一个舶来语,就更证明了这早已是一种国际化的潮流。
何樱 33 岁,如果按“败犬”的标准来划分,她就是一只典型的“胜 犬”。26 岁就顺利嫁给了第一个相亲对象。现在儿子也有 5 岁了。而且 她还急于把她的成功经验在我身上发扬光大。
每当她试图给我安排相亲时,我都搬出一套“办公室哲学”来搪 塞她说——何樱姐,你是法务部的经理,是我的顶头上司,所以人人 都可以给我介绍对象,唯独你不可以。因为你介绍的对象,如果我觉 得不合适,那就是忤逆了顶头上司的判断,有违办公室伦常。如果我 们好上了,将来事事他都拿你来压我,岂不是更加违背了家庭伦常?
何樱听得眼睛眨巴眨巴的,半天迸出一句 :“游游,你要是有机会 参加庭审辩论,肯定能发挥得不错。”
对我而言,每个工作日里最大的享受,就是在办公时间里偷偷打 开无涯网,先浏览一会儿新闻,胡思乱想,然后点击无涯社区,再点 击其中一个黑天使的图标,进入论坛。
努力念了 18 年书,又不迟到早退地工作了 5 年,忽然间,觉得人生不过如此而已。不知道正在读这些字句的你,是否也有过同样的感 受?莫名其妙什么都不想做了,就是想在下一分钟里,有谁能来陪着自己,哪怕在他怀里靠一会儿也好,可是,偏偏只有自己,想到谈恋爱又嫌麻烦。于是只能无聊地不断点开网页。
还有,无聊到极点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在搜索引擎里 输入自己的名字?“周游”,那一天,我就这么把自己的名字打进了 Google 的方框里,然后回车。23651 条搜索结果,没什么可惊讶的,怪 只怪我的名字就是一个词语,搜出来的也无非是一些“周游世界”之 类的网页。就在我翻到第 35 页、点击开第 523 条的时候,跳出了一个 页面,上面写着 :
周游,不知道有一天,你会不会看见这个帖子。写下这个帖子,是因为这个论坛的名字,它就好像是我心里一个重要的声音,让我第一次发现这里以后,又不知不 觉地逛回来了。
你知不知道,我在 MSN 上面不断地改签名,就是想让你知道我的心情。
你知不知道,我在你家电影院门口排队买票,排到了,又站到队伍后面去重新排,就是为了能遇见你正好经过,我 就可以对你说,这么巧,不如我们一起看场电影吧。
你知不知道,每次我看见你一边走路、一边皱眉头的时候,我都在想,如果有我陪着你,就不会让你有任何皱眉头 的机会。
你也许永远也看不到这个帖子,看不到我在这里对你说,周游,我是多么希望,由我来给你幸福。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看到了这些字句,我想,这么说也许有些夸张,可是我真的,死都会瞑目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