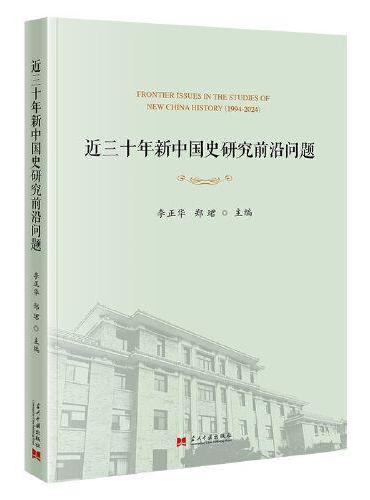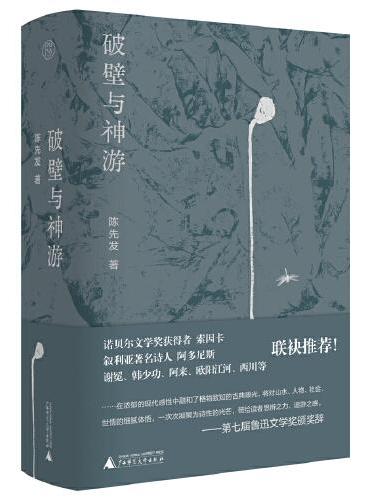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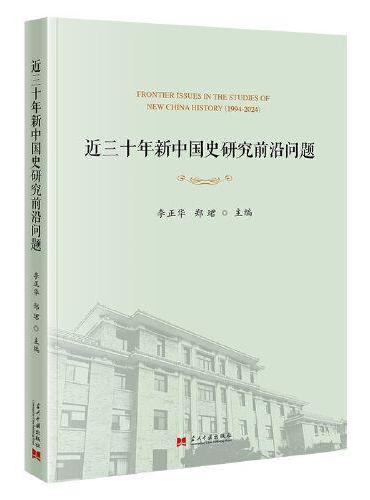
《
近三十年新中国史研究前沿问题
》
售價:NT$
500.0

《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
售價:NT$
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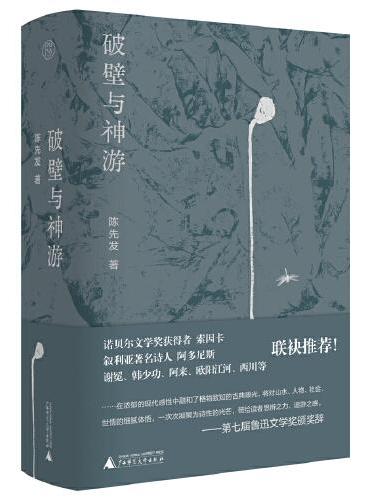
《
纯粹·破壁与神游
》
售價:NT$
418.0

《
春秋大义:中国传统语境下的皇权与学术(新版)
》
售價:NT$
449.0

《
女人们的谈话(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提名、最佳改编剧本奖 原著!)
》
售價:NT$
286.0

《
忧郁的秩序:亚洲移民与边境管控的全球化(共域世界史)
》
售價:NT$
653.0

《
一周一堂经济学课: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
》
售價:NT$
500.0

《
慢性胃炎的中医研究 胃
》
售價:NT$
3050.0
|
| 編輯推薦: |
“医学悬疑女王”苔丝˙格里森美剧《妙女神探》系列震撼新作,令人毛骨悚然的新角色登场!
警探、法医双女主强强联手,旧案新案错综复杂,惊险刺激,反转不断。
离奇死亡的恐怖片制片人,深陷泥潭的儿童日间托管中心。骇人的毁尸方式背后,是黑暗而残忍的秘密。
|
| 內容簡介: |
年轻的恐怖电影制片人躺在床上,姿态有种诡异的安详。她的手臂放在身体两侧,一袭黑衣,衬托得脸色如幽灵般苍白。她的耳朵上戴了好几个金耳钉,右眉毛上还穿了个金光闪闪的眉环。不过引起法医莫拉注意的,是死者眉毛下方。
她的两只眼窝都是空的,眼球被挖掉,只剩两个血淋淋的空洞。
而她摊开的手掌里,放着两枚令人汗毛倒竖的球状物。
平安夜,一个男人躺在码头边,穿着讲究,面容俊秀,像是商业精英。然而他身上插着三支箭,插得极深,只有一半的箭杆露在外面。
接连发生的凶杀案,匪夷所思的毁尸方式,扑朔迷离的神秘暗示。警探简˙里佐利和法医莫拉˙艾尔斯再次合作!
有时候,虚构的故事才能讲述真实。
|
| 關於作者: |
作者:苔丝˙格里森
美籍华裔女作家。一九七五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人类学专业。一九七九年,取得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博士学位。在夏威夷檀香山担任内科医生行医多年,后辞职成为职业作家。
一九九五年,苔丝˙格里森出版了第一本医疗惊悚小说《宰割》,迅速跃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前列。二〇〇一年,她的第一本犯罪惊悚小说《外科医生》甫一面世便获得瑞塔文学奖。波士顿警察局凶案组女警简˙里佐利作为配角首度登场,在随后的十二本小说里,她作为核心人物,与女法医莫拉·艾尔斯搭档冒险,共同探案。苔丝˙格里森被《出版人周刊》誉为“医学悬疑女王”,“里佐利与艾尔斯系列”为她的代表作,后被改编为美剧《妙女神探》,受到许多观众的喜爱。
译者:王冉
兼职译者,韩语专业,后来读了英文翻硕笔译。比较喜欢悬疑恐怖小说,入手第一本就是迪弗,觉得蛮奇妙的。译有杰弗里˙迪弗著作《冷月》《致命雕刻》。
|
| 目錄:
|
系列作:
《学徒》,新星出版社 / 2023-4;
《替身》,新星出版社 / 2023-5;
《消失》,新星出版社 / 2023-7。
欧美刑侦探案:
《天使的号角》,新星出版社 / 2023-1;
《罪恶捕手》,文汇出版社 / 2022-7;
《寒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2021-5;
《未完成的手稿》,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2022-10;
《夏日无声》,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2022-7。
惊险刺激悬案,真实感:
《黑色大丽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2022-7;
《没药花园》,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2019-10;
《李淼罪案故事》,中国友谊出版社 / 2021-9;
《不可能犯罪诊断书》,湖南文艺出版社 / 2023-2。
|
| 內容試閱:
|
1
我在七岁那年第一次体会到,在葬礼中悲伤落泪是多么重要。那年夏天,叔祖父奥森去世了。他生前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臭烘烘的味道,混合了呛人的烟味、熏人的口臭,还有毫不掩饰的臭屁。叔祖父活着的时候,似乎从来都不知道有我这么个人,我也从来不理睬他,我们漠视对方的存在。因此对于他的死,我没有感到丝毫伤心,甚至不明白为什么要参加他的葬礼,不过我那时才七岁,对于这种事情还不能自己做主。那个闷热的午后,我身着黑色裙子坐在教堂的长椅上,百无聊赖地扭来扭去,浑身冒汗,心里想着为什么我不能像爸爸一样留在家里。爸爸当时断然拒绝参加葬礼,说他瞧不上叔祖父,若是假惺惺地来参加葬礼,还要装出哀恸的模样,那就是虚伪,他才不要这样做。我不懂“徐伟”是谁,不过我也不想做“徐伟”。但令人无奈的是,我还是来了,夹在母亲和西尔维娅姨妈中间,被迫听着人们对奥森叔祖父乏善可陈的一生啰唆而虚假的赞美。
“一个傲然自立的男人!对自己的爱好有着长足的热情!他多爱收集邮票啊!”
没有一个人提到他的口臭。
人们追念叔祖父的悼文冗长且乏味,为了给自己解闷,我开始研究坐在我前排长椅上那些人的脑袋。唐娜姑妈的帽子上沾了好多头屑。查理叔叔在打盹,头上的假发歪歪斜斜地滑到了一边,看上去像是一只棕色的大老鼠正顺着他的脑袋爬下来。看到这一幕,七岁的我表现得像所有正常的七岁女孩子一样——
在葬礼上笑出了声。
人们对此惊诧莫名,瞬间转头,皱着眉看过来。母亲难堪地低下头,修剪尖锐的五枚指甲深深地嵌进我的肉里,她悄声说道:“闭嘴!”
“可是他的头发要掉下来了!像只大耗子!”
母亲的指甲掐得更狠了:“我晚点儿再跟你聊!霍莉!”
回到家后,母亲并没有跟我聊什么,而是一通叫骂,还扇了我一巴掌。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明白了在葬礼上要怎么表现:你一定要忧郁地沉默不语,有时候还得哭出几滴眼泪来。
四年后,在母亲的葬礼上,我号啕大哭,涕泪不止,表现得极度伤心。我知道,这正是人们想要看到的。
但今天,在萨拉·巴斯塔拉什的葬礼上,我觉得不会有任何人苛求我为她哭丧,毕竟我上次见她还是在十多年前。我们是同学,她那时还叫萨拉·拜恩。就算在那时,我们走得也不近,所以她的死并没有真的触动我。实话说,我大老远来到纽波特出席她的葬礼不过是出于好奇。我想知道她是怎么死的,我需要知道。“天灾人祸啊!”教堂里的每个人都这么哀叹着。事故发生时萨拉的丈夫出城了,萨拉喝了点儿酒,随后睡着了,但是床头柜上的蜡烛没有熄。她葬身于一场意外的火灾。至少人们都是这样说的。
这也是我愿意相信的,她的死因。
纽波特的小教堂里挤满了人,来的都是萨拉这短暂的一生中遇到的朋友,其中大部分人我都没见过,包括萨拉的丈夫凯文。
若是场合不这么悲伤,他应该是个很迷人的男人,那种会让我想要撩拨一番的类型,不过今天他看起来已经崩溃了。这就是所谓的悲痛欲绝吗?
我转头环顾教堂,发现一个高中同学此时就坐在我身后,我记得她叫凯西。她的脸上长了很多雀斑,睫毛膏因为泪水晕成一团。教堂里的男男女女似乎都在哭,是因为女高音歌手唱的这首歌吧——来自贵格会古老神圣的赞美诗:《简单的礼物》。这首歌不管什么时候响起,总会引来人们的泪水。几乎在我看到凯西的瞬间,我们的目光就相遇了。她的眼中饱含泪水,晶莹而湿润,我的眼睛却是干爽的,冷淡而疏离。高中之后,我的变化很大,任她再怎么念旧,也不大可能会认出我,但她还是一直盯着我,仿佛中了邪。
我转回身,继续看向前方。
《简单的礼物》唱完了,我也和别人一样掉了几滴泪。
我站在吊唁者的队伍中,排队与往生者遗体进行道别。走到紧闭的棺材旁,我仔细地端详着萨拉的遗像,照片就放在过道旁边。她才二十六岁,比我小四岁。照片中的萨拉脸庞水嫩,少女般淡粉的脸颊上露出迷人的微笑,与我记忆中学生时代那个漂亮的金发女孩别无二致。那时的我几乎没有存在感,对他人来说,我就像一个虚幻的影子,从来不会被人注意到。而现在,我还鲜活地活在人间,可萨拉,漂亮可爱的小萨拉,却变成了一堆盒子里的骨灰。我猜旁人也是如此,他们看到萨拉的照片,想到的也都是烧焦的皮肉和焦黑的头骨吧。
队伍继续向前挪动,我向凯文表示了关切和安慰之情。他轻声回答着:“谢谢你能来。”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也不知道我是怎么认识萨拉的,但他能看到我脸颊上的泪痕,于是礼貌地握了握我的手。我为他的亡妻落了泪,这就是我的通行证。
我快步走出教堂,步入十一月的寒风中。我之所以这样迅速地离开,就是怕碰上凯西或是别的熟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在躲,尽量避免和他们碰面。
又或者说,是他们在躲着我。
现在才下午两点,虽然老板给我批了一整天的假,但我还是想先回办公室处理一下邮件和来电。我是一名营销公关,在“高才生传媒”工作,现在负责联络十几位作者的出版业务。我要安排每部作品的媒体宣传,还要寄发样书,写推销信。不过,在动身回波士顿之前,我必须先去一个地方。
我开车来到了萨拉家——或者说她曾经的家。现在,这里只剩下被烧得黑漆漆的断壁残垣。曾经围在房子前院花园外的白色尖桩篱笆已经七零八落,被消防队员从街上拖来的水管和梯子弄得东倒西歪。消防车赶到的时候,这里的火势应该已经很大了。
我下了车,走近废墟。空气里还残留着浓重的烟味。站在人行道上,我能看到埋在黑色废墟下的一道微弱反光,那是一台拥有不锈钢表层的冰箱。我大致看了看纽波特的这片街区,就能够推断出萨拉家的房子价值不菲。不知道她丈夫是做什么生意的,是富二代吗?我从来没那么好命。
阵阵冷风扫动落叶,从我鞋边吹过,沙沙作响。这枯叶的脆响让我想起二十年前的秋天,十岁的我走在树林里,脚下的落叶随着我的步伐发出嘎吱嘎吱的呻吟。那天的阴影依旧萦绕在我心中,久久未散。这就是我今天来到这里的原因。
我低头看了看废墟旁人们为萨拉设立的临时祭坛。那里摆放了许多花束,其中有枯萎的玫瑰、百合和康乃馨,都是众多深爱这位年轻女子的人留下的哀思。忽然,我发现了一抹绿色,那并不是其他花束里的配饰绿植,更像是被谁故意放在那里的,有些故作神秘地被掩藏在一堆花束下。
一片棕榈叶,象征着殉道身死的圣徒。
想到这里,我觉得脊背一阵发凉,立刻后退。我心如擂鼓地走向车子,听到身后有汽车驶近,转过头,看见一辆纽波特的巡逻警车缓缓开了过来。车窗摇上去了,我看不见里面警官的脸,但我能感觉到他经过时细细地盯着我看了好久。我转回身,躲进了车里。
我在车里坐了一会儿,等待心跳平静,手也不再发抖。再次看向萨拉家房子的废墟,我又一次想起六岁的萨拉,漂亮可爱的小萨拉·拜恩,蹦蹦跳跳地登上校车,坐在我前排的座椅上。那天下午校车上一共只有我们五个人。
现在只剩下四个人了。
“再见了,萨拉。”我喃喃低语道,而后启动车子,开回波士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