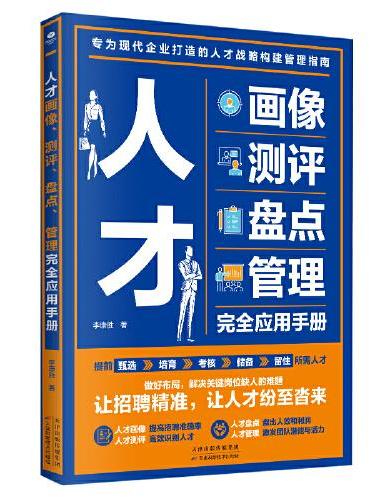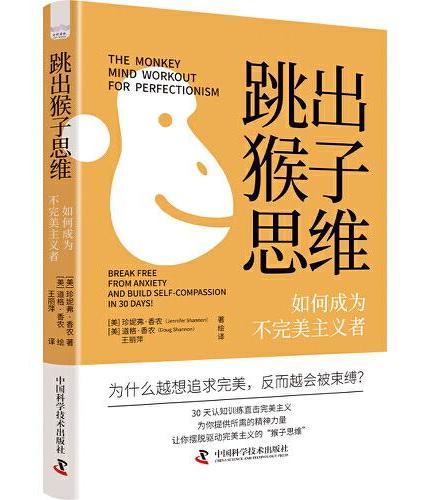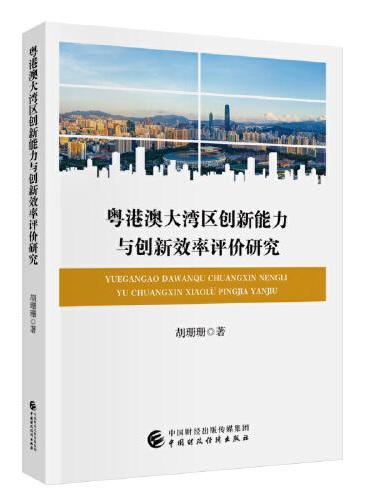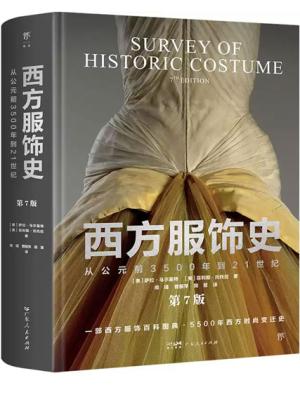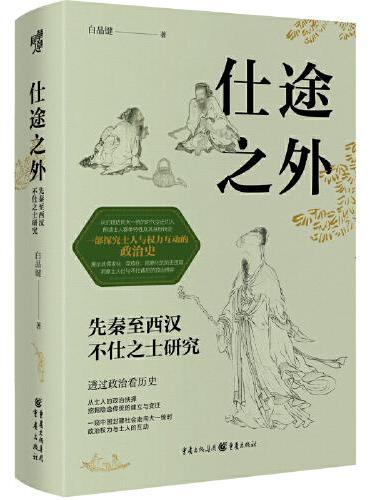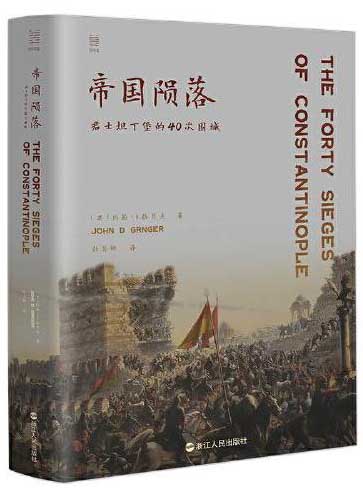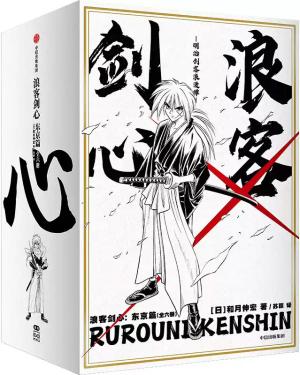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不止于判断:判断与决策学的发展史、方法学及判断理论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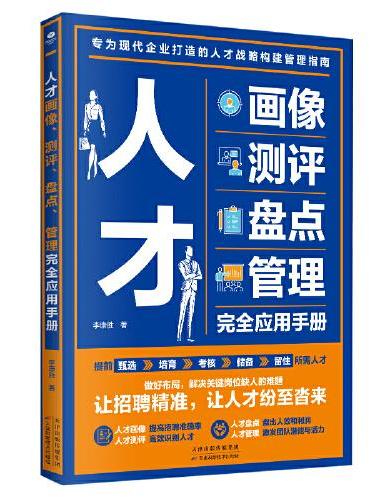
《
人才画像、测评、盘点、管理完全应用手册
》
售價:NT$
2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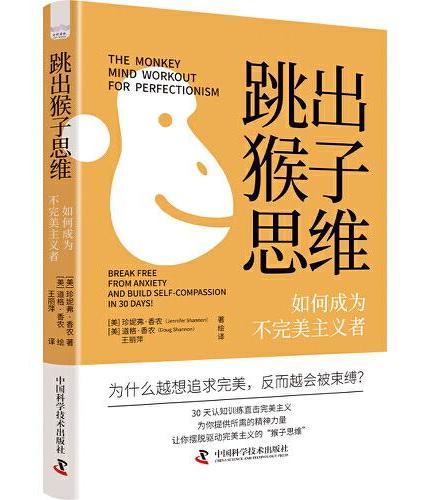
《
跳出猴子思维:如何成为不完美主义者(30天认知训练打破完美主义的困扰!实现从思维到行为的全面改变!)
》
售價:NT$
3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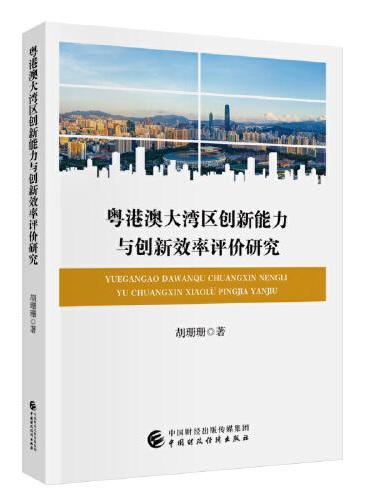
《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能力与创新效率评价研究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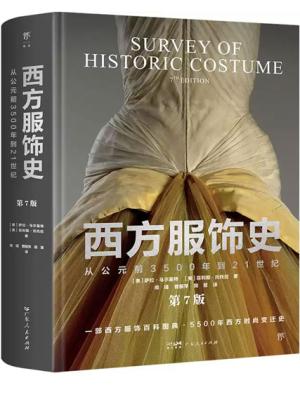
《
西方服饰史:从公元前3500年到21世纪(第7版,一部西方服饰百科图典。5500年时尚变迁史,装帧典雅,收藏珍品)
》
售價:NT$
20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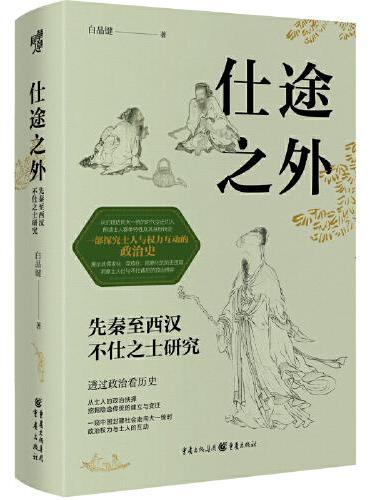
《
仕途之外:先秦至西汉不仕之士研究
》
售價:NT$
3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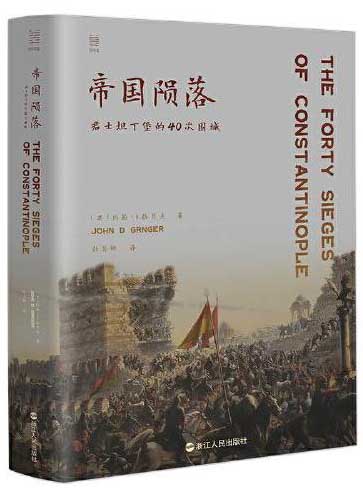
《
经纬度系列丛书·帝国陨落:君士坦丁堡的40次围城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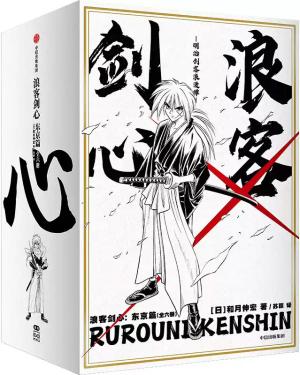
《
浪客剑心:东京篇(全6册)
》
售價:NT$
1163.0
|
| 編輯推薦: |
一个可持续的哲学之城以未来问题为对象,也总以未来问题来重新解释传统,而这是传统得以存活的唯一方式。在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里,传统先于未来,但在问题的时间顺序里,未来先于传统。不能被未来激活的传统终将死去。
未来世界将为科学和技术所定义,当代科学和技术倾向于以普遍相关性去理解万物并且系统化地控制万物,因此,未来世界的存在方式是万物的智能互联,存在论的基本问题将是关系和共在。
无论我们是否喜欢这种未来,思想只能接受未来,因此思想迫切需要视域革命和方法论革命,新的哲学问题将越来越具有世界性、共同性或跨文化性。
——赵汀阳
|
| 內容簡介: |
主体性是最具现代性的一个概念,几乎就是现代性本身。由笛卡尔发起端,康德总其成。其存在论单位是个人,还有若干的衍生形式,如国家、文化或文明,甚至异质于人类的新主体。
赵汀阳这本新著即是检讨现代世界以来,因为主体性的分立、扩张与争竞,而导致的个人主义、地缘政治及文化与文明冲突的诸多问题。他曾从政治哲学角度提出“天下体系”理论,以解决全球政治体系缺乏共识与合作的问题;本书则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提出“跨主体性”概念,即通过创造思想聚点和文化聚点,超越文明或文化冲突的边界,不仅在不同主体间形成“相互主体性”,而且要同时超越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局限性,从而建构一种能够超越主体性的独白话语并化解主体间无法协调一致的关系。
全书不仅从概念角度厘清何谓“跨主体性”,提出“文化边界”“新百科全书”与“综合文本”等新观念,而且对近期的热点话题,如外星文明、元宇宙、人工智能(GPT4)等高科技和未来世界是否会诞生异于人类并凌驾于其上的新主体做出了深入的分析与预判;与欧洲多位哲学同行就“天下体系” 的论辩,则是一个“跨主体性”的实践现场,理解与辩难纷呈,揭示了跨越文化边界的诸多困境与可能。
|
| 關於作者: |
|
赵汀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一级教授。主要代表作有《论可能生活》(1994)、《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2005)、《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2009)、《第一哲学的支点》(2013)、《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2016)、《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2016)、《四种分叉》(2017)、《历史·山水·渔樵》(2019)等。2023年三联书店将陆续出版“赵汀阳集”。
|
| 目錄:
|
前言:如何定义跨主体性?
第一部分:概念
1 跨文化聚点研究:文化边界,新百科全书与综合文本
2 关于跨文化和跨主体性的一个讨论
3 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
第二部分:争论
4 关于时间性和历史性:弗兰索瓦·阿赫托与赵汀阳对话
5柏林论辩:天下制度的存在论论证及疑问
6 全球正义如何可能:梅丽莎·威廉姆斯,莱纳·弗斯特,赵汀阳三人对话
第三部分:新主体
7 一个反存在的存在论
8 人工智能的自我意识何以可能?
9 最坏可能世界与“安全声明”——来自《三体》的问题
10 假如元宇宙成为一个存在论事件
11 GPT 提出的新问题
12 替人工智能着想
|
| 內容試閱:
|
前 言
如何定义跨主体性?
跨主体性(trans-subjectivity)是法国人类学家阿兰.乐比雄(Alain Le Pichon)提出的一个概念。他是欧洲跨文化研究院的创始人之一,另一位创始人是意大利的伟大作家和符号学家艾柯(Umberto Eco)。这个概念有着人类学背景,同时也是一个哲学概念。阿兰在制造概念方面有天才,他发明了“互观人类学”(reciprocal anthropology。旧译互惠人类学)、互动知识(reciprocal knowledge)和跨文化(transcultural)等概念,都很有想象力,但我倾向于认为其中最有潜力的还是跨主体性,也许是哲学偏好。
阿兰·乐比雄提出跨主体性的故事是这样的,我们经常一起讨论问题,10余年前有一次他说到很赞同我的天下体系理论,如果将来跨文化的政治能够成功的话,似乎应该就是天下体系了。然后他又说,那么,是否意味着,我们,各种文明,就因此能够形成一种“跨主体性”了呢?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新概念,请他给出定义或基本解释。阿兰思考良久,说,一个人类学家可以提出新概念,但不负责定义,那应该是哲学家负责干的事情(笑)。他反过来很认真地坚持要我为跨主体性做一个定义或接近于定义的基本解释。阿兰是个“作而不述”的人,喜欢出题胜过做题,我有点疑心他属于“灵知主义者”。总之,我同意做这道题,但可能有点过于自信了,至今也不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虽有推进,但还需要努力。跨主体性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在于触及当代发生的许多新问题,远远不止是文化间性,也触及技术或可能产生的新主体们,而复数的新主体将导致真实世界的概念发生改变。越想越发现跨主体性有一点像哥德巴赫猜想那种情况,看起来是对的,但要证明却很难。这个集子收集了我的一些相关思考,并非都是对跨主体性的直接解释,但与跨主体性的问题都有或远或近的相关性,以此向老朋友阿兰.乐比雄致敬。
要分析跨主体性的概念就会想到与主体性有关而区别于主体间性。关于这个问题,我和阿兰合著的《一神论的影子》有过不少讨论。主体性是人的一个存在论事实,几乎定义了人,但作为学术概念却是现代思想的发明。通常认为,笛卡尔的“我思”奠定了主体性概念的出发点,而康德建构了主体性概念的完整结构(也有不同意见,比如胡塞尔相信只有现象学才能够充分解释主体性)。主体性大概可以理解为一个具有认知主权和道德主权并具有自我意识的思想-行为终端,在理想状态下定义了人之为人的条件。可是,独立自主的主体性之间必定互相不理解、互相不同意甚至发生冲突,于是在主体间形成了对峙难题。阿兰对胡塞尔颇有研究,他说过,主体间性的问题化意味着主体间性需要进一步发展为跨主体性,否则主体间性就只是个社会事实却不是一个真正重要的问题了。显然,主体间除了有交流、对话、合作和互相理解的正面性,还有冲突、对立、战争和互相误解的负面性,这意味着,主体间性既是桥梁也是鸿沟,可以是善意也可以是敌意,可以是理解也可以是不理解。主体间性只是形成了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却不能保证能够消除互相隔阂的他者性、异己性甚至敌对性。主体间的难题就在于主体间性自身没有能力解开主体间的难题,就是说,主体间性不是自身问题的一个解。假如主体间问题存在一个解,那么,跨主体性就是主体间性的解——这是我的基本理解。
跨主体性的定位找到了,可是“跨”(trans-)的意思还是不明确,到底是意味着超越了主体性的局限性还是超越了主体间性的局限性,仍是个问题。我倾向于认为是“双超越”,即同时超越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局限性。接下来,如何实现这样的超越?以什么去超越?合理的想象是,跨主体性是一种建构性的关系,一种能够超越主体性的独白话语并且化解主体间互相不一致的关系。可是,如何建立这样的关系?说容易,做就难了。
按道理应该使用维特根斯坦式的“游戏分析”,这是分析意义、语境、条件的复合关系的最好方法。但有个特殊的困难,游戏分析的有效性一般基于分析概念的用法,用法的实例越多,意义就越清楚。可是跨主体性是个新概念,尚无足够多的用法,其实只有阿兰或我的用法,可是我们自己的用法正是尚未明确而需要被反思和批判的对象,就是说,我们自己还没有确定的用法,只是一些探索。这是个怪圈。看来需要某种更基本方法,即在游戏分析之前的方法,因为这个概念还没有资格进入游戏分析。更基本的方法一定是平平无奇的,正如最基本的事情都是平平无奇的,颠覆最基本的事情才是惊天动地的。对于跨主体性概念的解释,我使用的最基本方法可称为“分类学方法”,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是定位性的“坐标方法”(笛卡尔)。虽是平平无奇的方法,但并不容易,因为分类或坐标定位的同时也是建构,是人类建构秩序的基本方法。既然分类即建构,分类学的实质就是形而上的,而不是知识论的。事物本身没有分类,所以分类或定位不是一个被给与的事实,而是人所建构的秩序,所以是形而上的。
跨主体性既然是一种关系,那么可以推想,其基础必须是主体间互为主体的关系,即在互相平等条件下形成的对称主体性的主体间性,也就是以“互为主体性”(reciprocal subjectivity)能够定位的最优化的主体间性。如果不能形成平等的互为主体性,就没有希望去建立共享的或互相认同的跨主体性。通常设定,主体之间的初始状态是互为他者(极端状态即为霍布斯状态),互为他者的主体间关系未必友善,更未必平等,互为他者更多地意味着互相排斥或互不认同,经常在经济上、政治上、精神上和知识上形成压迫、剥削、奴役、支配和控制的关系。如果互为他者要转化为互为主体的关系,第一步就需要双方在知识论上成为互为平等被观察被认知的对象,或者说,我与他者之间必须存在着互相平等和互相可逆的知识论关系,简单地说就是互为对象。这正是所谓“互观人类学”的要义,也是建立互相理解的知识论条件。我把主体间性从互为他者的初始状态转变为互为主体的兼容状态定义为主体间性的最优化。这里的“最优”不是一个伦理判断,而是一个类似“物理学”或“数学”的指标。互为主体的兼容状态能够将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合作能量发挥到最大值,虽然我无法量化地描述那个最大值,但几乎可以肯定,那一定是个最大值。我想,跨主体性可以是互为主体性的最大值的一个表述。
现代建立了拥有完全精神主权的主体性,于是互为他者就深化为一个精神对抗的难题,而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上的对抗。利益对抗属于显而易见的基本冲突,而精神对抗属于复杂冲突,具有形而上的深度。人类学家们发现了这个问题,哲学家们也发现了。胡塞尔就试图通过主体间性的概念来建立对他者的理解和承认,然而,试图在自我主体性的内部建立一个“他我”(alter ego)结构来移情地理解他者,但此方案只是联想有效,并非实质有效,因为他者的主体性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是我的主体性的一个因变量,而是出现在主体间性中的另一个自变量,只要他者是个自变量,就具有“顽固不化”的绝对外在性。所以列维纳斯可以论证他者是超越的存在,尤其是超越了我的主体性的绝对者。维特根斯坦的“游戏”概念更清楚说明了,如果一个主体间的游戏是可能的,其游戏规则必是我与他者互动形成并共同承认的。当然,每个主体在私人领域里有绝对主权,但这种主权不能延伸而用于主体间性,否则会导致无法协调的绝对冲突。以主体性的绝对主权干涉主体间性的事情并非无稽之谈,当今世界就不断发生,在此不论。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并不存在一种先验的主体间性,与之相反,主体间性必定是我与他者共同经验或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后验事实。因此,由主体性推论不出主体间性,推论不出主体间的伦理或政治原则(康德的“绝对命令”就是以主体性推论主体间性的错误),也推论不出主体间性必须在伦理上或政治上承认主体性的特殊价值观或特殊化权利(“政治正确”就是要求主体间性必须无条件承认主体性的诉求和身份)。主体间性肯定是外在于主体性的一个实践性的事实,其外部性超出了主体性的解释力。
承认他者是对等的知识主体,既是解释主体间性的实践有效性的一个条件,也是走向跨主体性的一个前提。不过,我与他者互为平等而互相可逆的知识论关系尚不足以直接形成跨主体性,只是主体间互相平等然而仍然互为异己的关系而已,仍有可能是互相对抗的。虽然我们还不能充分定义跨主体性,但可以肯定,跨主体性一定与共识(consensus)和共情(communion)有关,而并非任何主体间关系都有共识和共情。仅依靠由主体性所发出的同情(sympathy)以及移情(empathy)能力并不足以形成共识和共情。传统伦理学往往以为同情或移情是伦理的基础(比如孟子开启的心学传统),其实与伦理事实有很大出入。显然,必须超出知识论或心理学而进入实践互动关系才能建立共识和共情,就是说,共识和共情并不是我思的意向性,不是一厢情愿,不能口惠而实不至,而必须在外在实践中的实在关系里获得证明。请允许使用一个有些简单化的比喻:单相思不等于爱情,因为爱情是共同的实践,而不是一种意向性。因此,主体间性不可能是现象学的一个结果,跨主体性就更不是。现象学的有效性仅限于主体性的内在性,而主体间性和跨主体性都属于外在实践。
因此,主体间性和跨主体性还需要实践性的平等而对等的伦理学条件。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概念。通常把communication译为交往,没错,但少了一点深层含义。communicate的本义是通过某种共同实践(比如共领圣餐)来实现“共同体化”。有了成功的“共同体化”,才生成了community(共同体),而和谐的community就一定有communion(共情),这几个概念的共同词根已经说明了要点所在。共同体的概念在西方有着宗教背景,一般来说,共同体的传统单位是发生共情仪式和传达神意的教堂。其宗教含义在当代已然隐退,但其信仰性的结构含义仍然在:共同体的共情预设了以共同信仰为前提。在没有共同信仰的条件下谈论共同体就缺乏根据了。这涉及到了更深层的难题。
20多年前我向哈贝马斯请教过一个相关问题,我说交往理性恐怕并非充分有效,因为交往理性的极限能力是消解“思”的分歧(属于mind的分歧),但没有能力消解“心”的分歧(属于heart的分歧)。哈贝马斯辩护说,交往理性需要足够长的时间才能形成满意的效果;而且交往活动当然还是需要一些基本共识为前提的,有了基本共识,别的分歧就有望解决。当时我觉得也对,但过后还是觉得交往理性不够用,在若干文章里我讨论过这个有趣的问题。我的批评是,“足够长的时间”是无效辩护,因为时间并不会偏心地有利于好事,时间会消除分歧,但同样也会可能加强分歧甚至产生新的分歧。至于预设的基本共识,实际上等于回避了真正的难题。显然,真正严重的难题就是缺乏基本共识所导致的异己性或他者性——缺的就是基本共识,别的分歧确实好说。比如文明的冲突,康德和平理论解决不了文明冲突,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也不能,因为分歧点不在思维(mind)而在心灵(heart)。其实,假如更细致地分析,甚至思维(mind)也存在不一致,比如在讲理上,中国式的“情有可原”或“将心比心”之类的常见论据在西式论理中不能构成论据,这意味着,克服思维方式的分歧也没有那么容易。但无论如何,哈贝马斯的理论是一个真正有益的推进,只是与问题的解决之间尚有距离,甚至存在着鸿沟,即由“思”无法跨越到“心”的鸿沟,这与to be 推不出ought to be的休谟定理异曲同工。休谟实在是厉害,从康德以来,多种努力都一直无法解决休谟问题。
至此可以发现,跨主体性不仅需要平等的知识论条件,还需要平等的伦理学条件,我与他者不仅需要在知识上互为主体,还需要在道德上互为主体。以互为主体去替换互为他者,才能够从“思”的理性共识进入到“心”的精神共情,才有可能(仍然不保证必然能够)建立跨主体性。这意味着,伦理关系才是跨主体性的基本层次。推进到伦理,似乎触及了基底问题,然而真正的困难才开始,伦理学是形而上级别的终极难题,伦理学理论貌似很多,却只在同一维度上展开,思考的角度多是多了,却只是同一深度。几乎可以说,伦理学已经积累了很多理论和争论,在问题上却少有进展,伦理学问题从最开始就是主体间问题,一直停留在主体间问题上,似乎没有推进的余地。伦理学问题难就难在伦理无法解决主体间的冲突,简单地说,如果他人不同意我们的伦理或价值观,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要解决主体间的分歧,如前所论,首先就需要互为主体性的普遍原则。孔子思想所以长久不衰,就在于直达了互为主体性的问题。“仁”的原则很可能是互为主体性的最早公式(仁的概念早于孔子,但孔子赋予的新意更有价值)。仁可解释为:仁是任意二人之间的最优关系。意味着必须满足:(1)在此关系中,任意二人仅以人之为人的纯粹身份互相识别;并且(2)任意二人形成相互对称的善意。这两个必要条件合起来就成为仁的充分条件。要点是,仁的概念只涉及对他人作为人的纯粹身份识别,排除了任何社会阶级或文化阶层的身份识别,这在那时是重要新意。可是众所周知,孔子同时又非常重视社会的阶级或阶层的身份识别,这是那时的社会现实,孔子也非常尊重这个现实,两者并非矛盾而是重叠性质,即人是人,也是社会中人。社会化的身份识别问题表达在孔子并列重视的另一个概念里,即“礼”的概念。孔子所重者,仁与礼也,两者分别处理了不同问题。礼是现实,关于礼的理论不足为奇,无非“从周”;仁却是孔子提出的新理想,所以特别。也许需要注解:虽然孔子说过仁者爱人,但此爱不是爱情也不是博爱,只是“在乎”人之为人的意思。孔子之仁,并非具体人之间才能达到的最高级别的最优关系(那是想象的爱情),只是抽象的任意二人的最优关系,足以定义相互善意而已。
列维纳斯所想象的互为主体性在相互善意的“热度”上就超过了孔子的仁。对于列维纳斯,他人不仅是必须尊重和在乎的主体,而且是必须绝对尊重乃至超过自己的至尊。这种以他人为核心,或向他人倾斜来理解的他人超越性和绝对性达到了互为主体性的最大值,比孔子的现实主义理想更为理想主义。但问题也在这里,最大值未必就是最优值,超越了可能性的事情其实就失去了实践意义,只是宗教性的幻想,但我不想过分批评列维纳斯的美好空想。更需要思考的是,孔子的现实主义也未必就是互为主体性的最优值。现实主义的局限性是缺乏超越的维度,一个现实主义的心灵有善意,却未必是触及灵魂的深刻善意。中国式的伦理善意是心理主义的,主要基于心理学现象的善意,比如同情心。孟子式的同情心虽好,但缺乏精神或灵魂的深度,只是感同身受的心理。如以同情心作为道德根基,这种道德难以成为自觉自律的、理性的、无条件或纯粹的高尚意识,很容易满足于小恩小惠的有限怜悯甚至有些廉价的“爱心”,难以解释献身、牺牲和责任的壮举,简单地说,善良而不高尚,好心而少壮美。不能解释道德壮举就终究缺少精神分量,所缺少的正是灵魂级别的深刻善意。这说明,伦理学还有着很大的展开空间,至今未能解释人之高尚性,甚至未能解释人在本质上区别于动物的“几希”德性——决不是同情心(动物也有),而必定是我们尚未发现或未能定义的某种互为主体性,或更理想的跨主体性。
这里并不准备在互为主体性或跨主体性问题上采用理想主义的解释。理想主义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只是思想所需的度量衡,不是实践本身。道德远远不足以支撑现实,现实永远需要政治、经济和法律。比如说,天下体系定义了一种能够化敌为友的新政治,同时也蕴含了相互善意的经济、对称公正的法律以及智慧民主,因此,天下体系或可期望是跨主体性的政治最大值,但天下体系不能保证成为一个理想化的完美世界。关于天下理论,我在别的书中已经做过详细的分析,在此不论。至于是否能够有一种跨主体性的理想道德,这个问题让我有些犹豫。道德是个很神秘的概念,至今很难界定。维特根斯坦已经分析了,很大部分的“道德问题”在实质上属于游戏规则问题,凡是能够还原为规则的伦理学事实,都不是真正的道德。这意味着,真正的道德是属于主体性的纯粹内在意志(康德最早证明这一点),并不是主体间博弈的一个讨价还价解。这正是难点所在:如果主体性直接决定了道德,无需成为主体间的博弈均衡,那么,从主体性的道德是否能够神奇地升级到跨主体性的普遍道德,我就不知道了,看起来很难想象。但如果道德只是主体间的一个产物,无非是主体间的讨价还价均衡解,那么就只是伦理而已,并非具有精神光辉的道德。
我还是没有能够为跨主体性给出一个严格的定义。不过或可借用博弈论家托马斯.谢林的“聚点”理论来描述跨主体性的一个显著效果——不是定义,只是描述效果,算是一种迂回的解释。聚点(focal points)的概念曾译为“灵犀点”,很传神,但过于文学了,容易想入非非,所以我还是选择“聚点”这个含义比较中立的译法。但focal point确实包含心有灵犀的意思,是双方能够互相理解对方怎么想并且理解对方怎么想自己怎么想的那种循环互相理解的意识相会点,后来发展出更容易理解的“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其格式是: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是如此这般想的。在双方有着相同价值观或相似文化背景条件下,“聚点”就自然产生。如果有着明显差异的主体或文化双方愿意并且有能力互相理解和互相接受来自他者的有价值的思想,也能够创造出本来缺乏的聚点,于是双方都能够形成知识和思想上的增长,就近乎跨主体性了,换句话说,创造文化聚点就是创造跨主体性。
思想聚点的形成基于意识所有条件的综合效果,无法完全罗列,肯定包括思维方法、思维框架、语言、基本观念、价值观、知识、信仰和信念、文化传统、生活习俗、语境等等,只好说是整个意识条件,相当于涉及了哲学、逻辑、知识论、宗教、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所有学科的对象。这种概括没有太大用处,真正有用的是去发现这些因素的配比,即思想的“配方”。这就很难了,涉及到相当于“复杂科学”的问题了,我很想说,哲学应该属于“复杂科学”的一个层面,是对复杂问题的哲学反思。如果一定要指出形成思想聚点的一个关键条件,我愿意说,多半就是语言的“关键词库”。如果每种文明的思想关键词能够互相进入他者语言的关键词库,转变为他者思想里的重要词汇,就能够形成思想聚点。至于知识、文化、艺术或时尚的交流只能形成不稳定的浅层聚点。关键词库的跨文化通用性才是跨主体性的真正基础。
跨主体性不限于人或文化之间的关系,更严重的跨主体问题或许出现于一些潜在但有可能发生的未来情况里,比如目前只是作为潜在可能性的外星文明,还有或许在未来能够成为新主体的超级人工智能,还包括可能存在于元宇宙里的多种虚拟主体。哪里有着多种主体,哪里就会产生主体间的冲突,哪里就需要跨主体性的解决方式。我已经几乎说出了关于跨主体性的想象:在互为主体性的条件下,通过创建足够多的思想聚点来形成跨主体性,尽管这仍然不是一个定义。最难的未决问题可能是“互相信任”。即使在人类内部,主体间也仍然未能形成充分有效的互相信任,更别说与其他真正的异主体们建立互相信任了。我几乎敢说,信任是一切有效关系和秩序的基础。人类似乎还没有发展出能够确保信任的方法——但不要举出区块链或量子认证之类的技术方法,制度、规则和技术确实是维持信任的好方法,但任何制度或技术系统都有漏洞,没有一种制度或技术系统具有覆盖所有可能情况的普遍性。而且,承认某种制度也还需要以信任为前提——这里似乎存在无解的循环。最难的事情都只能慢慢想,等着瞧。
赵汀阳
2023年2月22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