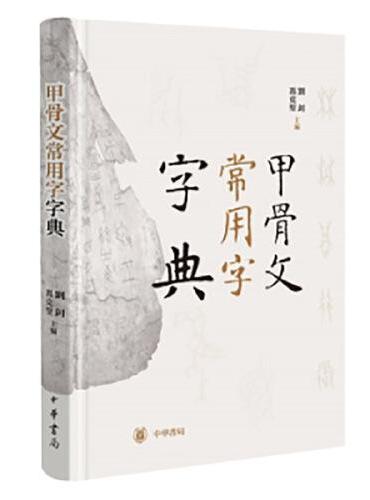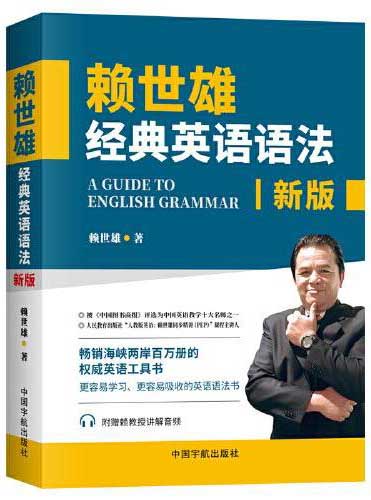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没有明天的我们,在昨天相恋
》
售價:NT$
218.0

《
流动的白银(一部由白银打开的人类文明发展史)
》
售價:NT$
296.0

《
饮食的谬误:别让那些流行饮食法害了你
》
售價:NT$
296.0

《
三千年系列:文治三千年+武治三千年+兵器三千年
》
售價:NT$
9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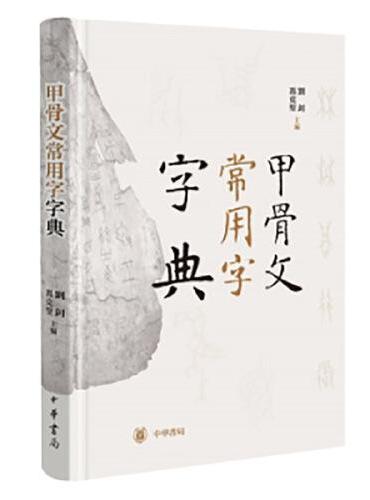
《
甲骨文常用字字典(精) 新版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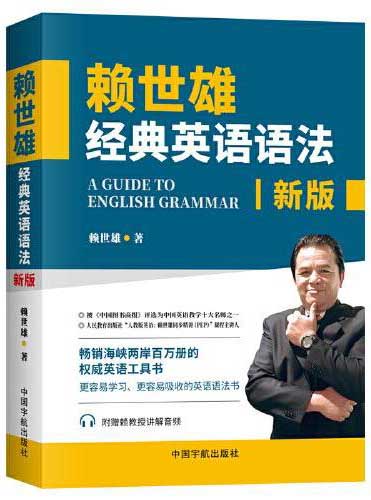
《
赖世雄经典英语语法:2025全新修订版(赖老师经典外语教材,老版《赖氏经典英语语法》超32000条读者好评!)
》
售價:NT$
305.0

《
影神图 精装版
》
售價:NT$
653.0

《
不止于判断:判断与决策学的发展史、方法学及判断理论
》
售價:NT$
347.0
|
| 編輯推薦: |
前两年发生在徐州的一个社会热点事件,曾经引发全民对于女性困境的热烈讨论与强烈关注。而事实上,类似的悲剧曾经在不同的国度与时空背景之下反复上演,让人在激愤唏嘘之余,不禁遐想:这些不幸的女性中间,有人曾经凭借自己的不屈意志,最终走出牢笼,重获自由吗?答案是:有。
本书女主人公玛丽·英格斯的万里归家路,乃是基于可靠史料记载的真人真事。历经重重险阻,最终得返家乡的“奥德赛”是文学作品的一个经典母题,而玛丽的奥德赛之旅之所以鼓舞人心,恰恰就在于她本身的看似弱小。与那些或沙场余生,或浪子回头的国王、武士、猎人、牛仔不同,玛丽只是一个手无寸铁的平凡农家女,没有任何装备、勇力或是求生技能傍身,还要时刻躲避无处不在的追捕者。而当她在严酷的荒野中被不仁的天地夺去了最后一粒玉米、最后一条毛毯时,苦苦支撑她穿越冰原的惟有她心中对于家人矢志不渝的爱,以及不自由毋宁死的信念。最终,这个女人竟然走到了终点,战胜了荒野,完成了一项在她之前的欧洲冒险家们都没能完成的壮举。这不能另同为普通人的我们为之动容且备受鼓舞——直到今天,她的后人们依然会在小镇中定期举办庆祝活动,纪念这位了不起的祖先。
这个故事的精神力量从作者
|
| 內容簡介: |
这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1755年的英属弗吉尼亚。是时,英法七年战争正撕扯着北美大陆,但这片平静的河谷似乎并没有被战鼓与狼烟所侵扰。然而,就在一个明媚的午后,一群与法军结盟的肖尼族印第安武士突然袭击了河谷中一个毫无防备的英国定居点,随之而来的便是一场血腥屠杀。待到一切尘埃落定,肖尼武士终于刀枪入鞘,俘虏了所剩无几的幸存者,连同载满驮马的战利品一道,押往河流下游的印第安村落。走在这群俘虏中间的,便是我们的女主人公玛丽?英格斯——一个怀着身孕的年轻母亲,还有她的两个幼子。
囚徒之路是艰苦而危机四伏的,但比这更可怕的却是奴役与屈辱。凭借着勇气与尊严,玛丽咬牙承受住了一路上的种种磨难,赢得了肖尼人的赞许,抑或是某种敬意。甚至,那位俘虏她的年轻首领在默默观察了她许多日后,还给了她一个选择,一个她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选择——这不仅仅关系到她自身的性命安危,更关系到她膝下的一双幼子和她刚刚在路上诞下的那个女婴。或许,以人格和自由为代价,为她和她的子女换取衣食无虞,相比死亡而言并不是一个那么坏的选择?然而,对于玛丽?英格斯来说,自由从来就不是可以拿来交易的筹码……
|
| 關於作者: |
|
詹姆斯·托姆,1933年生,美国作家,生于印第安纳州,早年做过报业记者与专栏作家。他的小说大多描写北美殖民地时期的历史,因其对历史资料的详尽调研与对印第安人部族文化的灵动还原而备受赞誉。2018年,托姆被印第安纳波利斯公立图书馆基金会授予终生成就奖。
|
| 內容試閱:
|
第14章
她们意外得马,大走好运;运气似乎还不止于此,天公也在作美。一连三天,南风吹拂,温和而干爽;天空淡蓝,飘动着被阳光镀金的轻云。风飒飒作响,高高吹过头顶的树木,吹皱河面,也吹落率先脱枝的秋叶。在高大阔叶木的树颠,常呼呼扫过一阵强风,树叶如阵阵黄色雪暴,飞旋飘下。红褐、橙黄、深红的落叶厚积于地,在脚下散出清香,踏上去松脆有声、柔软舒适。在斜射而下的光束中,不伤人的黄蜂和有倦意的苍蝇悠然穿飞。在这种干爽温和的天气里,玛丽与盖特尔一路前行,轮换着骑马、牵马,涉水过河,蹒跚走过沙沙作响的落叶,高举自制长矛,衣衫褴褛,俨若亚马孙族①骑兵队伍的两名残卒。一路上,玛丽常哼起那首归乡短歌。在攀爬一处陡岸时,马猛然前抢,盖特尔无马鬃可抓,自此不再倒骑。夜晚干燥清凉,但不冷。玉米在慢慢减少,当然,若敢生火熟吃,玉米会消耗得更快。棒子上的玉米粒一天天变干,嚼起来又硬又粉,简直像吃白垩土,不如先前可口,就吃得少了。每天找到的几把莓果、核桃、野葡萄和柿子是绝佳的调剂。盖特尔缺了槽牙,只好想办法将玉米粒砸开、磨碎,常常在石头上用战斧的钝面把玉米捣烂,得到一小堆脏兮兮、白中带黄的糙粉,可就水冲下。这种粗陋的碾磨掺入不少泥土和石粉。因为吃得糟糕,玛丽的牙齿出现疼痛和松动,牙床莫名感到痛痒,从槽牙间可咂进一股朽坏的味道。不过,至少吃玉米已止住腹泻。每天早晨,两人都解出一小团硬便,为此而窃喜。
玛丽估计,自得此良马,每天所走路程已比先前翻倍,部分原因是,遇到不敢涉渡的溪口与浅河,马能驮她们过去。这匹母马擅长涉水,入水不慌,立足稳健,即使急流高到鬐甲也能通过。两人跨骑马上,河水及臀,玛丽紧抓马鬃,盖特尔搂住玛丽的瘦腰。当马爬上对岸时,两人就会对它一番宠爱,搂抱脖子,亲吻嘴巴,抚摩喉革,用手喂些玉米,遇到草地,也许会让它歇歇脚、吃吃草。玛丽一向喜欢马,可从没如此喜欢过。这匹马善良可爱,在极需时出现在生命里。对它,玛丽爱到哽咽、流泪。有时,她会盯住那对长着柔软睫毛的深褐色眼睛,心头涌上一股几如祈祷时的感激之情。“啊,上帝,”她曾呼喊道,“真希望人也这么善良!”
然而,有时这种交流却令她心碎,因为在深情涌动的内心,三个失散子女的样貌会蓦地闯入,仿佛冲开一扇不意间未设防的大门。
得马第三天,她们来到一条河沙铺底的支流②。这条河玛丽清晰记得,被野猫队长押解途中曾见过。当时,印第安人乘独木舟过河,将船藏于这边河岸的一处芦苇丛。“等我。”她说着,将马交给盖特尔,钻入随风起伏的黄绿色高苇丛,把山核桃木长矛端在身前,既为分开芦苇,也为防范水蝮蛇或印第安人。她吃力地蹚过淤泥,在搜寻独木舟的踪迹。
前方几英尺远“扑通”一声响,吓得她直往后缩,冒出一身冷汗。她站住脚,心怦怦乱跳,最后断定,自己只是惊到一只晒太阳的牛蛙。这片区域到处是黑泥和微光闪闪的苇秆。她蹑手蹑脚地深入其中,鞋里灌满冷水,可就是不见独木舟的踪影。她想:嗯,好吧。有可能是哪支外出的队伍把船留在了对岸。她刚迈步往回赶,就注意到一坨黑亮亮的东西一张一缩,几乎就待在脚边的浅水中。
是一只大个牛蛙,一半没在水里,正准备跳开。
她急忙抄矛猛戳,将其刺穿。牛蛙猛力挣扎扭动。她背过脸,一直等到牛蛙不再动弹。
“玛——丽?玛——丽?”老妇喊起来。此时玛丽钻出芦苇丛,得意地举起长矛,矛尖上扎着软塌塌的牛蛙。
“瞧,盖特尔,瞧,咱们终于有肉吃啦。”
她俩拧下牛蛙的大腿,脱袜一般扒下黏糊糊的皮,像两个土著似的,蹲在河岸上,嚼起凉凉的、白中带粉的生肉。玛丽啃着骨头,一抬眼,见盖特尔扔掉蛙的腿骨,又开始仔细查看其余部分,一道口水从老妇的下唇淌下。
盖特尔伸手去扯牛蛙细小的前腿,玛丽只得看向别处。
盖特尔饥饿的眼神中有什么东西,似一道冷森森的闪电,让玛丽心头升起莫可名状的恐惧。
她们沿西岸走出五英里,一路跌跌撞撞地穿过沟壑,挤过灌木和棘丛,皮肤被割伤、被抽痛,本已残破的长裙被撕得更烂,最终发现一处沙石铺底的浅水,可骑马涉行。之后,又顺东岸回返。此处有一大片刺槐,葡萄藤交缠其间,只能牵马走过。葡萄又硬又老,皱皱巴巴,有些触手可及,但显然已过季,食之无味。尽管如此,两人还是揪下几串,塞进裹有剩余玉米的毛毯中。她们确信,到时这也是美味。
她俩终于挤出棘丛,满身是血。两人用河水洗净四肢,从伤口内拔出一根根小黑刺,继续朝下游去往俄亥俄河,没走几步就来到一处溪口。水不过膝,但水底有几码宽的地方布满苔石,石块扁平,边缘尖锐,小则如餐盘,大则如桌面,在脚下倾斜、滑动、翻转。待跌跌撞撞踩过石头到对岸时,烂鞋已彻底散架。只得丢下鞋,光着血乎乎的双脚,沿河岸继续走,感觉每块脚骨皆似断裂。细枝、石块扎痛足底,她俩颠着碎步,龇牙咧嘴,最后柔软的双脚到处都在突突抽痛,再戳再扎几无感觉。两人轮流骑马,可是,双脚垂在马的两肋旁,相比徒步似乎疼得变本加厉。
更令人忧心的是,踏石过溪后,马走路变得一瘸一拐。玛丽检查一番,发现马身有擦伤,伤口在渗血,一处在左前腿的蹄骹上,一处在右后腿的球节下方。玛丽明白,这都是要害处,如果她们倒霉,马会因此瘸腿,变得毫无用处。
两人全都下马步行。下午三时左右,俄亥俄河进入视野,一天的行程到此为止。
在这里,她俩将马颈上的缰绳系到马腿上,放马去吃草。玛丽跛着腿四处转悠了一阵,想寻些聚合草,给两人的脚和马腿做敷料,可惜一无所获。她由此推测,聚合草已过季。尽管没什么把握,但她还是决定,从河边挖些淤泥,敷在马的伤口上,觉得这样起码可缓解疼痛。弯腰时,她见到芦苇里有段又长又黑的东西,起初以为是烂木,细看之下,发现是印第安人的一只破独木舟:半淹在浅滩中,外覆的树皮已从山核桃木船体上片片脱落。这只能让她意识到,两人一直走的都是常过印第安人的小路,因此,决不可掉以轻心,也不可过多出声。她渴望燃火取暖,渴望烧水疗治脚伤;就算无燧石和火镰,或许也能点起篝火——她见过肖尼村女人用弓钻取火的简易工具点燃引火物。然而她知道,这样做简直鲁莽之极。
她将冰凉的黑泥糊在马的蹄骹和球节处。盖特尔坐在近旁瞧着,面露赞许,同时用战斧在一块扁石上将玉米和野葡萄一同捣碎。稍后,两人添入一捧水,将粗粉和成紫色面糊,虽说味道奇怪糟糕,但确有营养,也让所剩不多的玉米能多吃几顿。
她们每次睡醒起身,在营地周围走动时,阵阵剧痛自备受摧残的双脚上冲。玛丽想到近两天对威尔的思念、对他俩贴心伺候对方双脚的回忆。她看着身旁可怜的老妇,看着老妇皱纹纵横的皮肤刮得伤痕累累,似肉垂般从两臂下耷,骤然被一股强烈的怜悯之情左右。“来,盖特尔。”她说。
随后的一个钟头,夕阳照暖脸庞,她们坐在河畔,玛丽给老妇的双脚抹上黏稠的泥巴,又是抚摩,又是揉捏。这双脚布满老茧,瘦成两把骨头,关节凸出,已成畸形。盖特尔发出低沉的呻吟,既是痛苦,又是享受。玛丽边给老妇揉脚,边讲起威尔,泪水不时从鼻端淌下。
后来,盖特尔又给玛丽揉脚,跟她谈起往昔的荷兰③,自己是二十年前从那儿来的,“当时我跟你一样命好”;还谈起自己熟悉的大厨房:各式铜锅铜勺一应俱全,椽子上挂着香肠,裹在布里的奶酪在熟化,黄油盛在搅乳器中,大瓷炉逸出新烤面包的香气。最后,听得玛丽不禁大喊:
“求求你啦!你一面给我揉脚,一面又折磨我的心!”
次日晨起,体重初落两脚时,足痛钻心,不过,等走走路活动开以后,疼痛出现缓解,变得不轻也不重。显然,脚伤确乎大为好转。
这个早晨,两人都没骑马,而是牵马走路,留意着马的步态。马不再瘸,后来也没瘸过。她俩据此推测,泥巴不仅对自己有好处,对马也同样起作用。“兴许明天就能骑啦。”玛丽说。
整个上午,她们一路东行,没见到印第安人的踪迹,只觅得些掉落的橡实,来补充越来越少的玉米。中午时,她们折向东南。玛丽回顾着记忆中的地貌。按她所记,还要渡过三个主要河口,才能到达俄亥俄河拐向东北的大河湾,找到那个令人兴奋之处,在那儿新河汇入俄亥俄河。她想:大概还有七八十英里。可要是过那三条河也同样绕来绕去,加起来怕有两百英里。
正午时分,宜人的天气退场。冷风骤起,扫过河谷。无数叶片形成一股股红黄交杂的旋风,打着转儿飞走。风来势汹汹,发出吼啸,击打着树梢。铅灰色乌云自低空疾驰而来,拖着丑陋的边沿掠过山顶。未出五分钟,河水呈现出燧石般的灰黑色,翻涌起朵朵白头浪花。狂暴的冷风将两人的头发吹散到脸上、平贴在头皮上。周遭空中满是飞旋的树叶和枝条。身上的破烂衣裙随风飘摆。她俩眯起眼睛,躲在马的背风一侧,紧贴马身,一点点往前挪。不多时,大风刮来冰冷的雨点,重重打在身上,似冻雨般让人刺痛。此时,衣裙已被狂风撕扯得四分五裂,大部分身体都裸露在外。风愈刮愈猛,格外寒冷和强劲,似要夺走气息。距头顶几码远的斜坡上,一大株山毛榉枯木站立不牢,轰然倒地,同时也压垮几棵较小的树木,砸得这些树桠杈断折、七零八落。马受到惊吓,人立而起,随后猛跑开去。玛丽死死抓住马颈上的笼头,双脚几乎离地,如此过去惊心动魄的十秒钟。跑出五十码,她终于拽住这头牲口。马惊魂未定,鼻中呼哧呼哧地喷气。盖特尔在风里低声尖叫,上下摇动胳膊,一路小跑赶来,闯过笞刑时就是这般怪异姿势。
她俩强打精神,迎着冷雨和烈风,直走到天黑,手紧抓缰绳,生怕被吹进河里。玛丽长大后虽说主要靠近荒野生活,可从未有过此番感觉:自己形同微微一片谷糠,毫无重量可言,被遗落在一个风狂雨骤、林木呼号、群山漠然的世界。
脚下的树叶湿漉漉,又凉又软,淋湿的衣裙残片紧贴着起满鸡皮疙瘩的惨白皮肤。此刻夕阳将坠。终于,隔着水花翻涌的河流,一抹暗淡的瑰色晚霞照亮对面陡岸。西天上空,紫云间横向裂开巨隙,闪出猩红亮光,似一道道血淋淋的伤口。不久,落日透过裂隙露出部分真容,照亮每根枝条与每片草叶的每滴水珠。最终,太阳的整张圆脸冲破云层的遮蔽;风雨越过河面,渐渐远去,形成一片青紫巨幕,以此为背景,现出一道绝美彩虹,似乎横跨两岸。玛丽虽狼狈不堪,但仍觉见到上帝杰作,而自己已有多周没怎么想起过上帝。当晚,她和盖特尔裹严湿湿的羊毛毯,彼此搂抱,紧紧偎依,冻得浑身直抖,好在心脏如同微火尚存的炉子,最终暖了血液。
趁两人熟睡时,胆大的花鼠和松鼠悄然靠近,偷吃她们从毛毯里倒出的一小堆霉玉米。
次早,玛丽先骑马。盖特尔牵马,光脚踏上亮晶晶的白霜。湿叶匝地,从微红到火焰黄,色泽不一,因雨水、白霜及惨淡朝阳的点染,所有色彩皆愈加浓重。盖特尔用德语在自顾自地哼唱,声音近乎耳语。她和马呼出的气息凝结成团。玛丽肩披毛毯,如印第安人一般;玉米已所剩不多,用一条毛毯包裹绰绰有余。她俩商定,骑马的披毛毯,因为走路的会自己生热。不过,即使盖特尔不冷,也看不出。她的皮肤疙疙瘩瘩,像拔光羽毛的火鸡,而且每过几秒就从头到脚一阵猛颤。
玛丽暗想:上帝啊,她一把年纪,可真能吃苦。但我还是该跟她换个位子,现在就把毛毯给她,否则,不到天黑,她就会冻感冒的。
玛丽在毯里缩成一团。
还是再等一等吧。她想。
转天,强风再起。乌云曳动雨幕,掠过山顶。狂风劲吹,一分钟的工夫,乌云即从一侧天边被刮到另一侧。灌丛摇晃不止,哗哗作响,似乎被一只无形巨手掴来掴去。空中一直黄叶飘飞;树上的几片残叶迎风一再坚持,但总被扯下卷走;此刻,树木几乎已褪尽叶子,只剩灰白和褐色枝干,光秃秃一派萧条,令人心生寒意。玛丽边走边琢磨:我真觉得,瞧见这些火焰色的秋叶,我可怜的心就不再冷,跟瞧见火堆身子就暖和一样……
玛丽骑着马,低头看向盖特尔,此刻老妇在引马前行。玛丽不禁想到:
毛毯要是红色,是好看的大红,而不是这种冷灰,我们就会暖和许多……
对自己的异想天开,她感到好笑。
你今天有点儿发疯啦,姑娘。最好还是让老盖特尔骑上来晃荡晃荡,做会儿白日梦……
那天,她们来到另一处河口,河面过宽,而河水又太深太凉,无法涉过。盖特尔望着对岸哀叹。如此绕来绕去,她似乎比玛丽还沮丧,也许是因为她不像玛丽,不了解地形。每条新出现的河溪就是又一重意外障碍,似乎上帝有意刁难,每天都在创造新的河流,挡住去路,让她俩多走行程。
两人转弯,溯这条新的河流前行。
绕开河谷一处沼泽时,她们发现一片在转为棕色的茨菰茎杆,便将马拴在附近,在冰冷的泥水中踩来踩去,用脚指头探寻茨菰块茎,一旦找到,就弯腰拔起。她俩花去一个钟头,采到五六磅,与发霉的玉米搁在一处,继续循河而前。
因近日下雨,河面宽阔,棕黄色的水流速迅疾。看来要沿河走很远方可寻见涉渡点。俄亥俄河落在身后,渐行渐远,但在意识深处,两人一直记挂着她们的荒野向导。
当晚在一处凸岩下安营,几英尺下河水泛滥咆哮。两人试着吃了顿茨菰块茎,生吃味同嚼木,苦涩难咽。“要是有锅煮一煮,去去苦味就好啦。”玛丽皱着眉头说,“我豁出去了,现在非生堆火不可。”
不过,这东西一吃即饱。
两人顺这条无名河④大概已走出二十五英里。转天,盖特尔往前一指,喊道:“看!有桥!”
在河水轰鸣闯过似石阶之处,有一大片浮木卡在那里,泡得发白的树干、粗枝和树根挤在一起,横过整个河面,确像一座桥。河水棕黄,自中间和下方冲过,但这一大堆混杂的烂木仍待在原处。
“咱们能过去,对吧?”盖特尔催促道。她兴冲冲地咧嘴一笑,露出黄牙。
但玛丽看了看,心存疑虑:似乎没问题,不过……
“等等。”她说,“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不知为啥,我一点儿把握也没有。”
盖特尔脸色一沉,指向上游:“哎,你到底想沿着河走多远,啊?看吧!”
在浮木桥上游,河水依然又深又急。也许还要走二十五英里或更长,才能寻到涉水点。也就是说,从对岸返回俄亥俄河,要走五十英里乃至更远,想想都心怵。
而桥就在眼前,仿佛上帝放置于此,意在让她们少走三四天行程。
然而,这座桥却带给她不祥的预感。而且,她正在学会认真看待自己的预感。
“瞧我的。”盖特尔话音未落,已下到河边,伸手抓牢一截凸起的树枝,将一只脚踏上一根原木,接着,小心翼翼地将另一只脚抬离河岸。她在桥头站立片刻,而后开始曲膝、晃身,试探立足点是否牢固。后来她蹦得更用力,还高喊着:“看!看!禁得住!”
玛丽暗想:别这样。这似乎太莽撞,不顾死活。
木头的确禁得住。盖特尔退上岸,粲然一笑。“好过。”她说,“看见了吧?”
“对咱俩兴许好过,可马走不了木头,盖特尔。”
“我觉得可以。这跟桥没啥两样,玛丽,跟桥没啥两样。”
“我有这种预感……”
“让你的预感见鬼去吧!”盖特尔失去耐心,一脸怒气,“你要是不过来,我就自己走!没错,瞧着吧!谁要你,谁要你的预感!”
“不行,盖特尔,求你了……”
“可以,该死!要不我自己走!”
“那咱就先走一趟试试吧。”
“好!我来。”老妇一心想让玛丽看看过桥有多容易,于是摇摇摆摆,脚步轻捷,再次踏上浮木。她走在木头上,步履轻盈,每走一码左右就找到个抓点。不出两分钟,她已站在对岸,开心地举起双臂,露齿而笑。随后,她再次跳上浮木,走了回来:“看见了吧?”
“可是马……”
“跟桥没啥两样。”
玛丽这才同意。她和盖特尔合力将马拉到水边。马不愿走,蹄子牢牢钉在岸上,就是不上浮木。玛丽看着它惊恐的褐色眼睛,心里一阵难过。
“快走,你这畜生。”盖特尔喘息道。
马还是一动不动。
“嘿,那好,咱等着瞧。”盖特尔吼道,“你来拽,玛丽。我拿棍子捅这畜生的屁股,它就得走啦。等着瞧吧。”
她抄起一杆山核桃木长矛,绕到马后,用矛尖戳马臀,起初很轻,马依旧畏缩不前,老妇便加大手劲。见到马的双眼流露出极度恐惧和痛楚,玛丽真想大哭。她一手扯着缰绳,一手握住树枝,对马好言相劝,给它鼓劲。马终于依从,向前迈出一步。
马在木头上立稳前蹄,因在脚下找到支撑点,便比先前稍有顺从,但依然十分胆怯。脚下河水咆哮,马受到惊吓,玛丽并不怪它。
盖特尔用德语吼骂一句,或是发出命令,将矛尖直接刺入马的屁眼。母马一声惨嘶,离开河岸,猛然抢上浮木,险些将玛丽撞进河中。
玛丽一手向后去够树枝,一手扯住缰绳,在浮木上缓缓后退,任脚下河水奔腾,任浮木被马踩得摇颤不定,她全不理会。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匹马竟脚步稳健,往前走起来。每当它止步不前或要惊慌失措时,盖特尔便抄起已血乎乎的长矛捅它,马就往前猛抢一步。对马又捅又戳很危险,但显然不如此,马就寸步不行。
此刻,她们已到中途,仅剩十五英尺。
忽然,马的两只前足踏破乱木,落入水中。它发出哀鸣,猛晃脑袋,屁股高高撅起,胸膛倚在木头上,后腿紧绷,想拔起前腿。徒劳的挣扎仅持续数秒。有只后蹄侧向滑落一株树干,戳入浮木间隙,接着另一条后腿从树干另一侧扎进水中。一截断枝自右侧的肋骨后刺入,也不知刺进多深。马发出啾啾哀叫,胸膛托在浮木上,而四条腿浸在水中,身下的河水泛起血红。
玛丽又喊又叫,给它打气,毫无意识地对它发出指令和乞求。她开始呜咽,往上拽缰绳,似乎单凭拖拉就能帮这匹不断嘶鸣的母马脱困。盖特尔站在马后的树干上,丑陋的面孔不停抽动,满是疑惑和痛苦。她开始用德语大嚷,丢下长矛,握住马尾,用尽气力往上提。
由于两人用力,加之河水不断冲击,浮桥在抖,枝干在挪动、在嘎吱作响。“要散架啦!”玛丽大喊。马不停地晃头和惨叫,猛力挣扎却无以脱身。每动一下,身侧的伤口就被撕裂得更宽更深。
此时,老妇正从马的身侧爬过,一边朝玛丽过来,一边使劲朝她挥手:“下去!下去!”玛丽转身离开爱马,手脚着地,爬上河岸。盖特尔跳到她身旁。玛丽站在那里,哆嗦着,哭喊着,不忍去看在遭罪的牲畜。她急忙掩耳,不忍去听马的哀鸣。她看向地面,因痛失爱马而无助地大哭。盖特尔立在原地,无可奈何地打着手势,来回看玛丽和马,最终说了句“等一下”,重又爬上浮桥,悄悄靠近母马。
马顿时静下来,仿佛指望这人来救自己。它不住地从胸膛深处发出低嘶,从口中喷出湿气。
盖特尔缓缓来到侧旁,从马背上取下毛毯包裹,然后又往前挪,在马头旁边停住,解下马缰和铃绳。
老妇把两人的全部物品拿上岸,一只大手紧扣玛丽的上臂,拽起她,离开垂死的牲畜,朝下游走去。猛然间,马又开始尖声嘶鸣、晃起脑袋。
“哎呀,别叫啦,别叫啦!”玛丽抽噎道,“我受不了啦!”
她们沿东岸已走出一百码,但透过奔腾的河水声,马的哀嘶依然清晰可闻。玛丽感到,即使走出一百英里,似乎仍会听见马叫。
向下游约莫走了一个钟头,两人停下歇息。玛丽感觉要比以往虚弱十倍。似乎她们失去的,不只是马本身的力量,还有马的陪伴所给予她们的同等力量。
她俩坐在一株黑色朽木上。玛丽不再哭泣。她以手掩面,坐了片刻,之后将脸冷冷地转向盖特尔。
“你真是个蠢老太婆。”
盖特尔眉头一皱,垂下目光,而后又举目看向玛丽的眼睛,伸手去拍她的肩膀,说道:
“唉,得啦。的确,咱们也是没辙。”
玛丽躲开盖特尔伸来的手。片刻后,她说:
“你讲过,我有预感你就听我的。”
盖特尔点点头:“对。”
“可你没听。”
“唉,得了,玛丽,算啦。”声音变得有些生硬。马的事她很难过,知道全因自己,本已痛苦不堪,再加玛丽的怪罪她并不在乎。
“上次我感觉印第安人要来,过后你就说,打那儿起都听我的……”
盖特尔一蹦而起,站到玛丽面前,双手握拳过顶。“什么?”她吼道,“什么,玛丽?英格斯?我觉得听你太多啦!要不是听你的,我现在就暖暖和和待在印第安屋子里呢!又有火堆又吃得饱!”
“对,没错,是吧?满肚子都是南瓜和狗肉,这就是吃得饱!”
“反正能吃饱!有肉就行,活物是‘汪汪叫’还是‘哞哞叫’,我的肚子才不在乎呢!”
“你的肚子现在不在乎啦?”玛丽气冲冲地说,“可当初抱怨印第安人吃食的是你,不是我。是你吹嘘自己的漂亮厨房,还有可口的德国饭菜,要啥有啥……”
玛丽这样骂着,用起母亲的爱尔兰土腔,她生气时就会如此。她将失去爱马的哀痛和怒火一股脑儿发泄出来。老妇又坐回那根木头,陪在玛丽身边,拍起她的肩膀。
骂完后,胸中的委屈有所纾解,玛丽意识到自己的头正倚在老妇肩上。盖特尔轻柔地捋着她的乱发,同时说着:“好姑娘,得啦,好姑娘。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我的全部,玛丽?英格斯,我的全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