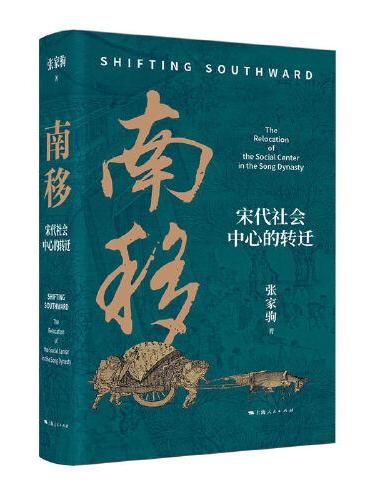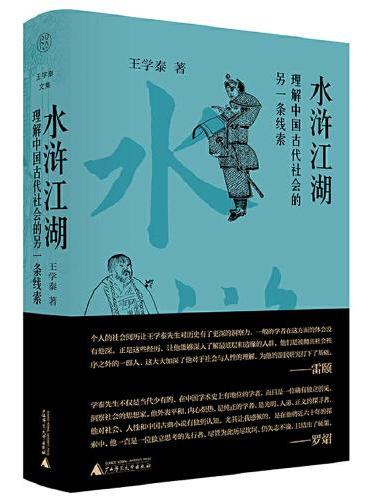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女人们的谈话(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提名、最佳改编剧本奖 原著!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简直是《使女的故事》现实版!”)
》 售價:NT$
286.0
《
忧郁的秩序:亚洲移民与边境管控的全球化(共域世界史)
》 售價:NT$
653.0
《
一周一堂经济学课: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
》 售價:NT$
500.0
《
慢性胃炎的中医研究 胃
》 售價:NT$
3050.0
《
南移:宋代社会中心的转迁
》 售價:NT$
755.0
《
纯粹·水浒江湖: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另一条线索
》 售價:NT$
469.0
《
肌骨复健实践指南:运动损伤与慢性疼痛
》 售價:NT$
1367.0
《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MySQL版)
》 售價:NT$
301.0
編輯推薦:
当自发的记忆不再存在,我们会如何应对遗忘的危机,历经各式各样的人类活动后, “记忆”是否真正地被保存了下来?在日本侵华的整个历史时期,南京以其独有的政治地位和象征意义,成为日本官民各界共同关注的对象,甚至成为战时日本国民动员与集体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结合中日史料,细致描绘、辨析了战时日本军政当局和民间群体在南京进行的一系列记忆与象征建构的政治文化活动,还原纯粹的南京记忆,进而追究日方活动痕迹在战后的历史命运。我们还将看到,作者引入的“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这一概念是如何贯穿南京这段历史的,“记忆之场”在被建构的同时,也在构建自身。
內容簡介:
日本侵华战争使包括南京在内的很多地区成为沦陷区,沦陷区问题由此重要起来。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指出:“中国沦陷区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生死问题。”本书在深入挖掘中日文史料的基础上,探究日本侵占南京时期的诸多罪行。具体而言,本书探讨了关于光华门战争遗迹、菊花台公园、日本纪元庆典、明孝陵祭典以及南京神社等课题,揭示了日本建构记忆与象征的政治活动及其欺瞒性。在强调侵华日军暴力性与罪恶性的同时,本书还注意到日本侵华战争中“软暴力”的一面,从而拓展和深化了日本侵华史研究。
關於作者:
谢任,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学衡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抗日战争史、中国革命的概念史以及学衡派研究。获评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在《学海》《江海学刊》《抗日战争研究》《史学月刊》《读书》和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非文字資料研究』等中、英、日文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
目錄
序:历史之重 001
內容試閱
绪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