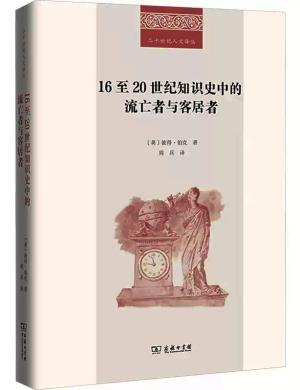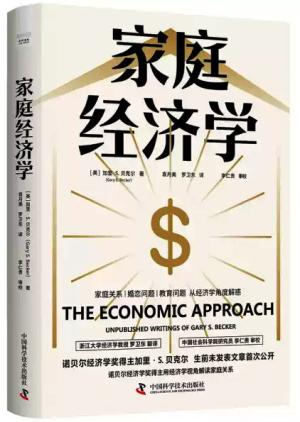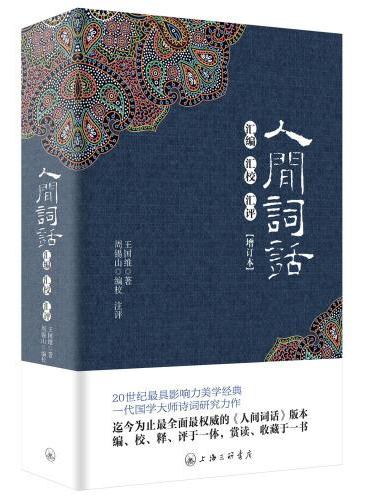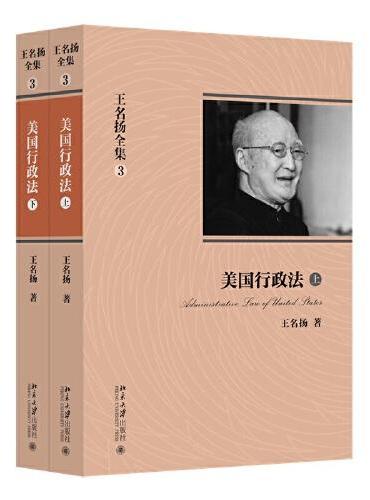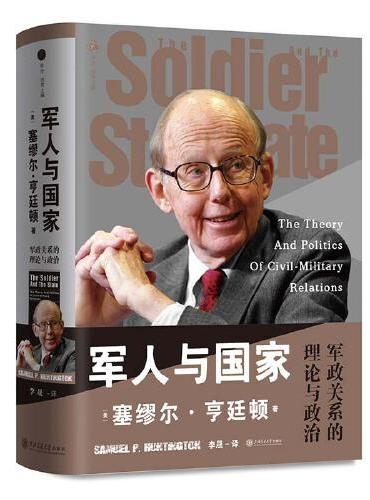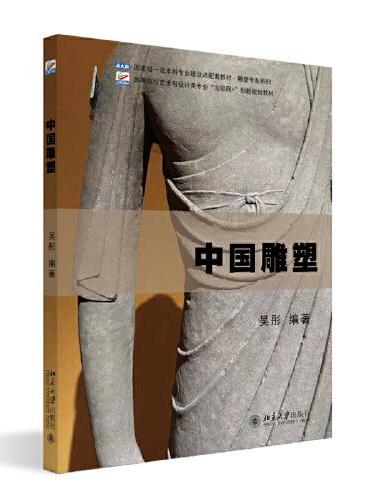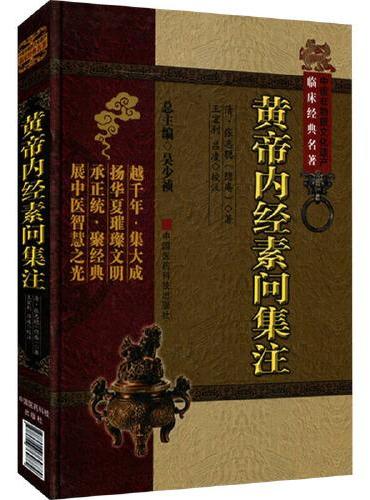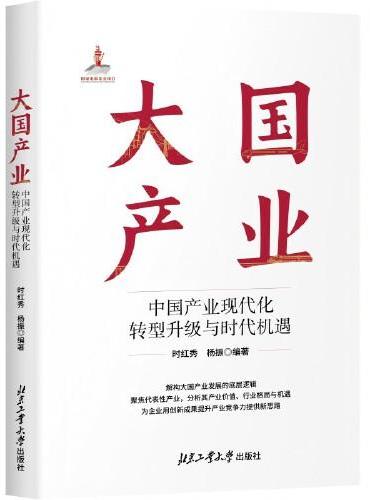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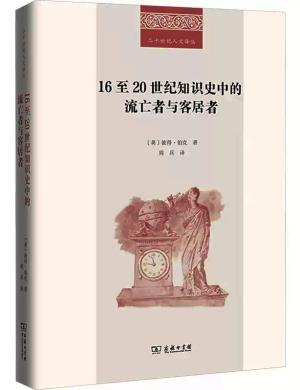
《
16至20世纪知识史中的流亡者与客居者
》
售價:NT$
48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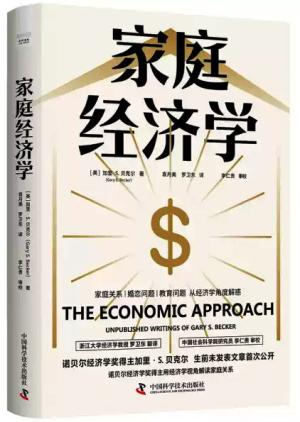
《
家庭经济学:用经济学视角解读家庭关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S. 贝克尔全新力作)
》
售價:NT$
38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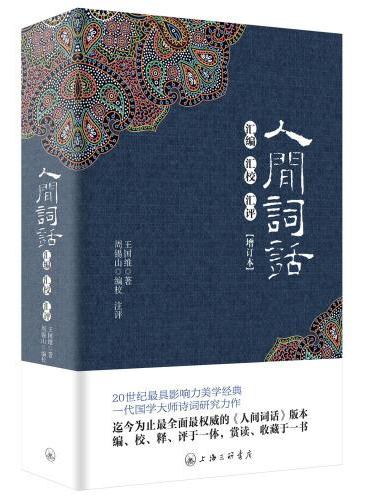
《
人间词话汇编汇校汇评(新)
》
售價:NT$
2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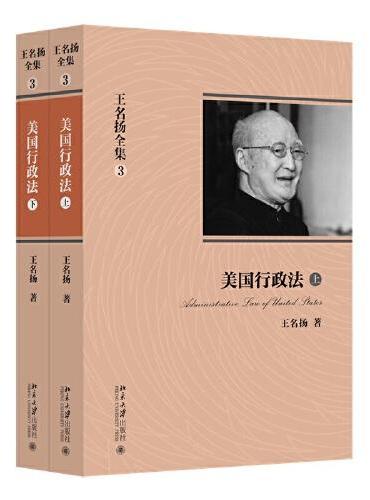
《
王名扬全集:美国行政法(上下) 王名扬老先生行政法三部曲之一
》
售價:NT$
8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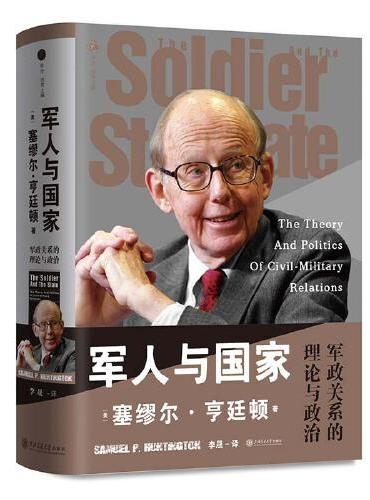
《
军人与国家:军政关系的理论与政治
》
售價:NT$
6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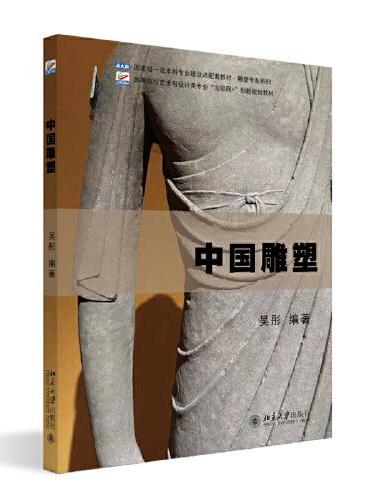
《
中国雕塑 高等院校艺术与设计类专业
》
售價:NT$
4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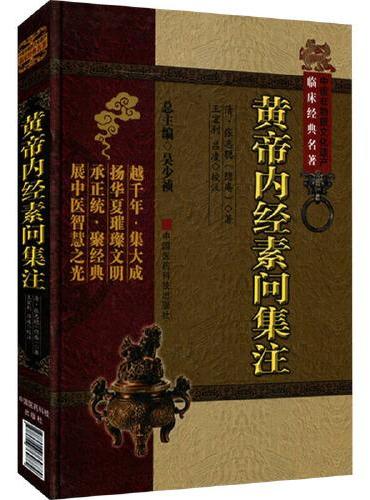
《
黄帝内经素问集注
》
售價:NT$
32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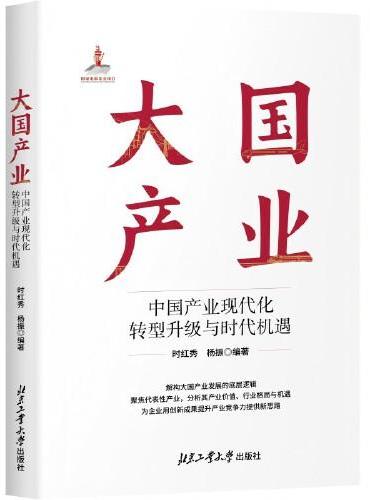
《
大国产业—中国产业现代化转型升级与时代机遇
》
售價:NT$
403.0
|
| 編輯推薦: |
|
《神女》是汉学家薛爱华的经典的唐代文化研究作之一,本此再版,邀请译者对全书进行了修订。这本书串联和追溯中国传统神话传奇中最为惹人怜爱的形象——神女,她可能是仙子、女娲、洛神,也可能是巫山神女,可能是湘妃,或龙女与雨女。在过往的传奇中,神女的形象往往与水紧密关联起来。水中女神光彩照人,然后褪去其表,或可发现在这一形象的演化中,神话与历史相互模糊了边界,从而让一个真实而悲伤的故事升格为传奇。
|
| 內容簡介: |
“神女”何谓?她从何而来,又如何出现在自古以来的诗文与传奇故事之中?
这是一本为了讲清“她”的故事而撰写的作品。美国著名汉学家薛爱华以唐代的诗文、民间传说和传奇故事为主要史料,探索中国传统叙事中的各种仙女/神女的形象,从女娲、巫山神女、洛神,到湘妃、汉女,再到书中重点陈述的龙女和雨女,这些独特的女性形象多半与水相关,以一种柔和而荡漾的意蕴寄托了古代先民对江河的崇拜。薛爱华梳理了神女们在不同时代、不同文体、不同语境的文本中,如同通过降格、隐喻、转换等方式,产生一系列变化——溺水的女子怎样变成神女,神女又如何变回溺死的女子。在文学风尚不断变化的潮流中,记录神女崇拜和中国文学传统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探讨一个神话主题形形色色的体现方式。
这本书论述的主题是各种各样的变相。它与中古早期的诗人以及神话记录者所描述的各种变化有关。它讲述一个溺水而亡的女子怎样变成神女,神女又是怎样变成溺死的女子。它讲述在文学风尚不断变化的潮流中,仙女们如何被降格,被改造成平凡的女人身,以及与此同时,那些隐喻如何被创造、如何被再次赋予新的含义。龙变形为虹,或者虹化身为神女,对这类转化,古代中国是习以为常、信以为真的。
所以,这本书旨在讨论文学作品中所开掘过的一个主题,它不是理论批评的论文,而是试图探讨一个神话主题的形形色色的体现方式,它不但体现于迷信崇拜之中,而且体现于文学作品,特别是体现于叙事小说以及抒情诗歌之中——叙事小说靠的是人物角色,而抒情诗歌中最重要的人物角色便是戴上面具的诗人自身。
——薛爱华
|
| 關於作者: |
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1913—1991),美国著名汉学家和语言学家,20世纪下半叶美国唐代研究乃至整个西方唐代研究的领军人物。1938年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士学位,攻读人类学;1947年获哈佛大学东方语言学博士学位。之后一直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直至1984年退休。曾出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并长期主编《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AOS)。
薛爱华深受传统欧洲汉学影响,重视历史语言文献的研究,加之其在民族学、民俗学和人类学方面的丰厚学养,使他的中国中古研究呈现出开阔的视野与多视角融合的特点。其研究领域主要有唐代的社会文化史(尤其是物质文化研究)、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原汉文化与周边民族文化的融合、道教与文学的关系等。
|
| 目錄:
|
代译序
四裔、名物、宗教与历史想象:美国汉学家薛爱华及其唐研究(程章灿)
引言
第一章 女人、仙女与龙
女人与仙女/女巫/龙/蛟龙/女人与龙/女娲/《老子》中的神女/神女/湘妃
第二章 中古时代之江河神女崇拜
女娲/神女/洛神/汉女/湘妃
第三章 唐诗中之江河神女
女娲/神女/洛神/汉女/湘妃
第四章 李贺诗中的神女显现
第五章 唐传奇中之龙女与江河神女
旧式龙女/蛟女/海湖神女/士子与江河神女的浪漫故事/女娲/神女/洛神/湘妃
结语
引用书目
译后记
修订说明
|
| 內容試閱:
|
神女与湘君
*选自第一章
神女
在古老的水中神女中,最讨人喜欢而又最具欺骗性、最有诱惑力而又最不可靠的,是在充满戏剧性的三峡巫山(女巫之山)安家的那一位。虽然她事实上往往无名无姓,但不同的传说却总是给她加上不同的名称。最为常见的一个是“瑶姬”,意为“绿宝石姬妾”。但是,尽管无名无姓,她的个性形象却比其他江河的神女更为鲜明。
她原来居住的山究竟在哪里,还不能确定,民俗传说和学术观点在这一点上说法不一。有位学者希望将这个地点确定在位于今日湖北的楚国故都附近,但通常的看法认为是巫山诸峰,高高耸立,俯瞰着从四川奔腾而下涡流盘旋的长江。根据古老的传说,巫山共有十二峰。唐代诗人李端写到它们:
巫山十二峰,皆在碧虚中。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十二座神圣的山峰全都有了名称,诸如“望霞”、“朝云”、“集仙”、“净坛”、“登龙”等等,恰好可以表现那种虚无缥缈的氛围,同时也切合上流社会通常对于巫山神女及其居处环境的感觉。
穿过笼罩神女及其所住山峰的翻卷的迷雾,她把君王、英雄以及巫师引诱入自己的怀抱。她的文学原型是在两篇著名诗作中受到赞美的那个让人神魂颠倒的尤物,这两首诗有散文序,旧说是宋玉所撰,而宋玉相传是古代楚国的一位宫廷诗人。这两篇作品叫做《高唐赋》和《神女赋》。在这两篇作品中,她曾经在神圣之地邂逅楚国先王,并暂时成为先王的伴侣。她从来没有与先王长时间待在一起,而总是很快就回到她在巫山的云雾缭绕的家里,把先王冷落在一边。
在第一篇赋中,神女展现了实体的一面,她是大自然的一股伟大的创造力量。在第二篇赋中,她呈现的是其非凡的一面,她是位惹人怜爱的仙女——神仙气较少,而人间气较多。但是,在这两篇作品中,她都是一个施雨与繁殖神女,她向人类展现自我时,显示的是明亮的光晕或外质——由于彩虹色彩的变化,引起这种云雾形式的变换。有时,神女本人就是以这个闪亮的光晕,作为其可爱的外形。因此,彩虹既是她的象征,也是她精神之精髓。她也是王族的女始祖。太阳使她受精,于是她有能力生育神圣的国王,有能力降雨,给人、动物以及植物带来众多的子孙后裔。
在以楚地神山命名的《高唐赋》中,描写了楚襄王在宋玉的陪伴下漫游。他惊讶地看到有雾气如柱从高唐之观上升起——这种云气时常动荡变化,忽焉改容,形状不定。楚王问诗人,“此何气也?”宋玉回答道:“所谓朝云者也。”“何谓朝云耶?”宋玉回答:“昔者先王尝游于高唐。”他接着讲述了从前楚王如何倦怠而昼寝,梦中,他见到一个妇人对他说: “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于是,王乃幸之。她离去的时候,对他说了这一番话:“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到了早上,楚王再去找她,却徒然无功。后来,他为她立了一座庙,名曰“朝云”。宋玉所作的历史解释到此为止。于是,与宋玉同行的楚王让宋玉作一篇神女赋。宋玉遵命而作。在他的作品中,他把她所居住的巫山描写成一座神秘的山,为浓重的云气所笼罩。他评说神女本身所具有的神秘力量,并以鲜艳富丽的语言,工笔描绘其美貌的方方面面,她那变化多端的形貌,以及她那渐渐消逝的魅力。她几乎是以天气现象的面目出现,闪光着,摇晃着,奔涌着,抖动着,就像一连串雾中的彩虹,但也时常像一只飞鸟。她最为活跃的时候,甚至让人类和动物都心生惊恐:
雕鹗鹰鹞,飞扬伏窜。
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抵挡这幅温柔景象的威力。她也具有龙的某些特征:
上属于天,下见于渊。
宋玉留给楚王一个希望,只要楚王能够恭谨地准备祭献仪式,他就有可能像其祖先那样遇到这位迷人而又威力无边的神女——这个经历将会净化他的身体和精神,给他带来令人难以置信的长寿。
毫无疑问,巫山神女是古代一个生殖女神,她与巫王仪式性的结合,对于大地的安宁康乐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诗人让她负责万物的生长。所有现象皆由她而滥觞。她是古代宇宙神话的文学版本——一个无形无状无名的云雾神女,孕育了种种可能性。她有很多方面与“道”相一致,同时也让我们联想到伟大的女创世者女娲。
在第二首诗即《神女赋》中,作者笔下的神女多少更靠近尘世一些,但他并未忘记赋予她以殆非人间所有的魔力。她既是一幅神仙景象,同时又是一场性爱梦幻。在这里,我们又看到楚王和诗人一起漫步在那片称为“云梦”的地区。宋玉又叙述了高唐的故事。那天晚上,楚王就寝之后,他梦见神女向他走来。第二天早上,他满怀激情地向宋玉讲述他的奇遇:
其象无双,其美无极。
但是,尽管有这种神灵的诱惑,她依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诗作以惆怅郁悒的音调告终。这种在浪漫奇遇之后别离的悲伤主题,为后世所有关于巫山的诗作设定了基调。实际上,这两篇赋在中世纪诗歌中培育了大量的模仿者,生产了一大批或隐或显的典故。在这些诗作中,随着时间的流逝,性爱色彩越来越鲜明,而神仙色彩则越来越黯淡。
古典的巫山彩虹神女(或者说与其非常相似的神女),在最受人崇敬的诗集《诗经》中也能找到。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由于数世纪间令人肃然起敬的儒家《诗经》注释越来越晦涩,她的存在几乎无法辨别。但是,已故学者诗人闻一多经过论证,指出她实际上在这部诗集中出现过,被人称为“季女”,特别是她曾大肆施展浑身魅力,在性方面采取主动姿态,并且扮演美艳诱人而又无所不可的少女角色。在一批《诗经》作品中,她都施展魅力,引诱情郎。她经常化身为一阵雨,或是一片朝雾。不管她披的是什么外衣,对她的崇拜通常都起源于对氏族女始祖和繁殖女神的崇拜。对她的祭祀,是与远古时代每年春天举行的部落婚配仪式密切相连的。她似乎与南方有某种关联,也有可能,即使她并不等同于宋玉赋中那个秀色可餐的神女,她也是亲缘很近的堂姐妹,只不过以某种方式游离,而进入到更为清明冷静的北方诗歌和神话传说之中。认同神女就是虹,这种观念在汉代的时候还非常流行,例如就有这样一种权威的看法,认为虹亦可称为“美人”。
湘妃
在中国诗人的心目中,唯一能与这位秀美的虹女那轻柔空灵的形象相比拟的,就只有湘水女神了(伊师塔变成了伊希斯)。湘水是中国南方的一条大河,它向北流经湖南,汇入长江中游及其犬牙交错的众多湖泊中,这是古代楚国的一个神祇所管辖的范围。由于她至少在过去曾是湘水女神,她与巫山神女也颇为类似,但她原先并不是楚王的妃子:她是一大片水域的威力无边的女保护人。她管辖的范围不仅包括湘水,而且包括广阔的洞庭湖流域以及壮阔的长江中游流域。有两篇模仿古代巫歌或是宫廷根据古代巫歌而改编的作品,勾画了她的古典样貌,其中写到,一个男巫向她求爱,但他的运气比宋玉那两篇诗作中写到的那位天赐方便的楚王差多了。
承载她的媒介是两篇作者尚不明确的赋体风格的名作,尽管传统说法将其著作权归于令人肃然起敬的屈原名下。两篇作品名为《湘君》和《湘夫人》。它们详细阐述了一个古老的、大概属于南方的口头文学传说,这一传说本身显然即是巫术实践的组成部分。它们保存在一部被称为《楚辞》的作品集中,至今犹存,现存《楚辞》一书,是从公元前一世纪编纂的一部选本发展而来的。
从汉代开始,这些华丽的辞藻所描绘的画面,有一部分被世俗化了;或者说,其意义主要从世俗角度来解释。取得这个成绩,要归功于将古代文献中的神话历史化的官方政策,此项政策用一层又一层厚厚的讽喻性阐释,把那些不受欢迎的幻想性或想象性的描写掩饰起来。周代以后新兴的正统观念反对泛滥的宗教表达,因此,对诸神和巫师们都得重新解释,以消除其影响。
只要适当思考一下就会发现,《楚辞》中三首涉及水中女神和繁殖女神的诗篇——《湘君》、《湘夫人》和《山鬼》,它们全都包含在《楚辞》的《九歌》之中,都是巫师献给他们的主人,亦即这些神祇的赞歌。它们留下了向神灵求爱的遗迹,并以戏剧性的方式表现出来,只不过有些变形。不幸的是,在这些残缺不全的剧本中,哪些是对话,哪些是舞台提示,界限大都含混不清。尽管在后来的主流传统中,这三篇诗歌中的头两篇指的是湘水的两位神女,通常认为她们俩是姐妹,但现在有一种更合理的看法,认为这两首诗都与这条南方大江独一无二的神女有关。
随着时间的流逝,她们的传说逐渐与关于另外一对神女的传说混淆起来:湘君据说就是娥皇,而湘夫人则借用了女英的称呼。在以其命名的《楚辞》篇章中,湘夫人也被称为“帝子”。这一称号见于《山海经》,其文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这两个可爱的女子也被吸收到关于伟大的帝尧的传说中,而尧则通常被视为《山海经》中提到的“帝”。因此,湘水女神就变成了尧之二女,而且嫁给了尧的继承人舜。在综合多种神话的基础上,产生了中古时代人们普遍接受的一种看法。唐代诗人刘长卿《湘妃诗序》为我们梳理了所有相关的古代文献,颇为方便。他总结说,在两个神女中,娥皇年龄较长,因此是帝舜之后,而女英较幼,故为帝舜之妃。在本篇论文中,湘水神女,不管用什么名称,都将使用单数形式,以保留其上古的特性,除非在特别顾及某些早期中国作家的观点时,才有必要改为复数。在他们眼中,她在形式上并非一人,而是两人。
也有人曾经提出,这位夫人或者这两位夫人并不仅仅是江河、湖泊和施雨的神女,而且也是月亮女神。娥皇不是别人,正是嫦娥(原来叫恒娥),即民间流行传说中耳熟能详的月亮女神。这种说法很可能是对的,因为她们彼此名字相似,而且在宗教和神话方面,又同样与女性—月亮—水有联系。
虽然隐藏在《湘君》和《湘夫人》那种神奇而又几乎使人迷惑的语言之中,我们仍然可以侦察到那种化石化的仪式:一个男巫在湘水神女最可能惠临的洞庭湖上,乘着画船出行,代表他的人间代理人寻求她的陪伴——这对他自己无疑也是有利的。(在其他地方,他乘的是一条龙,而龙舟在中国则随处可见。)两首诗的语言不仅充满洞庭湖水和有关龙的典故,而且有一大堆鲜花和香草。巫师似乎还在神女宫殿附近的水面上撒下花瓣,他许诺将来还会源源不断地送上礼品。一切都无济于事。神女似乎全神贯注于其他事情,对他的奉承无动于衷,巫师遭此挫折,萎靡困顿。
《九歌》中第三首有关女神的诗作,是献给“山鬼”的,它显然与巫山神女有关——旧题宋玉所作的那两篇伟大的诗作,其关注中心也是这位欢快的神灵。
这些作品中所描绘的神女绝不是如雾如梦的尤物。她们更像从奢靡的香薰沐浴中徐徐走来的优雅女子。当然,她们所有人都身份模糊,可以互换。尽管那些严肃持重的儒家学者努力要将她们与虚假的历史人物联系起来,尽管后来的神话编集者只将她们当作是溺水而亡的女孩变成的神灵,她们永远都是水神。
当我们试图从较开阔的语境来理解这些诗作时,循着霍克思的思路,我们就不会误入歧途。霍克思提出,楚国的这部诗集以某种形式保存了个人作品。霍克思认为追寻神女的主题与另一种常见的巫术主题(即遨游宇宙的神奇旅行,将自己的心灵注入神的领域)密切相关。但是,他的结论是,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这种追寻神女的主题不及宇宙遨游的主题那么繁盛。他注意到,在司马相如之类的作家手中,这种神异的旅行被改造成了理想化的帝王巡行:皇帝所周游的世界,可以象征性地还原成皇家畋猎园囿的上下、前后、左右各方面。全篇诗的结构,变成了君主神圣权威的象征。他周游于精心设计的园囿的各个区域,对应的是世界的几个区域,这种周游还能保证他对宇宙万物的掌控。扩展微观世界,是为了获得对浩瀚宇宙的神奇的控制,就像以严整步伐走过一座设计精当的花园,不仅是对穿越天堂之行的模仿和象征,而且事实上可以变成一次穿越天堂的旅行。诗中所写的这种全景图像,让我们回想起能够代表垂死的萨满宗教的那种心醉神迷的景象。他们本身是恍惚出神的状态,却变成了令人出神——言辞的魔力因其自身的缘故而让人欣喜。在不知不觉中,巫师已经被帝王甚至诗人取而代之。
下文我将努力展示中古时代“诗人巫师”艺术表现之个案,尤其是唐代诗人李贺,他似乎颇为怀旧地认为自己就是古典的巫师英雄。这种表现必然导致的结果就是,在周代以后的文学中,追寻神女的主题作为灵感的来源之一,并非如霍克思所言不及宇宙遨游的主题那么重要,相反,它已从辞赋形式转向传奇小说和抒情诗歌。实际上,我倾向于把这两种主题(追寻神仙和漫游宇宙)的分别,解释为仅仅是侧重点之不同,而不是霍克思所提出的截然分别的两种主题。召唤神女或者幻想神女到来,正是神游之人试图在水晶宫殿里找到她而付出努力的重要部分。这两种主题经常交错在一起,在世界各地的神话中反复出现:英雄的幻想行程及其与神女的神秘联姻,至少可以上溯到古巴比伦时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