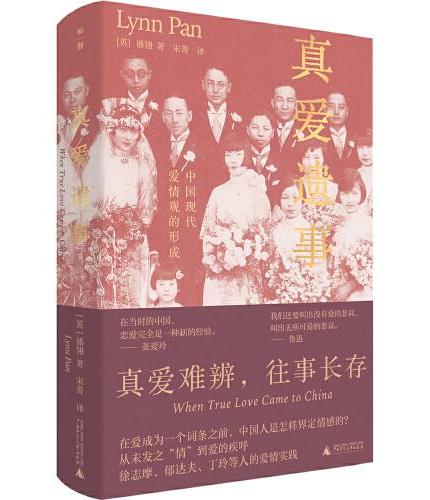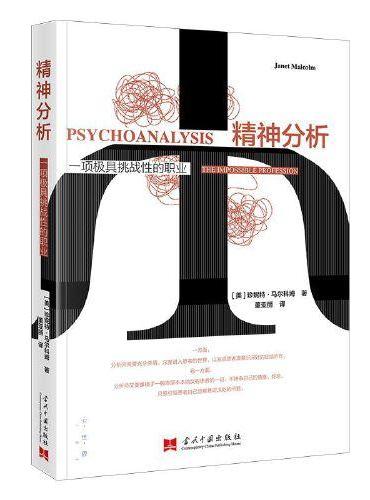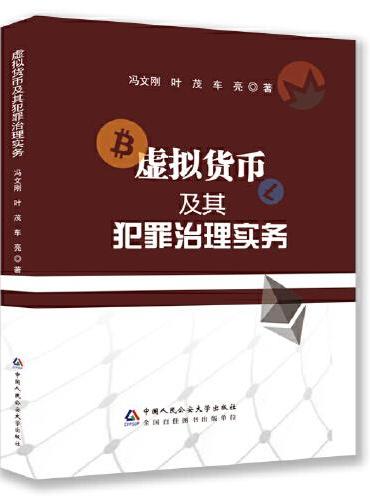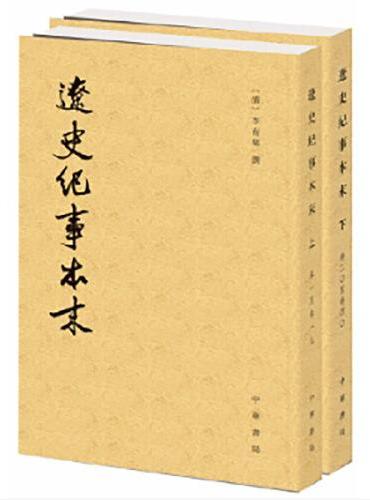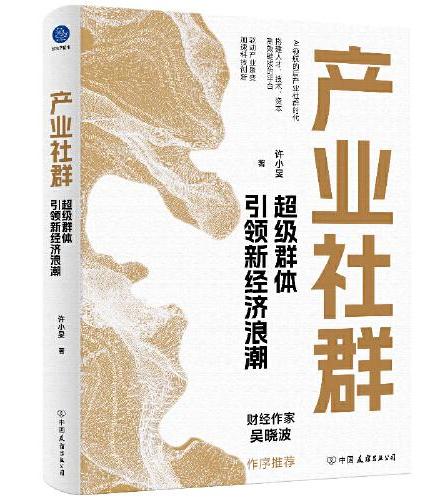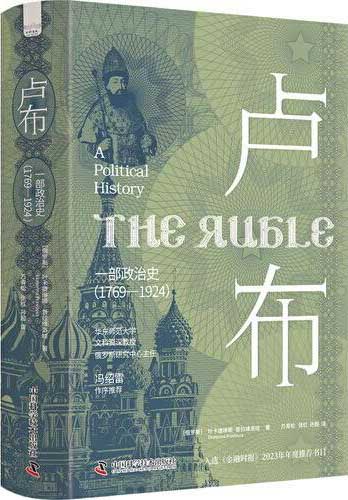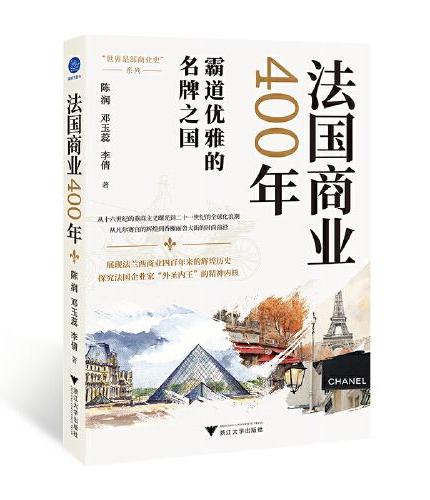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广州贸易:近代中国沿海贸易与对外交流(1700-1845)(一部了解清代对外贸易的经典著作!国际知名史学家深度解读鸦片战争的起源!)
》
售價:NT$
4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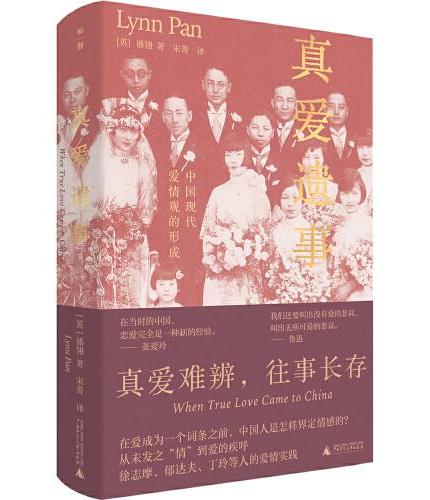
《
真爱遗事:中国现代爱情观的形成
》
售價:NT$
55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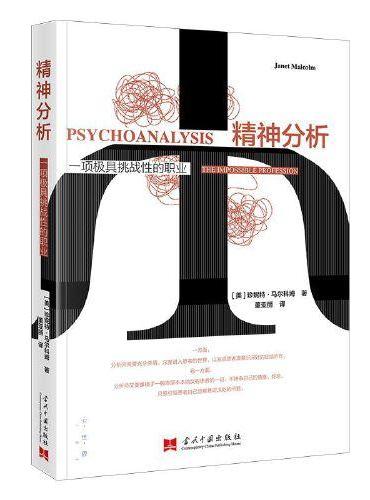
《
精神分析:一项极具挑战性的职业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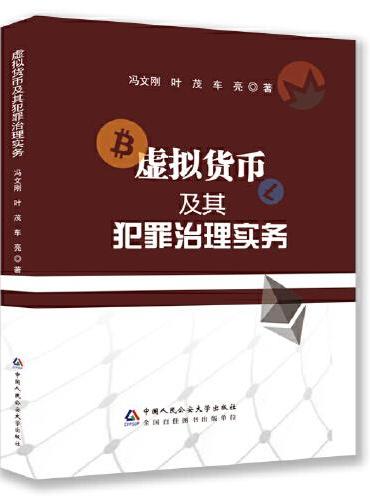
《
虚拟货币及其犯罪治理实务
》
售價:NT$
2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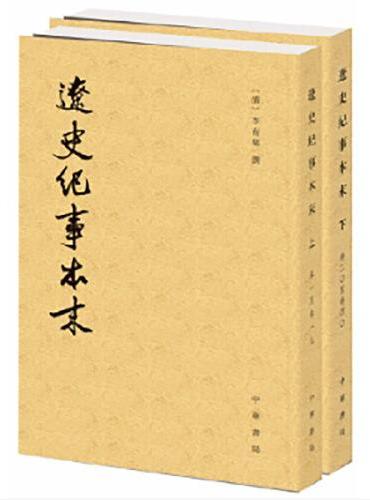
《
辽史纪事本末(历代纪事本末 全2册)新版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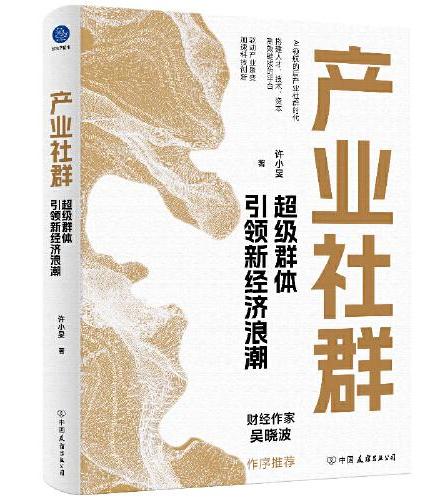
《
产业社群:超级群体引领新经济浪潮
》
售價:NT$
31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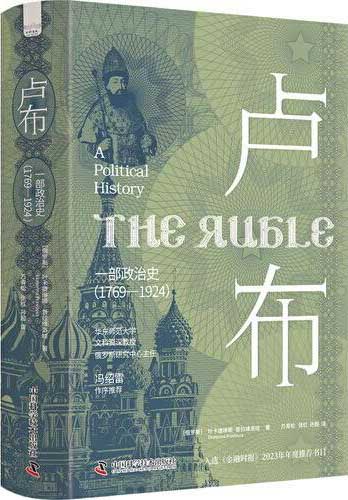
《
卢布:一部政治史 (1769—1924)(透过货币视角重新解读俄罗斯兴衰二百年!俄罗斯历史研究参考读物!)
》
售價:NT$
55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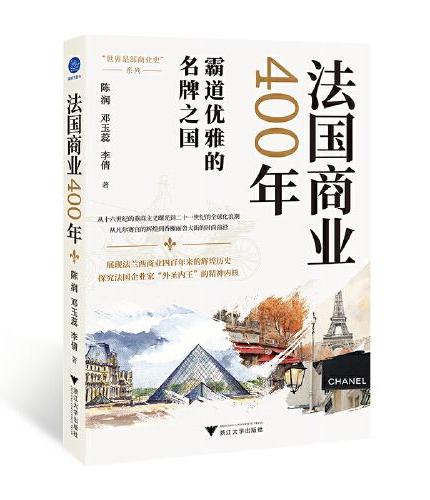
《
法国商业400年(展现法兰西商业四百年来的辉煌变迁,探究法国企业家“外圣内王”的精神内核)
》
售價:NT$
347.0
|
| 編輯推薦: |
1. 倔强少女VS偏执少年,“事业脑”和“恋爱脑”也可以是天生一对,是最适合彼此的存在。
晏藜:#在梦想和未来面前,那点心动情愫都算不上什么的“事业脑”女主#
晏藜只有一穷二白的口袋,和拼命想往上爬、想改变命运想疯了的心,因此她只能靠勤奋,靠比别人更多甚至几倍的付出,努力去够到那些别人轻易就能得到的一切。
她当然可以心动,但谁都别想用她的心动当把柄。
江却:#一开始蓄意接近占据主导地位,结果最后自己先栽进去的“恋爱脑”男主#
江却是疯子,是固执的、极端的疯子。就像他们十八岁那年,他追着她的火车跑了二十多分钟那样疯。
心动不是她的把柄,是他的。
2. 酸甜但治愈的现实童话——
爱而不得、恨而不舍,哪怕在爱人这条路上走得再坎坷主角也没有放弃过追逐,所以才有久别重逢后的破镜重圆。
当年晏藜想结束这段藕断丝连,所以她把江却逼到绝路。可她没有想到,对她,他从来没有绝路,只有绝处逢生。
她离开了五年,他就找了她五年。
那年苦夏他没有等到的人,没有等到的答案,经年累月,念念不忘,如今终有回响——
“晏藜,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
| 內容簡介: |
在一个蝉鸣不止的难熬苦夏,晏藜遇上了江却,这个光风霁月的少年从此闯进了她的生命。
他逆着光飞奔而来,救她于绝望之中。
他对她说:“没事了,别怕。”
之后分开的那么多年,晏藜再也没有遇见过如江却这样风骨卓绝的少年。
江却一直是极聪明的人。
他的人生已经早早规划好了方向,从未偏航。
直到那年夏天,他的衣摆被晏藜拽住,少女呜呜咽咽地哭着,让他心疼。
她的眼泪第一滴落在他的校服上,第二滴落在他的心上。
像一颗火种,径直在他心脏上烫出一个洞。
|
| 關於作者: |
槐序青棠
擅长书写美好青春,相信文字拥有无穷的力量,也希望用文字之美带给读者简单的快乐。
微博:@槐序青棠
|
| 目錄:
|
目录
楔子
第一章 端盘子那个叫晏藜
第二章 传说中的江却
第三章 草木皆兵的十七岁
第四章 江却的目的
第五章 收敛
第六章 披着羊皮的狼
第七章 他上钩了
第八章 真心换真心
第九章 给喜欢的人送苹果
第十章 夏天又快来了
第十一章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第十二章 只有路窄的冤家
第十三章 你就当我们从来没有认识过
第十四章 我想光明正大地爱一个人
第十五章 别怕
第十六章 我好想我们能有以后
第十七章 这就是爱
番外一 真正的天长地久
番外二 阳和启蛰
|
| 內容試閱:
|
楔子
一部电影落幕的时候,晏藜注意到最下面的进度条,足足两小时零十三分钟。
她从榻榻米上下来,披了件针织开衫,长至腰际的黑发末梢带着微卷,如海藻一般披散下来。
墙壁上的文艺挂钟指向九点过两刻,她慢步走到玄关,外头已经没了动静。
周遭很静,静得人发慌,落地窗外的高楼大厦偶有亮光,掺杂着隆冬呜呜的风雪声。
她握着门把往下按,咔啪一声,门应声开了。
下一秒,晏藜的目光触及门外的人,忽地愣住。
外面站着的男人,也就二十多岁的样子,他穿着黑色的毛衣和驼色的外套,身姿颀长,就那么站着,静静地看着她。
晏藜记得电影有两个多小时,那么他就站了两个多小时。
江却是疯子,是固执的、极端的疯子。
就像他们十八岁那年,他追着她的火车跑了二十多分钟那样疯。
他少时曾在给她的字条中写——“晏藜,我会和你纠缠一辈子”。
他做到了。
第一章
端盘子那个叫晏藜
1
1999年,晏藜第一次来到南平。她和母亲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看着人声鼎沸的鼓楼区火车站。这个自小在南方长大,说一口吴侬软语的小姑娘,还是对未来充满期待。
那年她十三岁。
父亲新丧,母亲很快给她找了个继父,她母亲说继父人很好,于是她渐渐忘却了那个凶神恶煞般的、已逝的生父。
但她没想到,她腐烂的人生也自十三岁那年开始,彻底拉开了帷幕。
鼓楼区分新旧,旧城区这时候还多是破败的楼群,拥挤、潮湿,四个字足以概括。南平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发展迅速的城市,但鼓楼旧区仍像过去一样,在这个城市里格格不入地苟延残喘着。
晏藜是被门外剧烈的吵架辱骂声惊醒的。她睁开眼,外面天还没亮,盛夏的清晨带着露水的凉意,从半开的泛着铁锈的窗户侵袭进来。她把薄毯整齐叠好,好像听不见外头激烈的战况似的,兀自慢吞吞地换好了洗得发白的衣服。
开门,迎面砸过来一个烟灰缸。晏藜不疾不徐地侧身,玻璃制的烟灰缸应声而落,清脆的一响过后,是更难听的男人的辱骂声:“丧门星!老子看见你就烦,趁早滚。再让我看见你,我掐死你!”
骂声浑厚有力,中气十足,晏藜却像没听见一样,她面无表情地越过一地狼藉的客厅,去卫生间洗脸刷牙,然后去厨房盛饭。
留下身后此起彼伏的男人女人的吵嚷打砸声。
赵文山穷,所以晏藜和她妈周琴一起受穷。所谓的早餐不过就是用昨晚的剩饭做的烂糊粥,还有半个没热透的、半硬的馒头。
头顶的灯因为年久已经有些泛黄了,和厨房随处可见的油渍一样泛着让人恶心的光。晏藜今天还要去做兼职,她只犹豫了两秒,就把那个一看就很难吃的馒头拿了起来。
她十七岁了,过完暑假就高二了。
因为上学期考了全市第六,她得以从十三中转到一中,免去学杂费和学费,还得到了一笔不菲的奖学金。
晏藜想起来,低头看了看白皙胳膊上的淡淡疤痕——奖学金被赵文山夺了,她在抢夺过程中被他推到地上,胳膊被锋利的柜角划过,就留下了这道疤。
赵文山是晏藜的继父。
客厅的骂战还在继续,现在又多了女人拔高腔调的哭叫。晏藜啃完馒头,喝了几口稀饭,就回房间收拾了,路过客厅时,免不得又要被连累着再受几句骂。
三言两语,晏藜不用猜都知道他们是怎么吵起来的,无非是些鸡零狗碎。赵文山总是会想尽一切办法地羞辱她们母女俩,以达到发泄怒火的目的。他无能,做什么生意都赔钱,回家了就找个由头把晏藜母女俩打一顿出气。
他该改名叫赵窝囊。
晏藜挎着帆布包下楼,社区门口“惠民小区”的铁牌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得东倒西歪,沾着仲夏清晨的露水,她能听见远处微微嘈杂的早点摊叫卖的声音,馄饨、包子、豆腐脑,清澈空气里若隐若现那些摊子上独有的炝香辣椒油味儿。
她在旧城东的蔡家牛肉面馆做兼职,从早到晚。那家店白天卖牛肉面,晚上就在店外面的空地支起塑料桌椅,卖烧烤。
这个点儿店里没什么人,晏藜纯粹是为了逃出来才拿兼职当借口的。她走得很慢,新城区里被视为违章建筑的石梯坎路,旧城区遍地都是,老旧的房子被这些路分得高低错落,一抬头就是遮天蔽日的桑榆香樟,还有乱七八糟的电线。
日头还没毒辣起来,但毕竟是七月份,已经有很热烈的蝉鸣了,给早起来往的人们平添了一份焦躁。
晏藜到店里的时候,只有前台坐着的蔡家的老板娘,戳着计算器的手指短粗白腻,脑门子一片反光的细汗。晏藜只知道老板娘姓赵,吃得滚圆,脾气暴烈。
晏藜才到后厨放下包,就听见外面老板娘的叫声:“小燕子,出来把牛肉洗了,待会儿喊吴师傅给它卤上,手脚麻利点儿……”
“小燕子”是老板娘给晏藜取的外号。这小馆子里大大小小的伙计,包括老板,都有各自的外号。这女人喜欢看琼瑶剧,店里人的外号多少都跟那些电视剧沾点儿关系。
晏藜低眉顺眼地系上围裙,去搬那个大塑料盆,里面盛了一块老板娘大早上请人送来的牛肉,还没处理,腥气冲天。推开门帘子出去的时候,她看见一个男人从另一头进来,胡子拉碴的,衬衫领子撇到一边。
“热死了,怎么不开风扇啊?”那男人叫喊着,声音粗噶,常年吸烟的嗓子像含了一口浓痰。
“开开开!就知道开风扇!一个月多少度电都是被你糟蹋的!一大早热什么热,嫌热滚出去,敢情这馆子不是你自己家的。”
胖老板娘尖厉的骂声落下,里面果然噤声了。这一幕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面馆里上演,蔡家面馆的老板是个老烟枪,挥霍无度,他老婆却是个尽人皆知的抠门鬼,挂在嘴上最多的两个字就是“省钱”。
一大早热得出汗的明明就是老板娘自个儿。当然,这话晏藜也就敢在心里说说。
十一点多,面馆里才陆陆续续有客人。
晏藜既要打杂又得跑堂,十几个来回下来,不到半个小时她后背就洇湿了。十一点半,蔡家的儿子上完暑假补习班回来,带了一群朋友冲进面馆。
“蔡景辉,你家这饭店真气派啊。这顿你请啊,吃完了哥几个带你去城南玩。”
“跟着我们,以后就不用怕了。”
一群人围着最中间那桌坐下,你一言我一语地吵嚷着,满屋的客人都看过来几眼,又摇摇头埋头吃自己的面。
晏藜的头低得更低了,她端着盘子,快步绕过那桌。
“晚上啊,带你见见我江哥。”远远地,晏藜听见领头的那个黄毛得意地放着话。
回后厨要经过前台,晏藜抬眼就看见老板娘跷着二郎腿坐在那儿,一脸慈爱地看着不远处的儿子。晏藜张张嘴,想说什么,又咽回去,默不作声地走了。
蔡景辉带来的那几个人,晏藜认识,是十三中出了名的刺儿头,不务正业最精通,逃课惹事第一名。
蔡家就这么一个儿子,跟他们玩,迟早被毁。
晏藜洗着菜,把烂菜叶子揪下来,扔到角落里。
“跟我有什么关系,瞎操心。”她想,把那些念头都烂在肚子里,省得自找麻烦。
晚上七八点,是崇安街最热闹的时候。
这条街纵横旧城区,头尾都是小吃店和杂货店,中间乌泱泱的社区楼,盖到七八层就顶天了,跟另一头的新城区实在不能比。
蔡景辉掀开后厨布帘的时候,晏藜正刷着盘子。
“晏藜,新上的那碗面,不要香菜不要小葱啊,多放牛肉。”男孩儿黑瘦,面容乍一看透着两分市侩之气。
他俩以前都是十三中的学生,只不过不是一个班。后来晏藜来找兼职,一开始蔡景辉他妈看不上晏藜,觉得她太瘦干不了活儿,还是蔡景辉一听她也是十三中的,才让他妈把她留下来。
蔡景辉这人,说好不好,说坏也不坏,只不过晏藜承过他的人情,他也没坏到她头上过,所以两人见了面说话还算和气。
“好。还是送到你那桌,加四瓶饮料吗?”
蔡景辉嘿嘿笑了下,伸手比了个数:“不不不,六瓶,我大哥今天带了个朋友来。”
晏藜点点头,对方就出去了。
后厨太热了,晏藜洗了手把松散的头发又扎了一遍,反光的推拉玻璃上泛着暗黄色的污渍,不甚清楚地倒映出她那张脸。
素面朝天,算不上漂亮,除了白,最显眼的就是她那双不讨喜的、狭长清冷的眼。
她端着托盘出去,中碗的招牌牛肉面,二十串烤羊肉。
扑面而来的闷风,混杂着佐料刺鼻的香气,嘈杂的人声、蝉鸣和狗叫,隔壁发廊外放着粤语歌,晏藜在这么一片纷乱里,目光搜寻着蔡景辉那一桌。
天蒙蒙黑,崇安街的路灯一如既往的昏暗,但晏藜还是第一眼就看到——也是那人太出挑,生着一张白皙明朗、下颌冷硬的脸,穿着蓝白校服,坐在一众平庸里。
这乌糟糟的地方,一抹这么扎眼的白。
2
“不要香菜不要小葱的面,就是江哥的。”蔡景辉喊了声,下巴点了点那个人。
晏藜把面和烧烤放下,桌上已经有人认出了她。
旧城区就这么大,大部分学生都在排名靠后的几个普高和职高上学,晏藜瞥了一眼那个“江哥”的校服,不是十三中的红,也不是职高的黑,看样式应该是新城区一中的。
桌上还有几个女生,一开始她们声音还压低着笑,等到晏藜收了托盘转身之际,那几个女生的嗤笑声陡然拔高了——
“还真是她啊。无语死了,怎么哪儿都能碰见,苍蝇似的,讨人嫌。”
“谁说不是呢,在学校抬头不见低头见就够恶心的了,出来了还得被迫看她那张虚伪做作的脸。真以为自己多高贵,装什么呀。”
“再高贵不还得给咱们端盘子倒水吗?学习好有什么用,得第一又怎么了,屎盆子镶金边。”
屎盆子镶金边,这话真是够难听的。
晏藜欲要离开的脚步顿住,她脸上还是那副要死不活的冷漠表情,转过头,静静地看着那些人。搁在以前,她可能会骂回去,只是这会儿对方人多势众,她打不过不说,再丢了工作,得不偿失。
只是她们话没说完,为首的黄毛像是突然反应过来什么,重重地拍了他旁边的女生周盈婼一巴掌,啪的一声脆响——
“说什么呢!没长眼睛,没看见江哥还在这儿?骂人就骂人,干什么提‘学习好’这几个字,江哥学习也好你又不是不知道,胡扯什么呢……”
晏藜不自觉地把目光又移向刚才那人,然后才发现他也在看她,只不过表情没什么温度,好像也并没有因为周盈婼等女生的冒犯而生气。
对视只有一瞬,对方立刻就收回视线了。
晏藜大概懂了,这人是一中的,成绩应该不错,在这帮人里有着不低的地位。
她前脚走,就听见身后周盈婼仓皇失措的道歉声,也是喊“江哥”,然后再指名道姓地点她:“我们……我们骂的是那个叫晏藜的,就刚才端盘子那个,不是说你。江哥你都不知道,那女的在学校有多讨嫌,特别装……”
直到她进屋,听不见那些声音了,他也没有回一个字。
怪人。
晏藜不懂,放着大好的出身和前途,竟然跑来和黄毛他们鬼混,真怪。
直到晏藜进后厨了,江却才不着痕迹地收回目光。
他摆摆手制止了周盈婼还没说完的话:“没事,先吃饭吧。”
周盈婼微红着脸点点头,刚才在众人面前的飞扬跋扈消失得一干二净:“江哥大度,我敬你一杯。”
江却点头,却抬手护住自己的杯子:“我自己来。”
江却这是不抬举她。
周盈婼收手,也不介意。桌上但凡见过江却的人,都知道他是什么脾气,一直以来他对谁都这样,冷淡疏离得要命,少有好脸色。
江却喝了一口,碳酸饮料刺激的气泡感从口腔流到喉咙,冰凉的温度勉强压住他心头莫名的焦躁。他微侧过眼,又看向没动静的后厨布帘。
黄毛离江却最近,看江却放下一次性塑料杯,就歪着头凑了过来:“江哥,刚才那女的不就是以前你问我的那个吗?可巧了,这家店是辉子他家开的,那女的就在这里打工。周盈婼她们都认识她,你想打听什么,尽管问呗。”
其他人一听,尤其周盈婼,一下子来了兴趣:“江哥也认识她?江哥不是一中的吗,怎么连这种人都认识?该不会是名声太臭,都隔着半条江传到新城区去了吧……”
江却默不作声。
晏藜,晏藜。这个名字,早就已经刻在了他脑子里。
周遭乱嚷嚷的,江却眼前恍惚了一下,好像又回到他十二岁那年,在医院,周围也是这么多七嘴八舌的记者,他被父亲牵着,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叫晏藜的女孩儿,对着话筒污蔑他母亲。
他眼里丝丝缕缕地泛起恨,然后一瞬又消失了。
黄毛他们摸不准他对晏藜的态度,面面相觑了一下,除了几个女的,没人敢轻易开口。
看这样子,像是认识,但是哪种认识?要是关系好,他们可不敢乱说;可要是关系不好,他们倒是可以顺坡往上爬,多说人家几句难听的,讨江哥高兴。
江却看出他们眼中的顾虑,垂下眼帘:“不用担心,有什么说什么。”
认识周盈婼的人都知道,她平生最恨十三中霸榜第一名:晏藜。
恨晏藜什么?
—— 明明晏藜穷得要命,跟大家一样都是旧城区的,却喜欢装清高,成天板着一张脸,让人看了就晦气。学习好,但是不合群。周盈婼身为学姐,还总是被老师以晏藜为例子训斥她。
江却早就听腻这些话了,一模一样的东西,黄毛以前就跟他讲过。这些话不是他想听的,他也从不觉得这些是缺点。
乌鸦群里出了只凤凰,所有的乌鸦都会嫉妒,要啄脏凤凰的羽毛才肯罢休——明明大家出生的时候都是乌鸦,凭什么就你成了凤凰!
江却见怪不怪了。
“没了吗?”他淡淡开口,看向周盈婼的眼神像攒了一丝凉霜。
周盈婼愣了一下:“没……没了吧?”这些罪状难道还不够让人讨厌的吗?单拎出来任何一条,都可以引起桌上所有人的共鸣啊。
江却闭了闭眼,眉眼间有一点儿不耐烦,正要开口,视线却忽然捕捉到那抹清瘦的身影。
晏藜抱着几瓶啤酒出来,去了门口那一桌。那桌大多是三十多岁的男人,微胖,穿着拖鞋、背心,啤酒肚格外显眼。
那些人笑得很大声,江却这桌听得清清楚楚,但不知道其中一个男人跟晏藜说了什么,她例行帮忙开了酒瓶后,没有立刻离开,而是自顾自倒了一杯,满上,然后面无表情地端起来一饮而尽。
几个男人都油腻猥琐地笑起来,第一个开腔的人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票子扔在晏藜的托盘里。
她转身回去,把钱折了折塞到口袋里。到门口时,路边不知道哪儿来的流浪猫,好像还怀着孕,大着肚子匍匐到她脚边,刚叫了一声,就被她冷着脸跺脚撵走了。
这场面,简直是现场给了周盈婼等女生一个切入点。
江却的目光还没收回来,旁边已经争着抢着开始骂了——
“你们看吧,真是不要脸啊,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学生,看她刚才那谄媚样,在学校的时候不是清纯得很嘛。”
“真够恶毒的,自己堕落就算了,连可怜的流浪猫都不放过……”
正说着,刚才逃走的那只流浪猫又拖着身子蹭到了他们这一桌,像是要讨吃的,被周盈婼一脚踢开:“滚开,小畜生,脏死了。”
那流浪猫惨叫一声,尖厉凄然。
江却皱了皱眉,再开口,声音带着冷嘲:“你跟她,好像也没什么区别吧。”
晏藜刚才原地跺脚只是吓吓那猫,周盈婼口口声声说晏藜恶毒,自己却毫不犹豫上脚就踢了。最有意思的是,她们竟然还能如此理直气壮、大言不惭地说出来。
一桌子人都怔住了,气氛一下子冷到极点。
然而他们都没想到,江却竟然还有后半句,他讥笑一声:“也不是,你没她强。她靠自己挣钱,最起码骨头不软。”
江却面前的面动都没动一下,他拿了钱扔在桌上,站起来,长身玉立的模样:“这钱是今晚一桌的饭钱,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他对晏藜是有私怨,但那是他们的事情。他厌恨晏藜,和他看不起周盈婼等人的胡说八道并不冲突。他忽然有点儿后悔自己当初为了打听晏藜就默认黄毛他们接近他了,跟他们打交道,让他异常烦躁。
江却推开塑料椅子就要走。黄毛他们后知后觉,一个个站起来,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好,面面相觑。
周盈婼等女生脸都丢尽了,气得半死,江却前脚走,她们后脚就叫骂起来,叽叽喳喳地引来周遭不少人的注视。黄毛一巴掌扇去:“行了吧,你还嫌不够丢人?得罪了江却,咱哥几个都没好果子吃,你看你干的好事儿!”
周盈婼瞬间噤声,捂着脸悻悻地坐下了。
晏藜在后厨,对外面发生的事一概不知。
直到那群人吃饱喝足地散去了,蔡景辉一路小跑到后厨,掀了帘子喊她:“晏藜,刚才对不住啊。你知道,我跟黄毛他们玩,也就是想在学校寻个庇护,刚才那场面,我实在没办法帮你说话,只能当怂蛋。”
晏藜低着头,手里的不锈钢钵子盛着还没拌匀的黄瓜和调料,一边搅拌,一边不太在意地回:“没事儿啊,我都理解。”
只是蔡景辉转身要走时,晏藜叫住他,问了一句:“刚才那个穿校服的,他叫什么?”
蔡景辉食指蹭过鼻尖:“好像叫……江却。你打听他干什么?”
晏藜扬了扬手里的钥匙串:“还能为什么,人家东西落下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