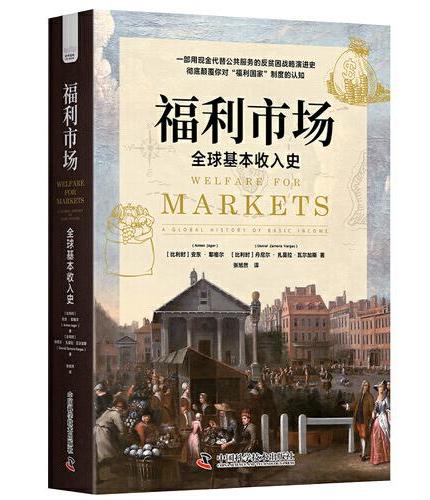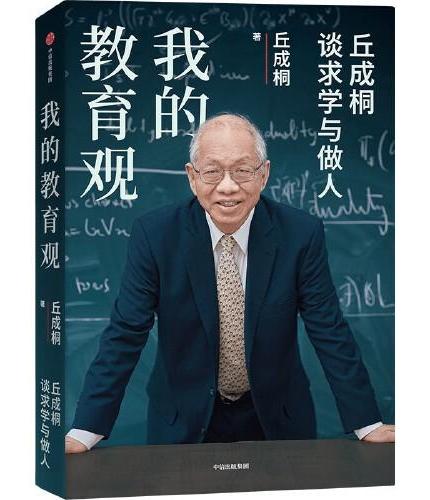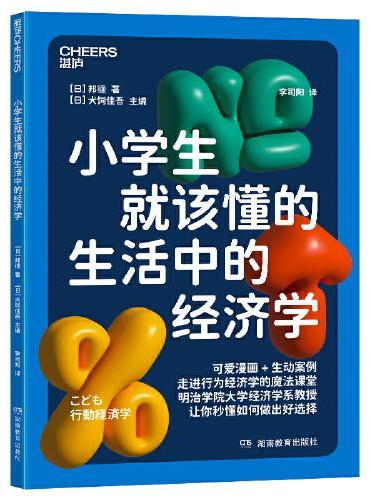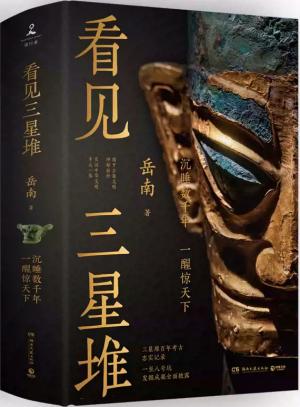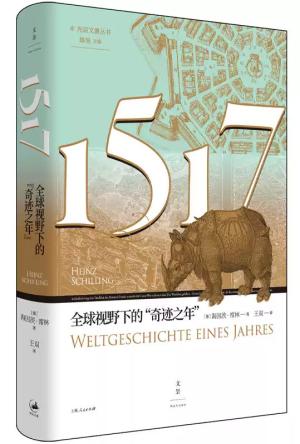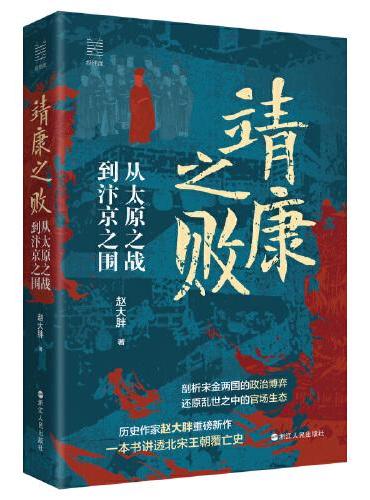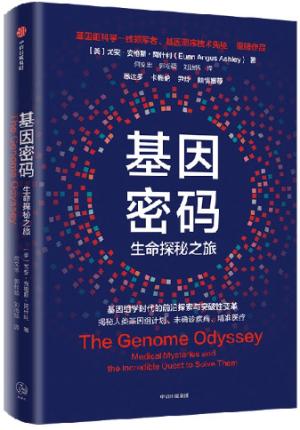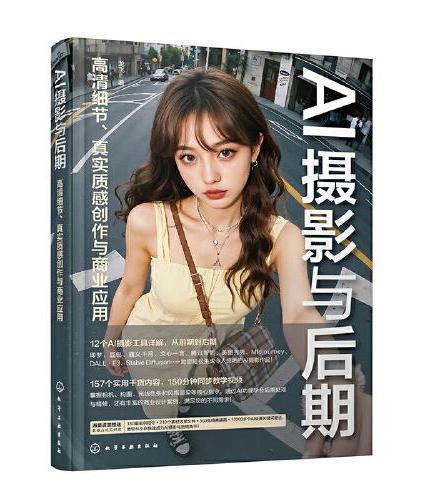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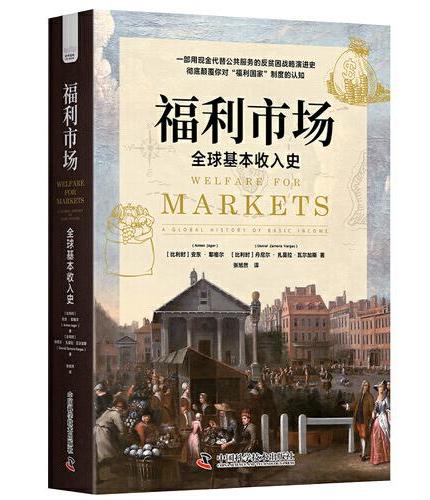
《
福利市场 : 全球基本收入史
》
售價:NT$
4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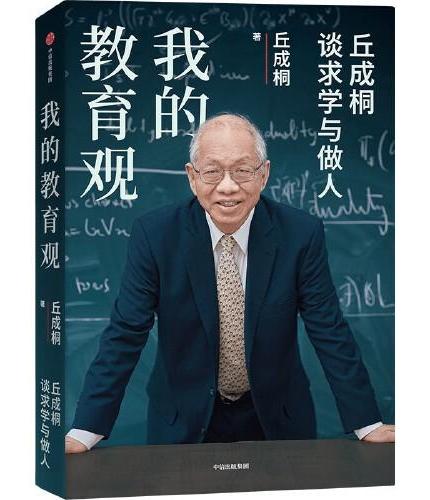
《
我的教育观
》
售價:NT$
4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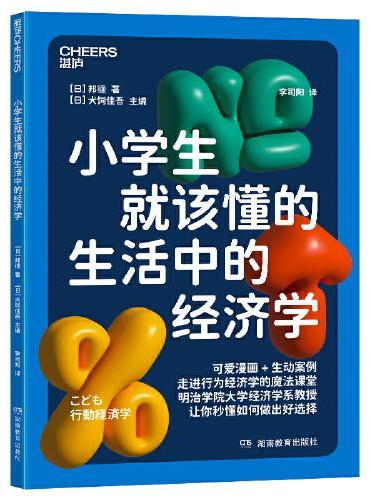
《
小学生就该懂的生活中的经济学
》
售價:NT$
3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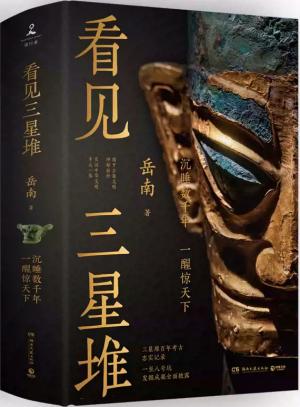
《
看见三星堆
》
售價:NT$
90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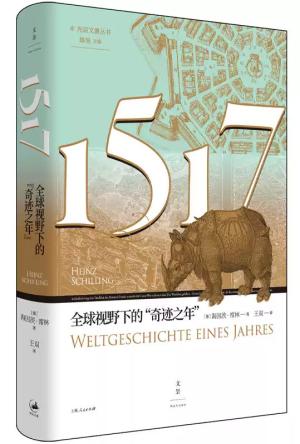
《
1517:全球视野下的“奇迹之年”
》
售價:NT$
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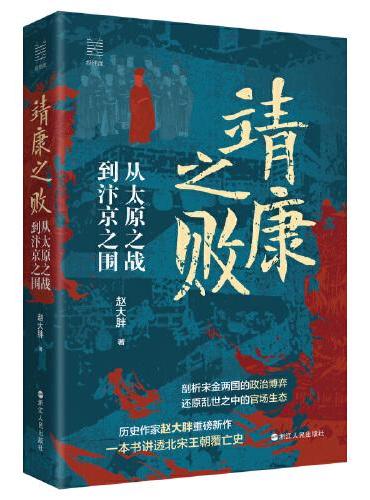
《
经纬度丛书·靖康之败:从太原之战到汴京之围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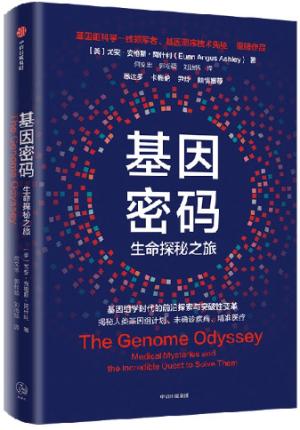
《
基因密码:生命探秘之旅
》
售價:NT$
4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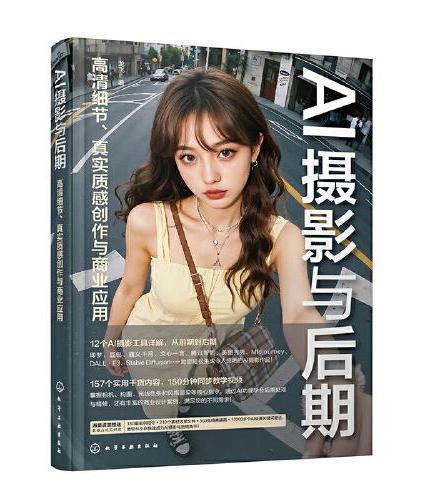
《
AI摄影与后期:高清细节、真实质感创作与商业应用
》
售價:NT$
500.0
|
| 編輯推薦: |
|
《战败者》是一部极具创见性和扣人心弦的历史著作,既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又不失学术的严谨性,作者在二者之间实现了较好的平衡。作者通过多个语种的丰富史料,展现了Di一次世界大战后波及欧洲多个国家的暴力冲突的完整图景。作者指出,Di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及和平条约的签署,并未解决困扰欧洲诸多国家的民族和边界问题,战败国国内及国家间持续数年的暴力冲突,为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等极端意识形态在欧洲的孕育提供了适宜的温床,并☆终引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本书不仅有助于读者完整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历史,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动荡的历史,更有利于加深对当下中东乱局的认知。
|
| 內容簡介: |
|
对于Di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来说,1918年11月11日即意味着战争的结束;而对于战败国来说,它却是一场巨大暴力灾难的开始。在很大程度上,Di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破坏性并不只是西线残酷的战斗,而是其所导致的毁灭性后果,即在战后爆发冲突的地区,人们被革命、大屠杀、种族清洗和不断升级的军事冲突彻底野蛮化了。1917年至1923年间,遍布中欧、东欧和东南欧的暴力冲突导致数百万人死亡,而正是在这样的战争废墟上,极端意识形态开始形成,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分别在意大利和德国取得胜利,并由此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Di一次世界大战虽已过去百年,但其直接后果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至今仍困扰着世界。
|
| 關於作者: |
|
罗伯特?格瓦特(Robert Gerwarth),现为爱尔兰都柏林大学现代历史学教授、战争研究中心主任。硕士毕业于德国洪堡大学,主修历史和政治科学,之后在牛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并获得该校的博士后研究资助,主攻欧洲史,尤其是德国史。格瓦特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和巴黎政治大学进行项目研究和讲学,著有《俾斯麦神话》《海德里希传》等。
|
| 目錄:
|
致谢
导 言
第一部分 战 败
1 一次春天的火车之旅
2 俄国革命
3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
4 胜利的滋味
5 命运逆转
第二部分 革命与反革命
6 战争没有结束
7 俄国内战
8 民主的大胜
9 激进化
10 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恐惧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第三部分 帝国的崩溃
11 潘多拉的魔盒:巴黎和帝国的问题
12 重塑中东欧
13 败者遭殃
14 阜姆
15 从士麦那到洛桑
结语:“战后时期”与欧洲20世纪中叶的危机
注释
|
| 內容試閱:
|
导 言
无论是战胜者还是战败者,双方都毁灭了。所有的皇帝及其继承人都被杀死或废黜了……所有人都是战败者;所有人都遭了殃;他们所给的一切都属徒劳。没有人能得到什么……那些从战场上数不清的日日夜夜中幸存下来的老兵们,归来时无论是带着胜利的桂冠还是失败的噩耗,他们的家园都已被战祸吞噬。——温斯顿? 丘吉尔《不为人知的战争》(1931)
这场战争是暴力的开始而非结束。在这个熔炉里,世界被锻造出新的边界和社会。新的铸模想要被鲜血灌满,而权力则被铁拳掌握。——恩斯特?荣格《作为内在经历的斗争》(1928)
1922年9月9日,由一场长达十年的战争而引起的仇恨降临到士麦那城。当土耳其骑兵开进这座奥斯曼帝国曾经最为繁华的国际化都市时,占居民人口大多数的基督徒都在惴惴不安地等待着。几个世纪以来,穆斯林、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东正教基督徒一直在士麦那和平共处,但近十年的战争改变了这种民族关系。奥斯曼帝国在1912年至1913年巴尔干战争中丧失了几乎所有的欧洲领土,1914年8月它作为德国的盟友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发现自己又一次沦为战败国。在被剥夺了阿拉伯地区(这一地区后来被称为“中东”)的领土后,战败的奥斯曼帝国及其羞愧万分的土耳其穆斯林很快又面临新的威胁:在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鼓动下,一支希腊侵略军于1919年在士麦那登陆,他们决心要在小亚细亚半岛基督徒居民的稠密区为自己开辟出一个新帝国。
三年的残酷冲突给穆斯林和基督徒都造成了惨重伤亡,而今战争已经明显不利于希腊。希腊军队被富有才干的土耳其民族主义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他将来有个更为人熟知的敬称——“土耳其之父”)引诱进了安纳托利亚中部,他们战线过长,指挥无能,在凯末尔1922年夏季发动的大规模反攻下被击溃了。仓皇撤退的希腊人对安纳托利亚西部的穆斯林居民一路烧杀抢掠,这使得在士麦那的基督徒有充分的理由担心会遭到报复。但是,这座城市的希腊占领当局的虚假保证,以及停泊在港口的至少21艘协约国船只给了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错误的安全感。既然当初是西方协约国——特别是英国——鼓励雅典政府出兵占领士麦那的,那么在穆斯林打算报复的时候,他们肯定会出手保护基督徒吧?
随着这座城市悲剧大幕的开启,这种想法很快就被证明是错误的。土耳其军队攻占士麦那不久,士兵们就逮捕了希腊入侵的坚定支持者东正教大主教克里索斯托莫斯,把他送到少将指挥官萨卡里?努尔丁帕夏那里。少将把克里索斯托莫斯扔给了住所外面聚集的一群土耳其暴徒,他们叫嚣着要取大主教的人头。一个旁观的法国水手回忆道:“人群尖叫着扑向克里索斯托莫斯,把他沿着街道拖到一个理发店,理发店的犹太老板伊斯梅尔从门口紧张地张望着。有人把理发师推到一边,抓了一块白布勒在克里索斯托莫斯的脖子上,叫道:‘给他刮个脸!’他们扯下主教的胡子,用刀挖出了他的眼睛,砍掉了他的耳朵、鼻子和手。”没有人来管这些事,饱受折磨的克里索斯托莫斯被拖进一条背街小巷,扔在一个角落里直至死去。
士麦那东正教大主教的惨死,只不过是暴力狂欢节的前夜序曲,这令人想起了17世纪欧洲宗教战争时期对敌人城镇的洗劫。在接下来的两周内,估计有3万名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被屠杀,还有很多人被土耳其士兵、准军事部队或是当地的青少年团伙抢劫、殴打和强奸。
9月13日傍晚,第一座被点燃的房屋是在这座城市的亚美尼亚街区。到了次日上午,大部分基督徒的房屋都起火了。几个小时之内,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逃到海边码头避难。英国记者乔治?沃德?普莱斯在港口停泊的一艘战舰上目睹了屠杀,记录下了这“令人无法形容”的场面:
我站在“钢铁卫士”号上看到的是一道连绵不绝的火墙,足有两英里长,锯齿状排列的20多处熊熊烈焰如火山爆发般喷吐而出,火舌扭动着蹿向100多英尺的空中……海水被映成深深的红铜色,最糟糕的是,成千上万的难民拥挤在狭窄的码头上,身后是不断进逼的烈火,面前是深不见底的海水,从那里不断传来恐怖绝望的疯狂尖叫声,几英里外都能听到。
当土耳其军队封锁码头时,许多铤而走险的难民试图逃到盟国停泊在码头的船只上去。越来越清楚的是,协约国不打算介入或是尝试用船只来搭救难民。很多恐惧至极的希腊人跳海自尽了,还有一些则拼命游到某条协约国的船上。老人和孩子惨遭被热浪从建筑物里驱赶出来的疯狂人流践踏,牛马在无法撤离的情况下折断前腿被推进海里淹死——这是短篇小说《在士麦那码头上》中的经典场景,作者是当时尚未成名的《多伦多星报》记者欧内斯特?海明威。
海明威只是记录士麦那之劫的许多西方记者中的一个,这座城市的可怕遭遇占据了好几天世界各地新闻的头条。英国的殖民地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写信给加拿大总理谴责这一暴行,称这是一场“人类罪行史上罕见的地狱狂欢”。
士麦那基督徒的残酷命运,以及前述土耳其穆斯林进行的屠杀,无情地告诉人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并没有立即带来和平。实际上,丘吉尔有关暴行罕见的说法是错误的,恰恰相反,与在安纳托利亚西部发生的同样悲惨的事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绝非罕见。“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一个界限明确的时间段,通常认为始自1918年11月11日停战协定的签署,迄于1939年9月1日希特勒进攻波兰。然而,这个时间段只是对主要的战胜国,即英国(爱尔兰独立战争算是一个明显的例外)和法国才有意义,它们在西线停止了敌对活动,的确意味着战后时代的开始。
然而,对于生活在里加、基辅、士麦那,以及中欧、东欧和东南欧许多地方的人们来说,1919年没有和平,只有连绵不绝的战乱。俄国的哲人和学者彼得?斯特鲁韦,在俄国内战期间从布尔什维克转向了白卫运动,这使得他能从当时公共知识分子更为有利的角度观察:“第一次世界大战随着停战协定而正式结束了。然而实际上,从那一时刻开始,我们所经历的和正要经历的,都是这场大战的延续和转型。”
不需要看很多就可以证明斯特鲁韦的话:大大小小抱有各种政治目的的武装力量,在整个东欧和中欧到处厮杀,暴力无处不在,新政权的更迭充满了血腥。仅在1917年至1920年间,欧洲就经历了至少27次以暴力方式进行的改朝换代,许多都伴随着可能或已经爆发的内战。最极端的情况当然就是俄国本身,1917年10月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政变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冲突,迅速升级为一场史无前例的内战,最终导致300多万人丧生。
1. 一次春天的火车之旅
在1917年的复活节,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进行曲”从一次火车之旅开始奏响。4月9日傍晚,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带着他的妻子和追随者娜佳,还有他的三十名同志,登上了一列从苏黎世车站出发的德国火车。
柏林当局在这个人身上寄予了厚望,批准了这次从中立国瑞士穿过德国领土的秘密之旅,并为他们前往俄国的旅程提供了物资准备。当时除了第二国际以外,知道他的人寥寥无几。他只是以“列宁”的笔名在小范围发行的左派外围刊物上发表一些时事文章。在大量资金的接济下,列宁夺取了他的祖国弱小的布尔什维克运动的领导权,在当年促成了推翻沙皇统治的“二月革命”,并和同盟国达成了停战。
自1914年战争爆发以来,德国外交部一直在秘密支持协约国后方不同政见者的革命活动:爱尔兰共和党力求与伦敦断绝关系,英国和法国有圣战分子,俄国革命者则在彼得格勒密谋反对沙皇。柏林并不关心这些革命者各自的政治目的,只是把他们看作可以从内部削弱协约国力量的战略同伙。然而令柏林的战略家们遗憾的是,这种努力似乎没有收到预期的成效。大约3000名穆斯林战俘被集中在柏林附近措森的一座“半月营”,他们将被派往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去进行宣传鼓动,然而他们并未动员起多少圣战分子来。1916年春,柏林又吃了当头一棒。德国支持的复活节起义没有在爱尔兰掀起大革命,而在大战头两年一直忙于从德国囚禁的战俘中建立“爱尔兰旅”的罗杰?凯斯门特,却在4月乘坐一艘德国U型潜水艇从凯利上岸后不久即被捕,并在8月以叛国罪遭到处决。
不到一年之后的1917年2月,沙皇倒台,柏林决定恢复向敌国走私革命者的计划。为了配合柏林在协约国内部煽动革命的战略野心,早在1914年,在中立国的德国外交官就已着手草拟俄国革命激进流亡者的名单。列宁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这些名单中是在1915年。沙皇退位后,德国外交部通知政府和陆军司令部,他们已经注意到一群在中立国瑞士的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他们返回彼得格勒,将会加强俄国极左派中反战的布尔什维克的力量。柏林的军政首脑批准了这一计划。
当列宁1917年4月踏上火车之旅时,他已经四十六岁,并可以回顾一下自己几十年的革命生涯。最初他生活在伏尔加河畔的辛比尔斯克(今乌里扬诺夫斯克),父亲是世袭贵族和省教育总监,1886年死于脑溢血。随后他和家人迁居到喀山母亲的家乡。灾难在下一年接踵而至,哥哥亚历山大因参加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行动而被捕处死。他因为哥哥的死而更加卷入马克思主义者的圈子。在因参加反对沙皇的示威而遭到喀山大学开除后,他继续保持着政治兴趣,在俄国的首都学习法律。考试结束后,他以律师的身份积极投入到革命运动当中,逐渐开始接触俄国社会民主党人。1897年2月,他从欧洲返俄后被作为政治犯流放到西伯利亚。在流放的三年中,他进行了广泛的革命实践,并开始使用“列宁”—很可能是位于西伯利亚的勒拿河(Lena)的谐音—这个化名来迷惑沙皇警察。
从1900年起,列宁到西欧居住,起初在瑞士,后来到了慕尼黑。在那里,他创办了《火星报》,在上面刊登了纲领性的文件《怎么办?》(1902)。列宁的思想虽然深深植根于卡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但在创建共产主义的方式上至少有一处重要的不同。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后阶段,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最后将因阶级对立而引起自发的人民起义。相比之下,列宁并不想等待这一自发的革命时刻。因为它要基于一个先进的工业社会,以及一种在产业工人中同样发达的阶级意识,这两样在俄国都不存在。相反,他计划由一批坚毅果敢、组织严密的职业革命家作为先驱,通过一场军事政变以暴力的方式夺取政权。1905年革命期间,苏维埃(或工人委员会)等组织在俄罗斯帝国的许多大城市自发地成长起来,准备取代旧有的权力结构,并促进阶级意识在俄国大批目不识丁的工人和农民中的传播。
由于1905年的革命风潮和沙皇随后颁布的《十月诏书》,列宁回到了俄罗斯,但很快在当年12月被迫再次流亡,并持续了十二年之久。那段时间,他在欧洲的许多城市——日内瓦、巴黎、伦敦、克拉科夫——生活过,直到1914年以后,他生活在苏黎世。这座瑞士最大的城市在当时是一个特别有吸引力的避难所,它是少数没有卷入欧战的地方之一,交通和通讯却四通八达,并且还有着庇护不同政见者的传统。苏黎世不仅是以伏尔泰酒馆的雨果?鲍尔和特里斯坦?查拉为核心的前卫的达达主义文艺运动的发源地,也是大批盼望革命的欧洲左翼激进分子的临时栖息地,他们常常在如何实现这一目的上产生分歧。
社会主义左翼之间的纠纷由来已久。自从1889年7月社会主义第二国际成立以来,不同派别就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乌托邦争论不休。到20世纪初,主张改良和坚持革命的人们之间分歧越来越深。就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而言,这种无法调和的矛盾主要产生于两个重要派别之间——列宁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和较为温和的孟什维克(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一致),后者主张在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发生前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并在1903年导致了党的彻底分裂。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加深了欧洲工人运动的裂痕。大多数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通过了本国的战争预算,于是把对国家的忠诚置于国际阶级团结之上。列宁是对左翼改良派不妥协的批评家和激进革命的热情倡导者,在柏林看来,他是进一步破坏俄国国内稳定的理想候选人。
列宁自己正生活在平静的环境中,他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在苏黎世公共图书馆里写作。当反对罗曼诺夫王朝的“二月革命”在彼得格勒爆发时,他十分惊讶。在苏黎世的移民完全依靠报纸来了解俄国的情况,直到1917年3月初列宁才得知这一消息。在杜马代表团和高级将领的强烈要求下,沙皇退位,他的弟弟米哈伊尔也宣布放弃皇位。尽管革命的确切结果是完全公开的,但列宁仍然发现了他的机会。不能再像1905年那样错过影响革命的机会,这次他再也不想浪费任何时间,而是要尽快回到俄国,以便实实在在地加入进去。
列宁很清楚,要穿过战火连天的欧洲,需要得到德国的支持,协约国不可能支持任何使俄国退出大战的行动,德国却一直在试图从内部削弱他们的对手。当列宁意识到被德国人利用之后,他觉得为了使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获得成功,这一手段是可以接受的。在和德国代表的谈判中,他要求自己和随从1917年4月乘坐的车厢享有治外法权;他用一支粉笔,将“俄国领土”划出了“德国领土”,并且成功地坚持了随行的德国军官不得牵涉进俄国革命的意见。
列车很快进入德国境内,这些从中立国瑞士来的旅客,以前只是通过报纸了解一些大战的二手消息,在法兰克福和柏林的火车站,他们第一次看到了瘦弱憔悴的士兵和筋疲力尽的居民,这使得列宁更加期盼战争也会很快引起德国的革命。在德国位于波罗的海的吕根岛,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坐上一艘开往哥本哈根的船,然后继续前往斯德哥尔摩,在那里登上另一列开往俄国首都的列车。与列宁的担心相反,他和同伴们在进入俄国领土时没有遇到麻烦。1917年4月16日——经过十二年的流亡——列宁抵达俄国首都,在那里受到布尔什维克支持者们的热烈欢迎,当列车抵达彼得格勒的芬兰火车站时,他们唱着《马赛曲》,挥舞着红旗并献上鲜花。列宁回家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