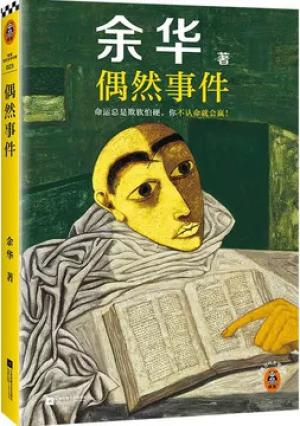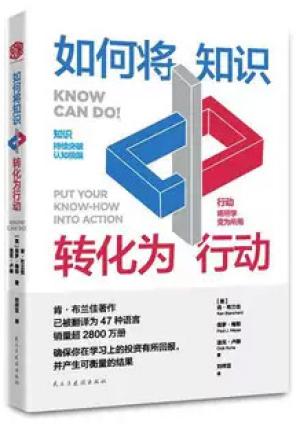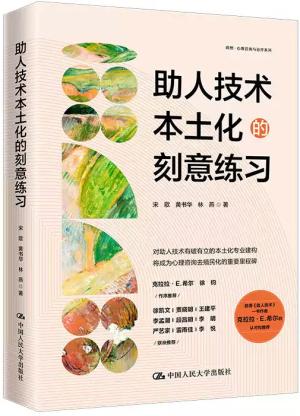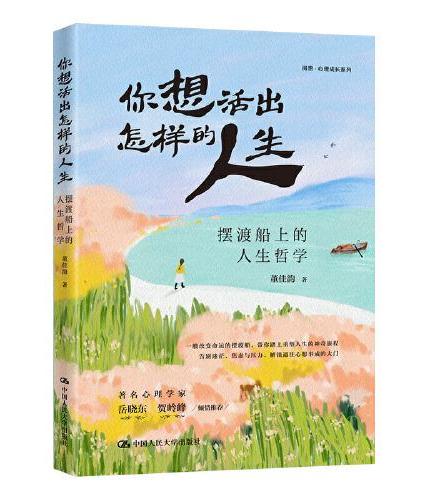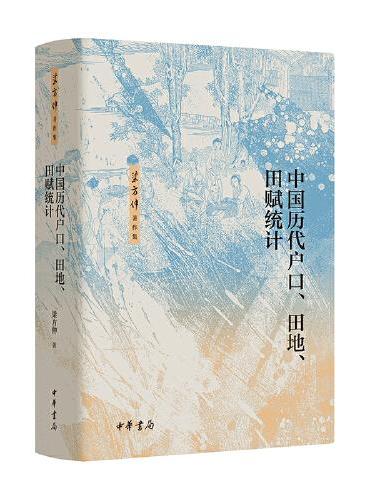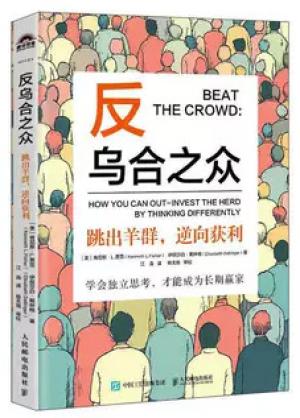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偶然事件(命运总是欺软怕硬,你不认命就会赢!)
》 售價:NT$
255.0
《
余下只有噪音:聆听20世纪(2025)
》 售價:NT$
959.0
《
如何将知识转化为行动
》 售價:NT$
356.0
《
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
》 售價:NT$
408.0
《
中国城市科创金融指数·2024
》 售價:NT$
500.0
《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摆渡船上的人生哲学
》 售價:NT$
306.0
《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梁方仲著作集
》 售價:NT$
689.0
《
反乌合之众——跳出羊群,逆向获利
》 售價:NT$
356.0
內容簡介:
本书勾勒了一个四川农村手工技艺从业者社区20世纪的社会变迁史。该村落地处成都与乐山之间的夹江县。传统上,当地居民利用当地自然产出的毛竹为原料从事手工造纸谋生,并围绕这一核心技能形成特定的亲属关系网络和社区组织形式。而“技能”这一话题以两种互相关联的线索贯穿全书:技术性的,或社会性的。作者试图通过聚焦一种技能劳作的相关细节,更加透彻地了解乡村民众的生活世界。
關於作者:
艾约博(Jacob Eyferth,1962-),现担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东亚语言文明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副教授。2000年在莱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牛津、哈佛和罗格斯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20世纪中国农村社会史,以及关于工作、技术、性别和日常生活的历史。主编 How China Works: Perspectives on the Twentieth-Century Industrial Workplace (Routledge, 2006)。计划出版Hidden Transfers: How Rural Women’s Reproductive Work Paid For Industrialization in Mao’s China
目錄
表格、示意图、图片目录
內容試閱
导 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