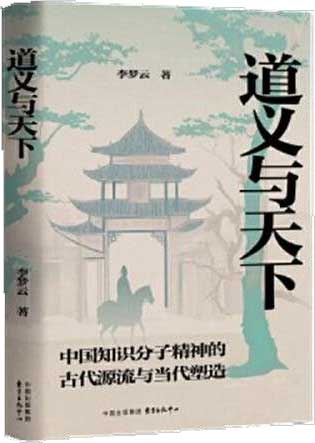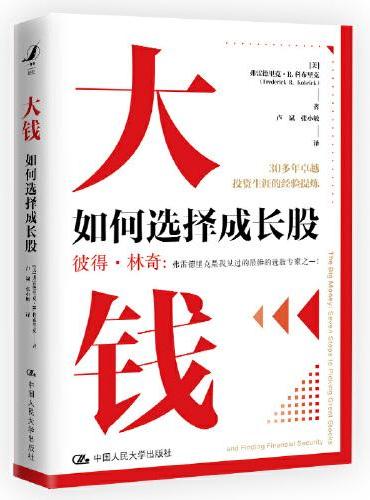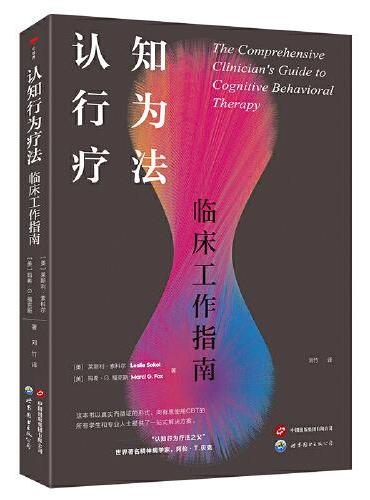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攀龙附凤:北宋潞州上党李氏外戚将门研究(增订本)宋代将门百年兴衰史
》
售價:NT$
454.0

《
金钱的力量:财富流动、债务、与经济繁荣
》
售價:NT$
454.0

《
超越想象的ChatGPT教育:人工智能将如何彻底改变教育 (土耳其)卡罗琳·费尔·库班 穆罕默德·萨欣
》
售價:NT$
352.0

《
应对百年变局Ⅲ:全球治理视野下的新发展格局
》
售價:NT$
398.0

《
前端工程化——体系架构与基础建设(微课视频版)
》
售價:NT$
4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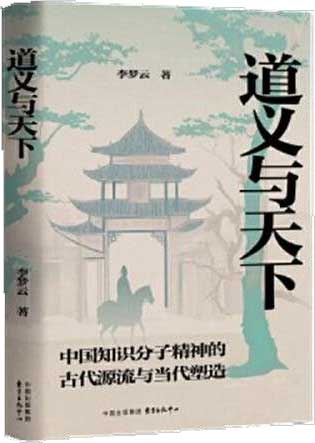
《
道义与天下: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古代源流与当代塑造
》
售價:NT$
40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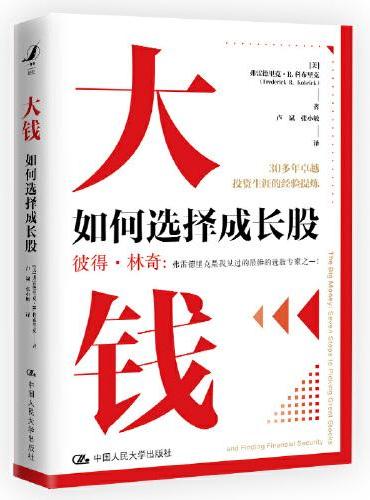
《
大钱:如何选择成长股
》
售價:NT$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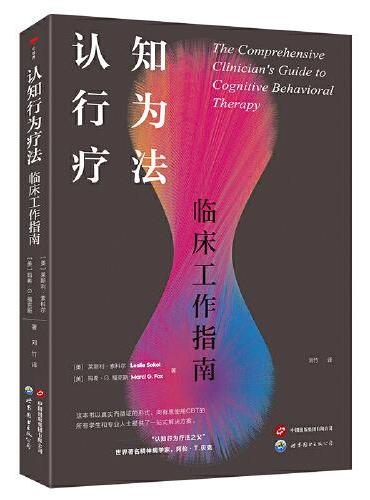
《
认知行为疗法:临床工作指南
》
售價:NT$
398.0
|
| 編輯推薦: |
【悲情满怀慈悲,缝隙里生满野草】
*小说家常小琥首 部短篇小说集
*“如今小说中的一些朋友已经悄然故去,每当我回到南城,那里于我而言也就有了另一种坐标,令我感觉自己仍会和他们擦身而过。那些不断被我描述的地方,也呈现出了另一种真实,连我自己的故事一起被留在那里。”——常小琥
|
| 內容簡介: |
隐秘而巨大的离心力扑面而来,有人浮出水面,有人活在海底。生活早已布下天罗地网的隐疾,在面目可憎之前将世界生吞,簌簌作响。
“小说家不该只是为了写作,我相信那是某种道义的火种在传递”。——常小琥
六则短篇故事,六场质地坚硬的悲悯之旅
聚焦那些失意却骄傲的人,形同虚设但生机勃勃
《岁寒三友》
写了这么多年的字,落笔在得意或意外的位置,分不清它究竟对我是种祝福还是诅咒。
《穿心莲》
打不着火的二手夏利、腾不出屋的蹩脚老房,和装在信封里的钱,变成为女儿生计奔走父亲的精准类比。
《大狗》
片警与混混、旧南城与大时代,谁也走不出的逼仄胡同,何时会成为一片明亮的平阔天地?
《回家》
精神科医生和努力想要与社会接轨的病人,声嘶力竭地要把一切推入正常的范畴,却唯独没有把回不去的家塞进去。
《变脸》
如父如子的师徒两人,一生苦攒的大活,在日暮前上演。杂技少年的旧时空里下起了一场阵雨。
《吉米,唱吧》
拥有绝对音感却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儿子,与曾经万众瞩目却中年失意的摇滚老炮,一段荒唐无力的父子情,一场摇摇欲坠的红尘梦。
“我总是在小说里写到从前。 其实我也说不好这是什么毛病,也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必要,只能套用《英雄本色》里的那句台词:‘这个世界变了,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了,我们太念旧了。’”
|
| 關於作者: |
常小琥
北京人,生于1984。
著有《秦腔》《收山》《如英》。曾获“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小说佳作奖、《上海文学》中篇小说奖、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华语青年作家奖、《北京文学》年度优秀作品奖等。
|
| 內容試閱:
|
后记
我总是在小说里写到从前。其实我也说不好这是什么毛病,也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必要,只能套用《英雄本色》里的那句台词:“这个世界变了,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了,我们太念旧了。”
就像我总想起那时的雨,那些雨水仿佛格外沉重,落到泥地上、玻璃窗上,落到脸和鞋子上,令我很小就知道下雨要论轻重,而不是问大小。可能自己还是色弱的缘故,那时总感觉到处浸着蓝黑色的钢笔水,看起来粗粝、含混、有杀气。当我望向天空,神魂颠倒地以为所有人都活在海底,他们承受着海底一样的压力,连行动都那么迟缓,并且大人讲话时,我也永远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所以当我的小学早变成了药房和超市后,我却仍然喜欢回到那里。在某个夏日的雨后,我会回到操场上,回到教室里,回到老师面前,听他们讲着什么。他们在讲什么呢?在那样的时间里,在那样一座海底之城里,他们会讲什么?我时常想。
我的数学老师是一位瘦骨棱棱的中年女性,她不仅永远面色煞白,而且还没长眉毛,加上一头板正的八字刘海齐肩短发,后来我一看罗大佑就会想起她。她的站姿和肢体动作也和机器人一样,枯槁的手总在冷酷地震颤着,如发电般对我们灌输知识。
在一节测验课上,她坐在前面正批改作业,忽然用凌厉的眼光盯住我,低声问你怎么一个字没写就交上来了。我赶紧接过作业本,发现昨天完成的两页纸已不知去向。我指给她看装订处留下的齿痕,可她没说什么只让我继续考试。吃午饭的时候,我还在独自苦闷,她又一手插兜一手拿个作业本,迈着机器人般杀气腾腾的步伐走进来。我的好哥们儿在全班的注视下被她叫了过去,她叫他赔个新本子给我,还要跟我道歉。看着她又机械地扭头走出教室,我才知道是谁把我的作业扯掉,还贴到了他的本子上。后来我想,可能她一上午都在对照其他学生的笔迹,要找出我那篇消失的作业吧。
时至今日,我还是会为那些在志怪奇观里追求道义的古人,为他们捍卫生命纯洁背后的精神世界大受触动。比如为助刺秦拔剑自刎的樊於期、不辱使命仍以死相报的程婴;比如《三王墓》里两手捧头及剑,立僵不倒的少年;还有《聊斋志异》里王六郎、田七郎的故事;甚至是在菜市口被锯头三十刀而殉道的谭嗣同,近现代的事例就更不用多讲。由此我想,来自于普通人的情谊与信义,就更显弥足可贵,引人深省。我相信在年幼时遇到的数学老师,便是某种道义的化身。我相信她是在坚持着什么,在守卫着什么。
道义的另一边,必是辜负。这成就了写作者永久的主题,那便是隐匿在人与人之间的深深的遗憾。借用布罗茨基对彼得堡的童年印象,北京南城在我儿时也是一座“工厂的半岛、作坊的乐园和工厂的欢乐之邦”。那时父母的工友、两边的亲戚,还有小姨和她的同学,他们坐下来会聊些什么,是否也生发出了某些承诺和辜负?我还想如从前那样躲在他们身旁,望着一张张忧虑、好奇且困惑的脸。在一次又一次被甩出车窗后,这里的人想的只是怎么能不让人坑了,或者怎么也能坑人一把。我相信他们还不习惯以真正的个体来介入彼此的生活和关系。我总是要写师徒、兄弟或者女性间的情谊,正源于我出自这样的地方,需要把先天缺失的不断理想化、合理化。这可能就是看哪儿都是海底的重要原因,至少也解释了为何我会如此敏感。
由此我落下个毛病,喜欢光顾别人的家。那时工友们还没完全从胡同的杂居中进化出来,热衷于带着爱人和孩子到彼此家中做客。在这前后小孩儿难免要被教训一顿,于是串门对我而言带有了某种神圣感。那就好比出国旅行,你的身体会对异国的气味和湿度极为敏感,你在别人家里一样能轻易闻出谁不爱洗澡、谁屋里有东西发霉了,或者谁家孩子刚烧过试卷。特别是在闷热的无处可去的夏日,我喜欢不请自来,独自等候主人的时候,更可以观察到家庭内部真正的丰富性以及他们忘记掩盖的秘密,那等于宣告你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如今再要享受这个待遇,我只能去老人家里了,只有他们还保留着这个传统。后来我拜访过一位在勤行饱经世事的老先生,他让我去家里亲自炒菜给我吃,我至今还能看见他炒干煸牛肉丝时,那个厨房里有多热闹。我记得他的床边就堆满了好几麻袋佐料,令整个家混淆着辛辣和苦涩的味道。这位年近八十的老人,始终沉浸在年轻时与师父共处艰难多变的往事中,我每次来都会看他翻出老菜谱和老照片,讲得自己泪眼婆娑、满面通红,直到把嗓子都讲哑了。他的老菜谱全是去首都图书馆影印的,当成宝贝一样用塑料袋裹着。我告诉他可以找到原版菜谱送他,老人这才像个孩子一样乐呵呵地给我夹菜。而我则要咬牙吃下他做的菜(因为味觉退化,他往菜里放了太多的盐),如果一个厨师为你在家里开伙,你是千万不能吃不了剩下的。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老人带我去品尝了几家老字号和小饭馆。只要他一进大堂,懂事的厨师长会立即出来听他训话、问候对方的师父是否还好,有时能问到师爷一辈,他才满意。接着他告诉对方,你这店里的菜不合道理,手艺也退化了。对方看了看我,没说什么。
后来有老板聘请他去做技术顾问。那是在一个极易迷路的大公园里,内部建有很多的蒙古包,老人在收徒仪式上,被各路媒体和徒弟簇拥在中央。之后他在毡房里开始讲授第一堂课,他不停地用吐沫蘸着破旧的横格本,那是他熬夜誊写的五十年代老菜谱。厨师与女服务员稀稀拉拉地坐在对面,每讲到要点,老人就慢慢转开矮胖的身体,去写板书。我看到众人打着哈欠、开着玩笑,有人为还没有备菜而着急,很快就溜走了大半,可老人只顾继续讲课。他把一个小厨师叫起来,考对方如何测油温的问题,那副逼问的模样反令众人笑作一团。我记得他喝口水的工夫,旁边的小伙计就用板擦把一半的字擦没了。那一刻老人怔住,但他很快埋头到横格本上,继续用胖嘟嘟的手指翻着笔记,以窘迫的沉默,念了起来。离开毡房的厨师越来越多,最后还在认真记笔记的,只剩一个女服务员了。
那之后的一个朔风如刀的冬日,我把原版菜谱送到老人家里。他双手把书捧在手心,我就没见他再放下。那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我总是会想,老人一定也是在坚持着什么,在相信着什么吧?可是我没有机会再问他了。
我把问题带向了处境更为现实也更复杂的医者,在长达六年时间里,我意识到这个精英群体,每个人都在执行着自己选择相信的观念,否则他们很难支撑下来。可是长年信奉的专业主义和职业感,令他们极易站在吊诡的逻辑里,或者为了莫名其妙的理由去放任悲剧发生。这时候所谓的道义就成了极其模糊、幼稚,甚至是需要警惕的念头。
我意识到自己没有能力完成这个题材,那几乎断送了我的写作道路。但是我并没认识到,正是这些迟暮义士,引导着我的写作道路,是他们连结出后来的一篇篇作品,如同交汇成一条河流。
于是我遇到了那位美丽且无比动人的姑娘,我们的对谈跨越了将近三年,每一次见面,她都做到了最大程度的坦诚。埋尸案的家属、被邪教男女诱拐致死的女孩儿,以及在农村被无数次侵犯的弱智女童……她不顾一切地为事件中的受害者追讨真相,永不停歇地在午夜的跨省大巴和各种流氓团伙中逃亡。可打动我的不只是那些残酷又迷乱的事件,而是她独特的生命状态和对自我的执念。在那三年时间里,即便已不再从事新闻工作,但她依然在介入每个向她求助的人,为对方寻求法律援助或者亲手写公众号和法律文书。我亲眼目睹了她的变化,以及那不可更改的底色。在她面前我习惯成为安静的倾听者,从不表露任何意见。以至于在我还未真正动笔,或者提出疑问时,女孩就匆匆离开了,并且我再也没有见到她。
这为我之后在叙事上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全感,令我一度感到懊悔和失落,因为那三年我有太多机会向她追问或者求证,而她看上去也在等待我问些什么,只要我能问到,她一定会讲给我听。可见我是个失败的采访者,我也不敢相信,只靠自己就能探究到那些像残留在海底一样的她记忆深处的某些东西。这意味着与以往借助想象完成虚构不同,我需要带上她意识上的枷锁,设想自己就是她,独自潜入到过去的经历和复杂心情里。直至被她帮助过的受害者的人生,与她某些自我痕迹和追求过的存在高度重合,仿佛三种时空交错到一起,我好像在她到过的每一处地方与其相遇,感受到种种可能性。
正是这样的经验一再延续,才有了这本书里的故事。当我为此又坐进别人家里,听对方将最隐匿的感受和生命中独有的经历告诉我时,某种连结便随之建立。这连结令我觉悟到,那不该只是采访,小说家也不该只是为了写作,我相信那是某种道义的火种在传递。如今小说中的一些朋友已经悄然故去,每当我回到南城,那里于我而言也就有了另一种坐标,令我感觉自己仍会和他们擦身而过。那些不断被我描述的地方,也呈现出了另一种真实,连我自己的故事一起被留在那里。
这本书是我在写作的第十个年头,出版的人生第一本短篇集。为此我要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尺寸品牌的宋杨女士和李骁先生,感谢他们对作者意愿的尊重和对创作权倾尽全力的保护,这是无比美妙的缘分,是上天的恩赐,我从他们身上亦感受到了出版人对于做书理想的坚守与专业态度。我同样不会忘记每一位在写作道路上,向我伸出过援手、给予我鼓励与启发的朋友和编辑老师们,我相信他们也是出于道义来帮助我的。最后我想特别感谢《上海文学》杂志的崔欣女士,在某种意义上,这本书是献给她的。
2024.5.4
北京,白纸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