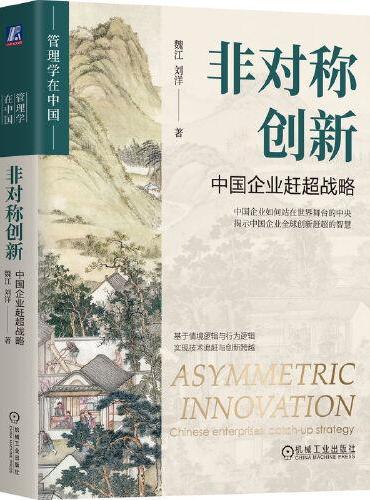新書推薦:

《
谁之罪?(汉译世界文学5)
》
售價:NT$
240.0

《
民国词社沤社研究
》
售價:NT$
640.0

《
帕纳索传来的消息(文艺复兴译丛)
》
售價:NT$
495.0

《
DK威士忌大百科
》
售價:NT$
1340.0

《
小白学编织
》
售價:NT$
299.0

《
Android游戏开发从入门到精通 第2版 王玉芹
》
售價:NT$
495.0

《
西班牙内战:秩序崩溃与激荡的世界格局:1936-1939
》
售價:NT$
9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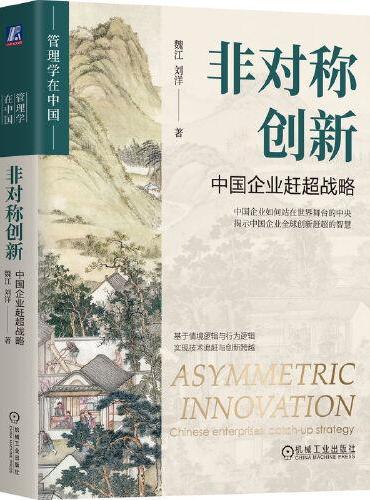
《
非对称创新:中国企业赶超战略 魏江 刘洋
》
售價:NT$
495.0
|
| 編輯推薦: |
本书卖点
作者李晓君以深挚的笔调、简约的叙述和对童年、故乡、青春、往事等富有质感和现场感的追述中书写了 七零后的共同记忆,锐利而精准地表达出一代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图景,探寻了一代人成长的隐蔽命运以及时代变化的显性与隐性特征,为当代人的精神蜕变留下了一个生动的“侧影”。
编辑推荐
《往昔书》为著名散文家李晓君对一代人集体回忆的梳理与呈现。作者将个体的回忆置于故乡家国变迁背景下,从多个视角、多个物事着笔,将往日时光书写成70后一代的心灵史,既有独特的抒情性质、形而上的理性思辨,又具有普遍意义的体验和共情,文笔朴实,感情真挚,是独特而又鲜活的文本。
|
| 內容簡介: |
|
《往昔书》是一代人心路历程的“追忆逝水年华”, 更是对一代人集体回忆的梳理与呈现。作为一名70后,在其成长历程中见证了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的城乡现代化等重要历史阶段,作者以冷静、温情而细腻的笔触将个体的回忆置于故乡家国变迁背景下,努力捕捉那消逝或凝固的斑斓往事,状写出一代人隐匿、沉没,而又夺目的精神世界。
|
| 關於作者: |
|
李晓君,本名李小军,1972年6月生,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江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在《十月》《人民文学》《花城》《钟山》《中国作家》等发表散文300余万字。著有散文集《时光镜像》《江南未雪——1990年代一个南方乡镇的日常生活》《梅花南北路》《后革命年代的童年》《暮色春秋》《暂居漫记》等。
|
| 目錄:
|
第一章 镜中童年 001
梦,和另一个梦 003
鹬鸟,或河边的行走 008
自我的囚禁,以及小故事 013
画画的乐趣超越了现实 021
菖蒲的夏天 026
马厩以南 032
阁塘冲,破落的军官和养蜂人 037
欢愉 043
父亲的医院与晚年生活 053
大山的客人 058
空山 064
酿酒厂里的旧色县城 069
…………
第二章 乡村之夜 195
山冈 197
醉与梦 204
一个冬天的夜晚 209
小店 215
撕裂或者抵牾 221
乡村爱情 227
束手就擒 234
未能展开的恋爱 240
在食堂的消磨 246
夜晚的微光 252
吃春酒 257
…………
第三章 补遗 387
官厅 389
摩丝头 396
从上海来的女人 404
文化馆干部 410
国画 421
异乡人
|
| 內容試閱:
|
异乡人
我很多未曾亲历的故事,来自他——另一个郭老师(郭佳明的堂弟)的讲述。这个学者,正是当年我读师范时,在报纸上看到的凭着一组获奖照片,调到省城来的那个人。他身上有种莲花男人的典型特征:急公好义、质朴却头脑灵活、不善于家务但擅长外交,最主要的是家乡观念重。只要是故乡的召唤,他会是二话不说首先响应的那个人。记得千禧年那年,我们县建成了据说是全省最大的县级广场,主政者倡议莲花籍在外人士捐款,以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我记得郭老师捐出了五位数,在捐款者当中数额名列前茅。就在前不久,我们几个老乡一起聊天,一位记忆力超群者(能完整地背诵王勃《滕王阁序》和郭小川《祝酒歌》,这些储存在他脑海里的篇章不下百部)说起一个故事:那是另外一次家乡发起的募捐,这位在某厅担任处长的老乡,向郭老师看齐捐出了五千元,后来发现郭老师的五千元是在为家乡助力的一个项目中的扣款。朱某(这位“朗诵家”)半开玩笑地说:上当了!这很能说明郭老师急公好义但并非没有头脑。他身上有种感召人的热情,但表现出的经常却是一个批评者的、怒其不争者的姿态。他最大的兴趣是研究学问。通常他身上却贴着喜欢打牌的标签。关于故乡历史、现实掌故,我没有见过比他更了解的人。他是从文化意义上、民俗学的角度,来叙述这些故事的。每次有郭老师参加的聚会我最兴奋。我像个比读者更期待新的精彩故事的那个人。
他,又总让我想起波兰作家布鲁诺·舒尔茨小说中的父亲形象:“父亲,那个不可救药的即兴诗人,那个异想天开的剑术大师……”(《裁缝的布娃娃》)
“父亲自觉地越来越远离了那个快乐的世界,逃进想全身投入的艰难晦涩的学术领域。”(《死季》)
有一天,我来到他还在画报社的办公室,刚在一个已经显出破损迹象的真皮沙发上落座,视线碰到零乱的办公桌上一只仿佛从遥远的县文联暗红旧桌上移来的“像一株模样怪异的菌群”的烟灰缸时,他便急不可耐地向我谈起董其昌——新近他在《新华文摘》上看到的一篇文章。他谈到董其昌“恶霸地主”的行径——“骄奢淫逸,老而渔色,有多房妻妾,且招致方士,专请房中术,竟到了变态的地步”,已六十高龄的董其昌竟然看中了诸生陆绍芳佃户的女儿、年轻美貌的绿英姑娘。更可恶的是,他的几个儿子都相当专横,尤以第二个儿子董祖常最为狠毒,带了人强抢绿英给老子做小妾。紧接着,他突然话锋一转,大赞董其昌的书画理论“南北宗”:“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干……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见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他几乎一字不落地把这段中国山水画史上影响深远的话给背出来了——我发现,在博闻强记的功夫上,他一点不落后于前面那位朱君。郭老师好抽烟,修长的脸膛通红,不再丰茂的灰白头发不时被电风扇吹起(他不断地用另一只手缕直,而夹烟的那只,半天没动,烟灰像一只弯曲的、开着玩笑的毛毛虫),他睥睨的眼神里射出激动的精光,略微弯钩的鼻子一耸一耸,说话时,嘴巴张开——以一种等待回应或者思索者的停顿引导着对方的思路,牙齿经年遭受烟熏火燎已变得黯淡无光,并略有黑黄色。他的谈话很有吸引力——他是那种很愿意交谈的、诚恳的人。我注意到,他桌上研好的墨,和一张册页大小已勾画了几笔山水轮廓的宣纸——他竟有些羞涩地说,他开始在学习国画。“首先要入古”“在取法古人中获得技巧”,他接着说起宋元的范宽、郭熙、李唐、马远、王蒙、黄公望、曹知白及清初“四王”。他滔滔不绝,显然在绘画理论上已经走得很远,为即将退休从事绘画创作做了充足准备。他扫了我一眼——仿佛具有看透我心思的灵异功能,说摄影(他是全省仅有的两位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之一)不能算是艺术,最多只能算是科技 美术,是近代技术进步的产物,依附于绘画上的一个视觉艺术的旁支。他并非信口开河、胡言乱语,而是建立在阅读、感悟基础之上。他自豪地讲起老家“郭家里”的故事,说你是作家,如果听我讲这些故事,将要写成厚厚几本书。他随口说起我曾写过的他家乡地方神祠“丛林寺”,一头身上插刀吐血而亡的猪(它倒地处成为神祠选址地);那个村善出教师和算命先生——后者70年代结队去县政府上访的故事,我至今印象深刻。他不避讳说自己很懒,四体不勤,家务事不做一分。他用家乡谚语形容——“蛇钻入屁眼都懒得扯”!他自豪地说,小时候,因为不爱干农活,被村里耆老诟病,母亲义正词严地护短:我儿子是干农活的人吗?他将来是要做秀才的!他的懒,让我想起在广东顺德,他的堂兄——那位不洗澡不洗脚(用报纸包住臭脚)睡在宾馆的人——难道懒并以懒自豪是“郭家里”男子的集体习性吗?
无论如何,郭老师出自一个社会结构复杂,同时人才辈出的村落。这个“郭家里”的地域,横跨了数个行政村。我们老家通常说,“郭家里,郭十里”(意即范围达十余平方公里)。这个村落,与擅长朗诵的朱君那个离县城一两千米的“莲花村”相仿佛。那个村子,有莲花桥等古迹,我们县名得来与此有关。朱姓,在我县不如李姓、刘姓显赫,但出过至今为人津津乐道的人物:一门三进士(父亲朱之杰及两位都入翰林的儿子朱益浚、朱益藩——后者是清末光绪、溥仪两位皇帝的老师)。该村另一位进士朱寿慈,曾做过白鹭洲书院山长。朱家人骑马坐轿,村子也叫花塘官厅——我未曾考证与我家所在琴亭官厅二者的关系。琴亭官厅早已倾圮,花塘官厅历经百余年依然完好。
朱君曾在南昌一家酒店担任老总多年。那家酒店的特别之处,就是屋顶戴着一个金光熠熠的巨大皇冠——那象征气派、豪华的浮华标志,老远便能从洪城路的建筑群中一眼认出。酒店顶着那皇冠从20世纪来到21世纪,如同一个揶揄的、穿着一套旧西装依然不愿意扯下标签的人,时时刻意让你注意到它的存在。朱君的普通话带着浓浓的乡土味儿——我们那独特的口音(永莲宁方言),外人一听便知道来自哪里——每次他即兴朗诵,我在他略显壮实的身躯,宽脸、五官齐整、一头浓密黑发的脸上,在那抑扬顿挫的气流造成的铿锵音节中,总仿佛看到那戴着金色皇冠的酒店在眼前浮现。酒店门口有几个印度男子,盛装打扮,彬彬有礼地向宾客展示周到服务(他们不仅会说普通话,而且会讲地道的南昌话)。我不知道他们是否适应这里不给小费的习惯。去年暴发的新冠疫情尚未结束,这几个印度迎宾,就在火急火燎地等待重返中国。一所高校副校长老乡,曾在一个小范围内介绍莲花男人的特点:一会写字(大多能写一手过得去的硬笔或毛笔字),二会做菜(也许郭老师是个例外)。会写一手漂亮的书法,在我们那里很能抬高门面。写字的传统,在家乡,可谓源远流长。这一点,也体现在朱君经营的酒店中。一楼的墙面和柱子,挂满了某次征稿来的书法作品,作为装饰和酒店文化的一部分。这些书法,在锃亮的、金碧辉煌的大厅,像笑语喧哗的乡贤,带着某种遗老遗少们僵硬的、作揖客套的举止,望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们,而忘了时间并在时间流逝的无声中变得衰老的自己。
在酒店大厅那易于流逝而让人迷幻的时光,和酒店内部空间所营造的一种似是而非的梦幻情调中,我看到墙上的书法在哗啦啦地“唱歌”——就好像,它们常年被压抑在博物馆阴沉玻璃柜后面的某种品性得到释放,像一群循规蹈矩的孩子突然获得了放肆、粗野的权利。无疑,我这个老乡是始作俑者。他任性而直率地拉近了书法与百姓的距离,将它们从展厅、博物馆那高高在上的位置请下来,让它们来到普通老百姓身边——甚至,这栋涉外酒店,还成了推广国粹和传统文化的一个“民间舞台”。我们被朱君邀请到酒店品尝一道特色菜——“莲花血鸭”,这道据说“不亚于莲花本地手艺”的菜肴,是想激发我们这些异乡人的乡愁吗?一只游进城市的鸭子,头戴着金光闪闪的皇冠,是要告诫乡族子弟,摆脱乡土的羁绊才能真正成功,其实最后,还是想回到那不可能回去的故乡?我记得小时候,听大人形容某家有实力,说“他家是开饭店的”。开饭店,无疑从小成为千万个孩童懵懂的理想。我想起开服装店的“摩丝头”,身上的神秘色彩和仿佛活在自己梦幻色彩中的特质,与朱君有着某种相似性。
记忆是生命成长、远航的某个起点。而记忆是无时无刻不在累积的,拨开记忆错乱纷繁的迷障,总能找到那最初的原点——它始终在召唤、引导着我们回到故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