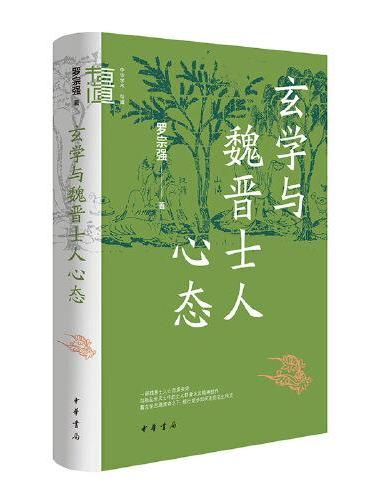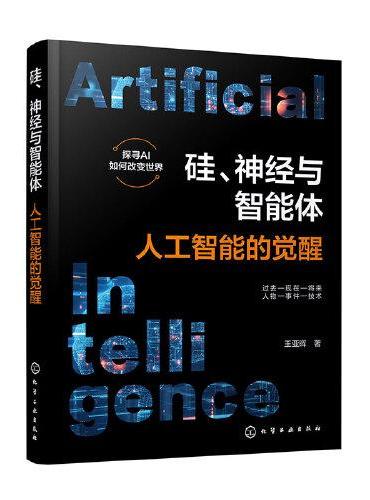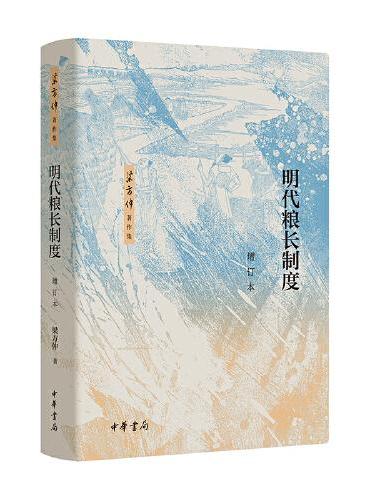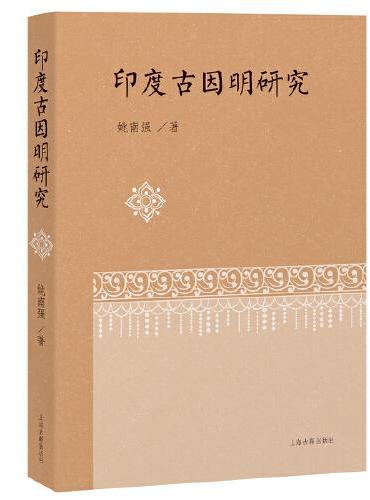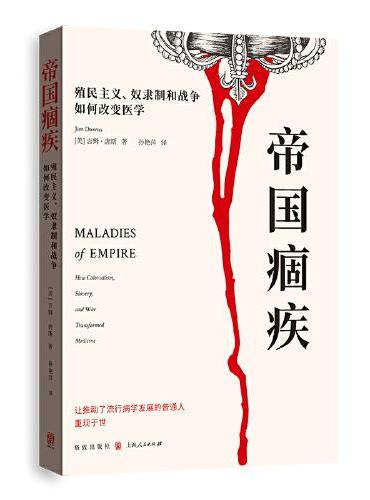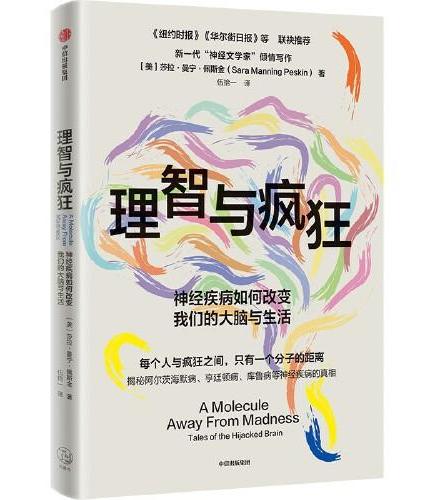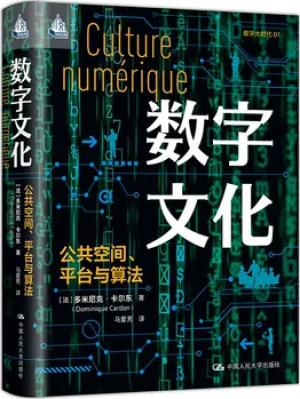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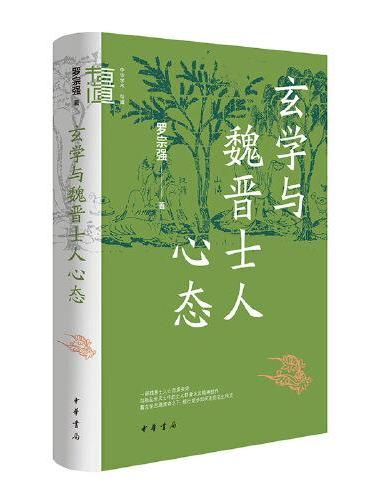
《
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精)--中华学术·有道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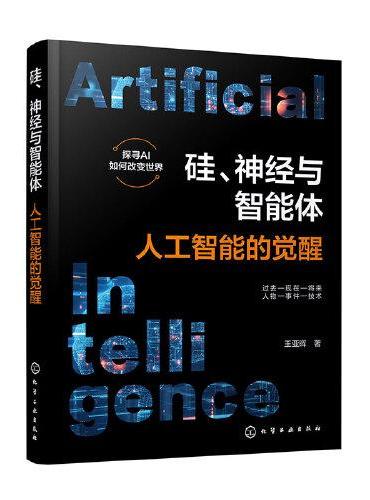
《
硅、神经与智能体:人工智能的觉醒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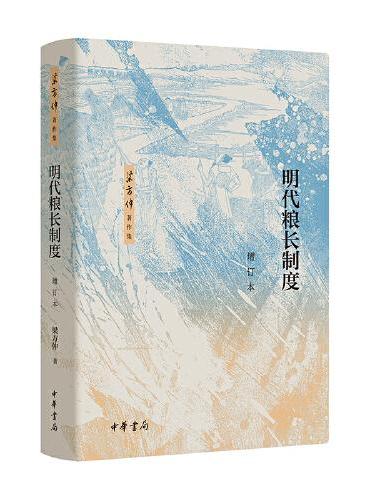
《
明代粮长制度(增订本)精--梁方仲著作集
》
售價:NT$
316.0

《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本雅明精选集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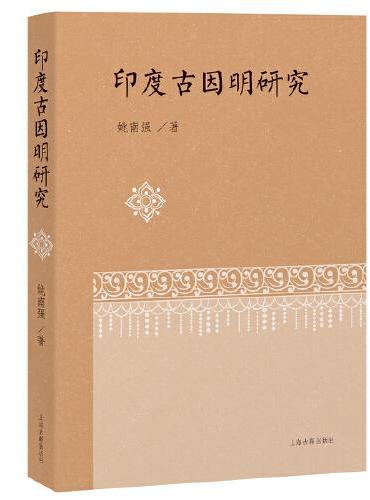
《
印度古因明研究
》
售價:NT$
6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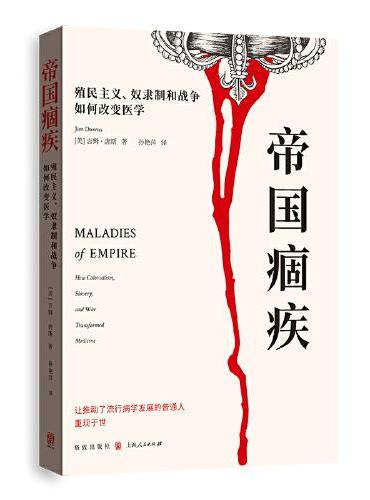
《
帝国痼疾:殖民主义、奴隶制和战争如何改变医学
》
售價:NT$
36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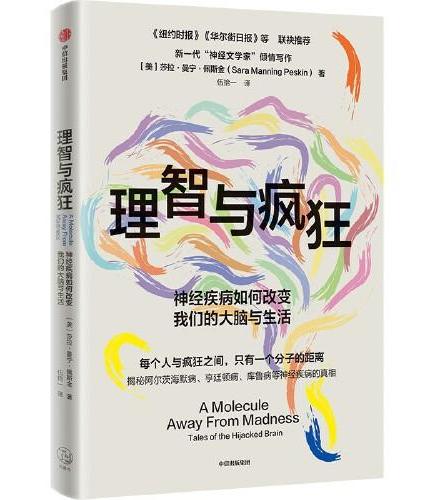
《
理智与疯狂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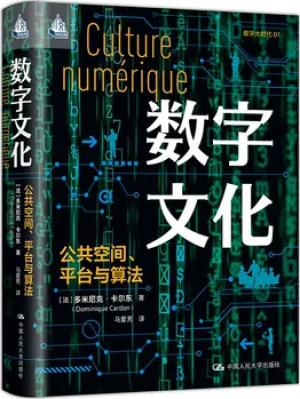
《
数字文化:公共空间、平台与算法
》
售價:NT$
505.0
|
| 編輯推薦: |
这是听障马拉松选手曹关天的人生传奇!
他从山间小路,一路奔跑,跑出大山,跨出省市,跑出人生的“围城”,直至站在极限长跑运动的“巅峰”。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生是一场自我对抗,不管起点有多低、路途有多艰辛,都该勇于涅槃,不屈不挠地前进到最后一刻。
|
| 內容簡介: |
长跑选手曹关天,出生于一个偏僻的山村,他两岁时被误打了一针抗生素,导致终身聋哑,成长时饱受各种欺凌,逃跑成了他唯一的抗争武器……六年级时,他的跑步天赋被一位叫“蔫蛤蟆”的体育老师发现,后者对他进行了魔鬼式训练,但随着训练强度的日增和全省长跑大赛的临近,他渐渐发现了老师背后不可告人的秘密……
他从山间小路,一路奔跑,跑出大山,跨出县城、省城,跑出了人生的“围城”。最后,他站到了马拉松运动的巅峰——100公里高原越野跑,然而,一场骤然而至的强冷气团却正汹涌于途……
|
| 關於作者: |
刘群,Leo,曾用笔名大刘。
上海作家,生于劳改农场的旷野小屋,那年春天的最后一场暴雪中。
十九岁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后任香港《文汇报》 记者十年,此后做过楼盘策划、广告合伙人、包租公、 诗人、咖啡店主理以及职业铲屎官。
曾四个夏天自驾近万公里横贯美国,通过采访、实地观察等方式,写下观察美国社会的非虚构作品《北美客》。
逢疫年,每日居家锁足,写下这本关于听障马拉松选手的人生传奇。
如果你也曾困顿过,迷茫过,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
那么,就拉过一把椅子,静静地坐一会儿吧,
听作者说说这位无声跑者的事儿,
和他一起,不屈不饶地,寂静地,奔跑一次。
|
| 目錄:
|
引 子 / 1
第一部 写稿的人 / 11
第二部 无声的马拉松 / 33
第三部 生死荒野 / 343
尾 声 / 403
鸣 谢 / 416
|
| 內容試閱:
|
谨以此书向欧内斯特·海明威 致敬
“一个人可以被摧毁,但不可以被打败。”
17
你想知道我这人生的第一条跑道是怎样的吗?
如果是冬天,需要打一个火把下山,因为早上六点,山里的天还是乌漆嘛黑的,山峦的黑色影子好像剪纸一样贴在暗灰色的天空里。我拿的那个火把是浇了煤油的,燃烧后有一股刺鼻的焦臭味,但可以把山道照得很亮,远看像一个火红的星星在晨昏中移动。下山的路大约两公里,因为其中要翻越一个山坡,拐过一个山崖,通常小跑也需要二十多分钟,等下了山,在一个种子店门口(院子里有条龇牙的棕色大狼狗),会遇到一条去镇子的公路,那是一条平坦的水泥路,周边全是水田,水泥路像一条孤独而蜿蜒的河流,穿越在亮闪闪的镜片当中。沿这条水泥路大约跑上三公里,就可以到达镇上的学校。
每天一来一去,就是十公里左右。
后来,渐渐形成了一种心理感觉,只要一踏上这条道,在密林、山径、溪流、公路、田野之间,我就进入了一个安全的港湾,疾奔在这港湾里,没有人可以捉弄我、追打我,没有厕所提裤子乱尿、没有垃圾筒扣头、没有丢石头吐口水吃狗屎,没有人欺负我、侮辱我。
逃跑成了我抵抗的武器,这其间,我还收获了一个沉默的陪跑。
18
还记得那条养蜂老人的癞皮狗小黑子吗?
一清早,它就颠颠地跑进土院子,等我把肉馅包子撕一小块给它吃。有时候,如果我喝稀粥,会在地上倒一点,它就伸出舌头舔一舔。它蹲坐在地上,一双热切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它脖子后面一大撮毛没了,估计是和其他野狗打架打没的,露出一块惨白的皮。
吃完肉馅,它就站在大门口等我,因为我跑步去学校,它是一定要跟去的。
深秋的清晨,寒雾像化开的稀豆浆,人们常常看到村里的哑巴带着一条赖皮小狗奔跑在山道上,对村里人来说,那可能是个滑稽的场面。
我们常常比赛,显然,我不是它的对手,因为它有四条腿,祖先是荒原上的狼。它在前面领跑,四脚翻飞,像一匹脱缰的小黑子野马,一会儿就跑得没影了。等跑得太远了,它就趴在前方草丛里或者某棵树下等我,等我呼哧呼哧跑到,它再猛地一蹿,超过我,跑得没影了。
有时候,在陪我跑下山的山径上,它会在前面捉蟋蟀、捉虫子,它抓住了虫子,都是前爪子一踢,踢得老远,然后再跑过去观察虫子四仰八叉的样子。
我们一起飞奔下山,路过种子店就拐上大路,站在那红色的砖墙旁,我挥手、跺脚,让小黑子回去,它迟疑地侧身后退半步,接着仍不依不饶地跟着我,一直跑到学校,看我走进人头攒动的校门,隔着铁栅栏,它黑亮亮的小眼睛呆呆地盯着我。校门口保安挥舞着竹棒驱赶它,它受了惊吓,才扭头一溜烟地往回跑。
那阵子,我跑在学校围墙外的公路、山道间。
初冬,山风疾而冷,带着特有的荒凉。它刮过我的脸,像一把把冰冷的刀片,割开皮肤,让神经末梢都能感受到它的粗犷。
我跑着,跑着,像一只被掷入山间的异类蝙蝠。
直到十五岁那年,学校新来了一个“怪人”,比我还奇怪的“怪人”。
19
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我喉结像一块小石头顶出来了,咕咕咕野兽般的声音估计更奇怪了,嘴巴下有黑色的绒毛,拉尿那货儿有时居然会犟头犟脑地翘起来。
这一年,来了一个新体育老师,欧阳,不过大家都不这么叫,背地里称他“蔫蛤蟆”。
他,黑皮如炭,头发剃得只剩两三毫米,远看就是一个行走的大土豆。据传他小时候就是长跑的好苗子,可是后来他身高体重涨得过快,初二就超了一米八,在省里出不了啥成绩,改练过其他项目,但毕竟时机已逝。他上身短而显瘦,看起来和普通人没啥两样,但是脱下长裤换上运动短裤时,就露出来两条像青蛙一样超级发达的大腿,肌肉鼓鼓囊囊地隆起,整个人从大土豆变成了一只直立行走的袋鼠。
如此强壮的家伙,他每天的精神状态却是蔫蔫的,整个人好像在梦游。
欧阳只要一站在操场上,便立马从口袋里掏出一副深色的墨镜戴上,那时候我们学生都叫这种眼镜为蛤蟆镜。一次,我路过外走廊,看到他戴着墨镜站着一动不动地看着远处,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天边的云也一动不动,估计云都被他看毛了。
所有人都看得出,他的心不在这所学校。
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老师,除了“蔫”外,他从来不笑,如果不戴墨镜,他总是低垂着脸,皱眉,眼白比眼黑多,两只手无所事事地插在裤兜里,流露出一种让人害怕的眼神。
我推测他的心情不好是有缘由的,因为据传他以前是省体育学院的,一定是犯了什么事情或者得罪了什么人,才被发配到我们这么偏远的黄岭小镇上当体育老师。只有病人、废材才会来我们这么犄角旮旯的地方当老师,比如说荷包蛋校长(他看上去有神经性焦虑症,开会时小动作比大动作多,总是不停地用手去捋他那只剩下一绺的头发)。
欧阳老师的阴郁就像是乌云遮住了太阳,云的黑影在大地上徘徊,弄暗一切。
上美术课,一张小纸条飘到了我脚下,这是小张伟和他的几个跟班在传看的东西,上面画了一只蹲在荷叶上的戴墨镜蛤蟆,脸俨然是欧阳,旁边歪歪扭扭地写了六个字:“蔫蛤蟆爱拉屎”。
第一堂体育课,“蔫蛤蟆”让全体同学在操场上集合,然后前后左右转体,操练了两把。通常,我看其他同学转,我也转。但是,当他命令全体向后转的时候,我反应慢了,所有人都转过去了,只有我一个人呆呆地站在原地。
他不知道我是聋子,大步走了过来,用力拉扯我的耳朵,我痛得喉咙里呃呃呃呃地怪叫,我看到旁边同学嘴巴在动,似乎是在告诉他“这是个聋子”,他的手才像触电一样地弹开。
看得出,他蔫蔫的眼神非常嫌弃我们全班同学,尤其厌恶我。
他的体育课都很简单,热身五分钟后,立即开跑。
我们那时候缺体育老师,同年级两个班的男生女生一起上体育课。于是,大伙儿一起开跑,像一群围栏里放出来的山羊。
女生绕操场跑三圈,男生则需要绕操场跑四圈。
欧阳蛤蟆老师就拿了秒表,懒洋洋地斜靠在升旗台前,等着我们出丑。
跑四圈就是1600 米。第一圈,小张伟把嚼着的椿树叶子吐在跑道上,他乱糟糟的一头黑发一直跟在我的后面,估计伺机想踹我一脚,以博得哪个女生的笑。但是,我跑得像一阵风,他没有得逞。到了第二圈,小张伟喘得像一只急待散热的狮子狗,但他眼神依然是一种戏谑的神情,他死死咬着牙齿。到了第三圈,他突暴着眼睛,喘着粗气,乱糟糟的黑发像烧焦的麦田淋了一场雨,他踢了一下脚,放慢速度,居然坐在跑道上,不跑了。班长李峰是最努力的学生,看得出他是想玩命地跑出好成绩,脖子像鹅脖子似的往前努力地伸着,一探一探的,呼吸像一只破旧的风箱。而小张伟的跟班臭咸鱼(隔壁班的)也好不了多少,我第一圈超过他的时候,他的腿好像已经被水草给缠住了,有点散乱而没有章法,随时要往前跌倒的感觉,平时欺负我的那股狠劲头荡然无存。
我那时还不知道自己为何跑得那么轻松,跑完第四圈,领先了第二名足足一圈的距离。我在终点线停了下来,给欧阳老师示意:我结束了。
我觉得他一定会很满意我的速度。
但是,昏睡的他像突然醒了过来,蔫不拉几地冲我跑了过来,他的脸一阵惨白,嘴唇上下颤动,而且张得很大,龇牙咧嘴,我知道他是在骂人了。
他挥手示意,让我再跑一圈!什么,再多跑一圈?我简直不敢相信,难道他没有看到我比其他人快很多吗?难道他没有看到我已经完成了吗?难道他前面一直在打瞌睡,没有看整个队伍?
我知道,委屈对自己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就像音乐和朗读对我来说一样没有意义。
难道,他不相信我用了别人跑三圈的速度,完成了四圈?
看到他愤怒的、不耐烦的表情,他的眼白,他的嘴唇颤动吐出的几个脏词,我满心愤怒。
他的确没有注意到我已经完成了四圈。
我一跺脚,就又上了跑道,不能申辩什么,这是我的命。我面无表情地在操场周边做着最后的狂奔,我喘着气,像个发神经的公牛,玩命地用上下飞动的前脚掌砸着煤渣跑道,蹬出一阵阵的灰。我撒腿如飞,超过了一个又一个同学,最后仍然第一个跑到了终点。
欧阳老师戴上了蛤蟆镜,看不出他的任何表情。
他让全班列队,在人群中用手拎着小张伟的领子,高我们一头的小张伟在体育老师面前,就像一头骡子站在一头大象旁,欧阳老师似乎在宣布着什么。
欧阳从脖子上掏出哨子,右手伸出四个手指头,嘴巴用力地一鼓,小张伟眼神冷冰冰的,翻了个白眼,衣领口散乱地敞开着,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欧阳老师摘下蛤蟆镜,抬起长腿,踹了小张伟一脚屁股,他才像被电击一样的,一脚高一脚低地又沿着操场跑了起来。
欧阳老师让他再跑四圈,全班同学观摩。
小张伟一缕焦黑的头发搭在脑门上,牙齿咬着嘴唇,脸色发白,像是一头精疲力尽的骡子拉着板车在爬大坡,我不禁生出一种报复性的快乐,原来幸灾乐祸是那么的开心!最后一圈结束了,小张伟四肢颤抖地倒在地上,冷冰冰的眼神直勾勾地看着苍白的天空,嘴巴只有出气没有进气,活脱脱成了被喷了杀虫剂的濒死虫子。
小张伟你也有今天?我瞪着他想。
那一刻,我忽然对“蔫蛤蟆”欧阳老师充满了一种复杂的心情,几乎已经忘记了我自己那个被冤枉了的第五圈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