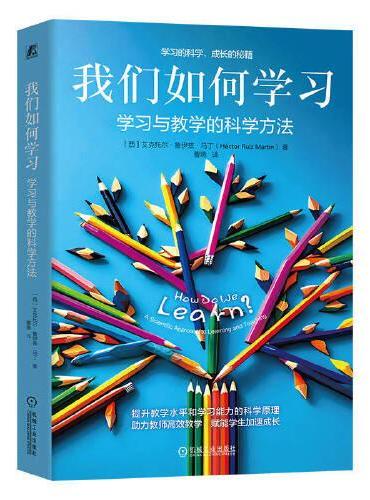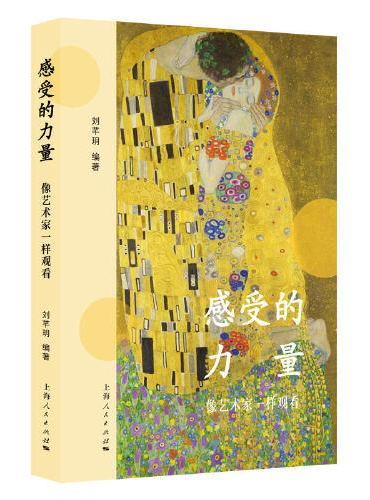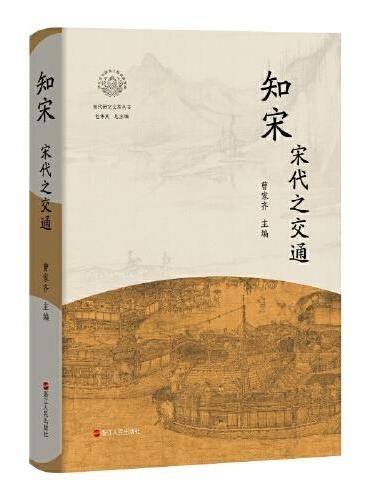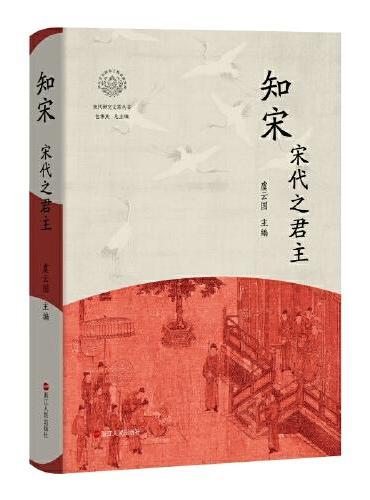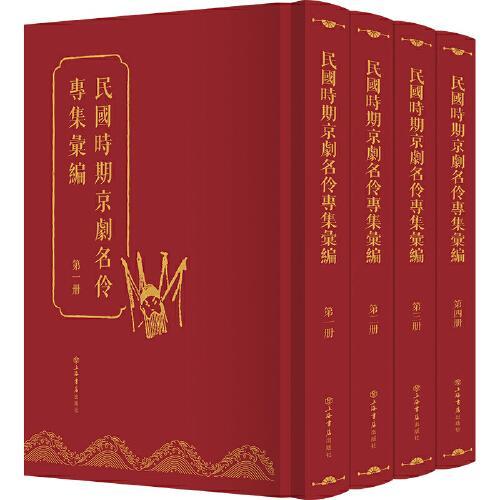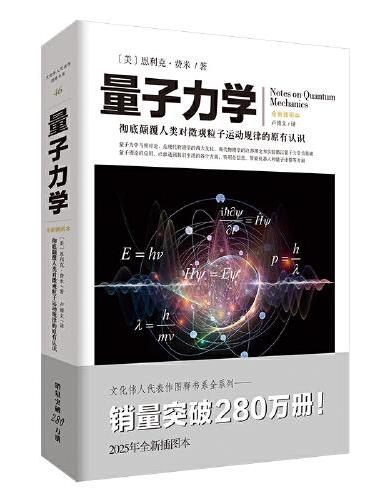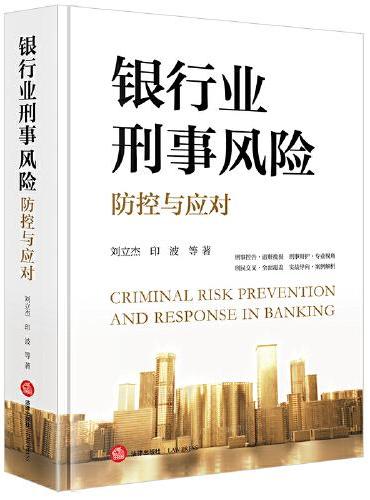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我们如何学习:学习与教学的科学方法 (西班牙)艾克托尔·鲁伊兹·马丁
》 售價:NT$
403.0
《
感受的力量--像艺术家一样观看
》 售價:NT$
265.0
《
知宋·宋代之交通
》 售價:NT$
403.0
《
知宋·宋代之君主
》 售價:NT$
454.0
《
民国时期京剧名伶专集汇编(全4册)
》 售價:NT$
20298.0
《
量子力学 恩利克·费米
》 售價:NT$
245.0
《
银行业刑事风险防控与应对
》 售價:NT$
449.0
《
语言、使用与认知
》 售價:NT$
321.0
編輯推薦:
1.记录哲学大师拉图尔生前的最后一次对谈,一书饱览拉图尔的哲学生涯。本书是法国哲学大师拉图尔生前最后一次与记者对话的访谈录,在这次重要的对话中,拉图尔对自己一生的思想结晶进行了总结,回顾了他五十余年的漫漫哲学之路。
內容簡介:
我们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科学家的话是否代表了权威?哲学究竟是什么?面对生态威胁,我们应该怎么办?
關於作者: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1947—2022),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代表作有《实验室生活》《我们从未现代过》《潘多拉的希望》《着陆何处?》等。
目錄
序 言
內容試閱
序 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