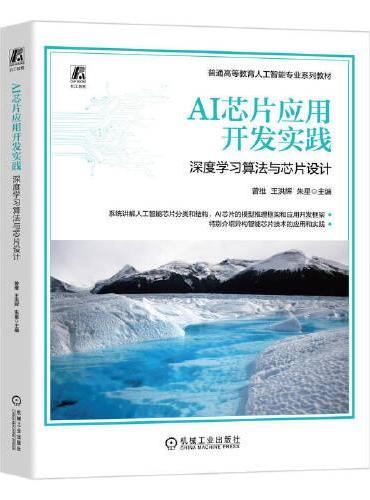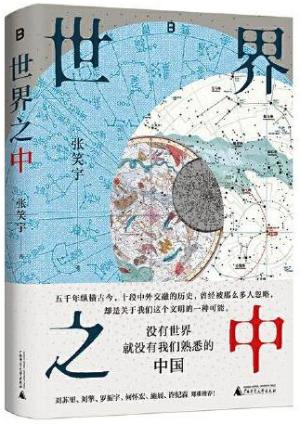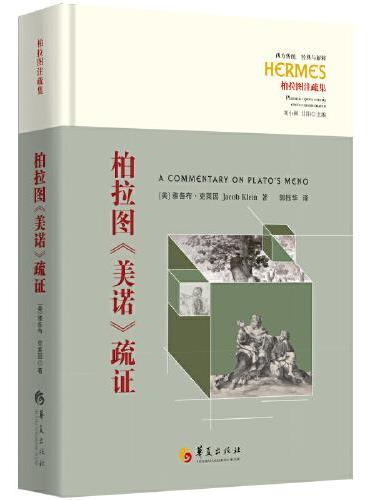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余下只有噪音:聆听20世纪(2025)
》
售價:NT$
959.0

《
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
》
售價:NT$
408.0

《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摆渡船上的人生哲学
》
售價:NT$
306.0

《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梁方仲著作集
》
售價:NT$
689.0

《
帝国作为装饰品:英国人眼中的大英帝国(帝国与国际法译丛)
》
售價:NT$
4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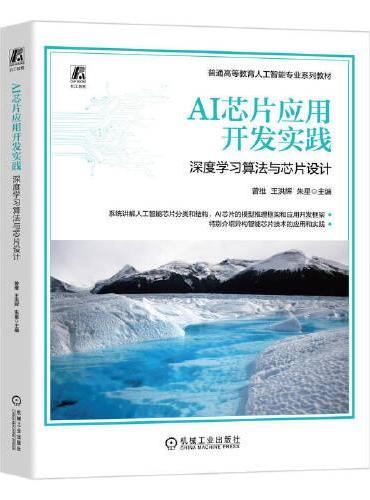
《
AI芯片应用开发实践:深度学习算法与芯片设计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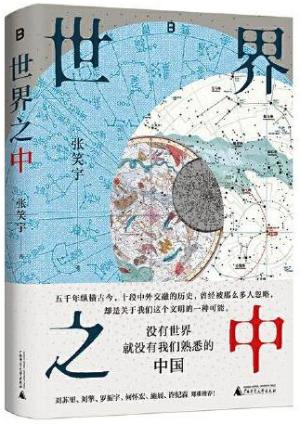
《
世界之中(文明三部曲之后,亚洲图书奖得主张笑宇充满想象力的重磅新作)
》
售價:NT$
4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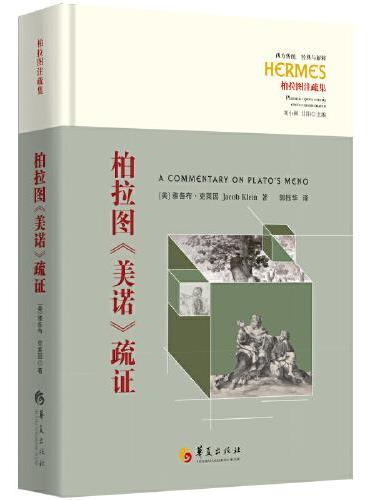
《
柏拉图《美诺》疏证
》
售價:NT$
449.0
|
| 內容簡介: |
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学者常常将自己描述为窃听过去对话的人、不同思想世界的探索者,以及过去社会的转译者,而批评者时常嘲讽他们只狭隘地关注少数人的思想;不过,从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当代思想并对其做出理性评估的角度来说,思想史俨然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
在这本引人入胜的思想史导论中,作者首先考察了思想史的发展历史,剖析了各种方法论争论,并提出了对这一领域的清晰定义。借助广泛的历史案例,他向读者展示了哲学、政治、宗教、科学、艺术的等等思想如何在其历史背景中起源,它们如何被其所处的社会所塑造,反过来又塑造了这些社会。最后,作者批判性地审视了思想史的现状,并简要讨论了其未来发展方向。
|
| 關於作者: |
理查德 · 沃特莫尔
----------------------------
理查德·沃特莫尔,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现代史讲席教授、思想史研究所主任,国际知名期刊《欧洲思想史》主编,曾任萨塞克斯大学思想史研究所主任,长期从事思想史研究。著有《启蒙运动的终结》《共和主义与法国大革命》《对抗战争与帝国》等多部著作。
岳秀坤
----------------------------
岳秀坤,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与外国史学史、全球史研究。先后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清华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副编审。译有《扭曲的人性之材》等。
|
| 目錄:
|
导 言 1
第一章 思想史的身份 15
第二章 思想史的历史 27
第三章 思想史的方法 63
第四章 思想史的实践 81
第五章 思想史的适用性 93
第六章 思想史的现在与未来 119
结 论 137
进一步阅读文献 141
索 引 165
|
| 內容試閱:
|
导 言
在英格兰西北部的坎布里亚(Cumbria),温德米尔湖的东侧,有一处艾克勒格峭壁,那儿曾经有过一个采石场,为这一地区的宏伟建筑提供石板和石材。从18世纪到20世纪早期,这里一派繁忙景象,采石场规模巨大,有自己的码头。这一切已经成为历史,后来此地建起旅馆,如今地面上还可以见到五块厚厚的石板,上面有细密的雕刻,此外,水中还有一些突兀的石头或隐或现。有些雕刻完成于1835—1837年之间。曾经有很多能工巧匠受雇于采石场,其中有一位显然是自发地在石板上刻下了一些信息。雕刻的信息中不乏国家级名流和地方名人,包括“纳尔逊”、“牛顿”、“沃尔特·司各特”、“华兹华斯”、“詹纳”(Jenner)、“汉弗里·戴维”(Humphry Davy)、“理查德·沃森”(Richard Watson);还有这个地方的拥有者,“约翰·威尔逊”(John Wilson),他是湖畔诗人的友人,当地名士,为《布莱克伍德杂志》写稿,还是爱丁堡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1820—1851);还有“约翰·劳顿·麦克亚当”(John Laudon McAdam),他以为本地筑路而闻名;此外,还有给当地学校捐款的一些人的名字。最大的一块石板,高达五米,刻写的字母硕大、清晰,石匠所持的观念由此可见一斑:“国债八个亿/哦,天佑吾国/乔治三世,威廉·皮特/财力是战争的支柱/陆军元帅惠灵顿/英勇的海军上将纳尔逊。”
历史学家们会用这些刻字做什么呢?社会史学者也许会尝试着从中发现一些信息,关于采石工人的社会地位、工作条件,以及工作之外的生活,还有他们所身处的社会属于何种性质,涉及阶级、性别、仪式和身份认同。经济史学者可能想知道另外一些信息,关于工人工资的比较,这一时期的经济状况,通过跟当地的其他行业或是更为普遍的全国性趋势比较,发现采石场雇工的相对地位。有可能还要寻找与之相关的其他雕刻,并且加以评估。文化史学者也许会推测个人或社会团体如何通过地方性、区域性和国家性的话语来表达自我,进而分析其中的权力关系,描绘出个别的历史人物跟更大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图景。思想史学者则必须从这些语词入手。作者刻写这些语词想要传达的是什么?为什么他偏偏选择这样一种方式?他所持的看法在别处是如何表述的?它们的渊源在哪里?反响如何?
这种研究是很困难的,遇到意义难以辨明的情况会尤其困难,比如像这个例子,刻写的只是一些孤零零的词汇,或是一些格言警句。依据雕刻中提到的人名去寻踪觅迹,还是相对容易的。它们显示出,雕刻者了解当地有哪些头面人物,看起来尊重他们的社会地位,对其慈善之举尤其是捐资给学校的穷人,评价相当高。它们也透露出,技术发明和科学,以及诗歌和文学,还有军事力量和英雄之举,是受人尊敬的。除了分析刻写在石板上的那些陈述之词中所包含的论点,想要再进一步,就比较困难了。它可以表明,这个国家因为国债负累而陷入困境,需要拯救(“哦,天佑吾国”)。对金钱与战争之间的对立关系,此处有清晰的表述——“财力是战争的支柱”。紧接着,威廉·皮特出现了两次,那么,就有可能——但无法确证或是否定——作者认为皮特是上一代人里的战争贩子,也可能是他自己年轻时代的战争贩子,因为提到了纳尔逊和惠灵顿。从爱国的立场赞颂这些大人物的品质,同时又哀叹战争及其后果的严重性,这是那一代人很可能会有的典型表现。
更为重要的是,“天佑吾国”这一引语直接取自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为罗彻斯特大主教弗朗西斯·阿特伯里(Francis Atterbury)博士所写的墓志铭。1732年,阿特伯里在流亡中逝于巴黎,临终前,他在女儿的怀抱中努力道出此语。阿特伯里说过此语是众所周知的,而他又是借用自教父保罗·萨尔比(Paolo Sarpi)。萨尔比是著名的威尼斯史家,临终前讲过“愿她长存”(Esto perpetua),祝愿威尼斯能够维持独立政权的地位。“财力是战争的支柱”这一说法,尼可洛·马基雅维利和弗朗西斯·培根都曾经反驳过,可以追溯到西塞罗的第五次反腓力王演说(Cicero’s Fifth Philippic),并且被拉伯雷、丁尼生等许多作者引用过。对于艾克勒格峭壁的石匠而言,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叹息社会日趋商业化,奢靡之风弥漫,预测所有的社会都会由于纵欲过度、穷兵黩武、债务日增而导致悲惨结局——在18世纪的文献里,这些也是老生常谈了。大卫·休谟收入《政治论文集》(Political Discourses,1752)的一篇文章《论政府贷款》,提供了石匠所继承的此类哀怨文献的一个绝好的例子。休谟为欧洲各国债务日增的后果倍感忧虑,用“瓷器店里动刀枪”为喻,描述当时的国际关系。事实上,瓷器必然会四分五裂,而那些债台高筑的国家,其国内经济和市民社会亦将崩溃。在干涉法国大革命以及拿破仑战争期间,债务恐慌达到了顶点,当时债务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50%,这是此前从未出现的数字。对于生活在那个时期的人们来说,皮特首相跟国债的关系是尽人皆知的——尤其是在1797年,政府解除了英格兰银行把货币兑换为黄金的义务。
跟休谟一样,18世纪很多关心国家生活的观察家都确信,英国这个国家正在走下坡路。他们之所以这么认为,对于战争或是债务导致破产的忧虑是一个主要原因。以我们的后见之明,所谓“工业革命”在当时已经显露出了端倪。有些历史学者认为,经济增长从未像18世纪那么快过。 而且,按照巴兹尔·威利(Basil Willey)等人的描述,这一时期的特征是稳定性在增强,构成了维多利亚时代自信(Victorian self-con?dence)的序曲。然而,对于当时人来说,18世纪的英国是一个处在危机之中的新国家,深受债务、战争和政治分裂的困扰,詹姆士二世党和汉诺威党对立,辉格派和托利派抗衡,还有圣公会信徒、天主教徒以及异见分子的分歧,以及社会商业化的支持者和敌对者的对抗。对于未来会怎么样,当时的观察家难做预判,仅有的共识是,有国家毁灭的可能。众人皆知,巨变即将来临;前途未卜之感,随处可见。甚至就连著名的冷静派,对英国的前景抱有乐观预期的学者,像亚当·斯密或让-路易·德·洛尔梅(Jean-Louis de Lolme),也不认为现状稳定,或是值得维持。哀叹英国将会崩溃和战败的论调,倒是更为
常见。
英国经受住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冲击,并且在经济和政治力量方面成长为欧洲的领先国家,这一点足以引人注目,即便还有许多观察家持保留意见。然而,尽管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成为其他许多国家的典范,英国的智识生活仍然充斥着虚假的自大感,认为在经历了一段非同寻常的发展之后,英国已经达到政治和商业的霸主地位,但这种状态注定不会持续,国家不可避免会走向衰落。到19世纪30年代,债务状况仅仅比18世纪的水平略有降低,唱衰英国的老调这时仍有回响。这正是艾克勒格峭壁的那名石匠所处的境况。他这个人,让人想起了那个过去了的时代,充满末世忧虑,预感国家注定衰亡。他的雕刻,其重要性就在于揭示了特定观念的持续存在,以及在“均势时代”即将到来之际对未来的持续担忧。因此,石匠的话非常重要,它给我们提供了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视角,而这个视角常常被人遗忘。
理解石匠的话有何意义,让思想史研究的能力得以展现,亦即:它可以揭示出过去的思想、观念或是论点背后所隐藏的东西,由于后代人的放弃或是拒绝,它们被忽视已久了。思想史家想要重现一个失落的世界,从废墟中恢复那些视野和观念,揭开面纱,阐明那些观念为何会在过去产生共鸣,俘获了支持者。思想,及其所创造的文化和实践,是所有理解行为的基础。思想,是那些前沿哲人之行动的表达,他们关于自由、正义或是平等的概念,仍然需要阐发;思想,也是所有社会中具有文化重要性的人物的行为表达,或者说,他们其实就是各种形式的大众文化的阐释者。就第二类人举一个例子吧,博物学者、作家亨利·威廉森(Henry Williamson),因1927年出版《水獭塔卡》(Tarka the Otter)一书而声名鹊起。1964年,他就世界大战问题接受了BBC纪录片的采访。他回忆道,1914年的圣诞节,在血腥的第一次伊普尔战役之后,他作为机枪军团的一名列兵,在弗兰德斯的战壕里,德国士兵跟他称兄道弟。德军跟敌方的英军自发地达成了停火协议,在阵地沿线的不同位置,这一停火持续了几个小时到几天不等。在此期间,威廉森跟一个德国士兵聊天,对方说,德国方面是为了“祖国和自由”而战。威廉森回答,战争是德国人挑起的,为了自由而战的是英国人,上帝和正义无疑将会站在他这一边。他又说,战事很快将会结束,因为俄国人在东线有很强的实力。德国士兵反唇相讥,认为德国不久将会取得胜利,而俄国就要崩溃了。争论毫无意义,因为谁都无法说服对方。这次交流让威廉森对战争的看法有了变化。他无法理解,为什么每一方的士兵都坚信自己是正义的一面;既然如此,战斗就失去了意义,变成白白送命、灭国的消耗战。20世纪30年代,威廉森一度参与法西斯主义运动,当时他相信也许它可以提供西方民主制度明显缺少的某些道德确实性。此举是他在1914年所感受的思想触动——双方都确信自己的事业绝对正确——的直接后果。给这种信念以解释,说清楚其源起、本质和局限,以免思想走入极端,正是思想史家要做的事。
还可以从大众文化中再举出例子。1935年,约翰·巴肯(John Buchan)的小说《三十九级台阶》(1915)第一次改编成电影,由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执导。“苏格兰飞人”(伦敦与爱丁堡之间的快车)抵达了爱丁堡的威弗利站,跟逃亡的理查德·汉内同一节车厢的有两位英国内衣销售商,其中一个对他看到的第一个苏格兰人——在窗口外兜售报纸——说:“你会说英语吗?”稍后,汉内在爱丁堡的北部低地被警察追捕,有个农妇把丈夫的外套送给了冻僵的汉内,并且因此遭到丈夫的殴打。约翰·劳里(John Laurie)——此人后来因为《老爸上战场》而成名——扮演的农夫刻薄、残忍、不讲公义、言而无信,拿了汉内的钱,答应保持沉默,却又想去警察那里告密。电影所表现的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人对待苏格兰人及其加尔文教信仰的偏狭心态。他们把加尔文教看作伪善、自私、野蛮的宗派。隐藏在这种民族成见背后的观念,其源起、传布以及没落,值得仔细考察。有关观念变化之影响,更近的一个例子出自电影《刀锋战士》,1982年由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执导,底本是菲利普·K.迪克的小说《机器人会梦见电子羊吗》(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1968),讲了一个发生在2019年的洛杉矶的反乌托邦故事。电影中,几乎每个人物都接连不断地抽着烟。无论是斯科特还是迪克都不曾想到,在世纪之交后不久,抽烟这一举动对观众来说已经不再象征着某人有地位、态度得体。这一点恰恰说明电影是战后时代的产物,而不是发生在想象的未来。思想史学者不管研究的是深奥的哲学论说、久远的文化实践还是民族偏见无意识的表现,都要对这些思想的源起和内涵加以解释,其历史不可能是简单直白的。就像伊丽莎白·拉布鲁斯(Elisabeth Labrousse)谈到皮埃尔·贝尔(Pierre Bayle)的《历史与批判辞典》(1697)时所说的:
观念史已经表明,作品一旦脱离了原初的社会历史语境,被当作传达普世信息的载体来阅读,那么,发挥其最大的影响力,凭借的不是对其思想的机械复制或是准确反映,反而是阐释过程中出现的含糊、误解和时代倒错。
诸多生活与观念的再现,关系到人们对于期待中的另一种生活状况的愿望,而历史,往往会跟那些号称有预言天赋的人开玩笑。
以上所述,可以归结为:尽管人类历史上看起来有时候会忽视思想,研究贸易周期、人口制度或是粮食收成等等问题,但思想是不能回避的。所有人都认可这一点。人们表达其思想,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伪装。因而,想要理解人们的所作所为、思想的真实意涵,以及它们与其所渊源的意识形态文化之间有何种关联,就需要仔细的重构工作。只有通过历史性的阐释,才能弄清楚思想的含义。思想史本身,非常近似于人类学以及相关社会科学中常用的各种人种志研究。这一点在格尔茨的著名文章《深描:迈向文化的解释理论》中有最精彩的阐述;格尔茨首先指出,文化是符号,因为“人是一种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面的动物”。
“深描”一词,格尔茨借自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赖尔讲过一个著名的例子。两个男孩眨右眼,其中一个是无意识的,另一个也眨眼,则是一个信号,给朋友传递信息。然后,第三个男孩也挤眉弄眼,做出模仿。此时,深描是指重新发现“意义结构的分层层次,通过这种分层,抽搐、眨眼、假装使眼色、戏仿和戏仿的练习得以区分,进而被感知,得到解释”。“深描”这一术语据说是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发明的,但我在他已刊和未刊的各类著述里都没找到这个词。不过,深描确实跟边沁在解释某些具体观念的意义时所讲的过程若合符节。边沁多次指出过这一点,尤其是在他试图对巴黎的国民公会给予指导时,曾经急切地强调了这一点:像正义或自由这样的概念,理解起来可能很困难,这就像一个眼部动作究竟是抽搐还是眨眼,很难做出判断。解决之道就是尽可能多地收集词汇使用的信息。比如说自由的含义,如果不提供各种例证,人们很容易犯糊涂,正如边沁所说,法国人越来越把实现自由和建立帝国混为一谈,并因此而感到迷惑。于是,边沁力求对自由的含义和内涵进行非常精确的阐述,在此过程中,他解释说自由往往意味着“被迫的自由”,亦即自由变成了有助于强者剥削弱者的工具。 只有仔细审查历史遗留下来的各种意见,我们才能弄清楚奥林匹克运动会究竟是单纯的比赛,还是一种有组织的政府形式,或者,只是人们普遍渴望强身健体的产物。又比如,黄金时代的荷兰静物画家,如安布罗修斯·博斯查尔特、彼得·克拉斯和扬·达维兹宗·德·海姆,他们笔下的骷髅、动物、花卉和昆虫,究竟是作为生死之道的象征、隐喻和符号,还是只不过就是郁金香、蜥蜴和蛾子,同样需要如此处理历史文献,才会有
答案。
尽管如此,思想史常常给人不好的印象。从很早开始,就有来自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的批评。刘易斯·纳米尔(Lewis Namier),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集体传记”方法——亦即在传记信息的基础上推导出一个群体的共同特征——的提倡者,早在1930年就在其著作《美国革命时代的英格兰》中声称,研究思想(ideas)是“痴人说梦”,因为在他看来,人类行为的真正驱动力只是利己主义。思想掩盖了社会行动的真正根源,因而是误导性的。持各种哲学立场的人已有论证,要想理解思想,唯有参照引起社会变动的真正原因,其中包括有意或无意的经济力量、无意识的自我或是无知无识的大众。所以,思想是关于这个世界的第二位的信息来源。真正的研究,应该是识别出上述力量所代表的特殊语境;唯有参照这些力量,思想才有可能得到解释。葛兰西曾经批评历史学家克罗齐是“可鄙的本丢·彼拉多主义”(despicable Pontius Pilatism),亦即,把知识分子视为必然高于群众,脱离大众的利益。克罗齐因为不表态、不愿对任何事情负责以及不直接参与公共事业而受到指责。 最近也出现了针对思想史家的类似抨击。思想史家被称为唯心主义者,跟现实毫无关联的嗜古癖,“从书本到书本”的政策鼓吹者,眼里只有精英和大人物的学究,不能理解社会,除了思想之外不相信偶然因素。本书要论证的是,如果针对目前实践中的思想史这一学科,所有这些批评都是站不住
脚的。
思想史家承认的观点是,思想就是关于社会现象的第一位的信息,与揭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的事实有直接关系,而且,除非参照思想,否则这个世界根本无法描述。因此,思想本身就是社会力量。思想有可能受到其他力量的塑造,但是,反过来,它们自身也总是会对人类世界产生影响。除此之外,思想史家们在其他问题上并没有一致意见。 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接受的影响来自20世纪下半叶之前或其间发展起来的不同的哲学流派。本书在后面将会对其中的某些流派有所描述。值得强调的一点是,思想史家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他们就职于各个文科院系,因此他们总是需要依据所在学科的主流研究方法来定义自己的身份。能否被历史学同行接受,常常是他们要考虑的特殊困境。人们常常指出,思想史家在“真正的”历史学家面前感到不自在,而这些历史学家认为,思想对于“真实的历史”的要素而言只是附属现象。唐纳德·温奇(Donald Winch)曾指出,思想史家在发表论文时往往像是在进行“客场比赛”。幸好,今天这种情况不再那么普遍了。本书的目标之一,是界定思想史家所共有的领域,让思想史家感受到自己是一个主场团队的一
部分。
达林·麦克马洪(Darrin McMahon)和塞缪尔·莫恩(Samuel Moyn)指出,当前思想史面临的问题之一是我们不再相互争论,在研究方法上尤其如此;这种现象被视为一个问题,因为在20世纪60、70年代,一些杰出的思想史作品的产生与方法论的辩论是分不开的。背后的预设是,如果我们停止相互辩论,就会变得自满,也就不会产生卓越的作品。马克·贝维尔(Mark Bevir),近年来历史哲学领域最重要的学者之一,曾经说过,他的著作《观念史的逻辑》(The Logic of the History of Ideas,1999)就是在方法论研究黄金时代的末期问世的。约翰·布罗提出了另一种观点,他写了一篇讨论方法论贫困的文章,认为如果痴迷于寻找审问过去的单一的方法,很可能会变得感觉迟钝。布罗称之为“方法论整体主义”,假如有人致力于此的话,就意味着对个人的认识论预设进行审问,那么,与之相伴随的往往是对过去的蔑视,对于过去思想貌似陌生但可能合理的本质丧失了欣赏能力。剑桥的一位思想史家伊斯特凡·洪特(István Hont)还有更加尖锐的批评,他声称“方法论是提供给愚笨之人的东西”。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当下一些最优秀的历史学者,如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回避了方法论争议。我并不反对对方法论的讨论,不过,本书不会刺激此类问题的辩论;本书旨在作为对思想史领域的入门介绍,仅此而已,我并没有什么原创的观点准备发表。但它确实旨在鼓励不同意见的出现。
以下章节旨在一般性地描述历史思想研究的历史,以及当今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式和相关的争议。在考虑了思想史的历史、方法和实践之后,接着探讨的议题是,思想史家所声称的历史研究与当代的现实问题无关。最后,本书将对思想史领域的近期走向做临时性的推测。我要提醒那些期望本书总揽思想史研究全局、博采众长的读者注意,我凭借的只是那些我最熟悉的领域。值得注意的是,就古代思想的研究而言,思想史的影响似乎很有限,部分原因在于,“古典学”这一领域领地分明,传统深厚。同样,对与莱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米歇尔·福柯和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相关的思想史方法,虽然本书也做了基本的介绍,但我主要做的工作,还是集中在与昆廷·斯金纳和约翰·波考克相关联的方法和实践上。原因在于,我认为后者是在英语国家的思想史学者中占主导地位的方法,并且在最近几十年对思想史家的工作所产生的影响是最显著的。当然,各种思想史取径彼此之间存在重叠,也有相似之处,在本书的最后部分将会对这一点有所讨论。关注点聚焦在所谓“剑桥”学者,可能是一个错误。2014年9月,我在乌梅奥大学(University of Ume?)参加了一场瑞典研究生的思想史会议,很快就发现,没有学生听说过波考克这个名字,没有学生研究过斯金纳的任何方法论论文,他们研究的灵感完全来自福柯。瑞典学生所做的研究主要关注20世纪的技术史;一个有趣的结果是,他们中有不少人会应聘到科学学院,去教那里的本科生。这跟其他地方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