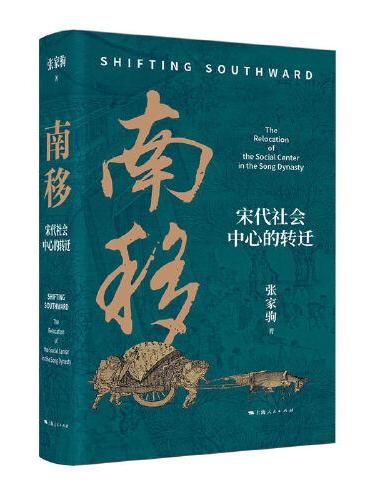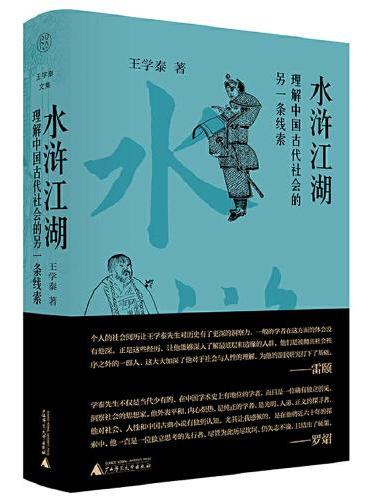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女人们的谈话(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提名、最佳改编剧本奖 原著!)
》
售價:NT$
286.0

《
忧郁的秩序:亚洲移民与边境管控的全球化(共域世界史)
》
售價:NT$
653.0

《
一周一堂经济学课: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
》
售價:NT$
500.0

《
慢性胃炎的中医研究 胃
》
售價:NT$
30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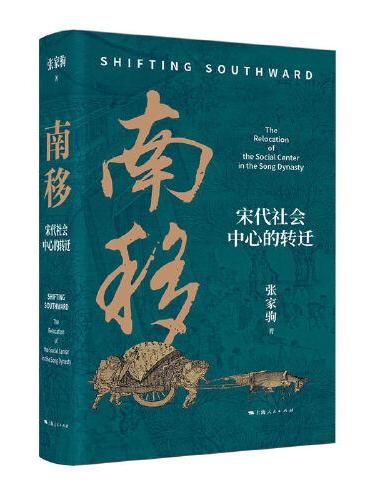
《
南移:宋代社会中心的转迁
》
售價:NT$
75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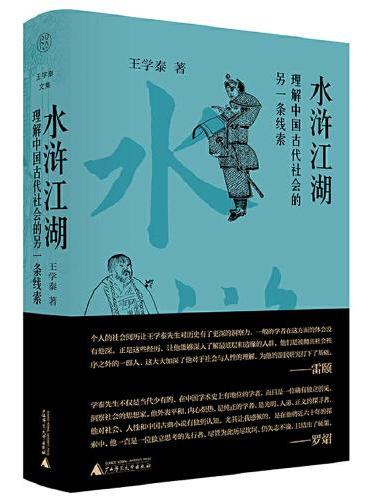
《
纯粹·水浒江湖: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另一条线索
》
售價:NT$
469.0

《
肌骨复健实践指南:运动损伤与慢性疼痛
》
售價:NT$
1367.0

《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MySQL版)
》
售價:NT$
301.0
|
| 編輯推薦: |
1.【一场轰击认知边疆的奥德赛,一部引人深思、重塑三观的作品】
这本书讲的不是如何预测未来,也不是概率论,而是一个更真实的世界观。作者以史学家般的精密与小说家的笔触,揭示了人类历史上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选择,如何引发巨大的连锁反应。借由一对夫妇的京都之旅到原子弹的投放历史,对因果关系的思维方式提出了直接挑战,让读者在历史的迷雾中看到命运的复杂交织。
2.【人生是宇宙开的“盲盒”,偶然才是主线剧情】
恐龙因一颗“偏航”的小行星灭绝,踢飞的足球救了海上落水的游客。每个人都是“人间触发键”,小动作能改写他人命运。书中用疯狂案例证明:命运最爱玩“蝴蝶效应剧本杀”。读完你会恍然大悟:那些搞砸的面试、错过的航班,可能是宇宙偷偷塞给你的隐藏彩蛋。
3.【理性看待人生际遇,尊重机缘,不再焦虑,才能收获幸福】
这本书深入剖析了偶然性在人类进化与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万维钢所言:“你控制不了整个系统,所以不用焦虑。凡事不必做到最优,次优也很好。看完这本书,你会减少纠结,活得坦然,心胸扩大。”
4.【燃烧般的智识密度,从交叉学科中汲取智慧、反思当下】
作者借鉴了历史学、进化生物学、社会心理学、
|
| 內容簡介: |
◎ 如果你的人生可以重来,一切还会和原来一样吗?
◎ 一对夫妇的假期和一片云层,如何决定数万人的生死和日本的命运?
◎ 人类的进化是不可避免的,还是只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产物?
◎ “复杂科学”“混沌理论”是如何作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的?
看似无关紧要的事件是如何引发连锁反应,以我们无法预见的方式塑造个人命运和历史叙事的?
这本书认为,事物发展受偶然因素的驱动,尤其涉及改变个人生活和重塑世界的重大事件时。小到个人的职业发展、人际交往、人生选择、命运际遇,大到人类进化、国运兴衰、政治博弈、经济危机,偶然性都在其中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作者通过复杂科学、混沌理论、量子力学、基因漂变、涌现现象、自组织临界现象、蝴蝶效应等自然科学的经典研究,对诸多历史大事件进行深度挖掘,细致地分析偶然性对人类历史、社会发展、个体命运的重大而不为人知的影响,强调在当时看来微小、偶然的个人行动,却最终酿成一场大风暴,进而影响全人类的命运。
人之于宇宙,渺小如沙粒,但有时一粒沙也足以让整个系统崩塌。因此,尽管我们无法掌控全局,但每一个行动、每一句话,足以逆转星辰。
|
| 關於作者: |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全球政治学副教授、研究员,牛津大学客座研究员。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方向:民主化与政治暴力。《展望》杂志2024年全球25 位“顶尖思想家”之一。
曾为《纽约时报》《金融时报》《洛杉矶时报》《今日美国》 《外交事务》《外交政策》等报刊撰写专栏文章。目前在《华盛顿邮报》开设专栏。 心理学博士。潍坊学院教授、中国理论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科普作家。
主要研究方向:进化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发表论文80余篇,科普著作《从猿性到人性:生命史上最完美的剧本》
入选 2021 年国家文津图书奖推荐作品。热爱科普写作,喜欢活泼、幽默又略带吐槽的表达,追求“严谨与通俗,兼具科学性与趣味性”的写作风格。
|
| 目錄:
|
第1章?引言 001
第2章?改变任何事情,都会改变一切025
第3章 不是每件事的背后都有目的051
第4章 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会歪曲现实083
第5章?人类的蝗群103
第6章?赫拉克利特定律133
第7章?讲故事的动物163
第8章?地球彩票181
第9章?人人都是蝴蝶201
第10章?时钟和日历229
第11章?皇帝的新方程式247
第12章?它是否有另一种可能277
第13章?为什么我们做的每件事都重要311
致谢?335
注释?339
|
| 內容試閱:
|
第1章 引言
如果你的人生可以倒带,回到最开始,然后重新按下播放键,一切还会像原来一样吗?
1926年10月30日,史汀生夫妇来到了古老的日本京都,他们走下蒸汽火车,住进了宫古岛酒店56号房间。安顿好后,他们漫步于昔日帝都,感受着这座城市秋日的缤纷色彩,枫树已变成了深红色,银杏树绽放出金黄色的光芒,峥嵘繁茂的树干高高耸立在郁郁葱葱的青苔之上。史汀生夫妇参观了京都的传统日式庭院,这些庭院掩映于城市泥岩山丘中。他们为一座座历史悠久的寺庙而惊叹,似乎寺庙中每一根木头都凝刻着昔日幕府时代的荣光。六天后,史汀生夫妇收拾行李,结账离开。
但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宫古岛酒店账簿上史汀生的名字将被写入历史,成为一系列连锁事件的启始符。在这些事件中,一个人如同上帝一样,在一念之间拯救了十万人的生命,但不幸的是,他也为其他地方的十几万无辜者带去了死亡。也许,这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私人观光旅行。
19年后,在远离京都上万公里的新墨西哥州,一群声名显赫的物理学家和军队将领聚集在一个代号为“Y站\的绝密地点。那是1945年5月10日,纳粹投降后第三天。此刻,太平洋上还正在上演一场似乎看不到尽头的血腥消耗战。然而,在新墨西哥州的这个偏远哨站,科学家和军人们看到了终结战争的希望:一种新型武器即将诞生,他们称之为“小玩意”,这个小玩意具有难以想象的破坏力。
虽然目前还没有任何一场成功试验能展示出这种新型武器的全部潜力,但Y站每个人都感觉到他们离成功越来越近了。为了早日做好准备,项目组成立了一个十三人的“目标委员会”,这些精英人士将决定如何让全世界见识到“小玩意”的威力。应该用它摧毁哪个城市?他们一致认为东京并不合适,因为猛烈的大轰炸其实早已摧毁了这座日本新首都。经过权衡,他们商定了一个目标,第一枚炸弹将投向京都。
京都是日本战时新工厂的聚集地,其中一家工厂每月可生产400台飞机发动机。此外,从战略上看,将曾经的首都夷为平地,这想必能给日军士气造成毁灭性打击。目标委员会还注意到一个无关紧要但可能具有特殊意义的问题:京都是一个知识中心,教育人口众多,著名的京都大学就坐落于此。委员会认为,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会认识到,这种武器代表着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日本不仅输掉了战争,在科学的战场上他们输的更彻底。于是目标委员会一致认为:必须摧毁京都。
委员会还商定了三个备选目标:广岛、横滨和小仓,清单随后被送交杜鲁门总统,他们现在需要做的只是等待原子弹就绪。
1945年7月16日,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广袤的空地上成功试爆,核能时代破晓而出。目标委员终于不再只是开展理论分析工作,军事战略家们查阅了京都的详细地图,并决定将爆炸地点定在京都的铁路车场。这里与宫古岛酒店只相距半英里,二十年前史汀生夫妇曾下榻于此。
1945年8月6日,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从天而降,但它没有落在京都,而是被“艾诺拉·盖”号轰炸机投到了广岛。多达 14 万人丧生,其中大部分是平民。三天后,也就是8月 9日,“博克斯卡”号轰炸机又在长崎投下了“胖子”,死亡人数增加了约 8 万人。
但是,为什么京都能够幸免于难?为什么长崎——一个甚至不被视为第一梯队轰炸目标的城市——会被摧毁?大约20万人在生死线上经历了摇摆徘徊,而起因,只是一对游客夫妇和一片云。
1945年时,亨利·史汀生先生已成为美国战争部长,他是负责监督战时行动的最高文职官员。作为非军队人员,史汀生认为他的工作是制定战略目标,而不是具体管理将军们如何实现这些目标。但是,当目标委员会选择摧毁京都时,这一切都改变了。
史汀生立即行动起来。在一次与曼哈顿项目负责人的会议上,史汀生强硬地摆明了自己的立场:“我不希望京都被轰炸”。在与美国武装部队司令的讨论中,史汀生重申“没有我的允许,有一个城市他们绝不能轰炸,那就是京都”。然而,尽管他一再坚持,京都还是不断出现在轰炸目标名单上。将军们执意认为,京都符合所有条件,它应该被炸平。他们想知道,为什么史汀生要如此固执地一心保护日本战争机器的神经中枢?
将军们不知道宫古岛饭店,不知道雄伟的日本枫树,也不知道金色的银杏树。
史汀生坚定不移地在高层游走。1945年7月下旬,他两次会见杜鲁门总统,每次都表示坚决反对摧毁京都。杜鲁门终于松口了,京都被排除在考虑范围外。最终目标名单包括四个城市:广岛、小仓、新泻,以及后来加上的长崎。史汀生拯救了这座被将军们戏称为史汀生“宠儿城”的古老城市,第一颗原子弹改为投放在广岛。
第二枚炸弹原本计划投向小仓市。但当B-29轰炸机接近小仓市时,云层遮挡导致飞行员难以看清下方。陆军气象学家小组曾预测小仓当天天空晴朗,云层的出现纯属意外。飞行员驾驶着轰炸机在空中盘旋,希望云层能散开,但一直没有达到理想的能见度。最后,机组人员决定不冒空投失败的风险,而是转向攻击次要目标。当他们接近长崎时,云层也遮住了这座城市。在燃料快耗尽时,他们尝试了最后一次飞行,云层在最后一刻散开了。1945年8月9日上午11时02分,原子弹“胖子”落下。长崎的平民是何其不幸:这个城市在最后一刻才被列入目标名单,它被夷为平地的原因是另一个城市上空一闪而过的云层。如果轰炸机早几分钟或晚几分钟起飞,小仓无数居民可能成为原子弹下的亡魂。时至今日,每当有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逃过一劫时,日本人都会说这是“小仓的运气”。
——————
云层使一座城市幸免于难,而一对夫妇几十年前的度假之旅拯救了另一座城市。京都和小仓的故事对我们因果关系思维提出了直接挑战,我们倾向于以一种简化、便捷、有序的方式看待事件的前因后果;我们乐于自己能够理解、预测和控制这个世界;我们希望可以用理性来解释混乱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成千上万人的生死不应该取决于几十年前一对夫妇愉快的旅行回忆,也不应该取决于天空中恰逢其时飘过的云朵。
儿童们总是不停地问着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从很小的时候起,我们就知道了简单因果模式——由X到Y。这很有用,它让我们可以看到现实的简装版——一个原因引起一个结果。通过因果思维,我们可以从事件中提炼出自己能理解的清晰关系,进而驾驭复杂世界。触摸热炉子会导致疼痛,吸烟引发癌症,云带来雨水,等等。
但在几十年前的日本,云层带来的直接后果不是雨水,是一个城市遭遇灭顶之灾,而另一个城市幸免于难。更奇特的是,长崎的无妄之祸源自一系列随机因素的组合,这些因素的数量几乎是无限的,而且它们必须以“正确”的方式环环相扣,才能导致长崎和广岛上空出现蘑菇云,比如:裕仁天皇的崛起、爱因斯坦在19世纪末出生、数百万年前地质变迁的力量锻造了铀、无数士兵牺牲于太平洋战场、才华横溢的科学家想到了原子弹的主意等等,直到最后,一次关键的假期和一片关键的云转动了命运的齿轮,如果之前无数因素稍有改变,一切都会不同。
如果你能重新翻看自己的人生记录本,你会发现,自己也曾经历过小仓式的幸运(尽管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当我们考虑“如果”时刻时,很明显,一些任意、微小的变化和看似随机的意外事件会改变我们的职业道路、重新安排我们的人际关系甚至颠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为了解释我们何以成为如今的自己,我们会承认,在许多“枢纽点”我们根本无法控制人生的行驶方向。然而,我们还忽略了那些看不见的枢纽点,忽略了那些我们永远不会意识到其重要性的瞬间,忽略了那些我们同生死“擦肩而过”但却不自知的时刻。因为我们从未见过、也永远不会真得看到自己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既然我们连事件的前因后果都看不清,又怎能明白哪些因素事关紧要呢。
如果数十万人的生死取决于一对夫妇几十年前的度假之旅,那么哪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选择或事故可能最终彻底改变你的人生轨迹?开会迟到或错过高速公路出口除了影响你自己生活外,会牵涉历史进程吗?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你能否意识到?或者,你完全不会觉察到,自己在茫然无知间造就了截然不同的世界?
我们对“当下”和“过去”的看法存在着一种奇异的脱节。当我们想象能够回到过去时,发出的警告都是一样的:确保不要触碰任何东西,对过去的微小改变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世界,你甚至可能不小心把自己从未来抹除!但谈到现在时,我们的想法会彻底改头换面。没人会小心翼翼、蹑手蹑脚,以防止错误地压死一只虫子;很少有人会由于错过公交车就认为未来无可挽回,并因此惶恐不安。相反,我们会想象小事并不重要,因为一切影响最终都会被时间冲淡。但是,如果过去的每一个细节都创造了我们的现在,那么我们现在的每一刻也在创造我们的未来。
1941年,在原子弹爆炸的四年前,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写了一篇题为《小径分岔的花园》(The Garden of Forking Paths)的短篇小说。该故事的核心隐喻是,人类在一个道路不断变化的花园中徘徊。我们可以俯瞰未来,看到无限可能的世界,但在当下时刻,我们必须决定下一步该往哪里走。每迈出新的一步,我们面前的道路都要发生变化,它会无休止地分岔。每一步都会开辟新的未来可能性,同时也关闭其他未来可能性。所以,每一步都很重要。
但这个故事中最令人惊叹的启示不止于此:请注意,我们的道路并不完全由自己决定。相反,我们所在的花园由前人开拓而成。我们面前的道路其实是过去历史的分支,是由别人的脚步所铺就的。而更让人感到茫然失措的是,前方的道路景观不仅取决于你的选择,当你在移动时,一些你看不到的人也在通过他们的移动而不断重塑园中之路。在博尔赫斯为我们描绘的这幅画面中,我们选择的道路常常被无情地调转方向,我们的前行轨迹总是被他人细微举动所改变,而我们自己一无所察,那些隐秘的京都和小仓时刻决定了我们将去向何处。
然而,当我们试图解释这个世界时——解释我们是谁,我们如何来到这里,以及这个世界为何如此运转——我们却忽略了偶然。被压扁的虫子,错过的公共汽车,所有这些我们都认为毫无意义。我们故意忽略了一个常令人感到手足无措的事实:一些微小改变可能会让我们生活和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当我们探寻直接因果关系时,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诉诸于现实的精简版本。如果X导致了Y, 那么X一定是一首主旋律,而不是一个轻微、随意的小音符。所有事情都可以被预测,可以被绘制为图表,并通过适当干预来加以控制。我们受到权威人士和数据分析师的引诱,这些预言家常常做出错误判断,但很少认为未来无法确知。当让我们在复杂的不确定性和令人欣慰的确定性之间做出选择时,我们往往会选择后者,尽管后者更有可能是错的。或许,世界并没有那么简单,我们能理解一个由偶然所造就的世界吗?
——————
1905年6月15日,克拉拉·马格达伦·詹森在威斯康辛州詹姆斯敦的一个小农舍里杀死了她的四个孩子,玛丽·克莱尔、弗雷德里克、约翰和西奥多。她清理了他们的尸体,把他们塞到床上,然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的丈夫保罗下班回家,发现全家人都躺在小床的被窝里,停止了呼吸。这肯定是人类所能体验的最可怕、最痛苦经历之一。
哲学中有一个被称为命运之爱(amor fati)的概念。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生活是我们之前一切经历的“聚流”。往上数四代,你可能不知道自己那八位祖辈的名字,但当你照镜子时,你看到的是他们的眼睛、鼻子、嘴唇以及其他特征的世代合成物,你的面孔记载了那早已被遗忘的时光。当遇到陌生人时,我们可以确定一个事实:他们的直系祖先里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有孩子前就去世了。这是废话,但也是事实。如果你的父母没有在特定的时间相遇、结合,你就不会存在。即使他们错过彼此,也会遇到其他爱人,生出其他的孩子。往上追溯几千年,你的祖父母、曾祖父母和曾曾祖父母与你也有同样的关系。你的生命取决于中世纪无数人的求爱,取决于冰河时代你遥远祖先对抗剑齿虎时的艰难求存,如果再往上追溯,它还取决于600多万年前黑猩猩的交配偏好。把人类的血统追溯到数亿年前,我们所有人的命运都取决于一种蠕虫状生物,谢天谢地,它没有被压扁。如果那些配偶没有按照已有历史剧本相爱、生活和生存,如果食物链没有按照已有历史剧本严丝合缝地运行,现在读这本书的就可能是其他人了,而不是你。我们是命运链环的突围者,如果过去稍有不同,我们就不会在这里。
回到威斯康辛州的小农舍,那个保罗是我的曾祖父,保罗·F·克拉斯。我的中间名是保罗,这是他留下的姓氏。我和他的第一任妻子克拉拉没有血缘关系,因为就在一个多世纪前,克拉拉不幸地切断了自己的血脉分支。保罗后来再婚了,娶了我的曾祖母。
在我20岁时,有一天我的父亲郑重地叫我坐下来,然后递给我一张1905年的新闻剪报,标题是“可怕的疯狂女人”,这则新闻揭露了我们家族近代史中最令人惶恐不安的一章。他还给我看了克拉斯家族墓碑的照片,所有的儿童在一边,克拉拉在另一边,他们的死亡日期是同一天。这让我很震惊。但更让我震惊的是,我意识到,如果克拉拉没有自杀,没有谋杀她的孩子,我就不会存在。一场阴森可怖的血案让我的出生成为可能,而那四个无辜可怜的孩子死了,现在我活着,你在阅读我的作品。命运之爱意味着我们要接受甚至拥抱事实,意味着我们要还要认识到我们是过去种种美好与黑暗的衍生物,前人生活中的胜利与悲剧共同构成了如今我们身在此处的缘由,我们的存在要归功于他们的仁慈与残忍、善亮与邪恶、爱慕与仇恨。如果没有发生以往种种,我们也不会是我们。
“我们都会死,这让我们成为幸运儿”,理查德·道金斯曾经观察到,“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死,因为他们永远不会出生。那些本可能占有我们生命、但实际上永远淹没于‘可能’深渊中的人,比撒哈拉的沙粒还多。这些存在于可能性中的生命,道金斯称之为“未诞生的幽灵”。他们的数量是无限的,而我们是有限的。只要做出最微小调整,一个生命就会被另一个生命所代替,后者会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过着不同的生活。所以,我们每个人存在的基础都像是叠叠高游戏中的木塔,岌岌可危,摇摇欲坠。
为什么我们要假装并非如此?我们存在的根基确实很脆弱,但这一事实违背了我们最根深蒂固的直觉。我们坚信世界的运行规律应该是另一种模式,重要大事件的起因当然也是重要大事件,而不是微小的偶然事件。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我接受的专业训练是:要探寻导致Y的X。几年前,我去了非洲南部的赞比亚,目的是研究为什么一场政变失败了。是因为政治体系足够稳定吗?或者,是因为政变缺乏民众支持?我出发去寻找真正的原因。
赞比亚政变的阴谋很简单,但也很有效:叛军头目派兵绑架了军队指挥官,他们计划逼迫司令官通过无线电宣布政变。策划者的预期计划是,一旦军方高层下答了命令,营房里其他士兵就会加入政变,这样政府就会崩溃。
但采访了参与绑架的士兵后,我感到自己所学的所有政治理论都崩溃了。当叛军闯入军营时,司令官从床上跳起来,跑出后门,爬上围墙。追赶他的叛军士兵伸手抓他裤腿,想把他从围墙上拉下来。接下来的发展就像电影中的慢动作画面一样,士兵抓住了司令官的裤腿,但裤子的布料从他指尖慢慢“挣脱”,司令官翻过墙逃跑了。顷刻之间,政变土崩瓦解。如果这个士兵再快一毫秒,或者握力再强一点点,现有政权可能就会垮台。毫不夸张地说,民主出于“偶然”存续了下来。
萧伯纳在他1922年的戏剧《回到玛士撒拉》(Back to Methuselah)中写道,“有些人看到已有的情况,然而问:‘为什么这样?’我梦想着从未出现的情况,然后问,‘为什么没这样?’”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每个人的存在都以几乎无限多的过往事件为前提,它们稍微有所变动,就会造成完全不同的结果,我们如何理解这样一个世界?在一个人的生命取决于其他人的死亡(像我一样)或者民主靠裤腿布料存续下来的世界中,我们该如何认识自己?如何认识社会?当我们思考宇宙的无限可能性时,我们可以想象出不同的世界。但我们只能观察一个世界,所以我们不知道如果过去有微小改动,到底会发生什么。如果史汀生一家在1926年错过了去京都的火车,转为去大阪度假,结果会怎样?如果前往小仓的轰炸机晚起飞几分钟,赶上了云层散开,结果会怎样?如果我的曾祖父在那个悲惨的日子早点回家,结果会怎样?世界会不一样,但如何不一样?
我是一名(幻想破灭的)社会科学家。幻灭是因为我长久以来就有一种让自己心绪不宁的感觉:我们“假装”世界按某种方式运转,但实际上它并非这样。我对现实的复杂性研究得越多,就越怀疑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令人欣慰的谎言之中,从我们讲述的关于我们自己的故事,到我们用来解释历史和社会变迁的神话,莫不如是。我开始怀疑,人类是否在参与一场无休无止但徒劳无益的抗争——我们试图将秩序、确定性和理性强加给一个由无序、偶然和混乱所主宰的世界。但与此同时,我逐渐倾心于另一个迷人的想法:只要我们接受了自身和周围的一切都源自宇宙随意的摇摆,我们也可以在混乱中找到新的意义,并学会赞美混乱而不确定的现实。
这种异端观念违背了我从小一直到研究生院所接受的所有教育。正统的教育思想告诉我们,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你只需要找出原因:如果你想了解社会变革,就多读历史书和社会科学论文;如果你想了解人类诞生的故事以及现代人是从哪儿来的,就去研究一下生物学,看看达尔文;如果你想探索生命中不可知的奥秘,那就多读哲学巨匠的著作;如果你想了解宇宙的复杂机制,那就学习物理学吧。
但是,如果这些永恒的人类之谜都是同一个大问题的一部分呢?
具体来说,人类必须应对的最大谜题是:为什么事情会发生?年复一年,我读得书越多,就越意识到,当这个巨大谜题摆在眼前时,我们无法从政治学理论、哲学巨著、经济学方程式、生物进化论、地质学研究、人类学论文、物理学证明过程、心理学实验或神经科学讲座中摘取出现成答案。相反,我开始认识到,人类每一个不同知识领域都提供了一个片段,如果把它们结合起来,我们能更接近这一扑朔难题的答案。本书想要挑战的目标正是尝试将这些碎片拼接在一起,形成一幅连贯的新画面,以重塑我们对自己是谁以及世界如何运作的认识。
当足够多的拼图碎片拼在一起时,一幅崭新的画面就会出现。当我们看到它逐渐轮廓清晰后,我们就有希望用一些接近更准确真相的想法来取代谎言——那些长久以来我们出于心理安慰而自己向自己编织的谎言,即使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从源头上颠覆我们根深蒂固的世界观。衷心提醒:你们中的一些人或许觉得这一翻转会让人迷失方向。但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让人迷失方向的时代了,想想阴谋政治、大流行病、经济震荡、气候变化以及由人工智能创造的新型“魔法”。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我们中许多人早就在一片不确定的海洋中迷茫无助了。但是,当我们在茫茫大海中不知所措时,紧抱着自我安慰的谎言只会让我们沉入海底,而真相可能是最好的救生筏。
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比我们想象得要更为复杂、也更为有趣。如果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简洁有序的叙事要让位于由偶然、混乱和随意性所交织而成的现实,在这个世界中,无论多么微小的时刻,都可能至关重要。
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将揭开一些我们自己写就的谬见,它们的破坏性更甚于简单的因果思维,却常常被人们奉为圭臬;另外,为了有助于我们理解自身,我们还会探讨三个关于人类的重要问题:第一,我们怎样成为了如今的人类,以及为什么这一点对我们很重要;第二,我们的生活到底怎样被自身无法控制的意外和随机事件所纠缠不清;第三,为什么我们会经常误解现代社会的动态关系。即使是最小的偶然也会造成影响,诚如已故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经说过的那样,“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最微小行动都会孕育出无限可能,因为一个行动,有时是一句话,足以逆转星辰。”
——————
有些读者可能已经开始反对这些大胆的说法和豪言壮语了。如果现实的“简化版”是谎言,偶然和随机引发的变化比我们想象的要多,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历史和宇宙中有那么多显而易见的秩序?的确,我们生活许多方面都是稳定的,世界充斥着规律和令人欣慰的常规模式。也许是我言过其实了,生活中大多数随机遭遇和意外举动都无关紧要,京都和原子弹的故事才是寥寥可数的怪诞事件。真的吗?
几十年来,进化生物学领域被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割裂为两大阵营。一个阵营主张生命进化会按照某个既定轨迹稳步前行;另一个阵营则不这么认为,他们相信生命之树会永远开枝散叶,并被偶然和无序所左右。生物学家用一对对立术语点出了这一争辩的关键:世界是发散(contingent)的还是趋同(convergent)的?核心问题在于,进化是否能以可预测的方式进行,而不考虑反常事件和随机波动,或者说这些偶然性是否会导致进化走上歧途?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些术语不仅有助于我们解释达尔文理论,有助于我们认识加拉帕戈斯群岛鸣雀的鸟喙,它们还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包括我们的社会——会出现意想不到的转折。
想象我们的生活就像一部电影,你可以倒退回昨天。在新的一天开始时,你改变一个小细节,比如你在冲出门之前是否先喝杯咖啡。如果无论你是否停下来喝杯咖啡,你的这一天基本都差不多,那么这就是一个“趋同”事件。该发生的事儿无论如何注定要发生,你生命的火车只是晚几分钟离开车站,但还是沿同样的轨道行驶。然而,如果停下来喝咖啡后,你未来生活的一切都以不同方式展开,那么它就是一个“发散”事件,因为很多事情都因为这一件小事而发生改变。
自然界似乎在发散性和趋同性之间摇摆不定。6600 万年前,一颗直径约9英里的小行星在地球坠落,它所产生的能量相当于100亿颗在广岛爆炸的原子弹。这颗小行星撞击到了尤卡坦半岛浅海下富含石膏的岩石,于是,巨量的有毒硫磺云渗入大气层,同时还有无数的粉碎岩石也被抛入到大气层,产生了强烈摩擦,最终形成“红外脉冲”。地球表面温度骤然升高了500华氏度,恐龙的遭遇就像烤箱中的烤鸡。
遭遇小行星撞击后,地表被严重炙烤。幸存者大多分为两类:一类可以钻入地下,另一类生活在海洋中。当我们观察如今尚存的动物时,从丛林生物到沙漠生物,包括我们自己,都是小行星撞击事件后幸存者的进化分支,都源自当年足智多谋的掘地动物。
但只要改变一个细节,我们就能想象出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如果小行星早一瞬或晚一瞬撞击地球,它就会坠入深海而不是浅海,这样一来释放的有毒气体就会大大减少,灭绝的物种也会大大减少。如果小行星的撞击时间推迟一分钟,它可能会完全错过地球。更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哈佛大学天体物理学家丽莎·兰德尔(Lisa Randall)提出,这颗小行星来自于太阳轨道穿过暗物质时产生的振荡。她认为,这些微小的引力扰动将小行星从遥远的奥尔特云抛向了地球。如果不是在难以想象的遥远深空中发生了一次微小振动,恐龙可能会幸存下来,而人类可能永远不会存在,这就是发散性。
现在,想想我们的眼睛。我们视网膜上进化出了极为复杂且具有专用功能的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它们使我们能够感知光线,我们的大脑可以对感知到的光线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将其转化为生动的图像。这些能力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但在地球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生物都是没有眼睛的。直到一个随机突变意外地产生了一团光敏细胞,具备这类细胞的幸运儿可以分辨出它们处于明亮还是黑暗的环境中,这有助于它们生存。随着时间推移,感光的生存优势通过自然选择得以强化,最终我们拥有了复杂的眼睛,它源于一段被称为“PAX6”基因的DNA突变。乍一看,PAX6突变似乎是一个发散事件:由于遥远祖先幸运地走上了一条分岔路,导致数百万年后,我们可以欣赏奈飞上精彩的剧集。
但是,当研究人员开始对与人类有着惊人差异的生物(如乌贼和章鱼)进行基因组测序时,他们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事情:章鱼和乌贼的眼睛与我们的眼睛极其相似。事实证明,章鱼和乌贼眼睛的突变基础与PAX6基因不同,但二者间又有很高相似性。被闪电击中已经是极小概率事件了,而现在发生的情况是,同一个基因被闪电击中了两次。到底是怎么回事?大约6亿年前,人类与章鱼和乌贼在进化轨迹上分道扬镳,但我们最终都拥有了差不多的眼睛。这并不是因为人类和章鱼都抽中了进化的彩票,我们真正可以得到的启示是,面对同样的问题,大自然有时会趋向于“提供”同类解决方案——因为只有这么多有效解决方案。这一洞悉至关重要,因为它表明,有时一些意外小事件造成的“颠簸”最终会被消除。既然章鱼的眼睛和人类的眼睛基本上一样,那么也许微小的变化并不重要。偶然性可能会改变某些事情发生的方式,但最后结果是相似的。这就好像早上按下闹钟按钮可能会耽误你上班行程,但是不会改变你的人生道路。无论如何,你都会到达同一个目的地,这就是趋同性。
趋同代表了进化生物学中“万事皆有因”学派,而发散则代表了“事情就是如此”(没什么“必然如此”的原因)学派。
这一框架对于我们认识自己大有裨益。如果我们的生活遵循发散规则,那么微小波动也会在我们的职业轨迹、结婚对象和子女等方方面面产生巨大影响。但如果遵循的是趋同规则,那么显然随机或意外事件更有可能仅仅引起一些奇异的小插曲,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忽略偶然。
几个世纪以来,一种能反映趋同信念的世界观——强调某些事物具有不可动摇性——主导着人们看待科学和社会的方式。牛顿定律不应该被打破;亚当·斯密曾写道,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导着我们的行为;生物学家们最初反对查尔斯·达尔文的理论,原因之一是自然选择假说太过于看重随机,而很少强调优雅的秩序。长期以来,不确定性一直被理性选择理论和时钟般精确的预测模型所排挤,微小变动被当作应该忽略的“噪音”,这样我们就可以专注于真正的“信号”。甚至我们的名言也灌注了简洁的趋同逻辑,例如“道德宇宙的弧线很长,但它终将弯向正义。”我们被告知,正义不会被随意扭曲。
几十年前,一位进化研究领域的“异端者”木村资生(Motoo Kimura)向传统观念发起了挑战,他坚持认为,微小、任意、随机的波动比我们想象得更重要。作为一个成长于20世纪20年代的孩子,木村好像并不是注定要从事学术研究。他讨厌上学,因为当时的教育体系要求学生必须遵从已被学术界公认的知识。尝试新思想的学生可能会受到惩处,知识传承于权威,它们意味着秩序和确定性。木村天性好奇,但他的学校容不下一副好奇的头脑。不过,在1937年时他终于受到了一位老师的鼓舞,木村私下对植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学术热情,他发誓终身致力于揭开植物的秘密。
然后,在1939年,木村全家遭遇了一次严重的食物中毒,他的兄弟甚至因此病逝了。木村不得不在家中卧床休养,由于无法研究植物,他开始阅读数学、遗传和染色体方面的书籍,他对植物的痴迷逐渐转变为对基因以及基因突变问题的痴迷。木村的事业轨迹——以及后来的进化生物学领域——都是被一顿变质的饭开启的。
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进化学者,木村仔细研究了生命的分子结构单元。随着观察的深入,他越发怀疑基因突变并没有多少规律和原因。木村察觉到,许多突变既无益也无害,这些变化往往是随机中性的变化,它们毫无意义。每当突变发生时,木村的前辈们都会搜寻相应的解释和原因,以便让突变“说得通”。对此,木村只是耸耸肩:有些事情的发生没有原因,事情就是这样。
木村的发现重塑了进化生物学领域,带来了影响几代学者的新观念。但其意义远不止于此,木村的思想,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的复杂性和偶然性。也许不是每件事的发生都有原因,也许,在一个相互交织纠缠的世界里,最小的变化可以产生最大的影响。
木村自身也是他思想的活生生例证,他的经历形象地表明,随意、相互关联的变化如何会导致偶然事件发生。1944年,木村离家去上大学,他希望避免被日军征召入伍。1945年8月时,他正是一名京都大学的在校生。如果史汀生夫妇错过了1926年去京都的火车,转为到大阪度假,木村和他的想法很可能会被湮灭在耀眼的原子光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