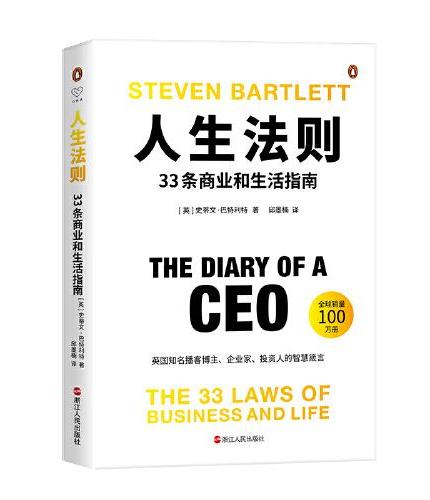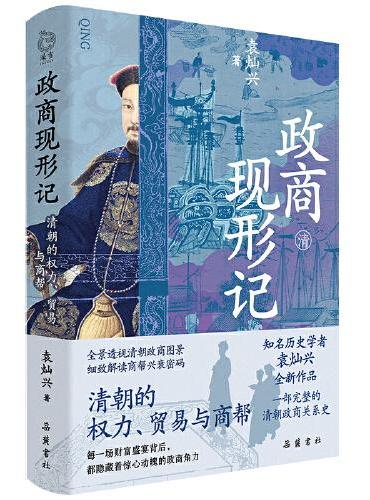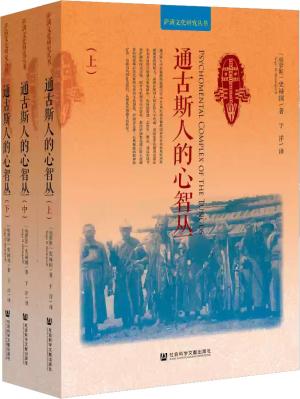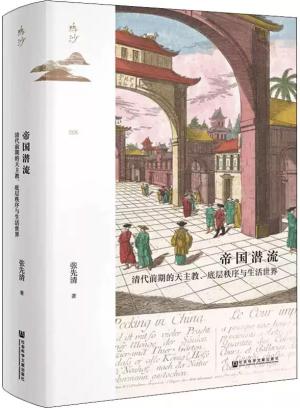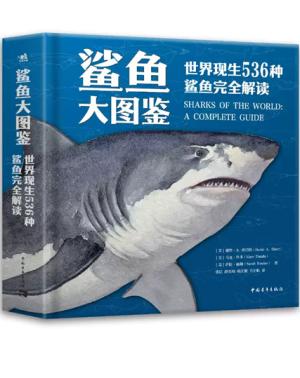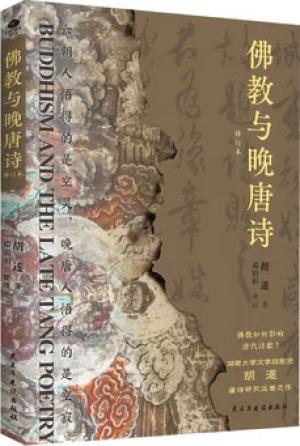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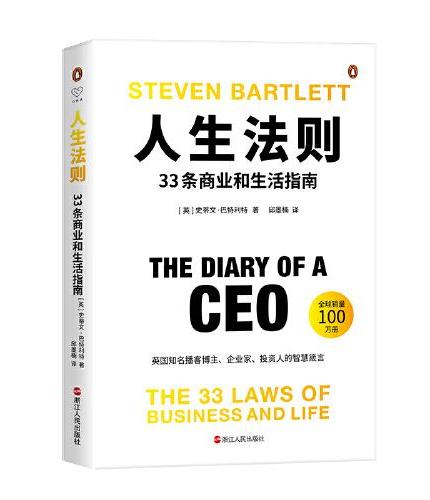
《
人生法则:33条商业和生活指南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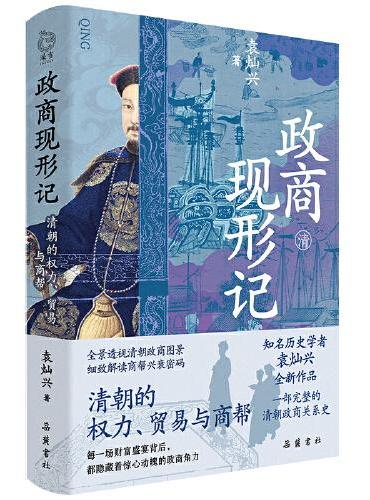
《
政商现形记: 清朝的权力、贸易与商帮
》
售價:NT$
398.0

《
早期干预丹佛模式辅导与培训家长用书
》
售價:NT$
53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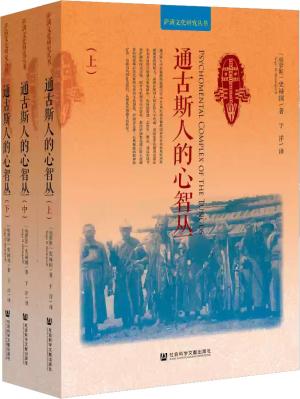
《
萨满文化研究丛书——通古斯人的心智丛(全三册)
》
售價:NT$
163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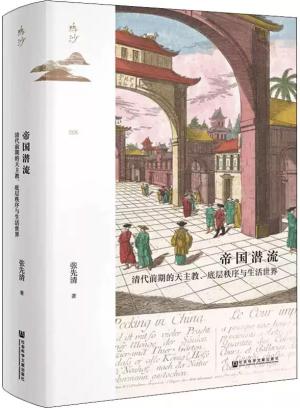
《
帝国潜流:清代前期的天主教、底层秩序与生活世界
》
售價:NT$
4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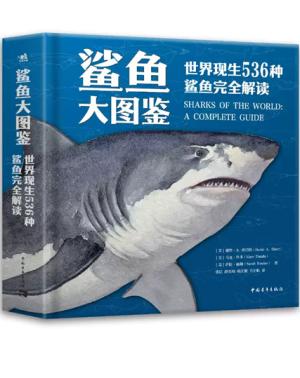
《
鲨鱼大图鉴:世界现生536种鲨鱼完全解读
》
售價:NT$
218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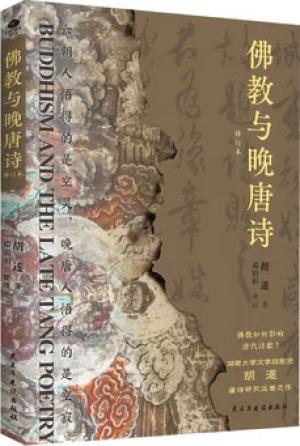
《
佛教与晚唐诗(修订本)晚唐诗人的群星闪耀时刻
》
售價:NT$
255.0

《
大模型智能推荐系统:技术解析与开发实践
》
售價:NT$
658.0
|
| 編輯推薦: |
一部深情讲述晚唐诗人的经典之作,取材诗人的传记、总集、别集等文献,如《唐才子传》《全唐诗》《李商隐诗歌集解》等,还原真实准确的晚唐诗人、晚唐诗歌,领略李商隐、杜牧、韦庄、杜荀鹤、许浑、陆龟蒙、司空图、李频、韩偓、张祜、方干、郑谷、刘得仁……等数十位晚唐诗人的生平抱负、悲欢离合、经典诗作、动人金句。
他们与我们的距离实际不远,千年以后依旧面临戾气与佛系、内卷与躺平、贫穷蹇困与无聊度日、精神内耗与适度发疯,看他们如何抉择,给我们怎样启示。
我们从晚唐诗中所看到的,也是那个时代的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们,面对无法改变的生存现实,在探索着,寻究着,如何能够安身安心,如何活得体面堂皇,如何调节心态,如何平衡情绪,如何自成自足自尊自信这样一段心路历程。
|
| 內容簡介: |
《佛教与晚唐诗》是胡遂教授关于晚唐诗研究的力作。
本书讲述了晚唐咏怀诗、怀古诗、隐逸诗、禅悦诗、酬赠诗五种类型与佛教的关系,进而提出佛教对晚唐诗人关于生存、历史、现实、精神、人格的影响,全面展现晚唐诗人“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的坎坷生平。同时从生存的感伤、历史的反思、现实的回避、精神的皈依、人格的标榜等多个角度出发,对佛教给予晚唐诗之影响与渗透这种文学现象作出了比较具体的探讨。
|
| 關於作者: |
胡遂(1956—2017)
文学博士,湖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佛学等方面的研究。
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中国佛学与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史》(合著)、《胡林翼集》(古籍整理)等,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中国文学》《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六十余篇。
邓田田 整理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期刊社副主任,教授、博士,胡遂教授之女。
|
| 目錄:
|
第一章 生存的感伤——佛教与晚唐咏怀诗 / 001
一、人生苦难之叹:生、老、病、死前四苦 / 002
二、人生苦难之叹: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蕴盛后四苦 / 043
第二章 历史的反思——佛教与晚唐怀古诗 / 087
一、四缘说诗:怀古情结的由来 / 088
二、四相迁流:诸行无常、万法皆空的体悟 / 099
三、空寂与空灵:晚唐怀古诗与前代所不同的山川风物之思 / 121
四、否定与肯定:晚唐人抚今追昔的意义 / 132
第三章 现实的回避——佛教与晚唐隐逸诗 / 139
一、晚唐诗人隐逸现象概述 / 140
二、佛教与隐逸的退避意义 / 152
三、佛教与隐逸的超越意义 / 164
四、晚唐诗人隐于佛门之三类型 / 177
第四章 精神的皈依——佛教与晚唐禅悦诗 / 201
一、止观双修说践行 / 202
二、去妄归真说认识 / 220
三、寂灭为乐说解脱 / 240
第五章 人格的标榜——佛教与晚唐酬赠诗 / 259
一、诗无僧字格还卑:晚唐诗人对佛门人物的歌颂与向往 / 260
二、空寂静净相标榜:晚唐诗人人格理想的转换 / 295
后 记 / 319
附录一 《关于佛教与晚唐山水诗的综合思考》 / 322
附录二 《大历文坛由儒入佛思潮》 / 328
《佛教与晚唐诗》整理修订说明 / 333
|
| 內容試閱:
|
前 言
在中国文学史上,晚唐是一个转折时期,也是一个备遭贬损的时期,后世诗评家论及晚唐诗时,多以“气弱格卑”“哀思之音”“衰陋”“衰飒”以及“叹老嗟卑”“力孱气萎”“寒俭有僧语”等语作为定论,认为晚唐诗格调低下无可取。这里仅以严羽《沧浪诗话》为例,即可见一斑。如其《诗辨》曰:“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又如其《诗评》曰:“大历以前,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晚唐分明别是一副言语。”“大历之诗,高者尚未失盛唐,下者渐入晚唐矣。晚唐之下者,亦堕野狐外道鬼窟中。”然而,正如叶燮在《原诗》中所指出的:“论者谓晚唐之诗,其音衰飒。然衰飒之论,晚唐不辞;若以衰飒为贬,晚唐不受也。夫天有四时,四时有春秋,春气滋生,秋气肃杀,滋生则敷荣,肃杀则衰飒,气之候不同,非气有优劣也。使气有优劣,春与秋亦有优劣乎?故衰飒以为气,秋气也。衰飒以为声,商声也。俱天地之出于自然者,不可以为贬也。又盛唐之诗,春花也。桃李之浓华,牡丹芍药之妍艳,其品华美贵重,略无寒瘦俭薄之态,固足美也。晚唐之诗,秋花也。江上之芙蓉,篱边之丛菊,极幽艳晚香之韵,可不为美乎?夫一字之褒贬,以定其评,固当详其本末,奈何不察而以辞加人,又从而为之贬乎?则执‘盛’与‘晚’之见者,即其论以剖明之,当亦无烦辞说之纷纷也已。”叶燮这段话的意思是:一、晚唐诗的确有衰飒之气,但其特征是虽“寒瘦俭薄”,但又“幽艳晚香”,也就是如同秋花一样,自有其特色;二、晚唐诗的“衰飒”乃是因其时代气候所造成的,而并非晚唐诗人本身气格低劣,故不应一味执着于“盛”“晚”之现象以贬责诗人作者,而是要详其本末,深究这种现象形成的原因。
对晚唐诗“衰飒”现象形成之原因的探究,笔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十多年来,也写过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同时进行的还有佛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但是,将佛教与晚唐诗二者联系起来做较为深入具体与系统的研究却是近年来才开始的。2003年,我的《佛教与晚唐诗研究》课题获准立项,从此便专力就此进行系统的思考与探讨。一年多来,感到还是有所心得的。首先,对晚唐文人与佛教结缘的原因基本上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其次是初步认识到晚唐安穷乐道的涉佛诗与宋代理学的建立之间是有一定关联的,再次是对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在安身立命方面的经验教训有了一定的感受。
关于晚唐文人与佛教结缘的原因,大致说来有这么几个因缘。一是时代走向所致。正如不少前辈与时贤所论及的,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东晋、南北朝、安史之乱后、晚唐、宋代、明末、晚清,几乎在每一个封建末世或者动乱衰微的时代,人们都有向佛教中寻找出路的迹象。二是此期社会动乱,官场倾轧,军阀混战,为儒已经基本无用,既无法治世,也无法治心,宋代“儒门淡泊,收拾不住,尽归释氏”的现象实际上是从中晚唐时开始的。三是佛教在晚唐武宗发起“会昌法难”之前势力已经极为高涨,经过“会昌法难”,虽遭打压,但不久又再度兴盛,至懿宗时已具相当规模,对当时社会造成的影响至为巨大。四是在晚唐科举选拔制度的严酷重压之下,广大不遇难达、身处下层的知识分子已经陷入难以解脱的生存困境,他们不得不另寻精神出路,另找安身立命之处将自己救拔出来。上述四因素中前三者人们已经论述得比较多,而对于第四个方面的原因至今还缺少足够的认识,因此本书在这一方面用力甚多,论析较详,并认为理学的产生与此也有一定关联。概言之,无论是佛学的为广大读书士子所接受并应用于生活,还是理学强调治心、修身以实现“内圣”人格境界作为人生成就的价值标准,都是读书士子们不甘心为包括科举取士在内的社会价值观念牢笼左右,而希求自我超越与自我成立以从生存困境中拔脱出来的一种尝试。
中唐以还,广大读书士子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被驱入社会边缘地位,处此穷途末路,便不得不考虑在精神的世界里树立独立的人格境界以实现自我救助,宋代理学即是沿着此一思路所产生,而中晚唐以来佛学日益为广大读书人所采用则成为此间的一个契机,一个中介。宋代读书士子最终选择了不遇不达却以崇高的人格境界成就了自我的陶渊明与杜甫作为前贤中的榜样,而否弃了叹老嗟卑、气格衰微的晚唐诗,在这一精神出路的探索过程中,晚唐诗虽然被作为历史教训来看待,但却自有它的认识意义。概言之,它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走出困境、开辟生路是付出了代价的。
文学史上,论及“魏晋风度”“晋宋风神”时总喜欢以“高蹈绝尘”“高慕远举”来盖定,并认为此种风神气度在后世已经绝迹,一去不返。其实此期文人的深层心理质素之所以高远而不卑近,与他们没有受到后世社会那样长期科举制度的精神摧压有关。自唐初开科取士以来,一代又一代的文人们就被牢笼于科场,很少有能逃脱的。到晚唐,不但科举取士已近定规,而且代代相递的承传,使此种制度日益成为一柄锋利的双刃剑,一方面可以开辟广大读书士子的出路,另一方面也在宰割他们的精神,磨损他们的灵气。而由于取录名额的限制,就在极少部分人开出生路的同时,绝大多数却在长期的生命耗损与精神摧压下,变得越来越气格萎弱,性情郁抑,就像是从小就被包了小脚似的,局促已成定势,始终难以放开了。六朝文人没有受到过这样从少年、青年时期就开始的科举压力,他们不是在压力与束缚下成长起来的,因此六朝人的高举,精神上是自由的,情性上是旷达甚至狂放的。自唐以来,文人很少有人能高蹈远举、放旷自然,再也无法形成魏晋、晋宋那样的一代风流,科举制度对文人们从幼年开始就造成的精神摧压当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后世文人很少能够像六朝士族文人那样具有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自唐以来,庶族地主阶级甚至贫寒出身的文人们由于利益的驱使,由于要解决衣食经济等的生活需要,其功利目的性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强烈。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不得不在包括科举考试在内的社会现实中处处就范,甚至摧眉折腰。这种在现实生活中的摧眉折腰,也必然导致精神上越来越难于高蹈振举。李白是最后一个具有魏晋风度的大诗人。正是由于他一方面受到时代社会环境的制约,也不得不屈己于人。另一方面,他又始终葆有魏晋那种高蹈放旷气质,时时感到这种摧眉折腰的痛苦不自由,因此他的怨愤比谁都大。正是这种精神上始终不息不减的对自由境界的向往与渴望,使他的诗发言出语比谁都高远,也由于现实生活中的难得自由与不得不抑情约性,他的痛苦与压抑感受也就比谁都来得敏感,来得强烈。而对于自中晚唐时代开始的无论从财力还是从才气上都远远不如李白的广大不得志的读书人来说,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只能感到深深的屈辱与痛楚,感到极为凄凉孤苦而又心酸无奈。
正是处在这种深陷人生困境不得脱拔的烦恼痛苦状况下,在中国历史上已经为六朝文人起过排忧解惑作用的佛教又再度走进了晚唐文人的心中,因着佛教特有的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实践论等理论,在晚唐时期,大量的咏怀诗、怀古诗、隐逸诗、禅悦诗与酬赠之作中,都充满了对现实人生的伤感,对历史功业的否定,对隐逸避世的向往,对佛寺禅门的倾服,以及对清、寂、静、净人格境界的推崇赞颂等内容。而融合佛教教义,此期此类诗歌的重点乃着落在苦、空、寂、静等几方面,其中“苦”是对生活现实的反映,“空”是对历史人生的认识,“寂”是寂灭来自世俗社会的种种尘劳妄念,“静”是自静其心,自净其性,从而使身心归于平静,安于宁静。它既包括了诗人们对世相人生的感受与认识,也包括了他们对隐逸避世与宗教皈依的生活实践与情感体验,一切都十分具体,也比较深入。可以说不但真实地表现了晚唐诗人们自我救拔的心路历程,而且无论从文学史还是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晚唐时代,由于动乱末世的原因,人们普遍遭受到比初、盛、中唐时要远为严重得多的生、老、病、死等来自现实生活的磨难。而作为读书士子的文人们,为了功名举业、仕宦前程,还要忍受着比一般人更为沉重的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等种种心灵的痛苦煎熬,惟其如此,佛教最基础的“苦谛”理论中“人生是苦”的教义便深深切入了不少晚唐诗人的心灵,一时间,叹老嗟卑、伤时怨命甚至咒天骂地的声音充斥弥漫于诗坛。其中最为伤心酸楚者莫过于在遭遇科举应考落第之后那种悲愤失望情感的发泄了,正如胡震亨在《唐音癸签》卷二十六中所指出的:“晚唐人集,多是未第前诗,其中非自叙无援之苦,即訾他人成事之由。名场中钻营恶态,忮懻俗情,一一无不写尽。”由此可见,这种种痛苦基本上都是集中于“求不得”这一人生最大痛苦的,而痛苦的根源又几乎都是来自于科举取士这一社会价值取向。也就是说,不取得科举功名,便不能进入仕宦从政的人生道路。不经由仕宦从政之路,便无法施展人生抱负,实现人生理想,而通过建功立业以显示的人生价值也无法体现。质言之,这一体现人生价值的道路便是经由科举及第——仕宦从政——施展抱负——建功立业而完成的。
然而,当怀抱人生失意情感的晚唐诗人们站在标志着前人所建树之功业的历史遗迹面前时,这种因无法体现人生价值的痛苦却又有所减轻。昔日的王图霸业已随历史浪潮逝去,长空渺渺,大河滔滔,一切都已经荡然无存。于是,一种古往今来,所有功名事业乃至荣华富贵都不可能永久长驻,都将归于幻灭的感受,融合着佛教“万法皆空”的本体论、认识论,使失意的诗人们终于由彻底看空、彻底否弃而得到了精神上的解脱。本来千军万马经过科举考试这一独木桥就是极其困难的事,何况即使取中进入仕途,即使也能建立重大功业,到头来也不过仍旧是一场空幻。既然如此,又何必为求不得而伤悲,为得到了而沾沾自喜、扬扬得意呢?纵观晚唐时大量的怀古诗,吊古伤今,抚今追昔,所指向的大都只是一个“空”字。可以说,这种对历史功业普遍持否定态度的思想认识,正是作者们在为自己从今天所遭遇的生存困境中解脱出来说法的。如果说咏怀诗中所充满的是一种自伤情调的话,那么不少怀古诗中所蕴含着的乃是晚唐大部分失意文人的一种自慰心理。当然这些作者中间也有不少是已经科场得中并进入了官场者,但是他们也普遍感到生不逢时,感到很难有通过功业立身扬名的可能,因此也就有通过否定功名事业来进行自我安慰的必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