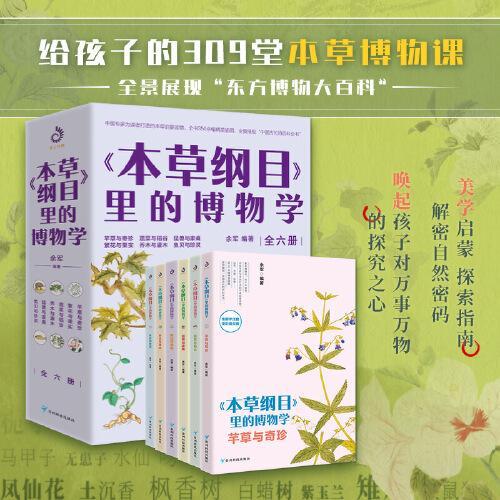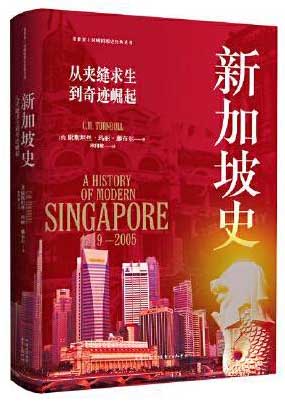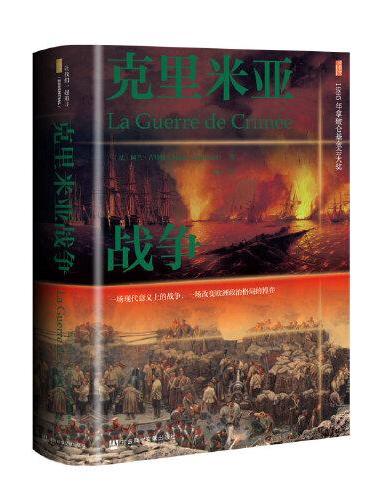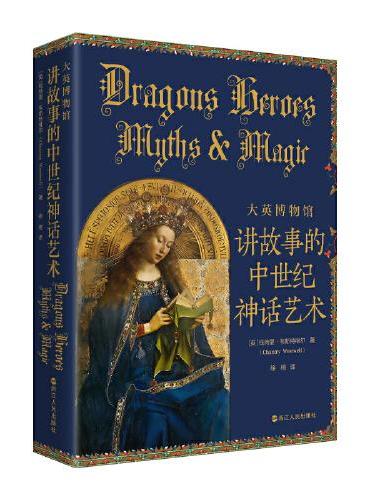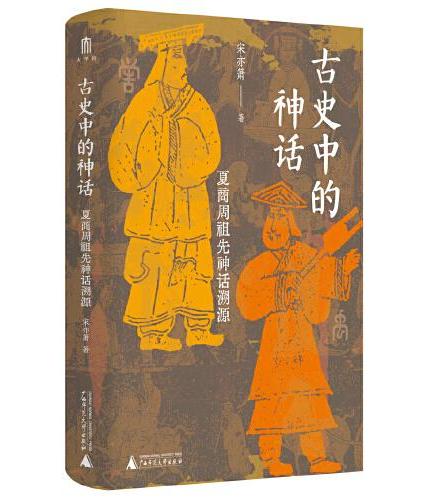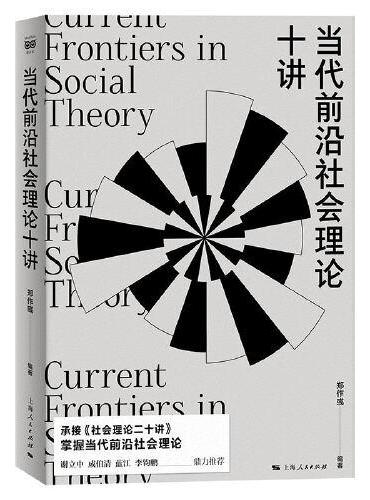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本草纲目》里的博物学(全6册)(给孩子的309堂本草博物课,全景展现“东方博物大百科,6大卷本草,41大体系分类,350余幅手绘图谱)
》 售價:NT$
1010.0
《
95%的不舒服,呼吸能解决
》 售價:NT$
459.0
《
新加坡史:从夹缝求生到奇迹崛起
》 售價:NT$
653.0
《
甲骨文丛书·克里米亚战争
》 售價:NT$
571.0
《
大英博物馆:讲故事的中世纪神话艺术
》 售價:NT$
1010.0
《
大学问·古史中的神话:夏商周祖先神话溯源(一部三代造神指南,重构夏商周祖先神话)
》 售價:NT$
449.0
《
俗说矩阵——线性代数详解(Python+MATLAB)
》 售價:NT$
505.0
《
当代前沿社会理论十讲
》 售價:NT$
500.0
編輯推薦:
1.直面当代人最关心的生存和生活状态的问题,与现实联系紧密,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比如:生存与财富、成功与失败、是与非、生活的复杂性和可能性,等等。
內容簡介:
在面临生活的不确定时,你是否会想:我要怎样度过我的一生?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怎么活才算有价值?我到底想要什么?很多人接受了外界,如父母、学校、朋友、电视、社交媒体关于人生的观念,并不自觉地按照这些观念生活,从而束缚了自己的人生。其实,你可以做一个积极的选择者,你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
關於作者:
作者简介
目錄
前 言
內容試閱
前 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