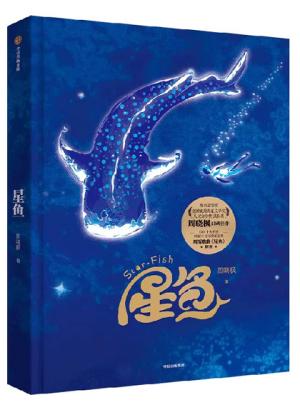新書推薦:

《
红楼梦脂评汇校本(平装版 全八册)
》
售價:HK$
1520

《
万物皆有时:中世纪的时间与生活
》
售價:HK$
449

《
英特纳雄耐尔——《国际歌》的诞生与中国革命
》
售價:HK$
857

《
去看看!我们的世界自然遗产(全5册)
》
售價:HK$
490

《
爱丁堡古罗马史(上辑1-4卷)
》
售價:HK$
1422

《
心悦读丛书·善与恶的距离:日常生活中的伦理学
》
售價:HK$
347

《
万有引力书系 · 崇祯七十二小时:大明王朝的最后时刻
》
售價:HK$
3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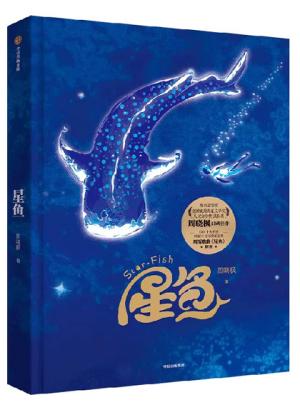
《
星鱼
》
售價:HK$
407
|
| 編輯推薦: |
沉郁风格,诗性表达
从二十四节气角度切入,展现中国西北部乡村农业文明真实形态
书中的父亲,是中国大地上无数任劳任怨操劳一生的父亲的缩影
|
| 內容簡介: |
|
本书是作者追述父亲往昔生活经历以及回忆与父亲相处的点点滴滴,潜心多年倾注深情书写完成的一部非虚构散文集,以二十四个章节组成,每章由节气话题引入。以自己的思考、当下的情景引出亲眼所见或听闻的父亲的往事经历。在作者描写的父亲的人生经历中,我们看到中国乡村发展几十年的变化历程,个人命运的起起伏伏,总是与时代的走向息息相关。父亲善良、朴实、勤劳、坚韧,用自己的双手劳作,努力撑起一个家庭,亦投射了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怀着东方赤子心的农民和父亲。
|
| 關於作者: |
|
耿翔,陕西永寿人。中国作协第六次、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出席第四届全国青年作家会议,参加诗刊社第九届“青春诗会”,2010年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塞尔维亚。已出版《长安书》《秦岭书》《马坊书》及四卷本《过山河记》等作品集十余部。曾获老舍散文奖、冰心散文奖、柳青文学奖、首届三毛散文奖及《诗刊》1991年度优秀诗文奖。
|
| 目錄:
|
一 / 001
我先是一愣,等缓慢地回过神来,便看见历书上醒目地写着:今日立春……
二 / 017
在雨水那天,我没有想到一个曾经在马坊劳作,或者咏而归的古人。 我想到的,是我的父亲……
三 / 033
我想喊他,一时嗓子发涩,没能喊出声音来。 这天正是惊蛰。我像在马坊的某一个陌生的地方,看见了父亲……
四 / 048
春分一到,在我们寄身的马坊,万物才算彻底活了过来……
五 / 064
清明这几天,人们不只是忙着祭祀祖先……
六 / 080
天明了,人们看到满眼金色的谷子河水一样涌流在脚下的大地上,便把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唤作谷雨……
七 / 090
看着落得一地的杏花、桃花、桐花和油菜花,我突然觉得,它们才是马坊的灵物……
八 / 104
每年到了小满,也是麦子最需要雨水的时候,父亲就想,这些水怎么不在地上流呢……
九 / 116
从进入芒种的那天起,马坊上的土地就都被麦子占领了……
十 / 131
卵卵用烟锅敲了那人的头,说:“过了今日,你的影子就慢慢长长了。 ”那人干咳了一声,记起今天是夏至……
十一 / 142
一年中天气很热的时候,很多吃着新麦的人,看着地里的玉米长得一片墨绿,厚实得像一块案板,就想起了五谷爷……
十二 / 158
天空和大地持续散发的闷热, 让夹在中间的人们感觉到,七月的每一个时刻都是流火的天气……
十三 / 178
立秋了,天上每落下一场雨,父亲都要跑到谷地里安静地坐着,看被风摇摆着的谷穗,怎么慢慢长成金黄的颜色……
十四 / 195
他不知道节气已经进入了处暑。 他摸了一下手上的镰刀,在心里说:谷子快要黄了,鹰都下到地上来了……
十五 / 209
那个时候遇到白露节气,都是漫天雨水。地上的万物,被雨水淋湿后,就有了伤心……
十六 / 223
到了秋分这一天,万物都在忙着收藏……
十七 / 239
这个时候的父亲,想着寒露节气到了,应该去前山和后山里走一走……
十八 / 253
马坊的万物,都在霜降之后,染上了一层很冷清的白色……
十九 / 272
冬天的雪落在父亲的眼里, 不像落在我们眼里那么令人惊喜。 他眼里看到的雪,是饥饿留给我们的一脸苍白……
二十 / 286
我在马坊的时候,每遇到一场雪落下来,就想起读过的鲁迅先生的《雪》……
二十一 / 299
看着大雪落下来的样子,看着父亲坐在那里的样子,我觉得马坊的天地都在这个时候被封闭了……
二十二 / 311
冬至,马坊人开始拖着自己瘦长的影子,在土地上行走……
二十三 / 322
我由此想到民国十八年那场在关中持续了五年的大饥荒,它像一座山挡在马坊人的面前时,也是一个冬天……
二十四 / 331
我的《父亲书》从立春开始,写到了大寒,就要全部落下笔了。我突然意识到,我是在纸上,一页接着一页,把父亲写向了死亡……
|
| 內容試閱:
|
掀开那天的日历, 像从吹过一个村子的风里突然听见谁这样回答我———地上的父亲。 我先是一愣,等缓慢地回过神来,便看见历书上醒目地写着:今日立春。
离开马坊后,我像从农历的温暖里一个人仓皇地逃了出来。立春这么重要的节气,我除了翻看历书,再也没有用身体及时觉察它的能力了。那片寂静的土地,用每一个生动的节气隐藏在我们所有人身体里的,能准确感知自然的密码,已经从我身上彻底丢失了。如果父亲还活着,他身体的一些部位一定会隐秘地告诉他,今天应该是什么节气。
母亲的身体,或许对节气更敏感一些。
在已经过去的很多年里,都有那么一天,等我从睡梦中睁开眼睛,会看到一缕失去往日寒气的光线正从窗棂上斜射进来, 落在一身新衣上。我的那身穿了一冬,里外都被尘垢落得生硬如铁的衣裳,已经被母亲拆洗了,晾在院子里。 而推开房门的父亲,一边放下担水的木桶,一边叮嘱我立春了。
我穿上新衣,走出院子,一身清爽地站在大街上。我看见很多人家的木门正被有声有色地推开,一些男人挑着大小不一的木桶,向村子东边的涝池走去。一些邻近的院子里也此起彼伏地传出女人的洗衣声。 很多年后,伏案读到“风来传消息,枝头晾春衣”的诗句,我突然站起来,向着长安北边的天空,有些心疼地眺望。 我的神魂突然颠倒着,像带我回到了马坊,回到了这个还被我记着的,开始立春的早晨。
我以为,一个村子的立春,是从父亲的身体开始的。
那一夜,他的还算结实的身体应该有了许多感应,让他在烧得很热的土炕上很难睡踏实。 他不会想象,但他的眼前,全是聚集在整个村子里和田野上的那些他能认识的事物。它们也像得到了一种十分有力的召唤,从寂寞了一冬的地方突然拥挤着出来。他像看见了,地里落得很厚的雪,河里冻得很厚的冰,都开始融化;他像听见了,树上飘摇的鸟巢里,村后冷清的狼窝里,都响起了叫声。有一刻,那些入冬前曾经在他粗糙的身上爬上爬下的虫子们,也像从他身上活了过来。它们集体蠕动着,让他用一冬的时间恢复了一些韧性的皮肤没有一处是寂静的。
他在他的身体里,确实睡不着了。
他翻了许多次身,但外面的天色还没有一丝亮光可以从窗户上透进来。他摸摸自己的骨头,今夜不但不乏软,反而有一种不让他躺下来的冲动之感。在父亲的劳动常识里,人只要累了,也就是骨头累了。
他由此及彼,观察着一村的牲口。
他说,骡马无论站在哪里,样子都很英武,你看不出它有被累着的时候。只要从车辕里走出来,进了饲养室,它们就在石槽边上一整夜地站着吃草,也一整夜地站着打盹儿。好骡子一个滚,它们只要仰躺在土地上,来回翻动几下身子,钻在皮毛和骨头里的乏气就会迅速被消除。 骡马的一生中,要是有一次卧下了,那就说明它活到了一个高角牲口的生命尽头。而那些行动迟缓的牛,用四只巨大的蹄子每天扑踏在大地上,只要从活路里走出来,便会就地卧下。
有一次,父亲指着一头卧在水渠边的牛,问我它被肩胛撑在地上的巨大身体像不像一座倒下去的黄土小山。 我以为它真像一座小山一样,倒下了,就再也站不起来。 正在为它的处境着急时,只见父亲轻扬了一下手中的牛皮鞭子,那头牛于出溜之间矗立在我们面前,摆出一副任劳任怨的样子。
我不知道,在马坊苦累了一生的父亲,到底像一匹英武的马,还是像一头迟缓的牛。
涌动在天地之间的立春的气息,最先被父亲的骨头感应到了。
他点亮油灯,他穿好衣裳,他担上水桶,他像有意赶在节气的前面,用他踏实的脚步,先把我们家通向涝池的那条一村人都要走的路有力地踩上一遍。当他站在结着厚厚一层冰的涝池边上,用扁担敲开冰层时,马坊这块不大不小的土地上那一年第一缕春天的气息,就从这里泛起了。我能想见,随着父亲那一阵有力的敲击声,马坊的万事万物都应该被惊动了。先是近处的树上有了鸟儿的鸣叫,接着有了远处的狗吠,那些在圈里吃了一夜草料的牲口也发出了不再沉闷的叫声。而埋在雪下的麦子、油菜,或许是在那一瞬间改变了生长的方向。 它们凝聚在根部的力气,不再带着它们的根须向地下深扎,而是拱着它们的叶芽,穿过雪层,开始向天空招展自己碧绿的色彩。
那时在马坊,我要是能理解这些麦子和油菜,就是父亲这样的人用一种传承下来的生存本能,年复一年在土地上出生入死种下的神圣的粮食,我一定会在立春这天,嚼着几颗红丁丁的麦粒,走在地气上升的村子里。
在一村人络绎不绝地去村东的涝池担水时,父亲已歇在房檐下,看着母亲用烧热的水洗着我们一家人的衣裳,直至把它晾在院子里的绳子上。
在父亲的眼里,或许立春,就是从这些洗得干净的土布上带着的皂荚清香开始的。
立春后的马坊,大地依然一片洁白。
那些落了一冬的雪,像一群守候在大地的舞台上来不及退场的演员,但它们臃肿的扮相,已不再令人感觉那么寒冷了。
父亲从村子里走出来。他穿着母亲早已缝补干净的衣裳,走得很有生气。他的肩上是那把跟了他好多年的铁锨,明晃晃的,把雪地上那么多的光全部反射在他的身子周围,让他像带着一身的光亮,在只有他一个人的大地上专心致志地走着。偶尔有一只邻家的狗跟在他的后面,打量着这个每天都能见到的人,猜想他今天怎么走得这么急。
急得像一阵吹过雪层的风。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