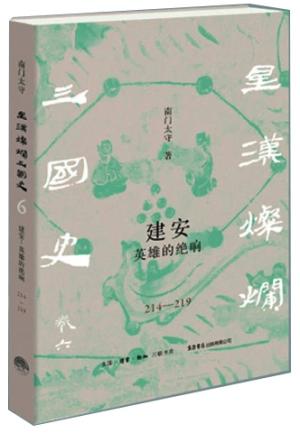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中国ESG卓越实践(2024) 探索创新ESG中国实践的路径和方法
》
售價:NT$
1010

《
大浪淘沙:从五代到十国(王宏杰五代史三部曲系列 一部生动而富有深度的乱世长卷 一幅反映人性的丰富画卷
》
售價:NT$
490

《
第八个侦探
》
售價:NT$
305

《
情结(精装)俄狄浦斯情结/该隐情结/自卑情结/救世主情结…… 在诉说与倾听中打开心灵的窗户,探索情结
》
售價:NT$
281

《
台湾百科全书历史篇
》
售價:NT$
8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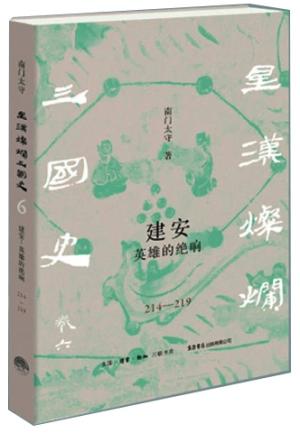
《
建安 英雄的绝响(214—219)
》
售價:NT$
301

《
经纬度·何以中国·周秦之变:地理·人文·技术
》
售價:NT$
500

《
永劫馆超连续杀人事件:魔女决定与X赴死
》
售價:NT$
281
|
| 編輯推薦: |
像一座冰山,只露出了海面上三分之一的部分,那底下,静水流深——
爱情的躁动,欲望的焦灼,人性的软弱……
充满迷离的气息和纠缠的味道。
有故事的人写的故事,迷离、忧伤、又独特;
月下以敏锐的嗅觉捕捉人物的情绪,再用睿智和幽默的语言把它们表述出来。她把感知变成一种诗意的行为。
|
| 內容簡介: |
本书讲述了一些边缘人的生存状态,他们的孤独、空虚和苦闷……他们执着于自我,以“非如此不可”的姿态落入这个“不干净、不纯粹、不彻底”的世界,在爱情、友情、人情里踟躇,有失落,有挣扎,有破碎,有涅槃重生。
比如在《人和猫一样寂寞》中,清秋一边回忆“恶魔”的爱情游戏,一边陷入“寂寞梧桐”的心理研究圈套——那个寂寞地研究他的小白鼠和人类心理的人,一边又去与循环往复地跟路人交换秘密的乌然交换她想知道的秘密;比如《这城市隐约有种沦落的美》,讲述了人被抛入这个世界从本真到非本真转化的过程中,他们所表现出的状态不一;比如在《玫瑰的灰烬》里,男人们宁愿牺牲“自我”来成全“生存”,他们自我鄙弃,却觉得自己赚到了。“四世同堂”,“婆媳关系”,到处都是眼睛,生活没有隐私,没有尊严……
|
| 關於作者: |
月下, 80后女子,现居北京。曾任网站设计师,现任图书策划。
在《羊城晚报》《青岛日报》《长沙晚报》《短篇小说》《文学港》等发表多篇小说、散文;出版小说《梦里也知身是客》《蛀空》《那些叫爱情的伤,我们总会痊愈的》等;传记《爱恨不如期:遗世独立张爱玲》《萧红别传》《倾我至诚 为你钟情:张国荣的影梦人生》等;随笔集《时间的灰烬》。
|
| 目錄:
|
喜欢植物的女子
有一天,我也开始种植植物,因为植物不会伤心。在我给一盆植物浇水的时候,似乎听到了敲门声,好久没人来拜访了,会是谁?我一边想着一边去开门。
阳台上的风景
十三岁,我升入初中,开始变得沉默寡言,总是一个人站在阳台上仰望蓝天。其实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我开始变得沉默寡言是因为我看到她从六楼坠下——
情花之毒
在海洋布景旁边,看起来像一条美人鱼,她在蓝色的光晕里静坐。这景象很美,却不真实。
在我的开始就是我的结束
我的生命只剩下了两件事:写不能发出的邮件,给一个从不写诗的诗人;读不必回复的邮件,来自一个在热闹里逃不出寂寞的人。
没有梦的冬天
我们之间的距离是漫长且未知的等待,而人类越来越经不起的就是等待,这个冬天像往常一样冷,只是没有梦。
人和猫一样寂寞
长长的睡袍拖在后面,像猫追着自己的尾巴;又像那个给自己写信的人,在一片健忘的天光中重复一个开始。
叶子
人类是野蛮的,一种过度粉饰的野蛮,一种不可言说的恐怖。仿佛在死人堆里摸爬滚打,她看着这些过早死掉的人这些行尸走肉冷笑:没有什么能够绑架我,没有人能够绑架我。她跌跌撞撞地从死尸上爬起来……
狂欢
她想:还以为日子总是暖和,所以一味地延宕。我们都是如此固执,固执地去寻求一个未知。我们总是喜欢把别人逼到极限,到了不可回头的时候才醒悟。
伤城
寂寞是听见某个熟悉的名字,不小心想起某些故事——
玫瑰的灰烬
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
这城市隐约有种沦落的美
在喧嚣与骚动的马路上,太阳如一团白色的黏液迷迷糊糊没有睡醒一般那么不耐烦地照向人间。他把她拉向一边,还是推向一边?他说:“就算我们要结婚,我也不能丢下她们不管。”
|
| 內容試閱:
|
喜欢植物的女子
她的房间里摆满了植物,黄葛兰、垂盆草、铁冬青、日本冷杉……绿茵茵的,不像走进种植园倒像是进了海底世界,因为种植园里还有阳光。我一直都感到奇怪,为什么,在阳光如此贫乏的空间里,她的植物仍旧茁壮地生长?
她说,她愿意做一株植物。
后来,她丢下那些植物,走了。
“因为梦见你离开,我从哭泣中醒来——”
舞会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又开始唱起这首歌,大概是为了压一压刚才的喧嚣,我总是在繁华落尽的时候想起你,你是否,也正在想起我?没有你来欣赏,所有的功成名就又要来有什么用呢?
琳达在我唱完的时候走过来递上一杯酒,然后我送她回家。
她在车上问我:“那个女孩是谁?”
我把音乐开得很大声,仍旧是那首英文老歌,我知道你喜欢,可是,你当时为什么不问我歌的名字呢?如果你问,你就会记住它,然后,每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可以想起我,或者,你就会决定回来——
琳达把音响关小,负气似的问我:“她到底是谁?”
“说了你又不认识。”我把车停在她的公寓前,示意她下车,她坐在车里不动。
“她离开了你?”琳达问。
“我不知道是谁离开了谁,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在一起。”
她的名字叫蕤,意为茂盛的植物,可是她看起来真的不算健康,瘦削的身躯,苍白的面颊,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认为她会“夭折”,她睡在植物里。
我说我们,是指我和罗。罗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是同学,毕业后又在一起工作,他是那种——很容易引起女孩子好奇心的男人。
那年我带蕤去看《泰坦尼克号》,她一直在黑暗里哭泣,其实我知道她并不是为剧中的角色哭,而是因为罗的漠然。我想她应该是爱罗的,不然不会那么在乎他的态度。
琳达靠得更近了,她似乎听得很专注,我想,我讲得也很专注吧。也许这本来就是一件应该让人专注的往事。
“他爱她吗,那个罗?”
“他是一个从来都不说爱的人,对于任何女子,都是漠然的态度。我曾经有一个师姐,那么疯狂地爱着他,因为他的漠然,她酗酒,夜不归宿,最后被学校开除了,她却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只为了仍旧能看到他——她卖画,或者,也卖身。”
“也就是说,他对她,那个睡在植物里的女子,也是漠然?”
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至今不能理解北漂人的心态。至今,不能明白罗的固执和冷淡。他说他生活在一个南方的小镇上,与爷爷相依为命,本来打算读计算机系,因为那时候IT业正流行,毕业后可以有一份丰厚的薪水,为了爷爷。可是最终,还是无法放弃自己的理想,选择了艺术系。毕业后我开了一家广告公司,自然要罗来帮忙。商业化的社会,他的才华根本用不上。他的表情永远是那么淡然,看不出任何不愉快的迹象,可是我能感觉到他的自尊被一点点磨损,我刻意付他额外的奖金,可是他从来不要。他一直租住在四合院那间小房子里,蕤的对面……
“我一直以为是这样的,我看不出他对蕤有任何不同。我不希望蕤成为第二个师姐,所以,我带她去看《泰坦尼克号》,他的态度是漠然的,她,因了他的漠然而伤心,或者是负气。”
“女孩子的心总不那么坚持的,她最终会爱上一个对她好的人。何况,像你这样完美的人。”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等了她八年——八年的时间足以改变很多事情,比如,罗不再画油画。”
琳达不解地摇着头。可能是因为我的思维跳跃得厉害,与其说是跟她讲述这些事情,不如说是给自己一个解释。面对一个又一个的疑问,我不得不自己解答。
“所以,我否认了一直以来的看法,他对蕤并非漠然,那样的性情,也只有隐忍的爱。”
“你们这些人真的很难懂,既然相爱为什么又不在一起呢?”琳达把头靠在座椅靠背上,企图轻松一些。
“蕤不是师姐,她选择离开,去了一个很遥远的城市,少有音讯。他愈加沉默,不和任何人来往,拼命地画画,他开始画水墨画,之前,他只喜欢画油画,水墨画是蕤喜欢的,就像喜欢植物——”
“他的画里总有一个熟悉的背影,瘦削,隐晦。”
我说到这里就停止了,走进这段往事就像走进蕤的植物里,绿茵茵的,凉丝丝的,纠结、缠绕。仿佛黏滞的海藻,不经意间就涂满你的额头。
琳达请我上去喝咖啡,她狡黠地眨着眼睛,说:“故事到这里应该还没有结束。”
我笑,当然,如果活着,故事就不会结束。
她一边磨咖啡一边问:“如果活着,你们的故事就会继续?”
“真的不想再思考这个问题,琳达,让我休息一下吧。”我躺进她的沙发里,双手抱着头。
她坐在我身边,手里拿着遥控器。香港周星驰的电影——我几乎睡着了,她却看得津津有味。我在她的笑声里醒来,厌倦地问着:“有那么好笑吗?”
“当然,你已经失去了幽默感。你的一生要用思念来填充,而我,要用拥有时的快乐。”琳达得意扬扬地仰着头,咯咯的笑声顺着她卷曲的头发荡漾开来。
“真是个孩子。”我说。
她调皮地把嚼着饼干的嘴凑上来。“可不可以到我的世界里来,忘了过去那些不开心?”
如果在几年前,这样的青春一定会让我悸动,而今,只觉得好笑。我从她的身上可以寻见自己的影子,只是,自从遇到蕤,那样的我就消失了。
“给我一杯酒。”我坐起来。
“你一定要喝酒吗?”她语气里带了嘲弄的意味。
我并不反驳,对于女人,该让的时候我会让的。
一杯红酒从我的胃肠里穿过,苦涩的味道蹿上心头。琳达的头发流到地毯上去,我俯在她的身上,满脑子里却是蕤的哭泣。
“他既然喜欢的是我为什么还要跟别的女人保持这样的关系?”她在Skype里哭诉,“那个女人竟然有了他的孩子——”
我终于愤怒了:“蕤,你不是小孩子了,他说得没错,你的问题太小儿科了。”
后来,我感到很抱歉,几次主动跟她打招呼,她都回得很客气,不再提起那个人,甚至客气得有些陌生,然而,让你觉得,她仍旧是蕤,挑不出任何纰漏,就这样云淡风轻地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
我开始恨那个男人。
你既然喜欢她为什么又要跟别的女人在一起?你跟别的女人在一起为什么又要让她发现呢?真是个失败的男人!
我开始烦躁,极度的烦躁。拿起一支烟。
琳达帮我点燃,轻声笑着:“你还是走不出来。”
我尽量让自己心平气和,倚在沙发上,吐着烟圈。我企图给她讲个笑话,却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来。烟灰掉下来,掉在她白皙的皮肤上。
她抹了一下便不管了,伸着手指在我的胳膊上写字,一个又一个,一行又一行。最终,我都没有感觉出她写了什么。
她娇纵地抓挠着我的身体,似乎很不满意。
“你们真的没有——在一起过吗?”琳达问。
“没有。”我回答得很不耐烦。
“那么,她和罗呢?”
我忽然想抽她,极力抑制了自己的冲动,大声说:“没有。”
“呵呵,”她笑起来,有些歇斯底里的意味,“真是奇怪的人。”
蕤临走的前几天,我们见过面,肥大的黑色外套裹着她瘦弱的身体,仿佛很冷似的,她正给她的植物浇水,极其认真。她从来不管那些植物叫各自的名字,一概统称为植物,我站在她身侧,有时帮她把植物的叶子挡到一边。
“你走了谁来给它们浇水呢?”
“生死有命,随它们去吧。”
“或许可以送人。”
“送谁呢?或者会是人家的负累。”
“你没有试过怎么知道呢?”
“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试过才知道。”
“你是个很不负责任的人。”
“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力量只够为自己负责,有时候连为自己负责都不够。”
“你走了,罗会伤心的。”
“他说他不会。”
“有时候人说出来的话未必是真的。”
“我只相信说出来的话,因为无论内容是什么那也需要勇气。”
过了几天,我去看罗,正赶上房东叫人把那些植物一盆盆搬上车,说是卖掉或者扔掉,伤感像决堤的水漫上来,我在水里游泳,企图对抗它的阻力。我要把这些植物都买下来,被罗阻止了。
他说,从蕤离去的那天起,那些植物就不再属于她了,至少已经不在她的心里了。
我有些气愤:“你为什么不把她留下来?”
“如果她执意要走,不妨让她走自己喜欢的路。到外面看看也好,一个喜欢写字的人,不能整天沉浸在只有单调的绿色的植物里。”
“如果她再也不回来呢?”
“我想,她会回来吧。”
罗说完便朝着自己的房间走去,我跟在他后面。那个时候,我们三个人一起在这个小房间里吃饭,罗做饭的手艺很好。他切西瓜,递给我们两个人,不动声色的。我弹吉他给他们听……
桌子上很凌乱:砚台、毛笔、水墨画。
其中一张就是那些植物。
他说那些植物已经不在她的心里了,他却把它们画下来,永恒地雕刻在时光的纤维上。
“你真的不去上班了吗?你不再帮我了?”我有些不甘心地问他。
“我想我也应该像蕤一样去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了。”罗低着头,看着他的画。
在这个喧嚣的都市里,我们总是容易忘记朋友。之后我很少再去看罗,他也几乎从不来找我。只是时常想起蕤,想起她在植物里穿梭的身影,想起她安静地坐在床上听我弹吉他,唱《一生有你》。有时候午夜梦回,心痛不止,仿佛被世界抛弃到一个没有出口的黑洞里,孤独、恐惧、没有希望。我从落地窗望出去,想,蕤已经不在这个城市。只是吸烟,不想扰人清梦,我不会打电话给蕤,也不会打给罗。
有时候会打给琳达,她在半夜驱车来陪我。可爱的小女子,看到她我会觉得温暖,觉得又回到了人间。
我们喝酒、跳舞、弹吉他。
她要求我给她唱《一生有你》,然而唱着唱着,我的心就开始游离。她就在我身上写字,胳膊上、腿上、背上,任何一个部位,用她纤细的手指。我终于可以感觉到其中两个字是“琳达”,她要我把她刻进心里,然后赶走蕤。
我的耳边总是响起她撒娇的话语:“到我的世界里来吧,到我的世界里来。”我抱着她,在地板上,又仿佛是在天花板上,我没有兴趣去区分,仿佛一大块海绵沉浸在水里,不由自主地吮吸着、膨胀着。
直到有一天,我从梦里惊醒,罗自杀了。
我猛地推开琳达,披上衣服匆匆地跑出去,东方已发白。潮涩的晨曦。夜里一定下过雨,我们没有听到。
我赶到罗的住处,旁边已经聚集了很多警察。罗已经死去三天了,在这个深秋的季节里,他的身边倒也没有蚊蝇之类的,只是散发着一股药香,房间里因为经常熬药也有了那种经年的腐朽香味。
还有一盆灰烬,我猜他临死的时候把画稿都烧掉了。果然,除了一些白纸,稍微沾染墨迹的东西都已付之一炬。
极度的悲痛,却没有眼泪。
直到警察确定他是自杀,送到殡仪馆。我打电话给蕤,她沉默了好长时间,最后说:“我想我回不去了。”
“你请便。”我啪地挂掉了电话。
罗没有什么朋友,她不来,就只有我。
旁边陪着琳达。她一直好奇地看着,也流了眼泪。“一个传说中的男子,有着水仙一样的气质,却溺死在水里。”她默默地念着。
这句话让我感动了很久,在我的记忆里,这应该是琳达说出的唯一一句具有诗意的话。我想,罗不仅是一个能够让女人产生好奇心的男子,还是一个能够让女人产生诗意的男子。
载着浩浩荡荡的悲伤,我们回家去。
琳达一直没有回她的寓所,她陪着我。我沉默,她也沉默;我悲伤,她也悲伤。
对于罗的死我是应负责任的,我是他最好的朋友,也是他唯一的朋友。在这个冰冷的城市里,我不该任由绝望一点一点将他吞噬。
我问自己,如果没有琳达,我会不会死?不禁被自己这个想法吓着了。也许,这样的状态真的应该结束了,我再次打电话给蕤。
她一遍一遍地确认:“罗真的是患了脑癌?”
我肯定地告诉她:“是的。”
问到最后,我终于犹豫了,说了实话。又是长时间的沉默,她似乎在撕扯什么东西,轻轻地啜泣。她说:“我曾经试着喜欢一个人。”
“为什么?”我问。
“我想从路途上停下来,我想进入一个现实安稳的世界,我想结束梦幻般的游离状态。这是罗不能给予我的。”
“所以,你放弃了他。”
“不,是他先放弃了我。”
“‘葳蕤’是茂盛的意思,它选择茁壮地成长,必须以牺牲其他的根茎为代价。”我冷冷地说。
她的哭声更响了,我们没有再说什么,挂断了电话。
其实我的本意并不是要跟她说这些的。可是,却不由自主。
我必须理解她的选择,一个脆弱的女子,如果不这样,她早晚有一天,也会溺死在种植水仙的瓷盘里。
我翻看她的日志,没有设置密码,我想,她终归是一个不在乎任何人的女子,随意地写,不管他人好奇的目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外在的那些人,那些关注着她的文字的人,在她的眼中只是透明。
可是渐渐地,我发现我错了,终究还有一个人,一个可以和她互动的男人。
进入她的电脑对我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八年前我就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我看到他们的聊天记录,热切的语言,蕤从来没有对罗和我说过这样的话。我想,他真是一个可以带她进入另一个世界的男人。
祝你幸福,蕤,虽然不是心里话。
我确定,另一个世界里的蕤一定是快乐的,但是不会像现在这么美,她会变得世俗,变得歇斯底里,变得像个女人。
我不知道我宁愿她美还是快乐,就在这样的矛盾中我发现了那个男人并非像她一样真诚,仿佛听到一度提高的琴声,一定会断弦的,一定会断的,我的心刚刚悬起的时候,就传来了蕤的哭诉。
我曾经去她待的那个城市里看她,我制造了遇见。蕤是一个生活在梦里的女子,她有着与众不同的嗜好,她喜欢遇见。
可是,她却又引用了另外一句话:“你以为制造了遇见就可以制造爱情?”
很不以为然。但是,我仍旧如她所愿。
天空没有太阳,云块也沉甸甸的。雨,欲下不下的样子。路边细竹萧萧,叶子一层层黄下去,几乎要干枯了。这样的情景仿佛罗笔下的水墨画,参差不齐,一派败落。“这小区真好,还种了竹子。”我说。
“是啊,最喜欢的植物。”
“唯一入得罗水墨画的植物。”
“罗——”
一提到这个名字我们同时喑哑了。仿佛两个刽子手守着同一个秘密,那个秘密本来已经压了箱底,却在看到对方的时候又悄悄冒出来,压也压不下去了。
“算是对我们的惩罚吗?”她说。
“怎么会呢,蕤?我们可是他最好的朋友。他一定希望我们能够好好地活下去,开心、舒服,不像他那样孤独又绝望。”
我说的是真的,不然不会那么凑巧——毛宁的《涛声依旧》从远处传来。我在心里狠狠地感激了一下罗。我们循着歌声走到那家饭馆,很旧的老房子,一灯如豆,这里的气氛就像那首老歌,茫茫的黑夜里,站在岸边,望着那只即将起航的小船。蕤就在我对面,也可能过一会儿就远离了。我们点了四个小菜,蒜泥空心菜、蒜泥小白菜、香菇油菜、水煮豆腐。这些菜经常出现在罗的饭桌上,三个人的口味竟是一样的清淡。涛声依旧,心是否依旧?偏就这首歌一直循环。“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我想我不开口,她也能听得到这句话。
之后,便是再见,我没想到这次会面这么匆匆,竟然没来得及听到她的答案。回来之后,我打电话给她:“蕤,我们结婚吧。”
她在电话里轻笑着:“我比较习惯南方的气候。”
算是婉拒。
我不甘心地问她:“是不是因为那个人?”
沉默,她不置可否。
我回过头,看见站在我身后的琳达。
我走近她,对她说:“我们结婚吧。”
她的脸上露出一丝不屑的嘲弄神色:“我是第几个?你求起婚来是这样按着顺序一个个问的吗?”
我无语,绕过她走出去了。
最终还是她来求我,琳达的和解方式就是像猫一样依偎着你,越靠越近。
我们决定结婚。或者只是想结束某种生存状态。
就在我忙着筹备婚礼和安慰在Skype里哭泣的蕤的时候,琳达失踪了。
当我再看到她的时候,她挽了另一个男人的胳膊。
笑眯眯的,就像我们第一次在一起时那样,眼神里带了嘲弄,她向我介绍着那个人,某某集团的副总——他的脸上露出所有加了一个“副”字的人都会有的表情,伺机而动,傲慢和卑微混合着的气味。在他走开的当儿,她说:“我只是想到你的世界里看看。”
我笑,毫不在意的样子。
咖啡馆的人来了又走,虽然我是这里的常客,可仍旧还是客。我们在咖啡馆分开。我还没有回到住处的时候就接到了琳达的短信。
第一条:我想我是爱上你了,但是只有他才能给我快乐。
第二条: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蕤喜欢的那个男人。
第三条:“一个传说中的男子,有着水仙一样的气质,却溺死在水里”,其实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偶然在一篇长满了植物的博文上看到的。
我想象着她跟那个强壮的发胖的男人在一起时的情景,不禁又笑了。她终于找到了一个不用喝酒的男人,一个只懂得享受拥有时的男人。他们各自有收获,那样比较好。人和人之间需要气味相投,每一个人的思念里都有一个特定的人,硬拼凑在一起只会成为滑稽的漫画。琳达是一个精明的女子,那个男人也是。
可是蕤不懂,我想,现在的她是不是正伤心呢?
有一天,我也开始种植植物,因为植物不会伤心。在我给一盆植物浇水的时候,似乎听到了敲门声,好久没人来拜访了,会是谁?我一边想着一边去开门。
黑色的外套,灰色的毛线围巾。
蕤轻笑着站在门口:“只是路过,借宿一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