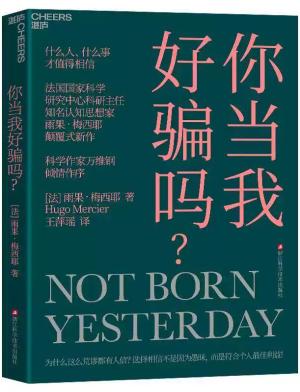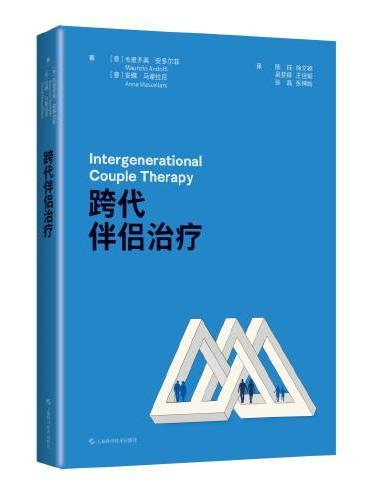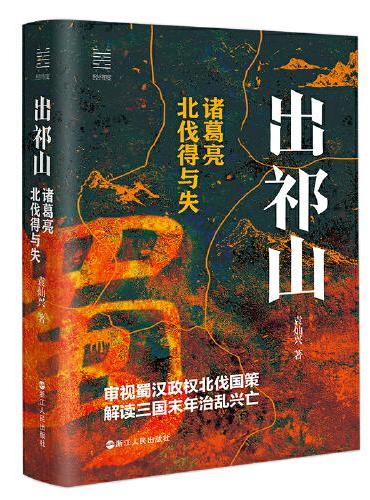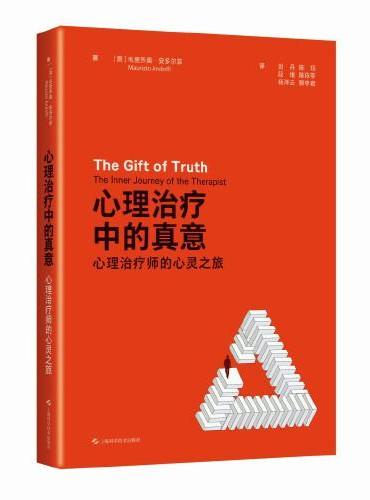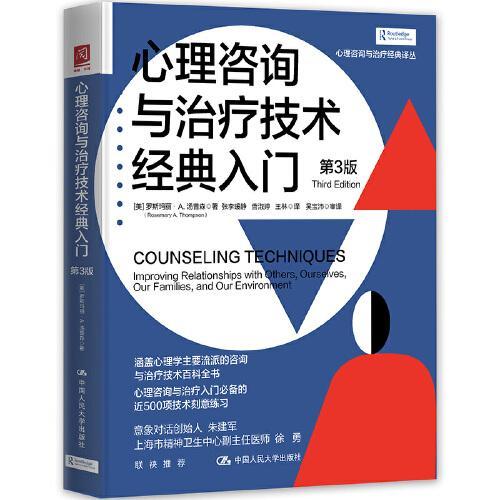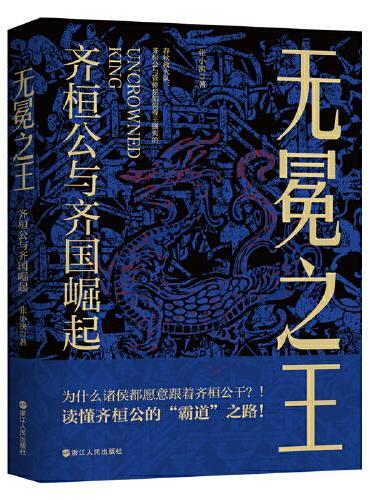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你当我好骗吗?
》 售價:NT$
550.0
《
跨代伴侣治疗
》 售價:NT$
440.0
《
精华类化妆品配方与制备手册
》 售價:NT$
990.0
《
经纬度丛书:出祁山:诸葛亮北伐得与失
》 售價:NT$
440.0
《
心理治疗中的真意:心理治疗师的心灵之旅
》 售價:NT$
440.0
《
心理咨询与治疗技术经典入门(第3版)
》 售價:NT$
650.0
《
无冕之王:齐桓公与齐国崛起
》 售價:NT$
290.0
《
中国涉外法治蓝皮书(2024)
》 售價:NT$
484.0
編輯推薦:
当代美国文学里程碑式作品
內容簡介:
《沉溺》多米尼加裔美国作家胡诺特·迪亚斯的成名作,讲述了多米尼加小男孩尤尼尔的父亲在他四岁时去美国做了非法劳工,撇下他和哥哥、母亲艰难度日,绝望等待。五年离散后,一度抛弃他们另组家庭的父亲忽然返乡将他们接去新泽西团聚,一家人开始了在美国的移民生活。
關於作者:
[美]胡诺特?迪亚斯,1968年生,多米尼加裔美国作家,《波士顿评论》编辑,麻省理工学院写作教授。1996年以处女作《沉溺》引起巨大反响,一举成名,这部自传色彩浓厚的短篇小说集已成当代文学经典。时隔十二年,他的长篇小说《奥斯卡?王尔德短暂而奇妙的一生》甫一出版便获2008年普利策奖。
目錄
早晨他拉上面罩,以拳抵掌磨了磨,走到蕃荔枝树下做引体向上,做了快五十个的时候,他端起咖啡去壳机,举到胸前,数了四十下。他的胳膊、胸脯和脖颈都鼓了起来,太阳穴周围的皮肤绷得紧紧的,几乎要裂开了。哦不!他是不败的。随着一声浑圆的“yes!”他放下了去壳机。他知道应该走了,可早晨的雾笼罩了一切,他听了一会公鸡叫。接着他听到了家里人的动静。赶快!他对自己说。他跑过姨父的咖啡地,瞥一眼就知道姨父在他的园地上种了多少红豆、绿豆和黑豆。他跑过水龙管和草地,然后说了声“飞行”,跳了起来,长长的影子切过一棵棵树冠。他能看见家里的篱笆,妈妈正在给小弟弟洗澡,揩脸擦脚。
內容試閱
早晨他拉上面罩,以拳抵掌磨了磨,走到蕃荔枝树下做引体向上,做了快五十个的时候,他端起咖啡去壳机,举到胸前,数了四十下。他的胳膊、胸脯和脖颈都鼓了起来,太阳穴周围的皮肤绷得紧紧的,几乎要裂开了。哦不!他是不败的。随着一声浑圆的“yes!”他放下了去壳机。他知道应该走了,可早晨的雾笼罩了一切,他听了一会公鸡叫。接着他听到了家里人的动静。赶快!他对自己说。他跑过姨父的咖啡地,瞥一眼就知道姨父在他的园地上种了多少红豆、绿豆和黑豆。他跑过水龙管和草地,然后说了声“飞行”,跳了起来,长长的影子切过一棵棵树冠。他能看见家里的篱笆,妈妈正在给小弟弟洗澡,揩脸擦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