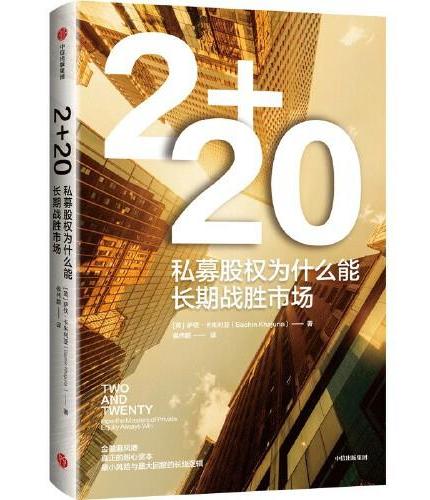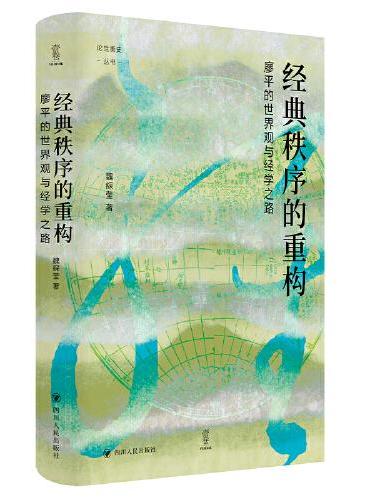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日和·缝纫机与金鱼
》
售價:NT$
194.0

《
金手铐(讲述海外留学群体面临的困境与挣扎、收获与失去)
》
售價:NT$
347.0

《
五谷杂粮养全家 正版书籍养生配方大全饮食健康营养食品药膳食谱养生食疗杂粮搭配减糖饮食书百病食疗家庭中医养生药膳入门书籍
》
售價:NT$
254.0

《
七种模式成就卓越班组:升级版
》
售價:NT$
296.0

《
主动出击:20世纪早期英国的科学普及(看英国科普黄金时代的科学家如何担当科普主力,打造科学共识!)
》
售價:NT$
403.0

《
太极拳套路完全图解 陈氏56式 杨氏24式和普及48式 精编口袋版
》
售價:NT$
1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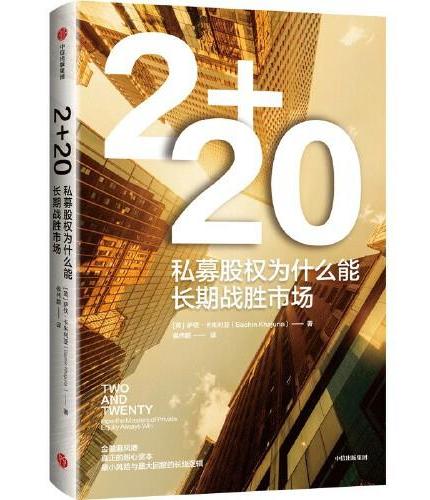
《
2+20:私募股权为什么能长期战胜市场
》
售價:NT$
4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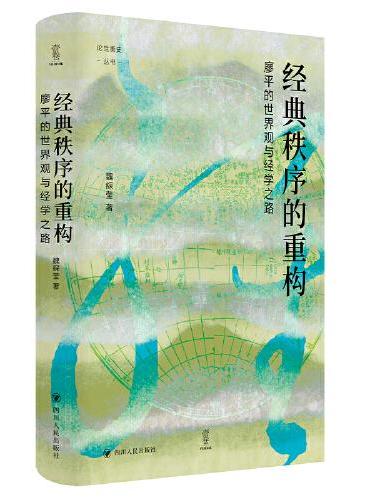
《
经典秩序的重构:廖平的世界观与经学之路(探究廖平经学思想,以新视角理解中国传统学术在西学冲击下的转型)
》
售價:NT$
454.0
|
| 編輯推薦: |
直木奖作家连城三纪彦力作
比《白夜行》更阴暗的人心 比《一朵桔梗花》更凄美的独白
惨死的少女 不伦的恋情 家族的崩坏
这是一部关于人性的绝望之书
遮蔽了我们内心中最后一缕阳光
|
| 內容簡介: |
一个炎热的午后,妹妹幸子四岁的女儿在姐姐聪子家被杀害,葬身于后院凌霄花之下。炫目的白色阳光开始照亮姐妹两个家庭不为人知的关系。每个人内心的阴暗让事情不可掌控,冲击人性底线的事实逐渐撕裂了整个家族……
“不杀了那个孩子,一切都将变得无法控制!”
|
| 關於作者: |
连城三纪彦 Renjo Mikihiko
本名加藤甚吾,1948年生于爱知县名古屋市。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毕业。在大学期间,以推理小说《变调二人羽织》获第3届“幻影城”新人奖,由此出道。1981年以《一朵桔梗花》获得第34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短篇部门奖,之后开始转向恋爱小说和恐怖小说创作。1984年以《宵待草夜情》获第5届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同年以描写两位女性复杂心理的恋爱小说《恋文》获第91届直木奖。1996年以《隐菊》获第9届柴田炼三郎奖。
|
| 內容試閱:
|
天快亮时,离世多年的亡妻突然在梦中对我嫣然一笑。
只是短短的一瞬间的相见。
可是,醒来以后亡妻的身影却一直在我脑中徘徊,始终挥之不去。平日的梦,醒来后很快就会忘记梦里的内容,可是今天随着天色的转亮,意识的清醒,数十年前的亡妻的面容却反而像显影液里的底片似的,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在我的眼前,清晰得是那样栩栩如生。
每到半夜之时,我都会醒过来,辗转反侧地想着一些事情,再慢慢重新入睡。然而,昨晚我像往常一样十点就寝,却罕见地一觉睡到黎明时分才猛然醒来。
睁开眼睛,窗帘上已经透过来一缕淡淡的晨光,无须再看时钟我便知道天已经快亮了。然后,我一直呆呆地睁着眼看着天花板,默默回想刚才的梦,可是,天花板上的木纹还未能辨别清楚的时候,我仿佛又重新回到了梦里似的迷迷糊糊的什么也记不清了……
自从过了古稀之年后,睡眠就如同一条沉积得满是淤泥的小河,变得越来越浅。
人说,上了岁数的人睡着时就像漂在河中,睡得很浅时像是被卡在混浊的浅滩上,睡得很沉时像是沉入了漆黑无边的河水深处,但并没有完全沉到水底,只是像一团淤泥那样一半陷进底部,一半在水中漂浮。如果完全沉入水底,那就意味着死去,再也无法从熟睡中浮出水面了……每天我从睡梦中醒来时,心里总会无意识地这样想。
有时候,虽然自己感觉已经醒来了,但意识却仍像陷进水底的淤泥似的恍恍惚惚,我便以为自己已经死去。
七十岁过后的头几年里,我总觉得自己离沉入水底不远了,感觉身体正一年不如一年,慢慢衰弱下去。可是自近一两年起,觉得身体内又像是多了一个自己,或是熟悉的朋友似的,似乎每天醒来并未意识到与昨天有任何改变……
“您起来了?”
儿媳聪子把门推开一道缝,探着头问道。
“嗯。”我回答。
“早饭……马上来吃吗?”
“哦。”我又回答了一声,然后闭上眼,总觉得自己也许就会这么死去了。
亡妻的面容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甚至比刚才梦里见到的更加真实。
我开始慢慢地把刚才梦中的情景又回想了一遍。
二十二岁时的妻子的面容总像隔着一扇朦朦胧胧的玻璃似的,隐隐约约地出现在眼前,我知道,那是火车车厢里的窗户。妻子正站在月台上,挥手向一位就要远去的男子送别……车窗另一边的男子,就是我自己。
那时自己是什么样的表情已经不得而知了,精神全都集中在微微哭丧着脸的妻子身上了。我的心里没有任何感情,只是木然地向外看着。
妻子像是流了眼泪,可是这层朦朦胧胧的玻璃仿佛过滤掉了她脸上的悲伤,只让我见到她的微笑。
一缕淡淡的笑容……也许还够不上微笑,正在从妻子黑黑的瞳孔中透出。以前,有位电影女演员拍摄肖像照片时总是摆出一副梦幻般的、注视着远方的微笑,这时妻子的表情就像是隔着几重模糊不清的玻璃,向我露出那种同样的微笑,注视着我。
二十二岁?
为什么那时妻子的岁数,竟能这样清楚地铭记在我的脑海深处?
我已经一点儿也记不起自己当年是多少岁了。既然记得比妻子大几岁,本该马上就能算出自己的年龄,可是不知为何,却总是记不清楚。但今年自己是七十五岁还清楚地记得……因此,如果自己真想算出当年自己多少岁应该不是难事,那是正处于人生重要关头的那年,现在首先记起的不是自己当时的年龄,而是那年妻子的岁数,还真是有些奇怪……
人生的重要关头?
梦里真能梦见自己人生中处于重要关头的那一刻?
那分明不是在做梦。我猛然想了起来。
天快亮时我虽然迷迷糊糊还在浅睡,但意识的一部分早已经苏醒了,我想起了几十年前妻子那时的面容。
那时的?
突然,周围响起一阵巨大的欢呼声。
家的附近有一所小学,每天清晨总能听到孩子们课前热闹的欢叫声,可是现在正值暑假,学校里应该是寂无人声,而且现在时间尚早,还没有到课前的时段……
原来这阵欢呼声是从我衰弱不堪的身体深处迸发出来的,周围的人群都在忘乎所以地高呼着“万岁——万岁!”……欢呼声震耳欲聋,几乎震碎了车窗上的玻璃,一直灌入我的耳中。只记得自己当时正坐在火车里,拼命想打开车窗探出头再看得更清楚些,可是车窗像是锈住了,完全打不开,坐在旁边的两位乘客也伸手前来帮忙,可是也没成功。于是自己慌忙用手抹了抹车窗上的雾气,伸出的手却在瞬间定格住了。
是的,顺序的确是这样的。不知道是谁伸手在车窗玻璃上抹了一把,于是,雾蒙蒙的车窗上留下了一片梧桐树叶形状的透明小框,我正是从那里看见了站在月台上的妻子的面容。妻子也凑近车窗,从那里透过窗户紧盯着我看……才露出微笑的。
不,当时我并未看清她脸上是否在笑,只是慌忙用新发的军装袖子使劲地擦拭起车窗玻璃来,于是看清了妻子身边人山人海的送别的人群。可是自己眼中能看见的却只有妻子的模样。
妻子并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身边还站着我年幼的女儿,妻子正紧紧拉着女儿的小手。
女儿刚满四岁,身上穿着像是过七五三节①
时才穿的色彩艳丽的和服童装,拉住母亲的手里还抓着一面小小的日本国旗……是左手。这些细节至今还能记得十分清楚。
自己俯身靠在车窗上,狠狠地擦拭着窗玻璃,刚能看清妻子的身影时,瞬间,发车的铃声响了。火车喘着粗气开始慢慢启动,山呼海啸般的“万岁”的欢呼声更加起劲地响了起来,人们手中挥动的日本国旗聚成一片潮水似的波涛,可是站在月台上身处国旗的海洋中的妻子却静静地呆立着,一动也不动,直到她的面容渐渐远去,直到马上就要消失了……直至这一刻,我的目光才离开妻子,落在旁边站着的女儿身上。女儿就像模仿母亲似的,脸上也是微微露出笑容,对着渐渐远去的我——也就是她的父亲——挥手送别。也许她并不知道父亲要去哪儿,也不知道手里的日本国旗意味着什么,只是高高举起旗子,轻轻摆动着。可是至今我分明还记得她当时挥动的是左手。
女儿并非出于自己的意思挥动着小旗,是母亲握住她的手在摇晃着,舞动着手里的旗子。
女儿本来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只是像被卷入呼喊“万岁”的旋涡中,身不由己地无心地微笑着……也许当初女儿并非学着大人的样子微笑着,反而倒是妻子在学着孩子的样子,脸上装出一副天真无邪的笑容。
那是个寒风刺骨的冬夜,按理说车站月台上应该飘舞着大雪,可是照片一样清楚的记忆中,却连一片雪花也没有。
窗外月台上的景象在蒸汽机车吐出的浓浓的水雾笼罩中渐渐模糊,一点一点地远去,因此留在记忆中的这段情景与其说是像照片一样留在记忆中,不如说像是一段让我经常回忆起来的纪录片或者电影。
而且,这段影像更像是无声电影时代的黑白影片,我能记起的场面中既没有声音,也没有颜色,女儿手上的日本国旗和身上的和服也像黑白电影似的看不出颜色来,耳中能听到的就是那串发车的铃声,眼里能看见的只是那个瞬间妻子眼中透出的一缕笑意……
其中……记忆最深的就是经历一个多月的艰辛旅程,我们被送上的那个位于南太平洋中的小岛,这段记忆又与离开车站时的一刻大不相同了。
那座岛上到处色彩都很浓郁,茫茫的大海和天空连成一色,都是那样湛蓝,就连白色的太阳光和暑气腾腾的大雨似乎也透着夺目的明媚颜色。
南太平洋上的小岛?
想到这里,仿佛自己又回到那座不知名的南太平洋上的小岛上。以前只在梦中才能回到那座岛上,可是最近明明醒着,却好像自己已经回到那座小岛上去了。刚才还在自家门前的院子里站着,可是回过神来一看,却突然发觉自己正身处于岛上的密林中,猛地大吃一惊……不,也许现在自己以为醒着,相反,却还在深深的睡眠中也说不定。躺在这间屋子床上的自己可能正是自己睡梦中见到的模样……真正的自己还是个年轻的士兵!趁着南太平洋上这座小岛上进行激烈战斗的间歇,疲惫不堪地躺在地下刚刚打了个盹儿,梦见了几十年后成为老人的自己的模样了也说不定。但是无论如何,现在我的脑子里正清楚地记得,自己已经是个经常容易忘事的七十五岁的耄耋老人,刚才聪子催我吃饭的叫声,以及昨天的事情都像是发生在遥远的过去似的很快就被遗忘了……
昨晚睡前有过什么事,为了何事发过愁……这些刚刚发生过的一切好像全都没有记住,相反,却对几十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般牢牢记着,仿佛昨天刚刚发生过。
就连按说早该遗忘的幼年时代的一桩桩小事,以及连小事都算不上的儿时经历过的点点滴滴也都记得清清楚楚……
比如,五六岁时自己上街去看祭典,回家的半道上被人踩断了木屐上的带子,稍大些时夏天晚上跟着朋友钻在寺庙里大殿的香案下过了一夜……祭典之夜母亲身上浴衣的颜色、夜店的推车上挂着的风车的模样、寺庙周围成片地盛开着的萩花的白色,以及漆黑的半夜飘来的萩花浓烈得呛鼻的芬芳……还有小道上偶然碰见过一两次的行人,全都像发生在眼前似的。
就连近在眼前,多年照料自己生活的聪子,我有时也会突然记不清她的模样,可是已经过了七十年,自己路上遇见的那位走街串巷叫卖膏药的老先生,以及寒冬的雪道上摔倒在地时,搀起自己的那位好心的老妇人的样子却清清楚楚地浮现在眼前……已经老了,也许活不了多少年头了吧?
但是自己心里已经没有什么割舍不下的事,对于死亡也已经毫不畏惧,甚至觉得,自己就这么双眼一闭,悄悄地死去倒是最幸福不过的一件事了。不,最好是连幸福也感受不到,极其自然地离开人世就行了……就像挂在树上的一片枯叶,不知何时被风一吹,离开枝头,回归大地,这样自然而然地死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