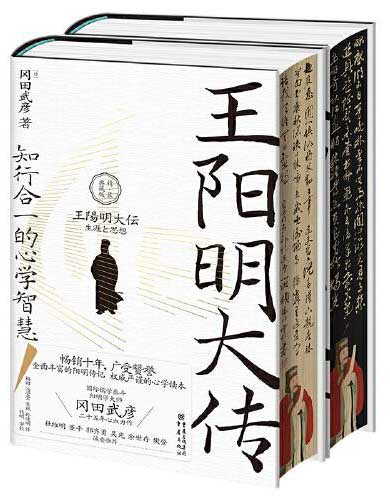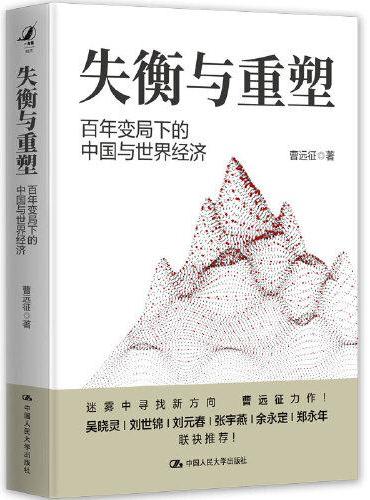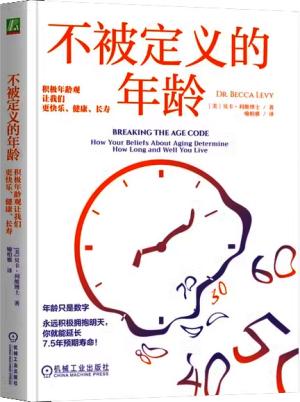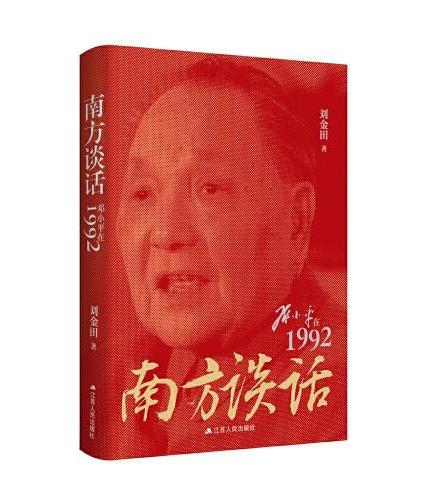新書推薦:

《
鸣沙丛书·鼎革:南北议和与清帝退位
》
售價:NT$
551.0

《
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兼论宗教哲学(英国观念论名著译丛)
》
售價:NT$
275.0

《
突破不可能:用特工思维提升领导力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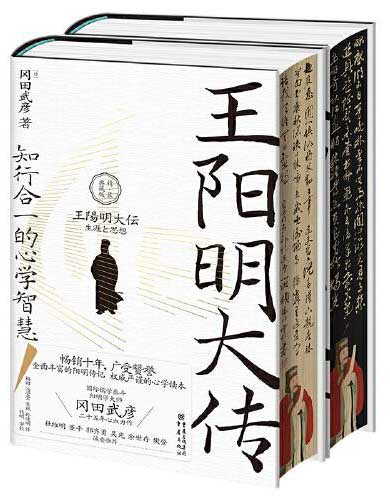
《
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精装典藏版)
》
售價:NT$
10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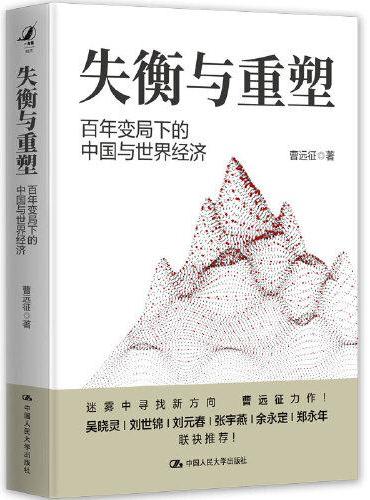
《
失衡与重塑——百年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经济
》
售價:NT$
6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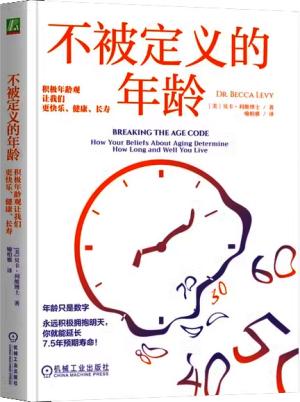
《
不被定义的年龄:积极年龄观让我们更快乐、健康、长寿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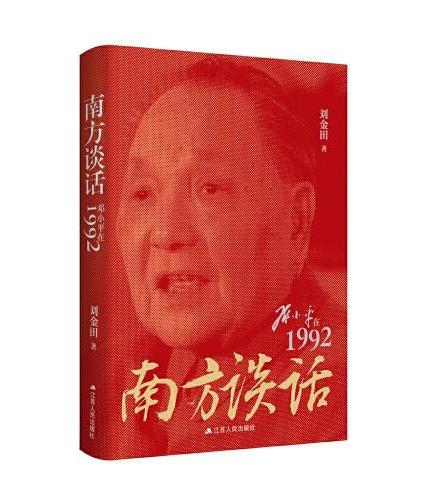
《
南方谈话:邓小平在1992
》
售價:NT$
367.0

《
纷纭万端 : 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
》
售價:NT$
500.0
|
| 編輯推薦: |
|
尤多拉?韦尔蒂是首位在世时作品入选“美国文库”的文坛巨匠。她是继福克纳之后,美国南方文学最伟大的小说家,被誉为“美国民族的纪念碑”。雷蒙德?卡佛、托妮?莫里森、艾丽丝?门罗、杜鲁门?卡波蒂、理查德?福特、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等等,都深受其影响。处女作《绿帘》被誉为美国南方小说中兴之作,是作家卡佛在教授写作时必与学生探讨的教材。本书内含韦尔蒂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17篇,被广泛收入各种文选和文学教材。其中,《莉莉?道和三女士》、《绿帘》、《搭车人》入选《美国最佳短篇小说》;《石化人》、《老路》曾获欧?亨利短篇小说奖。随书附赠韦尔蒂经典摄影作品明信片一套!
|
| 內容簡介: |
|
《绿帘》是韦尔蒂的第一部小说集,奠定了作者的文学地位,从此,评论家将她的作品和爱伦·坡、威廉·福克纳的名作相提并论。该文集包含17篇短篇小说,故事均发生在美国南方小镇,人物多是平凡如你我的常人,基调上有的调侃戏谑,描摹出平淡人生的庸俗、谐趣和虚伪,有的温柔婉约,透露出青春的情愫、年少时的懵懂惘然;有的则是沉重凄楚,揭示物质之困乏、精神之创痛、沟通之无道,总之是林林总总,把人生的秘密、辛酸、孤独、恐惧、危险描摹得入木三分。
|
| 關於作者: |
尤多拉?韦尔蒂(1909—2001)出生于美国密西西比州中产阶级家庭,母亲酷爱阅读,父亲热衷摄影,韦尔蒂自幼深受他们影响。
大萧条时期,韦尔蒂在州政府供职,有机会到各地旅行。旅行途中所见普通人家的生活情景,让她深深着迷。为了捕捉那些场景,她拍了几百张照片,并于1936年在纽约举办了摄影展。同年,她的第一篇小说也获得发表,作家生涯就此开端;此后佳作不断,在小说、述评和散文写作中尽显其才。
1998年,其作品被收入代表美国文学最高成就的“美国文库”系列,打破了过去只选已逝作家作品的传统,在文学界引起轰动。
|
| 目錄:
|
莉莉?道和三女士
一则新闻
石化人
钥匙
基拉,流离失所的印第安女郎
我为什么住在邮局
警哨
搭车人
回忆
克莱蒂
马布霍尔老先生
献给玛乔丽的花
绿帘
爱心探望
流动推销员之死
鲍尔豪斯
老路
[附录一]英文版序言
[附录二]译后记
|
| 內容試閱:
|
绿帘
有一年夏季,拉金山镇每天都会下点儿雨。这雨是有规律可循的,下午两点左右准会落下来。
一天,差不多都到五点了,还是阳光灿烂,太阳几乎像在如洗的天空中兜着小圈子;下方,街道两旁的树木上和镇上成排的花园里,每片叶子都如同镜面般硬生生地反射着阳光。几乎所有女人都坐在自家窗前,摇扇、叹气,等着下雨。
拉金太太自丈夫去世后就独居在一幢白色的小房子里,她的花园面积大,植物茂密,一直蔓延到屋后的斜坡下。那个夏天,太阳的暴晒、雨水的滂沱都阻止不了她每天在园里忙活。此刻,她穿着男式工装裤,挽着袖子和裤管,正荷锄劳作;强烈的阳光像把镊子揪住她笨拙、矮小的身影,将她从浓密的叶片中剥离出来,令她挥锄时的样子显得古怪而胆怯——用力过猛、姿势不佳、莽莽撞撞。
园边树篱高耸,形若高墙,邻家只能从楼上窗户才能看见园内的情形。这花园高矮不整,枝蔓缠绕,日渐稠茂过度、杂乱无章。拉金太太对这里定然了如指掌,很可能如今她都不堪想象人间还有其他地方;自她丈夫死于意外,谁也没在别处见过她。每天早晨,或许都有人看见她走出白房子,迈着慢吞吞、几乎是怯生生的步子,罩着件邋遢的工装裤,经常头发飘散着,没梳到的地方还打着结呢。起先,她会溜达片刻,迟疑着走到花木深处,任露水打湿衣衫,却不伸手触碰任何东西。然后,好像着魔般,几分刚毅降临其身——她安定下来,静静地站上一会儿,仿佛正在摘下眼罩似的;再往后,她便跪在花丛中,干起活来。
她干活时从不停歇。几乎隐身一般,她成天淹没在茂密、凌乱、高低起伏的植被里。开饭时仆人会叫她,她就去吃;但直到天黑透,她才真的放手不干,迈着拖沓的步子乖乖地走到房边,慢腾腾地打开低矮的小后门。甚至下雨也不过是让她暂停而已,她会到花园中央的梨树下避雨,这树四月中旬正值枝繁叶茂期,明艳的枝叶沉甸甸地几乎垂及地面。
拉金太太的花园土壤极为肥沃,这既让她有事可做,也给她出了难题。唯有不停劳作才能对付得了这肥厚的黑土,唯有对花枝、树丛、藤蔓进行剪切、移栽、修理、固定才能使它们不逾越边界,无序疯长。夏季雨水天天有,这只会让她的神经绷得更紧,令她本已过剩的精力更加充沛。然而,拉金太太甚少剪枝、移栽或者固定花木……某种程度上,她寻求的不是井然有序,而是多多益善,仿佛她特意要把自己的园中生活作为冒险进行得更远更深入。
任何花草,只要她能弄到的或从邮购目录上买到的,她都种上。她种得那样稠密,那样匆忙,那样不假思索,丝毫不在乎邻居们在养花俱乐部选种时的理念,比如如何构成合适的景观,或者达致令人惬意的效果,甚至于颜色的协调之类。到底为了什么,拉金太太在花园里如此埋头苦干,邻居们看不出来。好花朵朵,她自是一枝也没有给谁送过;任谁生病离世,她也绝不会送花致意。若说她毕竟还念及“美”感(他们想到她脏兮兮的工装裤如今和树叶差不多是一个颜色了),她自然也不是在花园里为“美”而努力:这样一个地方可一点儿也不赏心悦目。邻居们从楼上窗户俯瞰,这地方有点像原始丛林,其主人纤细、莽撞的身影每日都隐没其间。
起先,拉金先生刚去世时,人们每隔段时间就适当地拜访一下其遗孀——毕竟这镇子是以拉金先生父亲的名字命名的。但她并不领情,人们互相交流说。如今,早上精心梳头时,人们偶尔会从卧室窗户俯瞰一眼,找到她在花园中的位置,就像看地图时指尖戳向某个外国城市,差不多带着点好奇远远地看着她所在的地点,随即便抛之脑后。
那天一大早,人们听见拉金家花园里传来口哨声,辨认出那是杰米的调子,看见他在拉金太太身边,正跪在花间忙活。他不过是这一带按日帮工收费的黑人小子。据说,即便是杰米,拉金太太也仅是偶尔容得下……
整个下午她不时抬头,察看他移栽花木的进度,要他务必在下雨前完工。她自己忙着用锄头开垦仅剩的几小块荒地中的一块,好种上新的灌木。她在大太阳下弯着腰,硬生生地落锄,速度很快,毫不懈怠。有一回,她仰头盯了会光闪闪、悠远的天空,目光呆滞,眼睑皱起,好像是过于焦躁不安或困惑迷乱。她的唇线轮廓分明。人们说,她从不开口。
但是,没有任何先兆来警醒,甚至没有任何绝望情绪作铺垫,回忆就轻而易举地缚住了她。就像小小舞台上的幕布被哗地拉开,她立马就看见了:白房子的门廊,屋前方的林荫道,还有丈夫下班驾驶的蓝色轿车临近家门。那是一个夏日,前一年的夏季的一天。现在,回忆驱使她边锄地边重复一个动作——扭头,在轻快的扭头动作中,她又能看见那棵即将倒下的树。没有任何预警。但是,那棵巨大的树,那芬芳的楝树,突然一歪,像一团乌云缓缓斜压向她的丈夫。她正站在门廊里,在站立的地方柔声对他说:“你不会有事的。”她说话从来没有哪一刻像那时一样亲切。但是,那棵树倒下了,正巧压在车上,把他压死了。其后,她在门廊里等了会儿,一动也不动——陷在某种沉思中——仿佛要探下去,从无形中捞上来保护性的词语,一一重试……好能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那是让人无法相信的事故,她的爱本应该能保护丈夫平安。
她继续锄着刨开的地面,铲倒丰肥的杂草。不一会儿,她渐渐意识到在这个松松垮垮的所在只有自己在活动。一丝风也没有。鸟儿噤声不啼。太阳像被钳子固定在天边。一切再一次停顿,寂静催眠了植物的枝茎,突然间所有的叶子都变得厚重起来。花园中央梨树的阴影冷冷地映在地上。园子对过,杰米跪着,一动不动。
“杰米!”她生气地大叫道。
但她的声音在这花木稠密的园中几乎传不过去。一瞬间她感到恐慌,就像某种外力伸指扒开了篱笆,点明了她的孤单。霎时,她单手捂向胸前。那儿一种隐隐的振翼声吓到了她,仿佛那外力在对她低声絮语:你内心飞翔的小鸟冲不破漫天乌云……她面无表情地凝视着花园,紧紧抓住锄头,目光掠过绿叶,看向杰米。
这黑人跪在花草间的温顺背影叫她生起气来。她朝他走过去,手中拽着的锄头轻轻擦着身后的花丛。她迫使自己正视他,平生第一次仔细观察他——他那样子就像个孩子。当他把头微微歪向一边,棕黄的手指马虎地翻动泥土时,她怀着某种无所凭依的疑虑和渴望,看见了他脸上一种很不以为然的浅笑;他一边移栽着嫩苗,一边沉浸在某种不可实现的梦想中。他甚至没在吹口哨;甚至那口哨声也没有了。
她再走近一步——他一定是聋了!——几乎偷偷摸摸地逼近了正身心松弛、醉于冥想的杰米,似乎他那侧脸的悄然一闪,他那稍纵即逝的微笑都是揶揄人的、无邪的幻觉,若隐若现又美丽万端——是她紧张而迷离的眼神中的幻景。
然而,一种局促感,一种相应的、近乎于狂暴的绝望,以惊人的速度在她身上升腾。站在他正后方时,她有一阵子全然不动,就像处于她开始园中劳作前的那种奇特、自我封闭的状态。然后,她把锄举过头顶;两只臃肿的袖管全都滑落下来,露出那纤细、捂得白净的胳膊,那青春逼人的事实让人震惊。
她握住锄把,很紧很紧,好像确信木柄能有感觉,确信她的力气能让木柄表面吃痛而凹陷。就在她眼下,杰米勾着的脑袋看起来痴痴的,可怕又奇妙,几乎难以接近。然而,隔着这么近的距离,这个低垂着、注定要毁灭的头颅——其上有簇簇热乎乎的羊毛般的头发、精致而闪亮的双耳、细细的棕色汗流——还明显沉浸在可笑的梦想中,无从避开将至的危险。
这个脑袋她准能砍下来,只要存心去砍。她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她见过一个人所处的危险和死亡;她又是那样无能为力,眼睁睁地看着意外的发生、生死的发生、无法解释的事件的发生……生与死,她手握沉甸甸的锄头想道,如今生与死对她没有任何意义,生与死只是她一直被迫要用双手去实现的事情。她不住地追问:不可能去补救吗?不可能去惩罚吗?不可能去反抗吗?片刻的暗影遮住了阳光,像一片窄小的叶子在风中掠过花园。
在那一刻,下雨了。第一滴雨落在她高抬的手臂上。细密的声响和凉意打动了她。
叹息着,拉金太太把锄头拿低,小心地放到地面上,不让它碰到生长中的花木。她静静地站在原处,挨着杰米,听着落雨声。雨多么轻柔。雨多么密集——这声音宣告等待终于结束。
雨光和太阳光不同,雨中万物都显得熠熠生辉,不是因为反光,而是从内里,从其本身无言的结构里放出光彩。百日菊的小幼芽绿得纯净,几乎亮闪闪的。雨点光顾,一个接着一个,所有植物的幼苗都神采焕发,然后就是藤类张枝拔蔓。那梨树发出轻轻的沙沙声,就像飞鸟在扇动翅翼。她能感觉到身后屋子发出信号似的白色亮光,仿佛暗夜里点亮了一盏信号灯。随后,好像突然意识到下雨而吓了一跳,杰米转过脸来正面朝她,心中半是疑问半是愉悦,他笑容满面,本来舒展开的身体因受到惊扰而收拢。他磕磕巴巴说出几个不连贯的词,很是羞怯。
她没有回答杰米,也没有动。除了落下的雨,她现在什么也感觉不到。杰米说话的间隙,她注意倾听的是雨滴散落的轻柔声息,雨静静落在长矛样的鸢尾花叶上时的触感;厨师在门口台阶上放了个大水罐,雨点滴落,发出了清脆悦耳的铃音。
最后,杰米站在那儿不再出声,像是在等工钱。他用手在面前拂了一下,试图擦去自己的疑惑。雨下个不停,一阵风夹杂着浓郁湿润的香气向她袭来。
随后,柔弱无力的感觉膨胀开来,冲破了通常的限度,在她委顿的体内撕扯、旋转。
终于来了,她迷迷糊糊地想。她仰起头,眼睛无意识地看着天,天空开始动起来,帘幕低卷,云丛越来越软,漫天舒展。几乎是昏天黑地了,不久就是雨声喧哗、温和宜人的夜晚了。雨将敲打白房子陡峭的屋顶。屋里,她会躺在床上听雨。连绵不绝,雨点落啊落,敲啊敲。花园里一天的劳作结束了,她躺在床上,胳膊疲惫地歇在身侧,一动不动地享受着安宁:无穷无尽之物,无可抵挡。
随后,拉金太太一头倒在花丛里,躺着不省人事了,身上沾了片片雨水。她仰面朝上,陷在花草中,头发从额头散落下来,雨水打在睁开的眼睛上,眼睛立刻闭上了。她嘴巴慢慢张开,身体看上去微微动了动,像梦中人难受地调整了一下睡姿。
杰米连跑带跳地过来,蹲在她身边,看看脚下自己踩坏的花草,再看看地上这个形容不整、动弹不得的身躯,连连倒吸凉气。之后,他安静下来,稍稍后退,敬畏地看了看那张没有知觉的脸,那张脸惨白没有血色,显出被打击后的死寂。他记得,当感觉到她站在身后俯视自己时,有什么东西令他身心俱静,那一刻世间任何事物都不能令他转过身去。他始终记得,刚下雨的时候,邻家纷纷关窗发出的含糊的噼啪声……但现在,在这个无人关注的地方,是他自己站着俯看可怜的拉金太太。
他弯下腰,开始用惊恐、凄惨、哀求的声音呼喊她的名字,直到她动了动。
“拉金小姐啊!拉金小姐!”
随后他敏捷地跳起来,跑出了花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