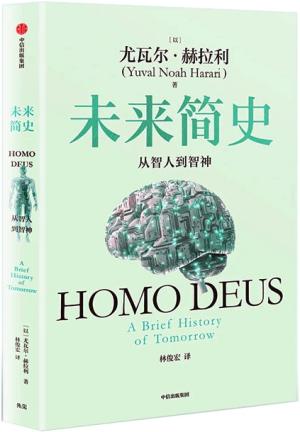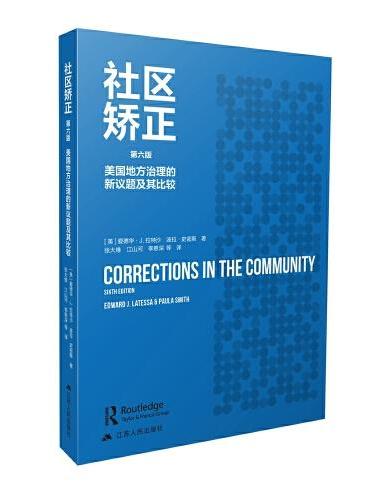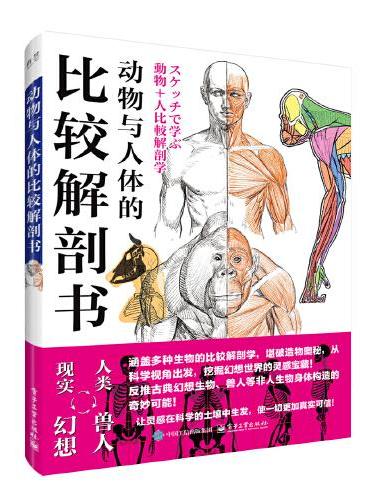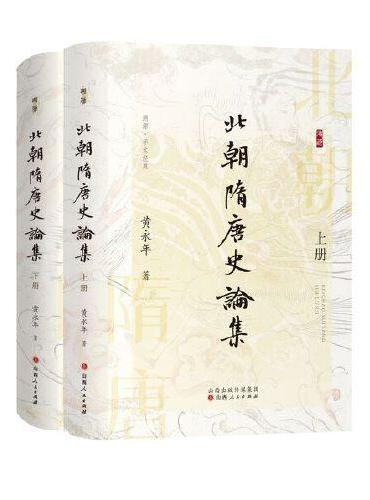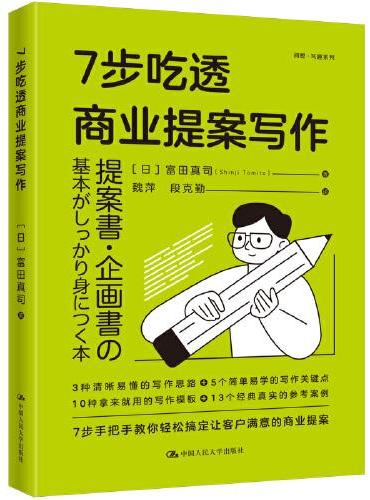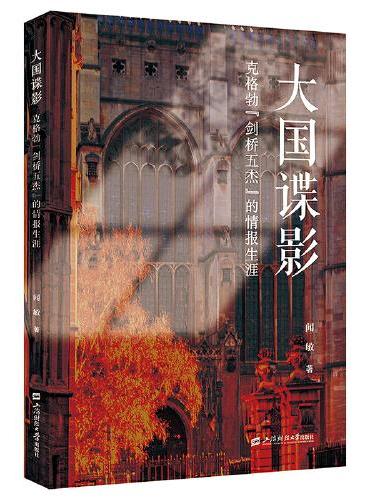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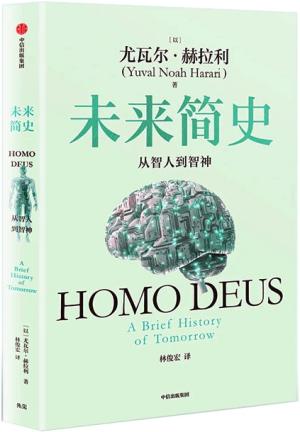
《
未来简史 从智人到智神(2025白金纪念版)
》
售價:NT$
4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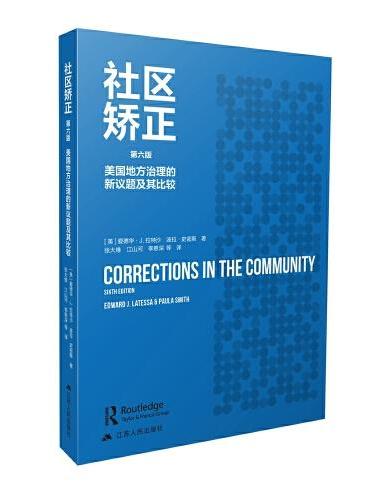
《
社区矫正(第六版):美国地方治理的新议题及其比较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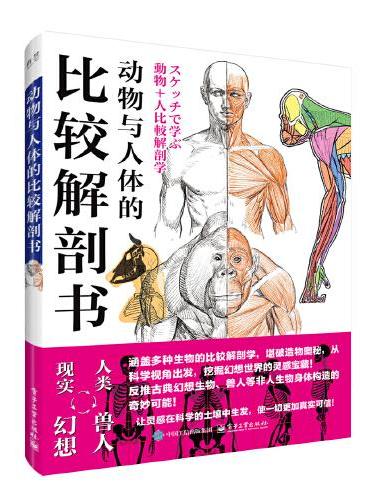
《
动物与人体的比较解剖书
》
售價:NT$
45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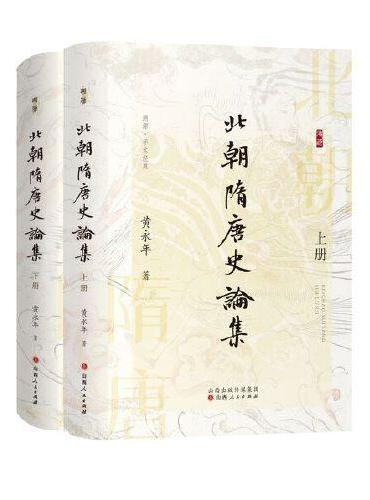
《
北朝隋唐史论集
》
售價:NT$
1270.0

《
半小时漫画中国史(全5册)
》
售價:NT$
127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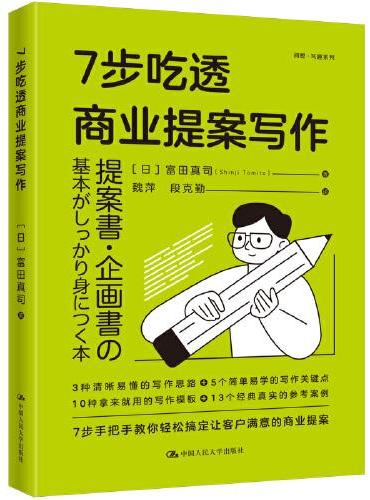
《
7步吃透商业提案写作
》
售價:NT$
3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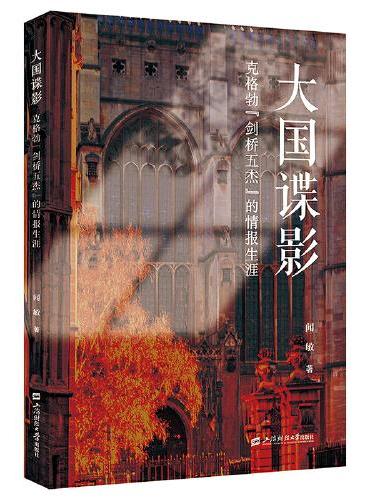
《
大国谍影
》
售價:NT$
449.0

《
制造消费者
》
售價:NT$
230.0
|
| 編輯推薦: |
闫红用文学之光照亮小城镇旧塌塌灰蒙蒙的生活,定睛一看,我们分明都是这样长大的。不过是九十年代,却已经像古代了,因而泛出古代生活所独具的美感。
——绿妖
这些回忆文字,像在一座向阳的屋子里,静静的玉簪、水仙,素淡、温馨、洁净,我们的阅读,像一次意外的闯入。
——韩松落
闫红笔下的“致青春”,虽然没有那么残酷暴烈,但是她淡淡的笔触,描述出更让人感同身受的小城里的青春。
——黄佟佟
闫红是文字和心思都清明细密的人,看她返回自己的青春场景旧事重提,活灵活现,似笑非笑。在她所有随笔里,我最好奇和期待这一本。
——黄爱东西
|
| 內容簡介: |
闫红的文笔一向细腻、犀利。她写张爱玲,写胡适,写秦淮八艳,一直都在讲别人的故事。而这次,她真正写了一回自己,用五年的时间一字一句地构建了这样一部致青春的力作。就像闫红自己说的:它是我唯一的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散文集,目光从他者,转向自己的内心。
《彼年此时》用细腻的笔触去讲述至亲至爱的家人,再也回不去的家乡,一辈子藏心底的朋友,以及成长角落里各样的真实感动。不曾温柔的妈妈,独居多年的姥姥,跟命运死磕的发小,澡堂子里的陌生女人,私奔的伶人,出家的乡村医生,尽入笔下;被斩首的乌龟,半透明的麦芽糖,院长送的红灯笼,买来的绣花鞋,迷宫般的集市,皆现纸上。
|
| 關於作者: |
闫红,生于安徽,现为媒体人。2005年出版作品《误读红楼》,轰动一时。2007年出版代表作《她们谋生亦谋爱》,在国内引发
“回归传统,重读古典”的热潮。另有代表作《诗经往事》《哪一种爱不千疮百孔》《如果这都不算爱——胡适情事》等。(新浪微博:@合肥闫红)
|
| 目錄:
|
文德路
哪一种爱不千疮百孔
发 小
走着走着就散了
马路求爱者
我听过最美的声音
铁轨上的记忆
浴室里的女人
仁里街
寂寞童年
两个吃货的小友谊
在仁里街能捡到什么
颍 上
姥爷的葬礼
荡子行不归
漂回的灯笼
清河路
火锅往事
被低俗打动
姥姥的绣花鞋
香水旅程
马圩子
马圩子的夜与路
乡间伶人往事
乡村医生的飞短流长
那时的古典爱情
忍耐也是一种征服
小燕儿
赶 集
马圩子杀夫事件
|
| 內容試閱:
|
多年以后回望此刻
即使作为一个话痨,我喜欢听闫红讲,甚于我对她讲。最喜欢听她讲童年的事。喜欢一个人,就会喜欢童年时的她。童年时的闫红,似乎比别的孩子都聪明,但又未必比别的孩子做得好,甚至某些方面比别的孩子笨拙些。总之,是一个喜感很强的孩子。尤其是她在乡村的生活,天啊,我有多么羡慕那段生活。
还喜欢听她讲一些听起来破败不堪的生活。比如说,底层人民的口味。其实闫红自己的口味,就有点奇怪。比如说她喜欢看上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初不入流的那些专科院校,觉得它们比规整光鲜的大学更能引起兴趣:陈旧简陋,还有点不分明的雾霭,看上去很颓的年轻人在里面走动。
她喜欢小县城,路上来来去去的人、飘进她耳朵的几句对话,她都能把它们脑补成一个故事;她还喜欢一些听起来很俗的流行歌,比如有一首俗得让人涕泪交加的“你已经做了谁的小三,我也不再是你的港湾”。
——她很喜欢有些破败的真实生活,喜欢那种粗粝的质感。不喜欢PS版的。我劝她把这些写成小说。
这一劝就是六七年。经常在她如痴如醉地讲了半天之时,我打断她,像钱玄同那样,幽幽地来一句:“你把刚才这事写下来吧?这起码可以写个一万字吧?”
在此之前,闫红出了几本书,都是文化散文,也就是说,她是以“文化散文”被公众所知的。但我知道闫红写得最好的,其实是小说。而她写得最快乐的,也是小说。
因为小说能够自成一个世界。在眼见的日常生活之外,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广大的更诗意的世界,它也许在过去,在远方,也许就在我们脑海里,等待被描述,等待被语言通知。写小说的人,在自己给自己的那个世界里,不知今夕何夕,不知老之将至,她们就是我最羡慕的人。
而闫红就在这些人中。就我所知,她还是写得最好的一个。
这一次,有出版商与我有一致的爱好,仿佛是退而求其次,闫红终于写了这一组本来可以作为小说题材的散文。
其实,书里几乎所有的事,我都听她说过,但是看书的时候,我还是时不时起了一种新的震动。
她特别善于捕捉细节,特别善于表达细节。韩东说,看见那些能正确表达自己内心的文字总是惊异万分、心存敬意。表达欲和表现欲一字之差,区别明显。我看闫红的文章,经常有这样的惊异和敬意。
比如她写到公共浴室里一个陌生的女人,——“许多次,我看到她仰起头,下巴与脖颈成一条优美的弧线,水柱重重地打在她脸上,水花晶莹,冲刷着她的短发,弹溅到她的肌肤上,我能够感觉到她的快意,仿佛,是她的灵魂,在经受着这样一场强有力的冲击,我不由想,她一定是在爱着吧。”——在她写出“她一定是在爱着吧”这几个字之前,我被这细致有力的文字感染,心中也觉得,必须有爱才配得上这有冲击力的美感。“她一定是在爱着吧”,当闫红这样写下,我仿佛隔空,与那个正在浴室里观察着的小女孩有了通感。
闫红与我,虽说几乎所有的话题都能谈,但其实,我们是不同的两种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她的距离感。
她是一个即使与发小在一起,仍会不时地受到距离感的提醒的人。看她写与发小重逢那一篇,看完会觉得自己的身体不知不觉地绷得很紧,一种感染力很强的紧张感,使这场阅读仿佛带有体力性质。
距离感和紧张感这两样东西,在我这里是不明显的。但我恰恰认为,这些东西,使闫红对生活有着我所没有的理解。
因为她无处不在的纠结、钻探,无处不在的紧张感,使得她的文字,会有一般人没有的张力。她能把很多微妙的地方,呈现得特别明白,又把一些很明白的地方,弄得非常微妙。
她的分裂感,对于生活也许是一种内耗,但对于写作,无疑是一种利器——她能穿戳到更纵深的地方。说到内耗,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是“耗”,就像她会得到比别人多的苦楚一样,她也会比别人得到更多的甘甜。她是一个活得非常充分的人。
读闫红这本《彼年此时》,有很多次,我读哭了。
印象中,泪水来得特别突然的一次,是她写到她给她姥姥买的绣花鞋,文章里那么轻松的气氛,姥姥还得意地编好了跟别人怎么说,“是娘家的一个侄女做的”。然后还要脱下鞋,把鞋底翻给人家看,看看,这针脚多细密。然后人家必是啧啧称奇。……
然后说到,姥姥央她给自己找一对红色的。接下去,闫红写道:“我把这份心愿理解为一个老去的女人对于自己的娇宠,对于自身女性身份的唤醒与确认,而姥姥选择最放肆最喧哗的那种大红色,是因为她太老了所以她活开了,不再瞻前顾后,不再畏头畏尾,她骄傲地、平静地穿着它,那双鞋和她的岁月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让人动容的美。”
还有一次流泪,是闫红说到她第一次去上海读书时。父亲陪着她坐着夜班火车到了宿舍,父亲还在向新认识的宿友介绍她,她却注意到“出门的那个女生的铺位上,挂着一件黑色的裙子”。是很精致洋气的裙子,她猜测它的主人必也是个特别洋气讲究的女子吧?不知会不会看不起人?不是虚荣,而是“我来这里,是要赤手空拳给自己打一个天地的,从一开始,就容不得一点闪失”。
闫红的这个复述里,让读者觉得有一种咬牙切齿的孩子气,好像看到一个绷着脸的小女孩,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她紧紧地把自己的手攥得发白,心里像艾略特一样默念:“非如此不可!”
她催促她爸快回,再三催促下,父亲方离开。那天晚上,她站在宿舍里,对着窗外的夜风,哭了。
我觉得我能看到那个第一次到异乡的女孩,她心情复杂地站在一个无法估量前景的处境里,对父亲的负疚,对异乡的恐惧,对未来的担忧,全在这一个细节里喷涌而出。我自己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呢?也许有过,但想必被我忘却。不然为何会在这几个段落里,心揪成一团。
年纪大了,真的觉得文章不是“做”出来的。文字的灵气、布局谋篇等等,固然重要,但作为一个也经常写字的人,能看出里面的技术措施。我也佩服,也赞赏,但我知道它是可以学得到的。但是闫红的文章,还有其他人难以学习的地方。那是她对生活的感受,那种既沆瀣一气而又总在抽离的状态,锥骨地纠缠而又截然弃之的态度,我从没有在其他人身上看到过。她仿佛比别人有更多的感官,生活对她充满了各种别人看不到的虚空间。她的作品有一种非常悠远的氛围,仿佛很久以前的某一天,又好像多年以后回望此刻。那种氛围令我非常着迷。
世间所有的书,写的都是作者本身。闫红写过张爱玲、秦淮八艳、胡适、《红楼梦》、《诗经》,其实都是在写她自己。现在这一本,最为直接地写自己,也是在她所有的书里,最动情的一本。我阅读的过程中,尝试去掉朋友这个身份,把她设想成一个陌生人,或者说,把自己设想成一个陌生人,想象身为一个陌生人,对这个写书的闫红会有什么感受?
想象的结果是,哪怕作为一个陌生人,我也知道,这就是我会爱上的酣畅阅读,这就是我会爱上的灵魂。
陈思呈
哪一种爱不千疮百孔
隐秘之所
我妈在纺织厂工作,这儿曾是小城里最大的工厂,现在已经破产。我妈说,破产对他们这些退休老工人来说,不是件坏事。她说了些理由,我没有听明白,总之,她对工作以及生活了几十年的那个厂区的没落,没多少感触。
工厂极大繁荣的年代,机器声终日轰鸣,走在大街上都能感到震动。厂里的女工,不但有像我妈这样从农村招来的,还有很多是上海下放的知青。这些知青在本地扎根,生儿育女,每年回一次上海老家。工友托她们带回最时髦的日用品。在我的童年,那双被我踢踢踏踏穿了好几年的红皮鞋,就“光荣地”来自上海。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件大红的滑雪袄,我仍然记得,在某个刚刚寒冷的日子里,刚下班回家的妈妈,高兴地把那件明显太长的袄子,披到我的身上。
太长了,所以并不好看,后来我长高了,它变得合身了些,还是不好看,到那时我们才看出来,它压根儿就不是一件好看的衣服,与合身不合身无关。不过我都穿了好几年了,也无所谓了。
上海人还给我捎过一条喇叭裤,时髦之极,我穿着它去奶奶家,特意跑出院子,走到公路上去,希望每个路人,都能注意到我的裤子。我舅爷吓唬我,说,“警察会把你当小流氓抓走的噢……”
我妈那时挺喜欢打扮我的(那时,是指我六岁之前)。上面说的这些,全是我六岁之前的事。六岁之后,我妈对于我的穿着,有种心灰意冷的潦草。要么是从我小姨那里接过来的旧衣服——我骨架大,撑得起;要么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比如某年的新年,我妈拿了一件绿军褂给我蒙袄,天哪,绿军褂流行是二十年前的事儿,再说那件衣服上还有个补丁。我妈后来更重视我的吃。我自小挑食,不吃葱姜蒜,还不吃猪肉。在普通的汉族家庭的餐桌上,猪肉是荤菜里的主力,这让她非常头疼。她的补救之道是每天炒两个鸡蛋埋在我碗底,再手疾眼快地将餐桌上猪肉之外的所有好吃的,抢到我碗中。
上海人带来的巧克力之类,她藏起来,见家里没人——主要是我弟弟不在家时,塞给我一小块,一盒巧克力我可以吃上半个月;家里偶尔吃个鸡,两个鸡大腿早早被剥了皮,放进我碗里,我妈还目光灼灼地盯着盘子,看见“好肉”就夹给我,武林高手般迅疾。我弟弟终于不乐意了,把饭碗一推,哇地大哭起来: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个小女孩吗?娇宝贝!
其实有些东西我也不爱吃,比如鸭子,我总觉得鸭肉有些腥。那些鸭心、鸭肝、鸭大腿,我实在吃不下去啊,磨磨蹭蹭,等全家人都吃罢离席,我妈洗碗去了,我便迅速地把那些东西放口袋里,转身塞到抽屉的最后一格。那时实在太小,不懂得怎么进一步销赃,还有点儿自欺欺人的鸵鸟心理,好像我看不到,那些东西就不存在了,但心里清楚地知道,那些食物正在抽屉最里面的一格变质——还好是冬天,不容易腐烂。惶恐地过着一天又一天,最快乐的时候,也会记起这心结,直到,它们终于被我妈勃然大怒地发现了。
抽屉最里面的一格,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每个家庭的隐秘之所。我妈也在那里面藏东西,有天,我妈对我说,抽屉里有些糖,你拿去吃吧。我打开抽屉,是我最喜欢的大白兔奶糖,我很快把那些糖都吃完了。我意犹未尽,却也未抱希望地把抽屉全部拉开,哈,里面竟然还有很多“大白兔”,我抓起来,一个一个地全部吃掉。
第二天,我弟弟也在家,我妈对我说,“你把抽屉里的糖拿出来你俩吃了”。我说,“让我吃完了”。我妈说,“里面还有呢!”我窘迫地说,“也让我吃完了。”
三尺之内是禁地
我有时猜在我弟弟的记忆里,我妈一定更偏疼我一点儿,但是,从童年到少年,甚至直到青年时代,我都在羡慕别人的母亲。近的是我同学郁葱葱她妈,那么温柔,郁葱葱经常跟我描述她是怎样的恃宠而娇;远的则有那些有名作家的妈。我甚至得出个结论,要想成为一个女作家,必须有个温柔的母亲(当然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所以,我沮丧地想,我这辈子是当不成作家了,我妈,也太凶了。
我记忆中总有一个片段。我让我妈下班给我带粉笔,她没有带回来,我扑在我妈怀里,扯着她的衣服胡闹,我妈笑着说,哎呀,妈妈快要死了!我们嬉笑着打成一团。那时我多大?两岁,三岁?不记得了,我只知道,这是我记忆里唯一一个和我妈嬉闹的片段,其他时刻,我妈就像一只惹不起的老虎,一触即发。
有一回,我妈给我报听写,我写错了一个字,被我妈骂了几句,骂完了,她消了气,拿糖给我吃。我情商没那么高,无功受禄更添了些无措,一时间竟恼羞成怒起来,我啪地把糖打到桌子上。太不识好歹了!于是我妈勃然大怒,把我抓过来暴揍了一顿。
经常会因为小错误挨打。比如中午踮起脚,走进房间,极轻极轻地去拉五斗橱上的抽屉,可是——从那时起我就知道生活不是可以控制的——抽屉还是发出了一声令我魂飞魄散的闷响,这响声惊醒了正在睡觉的我妈,不消说,又是抓过来一顿打。
凭良心说,我挨的打,最多也就是落在屁股上,跟我弟弟还是没法比的。也许我妈觉得小男孩更扛打,生起气来那是连拧带掐,且拣大腿上最嫩的地方,一通教训下来,大腿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触目惊心。
那年春节,我弟弟偷拿了他被我妈“暂时保管”的压岁钱。整个年下我们姐弟俩吃香的喝辣的,大手大脚地买花炮,在小城的大街小巷里晃荡。元宵过了,问题来了,我妈后知后觉地发现失窃了,我弟弟是主犯,我算是知情不报,双双受罚。我弟弟挨打时,那叫一个鬼哭狼嚎啊,闻者悚然。轮到我了,惩罚轻得多,我妈法外施恩是其一,其二当时我姥姥在我家,大大地给我说了些情。事后,我姥姥悄声对我说,要不是我,你看你得挨多狠!
对于我和弟弟来说,最幸福的时光,就是爸妈吵架之时。我妈搬回城西南的纺织厂宿舍,跟我姥姥住着。我和我弟弟,坐着纺织厂的班车两边跑:平时跟我爸,一到周末就去我妈那儿。
那段日子他们变成了一对好脾气的爹娘,给我们买好吃的,尽力争取我们。我妈总是说,要不是为了你们,我就跟你爸离婚了。我对单亲家庭的可怕缺乏想象,但对于我爸我妈再也不可能联手整我们的生活充满神往。每次听我妈这样说,我总是全无心肝地想,离啊,离啊,你干吗不离呢?他们最后当然没有离,非但如此,在某次我爸找我妈深谈了一番,他们共同梳理了多年感情,认清两人的共同目标之后,再也没有大吵过。
从此只有我妈上中班时,我们会感到些许轻松。纺织厂实行三班倒,早班是从早到晚,中班是下午去,半夜回,晚班是半夜去,中午回。我们最不喜欢我妈上夜班,这意味着她整个下午和晚上都在家,早班说起来白天不怎么在家,但是对于已经上小学的我和弟弟来说,漫长的夜晚,才是一天里的黄金时间,我们可不愿意让这段黄金时间,处于我妈的虎视眈眈之下,所以中班最好。后来我妈因病改换了工作岗位,上常日班了,我和弟弟连这点空子也钻不成了。
说起来,我和弟弟似乎十分冷血。对于我来说,我妈周围的三尺之内都是禁地,偶尔靠近,便有杀气袭来,锋芒在背,分外的局促。
有一次,我妈生病了,在房间里呕吐。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走进房间会不会讨一顿骂?病中的她,余威不倒,连那呕吐声,都带着强大的气场,似乎一秒钟就可以转变为咆哮。
我在房间外面踟蹰,听我妈伏在床上呕吐,实在听不下去了,才走进房间,把她呕吐的那个盆倒掉。端着盆出去时,我妈在身后冷笑道:你都不敢进来了,我将来老了还想指望你?我没吭声,端着盆出了门,现在想来,我妈那一刻的心应该很冷,以为我是怕侍候她,却不知,弱小如我,不过是心有余悸而已。
偶尔的温柔,出现在我十八岁之后,那一回,我妈患了美尼尔氏综合症,在医院里住着,我拎了饭盒去看她,她什么都吃不下。旁边那张床上的病人家属带来了韭菜鸡蛋馅饼,大大的一块,韭菜郁绿,鸡蛋金黄,面皮上煎出褐色的小斑点,香喷喷的,整个病房都闻得到。
我妈看了他们一眼,我明显地感觉到我妈对那个馅饼有兴趣。我有了点说不上话来的感觉。之前,我妈从来没有显示过她想吃什么,她永远在吃剩饭,或是在我吃过的残骸里敲骨吸髓地,剔出最后一点精华,以免浪费。她特别看不起馋嘴的女人,她的饮食态度,近乎“存天理灭人欲”。
我妈望向馅饼的目光,第一次把她变成了一个小女孩,陌生的小女孩。我跟她说,我去帮你买一个吧?她点点头。馅饼买回来,我妈没有立即吃,她似乎也有了点感触,看着我身上的衣服,用前所未有的温和声音说,等我好了,给你做件红大衣去,长的那种。
想要好多好多爱
后来我出去上学,放暑假时我爸总叮嘱我晚一点回来,他说,你妈脾气不好。我心领神会地在学校里拖延着。工作之后,依然经常被我妈骂得灰头土脸的,甚至我都来合肥了,几个月回一次家,还是会被我妈骂得气急败坏地逃出家门。路上碰到发小,他感兴趣地打量着我,说:你气色怎么这么坏?好像被人打了一顿似的。
不过这些我已经习惯了,反正我已远走他乡,我妈的性情,也在衰老中温和下来,以至于我时常希望她来我这里住住。我对我妈生出巨大的怨念,是在我刚结婚那会儿。
我弟弟比我先结婚,他结婚前后,我爸妈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兴奋期,买房子,装修,下聘礼,大办酒席,轰轰烈烈,得意扬扬。我结婚时,我爸妈也办了一场回门酒,详情不想再说,总之要冷清很多。
我当时无感,回头一想,怎么都不是滋味。后来听我妈聊起别人家的事儿,风轻云淡地说:闺女就是一门亲戚。
啊,这就是答案了,闺女就是一门亲戚,打发掉就行了。我原是敏感之人,抓住这句话,我近乎疑邻偷斧,爸妈对我弟弟说,你不要那么辛苦,将来我们这一切不都是你的?我微笑地听着,想,我并不想要什么,但,这种泾渭分明的话,是不是最好不要当着我的面说?
经常梦见跟他们吵架,激烈地指责他们不爱我,吵着吵着就哭起来,醒来时还在拼命地抽泣,一上午心情都很灰暗。经常感到被拒绝,打电话回家,爸妈口气冷淡一点,我马上就会有察觉,仓促地挂下电话,伤心上很久很久。
我老公不觉得有什么,他出身赤贫,家中兄姊众多,能吃口饱饭就不错了,从不指望更多。我的情况很复杂,一方面,我从小感到我爸的重男轻女,他虽然也用心教育我,对我的点滴成绩都感到无比骄傲,但一说起我弟弟,则更添了亲昵。他经常在无凭无据的情况下,说我不如弟弟聪明,哪儿哪儿都不如弟弟好,我也许是过于敏感地觉得:与其说这是他的一个评价,不如说是他的一个愿望,因为,女孩子终归是别人家的。
我一直以为,我妈对我更好一些,我吃下去的那么多炒鸡蛋、鸡大腿、鸡心、鸡肝、巧克力都在支持我的这个想法,却原来,闺女不过是一门亲戚。积怨加上错愕,加上“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使我常常黯然泪下,发起狠来,只恨不能像哪吒般剔骨还父剔肉还母。我自己这样上天入地地折腾,我爸妈一无所知。我陷入自设的死局,无以解脱。在文学作品里,这时需要外力出现,这种外力,通常是灾难。
是的,2007年,我爸遇到了一场大麻烦,几乎要倾家荡产。这麻烦还没结束,我姥姥又摔断了腿,大小便都不能自理。把我姥姥送进医院的那一晚,我失声痛哭,而我妈,这命运的直接承受者,在灯下慢慢地说,她想好了最坏的结果,大不了到街上卖小吃。她用心料理我姥姥的生活,对身边人无一句怨责,总说,他们又不是故意要这样。
我不由惭愧了。我比我妈,过得要好很多,我与那灾难还隔着一层,为什么,非要比她更不快乐?是我要求得太多了吧,我想要很多很多的爱,和很多很多的温柔。
未被这世界温柔相待
我妈不温柔,因为她从未被这世界温柔对待。
她生下来才五个月,我姥爷和我姥姥离婚了。我姥爷很快再娶,陆续又有六个儿女,我妈跟我姥姥过,我姥姥原本就是个暴躁的人,这会儿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我妈回忆,她三四岁时,大夏天,她跟我姥姥一块儿赶路,我姥姥人高马大,走得飞快,她追不上,我姥姥也不抱她,皱着眉头丢回一连串咒骂。
我姥姥逼她去找我姥爷要钱,她怯怯地贴着墙根,看过继母的脸色,来到她爸面前,低低喊一声,她爸瞥她一眼,叹口气,递过几个小钱,也没有别的话说。由于我姥姥跟她婆婆屡发冲突,回家的路上,我妈经常被叔叔们围起来骂,多少年之后,她说,想想那会儿,还挺可怜的。
终于参加工作了,每月的工资都交给我姥姥,终于结婚了,捉襟见肘的经济条件,多少年都过不上安生日子。
为了让家里经济更宽裕些,她下班之后还要帮别人打印材料,通宵达旦,上班都变成了休息,有段时间干脆请假在家里干活。好多个傍晚,我放学归来,一盏低瓦数的台灯下,我妈茫然地回过头来,仿佛在一个人状态里太久,有动响的世界都变得陌生了。有一次,她说自己不用再买新衣服了,又不出门,穿给谁看呢?许多年后,她对我说,女人一定不能待在家里,不然整个人都会“朽”掉,可就算快要“朽”掉了,她也未曾有一句抱怨。
她也不跟她父亲计较,逢年过节殷勤探望,那些欺负过她的叔叔们,时常来我家走动,她做一桌子菜,再尽己所能地打开一瓶好酒。说起过去的恩怨,我姥姥咬牙切齿,我妈却只叹一句:唉,人不就这一辈子吗?老记着那些事儿干吗?她轻轻松松地放下,高高兴兴地过日子——我和弟弟结婚后,她很少像过去那样疾言厉色了。最糟糕的日子里,她依然觉得命运待她不薄,起码我和我弟弟过得都还好。
我妈是对的。多和少,其实是个比较的问题,你希望得到的多了,自然就觉得自己得到的少了;同时,多和少,还是个感觉的问题,你觉得自己得到的少了,你拥有的,就真的少了。命运给我妈的礼物不算多,却给了她这点智慧。
我妈是对的。那些麻烦很快就过去了,一切并没有像我们预想得那么糟,要是早早透支了惊惧绝望,岂不是亏大了?
但还是常常很心疼她。有时她来合肥,回去时我送她,送到火车站,还是不放心,怕哪个环节会出错,要看到她进了检票口;看到报纸上有中老年妇女上当或是被人欺负的事儿,赶紧给她打个电话。在我心里,她的“气场”一点点消退,还原成一个小女孩:在医院里出现过一次的,想吃韭菜蛋饼的小女孩;童年的月光下,刚看完继母的脸色听完父亲的叹息又被叔叔们围着欺负的小女孩;若干年前的大夏天里,怎么用力也追不上母亲的脚步的小女孩……每一个小女孩,都应该被好好宠爱。
我妈对我,也比从前多了些惦记。我去内蒙古,出了蒙古包,手机显示四五个漏接电话,都是我妈打来的,打过去她说,刚才老打不通,我吓坏了。偶尔我说在考虑买车库,她说,我和你姥姥的本子(工资存折)上还有点儿钱,我给你送过去?——她还像当年一样,虽然难免被重男轻女的风气影响,但在她能做到的范围内,总想多给我一点儿,不管我是否用得着。
现在住的房子在六楼,我姥姥腿脚不方便,我妈也来得少了。有点儿遗憾,但也不是特别遗憾,我老觉得,将来,我和我妈还能在一起生活很久。我还想,到那个时候,换一辆好一点儿的车,带着她,沿着边境线旅游。她喜欢旅游,到哪里都高兴,遇到什么都不抱怨,时刻充满正能量,还有比她,更合适的游伴吗?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