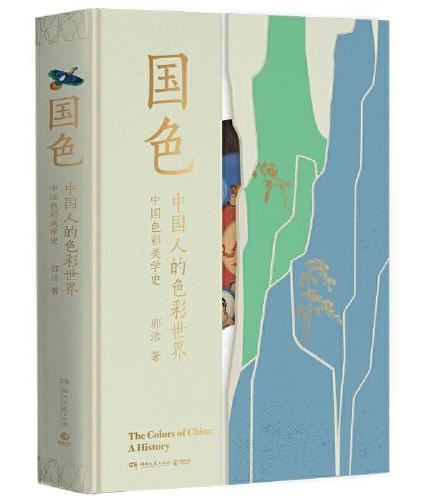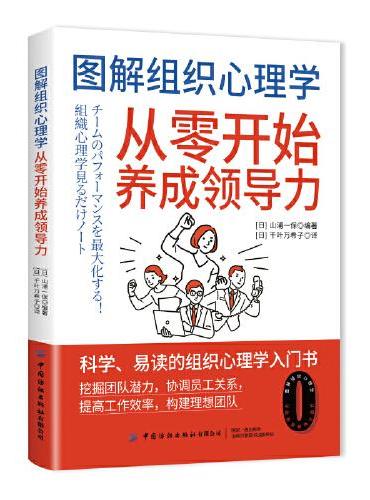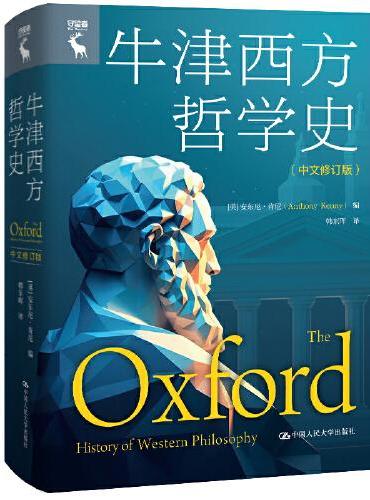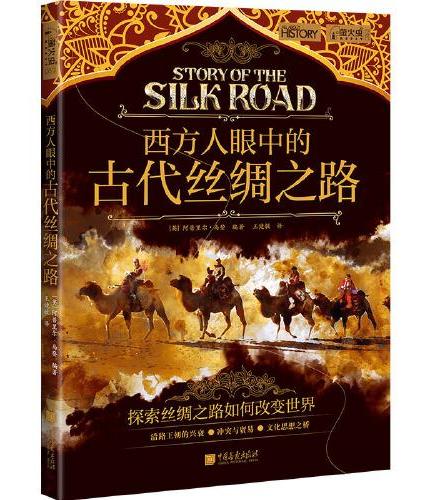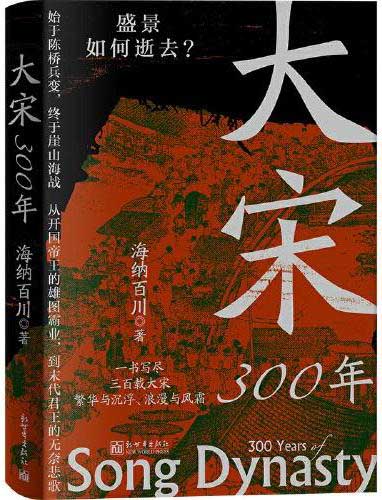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海外中国研究·中国古代的身份制:良与贱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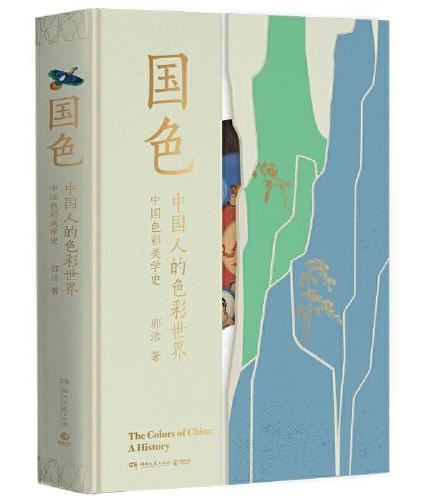
《
国色(《寻色中国》首席色彩顾问郭浩重磅力作,中国传统色丰碑之作《国色》,探寻中国人的色彩世界!)
》
售價:NT$
10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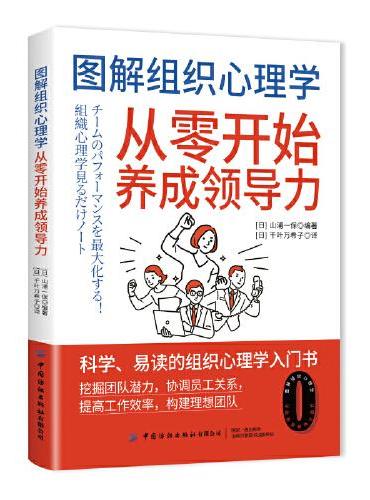
《
图解组织心理学:从零开始养成领导力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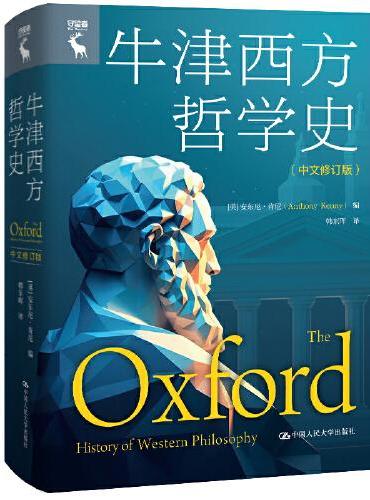
《
牛津西方哲学史(中文修订版)
》
售價:NT$
6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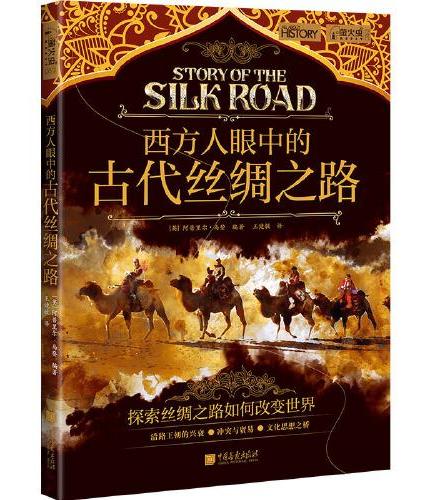
《
萤火虫全球史:西方人眼中的古代丝绸之路
》
售價:NT$
38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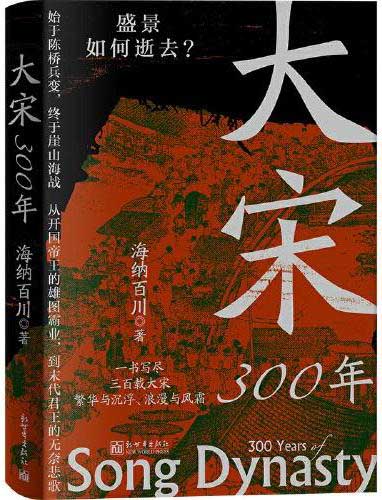
《
大宋300年(写尽三百载大宋繁华与沉浮、浪漫与风霜)
》
售價:NT$
352.0

《
害马之群:失控的群体如何助长个体的不当行为
》
售價:NT$
449.0

《
性别:女(随机图书馆01)
》
售價:NT$
352.0
|
| 編輯推薦: |
★《假面的自白》《金阁寺》作者三岛由纪夫的“文学自白”,简体中文版首引进!
★ 著名日本文化专家李长声作序,台湾作家杨照、郝誉翔联名推荐!
有论者言:三岛由纪夫是个有“魔性”的人。这魔性让三岛文学呈现出别样风景。莫言说:最后那一刀让三岛成了神。刀光耀眼,以至于后人谈及三岛,多先倒叙。
有趣的是,这位集魔性与神性于一身的三岛由纪夫,在《文章读本》里还原成了一个普通人、一位循循善诱的导师,告诉读者各种体裁下的好文体;同时又是一个率性的读者,乐此不疲地例举自己的偏爱。
一位将美学贯彻至身体每块肌肉的作家,他对文体又会有怎样的偏执和精到见解?文体之妙、文章之道,且听三岛道来。
|
| 內容簡介: |
|
文章读本,即“文章入门”之意,引导读者欣赏文学是作者的初衷。但实际写来却不止于此,作者将日本文学的特质及其形成原因条分缕析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继而例举经典范文、分类点评。日本文学、世界文学的趣味,甚至三岛由纪夫的个人趣味都在此融为一炉;小说、戏剧、翻译、评论,各种文类一一道来;川端康成的妙处,芥川龙之介的独到,东西名家逐个谈去。大文豪深入浅出,轻轻点破读者迷思,是文学爱好者的必读之书。
|
| 關於作者: |
三岛由纪夫(1925—1970)
日本小说家、剧作家、评论家。文风唯美、工于修辞,作品富于独特的审美趣味和心理意象;是日本作家中被翻译最多、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一位;在美国被誉为“日本的海明威”。后期热衷于政治运动,最终以惨烈的自戕谏世。
|
| 目錄:
|
“名作家文学课”总序
《文章读本八十年》
1本书执笔的目的
2各式各样的文章
男性文字与女性文字
散文与韵文
文章美学的历史变迁
品味文章的习惯
3小说的文章
两种范本
短篇小说的文章
长篇小说的文章
4 戏剧的文章
5 评论的文章
6 翻译的文章
7 文章技巧
人物描写——外貌
人物描写——服装
自然描写
心理描写
行动描写
文法与文章技巧
8 现实中的文章——结语
9 附录关于文章的问答
10 译后记
|
| 內容試閱:
|
● 本书执笔的目的
有所谓专供观赏之用的水果,一如佛手柑,其形可观,其芳可赏,却不能食,和一般可以下肚成为营养的实用水果不同。那么严格来说,文章是否也有纯供欣赏的作品?从前是有的,“美文”就是专供欣赏的华丽文章,比如中国的四六骈俪体1。当时写文章的技巧属于特殊的职能,如今教育普及,只要不是文盲,谁都可以写得一手文章,文章的特殊机能日渐退化,可以读到赏心悦目文章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了。
尽管如此,文章还是免不了带着几分微妙的专业性质。看起来谁都能写的普通文章,或是谁都读得懂的文章里头,其实都经过了特殊专业上的锤炼。现今即便有供人欣赏的文章,但由于外表装扮得和一般的实用文章没什么两样,使得它的意义也常隐晦不明。例如,杂志或各式各样广告上可见的标语,虽然没有高深的文学意涵,却都是在个别目的下锤炼出来的技巧结晶,绝非业余之作。
自从推行现代口语文之后,虽然一般大众的文章都改用日常生活语言,不过在部分书信当中仍旧存在“候文”的体裁,官厅及军队也仍在使用艰深的汉语。陛下的敕语本来只可心领神会,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敕语也不得不口语化。天下文章看似越来越平准化的同时,口语文也因为不同的目的与用途,存在着写作方法上和语感上的差别。先谈谈我个人的经验:当我还在大藏省3
服务的时候,曾为了撰写大藏大臣的演讲稿而吃尽苦头—我拟的一篇文采飞扬的讲稿,竟可能严重伤害大臣的威严。课长说我写得太蹩脚,让我的上司把稿子彻底修改,结果改成了一篇令我俯首称臣的杰作—它虽然是口语,却闪耀着八股文的光辉。那篇文章完全不带任何感情或个性,所有可能动人心弦的修辞都被小心地删除,变成了位高权重者对不特定多数大众发言的独特文体。
我没打算在这里就切入文体的问题,只是对先前出版过的《文章读本》一味迎合全民写作的风潮、鼓吹“能读就会写”的主张有些微词。妇女杂志上有谈论婚姻生活的文章,教导人们关于婚姻生活的规范、新婚的心得、初夜的感想等普遍的法则,但写文章并没有那样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守则。我们从小学开始学写字、习作,并学会写作文的一定格式,但要再更进一步的话,就得经过许多专门的阶段,研习专业的技术,毕竟实用文章和供人欣赏的文
章从某个阶段开始就分道扬镳了。但所谓的业余文学模糊了这种文类的疆界—一种模仿而来的品位—和无意识间流露出来的实用语气奇异地交相混杂,或许这就是业余创作的趣味所在。不过,我这本《文章读本》是从读者角度来谈,而非从创作者角度来谈,总得先把定位搞清楚,目的才会明确,也才能打破读者诸君对业余文学的迷思。
狄伯德把小说的读者分成两类:一类是“普通读者”(lecteur),另一类是“精读读者”(liseurs)。根据狄伯德的定义,“普通读者对于小说是有什么就读什么,他们不会追随‘兴趣’一词可能涵盖的任何内在或外在要素”,阅读报章连载小说的读者就属于这一类。另一方面,精读读者乃是“小说世界因他而存在的人”,他“并不把文学当成短暂的消遣,而是当成目的本身。他是小说世界的居民”。精读读者的境界必须通过同时具备美食家、狩猎高手等等其他的修养才能到达,他是所有嗜好者的最高等级,可谓“小说的生活者”—越是在小说世界中如真实世界般行走坐卧的人,就越是对小说体会深刻的读者。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期望能引导目前满足于当普通读者的人,进一步成为精读读者。请容我区区一介小说家讲句僭妄的话,我认为,作家首先必须是一个精读读者,若没有经过精读读者的阶段,就不能品味文学本身;若对文学缺乏品味,是当不成作家的。只不过,精读读者和作家之间还有“才能”这个神秘的关键。此外,由于每个人生来各有不同的性格和命运,所以有绝佳的精读读者,却当不成作家;也有充满偏见的大作家,始终拒绝成为其他作品的精读读者。评论家圣伯夫即是一例,他是位绝佳的精读读者,但他写的小说全都失败了;而日本相当出色的小说家志贺直哉,在读了司汤达的《帕尔马修道院》之后,立刻评论主角法布利斯说:“什么嘛!不过就是个不良少年!”志贺先生有种作家的洁癖,那就是对与自己素质不合的文学作品一概拒斥。这类作家下意识排斥和他们素质不合的文学,因此即便具备精读读者的条件,却不愿为之。对大部分读者来说,这种偏颇的阅读方式一点意义也没有。
直到现在,我对中学时代的作文教育仍然抱有很大的疑问。作文教育是以一般情感为出发点的,而被赞誉为好文章的则是那种平铺直叙、不加修饰的文章,或是淡淡写来却含意深刻的文章。只是,这样的文章乃是作家剔除了诸多额外的要素才能臻至的理想境地,如何要求中学生这种精力旺盛的年纪去理解?此外,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有各式各样不同种类的文章,很难界定哪一种就是最上乘。比如说,马塞尔?普鲁斯特的文章虽然清楚易懂,却不够简洁,截然不同于大部分知性又精练的法国文学作品。因此普鲁斯特的文章一开始被当成劣作,直到最近才被认定那是他所独创的新体裁。可见文章也会变化,依照作者的个性发展出最优秀的作品。这本《文章读本》并不打算独钟哪一种特定的文体,或武断地排列出文体的阶级,我只期望能尽量脱离自己的好恶和偏见,看见每种文章的趣味,对每种文章之美保持敏感,这就足够了。
●男性文字与女性文字
所谓纯粹的日文是假名,但平假名歪七扭八的外形很难让人感受到威武的男性气概。平安时代以平假名写就的文学作品,事实上也多出自女性之手,纯粹的日本古典文学即是如此由女性著述、以阴性文学为代表。这个传统绵延至今,说日本文学乃是女性的文学,可一点都不为过。
那么男性又是如何涉足文学领域的呢?平安时代把汉字称为“男性文字”,把平假名称作“女性文字”;像《和汉朗咏集》这一类汉诗诗集的作者几乎都是男性,而三十一文字或是和歌的歌集里面,虽然有不少男性作家,但女性在其中也不遑多让—何止不遑多让,还占有代表性的地位。《土佐日记》的作者在开头便写道,“男子所写的日记之谓,吾亦试作之”,这其实是作者为自己假扮女人、用女性文字写作假托的借口罢了。
想想看,当时的社会对逻辑与感性、理智与情思都有明确的男女之别,女性代表感性与情思,男性则代表逻辑与理智。这种分别本来根源于男女两性上的特质,而平安时代的文章针对两性不一样的特质,使用的语言也有殊异—逻辑与理智延伸出来的有政治和经济、社会关怀,以及一切与外在生活有关的事务;而感性与情思延伸出来的有热情、有爱恋、有嫉妒、有情爱不得报偿的苦楚、有悲伤,以及为人在世一切内在的心绪。
文学的重心通常偏向后者(感性与情思),即便以现代文学而言也是如此,可是在古时中国文化风行草偃的时代,文学并不一定侧重于后者。文学修辞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的所有面向,有些中国的古诗甚至可以在情诗的外表下抒发政治上的慨叹。如今文学几乎等同于个人生活和私人情感的反映,这是现代以后才出现的现象。文章本来具有公共机能和私人机能两个面向,例如在古希腊,悲剧同时也是仪典,俄狄浦斯王内心的起伏波澜呈现了人类命运不由自主的可怕,而且他的命运与希腊市民的生活同在神的支配下,有共通的范畴。联结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第三项要素就是宗教,以平安时代来说,这个联结可以是惠心僧都《往生要集》所代表的来世信仰,也可以是构成《源氏物语》中心思想的华严宗教义,而在古希腊则同样有对众神的信仰。虽然这里把宗教信仰在日本平安时代的力量,与西方的希腊、中世纪的宗教力量相提并论未免有轻率之嫌,然而它们在区隔公共生活与个人生活,以及同受宗教力量统率这点上是相对而等同的,并且与今日全然不同。在19
世纪浪漫派高唱情感至上以前,文章始终是带着公、私两方面的机能演进发展,这个现象同样可以在18
世纪的法国文学看到,例如,伏尔泰的文学不仅仅是政治讽刺,同时也是小说的一种典范。
然而归结到日文的特质上来看的话,会发现日本人很奇异地竟把男性特质、逻辑和理智的特质皆依附于外来思想。平安时代的汉语以及中国文学的修养,到了武家时代以后,在禅宗和儒教颓靡的风气下,陆陆续续被新的外来文化所取代。日本的男性文化几乎全假外求,另外也有不知外来文化为何物的日本男性,就像更早的《古事记》时代中的男人们,以原始的淳朴方式,单纯地凭官能过活,对感情全无概念。在男性发现感情之前,是女性先发掘了它,而后男性宁可自囚于外来文化所引进的各种概念之中。与发掘自己的感情相比,男性更愿意从理论概念中汲取乐趣。男性益加背离情感之后,便更进一步企图用各种哲学和宗教的概念去扼杀情感—儒教熏陶出的武士道有多么严厉,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
这样的影响到了明治维新以后仍然存在。当德国唯心主义的专有名词如风暴般袭卷日本知识分子的语汇后,大大小小的抽象概念旋即被德国唯心主义的用词取代。因为那时候的人认为:既然日本没有独立发展的抽象概念,就按照平安朝的老习惯拿外来语充数好了。至于日文中存在的抽象概念,始终包围着情绪的迷雾,浸润在感情的湿气里,永远没有机会获得一个概念该有的自主性、独立性和明确性。可是,这种语言的暧昧特性,却因此得以无分男女地渗进民众的话语里,造就了庶民文学诞生的基础。不过,这是后话了。
这么看来,日本文学—应该说是日本土生土长的文学—在起步之初是少有所谓抽象概念的,因此在故事构造和人物角色的精神层面上,这些抽象概念可以有效发挥作用的部分,日本文学往往忽略不提。换句话说,男性的世界,亦即男性特有的理智、理论与抽象概念的精神世界,可说长期以来受到忽视。到了军记文学的时代,虽然出现了叙事诗般的讲唱文艺以及《平家物语》、《太平记》这样的巨著,但其中所描写的男性不过是会走动的战士,或者杀人或者被人杀,或策马疾驱或冲锋陷阵,或将敌人的扇子射落等等,传达的不过是男性动态的一面而已。
另一方面,平安朝的女性作家虽然开拓了书写男性的领域,但那是从女性情感所见的男性形象。平安朝女性作家笔下的男人莫不献身爱情、一心爱着女人,他们都是女性理想的化身,只活在男欢女爱的世界里,即便像光源氏那样才气纵横的美男子,也被描写成见一个爱一个的登徒子,这和军记文学只写男性武勇的一面同样偏颇。可是,恰好是这方面的男性书写形成了日本文学最长、最深厚的传统——元禄时代(1688—1703
)的西鹤《好色一代男》也属《源氏物语》之末流,同样是描写风流成性的男人。虽然这些作品代表了与当时主流的武士道德截然不同的庶民思想,但仍轻忽了男性的精神层面—这个传统在人们的无意识之下,一直延续到明治时代以后的现代文学。举例来说,志贺直哉《暗夜行路》里的主角时任谦作,不但是个主动积极的人,同时也是个有异常官能需求的人,光凭这一点就和西方的现代小说大相径庭。从这里或许可以观察到日本作家书写男性形象的局限—这些作品里的男性完全不带任何的抽象概念,只有在主动、多情以及官能享受上才表现得“像个男人”。
我们必须时时正视日文的这一特质,因为尽管有许多作家为了摆脱这个特质做过无数尝试,但根本上只要日本人仍继续使用日文,就没有人能够脱离这个传统和这项特质的影响。不管你觉得日本文学是好是坏,都无法否认它在女性想法和情思的表达上独冠全世界。就这一点来看,日本现代文学里,继承古典文学最多特质的作品,成功的希望也最大,即便作家本人缺乏古典文学的造诣,他仍会因为所使用的语言本身,处处受掣肘却也得到古典的滋养,而终究得到上述的结果。
他越是这么想,偏生越是想念空蝉。但是现在这个轩端荻,态度毫无顾虑,年纪正值青春,倒也有可爱之处。他终于装作多情,对她私立盟誓。他说:“有道是‘洞房花烛虽然好,不及私通趣味浓’。请你相信这句话。我不得不顾虑外间谣传,不便随意行动。你家父兄等人恐怕也不容许你此种行为,那么今后定多痛苦。请你不要忘记我,静待重逢的机会吧。”说得头头是道,若有其事。
“空蝉”《源氏物语》
却说那藤壶妃子身患小恙,暂时出宫,回三条娘家休养。源氏公子看见父皇为此忧愁叹息,深感不安。但一方面又颇想乘此良机,与藤壶妃子相会。因此神思恍惚,各恋人处都无心去访。无论在宫中或在二条院私邸,总是昼间闷闷不乐,沉思梦想,夜间则催促王命妇,要她想办法。王命妇用尽千方百计,竟不顾一切地把两人拉拢了。此次幽会真同做梦一样,心情好生凄楚!藤壶妃子回想以前那桩伤心之事,觉得抱恨终天,早已誓不再犯;岂料如今又遭此厄,思想起来,好不愁闷!但此人生性温柔敦厚,腼腆多情。虽然伤心饮恨,其高贵之相终非常人可比。源氏公子想道:“此人身上何以毫无半点缺陷呢?”他觉得这一点反而令人难以忍受了。
“紫儿”《源氏物语》
逐吹潜开,不待芳菲之候。迎春乍变,将希雨露之恩。(立春日内园进花赋)
池冻东头风度解,窗梅北面雪封寒。(笃茂)
《和汉朗咏集》
●两种范本
据说要懂得吃,必须先吃过许多好菜才能知道味道;要会喝的话得先喝过上乘的好酒,而若要培养鉴赏的眼光,就要去看最好的绘画,这大概是一切嗜好的准则,不管原来的感觉灵不灵光,都能藉由品评最上乘的东西得到磨砺,养成对劣质品的判断能力。在这里,我想让各位读读两篇对比分明的文章,一篇是森鸥外《寒山拾得》的一节,另一篇是泉镜花《日本桥》的一节。
闾氏唤了女孩,命她取来一钵刚打上来的水。水来,僧人将水置于胸前,目光直视闾氏。水是清是浊并无所谓,白开水或茶亦皆无可厚非。端上来的水凑巧不是脏水,这是闾氏的侥幸。他被僧人凝视了一段时间后,心神不知不觉专注在了僧人手里捧着的水上。
森鸥外《寒山拾得》
“那是给客人尝的。”
“什么?”
“那个糖果。”
迟迟的春日底下,卖糖果的正打着呵欠,把一张嘴拉得老长。几个调皮的毛头小孩由七、八个十一、二岁的领头,在路口的糖果店前玩推挤的游戏,手里还握着红的、黄的、紫的色彩鲜艳的螺贝陀螺。在这距离日本桥不过一条街的小巷子里,撒在地上的水渍只剩下如梦一般苍白的痕迹,彩色的陀螺变成了一只又一只的蜜蜂和彩蝶,仿佛纵身就能飞起,可是一放手,却成了闷声鼓噪的苍蝇,嘈杂不已。
侧耳谛听着这些声音的,是一个在阳光底下犯忧愁的花样少女。她还年轻,正在牡丹盛开般的青春年华,却在岛田髻的几丝散发中藏着一抹暗影……衣服看样子是刚刚放宽过的。身材和体型已经丰满起来了,却还穿着黑襟的条纹单衣,身前系着的是友染的罩衫和同色的和服腰带,朱红色的系带使她看起来还像小女孩般纯真可爱。或许是打算去去就回,一双小巧的脚只穿了厨房的拖鞋、也没撑阳伞,两手拿着以红和浅黄彩绘的画糖鸟和打切糖的纸袋要送去熟识的店家。
泉镜花《日本桥》
《寒山拾得》的故事是说有个神秘的僧侣去拜访一位姓闾的地方官,自愿医治他的头痛宿疾,引述的部份是僧侣为了施术而向闾氏要水的桥段。《日本桥》摘录的则是故事开头的一段。
《寒山拾得》是短篇小说,《日本桥》则是长篇,除了这个显而易见的差别之外,这两篇文章也是对比分明的文章,任谁读了都能察觉它们是现代日本文学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对比。首先,这两篇都是上乘的文章。森鸥外的文章建立在汉文修养的基础上,简洁、干净、不假修饰。尤其令我佩服的是“水来”一句。“水来”是汉文的用法,森鸥外文章的味道就在这个地方。换做一般历史作家来写的话,在闾氏命令女孩取一钵刚打上来的水,在水端上来的时候也不会用“水来”来叙述。业余作家也不会这么写。能这样近乎冷酷地裁剪现实、舍弃一切不必要的枝节,而后在不经意处呈现绝佳效果,正是森鸥外的独到之处。在森鸥外的作品里头,极尽奢华的人可以很自然不过地把华丽的衣裳穿在身上,却让人不见奢华,仔细瞧才会发现,那些不显眼的便服若不是上等的结城绸就是久留米染,同样,若非老练的读者绝不能了解文章的滋味。“水来”一句凝聚了文章的要义,各位若是在坊间的通俗文学作品里看到上述桥段的话,那叙述可能会变成:
闾氏唤女孩去取一钵刚打上来的水。不一会,女孩胸前的红色带子就从长廊尽头浮现,带着小女孩啪搭啪搭的脚步声,将盛了水的钵小心地捧着送来了。那水或许是反射了庭园的绿光,在女孩的胸前亮晶晶地摇动着。僧侣对女孩看也不看,只是用一种令人感到不祥的眼神盯着这碗水。
以上是我写来当成劣等文章的范例。这种文章把森鸥外用“水来”一句就带过的一切,拉拉杂杂地涂上了想象的情境、人物心理、作者恣意的诠释、对读者的谄媚、性的挑拨等等。所谓的时代小说作家也常有这种通病,在描写古代的情景时往往带进现代人的感觉,因为他们受不了古代的传说故事总是那么言简意赅,于是非得用现代的感觉厚厚粉饰一番不可。原本简单扼要的中国传奇故事,经过他们添油加醋之后就失去了原来清楚的轮廓,比方说衣着好了,描写得越多反而离我们的感觉越遥远,仿佛看图听故事一样。然而森鸥外不加修饰地只用“水来”一句表达的时候,传奇故事所拥有的强劲和明朗就历历在眼前了。透过汉文直接了当的表达方式,反而令我们对这个故事所述说的世界,有了身历其境的感受。
这样的写法当然也出于森鸥外个人的气质,使得他的现代小说具有如此风味。森鸥外不能忍受任何暧昧不明的东西,他的神思若不能清楚看见这个装了水的钵仿佛就在眼前,就知道没有一看的必要了。他晓得文字不能滥用,用多余的想象污染文字,只会让作品里的物象变得模糊不清而已。有人问他写文章的秘诀,据说森鸥外的回答是:一是明晰、二是明晰、三是明晰。这是作家森鸥外对文章的一个绝对态度。斯汤达尔以《拿破仑法典》为范本,创作出难得一见的清晰的文体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其实这种清晰明快的文章才是新手最难模仿的,它的滋味尽在幽微之处;和枯燥乏味只有一线之隔,却又相去不只千万里。赫伯特?里德曾经针对霍桑的文章有过一段评论,我认为这是针对所谓“明晰的文章”,所做的相当清楚明白的定义。
“经常听人说,创作好文体的诀窍在于清晰的思考。没错,清楚的逻辑绝对可以避免许多坏文章经常落入的陷阱里,但要兼顾散文艺术的话,还需要其它的特质。例如,比思考还快的眼睛,或是对文字特性——它的音调、粗细,乃至其历史——的感官感受度也是必须的。另外还有一种特质,那代表着对整体情况拥有完全知觉的某种能力。综合了这些特质,便甚至能够在语言和文章之上完成一个更大更持久的整体。”
赫伯特?里德所说的“代表着对整体情况拥有完全知觉的某种能力”,正是森鸥外文体的秘密,也是斯汤达尔文体的秘密所在。若不具备这种知觉,就算致力写出的明晰文体,也会变得索然无味、单调沈闷。明晰的文体、逻辑清楚的文体、直接了当不假修饰的文体,这种乍看之下和水一样无味的文体里有诗,就像水里看似无物,实则在
H2O的化学方程式里蕴涵了诗的终极元素。它不是肉眼可见、光彩夺目的诗,而是压缩成元素、精炼到底的诗,因而诗才是这种文体的真正魅力,也正是赫伯特?里德所说的“整体的知觉”,它和诗人们常说的“宇宙感觉”,或许也有共通之处。
接着再读泉镜花的《日本桥》,就会发现我对森鸥外文章感佩不已的要素,在这里一个也看不到,反而和我方才所改写的差劲文章,在各个方面多所类似,于是在这之前,我对森鸥外的赞扬到这里仿佛都成了对泉镜花文章的贬抑。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泉镜花文章的美学和森鸥外完全背道而驰,这种美学推展到极致,就远远超越了我刚才改写的差劲文章。泉镜花的世界充溢着绚烂的色彩,对感官所追随的事物很诚实地追溯,他并不对任何单一的事物有明确的表达,然而他的文章整体却诱引读者进入一种纯粹而持久的愉悦。被这种文体袭卷的读者们,无法看清楚其中的每一件事物,乃是一次又一次地让缤纷的文字眩惑自己的眼睛,沈醉于一种理性的酩酊里。我称它为“理性的酩酊”,是因为小说毕竟是语言的艺术,无论如何都得透过语言、透过文字才能获得它所媒介的感觉,因此终归要仰赖理性的运作。泉镜花的文体将理性所能获致的、最大程度的陶醉给了我们。泉镜花除了自己以为美的事物以外,其余皆视而不见,因此对他来说,事物的存在与否并不具有任何意义,就算这里存在着这一个盛着水的钵,如果泉镜花觉得它又旧又脏算不上好看,他也会毫不留情地将它抹煞,只把感情和思想专注对着他认为美的事物,从不一样的路径投入先前赫伯特?里德所说的“整体的知觉”。
如果把森鸥外的文章称为太阳神阿波罗式的文章,那么泉镜花的文章就是酒神狄奥尼索斯式的文章了。从传统文学的分类来看,泉镜花的文章不属于汉文的系统,而是日本原生的文学,是江户时代的戏文、俳谐的精神(特别是松尾芭蕉之前的谈林风俳谐的精神),以及日本中世以来反复陈述的各种人生观的结合,日本文学所有的官能传统可说在泉镜花的世界里开花结果。泉镜花的文章虽是小说作品,但他追求的既非人物性格,也非事件本身,而是作者自己的一种美感告白,泉镜花的文体全系于这一点上,除却这一点便不能成就泉镜花的世界。偏偏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和差劲的文章也有几分相似。先前我改写以做为范例的坏文章,坏就坏在作家并未诚实地细察自己的感觉、想讨好读者,采用半调子的写实主义和半调子的想象力,以妥协的心态在一般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点到为止;如果他们能够像泉镜花一样,把自己的个性挥洒到极致,相信也能够成就出一种文章的典范。
上一章曾经提到普鲁斯特的文体看起来和传统的法国文学大相径庭,后来成了法国文学中重要并且具有代表性的文体之一,或许有一天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普鲁斯特的例子在这里发生。不过,泉镜花和森鸥外的情况不是这样,因为泉镜花的文体属于日本文学的传统之一,而森鸥外也承袭了另一个传统——即汉文的传统而来。我之所以在开头分别引用他们的两段文章,就是为了要点出之前提到的男性文字与女性文字的传统、论理的世界和述情的世界各自对立的情况,在现代文学的森鸥外和泉镜花当中依然历历可见。其它作家的文体就像星座一样居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这当中有各式各样的折衷,也出现各自的变种。
还有一个问题是,森鸥外的文章是短篇,而泉镜花的是长篇小说。森鸥外毕生没写过真正的大长篇,不免令人猜想,像他那样绝顶理智又明晰的人,是否很难写得出真正的巨着来,例如保罗?梵乐希就没有一连几册的巨作,森鸥外也没有。如果他脑海中的世界已经压缩成无比明确又单纯的形态,那么再虚填几张稿纸也是无益,只是在浪费文字而已。虽然还称不上是禅宗的“不立文字”,森鸥外极度节约的文体就像中国古人所说的惜字如金,实在不适合写洋洋洒洒的长篇。《涩江抽斋》算是森鸥外最长的作品之一,已经是这种简洁文体所能拓展到的篇幅极限。因为高度精炼,人生的波澜也高度浓缩在其中,使得作品就像纯度太高的精华液一样,一般读者尝起来只觉得苦;可是若将《涩江抽斋》的短短一行放进水里,醇厚的精华马上就扩散开来,成为容易入口的饮品,任谁都觉得好喝。只不过,这样稀释过的森鸥外就已经不是森鸥外了。森鸥外的文章一方面是在极度简洁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短篇小说,另一方面就像是专写小品的文体。志贺直哉的文体与此也相当类似,他真正的长篇小说只有《暗夜行路》一部,这部小说是经年累月推敲又推敲之后才写出来的。
相较之下,泉镜花的文体实在太适合写长篇小说了。它像一道流水脉脉地流,水上仿佛洒着花瓣一样,有各种鲜艳的色彩一路华丽地前行。其中,作者也和读者一样随着自己文章的水流漂流,看来还带着一点微醺的陶醉。泉镜花的故事没有核心的思想主题,也没有理智的牵绊,因此得以推展出森罗万象而绵延不断的物语世界。谷崎润一郎的文体在某个意义上也是如此,和泉镜花相较之下,他的作品更写实,他在文学传统上受平安朝文学的影响叨叨絮絮地述情,同时又善于在作品中重现庞大的现实世界,最好的例子就是他的巨着《细雪》了。
●现实中的文章——结语
我是一个小说家。我坐在桌前,就像一个将空气中的氢气与氧气化合起来,以制作出某种药品的人一样,我也在一无所见的空气中汲取某些元素,将它们固定在文章里。尽管我持续从事这项工作已经十多年了,技巧上仍然时而熟练,时而生疏,有时写来轻松愉快,有时窒碍难行。一边受到各种肉体上、精神上的状况所牵制,一边遭受各式各样的文学理论、梦境,乃至现实的多方胁迫,要求我在每一行文字里满足诸多艺术上、社会上、历史上的要求……这一切都让我的笔停滞不前。
新手作家经常提出来问我的一个问题是:你写作的速度如何?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月写一千张稿纸的作家,也有一个月写不到三十张稿纸的人;有的人可以一个晚上写足一百张稿纸,有的人写不到一张。已故的神西清先生曾经受邀写一篇不到两千字的文章,却足足花了好几年才写成。我的情况是,平均而言,每个月不超过一百张稿纸;这一百张稿纸里头,有杂文、小说,也有戏剧,下笔的速度也不一而足,从这一百张稿纸里头来算出写作的平均速度并没有多大意义。有时像疯了一样思潮汹涌,可以一个晚上写完十几张稿纸,有的时候则枯坐一个晚上,也写不出半点东西来。写得多或少并不是一个作家值得在意的事情。谷崎润一郎《盲目物语》这部总计两百数十张稿纸的小说,是作者把自己关在高野山上,以一天仅仅一、两张稿纸的进度写出来的,由此可见,谷崎表面上流畅无碍的文笔,其实是如何苦心经营的成果。
文章奇特的地方在于,匆匆写就的文章不一定紧凑,而节拍紧凑的文章往往是长时间苦心经营的结果。关键在于密度和节奏——文章写得快,密度就疏松,读者读起来也就没有紧凑感;慢慢写的话,文章当然相对压缩,读起来就有强烈的张力。
我所见过节奏最快、最紧凑的文章是谷克多的《骗子托玛》以及《一字开》,这两篇作品紧凑的节奏,即便经过了翻译仍然清楚可感。日本文学的话,之前引用过的《涩江抽斋》或许可算是快节奏的代表。
星星和白光灿灿的照明弹镂刻出这冰凉的夜晚。吉庸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孤独。最后一幕已经开始上演,这一幕带着一些童话色彩。吉庸毕竟是陷入爱河里了。
他决定不绕路,直接沿着最前线的掩体一路到达了埋坑的地方。从这里开始就得用爬的了。他和布维耶在伪装成红土色匍匐前进的操练上一向是非常杰出的。
前进几公尺后,就有一具尸体横挡住了他的去路。一个灵魂没来由的匆匆将这具肉体弃之而去。他以好奇又冷静的眼光仔细地审视了这具尸体。
当他再往前进时,又遇到了别的尸体。这一个是被折磨死的,他的领子、鞋子、领带和衬衫就像醉汉脱下的衣服一样被散置一地。
四肢上的泥泞让爬行变得困难,有时仿佛行走在天鹅绒上,有时又像保姆热烈的亲吻,把你留在原地。
吉庸时而停下、等待,然后再往前进。他在这里必须卯足了全力求生。
他无暇去思索安利耶德或是鲍尔门夫人的事,但鲍尔门夫人的身影就这么出奇不意地在他心底浮现。
壕沟的这一边已经因为水雷炸过、面目全非。仅管如此,他仍然记得四、五天前夫人在这里向他倾吐胸中悸动的情景。
——无论如何,只能说我们的运气够好。他心想。大家都以为这个防御区安稳无事,只有公爵夫人比我们更早感知到了将来的危机。夫人可说是预见了这个壕沟的毁灭。
谷克多《骗子托玛》
我从不回头对文章做修改。写出来的每一篇文章,都真实呈现我在不同年代里各种不一样的所思所感,因此,时过境迁后再加以修正是不可能的。对我来说,推敲就是在每一张稿纸里一决胜负,然后将文章合宜地誊写在稿纸上,如果密度恰当又没有暧昧不清的地方,就可以往下一张稿纸迈进。
从前只写短篇小说的时候,我对文章里即便只有一行平庸的文字都会感到极度不快,后来终于体认到,这对一个小说家来说不过是个无聊的洁癖。如何让凡庸显现出美,并且融入整体作品当中,才是小说这个大开大合的工作之要务。如果是从前的我,大概很难不揉杂了自己的感觉,简洁单纯地写出“月亮升上来,屋顶的遮阳板也明亮起来。两人走出门去散步”这样的句子,一定非得对月亮多加形容,对遮阳板的光线、独特的色调加油添醋一番才肯罢休。如今我已不再在形容词上下功夫,反而热衷为文章做裁剪,但也要小心断句过多会让文章变得难以下咽。另外,我也会注意文章看起来是否太个性化,因为太过个性化的文章会吸引读者只看表面,反而无法关注故事本身。
我还格外小心同一个用词是否每隔两、三行就重复出现,所以若是刚刚写了“生病”,下一个地方就改用“疾患”这个词。古代中国的对句也给我很深的影响,比方原本想表达“她轻蔑理智”的地方,我喜欢加上对偶写成“她看重感情、轻蔑理智”。这就像是对领带的个人偏好一样,改也改不掉。
有时我为了能简明扼要地描写行动,会在那之前铺陈冗长的心理或风景描写。文章的琢磨会因应各式各样的目的而有不同的形式,但对我来说,维持一贯的节奏乃是唯一无可妥协的坚持。节奏不一定非得是七五调,借着语词细微的调整,就可以排除掉阻碍节奏流动的小石头。当然也有蓄意撒石头、存心造成文章磕磕绊绊的手法,但我宁可试着变动小石头的位置,让水流发生有趣的变化。西田几多郎的文章里因为折衷了汉字与德语,这种融合所产生的节奏,在我听来就像久远以前的乐音,令人怀念。据说维利耶的作品会令人联想到华格纳的音乐。我虽然认同文章在视觉上的美感相当重要,但文章当中某种厚重的节奏感,往往更容易将我打动。可话说回来,华格纳式的文体显然不是我想学就能学得来的。
重读几天前写的文章,我发现自己在肉体上、精神上极端亢奋时所写的文字里,洋溢着无法重现的热情。写长篇小说的时候,最痛苦的就是心情明明已经降温,却还要接着之前热情洋溢的文字继续写下去。不过从巨观来看,人内心的节奏在无意识底下仍然持续着,因此就算文字表面上有巨大的起伏、有细腻和粗糙的分别,回头再读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全都在同一个节奏里。或许只要作品写得够长,这作品所有的节奏终究会成为自己的一部份。
有时小说才写到中途,我便回头去重读文章,然后把一些频繁出现过去式的地方改成现在式。在过去式接连出现的地方,硬生生插入几个现在式的时态,就可以轻松改变文章的节奏,这是日语的一项特权。因为除了倒置法以外,日语的动词总是出现在句子的最末尾,因此过去式接连出现的时候,就很容易一迭声全是过去式的语尾,所以需要适度地安插进几个现在式的句子。
我在写《潮骚》的时候,不时会用「……であった」做结尾,这个语尾加强了故事的氛围。不过,若是在写实的小说里过度使用,反而会让内容显得滥情。有段时间,我因为喜爱堀口大学翻译的哈狄格小说,开口闭口都炮制它悲观的语气,如今想起来十分汗颜。
我也曾和大冈升平提过,“他”的故事好写,“她”的故事则不;因为“她”这个词在日语中还未完全成熟,所以读到“她”在小说里排山倒海来的时候,往往让我皱眉头。
小说里有女性角色登场的时候,我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直称其名,尽全力避免用到“她”这个代名词。附带一提,这种用词上的好恶相当个人,在小说以外的随笔文章当中,我就非常不喜欢用「ぼく」来自称。「ぼく」这个字眼里伴随着的日常会话般不经心的感觉、以及刻意炫示年轻的意味,都会损害文章的格调。我不认为「ぼく」是一个适合在公众面前使用的词汇,它只适合在日常会话里流通。
我们对词语的感觉自然也会因为文章的属性不同而有变化。例如,我不喜欢在小说里提到电影明星的名字——今日红极一时的玛丽莲梦露在十年之后还会有谁记得呢?即便我的文章过了年就不值一文,但创作的时候,若不想着十年留芳的愿景,如何还有书写的乐趣呢?假如我在文章里写,“像玛丽莲梦露那样的女人”,恐怕十年之后已经没有人清楚“玛丽莲梦露”这个女人所代表的意涵,也没人看得懂这句话的意思了。不过,这个洁癖只能在小说或戏剧创作里贯彻,要是在随笔、手记等等杂文当中都不准提到电影明星的名字,恐怕是强人所难。
我是一个小说家,对于评论、随笔这些小说以外的文类难免就比较随便,荤素不忌,有时甚至刻意调笑,不像写小说时那样坚持自己的好恶与洁癖;但同时我也要求自己必须逻辑清楚,然后用一些流俗、不正经的表达方式来缓和文章当中讲的道理。
我虽然是以这样的坚持在创作,仍然会对自己过去的作品感到不甚满意,明年再看现在这篇文章的时候,大概也不会觉得满意吧。要说这是不断在进步的证明,也未免太过乐天,有些看不清自己的人往往就在不满意中停滞,甚至退步。对文章的喜好会不断在改变,但没人能保证,改变一定会从坏的喜好转变成良性的喜好。既然要创作,写出自己现在觉得最好的文章才是最重要的。
或许有人会说,这是一种中产阶级的脾性,但我仍然主张格调与气质才是文章的至高目标。我尊敬有格调、有气质的文章,即使它的立场与我相左。我在看当代作家的时候,同样是依着自己顽固的好恶,做出与一般评价截然两样的看法。在日语的内容逐渐增多、模样也日益驳杂的今天,在流氓的语言和绅士的语言可以混淆不清,而娼妇的语言和闺秀的语言也已经无所区隔的时代里,要求文章要有格调、气质或许已经不合时宜,然而我相信,持续谈论“格调、气质”这些很难一语道尽的理想,或许有一天会像在黑暗中逐渐清晰的眼睛,给后世的人们看见光亮。
说得具体一些,文章的格调和气质完全由古典的造诣而生。古典的美与素朴无论在任何时代都能打动人心,就算是包罗万象、人事纷杂的现代文章,要能不受当今的怪象扭曲,都必须在某些方面依赖古典以克服乱象。如果文章的最终理想是藉由文体来抓住浮表的现象,那么气质和格调毕竟仍是文章最终极的理想。
●情欲的描写可以深入到什么地步?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对情欲写实的描绘曾引起轩然大波,最后吃上官司成了禁书。其实劳伦斯这本书不是为了性行为而写,他不过是把性的描写当做一种思想传达的手段。随手翻翻同人志的话,一定可以看到更多既猥亵又别脚的性交桥段。河上彻太郎说,性行为和运动是一样的,一回生、两回熟,熟练之后就能找出乐趣;性和运动的这种共同特性不太可能在文章当中传达出来,不过这段话真是至理名言,世上并不存在描写“性行为”的好文章。这和我在谈行动描写时说的是一样的原理。
先代梅幸走进舞台上的一个隔间,和男人睡了一觉再走出来的时候,腰带的系法变了,这是性行为的艺术性暗示。具体的性交描写只会让人觉得猥亵,我们从文学当中得到的色情感受,基本上经过大脑和理智,属于本质性和抽象性的感受;我们并不是从文章当中得到直接的色情,而是观念上的性刺激,是一种自己的主体并不参与其中,只在官能上得到刺激的状态,依据沙特的定义,躲在洞眼后头偷窥他人性行为的癖好就是猥亵。文章描写得越抽象就越接近猥亵,拉克罗写的抽象小说《危险关系》,恰恰证明了这则真理。
因此,法律和民众如果稍微聪明一点的话,就应该在处罚《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之前,先办了《危险关系》才对。只不过,后者的猥亵是需要高度知性做媒介的猥亵,不具普遍性而已。
●幽默和讽刺的分别在哪里?
学术上对此有各式各样的定义,简单来说,幽默无毒、讽刺有毒,所以幽默有分高级幽默和低级幽默,却都不伤人。讽刺也有大众形式的讽刺——例如江户时代的落首、现今的漫画等——以及伏尔泰《憨第德》那种高水平的讽刺小说。讽刺小说的杰作大多出于十八世纪,例如孟德斯鸠《一个波斯人的信》,就是以一个初来乍到巴黎的波斯人为主角,从他的观点写成的小说,利用一个外国人新鲜而无预设立场的眼光,来讽刺巴黎种种滑稽的风俗。
粗略来说,讽刺抓住的是,在毫无成见或定见之下关注事物时所看到的畸形,它本来就不为特定的政治或党派服务;讽刺揭开了我们往往从表面或照习惯理解的事物面纱,它是暴露事物本质的一种评论形式,只不过它揭开面纱的方式,和一般的评论比较起来乱无章法,结果让人不禁因为它的怪异而发笑。《格列佛游记》就是一部了不起的讽刺小说,它让我们看见讽刺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一个和我们日常生活截然不同的世界,进而从那个世界来反观我们的愚昧,又比如包括伊索在内的许多讽刺作家,就常常借用动物、侏儒、怪物、巨人等等非人类的眼光,甚至波斯人等等外族人的眼光来叙述。
相反的,幽默则是人类生活中的润滑剂。它使人类因紧张不自在而绷紧的神经得到松弛,鼓舞人以轻松愉快的心情面对生活中的种种作为,所以英国人即便是在激烈厮杀的战场上,也要发挥幽默精神。幽默、沉着、男子气概就像同一辆车的车轮长相左右,它是理性最温和的型态。由此看来,虽然德国人素称是阳刚尚武的民族,可是就缺乏幽默感这一点来说,不免少了一项男性的重要特质。
●好的比喻应该是什么样子?
恰当的比喻能够使小说免于过度的抽象乏味,令读者耳目一新,并在一瞬间掌握到事物的本质。另一方面,比喻的缺点是将小说好不容易结晶起来的统一单纯的世界,分化成各种不同想象的领域,所以比喻使用过度就会显得轻佻浮薄,有让坚实的小说世界像烟火一样炸开的危险。这里就从谷克多的小说里选出几个好得不得了的比喻,让各位看看:
到底是什么神秘的法则,能够令纪优、梵利舒和波蒙公爵夫人这样的人像水银一样结合在一起。
人们看着坏疽逐步地侵蚀他,彷佛藤蔓包围着一尊石像,只能眼睁睁地见死不救。
人们就在我军如特快车般轰行的枪林弹雨下,在德军那彷佛优美的署名之后一点黑色墨迹般的炮弹交错中,照样地生活作息。
他继续往前走,又看到了别的尸体。这一次是被虐杀的。领子、鞋子、领带和衬衫就像是醉汉边走边脱似地散了一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