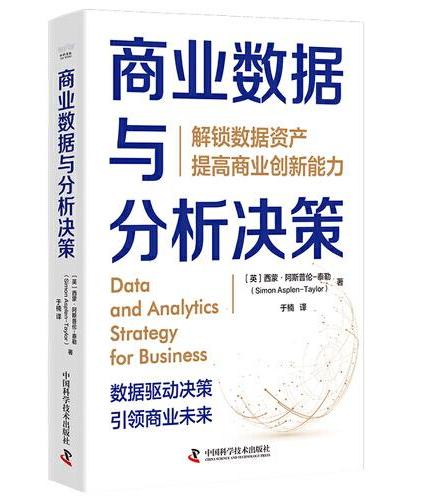新書推薦:

《
肌骨复健实践指南:运动损伤与慢性疼痛
》
售價:NT$
1367.0

《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MySQL版)
》
售價:NT$
3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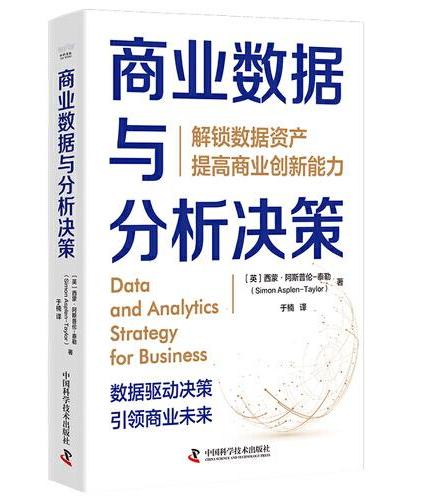
《
商业数据与分析决策:解锁数据资产,提高商业创新能力
》
售價:NT$
367.0

《
倾盖如故:人物研究视角下的近世东亚海域史
》
售價:NT$
357.0

《
史学视角下的跨文化研究(一): 追踪谱系、轨迹与多样性
》
售價:NT$
485.0

《
历史文本的文化间交织:中国上古历史及其欧洲书写(论衡系列)
》
售價:NT$
551.0

《
1688:第一次现代革命(革命不是新制度推翻旧制度,而是两条现代化道路的殊死斗争!屡获大奖,了解光荣革命可以只看这一本)
》
售價:NT$
1010.0

《
东方小熊日本幼儿园思维训练 听力专注力(4册)
》
售價:NT$
408.0
|
| 內容簡介: |
“黑白阎连科”囊括了阎连科的“黑与白”——神实与真实,荒诞与感动,狂欢与纯情,先锋与质朴……第一辑“中篇四书”,精选阎连科“最经典、最钟情”的十二个中篇,每本三篇,让读者以最短的时间,读最好的阎连科。
中篇四书为:《 年月日 朝着东南走 横活》《耙耧天歌 大校 乡村死亡报告》《天宫图 平平淡淡 瑶沟的日头》《黄金洞 寻找土地 中士还乡》。其中,《黄金洞》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年月日》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八届《小说月报》百花奖、第四届上海优秀小说大奖;被法国教育中心推荐为法国中学生课外读物;《耙耧天歌》获第五届上海优秀小说大奖;《大校》获第八届解放军文艺奖;《朝着东南走》获1999年《人民文学》优秀作品奖;《瑶沟的日头》获阎连科颁给自己的“最钟情奖”。
|
| 關於作者: |
|
阎连科,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1978年应征入伍,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79年开始写作,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风雅颂》《炸裂志》,中篇小说《年月日》《黄金洞》《耙耧天歌》《朝着东南走》,短篇小说《黑猪毛 白猪毛》,散文《我与父辈》《北京,最后的纪念》等作品。先后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其他国内外文学奖项二十余次。入围2013年度英国曼布克奖短名单,并获得第十二届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作品被译为日、韩、越、法、英、德、意、荷、挪威、以色列、西班牙、塞尔维亚等二十多种语言,在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现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为教授、驻校作家。
|
| 目錄:
|
目录:
耙耧天歌
大校
乡村死亡报告
黑白阎连科(总序)
|
| 內容試閱:
|
《耙耧天歌》节选
一
一世界都是秋天的香色。
熟秋的季节,说来就来了。山脉上玉蜀黍的甜味,黏稠得推搡不开。房檐上、草尖上,还有做田人的毛发上,无处不挂的秋黄,成滴儿欲坠欲落,闪着玛瑙样的光泽,把一个村落都给照亮了。
一个山脉都给照亮了。
整个世界都给照亮了。
旺收呢。这样的年景,先是浅旱,后是深涝,到了玉蜀黍授粉的关口,该雨是雨,该日是日,结果平地川地,收成一般,山地梁地,却旺收得罕见。玉蜀黍穗人腿似的,秆儿都被压得驼了,一些还骨折,卧伏在了地上撑着生长。那被叫做尤四呆子村的尤家村落,原本都是些坡地,其旺收的景况是不消说的。白露和秋分之间,便有人开始收获玉蜀黍。尤四婆家的地全在梁上。全在离村最远的梁上。去年调整地块时节,村人各户都嫌那地遥远,村长说尤四婆子,你家三傻四傻肯吃,那地你家种吧,想种几亩都行。尤四婆便领着她的傻妞呆儿种了。种了一道山梁,也许八亩,也许十亩,哪料它今年就旺收得山山海海哩。
尤四婆已经领着她的傻妞呆儿来这收了三天,运了三天,一道梁才收获了三成有一。人是累了,也被旺收弄得烦了。无边无际的玉蜀黍地里,绿秆枯叶棚着,人钻进去同入了海样。尤四婆把掰到竹篮里的玉蜀黍往田头运着。运着的当儿,她就听到身后三妞儿青灰灰的尖叫:“娘——娘——你管不管你们四傻子,他追着撵着摸我的奶哩,把我的奶咪咪都捏得疼哩。”田头已经码起了一条堤似的玉蜀黍棒子。天高远得很。云淡远得很。玉蜀黍那紫色缨丝脆碎成粉末腾起来,在梁道的日光下荡来荡去。尤四婆循着唤声回过身去,果然见四呆在三妞身后追着,把三妞的前衣襟儿扯开了,她那胀鼓的双奶兔头样白亮亮地欢蹦乱跳,仿佛立刻会跳跃下来。尤四婆愣住了,她看见三妞被四傻抓了奶子,脸上没有羞耻,没有苦相,倒是有一层浅红色的快活年画一样贴着。而在三妞身后呆立着的四傻,一边嘿嘿地笑着,含了口水,又含了两眼对娘惧怕的泪。尤四婆不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她想问个清醒明白,可又觉得这双儿女是一对透呆,不知该从哪儿破题问起。就在这犹豫的当儿,她的眼前一晃,男人尤石头立在了田头上。他说是四呆先动手去扯三妞的扣儿哩,我在边上看得清白呢。尤四婆把目光从男人身上收回来,望着四呆说:“四娃,你过来,娘给你说个事儿。”四呆娃便迟迟疑疑过来了。尤四婆手起手落,一个耳光打在了四呆的脸上。
四傻捂着脸呜呜哦哦地哭将起来。
尤四婆子吼:“不知道三妞是你的亲姐啊!”
四傻朝着玉蜀黍地的深处走去了,就像一条被打了的狗躲到草丛深处呆着样,盘坐在玉蜀黍的棵秆上,盯着天空哭起来,弄得一面坡地都是四傻青痴痴的哭唤声。
以为一切也就过去了,风息浪止了,该接着紧收旺秋了。尤四婆把地上那篮玉蜀黍穗倒出去,对她的男人说,你走你的吧,忙得昏天黑地,以后你就不要隔三错五地回来了。然后,她旋过身子,看见三妞依然在那儿死死盯着她,像饿了要吃那样满脸可怜相。
她说:“把你兄弟打了,你还想咋样呢?”
三妞说:“娘,我想有个男人哩,想像大姐二姐那样有个男人搂着睡觉哩。”
尤四婆轰隆一下愣住了。
她男人也轰隆一下愣住了。
站在玉蜀黍穗堆旁,看着比她高出一头、宽出半肩,胸脯如山样隆着的痴三妞儿,她猛然灵醒三妞已经二十八岁了。想到三妞二十八岁时她把自己吓了一跳。她二十八岁那年,早已经生完了四个孩娃。就是在她二十八岁那一年,四呆儿岁半时候,她男人朝着那边走去了,丢掉这活生生的日子不要了。那一天他们抱着四呆去了镇上卫生院,是卫生院的大夫把他们尤家日子中的最后一滴灯光吹熄了。她十七岁时是哼着戏文嫁到尤家的,十八岁开怀生育,平均年半给这世上送来一个妞儿,生完第一个妞儿时,她还在月子床上享受着男人的侍奉,哼唱了一个月,可没想到的是,她生的大妞、二妞、三妞竟都是痴呆,都是在长至半岁当儿,目光生硬,眼里白多黑少,到三岁四岁才能开口叫娘,五岁六岁,还抓地上的猪屎马尿,十几岁还尿床尿裤。因为一连三胎傻痴,吓得她和男人不敢生了,连一句戏文也不再哼唱了。然歇了几年身子之后,想要个男娃,怀着撞命的心情,又彼此劳累身骨,再一次却果真生了男娃,且半岁之后,孩娃就能咿呀说话,八九个月,就能满地跑了。以为终归算生了一个精灵,有时也哄着孩娃念唱几句戏台上的话,哪知孩娃岁半时候,淋雨发烧,本是家常病症,可烧了一夜,来日做爹娘的细心一看,孩娃嘴歪眼斜,话又不会说了,饭碗也不会端了,除了呵呵地傻笑和嘿嘿哦哦地呆看,其余一无所知。
全村人都为这一变故惊着。尤四婆和男人尤石头的脸上、身上、屋里、院落,到处都惊硬满了苍白和漆黑。
村人们说快到镇上卫生院瞧瞧吧。
便就去了。
大夫问:“他兄弟几个?”
尤四婆说:“姐弟四个。”
大夫问:“他姐们好吧?”
尤四婆说:“姐们心里……有些不够数哩。”
大夫微微怔着,盯着尤四婆看够了年月,说你家祖上有没有这病?尤四婆说没哩,我爹我娘都是全人。大夫说,你爷你奶呢?尤四婆说,也是全人。大夫说,你祖爷祖奶呢?尤四婆说我没见过他们,可我爹说我祖爷活到八十二岁还能在村里耍狮子跳龙头,我祖奶七十九岁时还能大大段段地唱戏文。大夫不再对尤四婆询问啥儿,他把目光辗转到尤石头的脸上去。
大夫说,你呢?
尤石头默死着不语。
尤四婆扛了一肩男人,说问你哩。
他才吞吞吐吐说,我爹有过羊角风,我三岁那年爹正在梁上犁地,病一犯扶着犁就栽进沟里死了哩。
尤四婆的目光直硬了。
大夫便出了一口长气儿,释然地说你们回家吧,这病请了华佗也没法救治了,是隔代遗传哩,你们生四个孩娃四个是痴呆,生八个八个是痴呆,生一百有两个五十都是痴呆儿。回去好好思谋思谋你们如何陪着这四个痴呆过一辈子吧。
不消说啥他们便走了。回耙耧山脉深处的尤家村落了。一路上,他都背着四娃儿跟在她身后,刚出镇子时彼此还有一搭儿没一搭儿地说些啥,然到日将西去,日头酷烈时,他们就彼此不言不语了。累了哩。连孩娃都在他肩上流着口水睡了呢。可至村岭下边的十三里河边时,他立下看看那河水,又扭头看看肩上的傻孩娃,没想到那孩娃在梦里似哭似笑地朝他咧咧嘴,然后突然一阵哆嗦,眼就泛白了。这景况正让他吃惊,孩娃的异样却又风吹云散了,对他哭半声笑半声睡着了。
他立在河边无休无止地盯着傻痴孩娃的脸。
走远的媳妇回过身子唤:“走啊——快走啊——天要把人热死哩。”
他说:“你先抱着孩娃到前边树荫儿里歇一会,我喝口水立马就赶上来。”
她接过孩娃到一棵楝树下边等去了。
她等得月深年久、天昏地暗也没见男人走上来。她沿着河岸边走边唤:“妞她爹——娃他爹——你死哪去哩?——你死哪去了娃他爹!”沿河走了数百步,她在一个水潭边上看见了那让她生了四胎痴呆的尤石头,跳河死后漂在潭边如一大段枯腐的树身儿。她迅疾地跑到潭边把他拖上岸,把手放在他的鼻前试了试,愣一会儿,马一样往村落里边奔去报丧了。
男人就死了。被未来的日子吓死了。
男人死了,日子中的光亮便呼地暗下来。农忙时没有了扛锨拿镰的人,农闲时没有了聊天解闷的人。就是冬天水缸冻裂了口,想用铁丝捆上,都要尤四婆子自己动手了。
那年麦天,她把四个傻痴像四只狗样拴在麦地头的树下,在他们面前放了蚂蚱、麻雀和圆石、瓦片供他们耍着,自己在田里割麦。从日出割到日正顶上,回到树下歇时,看见四个孩娃把那蚂蚱和麻雀用石头在瓦片上铿铿锵锵砸了,砸得麻雀脑浆迸溅,鲜血淋淋,蚂蚱头像蒜汁样摊在瓦片上。四个孩娃在分吃着麻雀的腿、翅、肚子和头哩,一个个的嘴上、脸上都红红海海一片,弄得一世界都是麻雀青红的生血气息呢。
尤四婆先是惊着,呆呆地立在那儿不动,后来就冷丁儿号啕起来,哭得死去活来,面对着埋了男人的那方梁地,边哭边骂道:“尤石头,你这该千刀万剐的享福去了,把我和孩娃们留在这个世上受苦受难哟。”
又骂:“你这狗人还算男人吗,你坑我害我,还坑害这四个孩娃儿。”
还骂:“你以为死了就好啦,死了你能安生享受啦,给你说,孩娃们一日不成家立业,我一日就不让你这狗人安宁哩。”
她说:“姓尤的,你给我滚过来,你躲离开这世界到哪儿去了哩。”
她说:“你出来给我跪下哟姓尤的,跪下看看你的四个孩娃儿。再看看我一晌儿独自割了多大一片麦。”
尤四婆骂着说着时候,声音就由大到小变得嘶哑了,脸色也由青怒转成了灰白色,慢慢地哑无声息,盯着眼前的一片空地不动了。那空地在麦田和梁道的正中间,有草席样一片,生了许多黄色礓石和茅草。茅草从礓石缝中扎出来,把礓石盖在草丛下。她男人尤石头果真就跪在那片空地上,把茅草压倒了一片儿。日光把他的影儿晒得和蝉翼一样薄,且是一种灰白色,在青茅草和黄礓石上晃动着。远处收割的村人,都已回村吃过午饭,磨了镰刀,重又从村里出来,朝自家麦田摇过去。有的正在田里把割过的小麦摊开来,请那日头晒干。她男人跪在那儿,先还抬头看她一眼,最后就深深地把头勾埋下去了。
他说:“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是你哩。”
他说:“留下你在世上吃不完的苦,受不完的累。”
他说:“你再难也要把孩娃们养大成人哩,他们成家立业了,你就有好日子过了哩。”
说到孩娃,尤四婆回身望了一眼,看见那四个傻痴仍在吃着生雀蚂蚱,慢慢地她脸上那伤鳞鳞的白色淡去了,刚才失了的青色重又走回来。她冷丁儿从地上抓起镰刀,朝前扑了几步,挥着镰把疯了样朝男人尤石头的身上打起来。头上、脸上、胳膊上,镰把落到哪儿是哪儿。一个山坡都响满了青白色的抽打声。从这面山坡又响到那面山坡去。日光被她挥着的镰刀割得零零碎碎。细长的凉风也被打得一截一截,变得热烫起来了。
又一年,割完了麦,却是种不上秋。有的人家种上的秋庄稼都已露了苗,可她的麦地却还一块块白在天底下。各家的耕牛都忙得昼夜不消停,尤四婆只好借着月色,用锨在麦茬地里翻挖着。她在田头上铺了一领席,让四个傻娃在那席上睡着觉,自己脱了上衣,从田的这头翻到那头,又从那头翻回来。新翻的土地里有一股清新潮润的泥土味。泥土味是一种深红色。旺茂的麦茬白亮亮在月光里,散发着温热腻人的白色的香,那两种红白味道,如烟如雾样在夜里流淌着,还有她翻地的吱喳声,孩娃们睡着后的鼻息声,都在水样的月色里漫浸浸地流。尤四婆翻地翻到累极时,刚坐在凉爽的新土里歇下来,这当儿就从梁上走来了一个人,是邻村别姓的中年汉,他过来把锨插在田头上,望了赤裸着上身的尤四婆子说:
“还没翻完呀?”
尤四婆忙去地边穿她的布衫子。
男人笑了笑,说:“别穿了,我啥儿没见过?”
尤四婆就又坐到了原地上,脸和奶子都对着那男人。
男人说:“要我帮忙翻地吗?”
尤四婆子说:“你翻吧。”
男人说:“啥报偿?”
尤四婆子说:“你要啥报偿?”
男人说:“我把这地翻得比牛犁得还好,坷垃打得和磨面一样碎,可你得就这么赤裸着坐在田头上,让我扭头、抬头都能看见你的上半身。”
尤四婆说:“你翻吧。”
男人说:“地翻完了,我再给你种上秋,没别的啥要求,就是今夜咱俩在这梁上睡一夜。”
尤四婆说:“别动嘴,你赶快翻地吧。”
男人就弯腰翻地了。男人翻地果然比女人好许多,快许多。铁锨往地上用力一扎,前后推一下锨把,弯下腰,卖力一翻,一股生土的香味就漫卷在了田地上,这时候男人就抬起头,望一眼裸了半身的尤四婆子,说:“你自个不知道你自个的奶子好看吧?”然后又翻地,又抬头,说:“我留心看了,几个村的女人就数你的奶子好,奶过四个孩娃,还直挺挺地立着哪。”再翻地,再抬头,说:“天凉了你可以把布衫披身上,可扣子不能扣。”尤四婆就把布衫披在身上,又把四个孩娃用单子盖了盖,重又回到原来坐过的席角上,端端地露着胸脯和双奶,端端地对着那男人。男人一边倒退着脚步翻着地,一边不时地抬头望那挺立的奶,为了看得方便,他把地翻到头时,不是转身从那头翻回来,而是从那头走回来,重从这头退着看着翻回去。且每看一眼,都要对尤四婆说一句花好月圆的话。尤四婆不接那男人一句话,就那么裸着身子裸着奶,把胳膊交在一块放在双膝上,或者把胳膊放在两侧旁,任那男人远远近近、细细微微地看。山脉静得如卧下睡了的一片牛。尤四婆的男人尤石头就坐在尤四婆的身后边。
|
|